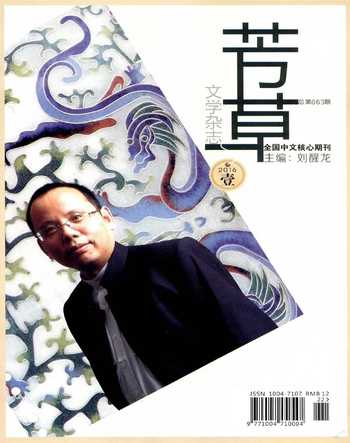路内:以小说的方式掀开历史
杨晓帆:今年《收获》第三期发表了您的新作《慈悲》,我觉得跟您之前的创作比有变化。首先是语调变得更平实了,没有之前那么多反讽、特贫的轻喜剧因素。跟《花街往事》相比,我觉得您还有意隐去了小说中特定的历史痕迹,把小说重心放到人物身上。与路小路那种自觉意识特别强的人物不同,《慈悲》里水生、根生、玉生们,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个人态度,甚至有点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但这种特别自然的生存状态,反而显出小人物的尊严感。您能谈谈《慈悲》的创作缘起吗?
路 内:《慈悲》的题材其实来得很偶然。去年一直在弄电影的事,老跑片场,我就想写一个关于电影演员的小说。等电影拍完,我父亲跟我聊起来,他七十多岁了,跟我讲他当年怎么在厂里帮人要补助。我说你不就是当年在工厂里教人跳舞,教人学坏的呗,怎么还帮人要补助呢?我父亲说一九六O年闹饥荒的时候,国营工厂真给钱,工人虽然营养不良,但也都活下来了,结果到了八十年代,贫富差距拉开,很多工人家里还在睡稻草席,生活很潦倒,所以要补助就成了很重要的事。那时候说是按定额给每个车间分配两个补助名额,但事实上是比谁口才好,如果哪个车间口才不好,你去要,工会也不给你。结果全车间就推选了我父亲,靠他软磨硬泡地帮别人把补助拿下来。以前哪家拿补助,是被别人看不起的,我们家没拿过,但很多人要生活,就得拿。
虽然题材来得偶然,但《慈悲》的写法是我一直想要的。当年写《花街往事》时,我遇到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要写一个长达二十八年的故事,里面的人物、视角不断转换,整个小说很难一把打通。所以有人就觉得我分成七八个短篇的方法是有问题的,说我不会写长篇。尽管这样写也有先例,比如福克纳的《去吧,摩西》。去年我遇到山西大学的王春林老师,他说你不要再写工厂了。我说为啥,读者爱看,你也让我卖点钱。后来我想,他到底是说你不要再写这种题材了,还是说不要再用这种语言方式去硬侃。就像我在写《天使坠落在哪里》时,完全用第一人称,稍微有点故事、结构,就能用非常纯熟的小说语言硬侃下来,但我知道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这属于一种欺负人的做法。所以我就琢磨,王老师到底是说你不要再写工厂,还是说你不要再欺负这门手艺。我觉得一个作家在一个题材上不断挖掘下去,并不是一件错误的事,关键还是看表达方式的调整。
杨晓帆:可能因为您以《少年巴比伦》出道,很快被贴上“工厂题材”、“成长小说”的标签,这样一归类,反倒把题材和表达方式磨合的丰富性给一笔勾销啦。
路 内:尤其我写完“追随三部曲”以后,七八十万字,特别容易被读者和评论界简单归类。不仅归类你的题材,还归类你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方式。我承认很多作家始终用同一个风格写作,我觉得没问题。但对于我来讲,还年轻,应该还是有能力把写作方式拓展一些的。比如很遗憾,《慈悲》是我的第六个长篇小说了,才是我第一次真正开始全部用第三人称视角来写作。像《花街往事》里虽然部分使用第三人称,但很奇特,写“我”的时候,可能恰恰是第三人称,写第三人称时,反而更像是一个主视角。《慈悲》我不想写太长,如果写长了容易碰到几个问题:一是这样一种语言如果用来写二三十万字的小说,故事容易散掉,十万字差不多;另外,这篇小说跨度五十年,很多细节不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我也可以去采访很多当事人,调查当时的房子怎么样,但这么写没有意义,因为这个工作在《花街往事》时我已经做过了,把当时很多重要的历史细节像电影一样再现出来。所以你看《慈悲》这个小说和《云中人》有一点很像,几乎不写人物的外貌,除了女儿还写了点儿,其他主角的外貌都是很虚的,如果这都不写,我也就没必要去呈现七十年代以来特别具体的历史细节了。那样写会让小说变得很重,不知道讲什么,我愿意这篇小说更偏向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又遭遇另一个问题,我们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特别容易偏向内心,但一写工人农民就没有内心了。
杨晓帆:说得好!今天我们经常讨论“底层文学”的概念。有的底层写作虽然有眼光向下的悲悯,但作者跟底层之间有隔膜,端着“五四”启蒙文学中那套“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往往注意不到底层也有他们的自尊,他们的生活态度。
路 内:我觉得这些人很有尊严啊,只是他们寻求尊严的方式可能跟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求神拜佛,包括《慈悲》结尾的老太太,她愿意经过庙时把身上所有的零钱都捐出来,她觉得自己获得了救赎,非常幸福。小说主人公说这是假庙,你不能获得救赎。但事实上真庙假庙这已经不是佛教的观念了,而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观念。佛教有时候是承认假庙可以让人获得救赎的。
杨晓帆:《慈悲》里有一种“业报”的因果联系,比如师傅的遗训和水生、玉生夫妇后来的生活,水生从土根家领养来的孩子,根生和汪兴妹的情、和宿小东的怨,叙事上的一些小重复和前后呼应,写出了小人物的人生。我很喜欢结尾,既是“渡”,从一个城到一个厂,到一条河,也是“度”,是灵魂从此岸到彼岸。您在创作时是怎么考虑这一情节设置的?结尾由皈依佛门的弟弟说出人生虚妄、放下欲念,是不是对主题的指涉性太强?
路内:如果由弟弟下了这个结论,那这篇小说就太庸俗了。事实上他们没有达成共识。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要求写了一个跋,谈到了这个问题,人何以战胜历史呢,或者再往深了谈一点,文学何以战胜历史呢。如果我写完这么一篇小说,就声称自己书写了五十年的历史,站在了某个神级视角,那就太傻了。我不需要那样的“宏大叙事”,也不需要利用小说来建立一个精神制高点。这个观念,一部分地也影响了这个小说的表现形式,但我希望这种影响是合理的,是符合写作逻辑的。这个小说里呈现出来的“慈悲”其实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它是非理性的。我并不是说中国的普通民众怀有这样一个东西就能活。小说结尾那个公司靠一座庙来做房地产,多么荒诞,你报复不了它。《慈悲》的结尾带有一点寓言性质。
杨晓帆:我们来聊聊您的成名作《少年巴比伦》吧。我记得在一个创作谈里读到,您当初准备把《少年巴比伦》投稿给《萌芽》杂志,是《萌芽》的编辑赵长天老师建议您发《收获》,让您在青年作家中有了一个特别高的起点。我觉得这则小插曲本身,也说明《少年巴比伦》要远远溢出一般青春文学、成长小说的概念。
路 内:我三十岁以后那几年过得特别无聊,觉得自己年轻时还发表过小说(发表在《萌芽》),但是一无所获,此后就想谋生糊口,一直混到了三十三岁。那一年我母亲很突然地去世了,我特别沮丧,真觉得这半辈子白活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也就是这样,想把自己白活了的经历,浪费了的时间写一写,也不单是写自己,还有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用一种虚构的方式。小说有一点自传性质,但那完全不是我,我好像没有主人公的那种粗俗和无所谓,如果有的话反而好了。
这个小说呈现的是一种回溯式的伤感,里面有很多挽歌,其实不是青春型的。后来被定义成了青春型,也有一些青年读者爱看,其实我很惭愧,谈多了觉得自己确实是“自发式”的写作,没有受过系统文学教育的写法。小说最初是投稿给《收获》的,但是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结果。我就去问赵长天老师,能不能帮看一下。我也是没在文学圈待过,不懂规矩,这是一稿二投。或者说我其实根本没有信心能在《收获》发表,但《萌芽》我是发表过的呀。后来长天老师真看了这小说,让我继续等《收获》回音。他是内行,他懂得这里面的出入,我当时蒙头蒙脑什么都不知道。这两份杂志我都很感念,还有《人民文学》杂志,都是帮助过我的。如果没有文学期刊,我大概也就随便写写,就算了。另外我觉得自己头脑还是清醒的,也越来越谨慎,因为我想知道终点到底在哪里。
杨晓帆:从二OO七年发表《少年巴比伦》,到去年以《天使坠落在哪里》终篇完成“追随三部曲”,今天再看“路小路系列”,您会怎么总结它对您整个写作道路的意义?
路内:第一、第二部我是顺着写的,第三部大概等了七年,我自己跨过了一个状态。第三部《天使坠落在哪里》是用一种比《少年巴比伦》更强烈、更无所谓、原始的笔法写出来的。虽然写完第二部《追随她的旅程》后,我就有了三部曲的想法,但我没有顺着把三部曲写完,而是在中间隔了两个长篇《花街往事》和《云中人》,这里面很多状态其实是对评论界的一个反弹。
我写完第二部以后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对之前一部的推翻。《追随她的旅程》很随意,有种甜腻的忧伤,对于一个酷酷的、卖帅的小说家来说,这样写不是很合适。别人会说,你就是想让大家哭一通,打动下少女心吗?所以我的下一部小说是《云中人》,整个风格颠倒过来,写得很黑暗,我自己写完后都一度精神状态不太好。接着就写了《花街往事》,跟《云中人》又有非常大的差异。写完《花街往事》后,我折回头来写三部曲,我知道这个故事不怎么样,但我一定能用自己的语言硬侃下来。《花街往事》写得很诗意、很讲究细节,可是过于温和了,所以我要写一个随意的东西。但写完《天使坠落在哪里》以后,我又反省自己,我是不是因为语言好,就故意欺负这门手艺,所以我想要写个简洁的东西出来,于是就有了《慈悲》,退回到我没操作过的第三人称叙事。就这样,我的每一个长篇可能都对下一个长篇造成了一个反向的推力。这个推力有时候让我失控,我也尝试过克制自己,但或许是出于厌倦感,或许是因为写长篇小说的心理机制不同,它会在不同的作品之间产生很明确的风格分界线,这种反向补偿也算是进取的尝试,也有可能是作家自我认知的不稳定造成的坏结果。
杨晓帆:路小路的形象是一个无目的的漫游者。他的起点很明确,在戴城,一个工厂青工或待业青年,他有种无所事事的不屑,却也有在路上寻找的冲动,但我感觉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他跟他的时代之间是陌生的。三部曲的一个叙事动力就是“逃亡”。
路 内:对,路小路没有什么目的性。他什么都讨厌。你看第一部结尾,这个城市非常王八蛋,就靠出卖它两干五百年的历史掌故活着。等到第三部,都成了工业园区了,忽然我们家边上成了联合国,也不满意啊。我觉得路小路的态度和许多中国人一样,这个也不是很喜欢,那个也不是很喜欢,什么都不是他想要的,但其实什么也都不是给他的。可能会有人觉得路小路虚无,但我觉得全世界都在这么写。文艺座谈会后不是说反历史虚无主义吗?于是大家都说虚无主义不好。但历史虚无主义和虚无主义是两码事。小说就是虚无主义的东西。要从反历史虚无主义进入到一个反虚无主义的状态,这个跨度太大了。你可以反历史虚无主义,但虚无主义你是反不了的。
杨晓帆:的确,评论界一直有种对六O后、七O后作家“晚生感”的印象,认为他们是没有历史的新一代。但你的小说有很强的历史感。例如“追随三部曲”始终有一个人到中年的路小路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是站在干禧年后的新世纪回望九十年代。《花街往事》虽然集中写八十年代,但也写到由八十年代的光彩焕然如何进入九十年代的衰朽,是在两代人的精神蜕变和少年的成长故事中写大历史。
路 内:那一代作家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他们对历史细节、心灵状态的体会跟后来出生的作家非常不一样。他们身在其中,跟历史的脉络也容易理清。七八十年代我也算经历过,但今天写一定不能是回忆录的形式。小说家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你站在什么位置上替谁说话,你看历史是什么态度。我更看重人物,而不是把历史凝固起来。就像《慈悲》,如果我大量写七八十年代的细节,就容易出现一种我称作“轻易地战胜了历史”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正确的。我不能因为完成了一个小说,就站出来说,OK,耶,我写了五六十年代,怎么样,我牛吧?你不能因为写了一个小说,就声称战胜了历史,连历史学家都没说过这样的话。尤其在当下中国,小说家可以有对文本的自尊心,但要把对历史的态度放低一点。
我举个李洱小说《花腔》的例子。《花腔》讲四十年代,但有一半都立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实。他在一个不可言说的大历史和说出来也没什么意思的个人史之间,找到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组合方式。以小说的方式掀开历史,刀口大不大是一回事,但流出来的血有多深则是另外一回事。好的历史感一定要建立在好的现实感基础上,这种现实感是一个作家自身心智成熟的表现。
杨晓帆:我想您的历史感也跟做过工人的特殊经历有关吧,特别是怎样理解九十年代。我的妈妈是工人,我小时候还对毛泽东时代的单位体制有些许印象,但今天即使是我妈妈,大概也没有她年轻时那种身为工人的自豪感了。见证了那个时代老工厂的瓦解和变化,您觉得这段经历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路内:最大的影响就是荒诞感吧,尖刻点说,体会到了历史虚无主义。《少年巴比伦》写的是一九九O年到一九九二年。这是一个历史断层。九十年代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一九八九年还是一九九二年,如果这两个都是开始的话,处于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两年时间又是什么?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现在还有人谈一九九O年亚运会吗?大家都起劲儿谈奥运会。一九九O年到一九九二年间其实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但没有人去谈。这两年怎样从一个非常严肃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比较缓和的状态?我记得那时小城市的工厂里非常警惕和平演变、青年工人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又同时认为国企可以永远地生存下去。这个时候国家经济进入一个短暂停顿,跟八十年代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八十年代后期大家都知道做工人是没有前途的,最好的是个体户,农民都比工人有钱,要不你就考大学。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大家又觉得做工人非常好,非常安全。那时的工厂系统很高级,有自己的大学,不一定要通过考大学才能做干部。你在这个系统内有向上的通道,那么多大学生不都下车间了吗?你先做工人,再在那个系统里念大学。国家给你安排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到了后来才被干掉的,我们要全球化,而全球化的结果就是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打破。一旦打破,你会发现能保留下来的都是所谓优质资产,那时才发现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劣质的系统里。这种失落感到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爆发出来,工人下岗,甚至一个城市都会被抛弃掉。而回过头看,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时的工人还有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奇怪的幸福感。往小了看,那两三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不存在的时间,但放大了看,两三百年的历史,尤其我们经历的二三十年,也是不存在的时代;因为你不能判定,你只能猜,这个时代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很有可能二OO八年之前的十八年是一个不存在的时代,而所谓“后奥运时代”,也什么都没积累下来,既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
杨晓帆:您在《慈悲》里就处理了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工厂完整落幕的过程,特别是小说后半段写到资本的强势进入。宿小东卖厂,国有的变成了私人的,水生出来单干,“把图纸免费画给全世界的资本家看”。水生的困惑很有象征意味,他自问,自己是在做好事还是坏事?让退休的老工人们有钱赚,为产品质量把关,是给国家作贡献,但毕竟搞垮了自己原来的厂,这又算是公报私仇吗?后面写水生祭炉的场景,读来很沉重。
路 内:这里面有很多我父辈们的真实故事,他算不算复仇,好像也不是,他是很茫然地走上了这条路。得是在事情发生后,他才能意识到有这么一个结果。这些人活得很被动的。当然,这里有一个作家视角,把它们串了起来,如果我写一个非虚构的作品的话我会失去故事递进的路线,因为,可能所有的事件都不具备象征性,它们都是庸俗的,形而下的。可能只有死亡会在这些人的心里留下象征意义,中国人敬畏死者,死者构成了时间线上的刻度。于是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通过死者刻度联系了起来。
杨晓帆:今天文学史上“工业题材”的概念基本属于过去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世纪以来,才陆续又出现了“底层文学”、“打工诗歌”、“新工人美学”等涉及工人、农民工生活的讨论。像之前的电影《钢的琴》,郑小琼、许立志的诗,北京的新工人艺术团等等,您会关注这类作品和讨论吗?
路 内:你说的好多我都没怎么看过,《钢的琴》看过,但是这部电影在电影界认为是摄影好、节奏好。平时确实是不大关注的,过去年代的作品当然很少读,没有那个语境了,我也不研究文学史,读着浪费时间。当下的作品呢,我比较相信客观陈述,我看过一些梁鸿的作品。但是如果牵扯到美学的话,我还得用《钢的琴》来作比喻,它的摄影师和导演都很好,但他们之所以出色是因为才华,而不是因为他们来自下岗工人家庭。国外时尚杂志曾经把街头工人拉到T台上走秀,这不能代表着时尚界变“左”了。当然我也非常讨厌专业作家对“打工诗歌”地不恰当贬低,艺术上确实是专业作家强一些,但那个“纳粹”的嘴脸让人恶心。在美学上,这些所谓成熟的艺术家,搞不好也是死胡同一条,依靠天分或手熟,也许可以在有生之年维持一点体面。
杨晓帆:所以笼统用“底层”、“小人物”等概念来谈当下写作常常是无效的,恰恰暴露出对复杂社会现状的认识不足。
路内:九十年代很滑稽,它有点像一切结束而一切都还没开始的胎儿状。但我们讲这个,可能已经偏离小说了,只能随便讲讲。比如我觉得过去的中国,只有特权、精英和中下层平民,但是在新世纪以后似乎诞生了一个新阶层,介于精英和下层之间的,由于通信成本的降低、传媒手段的快捷和城市人口流动的快速化,这些人用他们庞大的人口基数占领了一个位置。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你看《聂隐娘》的票房四千万(到头了)和其他烂片的票房十亿(起步数字),就知道大致是这个四比一百的情况。粗俗地说,论群殴,四个人是打不过一百个人的,论投票也投不过啊。过去年代,这个一百是没有发声通道的,但现在有了,尽管仍然是小人物,但是那个四看上去更渺小啊,而现在真正的底层是那些没有智能手机的人。这一点,也许会改变我们文学评论界对“底层”的定义,也会让作家重新审视社会结构的变动。我个人对此阶层并不持否定态度,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现象,有政治经济因素,也是借助技术进步达到的新阶段,只是我们对一百个人发出声音感到一丝恐惧,也许我们太习惯四个人交头接耳了。
杨晓帆:我个人认为《花街往事》是您最重要的作品。有评论认为是在村上春树式的青春物语之后,向巴尔扎克式的十九世纪大师们靠拢。但我始终认为即便写实,你还是一个非常现代主义的作家。“当年情”、“相册”、“跳舞时代”这些小标题,都让我想到本雅明谈过的“收藏家”形象,总体的历史只有在这些碎片中才能有迹可循。
路 内:《花街往事》的开头写武斗,结尾本来有呼应,但没法写了,有点虎头蛇尾。武斗很难写,没有谁是真正正义的一方。我没有经历过武斗,但我爸爸兄弟六个,还有一个姑妈全经历过那个时代,打得非常凶残,暴力与狂欢共存。假如今天再搞武斗,我们会认为是非常反现代的野蛮的东西,但在六七十年代却非常后现代,像一部科幻电影。在那一代人身上,他们既是普通人,也是受害人和施害者、保卫者和被保卫者,这些身份都奇特地缠绕在一起。今天我们历史学家来谈这些问题,会讲当时的人多么愚昧、残忍,这是对的,但这样不能把历史的复杂性给讲清楚。事实上,我也讲不清,到了八十年代,仍然很复杂,普通人感觉不到的,政界和文化界会有感受,但是这些事情到我现在听来觉得十分遥远。我只知道八十年代我们家陆续添置了冰箱彩电,我爸爸跳舞打麻将,我叔叔开店做个体户。于是我认知中的故事和历史成了两套系统的话语,我那套系统有点像现在的广场舞,没有反思,也不祈求真的重来,就跳个舞开心一下。这样的东西,花花绿绿的,适合写成小说,或者最近大家都在批判的“传奇”(据说中国人只爱看传奇),可是真落笔写下去,会发现两套系统的话语有隐隐的重合,它不只是奇闻逸事。甚至它的伤感落幕,显得俗气,但它确实是这么发生了。另外,我也觉得,我可不可以写点美好的东西呢,小说里的那些人我太熟悉了,他们确实挺糟糕的,但是在一个修复式的写作手法里(不惜动用童年视角),是否可以仅此一回写得善意一点,让他们不要死在阴沟里。总得尝试一下。
杨晓帆:我们谈谈你的阅读史吧,你还是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影响大?
路内:偏二十世纪。比如福克纳、卡夫卡、帕维奇;福克纳的视野对我影响非常大。虽然我从来没有用帕维奇的方式写过小说,但他讲述寓言的方式对我很有启发。中国或者说亚洲当下的事实,有它自己的特点,跟西方不一样,你要讲得出来。我觉得印度作家就能做到,不管用什么方式,严肃的、戏谑的,能把他们国家当下的现实讲出来。最近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波拉尼奥,《二六六六》,还有他的短篇,他迫使我去重读博尔赫斯。我以前觉得博尔赫斯不是那么重要,但读完波拉尼奥,博尔赫斯变得重要了。博尔赫斯是在现实世界中间没能找到他的讲述物的,他的很多东西是空的,这些凌空的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去继承,但波拉尼奥站在地面上,把这些东西给接住了,这是某种程度上,波拉尼奥比博尔赫斯更高明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作家去对比这两个作家,经由波拉尼奥,我知道博尔赫斯非常重要,你不能学其他中国作家那样凌空地接,你会没有任何机会。波拉尼奥这一代始终在思考墨西哥六七十年代屠杀学生的历史,他的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土地。当我明白这一点时,博尔赫斯还在那儿,只是我看他的位置变了。
杨晓帆:您怎么看中国的先锋文学作家?特别像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也有残酷青春,有“文革”经验,您的阅读体会是什么?
路内:我觉得也很矛盾,一方面我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才阅读了先锋派的作品,其实那时候先锋派运动已近尾声了,但它的影响力有一个延宕,我坚持认为它们对我的青年时代构成了很大的文学影响。我们那时候认知到格非,文学青年都说他非常年轻,年少成名;其实他们都很年轻,但一个一个都有大腕相。如果否定先锋文学,那我觉得自己的阅读脉络就出问题了。另一个方面,我也承认,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存在着学界所说的诸多问题,它确实是死了,也没必要硬撑着说“先锋不死”这样的话。我宁愿认为,先锋文学是为中国文学腾挪出了一个空间。也许有一些文学流派之间的恩怨,但那是文学史的事情了。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怎么说呢,我可能都没有把它们当先锋派来看待,因为它们涵盖了短篇小说的诸多要义,其中大部分作品在二三十年后看来都没有减色,也许它们会永远留下来了。
杨晓帆:你的《云中人》很有点实验小说的意味,我觉得是以精神分析的方式重写了“追随三部曲”。你在创作谈里说过《云中人》“大概采用了齐泽克对应拉康的一些哲学分析”,小说的谋杀题材又让人联想到希区柯克的电影,齐泽克有本书叫《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问拉康吧》,我觉得很多作家都没有你那么强的理论意识,除了文学作品,平时您还爱读些什么书?
路 内:我也是特别不懂事的,我开手就谈拉康,其实也是一知半解。后来听了几场无关的评论会,我发现程德培老师谈拉康很熟,再问问,发现评论家都看过拉康。这就没救了,基本上我是把自己往枪口上送,别人还不乐意开枪的意思,以后我再谈小说就屏蔽一切哲学家了,随便讲点家长里短的,比较容易蒙混过关。
我的理论知识全是半吊子,完全讲不清楚,狡辩能力较强,这特别不好,在话语系统的边缘胡搅蛮缠。而且也不懂外语,都是经过翻译的词汇,望文生义得很。现在还看些理论方面的书,比如伊格尔顿,也看诗,不太懂诗学,也看社会学和历史方面的书,胡翻而已。
杨晓帆:虽然您常写城乡接合部发生的故事,但“上海”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符号,是旅程的终点。现在您也算跻身海派作家,您怎样看待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和其他写上海的作家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特色在哪里?
路 内:今天我们觉得“城乡接合部”这个概念很重要,但九十年代这个概念不重要,很寻常。就像我写《花街往事》,评论家说我书写社会底层,八十年代哪有什么“底层”概念。这样写是跟某个特定时代有关,比如九十年代初上海西站,再过去点就是客运站了,跟现在中国一个三线城市差不多。八十年代城市人口就是上等人,农村人口就是下等人。上海其实意味着一个阶层的距离,这个距离在不断地扩大。过去从苏州到上海两个半小时,后来一个小时,今天三十分钟,但你仍然会觉得这个距离在慢慢扩大。距离不是空间上的,除了北上广,其他城市你想喝杯像样的咖啡都找不到地方,这对有些人不重要,对有些人就相当重要。中国内地很多城市,对我来说是无趣的,玩一趟可以,但让我在那里生活我会觉得非常压抑。只有极少数的城市,比如重庆,我对它一直怀有感情。上海反而是一个跟我没什么关系的城市,不会让我觉得压抑。你越想和一个城市发生关系,反而对它的期望和要求越多。我有个朋友,一个女孩,九十年代孤身一人去了纽约,唯一感觉是我终于自由了。事实上我在上海也有这种体会。这个城市跟你没关系。它非常庞大,你要和它整体地对接起来会产生困难,产生盲点;而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自尊心来说,他又会觉得,全宇宙都是虚构的,凭什么会在一个城市面前产生盲点呢?我对城市啊、时代啊、人啊,尽可能还是保有谨慎心,不要那么早地下判断,不要在没把握的情况下用长篇小说去构筑一个现实的世界观。和其他写上海的作家相比,我的特色大概就是:没怎么写过上海。
杨晓帆:《少年巴比伦》已经拍成电影,您刚提到又有新的电影改编计划,能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吗?
路内:电影这事情在目前的中国来说,既不是作家的事,也不是导演的事,大体上是投资人的事。这个行业有聪明人,也有极其愚蠢的,如果你只是待在家里卖卖版权的话,是比较安全的,但踏人影视界就什么人都能遇到了。有些作家适应不了。我因为在广告公司做过十二年,大体上能理解这个系统。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挺好的,但是没必要炫耀。如果跨界做编剧,编剧是门手艺,得从头学起,辛辛苦苦学会了,也就是这么回事,能干点别的。
杨晓帆:最后说说您最近的创作计划吧?
路内:在写一个和《云中人》平行的小说,写法不一样,体量很大,写六七个人的二十年,被毁坏的青年和中年。写一个血汗工厂,这一批人怎么走进去,又怎么走出来,写爱情和谋杀。某种程度上,《云中人》这个小说的不尽人意之处,我想用现在这部小说来“善后”。《云中人》我觉得写得有点紧张,对于事件连接点过度关注,形式优先于内在。我希望这部新的小说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也会写到各种城市、农村、城乡接合部,看看我能否彻底抛开地域限制。希望善始善终吧。
——到壮族花街节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