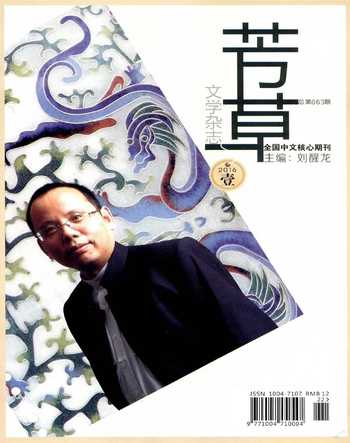后惊
贾桐树

我可不敢说是我姑撒谎,打死我都不敢:但我敢说,一定是姑耳性不好,她记错了。
那年我十五岁,什么事都可长记性了。姑呢,却五十好几了。我跟妈犟过嘴,说,就姑那岁数,天天乱乎事儿拿着,忙三火四不着两头的,耳性能不出岔头吗?妈才懒得听我的,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不说,还陪着姑拿我想当然地说事儿。姑告诉妈,那可真是烧大发劲儿了,那头发吧,我眼瞅着的,说立起来忽地就立起来了,说趴下忽地就趴下了,可把我吓的。妈说,你侄儿可不就那样,打小就是,知道的是感冒发烧了,不知道的还以为着啥惊了呢!
——我没病,我也没着啥惊。大人们可真是的,我的话他们咋就一句也不信呢……可倒好,姑说的,就说一遍,还说得颠三倒四的,他们却一五一十地全信。整得好像就是我在撒谎了。
这事儿,都快闹哄死我了……
等姑走后,我还得跟妈学说,好歹让妈信我一回,哪怕就这一回。姑有些事儿是没记错,不假;可有些事儿吧,她确确实实记错了,我敢发誓起愿。
我要从头跟妈捋这事儿,清清楚楚的,从腊月开始捋……
每年,一进腊月门子,村子里家家户户就都开始张罗杀年猪了。奶奶在的时候,我们家的年猪杀得最晚了,因为破五后姑才回来,杀早了,猪肉一冻时间长,就不新鲜了。姑和姑父吃不着新鲜肉,奶奶可不干。后来奶奶过世后,我家调了个个儿,年年都第一个杀。因为奶奶一过世,姑就不年年回来了。妈说,老早就把年猪肉给你姑送过去,别让你姑寻思娘家妈不在了,娘家人就不惦记她了。
给姑家送肉,年年都我去,十五里地,对我这个半大小子来说,跑平趟一样。一个肘子,一扇排骨,还有一条猪尾巴,二三十斤分量,死沉死沉的。但一想到到了姑家,肥吃肥喝的,我就一点儿都不觉着沉了。而且,姑父一见着我,指定说,猪尾巴给姑夫背来没?我说,那还能忘,背来了。姑父就一脸酒瘾盎然的样子,说,好小子,没得说,明个儿就叫你姑给你整套过年的新衣裳穿。
姑父最爱吃猪尾巴了。我到姑家当天,姑就把猪尾巴给姑父烀上了。姑父说,猪尾巴是活肉,肥而不腻,香。我就跟姑说,我也想尝尝。姑说,小孩子可不能吃,吃了后惊。我说,姑,你咋和我妈说得一样,我可不是小孩子了,我都十五了。姑父有点儿小孩子气,跟我直挤咕眼睛,一边说,你要是吃了走黑道儿可后惊,总觉着身后跟个大姑娘……那可咋整;一边趁姑一眼没看到,就偷偷地把一块猪尾巴肉夹到我碗里。又说,小孩子家家的别瞎说话,食不言,寝不语……我笑嘻嘻地配合姑夫,只吃不说。
我鼻子下面的汗毛都重了,原来睡觉时都光不出溜地钻被窝,现在可不敢了……可大人们却偏偏视而不见。只有姑夫还算够意思。说实话,猪尾巴肉并不比肥膘子香,没啥吃头,但我就是要吃,我倒要看看,到底我是大人还是小孩儿,能不能后惊。
傍晚,我特意踪到外面大街上瞎溜达,而且,我还要等到天完全黑下来,再溜几圈。大人们老套,迷信。我都上初中了,我可不信那一套。
姑家住在镇西,从镇中心最繁华的十字街往西一走,过个小桥就到了。土街道不咋窄巴,可两边的老式青砖房子举架太高,好像把街道挤成了瘦瘦的一条。我走在傍晚的天光里,长长的影子跟着我,寸步不离地提醒着我,要天黑了,我马上就能证明自己不是小孩子了。
冬天天短,天马上就暗了下来。我还在瘦瘦的街道上走。路两旁人家昏暗的灯光逐次亮了起来,显得一幢幢房屋阴森森的。天空中开始出现星星,先是最亮的那两颗,妈告诉过我,一个是牛郎星,另一个是织女星。但究竟哪颗是牛郎星哪颗是织女星,妈也没整准,说不清。我问过。妈说,管他哪颗是哪颗呢,等七月七那天这两人就鹊桥会跑到一块儿了,不撒谎的好孩子那天晚上要是趴在黄瓜架底下去听声,就能听到这俩苦命人儿说悄悄话。我年年想听天上的人说话,但年年都忘记哪天是七月七。
星星越来越多了,牛郎和织女站在银河两岸还眨着眼睛,嘲笑我似的。街面上寒气袭人,小冷风顺着我的脖领子直往我后脊里钻,但我忍着不打寒颤。向东走,我一直走到小桥头,听河筒子里小北风呜呜地在树梢上打颤,再听一两声桥下的坚冰被冻裂得咔嘣咔嘣的动静……就急急往回来,再向西去。西边,道北有所小学校,房子是早些年没收大户人家充公的,是前出狼牙后出梢、屋脊扣着八宝琉璃瓦的那种庙一样的建筑,门口还蹲着俩卷毛石狮子。白天我路过这里,顺着大门洞往里瞅一眼,都毛得溜的。现在,学校正放寒假,到了黑天,空荡荡的大院子,更是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有风一吹,操场边儿那块宣传板上的破纸片子就一声紧一声地哗哗啦啦直响……我走到学校门口,都不知道棉袄快被汗溻透了,麻溜没事儿人似的再折回来。就这样我熬了几个来回。最后,天色把一只流浪猫漆得只剩下一双冒蓝光的鬼眼了,我才告诉自己,差不多了,该回姑家了,要不,姑该出来喊我回屋了。但我故意放慢脚步,不能走快,我可没后惊。
从小学校那边往回走,我多么渴望能在街道上碰见来往的行人啊。有唠嗑声或是打招呼声那最好不过了,哪怕是一两声咳嗽也行啊……但镇上的人也真是怪,好像家家户户都灶台打井房顶扒门,谁家跟谁家也不走动似的,街上别说有人声了,就连个鬼影儿都见不着,冷清清的灯光隐隐约约洒在黑暗的深处,都快要打瞌睡了。这里的小孩子也娇气,要是在我们家那儿,这大长夜的,小孩子们早蹽出家门了,在最宽畅的大道眼儿上,不玩干草垛抡闸刀也得靠在谁家矮矮的土墙上玩挤香油挤出眉屉换糖球儿呀……
我冻着了,小棉袄先是给汗溻透,落汗时又给风打透了……后来我姑到我们家去,告诉我妈,说那天晚上我说了一宿的胡话,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哪儿都不挨哪儿。姑的话我可不敢不相信,那是我姑,是长辈,不能唬我。可是后来我思来想去,却只记得那天晚上我是在姑家小胡同里碰见了那个小女孩儿,兴奋得一宿没睡好觉……感冒可是第二天晚上的事儿了,要是我真说胡话了,也应该在第二天晚上呀。再说了,不感冒我也只能是说梦话。
姑记错了。
姑家在道南。道南的房子都俩门,北门和南门。冬天,天儿冷,冲道的北门都堵死了,走南门。姑家家西是两家夹一道的小胡同,胡同里有两家为走南门开的小偏门。我一身透汗,毛手毛脚地拐进姑家的小胡同,迎面突然撞上了个人影儿,心呼啦一下子就敞亮了。终于瞄见了人影儿,就算不跟我搭话,我的心也踏实多了。
人影儿是个小女孩儿,在对门另外一家的小偏门那儿关门呢,她瞅着我走近,说,小孩儿,我一看你就是外街人,大黑天儿的这外面可有啥溜达的呢,多冷,别冻感冒了。
我站在姑家小偏门前,想告诉她我这是在证明自己是大人了,正试自己胆儿呢,听她话里有瞧不起外街人的意思,还管我叫小孩儿,就懒得搭理她,没稀得跟她说话。
小女孩儿没看出我的怠搭不理,又说,小孩儿,你叫啥名呀?
我忍不住了,说,小孩儿,你叫啥名呀?
她扑哧一声笑了,说,小孩儿还挺冲……我叫七月,你呢?
我只好告诉了她,我叫臭臭。
七月又笑了一下,说,你真有趣儿……
许是觉得我声调不大对头,她关上门,说了句明天见啊,就回屋了。
我靠在姑家小偏门上,一直望着她。灯光从她们家半掩的屋门缝里射出来,映着她轻盈移动的身子,她的两条柔软的黑辫子也跟着她轻盈的身体甩动着。
七月,挺好的女孩儿,我是不是说话太冲了呢……
那天晚上,我有很长时间没睡着觉,她的名字总是使我蠢头蠢脑地激动。好不容易要迷糊过去了,突然间我想起来了,我以前来姑家,西边那家原来住着的是老许头子和老许太太,说是几年前这老两口子给儿子接城里去住了……莫不是老两口子从城里又搬回来了?七月是不是那老两口子什么人呢,孙女吧?还是又有一家新搬来的呢……哦,新搬来的还敢笑我是外街人,等明天再见着她的……
明天,我记着的是我要陪姑去十字街百货商店购买年货啥的,要帮她拎一大堆东西。往年,这是我最盼望也是最高兴的一天:但今年……这会儿,我却总是精神溜号,总是想到那个瞎叫我小孩儿小孩儿的小女孩儿七月。想到今天我还能不能见着她,见着她时她还能不能跟我说话了;要是说了,她是叫我臭臭呢还是还叫我小孩儿呢……有时,我想着想着便会脱口而出,小孩儿……吓得自己慌忙吐舌头,脸红。有一次,给姑听见了,姑没太在意,只说,这孩子,咋还自说自话呢。
哦,对了,上面这段记忆在时间上也和姑告诉妈的对不上茬儿。姑说,我说了一宿胡话,高烧了,第二天根本没起来炕。跟她去买东西是三天后的事了。我犟不过姑。大人不会撒谎的,只有小孩子才撒谎。我要是犟嘴,不尊重姑,就是撒谎。
可是我确实没撒谎。当然,姑也没撒谎。我宁愿相信是姑岁数大了,耳性不好了。
我记得我跟姑逛完百货,回到姑家,扒拉一口饭,就麻溜跑出姑家。我想见那个叫七月的小女孩儿,但我不敢在小胡同里多逗留,我怕姑看见我抻着脖子往七月家瞎撒目,该说我了。我就跑到姑家房后的土街上瞎溜,但我的眼睛却一刻也不肯离开小胡同口。
冬天的午后还不算太冷,阳光很冷静地照暖靠北侧的半面土街。街上很少有人走动,只有房顶上的麻雀闹腾得挺欢实,一会儿从这片青瓦踅到那片青瓦上,一会儿没准儿又都落到电线上,叽叽喳喳的,没一会儿消停的时候,老烦人了。七月家的房顶麻雀最多,许是原来屋子空着没人收拾的缘故吧,房顶上还摇曳着一堆堆一丛丛去年的蒿草,招麻雀。我无心看麻雀,但在等不到七月那工夫,我无所事事,顺着冷风嗖嗖的街道往东或者往西溜几趟,又不能离姑家那条小胡同太远,万一七月出来了呢,所以更多的时候我还得是看那些仨一群俩一伙的麻雀。偶尔有行人路过,我还不能傻站在一个地方,我得假装行人的样子走两步,得让人家以为我也是过路的人,直到那行人走远,已不再注意到我,我才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看那些无忧无虑的麻雀,等着七月没准儿会突然出现,喊我,小孩儿……她昨晚说过明天见的,她不像撒谎的那种孩子。
我想起来了,我发烧说一宿胡话是这天晚上的事儿,要说冻着,我是在大街上看麻雀等七月时冻着的。姑是长辈,奶奶在世时的小棉袄,爹妈都让着她三分,我能直姑的罗锅实话实说吗?不能,妈会骂我不懂事儿,没准儿还兴许打我几巴掌,多不值当。我才不干那种傻事呢。姑后来说我烧糊涂了,我也没跟姑争辩,说我烧糊涂就烧糊涂吧,烧没烧糊涂我自己心里有数,只不过懒得跟他们大人较真儿而已,没意思。
那天,我在街上逗留了太长的时间,眼瞅着南面那趟房子的阴影都爬过了半条街了,我也快被冻得透心凉了,尤其是脚尖,跟猫咬了似的,却还不见那个叫七月的小女孩儿有什么动静。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急的,我已经忍不住热泪盈眶了。我看了胡同口一眼,又看了一眼……一咬牙,就恨恨地转身往东边小桥头那儿去了。
七月她不是好孩子,她撒谎。
天太冷了,我都听见我上下牙巴骨打架了。我得活动活动,直到身体发热为止。河套里有几个比我小的孩子在滑冰车,叫着,喊着。我站在桥头发愣,要不是等七月,我指定会跑过去,在冰面上来回打几个滑出溜,身体一会儿就热乎了。在家时,我一天天长在河湾子里,滑冰车,滑单腿驴,我还会溜冰鞋呢……要是七月能看见我溜冰鞋,我指定单腿给她溜一圈,哧——哧——动静老好听了,一准儿像王母娘娘拿她头上那把银簪子在牛郎织女间划出一条银河的动静……可惜我的冰鞋没背来。
小孩儿……七月突然出现在我身后。不用转身,我就嗅到了她头上迷人的香皂味道。但我还是转过了身子,被她全新的打扮惊住了。她的两条柔软的黑辫子不见了,一袭长发披垂下来,水波浪一样漫向她纤弱的腰肢,风一吹,把我的心都荡得快要停止跳动了。
臭臭。她改口了,叫我臭臭了。她说,方才我洗头来着,出来泼水时看见你无着无落的小可怜样儿了……她笑了一下,说,头发湿,没敢马上出来……她稍微叉开腿,双脚脚尖儿稍往里勾,从容地站在桥头,一只手轻轻地扶着栏杆,瞅着我。
我低下头,再也不敢看她,两只手紧紧合在一起使劲搓着,感觉手都颤抖了,好像全身快要失去知觉了。我不知说什么好,呆在了她对面。
都来不及编辫子了,她说,怕你着急,披头散发就跑出来了……
我说,你不编辫儿……更好看……
我妈说,披头散发的,跟鬼似的就往外跑……七月说,你还说我好看,嘴巴抹蜜了吧?她笑了,又说,有空我得去十字街百货买个发卡卡上,那还凑合。
她说这话时,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我跟姑逛街时看见过一种发卡,蝴蝶状的,可好看了……
现在,我已记不起那天我后来又胡乱地跟七月语无伦次地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站在桥头居高临下,微低着头,凑近我,总是能有说有笑大大方方地跟我说话。夕阳照着她白嫩的脖子,照着她披垂的头发,也照着她风衣内衬隐约可见的月白色镶边儿。
临分手时,她问我会不会吹口哨,我说会,就吹给她听。她说,明天你别傻站在街上等着了,多冷,冻感冒咋整?你一出门,在胡同里吹一两声口哨就是了,小臭臭孩儿。
我激动地嗯呐一声,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点头,说不出话了。
那天,我才真的被冻着了,我记得七月居高临下跟我有说有笑时我都哆嗦了。晚上,我开始发烧。姑说我说了一宿胡话,应该就是这天晚上。没错。我没敢问姑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都说啥胡话了,我怕我胡说出了七月的名字。白天,姑给我吃了药,喝了姜汤,发了汗……但我还是起不来,头一直昏昏沉沉的,往起一抬,就恶心,要吐。我想,这回可把人家七月骗惨了,说不准这一天人家也没敢动地方,就等着听我口哨响呢。
迷迷糊糊中,七月突然趴在栅栏上喊我吹口哨……我一激灵,醒了。是个梦。后来我发现,我睡死死的时候,根本就梦不到七月,越是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准梦见。
神智刚一清醒,我就迫不及待地跟姑说,姑,借我几块钱呗。
姑说,借钱干啥?
我说,我家后街杨大丫儿要我给她捎个蝴蝶结发卡,说捎回去再给我钱。
我早就想好怎么跟姑撒谎了,杨大丫是我亲表叔的大女儿,姑的亲表弟的女儿,姑认识,信了。
姑说,行,你好好养病,刚喝完一碗姜汤,再发一身透汗就好了,我一会儿正好去街里给你爹打两瓶好酒,给你捎来。
我又强调了一句,姑,人家要蝴蝶结的那种……
大下午的时候,姑买回了发卡,黑褐相间的蝴蝶结发卡。我一看见,就晃晃荡荡爬起来。我要去吹口哨,我要把发卡给七月的长发拢一拢卡起来……
姑说,这孩子,快好好躺着,起来干啥呀?
我说,姑,我好了,躺得我又迷糊又恶心,我得出去吹吹风。
姑说,那可不行,外面都阴天了,冷飕飕的,好像要下雪……再说了,你刚得病的身子骨弱,火气低,容易招东西,那可不行……
姑迷信,每年一回我家,正经嗑跟妈唠完了,就东家什么人招没脸子啦,西家什么人出门碰上鬼打墙啦……唠个没完。姑说啥也不让我出去。但我惦记七月,就说,我不远走,姑,就上趟厕所,我要吐。我小时候一感冒,妈就给我做喷香的小米饭吃,每回病好之前,吃的第一顿小米饭,都要吐出来,坐下病了。姑也知道我有这个毛病。为了见七月,我撒谎了,从厕所跑出了姑家。
一出小偏门,我就急着吹口哨,但感冒刚好,嘴唇软,没吹响。我这个急呀,虚汗马上就下来了。我瑟瑟发抖地靠在冷风中的栅栏上,又努力地试了几次,终于滋滋地吹响了几声。我怕七月听不见,又多吹了几下,才晃晃荡荡顺着昏暗的街道往小桥那边走,脚下像踩着棉花似的,用不上劲儿。我一边走,还要一边回头回脑地看,我以为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工夫,七月就能从后面赶上来了,她指定听见我的哨音了。
可是,就在我以为七月还在我身后时,她却突然出现在了我的前面。天啊,七月在桥头等着我呢。怪了,刚才我为什么没看见她呢?是感冒把我烧迷糊了吧。我扑通扑通地紧赶紧踩了几下棉花。
我说,……我来晚了……感冒了……
她嘘了一声,示意我别说话,用双手捧起了我的脸。我感到了她手间的凉。她一定在桥头等我好长时间了。她捧着我的脸不说话,离我那么近,近得我都能看清她胸脯急促的一起一伏了,水波浪一样的长发给风轻轻地一吹,就快拂到我的脸上了……
她说,我看见你姑给你买药去了……这脸,还烫手呢。
我怯怯地掏出了蝴蝶发卡,递给她,想说什么,嗫嚅了半天,没说出来。
你咋知道我喜欢素气的?她接过发卡,捧着,像捧着我狂跳不已的心,使我迷迷糊糊地听不清她又说了些什么……好像有一句是说,谁要你买了,小破孩儿,臭臭孩儿……就慢慢地转过头去了。
河套里,一个滑冰嬉闹的影子也没有,阒无声迹,只有坚冰的炸裂声偶尔把我狂跳的心炸得隐隐作痛。我想说我是真心的,她飘飘的长发别上这个卡子更好看,却还是说不出来。我勉强地站着,等着她回头。她披散的长发在我的眼前飘着,飘着……突然,她转过头来,说,臭臭……就飞快地掐了一下我胳膊,那么轻,那么软,那么的令人猝不及防,我感到我都喘不上气来了……
她跑开了,好像一朵花似的跑开了。
臭臭,你也赶快回家吧,她站在了胡同口喊我,要下雪了……
隐隐约约的,我好像听见她又说,她就是为我才没编辫子的……然后,她向我招手。手中的蝴蝶结也闪了闪。明天见,她说,眼里忽然有一种婆娑的光一闪。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有一股热流迅速地滚遍了我的全身,暖得我刹那间脚下就不踩棉花了。我的目光一直尾随着她逃也似的背影,没入了向晚的街巷、胡同口。两三声狺狺狗吠,我都感到动听。
之后的日子,一场大雪叫我又在姑家多逗留了几天。这几天,我偷偷地和七月顶着冒烟儿大雪跑去了百货商店,看花布、看发卡、看布娃娃……一路闲逛。
七月说,你姑真会买东西,这个深色儿的蝴蝶卡子是最好看的了。
我得意地说,是我告诉姑买的。
七月刮了一下我的鼻子。
那天,雪停后,在胡同口,我和七月堆了两个雪人,一旁一个。七月说,一个是她,一个是我。她还说,等我走了,她就一个人看着这两个雪人白头偕老…..
七月还调皮地说,臭臭,知道啥叫白头偕老不?
我说,就是春天一来,雪人化了,就老了。我逗她。
七月说我坏蛋,脸绯红。但她说是冻的,我不拆穿她。
姑后来还说,我是感冒好了以后离开的她家,这对;但姑又说大雪是我烧迷糊那几天下的,这就不对了。那天我走半道上又返回姑家,我分明看见了那两个雪人还立在胡同口呢,我烧迷糊能堆雪人?而且,我是在和七月逛完百货商店堆完雪人后的第二天下午,天头稍微暖和一点儿后上路回家的。七月还说呢,你姑心挺细呀,上午还真是不好走,那小北风,刮鼻子刮脸儿的。
七月偷偷送我出的镇子。
大雪覆盖了原野,道路几乎消失了。赶路,我的身后,多了一双女孩儿的眼睛。脚下的十五里地,那么长,我走不动。我忍不住回望镇口,七月摆手呢。我再往前走,忍不住再回头,镇子已经影影绰绰的了,但我分明看见七月还在摆手呢……
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分手的那一刻,我说了什么吗?七月呢,她都说什么了呢?我的记忆一片空白,好像白雪覆盖的茫茫原野把一切都消除了。
镇子也消失了。雪原遥远,似乎没有尽头。
风声。
但雪原把风声砥砺得又尖又啸、似有似无。呜——响一声,也不知在哪响;呜——又响一声,好像哪都在响……但侧耳细听时,又好像哪都不响了,是我自己在吓唬自己。路两旁远远的黑暗的野树丛,也黑得疹人,不经意间瞭上一眼,里面好像藏着无数双更黑的眼睛,盯着我……
阒无一人。回家的路不但遥远,而且,被埋在雪下,静得连一点儿回响都没有,只有我自己单调的踏雪声,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哦,动静这么大,一定得惊着什么……
咔哧,咔哧……不对,好像不是我的声音,感觉是从我背后传过来的。背后有人。我忙停下来,回头。行要有伴儿,住要好邻。我想我有伴儿了……
我回家的路是东北方向,我回头,恰好是迎着下午西南方向的阳光。雪原上,刺目的雪光扎得我睁不开眼睛。一阵晕眩,咔哧声也没了。是我自己的回声吗?在我终于看清自己的身后只有自己的一行脚印的时候,我知道可能是我自己产生错觉了。我突然感到我的孤身一人,是雪原的寂静让我产生了错觉,我沉湎在某种幻想里了。于是,我转身重新赶路。
但没走几步,咔哧,咔哧……我再次感到身后确实有人跟着,而且,离我不是太远。这次可是真的……我心惊肉跳,又停了下来,侧耳细听……但是,却什么也听不见了,甚至,连风声都没有了。雪原把一切都吸净了,只留下了属于我的莫名的恐慌……
后惊?
我的鬓角、额头,都在冒汗。我摘下了头上的狗皮帽子,深深吸气。我已经长大了,我是大人了,我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儿七月了,七月也喜欢我。我想,我不要怕,这大白天的,有啥怕的?爹告诉过我,走道就怕碰上狼,碰上了也别慌,蹲下,划拉蒿草,狼要是再不走,就拿蒿草笼火……我摸摸兜,出门时带的安全火柴还在……
我拒绝了恐慌,站在雪原上不走了,我要等,等后面的动静由远及近,死等。假如有人在后面走,等上一会儿,我就不信我看不到人影。我要告诉七月,告诉更多的人,我不再是小破孩儿了。
当然,还是空无一人。
这可真怪了。我走,后面就有动静;一停下来,跟着走的那个人也就停了。谁呢?这冷的天儿,这荒郊野外的,沉在后面要干啥呀,吓唬我呀,可我不怕……
我已经无法摆脱我身后有人的念头了。我本想冲雪原喊一嗓子,给自己壮壮胆儿,但我张开大嘴,吸气……顿觉凉气袭人。我的嘴巴僵硬,感觉冻得喊不出声了……
好吧……那我索性就不等了,返身往回慢慢地走,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后面有人跟着,还是我真的后惊了呢……
雪地上只有我深浅不一的脚印,偶尔也有小鸟留下的几处爪痕,除此,积雪处处完好无损。
我突然想起了七月,但马上我就否定了自己。我记得很清楚,出了镇子,我回过无数次头,看见她时,她都一直在摆手。镇子不见时,她也不见了,她一定是早就回家了,回家看着胡同口那两个雪人白头偕老去了。
约莫往回走了几里路远,好像除了我自己踏雪踏出的咔哧咔哧的声音,已没有旁人的声响了。刚才一定是自己的幻觉,是自己还没长大成人的小小恐慌吧。我终于吸足了一口冷气喊了一嗓子。然后,我一边自言自语,责怪自己,一边怕真有人突然出现,听见了我的自言自语,忙往四周扫了一眼。突然间,我看见前面不远处,我脚印旁的积雪上有一个缺口,很像有什么东西掉落了砸出来的。我急急跑了两步过去,惊讶地发现,是那个蝴蝶结发卡在雪中闪着黑幽幽的光。七月,是七月。我捡起发卡,紧紧地攥在手里,四处张望。雪地上的阳光仿佛轰轰地响着,我的头瞬间胀得有多大。
我向我身边的雪原最高处跑去,我要打开我的视野去搜寻七月的身影。哦,七月,一头长发飘飘,一袭风衣也飘飘……我四处喊,七月,小女孩儿!小女孩儿,七月!喊着喊着,我突然觉着不对劲了,就又跑回路上,我要在我的脚印旁找到证据。
确实没有别人的脚印,我的脚印有的也孤单得快要消失了。我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了。
姑后来说,我就是烧迷糊了,做了噩梦了。但我那时还不信自己迷糊,只是有点儿糊涂。我往回跑,我要跑回姑家那条胡同,先看看那两个雪人,然后直接打开姑家对面那个小偏门,喊那个叫七月的小女孩儿出来,问问这到底是咋回事……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了姑家。
姑在胡同口意外地撞见了我,吓了一大跳,说,这孩子咋又跑回来了……麻溜把我拽进了家门。
看见姑时我眼泪都快要落下来了。姑后来跟我妈告诉说,这臭臭……我一看,背包摞山似的,跑得满脑瓜子都是汗,非要去老许头子和老许太太那个空屋子看看,说是要喊什么月,一个小女孩儿,这不是大白天撞见鬼了吗,吓人不?指定是烧迷糊了……我们家那死鬼也是,偷着给他吃猪尾巴干啥?要是不吃猪尾巴,孩子能大后晌黑灯瞎火地跑街上练胆去吗……先是后惊,吓着了……再感冒,烧得七荤八素的……对了,我想起来了,臭臭说胡话时是说了七月…一
姑这番话是在我家说的。我二返脚赶回姑家来,姑说啥也不让我一个人走了,非要把我送回家,弄得我连七月的影子都没看着。姑像看贼似的没让我出屋。
我承认我的一个衣服兜确实烂了一个大窟窿,但不是姑说的那样,蝴蝶发卡绝不是我掉的,我压根儿就没往自己的衣兜里揣过。我是紧紧攥手里在那座桥头直接给了七月的。
这事儿,只要让我见到七月,就能证明我没撒谎……而且,我没烧糊涂,也没做噩梦,我真真地遇见了一个小女孩儿,她叫七月,可好看了……
姑是我最敬重的人,后来,她一口咬定是我后惊了。她说,要不,十冬腊月的,跟七月十五根本就不挨着,咋就冒出个七月呢?姑说得有根儿有蔓儿,把鬼节都拉来说事儿了。
我也就没再争辩什么,争辩也白争辩。不过,姑不知道的是,再再后来,我又见过一次七月,而且,还是在姑家的大街上,只是,那天人太多,眼花缭乱的,七月她没看见我,就蹦蹦跳跳一晃而过,消失在赶集的人群里了。等我醒过神儿来,赶紧去追她,却说啥也没追上……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失去了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而已。
不管大人们怎么说,他们说他们的吧。藏在我心里的秘密,他们也永远别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