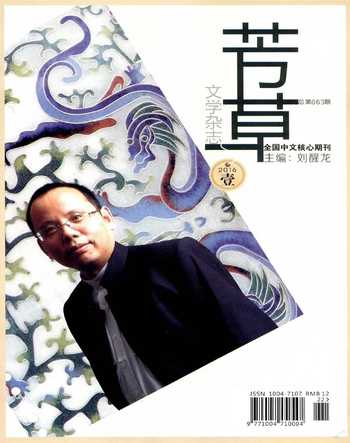主持人语
2016-05-30 10:48:04朱小如
芳草·文学杂志 2016年1期
朱小如
认识吴克敬是参加二O一四年底芳草杂志社主办的“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颁奖会议时,记得一起在江边闲走闲聊,走出挺远险些误了会。我谈到那个年代,文学是一种“负能量”教育。他颇有同感。此次对话里他说:“文学不等于生活,而且不要把文学理想化。但在此之前不久的我,以及像我一样的作家,都太把文学理想化了,而且太过注重文学的生活化。”可知他这样的“文学观”的确由来很久,思考得很透彻。文学理想化一旦过度就必然生硬地“干预”生活,而不是“尊重”生活。
细读两人的对话,其中有关“文学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男性作家特别会刻画女性形象”,这个话题有趣,也很有“感性文学史”意义,我们的文学史以“时间、事件”为维度的多,以“文学人物”为维度的几乎没有,挺遗憾的。
叶舟的诗歌,更多的是“歌”,我许多年前就很有感触。尤其是去过河西走廊,到过边关,见过大漠荒原,那里的自然环境气息,令你不得不放开喉咙喊两声,喊成调了就是好诗。叶舟的情感丰富充沛,诗和小说创作两不误,也是一绝。
路内的小说有上海的城市文化照耀,城市文学又是当代文学中时常被遮蔽的那个阴影地带,理论上说,可以尽情施展拓宽的空间很大,关键还在于要找到一处不那么容易被遮蔽的阳光之地。
在此对话中,路内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父辈们”的“全民经商”时代和“工业衰退”时代的细致体会,让我感觉到路内似乎找到了上海城市的“神经”,但如何让“神经”变为“精神”呢?
猜你喜欢
边疆文学(2020年4期)2020-05-14 11:26:52
心潮诗词评论(2019年12期)2019-05-30 12:24:36
心潮诗词评论(2019年12期)2019-05-30 12:24:28
东坡赤壁诗词(2017年3期)2017-07-05 10:44:36
金色年华(2017年8期)2017-06-21 09:35:24
IT时代周刊(2015年7期)2015-11-11 05:49:50
中国卫生(2015年6期)2015-11-08 12:02:52
新闻传播(2015年10期)2015-07-18 11:05:40
江汉论坛(2015年7期)2015-02-27 16:05:30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2011年1期)2011-08-22 12:5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