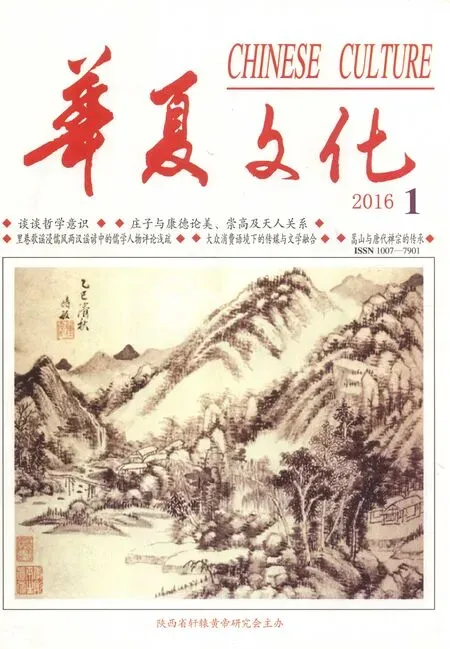里巷歌谣浸儒风——两汉谣谚中的儒学人物评论浅疏
□黄有年
里巷歌谣浸儒风——两汉谣谚中的儒学人物评论浅疏
□黄有年

一、人物评论现象的渊源与界定
人物评论的产生及存在由来已久,有文字记载以来,这种文化现象就被流传下来了。例如:“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尚书·康诰》)周公勉励康叔对周王朝承担责任时,追溯了文王创业的艰难,同时也是对文王的评论。又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经·魏风》)这是当时下层受剥削的百姓对贪得无厌的统治者不顾劳动人民死活而实行繁重的赋役制度的讽刺和评论。再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这是孔子对鲁国执政季氏僭越行为的一种愤慨评论。再如:“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冯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妒忌。”(《楚辞·离骚》)这是屈原对当时误国群小的评论。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典籍中流传下的人物评论。以上引述的人物评论中既有具体的评论对象,也有比较模糊的评论对象;既有后人评论前人,也有当时人评论当时人。
迄至汉晋之世,人物评论的内容蔚为大观,前辈学者对此有所注意。盖汉晋之时士风大变,文物制度迭出,先是察举制、孝廉制和举谣谚制,后有九品中正制,因而人物品题风气勃发。不过在什么是“人物评论”这个问题上,大家似乎追究不够。
我们认为,人物评论具有十分宽泛的内涵。就人物评论的发出者而言,它可能是具体的,也有可能是抽象的;就人物评论的对象而言,它可能是某个人的言,也有可能是某个人的行,还可能是某一事项——因为事项的背后隐藏着人;就人物评论的真实性而言,有的人物评论合乎事实,有的则与事实相去甚远。但是无论如何,在对人物评论的考察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被评论的对象,也会看到人们情感的抒发,其中伴随着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因此,人物评论是评论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对特定时空内的评论对象的言行、事项进行某种情感表达的话语叙说方式。在话语叙说的过程中,评论者往往会流露出自己的道德、价值、审美和文化倾向。这种话语叙说方式包括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在此,我们将针对儒学人物而做出的评论统称为儒学人物评论。
两汉时期流传下来的谣谚中保留着丰富的关于儒学人物评论的历史内容。通过这些谣谚中的儒学人物评论,可以一窥当时民间社会对儒学、经学和儒学人物的一般看法。
二、两汉谣谚中的儒学人物评论
两汉时期,谣谚中关于儒学人物的评论很多。虽然这些评论的起始形式各异,如“诸儒为之语曰”、“邹鲁谚曰”、“关东号之曰”、“乡里为之语曰”、“京师为之语曰”、“时人称曰”、“京师号曰”等形式,但它们的评论内容无一例外,皆是针对儒学人物而言。
“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汉书·朱云传》)汉元帝好《梁丘易》,要考其异同,就令五鹿充宗与诸《易》家论。史载当时的情形是:“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后来有人推荐朱云跟五鹿氏辩论,朱氏“摄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汉书·朱云传》)。这场关于《易》的辩论最终由朱云胜出,并且因此成为经学博士,迁杜陵令。在这场关于《易》的辩论中,五鹿氏的“鹿角”终为朱云所折,故时人对朱、五鹿两人有上述的评论。
“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史载:“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汉书·韦贤传》)此外,韦贤以经学传家,最终让四个儿子都有成就,二子分别当上太守和县令,少子玄成以明经历位至丞相。这正所谓“黄金不如黑金贵”,“书中自有黄金屋”。
“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汉书·匡衡传》)这则谣谚评论的是匡衡在《诗》方面有造诣。史载匡氏幼时家穷,白天替人放牛劳作,晚上凿壁偷光学习,实属不易。
“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这则谣谚是以经学家张禹为评论对象的,人们认为当时讲《论语》最好的经师就是张禹。史书记载:“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汉书·张禹传》)张禹师从各大名家,最后撮为己旨,所以他在《论语》方面成就最为突出。
“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后汉书·鲁丕传》)这则谣谚的评论对象是鲁丕。元和元年,鲁丕拜赵相,史载门生来就学者常有百余人,故而有如此评论。
“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纵横周宣光。’”(《后汉书·周举传》)史称周举虽然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但是其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正是因为周举才学博洽,深通经术,才赢来人们好评。
“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后汉书·儒林传》)本条谣谚评论的是召驯。召驯,字伯春。史称驯自小精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显然,人们的评论是针对召驯“博通书传”和“志义”展开的。
两汉谣谚关于儒学人物评论的例子还很多。如“解经不穷戴侍中”(戴凭)、“说经铿铿杨子行”(杨政)、“《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五经》纷纶井大春”(井丹)……这些谣谚评论都是说某人在经学上的造诣,兹不一一列举。然而也有一些例外,譬如有一些儒生生于乱世,就不那么走运了。献帝时,就有一群人被评论道:“长安中为之谣曰:‘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后汉书·献帝纪》注引)
以上材料表明,作为民间社会产物的谣谚在臧否儒学人物的时候,往往会遵循着一定的尺度。一些儒学人物凭着自己精通儒家经典而得到民间社会的高度评价,许多人更是由此步上了“干禄之途”。这些人有的精通一经,有的则兼通数经,他们在经学上的成就确实非同凡响。还有一些人一生在儒家经典当中涵泳,坚持经书所教导的安身准则,同样得到了民间社会的普遍赞誉。
三、余论
谣谚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我们通过这些谣谚可以了解和认识当时一些具体的潮流风尚和社会习俗。清人刘毓崧云:“《虞书》曰:‘诗言志。’《礼记》申其说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大序》复释其义曰:‘诗也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观于此,则千古诗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乃近世论诗之士,语及言志,多视为迂阔而远于事情,由是风雅渐漓,诗教不振。抑知言志之道,无待远求。风雅固其大宗,谣谚尤其显证。欲探风雅之奥者,不妨先问谣谚之途。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其关系寄托,与风雅表里相符。”(《古谣谚》序)依刘毓崧所言可知,我们在谣谚里是可以看到其中所表达的“言”与“意”、“下情”与“上德”的。总而言之,谣谚可以成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历史的载体。
两汉时期,人们对经学人物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学问以及道德方面,而在学问和道德的下面还有许多子目。但是不管怎样,人们关注和评价经学人物的时候,很看重儒家的经典,某一个人一旦在经学方面有造诣,往往会赢来人们的高度评价,而且也会使其踏上仕途的门槛,乃至于飞黄腾达。盖自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经学思想就笼罩着学人。一方面,这是王朝统治阶层进行上层建筑的一种设计;另一方面,儒生们也秉持着明经致用的目的投入到经学学习和研究中来。两汉太学的建立及规模的不断扩大,在民间社会和儒生学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班固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赞)毫无疑问,这样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评论人物的取舍标准和价值标准。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明显。儒家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在儒家的意识里,“仕”与“学”是实现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的两大关键。就两汉而言,政治影响了经学,经学同样对政治施加了一定的作用。这就是“仕”与“学”在现实中最为明显的交互作用。正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里巷歌谣对儒学人物的评论才会产生普遍而广泛的反映。因此,两汉时期的尊经思想对人物评论——特别是对儒学人物的评论——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过去在研究魏晋南北朝人物评论的时候,学者们往往借助《世说新语》一书,并从美学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而忽略了谣谚中的部分。事实上,肇端于两汉的谣谚中的儒学人物评论现象一直存在。即便是玄风劲扬和梵音缭绕的魏晋南北朝,当人们对士人进行评论的时候,经学造诣依然是人们评论人物的重要标准。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