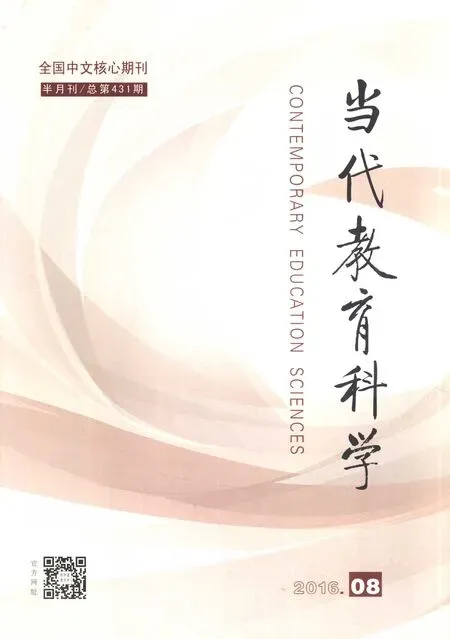社会学视角下特岗教师生活世界探析*
● 宋立华 孙久艳
社会学视角下特岗教师生活世界探析*
●宋立华孙久艳
摘要:特岗教师是我国特岗政策的产物,特殊的岗位和特殊的政策使得特岗教师具有不同于一般教师的特殊之处。用社会学之眼透视特岗教师,从个体行动的角度关注特岗教师,发现他们的身份认同在国家赋予与个体建构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生存状态呈现出悬浮在城市与农村中的流浪者与无根人的特征;专业成长在困境中努力与无奈并存;未来生活具有不同的抉择与愿景。对特岗教师的生活世界进行揭示和描述,可以为修订、完善特岗政策提供鲜活的一手资料。
关键词:社会学;特岗教师;生活世界;探析
宋立华/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
孙久艳/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日常生活世界是人的基础性的世界,它蕴含着巨大的动力。潜入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之中,揭示平淡、无聊的外表背后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事件是如何生成、运转和变革的。特岗教师是我国自2006年起实施的西部“两基”攻坚县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政策的产物。缘于特殊的任务、特殊的岗位和特殊的政策,特岗教师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其它教师的特征。社会学具有“关注特定人群”、“转向事实背后”的研究品性。[1]自美国学者迪尔凯姆(Durkheim,E.)在《社会分工》一书中从社会学视角关注教师职业开始,经由Lortie,Dan C.所著的第一本教师社会学专著《学校-教师:一种社会学的研究》(School-Teacher:A Sociological Study)诞生,时至今日,教师社会学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笔者近年来一直承担着特岗教师岗前以及在职培训课程的讲授,并与他们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因而能够得以走进这个群体,近距离感受特岗教师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喜怒哀乐;用社会学之眼透视特岗教师,从个体行动的角度关注特岗教师,潜入特岗教师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再现其真实的工作生活状态及心路历程,进而为修订、完善特岗政策提供鲜活的一手资料。
一、“我”是谁:特岗教师身份认同分析
“身份”(identity)是人在社会中的一种定位,也是人之存在的归属与行为的依据。对“身份”的追问往往意味着我们“是其所是的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标识、位置及其社会属性的制度安排”的反思。表面看来,特岗教师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称谓:“特岗”指的是特设岗位,即在“两基”攻坚县等偏远艰苦地区现有教师编制内设立的特别岗位;“教师”可以被理解为社会角色或这一角色的承担者,即在学校中担任教书育人任务的专业人员。然而若细究起来,并非如此简单。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特岗教师”作为一种身份标记,是国家政策赋予认定与特岗教师自身建构的双重结果,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一)政策规定下的“我”:责任期待重大的特殊教师
查找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的相关规定是判断群体或个人身份的最简单的办法之一。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原人事部、中央编办下发的《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下称《通知》)是确定特岗教师身份的主要依据。解读《通知》并将其与其它教师进行对比,我们发现特岗教师是一种责任期待重大的特殊教师。
特岗教师的责任期待主要体现在设立的目的上。在《通知》中,明确表示设立特岗教师的目的是“创新农村学校教师的补充机制,逐步解决农村学校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从这个表述中可以看出国家对特岗教师的设立的责任期待重大,希望能够通过特岗教师这个高素质群体的引入改变农村教育的师资结构进而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解决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现状。可以说,这是自建国以来我国教育部门历年招聘教师中赋予责任、给予期盼最大的一次,任重而道远将伴随着特岗教师的群体发展。
特岗教师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特殊的准入、退出与管理机制上。从准入机制上看,特岗教师是“采用公开的形式,在经历自愿报名、考试和考核、体检、岗前培训、教师资格认定等程序之后与政府签订协议,派遣上岗。”这种通过每年进行的公开考试招聘获得聘任资格的准入形式不同于其它教师的直接由教育局或学校招聘的形式,相对来讲,更为开放、透明、常态、公平。从退出机制上看,聘期结束后,“对考核合格,自愿留在本地学校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上编制、核定工资基金等手续,并分别报送省、市(州)人事、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同时将其工资发放纳入当地财政负担范围,保证其享受当地教师同等待遇。”也就是说,特岗教师的留任与否既与本人意愿有关,也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关,这明显不同于以往教师身份的“铁饭碗”特征,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从过程管理上看,聘期内“对不适合继续在教师岗位工作的,应及时将其调整出教师队伍并相应取消其享受的相关政策优惠”。这个规定改变了教师“只进不出”的现状,体现了过程之中的管理。
(二)“我”眼中的“我”:介于正式教师与代课教师之间的“临时工”
个体的自我认同通常是在将自身同他人或某个群体进行对比时所意识到是其自身而非他的一种“是其所是”的意识,它与“人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什么对他们有意义的理解相关”。[2]在学校中,特岗教师可以参照对比的群体是正式教师与代课教师(在部分特岗教师存在的偏远地区,代课教师并未完全清退)。从工作的性质来说,三者并无太大的差别,都是同样担负着一定的教育教学任务。但是国家认定的身份以及伴随法定身份而来的各种差异使得大多数特岗教师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知、未来发展的期盼以及专业情意等方面表现异于其它群体教师,他们将自身定位为“介于正式教师与代课教师之间的临时工。”“临时”这个词一方面表明这份工作并不是长久稳定的,可能会因为自身或他人的原因而失去教师这个身份,也可能变为正式教师;另一方面说明这份工作的待遇虽远远高于代课教师,但也并非与正式的教师等同,仅仅是“临时客串”了教师的角色,履行教师的义务。这样的身份认同在访谈以及调查中多有所反映:“先这么干着吧,还不知道三年后能否转正有编呢”;“我们的学历比那些教师要高,工作却是一样的甚至更多,工资待遇也不同,我们就比代课老师强点”;“别的教师能够评职晋级,我们特岗教师聘期内却不行,明显是差别对待”;“怎么说呢,那些有编的教师人家是铁饭碗,我们是纸饭碗。要是落不了编制,我们就是白付出三年时光”。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特岗教师受制于政策约束时的无奈与不满以及对这种“特殊”“临时”身份的敏感。
特岗教师是特岗政策的产物,它在身份标识上带有不同于我国其他类型教师群体的特征。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家政策规定下的特岗教师寄托了国家层面的殷殷期望,责任重大,而且准入机制公平,过程管理严格,退出机制灵活,具有不同于以往其它教师的明显特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教师。但是特岗教师自身的身份认同并未明显感到这种“责任期待”,反而是政策的“特殊”使其产生了一种“临时”的感觉。这样的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为特岗教师制造了一个不甚满意的现在与不确定的未来,使大多数特岗教师陷入窘迫的境遇。而“对一个具有资格能力完整的社会成员来说,窘迫意味着某种威胁,”[3]意味着痛苦以及对痛苦后的麻木或者痛苦反思后的多种发展可能与抉择。
二、“我”的生存状态:悬浮在城市与农村中的“流浪者”与“无根人”
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4]而“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5]当特岗教师“审视”“反思”自身的生存状况时,他们发现自己是悬浮在城市与农村中的流浪者与无根人。
“流浪者”通常是指因经济能力不足被迫居无定所、到处漂泊的人。“无根人”是指没有基础或基础缺失的人,二者同指一种落魄潦倒、无依无靠的状态。用这两个词形容特岗教师意指的是特岗教师的精神层面上的困顿与漂泊状态而非实际的形体存在状态。在访谈中,特岗教师纷纷用不同的话语表达了这种精神上的“流浪”和“漂泊”:“我很少与当地人交往,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我很迷茫,不喜欢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工作,可是又没有办法”;“虽然住在这里,但是没有一丝家的感觉”;“如果有可能,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到城市中教学”;“我经常上网,关注一些新鲜的事情,这里太落后了,死气沉沉的。当然了,我的朋友也多是以前的同学,在这能说得来的很少”……实际上,特岗教师是一群在当地现实中缺少立足点的人,他们在基本物质得到满足的表象下精神世界是贫困的,无论是与当地人相处还是与城市人相处,普遍有一种强烈的局外感和边缘感。此时,虽然没有形体的流浪,但精神的流浪和漂泊,却在巨大的孤寂感主导之下强烈地存在着,并由此导致剧烈的精神痛苦。
特岗教师的这种“流浪”与“无根”并非是特岗教师自身造成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我们知道,政策规定设立特岗教师的地区基本都是艰苦的农村地区,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使得城市和农村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在各种条件上存在着天壤之别;基于城市教育的教育体制使得农村教师与城市教师差别很大。虽然特岗教师既有来自农村在城市大学求学后又回到农村的,也有一直生活在城市,大学毕业后从事农村教育事业的,但不管是何种来源,他们所受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城市教育或者说是“离农”的教育。大学期间又长期侵染在城市文化中,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已经打上了城市的烙印,与工作所在的贫困地区有着明显差别。在当地人看来,他们是和当地人不同的“城市人”“大学生”,有着和当地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在那些仍旧留在城市中的老师和同学以及其它城市人看来,他们就是“农村人”,是低于城市教师好几等的“农村教师”。工作日和节假日,他们往往做“候鸟状”,奔波在学校与家之间。而这样的“流浪”和“无根”给特岗教师带来的痛苦是深层次的:一面是他们认可并追求向往的城市价值观、城市生活方式和优厚的待遇,可望却不可及;另一面,是他们厌弃的农村价值观、农村生活方式和贫瘠的物质待遇,实实在在环绕周围。通过多年的努力读书,高考金榜题名,似乎愿望达成,然而却是镜中月、水中花,复归原点。他们和众多的农村教师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既是播撒城市文明的激情满怀的‘传教士’,又是远离城市的‘失落天使’”,[5]是时空与价值观断裂之中的城市化的乡村教师。努力——实现——短暂繁华之后复归原样,这种痛苦宛如黄粱一梦,昭示着他们曾经奋斗的失败以及当今精神上的“流浪”与“无根”。
三、“我”的专业成长:困境中的努力与无奈并存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对专业成长的渴求与期盼是每一个教师心灵深处最热切的呼唤和美好愿望。然而,对于特岗教师来说,实现这个愿望却是一个远比其他教师更为艰难和漫长的过程,“努力”和“无奈”是其中最为明显的行为和感受。“我响应国家号召、满怀着热情来到农村学校,希望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为落后的农村教育做出贡献。这既是我自身价值的体现,也是青春无悔的凯歌。可惜,要想成长困难重重……”一位特岗教师在深度访谈时发出这样的慨叹和无奈。与城市教师相比,特岗教师在专业成长中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新手教师的一般困境。特岗教师多数是新手教师,刚刚经历由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在教学内容、班级管理等方面处于从头开始进行摸索的状态,应对教育教学可以说是手忙脚乱。二是适应农村教育特殊性的知识和技能缺失。比如地方性知识,它是由地方生产经验、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构成的一个符号系统,是地方居民为适应当地环境创制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意义系统和生存智慧。[6]地方性知识的缺失使得特岗教师在适应当地生活方面存在困难,在与当地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上存在障碍。三是农村教育的特殊环境对教师发展有重要影响。这种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贫瘠的文化氛围、落后的经济条件、大量的留守儿童以及家庭教育的薄弱等都对特岗教师的专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身处重重困境之中特岗教师努力着,试图走出困境。然而,他们自身能力有限,外部相应的引导与支持不仅难以到位,还以各种形式加重了这种困难。比如大多数特岗教师教学任务繁重,一人担任多门课程或多个年级的教学任务、班主任工作,甚至有些教师教非所学。繁重的任务加之新手教师的角色使得特岗教师疲于应付。再如专业发展外在支持不到位。缺少优秀教师的指导,专业成长同伴互助力度不强;缺乏外出学习、培训等机会,专家引领不足。对于许多特岗教师来说,专业发展更类似于“闭门造车”“自我琢磨”。这也给特岗教师带来了极大压力。有研究表明,特岗教师主观感受到的教师职业压力不仅高于一般青年教师,同时也高于农村教师。[7]所以,尽管特岗教师囿于任期内考核和聘期满后入编等外在要求的限制,无论从内心来讲还是从外在的名分需要来讲,都是非常努力地争取实现专业的快速成长。然而,现实的条件限制了发展的速度和可能达到的高度,无奈的情绪暗自滋生并蔓延。
四、“我”的未来生活:不同的抉择与愿景
聘任期是个敏感的词语,它往往意味着时间限度内应该做的事情以及期满后何去何从的重新选择。实质上,对于特岗教师而言,当初选择成为特岗教师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之中的被迫行为,是在衡量各种可能情况下的“最优选择”。通过访谈和调查得知,很多特岗教师是在多种就业途径无望的情况下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或考研没有成功,或在城市中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没办法,城市学校留不下,改行又做不来。家里还有一定的经济负担,先就这么干着再看吧”。“我是从农村出来上大学的,现在又回到农村,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吧。”这样的认同状态和抉择理由是受我国大学生就业大背景影响的:最优秀的高中生不会选择师范院校;师范院校的优秀学生如有可能首选是公务员或者那些薪金待遇高的职业而不是教师;能够成为城市教师决不当农村教师。所以,在特岗教师当中流传这样的话:“好人(能力强的优秀人才)不愿意考,孬人考不上”。在这样的选择意愿下,许多特岗教师自身并没有相应的自豪感和责任感。相反,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理性与迷茫。理性使得他们做出了最现实的选择,迷茫则是基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诸如婚恋对象的选择范围狭窄、物质待遇不高、未来发展前途暗淡等)对未来生活何去何从的考虑,亦或是说对三年期满后不确定的打算。通过调查得知,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打算,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将三年的特岗生活作为一个跳板,是暂时积蓄力量的时期。持有这样打算的特岗教师往往在完成基本的教育教学任务之后将精力用于研究生、公务员的备考或者其它可能的出路。一旦目标实现,会毅然决然地辞职离去。二是将教师视为终身职业,在努力提高专业水平的同时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准备期满获得编制后调动到条件较好的学校中去。三是因为诸如结婚或家庭等因素的影响,打算扎根在此处。这样的教师能够更加主动地融入到当地学校和生活中,努力成为“当地人”。当然,不管对未来生活的何种打算,毕竟只是一种“预设”,能否实现,还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抉择和愿景主导了特岗教师现实的行为和努力的方向。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特岗教师作为一个特殊政策的产物,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确呈现出不同与一般教师的特殊之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不同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现状使得各地的特岗教师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因此,从普适性的角度来看,本文所揭示的特岗教师的生活世界并非是每个地区、每个特岗教师所共有的。然而我们无法否认这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并且这种存在在一定范围内正在蔓延。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政策制定者、基层实践者还是教育研究者都应予以重视,否则“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8]最终可能导致特岗政策的实效性以及结果与初衷背离。
参考文献:
[1]王丽琴,蔡方.从师范生到骨干教师——关于教育研究在教师专业成长中地位与作用的个案考察[J].当代教育科学,2004,(3).
[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8.
[3][英]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第2版)[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3.
[4][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0.
[5]高小强.乡村教师的文化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09 (20):53-72.
[6]潘洪建.地方性知识及其对课程开发的诉求[J].教育发展研究,2012,(12).
[7]朱艳丽.农村“特岗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2.
[8]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J].读书,2002,(7).
(责任编辑:刘君玲)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12年青年基金“从功利主义到公共责任:我国当代学校改革的价值范式转换研究”(课题号:CFA120127)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