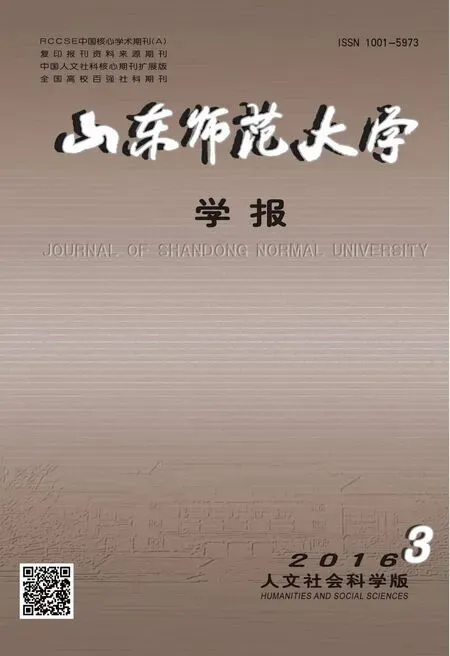静穆之下:隐匿的狄奥尼索斯——温克尔曼的《拉奥孔》*
高艳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001 )
静穆之下:隐匿的狄奥尼索斯
——温克尔曼的《拉奥孔》*
高艳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001 )
温克尔曼关于拉奥孔群像的描述,其前后期有所不同。早期强调拉奥孔群像的静穆的特征,后期则强调它的表现性。但两者之中,皆可见温克尔曼关于希腊精神的阐释中隐而未现的狄奥尼索斯之维。早期温克尔曼之所以无视拉奥孔群像的表现性特征,是因为他投身于启蒙运动的德国对抗巴洛克的文化运动之中。
温克尔曼;拉奥孔;狄奥尼索斯;尼采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3.008
在1755年出版于德累斯顿的《希腊美术模仿论》(GedankenüberdieNachahmungdergriechischenWerkeinderMalereiundBildhauerkunst)中,温克尔曼以“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形容《拉奥孔》*1506年1月14日,一个叫做Felix de Fredis的人在罗马郊外发现一座雕像。据判断,很可能是罗马皇帝Titus(79-81A.D.)的地下浴室。发现之初,教皇朱利斯二世携建筑师Giuliano di Sangallo和米开朗基罗到现场察看,认为正是普林尼所礼赞过的拉奧孔群像。温克尔曼在德累斯顿初见其石膏复制,到了罗马之后又见到青铜制作的罗马复制品。群像(参图1)的希腊特征。该命题常被视作温克尔曼之希腊阐释及其美学精神的特质所在,而事实却不尽然。温克尔曼在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中,对《拉奥孔》的描叙已有明显的变化。其一,温克尔曼认为拉奥孔由于过度炫技而失去了崇高的情韵,从属于优美风格。当美的表象以过度精细的表达为特征,崇高感也就从中滑落。拉奥孔不再是崇高风格的代表。其二,拉奥孔被界定为经过理想化处理的自然肖像。“人们在拉奥孔中发现由理想和表现所装饰过的自然。”*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366.其三,《希腊美术模仿论》强调拉奥孔抑制感受的激烈性而欲显其静穆的一面,《古代艺术史》则认为《拉奥孔》是表现性的:“拉奥孔表现的是自然间最高的悲哀”*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324.,揭示人的激情与巨大的痛苦。
凡此种种表明,温克尔曼后期了然于《拉奥孔》的非静穆特征,发现了其中关于痛苦的叙述以及自然主义的表现方式。而由此追溯并抉发,可见温克尔曼的希腊文化阐释中隐而未现的狄奥尼索斯之维。
一、拉奥孔:作为表象的痛苦
任何一种对视觉作品以文字为媒介的描述都有可能导向新的暗示。温克尔曼是从拉奥孔的姿势和表情中读出了希腊的精神方式——其情感如此敏感、深沉,从而必有痛苦的强烈表征,而其精神又如此超然、沉静,从而又从痛苦中超逸出去。
“在强烈的痛苦(Leiden)之中……我们无需审视脸和其他部分,而只要在受着疼痛的、收缩的下腹就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全部肌肉、肌腱以及整个人的疼痛(Schmerz)。”*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Berlin und Weimar:Aufbau-Verlag, 1982, pp.17-18.拉奥孔上身肌肉的收缩表示着遭到剧痛袭击的迹象。在此,温克尔曼的语调是暗示的、说服性的、雄辩的,提醒并说服读者:拉奥孔在遭受痛苦。他同情式的精神方式以及文学性的渲染又使得其阐释显得无懈可击:“拉奥孔受着苦,但是他如同索福克勒斯的菲勒克忒忒斯那样受苦:他的困苦进入到我们的灵魂之中,但是我们也愿望,我们像这个崇高的人一样,忍耐这困苦。”*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p.17-18.但是,身体之痛本身并未被具体呈现,而被表示、被指涉的仅仅是温克尔曼对之的感受。在此,痛苦是作为认识拉奥孔的概念,而且痛苦更是一个中介。《希腊美术模仿论》对《拉奥孔》意在阐说超越痛苦的理性精神,作为障碍的痛苦是理性精神得以考验自身存在的工具。痛苦的强度也正好用以标示超越的强度,痛苦无论多么强烈,却是工具性的,是有待克服之物。
在《希腊美术模仿论》中,温克尔曼对呈现于脸部的痛苦的描述较为简略,他感兴趣的是拉奥孔雕像脸部抵御痛苦的性质以及从中呈现的节制的心意状态,有意略去了脸部的痛苦反应的细节。温氏又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提到尖叫。他说道:“他没有像维吉尔在他的拉奥孔中所吟唱的那样发出可怕的尖叫。嘴之张开在此是不允许的;不如说,这尖叫是一个惊恐的、不安的叹息。”*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p.17-18.尖叫作为痛苦最强烈的表征,经温克尔曼的修辞,转化为与之相异的东西——叹息。
温克尔曼时而将拉奥孔比作菲勒克忒忒斯,时而与维吉尔笔下的拉奥孔对峙。无论是索福克勒斯的菲勒克忒忒斯、维吉尔的拉奥孔,都在悲剧中、舞台上、史诗中发出实质性的尖叫。尖叫是表达痛苦的前语言状态,它既是身体对痛苦的最直接的回应,本身又具有语言表现的样态。索福克勒斯的菲勒克忒忒斯在蛇毒发作之时,大声喊叫、咒骂自己的命运,间歇性地昏倒,而维吉尔的拉奥孔放纵哭喊:“他那可怕的呼叫声直冲云霄,就像一头神坛前的牛没有被斧子砍中,它把斧子从头上甩掉,逃跑时发出的吼声。”*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第33页。维吉尔这样写道:“两条蛇就直奔拉奥孔而去;先是两条蛇每条缠住拉奥孔的一个儿子,咬他们可怜的肢体,把他们吞吃掉;然后这两条蛇把拉奥孔捉住,这时拉奥孔正拿着长矛来救两个儿子,蛇用它们巨大的身躯把他缠住,拦腰缠了两遭,它们的披着鳞甲的脊梁在拉奥孔的颈子上也绕了两圈,它们的头高高昂起,这时,拉奥孔挣扎着想用手解开蛇打的结,他头上的彩带沾满了血污和黑色的蛇毒,同时他那可怕的呼叫声直冲云霄,就像一头神坛前的牛没有被斧子砍中,它把斧子从头上甩掉,逃跑时发出的吼声。”这个无辜地成为诸神相争的牺牲品的拉奥孔,其痛苦的丑态毕露。维吉尔是站在希腊人的角度看待此事,拉奥孔所遭之苦似罪有应得,故而并不惮于让拉奥孔的形象受损。这其实就是温克尔曼用其“叹息”所暗示的身体之痛的极境的另一种表达。
到了《古代艺术史》,对于痛苦反应本身的描述占据了本位。在此,温克尔曼几乎是在投入地观察一具受苦的人体,而不再受其有待发明的理念所左右。同样是描述拉奥孔的身体部位的痛苦,《古代艺术史》的描述极其详尽,虽然充满同情,语调还是显出冷静、客观与分析性:“拉奥孔是最强烈的痛苦的形象,这显现于他的肌肉、腱肉、血管之中。因蛇的致死一咬,毒素进入血液,这引起了血液循环的最强烈刺激,身体的每一部分似乎因为痛苦而紧张着。”*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167.温克尔曼描述了蛇的毒液在人体上发作的过程,描述中对肌肉、腱肉、血管的区分,其本身成为极度自然主义的描摹。此时被痛苦席卷的拉奥孔已不再庄严与静穆,而仿佛是痛苦反应的分析样本。
尤其是“这引起了血液循环的最强烈刺激”一句,更令人陡然间感到如此突兀,“血液循环”、“刺激”一词的出现,分明是医学话语的悄然闯入。这种话语与《希腊美术模仿论》的超越性的精神话语如此不同,一者是自然主义的,一者则是理想主义的、浪漫化的。
医学话语与审美话语的结合也许不仅仅是巧合。有人指出,在18世纪,医学话语和美学话语共同关注人体并且皆从人体的痛苦下手。*Simon Richter, Laocoon’s Body and the Aesthetics of Pain : Winckelmann, Lessing, Herder, Moritz, Goeth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33.但即便如此,医学与美学之间的不同也仍然是明显的:医学揭示可怕的残酷,而美学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尝试对痛苦进行转喻(trope)。温克尔曼曾一度立志医学,在耶那大学修过医学,应该熟悉名为《论人的身体的感受与刺激》(Departibusvorporishumanisensilibusetirritabilibus)的演说,其于1756年译为德文。该文于1753年(《希腊美术模仿论》出版前两年)出自一位卓有成就的德国生理学家哈雷(Albrecht von Haller)之手 (据称, 哈雷之于生理学,相当于牛顿之于物理学领域),总结了几百年来研究动物各部分如何对痛苦做出反应的实验。
与此相类,《古代艺术史》中对《拉奥孔》的描述则如同是一桩有关人体如何对痛苦做出反应的研究。温克尔曼周全地描写了拉奥孔的脸部,包括上嘴唇、鼻孔、额头、眉毛、眼皮等脸部各器官的反应:“拉奥孔的样子是万分凄楚,下唇沉重地垂着,上唇亦为痛苦所搅扰,有一种不自在所激动,又像是有一种不应当的、不值得的委曲,自然而然地向鼻子上翻去了,因此上唇见得厚重些,宽大些,而上仰的鼻孔,亦随之特显。在额下是痛苦与反抗的纹,……因为这时悲哀使眉毛上竖了,那种挣扎又迫得眼旁的筋肉下垂了,于是上眼皮紧缩起来,所以就被上面所聚集的筋肉遮盖了。”*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4-175页。Cf. 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p.324.在其“佛罗伦萨手稿”中,温克尔曼更提到拉奥孔脸部因为痛苦而扭曲的鼻子:“脸部的鼻子在表现痛苦之时无法保持直的向上的表面。”*Fcited in John Harry North, Winckelmann’s “Philosophy of Art”:A Prelude to German Classicism,( Cambridge Scholar publishing,2002),p.131.温克尔曼这种细致的描摹甚至引发过面相学家J.C.拉维特(Johann Caspar Lavater)的兴趣。*Cf. Henry Hatfield,Winckelmann and his German Critics,1775-1781·A Prelude to the Classical Age,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1943 pp.109-110.
温克尔曼认为,拉奥孔像兼有自然和理想的双重摹写,是“理想和表现所并装饰过的自然”*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366。如果说,《希腊美术模仿论》重于其理想精神的摹写,《古代艺术史》则多发掘其人类痛苦反应的自然主义描述。
二、隐匿的狄奥尼索斯
温氏对痛苦及其痛苦表象具有高度的知觉力。当温克尔曼描述拉奥孔遭受的痛苦时,几乎触及后来为尼采所开掘的希腊酒神的迷狂,但温氏侧身而过。
如果说尼采从悲剧中见到人类在悲剧命运中个体性消亡的过程,那么温克尔曼的悲剧英雄却在痛苦中经历了个体化的最高阶段,超越肉体痛苦的个体确立了理性主体,而这个主体一边受苦,一边对自己的命运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清晰的觉照。温克尔曼的拉奥孔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如此。拉奥孔即便处于因肉身之痛而陷入自失的状态中,仍保持着理性的内视,从而其外观(Schein)得以保持平静,静穆的表象确立。《希腊美术模仿论》如此描述拉奥孔:“为了将这特别之处(即痛苦的表情)与灵魂的高贵结合在一起,艺术家赋予他一个动作,这动作是在这巨大的疼痛中最接近于宁静的站相的”*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18.,“仿佛大海虽然表面多么狂涛汹涌,深处却永远驻留在宁静之中”*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1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克尔曼的由拉奥孔所引申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精神其实正与尼采所称的阿波罗式的理想相关,亦接近叔本华的描述:孤独的人平静地置身于苦难世界之中,信赖个体化原理。
即便他在拉奥孔描述中清晰地指向自己的文化理想,赫尔德还是发现其中对痛苦与死亡的深刻觉知,并从中解读出“我痛故我在”。布克哈特认为希腊人是对痛苦感受至深的民族。尼采认为希腊人又具有极强的悲剧意识。实际上,这幽暗而生动的部分的关注,并非完全从温克尔曼的思想中缺席。
尼采在他的一份笔记中说道:“‘古典的’这一概念,当温克尔曼和歌德形成它的时候,既无法解释狄奥尼索斯因素,也不能将它从自身中排除出去。”*[美]C.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38页。实际上,虽然对静穆表象投入全部赞美,温克尔曼并未对表象下面的汹涌视而不见,也未将这种质素从拉奥孔雕像的表征中排除出去。他在描写《拉奥孔》时,以海作喻,写道:“仿佛大海虽然表面多么狂涛汹涌,深处却永远停留在宁静之中。”*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17.温克尔曼对这汹涌的表面的描述,时而又以另一种描述出现:“拉奥孔的肌肉运动被推到了可能性的极限;它们如同山峦描画自己,为了表达在愤怒和抵抗之中的极端的力。”*Johnann Winckelmann,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s. I&II, translated by G. Henry Lodge, Boston:James R. Osgood and Company,1880, p.338.
温克尔曼未命名的大海的狂涛,像极了尼采酒神精神的洪波。同样是以大海作喻,尼采写道:“为了使形式在这种日神倾向中不致凝固为埃及式的僵硬和冷酷,为了在努力替单片波浪划定其路径和范围时,整个大海不致静死,酒神精神的洪波随时重新摧毁日神‘意志’试图用来片面规束希腊世界的一切小堤坝。”*[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1页。温克尔曼的“拉奥孔”以意志规束精神的堤坝,但温克尔曼的希腊精神从未凝固为埃及式的僵硬和冷酷——这也是温克尔曼本人所批判的——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狄奥尼索斯的生动有为。他这样形容“拉奥孔”:“这灵魂是宁静的,但同时又是生动有为的,是静默的,同时又不是冷淡的或是昏沉的。”*Winckelmann,“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in Winckelmanns Werke in einem Band, p.18.因此,既静默又激烈的“拉奥孔”既具有尼采所言的阿波罗精神,也拥有狄奥尼索斯精神的质素。
实则,温克尔曼从未视此静穆超然的品质为希腊人的天然,而是一种属于智慧的伦理特征。这种阿波罗精神是在与汹涌的情感的洪波的抗争中挣得。温克尔曼并非对幽暗的部分视而不见,而是未将之视为希腊人的本质构成。
三、何来静穆?
正如《古代艺术史》所察见,拉奥孔雕像以精细的手法表现痛苦,而又极富动态和戏剧性,因此被后世称作“希腊巴洛克”。那么,德累斯顿的温克尔曼因何将其作为“静穆”的集中表征?
现在,不妨回到温克尔曼在德累斯顿的“大花园”(Grösser Garten)的场景。温氏曾于此间盘桓。在其半暗半明的阁室中,雕像的细节几乎难以被真正观察到,但它足以唤起温克尔曼的想象以及内藏于心的对古代希腊如同前生般的回忆。可以想见,在他或内视或向雕像周围的空气凝视的观看中,温克尔曼下意识里关于希腊文化的静秘、单纯、崇高的主要论点浮现了。于是,动荡、激烈、挣扎的拉奥孔,繁复、精细、自然主义的拉奥孔,在他这里却倒置般地成为了“静穆”的集中表征。
温克尔曼的这种潜意识来自于他早年的阅读。充满元音的希腊文曾一度占据着温克尔曼全部的精神世界。温克尔曼重荷马而轻品达,喜爱索福克勒斯,热爱柏拉图和色诺芬,视希腊黄金时期的文化、哲学为最佳典范,他同样心仪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不同于同期法国人在希腊悲剧和荷马史诗中看到残酷、血腥,温克尔曼从中发现的却是一个光明、节制、静穆的世界。荷马在描写一切混乱时却依然让明喻绽放的文本,其超然笑言、目光遍及一切物事的语调同样征服了温克尔曼。
更为关键的是,温克尔曼从希腊艺术中拈出“静穆”与“单纯”,其实是他反对巴洛克的文化策略的一部分。虽然在18世纪中期,对巴洛克和罗可可的反抗已经在法国和意大利展开。罗马地区的绘画已开始从古典寻找资源,而法国似乎从未完全拥抱过巴洛克,在路易十四时期即已发展出自己的新古典主义形式,如普桑。温克尔曼理应知道这些变化,然而,当时他所在的德国的萨克森,仍残留着17世纪的巴洛克趣味。巴洛克艺术多追求自然主义的效果,以激情为表达内容。温克尔曼对此屡有批评,在《希腊美术模仿论》中,以拉法奇(La Fage)的绘画为例证,他嘲笑巴洛克艺术中的一切皆在动荡。他希望引入古代希腊这巴洛克的“他者”,为自己的时代迎来一个庄重的艺术年代。
但略显反讽的是,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家贝尔尼尼,却是不折不扣的《拉奥孔》模仿者。他的《圣特雷萨》圣女的姿势与表情与拉奥孔次子酷似,《月桂树》的动荡的姿态又与拉奥孔雕像整体的构图近似,他的一些雕像造型甚至被称为“基督教的拉奥孔”(christian Laocoon)。而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在这种显见的裂缝之中,温克尔曼试图为巴洛克文化提供解毒剂的意图才显得更为昭著。有意或无意的误认(misrecognition )正是其文化策略的诡计。
实际上,到了《古代艺术史》,温克尔曼似乎发现了更完善的巴洛克的他者。这就是《阿波罗》和《尼俄柏》。他论及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像,赞其激情的表达被抑制到了最低的限度,愤怒只现于鼻腔,轻蔑只现于嘴唇,因而拥有“崇高的精神,柔和的灵魂。而阿波罗的这种崇高,是拉奥孔所没有的”*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 p.115.。在尼俄柏及其女儿遭受死亡威胁的场景的雕刻中,温克尔曼注意到她们的表情,与其说是抗争的庄严,不如说是淡漠:“在这种状态中,感受和思考停止了,这就像淡漠,肢体或面部不动。”*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166.淡漠和节制恰恰是希腊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因而这两具雕像更进一步扩充了希腊艺术精神中的伦理精神内涵。如是,拉奥孔所指涉的“他者”世界,在阿波罗和尼俄柏的雕像中得到更加完善的具身化。正因如此,在《古代艺术史》中,温克尔曼已不再需要拉奥孔作为他所要解读的希腊精神的符码。《希腊美术模仿论》通过逻辑与修辞的努力而最终论证成功的希腊精神,在罗马时期归附于别的伟大的希腊杰作,《拉奥孔》也随之不再是表述的核心对象,温克尔曼的观感反而更为客观,观点也更加坦诚。由此可见,温克尔曼希腊阐释中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压抑正是其文化策略的必然结果,及至发现更为合理的巴洛克的“他者”,他才不惮于道出《拉奥孔》的非静穆、非理想化的自然主义的一面。
四、温克尔曼与尼采
尼采心目中的温克尔曼,停留在《希腊美术模仿论》,没能注意到《古代艺术史》中对希腊艺术的描述和阐述的变化。这多半是因为《希腊美术模仿论》的观点和风格几乎旗帜一般地鲜明。相形之下,《古代艺术史》中的观点则包裹在混杂的文体中,不易辨识。
尼采被认为是发现了希腊经验的古代的、地下性的、迷狂维度的人。“他对温克尔曼的阿波罗理想(那种带有宁静美和静态和谐的雕像)的狄奥尼索斯式攻击,被证明在从一种古典的希腊模式到一种本原的[希腊模式]的转变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对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解释(解释成‘本原的’)构成了一种反古典主义,一种对德国人关于五世纪雅典的传统图景(古希腊文化的最高峰)的无拘无束的攻击。”*[美]C.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37-338页。尼采攻击温克尔曼的希腊阐释,认为温克尔曼(以及后来的歌德)仅仅见到希腊文化的一半——阿波罗精神,而未能品赏希腊文化的更为本原的一面,即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发现的酒神精神。他认为,温克尔曼仅仅强调阿波罗显示的秩序、和谐和宁静,但低估了阿波罗精神底下的本能力量,即希腊人以狄奥尼索斯表征之物。
尼采认为,温克尔曼的“感受性在历史上的影响,就是阻塞了任何前往苏格拉底思想之土地性源泉的真正通道。没有了这种土地方面的联系,就无法期望任何德国人能把握住真正希腊的古代经验的种种深层因素了”*[美]C.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47页。。温克尔曼在这隐蔽的地底入口设置的屏障,正好为尼采提示了可能的通道所在,“阻塞”实则构成了道路自身被隐蔽的标记。
在温克尔曼的感受中,拉奥孔式的静穆与宁静并不能掩盖其深处的激烈情感。温克尔曼在希腊雕像上所见的自我克制的希腊精神之背后恰恰是人性的冲动和激情的复杂景象。若说中道的力量在于在两极之间寻找平衡,那么对两极的深刻意识是其前提。温克尔曼对所谓希腊经验的暗面,即不受道德控制的直觉、感受和欲望的一面,并非没有意识,惟并未命名而已。但,温克尔曼所见到的希腊经验的另一面,却又非尼采的狄奥尼索斯所能涵盖。除了对狄奥尼索斯式的力量有所暗示之外,温克尔曼所感知的希腊经验的土地性的方面,其幽暗的自然涌动的生命活力,还在于其梦幻般的爱欲。在温克尔曼笔下,少年酒神“踏在生命的春光和丰裕的边界中,骄奢的情感正如植物的嫩叶在萌芽,他介于睡眠与行走之间,半沉迷在有着剧烈光亮的梦中,开始收集和纠正他的梦里的图像;他的形象充满了甜蜜”*Winckelmann,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Darmstadt: Wissensch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2,p.160.。他是轻松、欢乐、甜蜜的,在半明半暗中沉醉或迷狂,其源起并非是痛苦,而是梦幻。
有人指出,温克尔曼与其说是酒神的信徒,不如说是柏拉图的第俄提玛的信徒。*Frede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Leibniz to Less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9,p.194.听从第俄提玛,温克尔曼相信,一切欲望都是爱的形式,一切爱欲源自某种朝向永恒的冲动;美是爱的目标。温克尔曼所发现的希腊人的迷狂在于希腊人对爱与美的投身与想象。他自身对美少年的同性之爱使得他与古代希腊人之间建立深刻的同情,也使得他的文化阐释中明显地嵌入个人性情的因子(如他对男性雕像的热情明显高于女性雕像)。
如果说,尼采是在康德和叔本华的影响下以自然和理性之间的二元论看待日神和酒神的区别*Frede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 Leibniz to Lessing, p.194.。在其中,酒神的领域是感性的欲望,欲望和感受是给定的和自然的,不同于或优先于理性领域;那么,温克尔曼的柏拉图遗产却在于,他从未在非理性意义上解雇欲望和感受或将其当作盲目的自然力,而将理性和感受视作相粘连的整体。如同柏拉图《斐德若篇》和《会饮篇》所示,欲望和感受本身是经过理性化了的,是内在精神冲动浮现到形式领域的表征。这即是说,温克尔曼与尼采是从不同的哲学观点接近希腊文化的。“不同于尼采以叔本华的意志学说和二元论接近希腊文化,温克尔曼则以柏拉图的理智主义和一元论来阐释希腊文化。”*Frede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Leibniz to Less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9,p.195.温克尔曼以《拉奥孔》为例证的理性精神(阿波罗精神),从未将狄奥尼索斯从其自身中分离出去。
责任编辑:寇金玲
Hidden Dionysus Element under Stillness:On Wincklemann’sLaocoon
Gao Yanpi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001)
Winckelman describeds the Laocoon sculptures in his 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 as well as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But in the former, he regards it as a property of stillness, while, in the latter, he discovers the pathos expressed in it. Actually, we can find the hidden Dionysus element in both of them. In order to disclose this,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Winckelmann’s description in a close way as well as a necessary comparison between Nietzschze and himself. Besides, mention is to be made that the reason why Wincklemann failes to mention the expressiveness in Laocoon in 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 lies in his intentional tactics being against Baroque culture in his era.
Winckelmann,Laocoon, Dionysus element , Nietzsche
2016-02-20
高艳萍(1978—),女,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B83-09
A
1001-5973(2016)03-01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