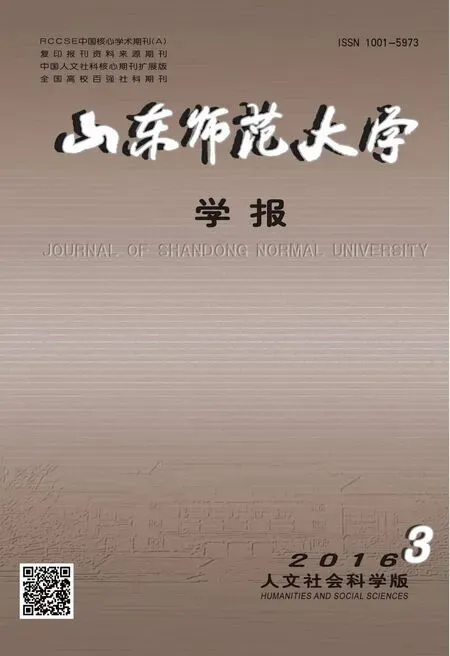文革电影的乌托邦色彩*①
陈吉德
(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
文革电影的乌托邦色彩*①
陈吉德
(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
文革电影的乌托邦主要体现在对理想社会蓝图的构建,这种乌托邦既存在于银幕之内,也存在于银幕之外。但在建构理想社会蓝图之前,文革电影总是先展现现实世界中的诸多问题,比如战争、阶级斗争、疾病、自然灾害等。本质上,文革电影的乌托邦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它重阶级性而轻人性,重集体而轻个体,重精神而轻肉体。这种乌托邦的出现主要与当时狂热的文革运动和深远的中国革命史有着必然联系。它营造了“全国一片红”的大好形势,同时也遮蔽了触目惊心的现实。
文革电影;乌托邦;表现;本质;成因;利弊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3.009
1516年,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大法官在《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乐天福地般的美好景象。从此,“乌托邦”(utopia)一词流行开来。在希腊语中,ou相当于not(不),eu相当于good(好),所以utopia既可以指outopia(乌有之乡),也可以指eutopia(乐天福地),或者二者含义兼而有之。其实,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乌托邦在东西方古已有之。东方可以追溯到《礼记》,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之前的希伯来先知。到底什么是乌托邦?《牛津英语词典》指出了其四种含义:“(1)托马斯·莫尔所描绘的一个想象中的岛,岛上有一个具备完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理想社会;(2)任何想象中的或不明确的、遥远的国家、地域或场所;(3)在政治、法律、风俗、生活状态等一切方面都完美无缺的地方、国家或场所;(4)一种不可能的理想计划,尤指社会改革计划。”*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485.乌托邦的特征有二:一是完美;二是“不在场”。完美在于它能超越现实;“不在场”指在现实中不存在。在我看来,乌托邦的“不在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乌托邦的理想超越现实,这是一种向前看的积极的乌托邦,“它首先预设了一个绝对的至善理念或理性本体,然后以为社会历史不过是它们的展开、实现和回归的历程;从它们出发,人类历史不断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最终达到至善至美的终极境界”*贺来:《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的真实根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页。。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康有为的《大同书》即是如此。另一种是乌托邦的想象落后于现实,这是一种向后看的消极的乌托邦,认为人类社会的早期是完美的“黄金时代”,所以最理想的出路是回到过去。基督教的“失乐园”、道家的“小国寡民”即是如此。
即便是对向前看的乌托邦,人们在使用过程中也分别有两种感情色彩:一种是贬义,认为乌托邦是空想,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恩格斯著有《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乌托邦是一种与科学相对立的纯粹空想。另一种是褒义,认为乌托邦是理想,它使人们对未来产生美好的憧憬和期待,可以为实践提供精神动力。哈贝马斯就说过:“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文革时期是全民狂欢、失去理智的疯狂时代,乌托邦色彩比较明显。“乌托邦时代的最大风格,正在于以一整套道德理想主义的符号系统,来实现对民众思想、意识和心灵的全面诱导、改造和控制。”*刘艳:《样板戏观众与乌托邦文化》,《艺术百家》1996年第3期。文革电影就是渲染乌托邦色彩的重要符号系统。这种乌托邦是一种向前看的、褒义和贬义混杂的乌托邦。
一、问题丛生的现实世界
文革电影的乌托邦色彩主要体现在对理想社会蓝图的构建上,但在建构理想社会蓝图之前,文革电影总是先展现现实世界中的诸多问题。当然,这里所谓的现实不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实,而是指影像世界中的艺术现实——虽然二者有一定联系。
文革电影所展现的现实中最明显的问题是战争。战争是魔鬼,它能唤起人的兽性,把隐藏于人们内心世界的恶魔赤裸裸地释放出来吞噬一切。因此,人们总是谴责战争,呼唤和平。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把战争和瘟疫、饥荒相提并论,认为战争可以“大批地,然而有间隔地摧毁人类”*[法]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罗大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79页。,战争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文革的影像世界中有各种各样的战争。有反映秋收起义的《枫树湾》,反映土地革命风暴的《闪闪的红星》《杜鹃山》,有反映抗日战争的《红灯记》《平原游击队》《平原作战》《烽火少年》《黄河少年》,有反映解放战争的《南征北战》《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渡江侦察记》《侦察兵》《车轮滚滚》《沂蒙颂》,还有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碧海红波》《激战无名川》《长空雄鹰》,等等。中国革命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被呈现在文革影像中。战争是非人道的,《烽火少年》中小松见到八路军指导员张伟后是这样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我爸爸叫鬼子抓走了,我妈妈叫鬼子的大皮鞋踢死了,我的家叫鬼子给烧光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接着影片闪回到那个惨无人道的场景:爸爸被几十个日本鬼子五花大绑带走,妈妈出来营救,被踢死,小松拼命地呼喊,画外是激昂悲壮的音乐。
文革电影所反映的现实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1879年在写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这样说道:“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5页。以马恩理论为指针的中国革命必然重视阶级斗争,以新中国革命建设为题材的文革电影必然弥漫着阶级斗争的气息。这在《龙江颂》《海港》《创业》《火红的年代》《向阳院的故事》《第二个春天》《决裂》《沙漠里的春天》《战船台》《海上明珠》《欢腾的小凉河》《开山的人》《芒果之歌》《牛角石》《青春似火》《山村新人》《山花》《山里红梅》《锁龙湖》《新风歌》等大量文革影片中有着极为明显的表现。在上述影片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随处可见,“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随时可闻,每个人都在阶级斗争的场域中忘我地舞蹈而乐此不疲。在《青松岭》中,队长周成最后认识到了自己的思想错误,万山大叔亲切地说:“这码事儿你得牢牢记住,记它一辈子,阶级斗争,到啥时候咱也不能忘啊。”党支部书记方纪云紧接着说:“是啊,如果忘记了这个,夺到手的政权也会丢掉,建成的社会主义也会变质啊。”在文革电影中,一副保险带(《一副险阻带》)、半篮花生(《半篮花生》)、一根银针(《无影灯下颂银针》)、几根木筏(《阿夏河的秘密》)、几只木桩(《三定桩》)等都与阶级斗争紧密相联。阶级敌人可能是地主,如《龙江颂》中的黄国忠、《半篮花生》中的王友财、《阿勇》中的凌金财、《主课》中的山蚂蝗;可能是富农,如《金光大道》(上)中的马少怀、《青松岭》中的钱广;也可能是特务,如《小螺号》中的容阿六、《江水滔滔》中的白云飞、《难忘的战斗》中的陈福堂、《磐石湾》中的裘二、《征途》中的马熊等。总之,他们形色各异,共同构成了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疾病是文革电影呈现出的另一种可怕问题。疾病是有机体因调节紊乱而产生的异常生命体征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外在形体的,也可能是内在功能的。《圣经》中,上帝将疾病作为对不洁、纵欲、不忠、不公的罪人的惩罚方式。当人洗清罪恶后,上帝就会让疾病拂袖而去。福柯认为:“生命是直接的、在场的、超出疾病之外的可感知事物;而疾病则是在生命的病态形式中展现自己的现象。”*[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文革电影完全以疾病为题材的有四部,即《无影灯下颂银针》《春苗》《红雨》《雁鸣湖畔》。此外还有些影片部分涉及到疾病,如《沙家浜》《平原游击队》《金光大道》(上)《黄河少年》《沂蒙颂》《红云岗》等。疾病是生命之树投下的可怕阴影,时刻阻碍着人类前进的健康步伐。《春苗》剧本对生病的小妹是这样描写的:“小妹无力地抽搐着,微弱的哭声。”《红雨》剧本对王老庆生病的孩子是这样描写的:“泡子灯被油熏黑了,光焰无力地在闪动。王老庆抱着重病的孩子在地上走着。孩子无力地嘶哑地哭着。王老庆夫妇焦急的脸色。”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疾病对生命的威胁。
除战争、阶级斗争和疾病外,文革影像世界中还有可怕的自然灾害。《战洪图》展现的是洪灾。1963年,华北海河地区爆发了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严重威胁着冀家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龙江颂》展现的是旱灾。1963年,东南沿海的某人民公社龙江大队虽然丰收在望,但附近地区的旱情却百年未遇,河塘干枯,无水可用。自然灾害是自然环境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异常事件,会使人员伤亡、社会失稳、资源破坏,阻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展现自然灾害的影片还有《山花》《艳阳天》等。
战争、阶级斗争、疾病、自然灾害……文革电影展现的俨然是一个问题丛生的可怕现实世界。如果文革电影就此止步,肯定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因为这样一来,文革电影就会给正在进行的社会运动抹黑添丑。而实际上,文革电影展现如此可怕的现实只是为描绘乌托邦的色彩做铺垫,不然乌托邦的出现就会显得很突兀。也就是说,有了这些铺垫,乌托邦的色彩更容易引起观影者的注意,更能达到文革电影的“询唤”目的。
二、银幕内的乌托邦
乌托邦像个懵懂的少年,喜欢对未来作出美妙的设想,这种设想是对其现实处境的否定和超越。曼海姆指出:“一种思想状况如果与它所处的现实状况不一致,则这种思想状况就是乌托邦。”*[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明、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6页。从历史上看,乌托邦的完美大都源于现实的不完美。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雅典城邦的衰落不无关系,莫尔的“乌托邦”与英王政府血腥统治下的“羊吃人”运动密切相关,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当然也可以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腐败堕落、内忧外患的危机中找到依据。所以说,“在压迫最惨烈的时候,就是乌托邦冲动最为激烈的时刻;在黑暗最沉重的地方,就是乌托邦冲动注定要前往扫荡的场所”*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具体到文革电影中,我们不难发现,其电影在展现战争、阶级斗争、疾病、自然灾害等诸多问题之后,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迎来一片赤色的天空。
在文革电影所反映的战争中,敌人的势力通常很强大,正因为如此,才能显示出战胜敌人的难能可贵。《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的家乡柳溪镇被大土豪胡汉三所占据。后来,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冬子的爸爸潘行义也随部队转移,柳溪镇更是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潘冬子和母亲暂时离开了柳溪镇。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母亲壮烈牺牲。这种死亡说到底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策略,目的是通过普通民众的死亡,唤醒更多的人对敌人的憎恨。后来,潘冬子凭借着智慧和勇气,砍死了胡汉三。请看剧本对此场景的描写:
深夜。小冬子背插柴刀,手提一把煤油壶,蹑手蹑脚来到胡汉三睡觉的房门口。房门虚掩,门上挂着一把铮亮的铜锁。
屋里传出胡汉三的鼾声。
小冬子止步,想了想,轻轻把门推开,走进。
桌上,一盏带罩子的半明半暗的煤油灯。
小冬子毅然提起油壶,把煤油全部浇在胡汉三的床上。然后,拿过油灯,拔下灯罩。
被子点燃了,帐子烧着了,满床腾起了熊熊烈焰。
火光映着小冬子充满愤怒和仇恨的脸。他从容地拔出柴刀,提在手里,大步向房门走去。
就在这时,被烧得焦头烂额的胡汉三,连滚带爬地滚到床下,又挣扎着向门边爬了几步。
小冬子回转身来。他威严地站着,鄙夷地盯着脚下的胡汉三。
胡汉三仰脸向上一望,惊惧地:“是你?……”
小冬子厉声地:“是我!红军战士潘冬子!”
雪亮的柴刀,迎着火光,高高举起,又凌空劈下。*《闪闪的红星——电影文学剧本·评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5页。
尽管这样的场景描写带有血腥和暴力倾向,但我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少年观影时畅快淋漓的感受:仿佛除掉的不是胡汉三,而是我自己的心头恶人。
在《枫树湾》《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激战无名川》《长空雄鹰》《平原作战》等战争影片中都有这样的胜利场景。这样的场景以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很好地满足了观众的想象。
在反映阶级斗争的影片结尾几乎都有批斗阶级敌人的仪式。这种仪式大体由三方人员构成:批斗者、被批斗者、围观观众。其功能有二:一是彻底打击阶级敌人,以证明阶级斗争的合法性和权力获得的正当性。二是批斗者的发言,通过发言,批斗者可以诉说自己的阶级苦,也可以痛斥阶级敌人的罪恶,从而进一步强化自己的阶级立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阶级的分类是社会动员不可缺少的基础,也是治理社会的主要方式。”*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页。在《艳阳天》中,被批斗者是混进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马之悦。批斗者是肖长春,他说:“同志们,别看我们抓住了个马小辫,挖出了个马之悦,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道儿走下去,乌云就遮不住太阳,社会主义的东山坞就永远是大好春光的艳阳天!”《向阳院的故事》中,批斗现场背后有醒目的毛主席语录,被批斗者是阶级敌人胡守礼,主持人是小铁柱,一群少年振臂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发言者是校外辅导员石爷爷,他说:“同志们、同学们,用什么思想教育孩子在向阳院里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胡守礼的罪恶活动已经给他自己做了应有的结论。他的问题并不是他个人的事,他是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批斗阶级敌人的仪式在《青松岭》《金光大道》(上)《锁龙湖》《沸腾的群山》等影片都有明显的表现,这与其说是创作上的同质化,不如说是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作用下创作者的思维僵化。关于批斗仪式,有人说道:“农民一旦张口言说并诉苦,就陷入了诉苦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从而在从受苦到不受苦(解放)的乌托邦/革命实践中,确立起恩人和仇人的二元对立结构。”*史静:《革命历史电影中的身体与复仇》,《电影艺术》2012年第1期。
在文革影像世界中,虽然疾病的幽灵不时闪现,但总有智勇双全的医者挺身而出,让疾病的幽灵无处藏身。像《红雨》中年仅16岁的红雨、《春苗》中的妇女队长春苗、《雁鸣湖畔》中的下放知青蓝海鹰、《无影灯下颂银针》中大胆提出采取针刺麻醉手术方案的上海某医院医生李志华等人就是这样的医者。他们在学医、行医过程中虽然阻力重重,但最终还是完成了救死扶伤的重任。
在文革影像世界中,虽然也有自然灾害,但在自然灾害面前,一定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党和人民鱼水情深,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其中,虽然个别阶级敌人进行阻挠,但这肯定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战洪图》就是这样的绝好文本。在特大洪水面前,冀家庄人民主动舍小家,保大家,破堤行洪。隐藏的富农分子王茂虽然从中破坏,但结果肯定是败下阵来。影片的结尾很有意思:破堤行洪后,上级派飞机给他们空投粮食。人们激动万分,高呼:“毛主席万岁!”坐船而来的张县长兴奋地说:“社员同志们,首先让我转达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人民对我们灾区人民热情的关怀和亲切的慰问……”一位老奶奶握着张县长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我的亲人啊,我们怎么谢谢你们呀?”张县长回答道:“大娘,这都是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老奶奶一番忆苦之后道出了肺腑之言:“千好万好,没有社会主义好;爹亲娘亲,没有共产党亲啊!”此情此景,全国人民一家亲的乌托邦想象表现得再明显不过。
文革电影通过对战争、阶级斗争、疾病、自然灾害等诸多负面因素的移除,营造了一个至真至善的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里,无论是多么大的困难,最终都会得到圆满解决,因为理想国的主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人。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总之,他们是中华传统美德和时代美好精神的统一体。套用文革电影的名片来说就是,他们置身在“火红的年代”,他们“青春似火”,他们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是“钢铁巨人”,他们唱的是“长城新曲”,走的是“金光大道”,这期间虽有一些负面因素,但丝毫遮挡不住社会主义的“艳阳天”。
三、银幕外的乌托邦
文革电影的上述乌托邦只是银幕内的乌托邦,这是一种可见的乌托邦。文革电影还营造出一种银幕之外的乌托邦,它存在于电影后史中,或者说存在于对未来的憧憬中,这是一种不可见的、超越性的乌托邦。“乌托邦永远不会‘在场化’,也正因为无法彻底实现,乌托邦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乌托邦的‘不在场’并不表示它消极无为,而是更深层意义的‘有为’,它不断向现实输送新鲜的‘血液’,以防止其‘凝固’而堵塞历史向前发展的道路;它只有与现实保持相当的距离,才能葆有自身的超越性、终极性、无限性和总体性,才能对现实社会的发展起到道德制约和价值制衡作用。”*张彭松:《“永不在场”的乌托邦——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张力》,《北方论丛》2004年第6期。文革电影通过种种方式指向这种银幕外的乌托邦。
一是开放式结尾。这是文革电影展现银幕外乌托邦最常见的方法。《第二个春天》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海军某部支队政委冯涛奉命带领人们研制“海鹰”号新舰艇的故事。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让“海鹰”在春光似锦的第二个春天飞了起来。结尾时,“海鹰”甲板上的群众欢呼雀跃,欢呼声、笑声、汽笛声响彻海空。冯涛激动地说:“帝修反并不怕我们造了一个‘海鹰’,它怕的是我们照着毛主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五年、十年、二十年……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接着的画面是舰艇编队破浪前进,溅起的浪花形成壮阔的线条。远景,俯拍,雄壮的画外音乐,将观影者的思绪引向无际的电影后史中……《车轮滚滚》《长城新曲》《碧海红波》《激战无名川》《长空雄鹰》《决裂》等都是这样开放式的结尾。
二是主题歌。主题歌虽然不参与影片情节的发展,但同样能昭示出无际的“天边外”。《青松岭》的整个叙事围绕着马鞭展开,马鞭其实是个象征符号,如果被富农钱广掌握,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被年轻人掌握,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番较量,年轻人终于从钱广手中夺过了马鞭。影片主题歌是这样的:
长鞭一甩叭叭响,
赶起大车出了庄。
劈开重重雾,
闯过道道梁,
要问大车哪里去?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立志战恶浪,
哪怕风雨狂,
要问大车哪里去?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这个主题歌旋律优美,节奏欢快,在20世纪70年代广为流传。它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产生绵延不绝的遐想。
三是台词。这是指向银幕外乌托邦的一种最为简便的方法。《金光大道》(上)的片名就带有浓浓的隐喻色彩,旨在说明走互助合作道路是平坦的“金光大道”。在缺少农具、耕畜的芳草地,共产党员高大泉带领大家进行互助组运动。但村长张金发、富农冯少怀等人却在搞“发家致富”,并利用彩凤和高二林的婚事,煽动二林与哥嫂分家。高大泉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的行为得到了县委书记老梁的支持。老梁送给高大泉一本毛主席著作《组织起来》。高大泉回来后拿着书激动地对人们说:“这就是毛主席给咱们指出的金光大道啊!老梁同志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燕山区给咱们做出了样子。人家呀干得可欢吵啦,有临时互助组,有常年互助组,还有农业社呢!就为这,老梁同志说还要给咱们派一个区长呢。只要咱们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条道走,就能一步一步地挖掉毒根子,栽上新苗子。按老梁的话讲,咱们这个互助组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苗子,有苗不愁长,今天的小苗明天就是一片青纱帐,一片红云彩。”接着是隐喻蒙太奇:一棵棵绿油油的幼苗茁壮成长。这段台词显然寄托着芳草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哈贝马斯说:“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方向,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赫茨勒也说:“乌托邦思想家都站在未来的土地上,向人类展示摆在他们面前的美好生活。”*[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51页。是的,银幕外的乌托邦以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已然与应然的二元对照形式展现了未来社会的和谐、幸福和圆满,为置身此岸世界中的人们树立了前行的参照物。
四、政治乌托邦
文革电影的乌托邦既存在于银幕之内,又存在于银幕之外。这种想象与狂欢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乌托邦。“政治乌托邦指的是一种倾向,它相信合乎人性的、高级社会制度的存在,认为完美社会关键在于政治制度的建设,倾向于通过政治斗争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打造崭新的现代的国家,最终完成理想社会的建构。”*李雁:《新时期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1年,第20页。由于文革电影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所以其展现的政治乌托邦又有自身的特点。
一是重阶级性而轻人性。在文革电影构建的政治乌托邦中,阶级性是引人瞩目的景观。在创作者看来,无论什么事,只要放在阶级性的高压锅里蒸煮一番,就一定会色香味俱全。文革电影有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大家在进行着一个集体性的正义行为,比如开采石油(《创业》)、研制钢铁(《火红的年代》)、抢收抢种(《阿勇》)、开门办学(《欢腾的小凉河》等,一定有人从中破坏,经过一番较量,破坏者败下阵来,结果发现破坏者是隐藏的阶级敌人——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再不就是特务。2004年3月,我有幸在南京采访了《战洪图》的导演苏里。苏老告诉我说,1972年10月,自诩为“文艺革命旗手”的江青忽然心血来潮,认为当前文艺作品太少,决定将包括《战洪图》在内的一批文革前的优秀影片重拍,并嘱咐苏老一定要加上阶级斗争的标签。于是苏老就在剧中硬加了王茂这个人物,把他设计成隐藏的敌人,阻挠破堤行洪。王茂被发现后,大家才明白真相,他根本就不是冀家庄的王茂,他的真名叫陈耀祖。前几年发大水时,王茂随其父逃荒到东北,在他家当长工。土改时,他把王茂父子杀害了,就冒名顶替,隐藏到冀家庄。今天看来,这样的情节实在是荒唐可笑。陈耀祖冒名顶替到冀家庄,都是乡里乡亲,村民们怎么可能信以为真?生活是纷繁复杂的,如果一切都归之为阶级斗争,只能是创作者一厢情愿式的政治乌托邦想象。
由于过分突出阶级性,人性也就不见踪影。人性即人的本性,它是人的社会属性,其含义要比阶级性广泛丰富得多。在非阶级社会中,人性当然无阶级性可言;即便是在阶级社会中,生病之痛、死亡之惧、夫妻之欢、朋友之乐、相爱之悦虽然可能会抹上一定的阶级色彩,但决不能用阶级性来取而代之。《艳阳天》中就出现了这样匪夷所思的情节,在紧张的麦收之际,为了达到破坏目的,马之悦将肖长春的独生子小石头骗到东山坡,小石头被马小辫推下山崖。不见了小石头之后,作为父亲的肖长春并不着急,而是扛着铡刀走向麦场。发现人们都去找孩子之后,他火冒三丈,立刻敲响槐树下的大钟,把人们叫了回来,激动地说:“同志们,麦子是咱们用汗水浇出来的,咱们不能眼看着麦子烂在垛里,都到场院里去,拆垛,摊场,打麦子!”有人建议先找孩子,肖长春却执意要先打麦子。此时,肖长春的父亲肖老大把在东山坡捡到的、带有小石头血迹的小木枪交给了肖长春。肖长春仍然抑制住悲痛,拒绝找小石头,并且告诫大家说:“敌人的阴谋就是要拖住咱们打场,让麦子全部烂掉,搞垮咱们农业社呀!……让那些坏蛋们看看,搞社会主义的人都是硬骨头!”接着是一个热火朝天的麦收场景,激昂的画外音乐、振奋人心的歌曲、快速的镜头切换,将人们的阶级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是在这样的场景中,珍贵的人性逃逸得无影无踪。
二是重集体而轻个体。有人指出,乌托邦总善于“预先精确地、一丝不漏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方案,其中大家都按照同样的模式生活,遵循着同样的生活准则。乌托邦总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人类,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总体而没有看到它是由众多单独的个人所组成的;个体具体、真实的存在虽然原则上被予以尊重,但并没有真正加以考虑。乌托邦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作为‘类’存在的社会,单独的个人很少成为其关注的对象”*李书巧:《完美的边界:乌托邦政治内涵分析》,《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文革电影的政治乌托邦即是如此。“我”被“我们”取代,“私”被“公”取代,个体价值的启蒙被彻底消解在民族、国家、阶级等集体意识的狂欢中。《碧海红波》中小英子死前想到的是把水给志愿军叔叔,《平原游击队》中小狗子临死前想到的是打鬼子,《激战无名川》中老班长临死前想到的是如何取得战争胜利。他们没有一个想到自己的痛苦,想到亲人的伤心。最耐人寻味的是讲述“三自一包”的《牛角石》。“三自一包”是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总称,能够“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潘淑渟:《三自一包》,《档案天地》2010年第11期。,但在影片里却遭到了嘲笑和抵制。地委副部长陈秉仁带人来分地时,一位老农手拿着地界牌子深情地说:“这地界牌子土改的时候我们插过它,那时毛主席领导咱们穷人闹翻身,分的是地主的地啊!那时咱们心眼里是多热乎呀!后来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咱们拔掉了它,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大伙儿才过上好日子,今天你让我们插着地界牌子,分的是人民公社的地,让我们再去单干呀!陈部长,你知道我们心眼里是啥滋味呀?”人们又纷纷指责说道:“你们是成心把我们往火炉里推呀!”“我看你们这搞的是资本主义。”“想让我们复辟倒退。”“明明是拆人民公社的台,坑害贫下中农。”通过指责和诉苦,农民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集体意识。最后,陈部长等人在人们嘲笑声中灰溜溜地逃走。其实,这种逃走行为是在那个年代个体意识处境的绝好隐喻。
三是重精神而轻肉体。身体是一个神秘的场域,既应该有精神层面的沉思,也应该有肉体层面的享受。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非理性的;前者是上半身的凌空蹈虚,后者是下半身的世俗体验。如果仅有前者,就与圣人无异;如果仅有后者,又跟动物同类。但在文革电影构建的政治乌托邦里,精神的大旗高高飘扬,冲动的肉体就像柏拉图理想国里的诗人一样不受欢迎。《女飞行员》中的林雪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创业》中的周挺杉有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沂蒙颂》中的英嫂有爱党爱军的精神,《主课》中的老队长有一心为公的精神。他们都是无性别意识的中性人,是无私心杂念的玻璃人,是六根清净的出家人。总之,他们无情无欲——如果说有情,也是革命情;如果有欲也是斗争欲。他们在乌托邦的狂欢中早已忘却了肉体欲望的存在。
五、乌托邦色彩的成因
阿多尔诺说:“根本就不存在不再会有邪恶的世界。”*[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是的,人类永远生活在战胜邪恶的理想中,永远生活在对美好世界的憧憬中,正因为这样,人活着才感到有意义和价值。文革电影的乌托邦正是对完美无缺的社会状态的想象,这种乌托邦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鉴于福柯所说的“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我们应该首先对文革这个特殊时代背景进行分析。整个文革的思路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创造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奇迹。具体方法就是“斗、批、改”。1968年,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指出:“我们一定要深入地持久地革命大批判,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攻,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隐藏在阴暗角落里从事捣乱和破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今天看来,这个社会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多少带有假想或者说扩大化倾向。在“全国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全国上下的人们无不陷入对美好未来的狂热憧憬中。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96页。。这个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被当时的《人民日报》视为在全国建立“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行动纲领。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革命的年代呵,
一天等于二十年。
看,到处是火红的旗帜,
到处都是飞撒的传单,
到处是前进的步伐,
到处是激情的召唤。
啊!
久经风霜的万里长城呵,
你可曾经历过这样的暴风雨的世面?!
阅尽人间春色的昆仑山峰呵,
你可见过如此的画卷?!*《文化大革命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29页。
在全国都陷入乌托邦的狂欢背景下,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作品出现乌托邦色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闪闪的红星》的创作即是印证。创作者这样写道:“现实中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又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在我们创作过程中,欣逢党的十大胜利召开。十大文件强调指出,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千百万’,都是从儿童团过来的。要重视儿童团,决不能轻视儿童团,这一光辉思想又进一步照亮了我们的构思。”*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创作组、摄制组:《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影片〈闪闪的红星〉的一些创作体会》,《红旗》1974年第12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文并非发表于文艺刊物,而是党刊《红旗》,可见文革电影在当时影响之大。
其实,如果我们仅仅从狂热的文革运动来探讨文革电影乌托邦色彩的成因还不够,还应该从中国革命史的更远背景中进行透视。毛泽东一生有着浓浓的乌托邦情结。早在1919年12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的《学生之工作》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新村”设想,新村中“公”字当头,有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等。到了1939年,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归宿就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1-652页。1945年,毛泽东又自豪地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出了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页。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乌托邦情结日渐清晰,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蓝图是这样的: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生产资料属于公有;限制和逐步取消商品,劳动产品平均分配;逐步取消社会分工,自给自足;逐步缩小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实行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正是在这种乌托邦思想指导下,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顺势展开。有人这样评价:“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五·七指示’,毛泽东的晚年始终沉浮在其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的汪洋大海之中,硬要把他希望的超现实的完美的道德理想强加给人们正在创造的不完美的现实,从而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郑黔玉:《试析毛泽东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乌托邦情结》,《贵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我们在文革电影的影像世界中很容易发现毛泽东的乌托邦情结对其的影响。《决裂》讲述的是江南某地区党委决定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故事。延安“抗大”毕业的垦殖场场长龙国正被派往松山分校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根据地委副书记唐宁的指示,决定把学校办在山头上,主张打开考场大门,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工农学生进考场参加考试,请贫下中农参加评论。代表保守势力的副校长曹仲和坚持要把学校建在城郊;教务主任孙子清为追求学生质量,拒收没有文凭的工农学生。为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传来毛泽东来信肯定“共大”的消息,龙国正号召全体师生掀起的“教育革命”终于成功。他激动地说:“同志们,毛主席光辉的‘七·三○指示’是我们胜利的旗帜,前进的方向。在教育革命的征途上,是不会风平浪静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于是,影片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激昂歌声中结束。因此,美国的一本《世界电影史》评论该片时,说这“是一部关于一所所谓农业学大寨的极具戏剧性的影片,极好地图解了毛泽东的思想”*[美]克莉丝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世界电影史》,陈旭光、何一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6-527页。。
当然,文革电影乌托邦色彩的出现还可以从文艺创作的相互影响、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国际环境等因素加以分析,但上述两方面是最明显也是最主要的。
六、乌托邦色彩的利与弊
文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在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运动中,领导者需要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作品来营造“全国一片红”的喜人景象,而文革电影所呈现出的乌托邦色彩恰恰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要。无论多么残酷的战争,我们都能取得胜利;无论多么顽固的阶级敌人,我们都能打倒;无论多么可怕的疾病,我们都能医治;无论多么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都能降服。我们有坚定的阶级立场,我们有宝贵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之所以有此境界和伟力,是因为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文革电影呈现出的乌托邦色彩着实达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目的,让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向往。有人在看过《青松岭》之后这样写道:“我们有些人对物质刺激等资产阶级的东西津津乐道,明知一些事情违背党的利益,但由于战胜不了世界观深处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也就听之任之,随波逐流了。这样下去,就可能像孙福跟着钱广跑一样,上林彪一类的当,走资本主义斜路,甚至还当传声筒!因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世界观,破除头脑中的私有观念,树立共产主义思想。”*王洪:《从钱广讲“按劳分配”所想到的——重看<青松岭>有感》,《吉林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在看过《龙江颂》之后,有人在学习札记中这样写道:“只有像江水英那样,时刻牢记‘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不停顿地挖掘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才能使黄国忠这样的阶级敌人无机可趁;才能在第二个、第三个比黄国忠更阴险、更狡猾的阶级敌人出现时,就能立即识破他,战胜他;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使社会主义江山坚如磐石,万古长青。”*贾锦福:《立共产主义理想 做继续革命战士——革命样板戏<龙江颂>学习札记》,《文史哲》1975年第3期。也就是说,这些人对文革电影的乌托邦色彩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凡事都有两面性。文革电影的乌托邦营造了“全国一片红”的大好形势,同时也遮蔽了触目惊心的现实。有权威著作曾这样描述文革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的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48页。这无疑从反面证明,文革电影所打造的那个思想先进、生活富裕、干劲十足、处处洋溢着歌声和笑声的理想社会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国家想象了。
责任编辑:孙昕光
Utopian Color of Movi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Chen Jid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Utopia of “Cultural Revolution” movies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lueprint of an ideal society both in and outside the screen. However, before constructing the blueprint of such a society, Cultural Revolution movies always raise many problems in the real world, such as wars, struggles between classes, disease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is utopia is essentially a political utopia. It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class character, collectivity and spirit rather than human nature, individuality and the flesh. The appearance of this kind of utopia is necessarily related to the fanatical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and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s at that time. It works out a good situ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is Red” but covers the soul-stirring reality at the same time.
movi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utopia; representation; essence; cause of formati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2016-04-20
陈吉德(1968—),男,安徽凤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11年度规划项目“文革电影研究”(11YJA60005)的阶段性成果。
J974.1
A
1001-5973(2016)03-01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