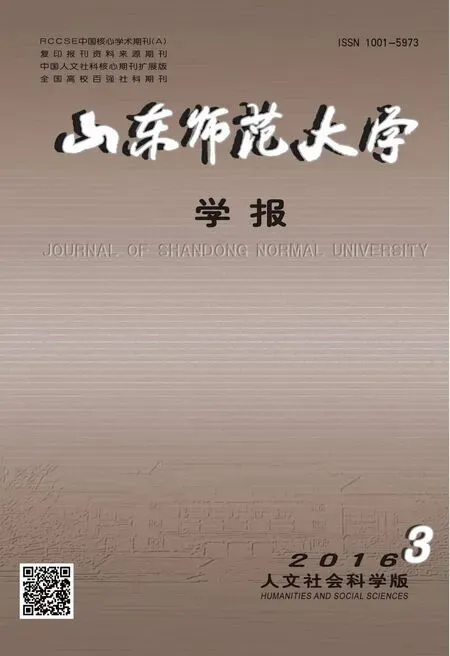构建完善的政治生态环链体系——关于腐败问题的“恐惧生态学”探讨*①
刘京希
( 山东大学 《文史哲》编辑部,山东 济南,250100 )
构建完善的政治生态环链体系
——关于腐败问题的“恐惧生态学”探讨*①
刘京希
( 山东大学 《文史哲》编辑部,山东 济南,250100 )
有政治生活的地方,就不免有腐败。但就腐败发生的几率和程度而言,制度性政治生态链完整与否,与政治腐败发生的几率和程度,显然是成反比关系的。人都有趋利本性,握有权力的人,往往会忘记权力的公共本质,不免会权为己谋,权为私谋。此时,就需要制度性的“政治恐惧生态学”发挥阻吓与制约作用,约束擅权者的私欲意图。制度性的第三方的独立而权威的存在,即是那个“政治恐惧生态机制”。而以发挥“第三方”社会责任为己任的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建构,无疑是“政治恐惧生态机制”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完善民主制度,赋予民主的主体——公民——以“第三方”的社会责任,利用公民及其代表手中所掌握的选举、罢免、弹劾、质询、听证等法定权利,约束权力代理者的权力行为,阻吓与制约权力代理者的越权言行,当是“政治恐惧生态机制”建构的最高境界。
政治腐败;政治生态;第三方;司法体系;公民权利;民主政治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3.006
现代国家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正、高效、开放和廉洁。其中的每一个特征,都与反对和遏制腐败息息相关。民主、法治与公正自不必说,高效、开放而廉洁的政治体系,自是与腐败相绝缘的。因此,凡是腐败案件高发的国家,必定是政治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
在人类社会,有利益分别就有腐败,有社会政治行为就有政治腐败。腐败问题与社会政治肌体同卵而生。因此,有关腐败问题,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持久话题。
比起国内学术界,国际学术界对腐败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关于腐败发生的机理,美国学者维托·坦齐认为,腐败是在两个层面上发生的:政治层面和官僚层面。在政治腐败的情况下,决策者把政策出卖给那些愿意出高价的人。某些生产和贸易垄断权的出售就可以划归这一类型。腐败的另一种形式即行政腐败,它是指政府官员与私人机构的不正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有的人通过花钱购买对现行法律和规制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或绕过它们。当官僚们的游戏规则没有被清晰地加以界定,他们在颁发具有经济价值的特许权或政府合同以及招聘人员拥有自由处置权时,就会受到诱惑去收受贿赂。自由处置权越大,规则越不透明,腐败的潜在可能性就越大。*[南非]罗伯特·克里特加德:《控制腐败》,杨光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页。就腐败发生的程度而言,后发国家所存在的腐败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有关后发国家的腐败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兴趣。以南非学者罗伯特·克里特加德为代表的腐败问题研究专家,把后发国家腐败多发的原因,定义为后发国家社会分层程度较低,公共机构起着巨大的和中心的作用。所以,反腐的重点在于解决公共权力机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像先发国家所做的那样,将公共机构所操控的经济活动转交给私人企业来完成。总起来看,国际学术界有关腐败问题的研究,已经跳出了腐败的“文化决定论”、“习俗决定论”、“道德决定论”、“人性决定论”的窠臼,更加注重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制度机理的探寻,因此,如何遏制腐败,也多从制度角度予以考量。
国内学术界对腐败问题的探讨,前些年多集中于对腐败产生之原因的分析,尤其是市场经济与腐败之关系的分析。形成了市场经济与腐败现象“没有必然联系”、“存在必然联系”、“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诸种观点。同时,“道德决定论”、“人性决定论”等从道德角度探讨腐败原因的观点也颇为多见。因此,反腐工作一度纠缠于“高薪养廉”、“思想反腐”的误区。
近来,制度分析日益进入腐败问题研究领域。制度分析理论认为,腐败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和那些参与腐败交易的人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使下,经过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后作出的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而制度通过影响人们对各种行动方案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最终影响个人的选择。它告诉人们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为个人的行为提供了激励机制、机会结构和约束机制。个人选择就是在制度这只既有形又无形的手指引下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如果仅仅着眼于案件的查处和单纯强调思想教育与自律,显然是不够的。只有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改变人们行为的激励机制,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并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这是腐败问题研究的一大进展。包括韩国“卢武铉门”、台湾“陈水扁门”等“黑金”案件在内,所有腐败案件发生的共性因素,就是制度没有独立性;或者曾经有独立性,后来失去了独立性。通俗地说,就是制度成了财富与权力的附庸和奴仆。
一、腐败的实质及类型
腐败,是人类社会自有财产概念以来,即发生和存在的普遍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人类社会之所以始终不渝地同腐败现象作斗争,不仅是因为它极大地腐蚀着人们的精神,恶化着社会政治环境,加深社会矛盾和对立,更因为它加大了政治运行成本和社会运行成本,甚至于造成主权者的合法性危机。因此,腐败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公务人员的贪污受贿和腐败,是引起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腐败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属于道德性的问题,还是文化习俗性的问题?拟或是制度性的问题?只有厘清腐败的诱因及其性质,方可对症下药,也才可药到病除。
(一)腐败的类别及其诱因
腐败,从类别上看,有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相较而言,政治腐败之于社会的危害,更甚于经济腐败。因为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政治领域就成为社会的核心领域,决定着社会其他领域的进退。毫不夸张地说,社会的健康程度,取决于政治的健康程度。而政治的健康程度,又取决于其制度化的程度,以及制度健康的程度。
腐败之所以频生,从制度的层面看,是由于体制本身的进步和变革,并未赶上其监管对象为应对监管而产生变化的频率。当下中国社会腐败的频发,则是由于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并存,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和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的恶性结合所导致的结果。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盟,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也加剧了弱势群体的抗争。
在一个遭受腐败困扰的国家,政府的职能超越了公权力的“公共”界限,而进入了“私人领域”,这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国家更为明显,因此,最重要的是,腐败的机会需要通过削减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来加以减少。政府的急剧膨胀及其对经济生活的渗透,创造了诱惑官员和决策者用以优待他们的“朋友”的租金。除此以外,精心设计规则和规制能够提供激励去促使人们保持距离,从而降低腐败的吸引力。*[美]维托·坦齐、[德]卢德格尔:《20世纪的公共支出》,载子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03页。其实,腐败多发的直接诱因,是政府权能的急剧膨胀,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由裁量权和处置权的失控。公共部门垄断权与自由裁量权的结合,招致各种各样的寻租行为或没有直接社会生产意义的谋利行为。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间接的原因,则往往是第三方监控的缺失或流于形式。正是第三方监控的缺失或流于形式,使得官员的自由处置权越发扩张,进而造成权力的滥用,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第三方监控的缺失或流于形式,一般表现为,作为第三方的司法、监察体系的不健全,如建制或组织关系的非独立性——包括对地方政府的隶属性,以及人财物的受控性,和由此造成的非权威性。与之相关,还有因律师制度的不完善所造成的,对于律师的执业权利的莫名侵害。政府无论大小,总是会与经济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联系就难免产生交换,诱致腐败。此时,制度性的第三方的独立而权威的存在,对于遏制腐败,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这里,第三方就是一个“政治恐惧生态机制”(第三部分将予以详述), 当它充分发挥其阻吓与制约作用的时候,权力拥有者的私欲企图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和代价。这是就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直接目的而言的具体制度上的“第三方”。而从根本上说,完善民主制度,赋予民主的主体——公民——以“第三方”的社会责任,利用公民及其代表手中所掌握的选举、罢免、弹劾、质询、听证等民主权利,约束权力代理者的权力行为,阻吓与制约权力代理者的越权言行,当是“政治恐惧生态机制”的最高境界。
腐败现象的多发,表面看,是官员的“官德”出现了问题;深层看,还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同样的社会道德水准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否完善与严格,决定着腐败的轻重程度。多国的反腐实践证明,用加强道德建设的方式预防腐败,效果微乎其微。许多腐败案件多是窝案串案,是集体共犯,你不能说这些犯案者全部而且同时道德低下,只能说,是制度上存在漏洞而被腐败分子所利用。另外一种习见的说辞也应予以驳斥:腐败往往与一定的社会文化习俗相关联。说明这种观点的一个显例,是香港一度泛滥成灾的公务腐败,缘于香港礼尚往来的文化习俗。社会文化中的以权谋私传统,以及广泛盛行的“送礼”和“酬劳金”做法,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可否认,香港一度确曾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公务腐败声名远播。但令文化决定论者不可思议的是,今天的香港政府公务,仍然置身于同样的文化氛围,却已洗脱了腐败的恶名,转而成为清廉的典型。原因何也?首要的原因,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独立的廉政公署的创立,是香港政务从贪腐向清廉转变的界标。一个更有说服性的特例是,晚清中国海关的“不腐金身”。在晚清,中国海关因廉洁而著称,甚至被称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是英国人赫德缔造的。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从1861年到1908年,赫德掌握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达半个世纪之久。晚清的中国海关也称“洋关”,与之相对的则是“常关”。前者管理国际贸易,由赫德等洋人主持;后者管理国内贸易,由清政府官员主持。在海关之内,无论是“洋员”还是“华员”,都能廉洁自守。与之相应的是,同是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自守,在“常关”工作则个个腐败。同在中国的土地上,“洋关”廉洁而“常关”腐败,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而在“常关”工作则贪污腐败,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腐败在中国是可以治理的,腐败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所致。腐败,只能是制度使然。赫德在制度建设方面,主要是借鉴了英国经验,并予以严格执行。一系列防范贪污腐败的管理制度,比如监督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巡视制度等;再加上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和严明的奖惩制度,使得海关职员不仅不能贪,也不需要贪,廉洁就有了保证。*洪振快:《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的衙门》,《学习时报》2010年1月4日。这恰好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良好的制度之于反腐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说,政治腐败是对制度的污染,因其制度本身存在易被腐蚀的缺陷;那么,预防与铲除政治腐败,就是在从事制度的环保,弥补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给制度涂上一层防腐保护膜。
(二)谁来监督贪官?
《中国青年报》曾发表文章说,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谁来监督像成克杰、陈良宇、段义和这样的贪官呢?民众吗?民众根本就不知道书记、市长们在干什么;媒体吗?媒体动不动就会被指侵犯了名誉权,没有哪个编辑、记者愿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纪委吗?陈良宇是市委书记,纪委还要向他汇报工作。可以说,这些高官基本上处于不受监督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电话就可以成千上万地赚钱,谁能经得住这样的诱惑?*邬凤英:《同样沾上情妇 中美高官何以下场迥异》,《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4日。
中国近年来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党(纪委)、政(监察部门)、法(检察院)三个系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都有目共睹。近年来所发现和查处的大小贪腐案件不计其数,包括几个震惊世界的大案,如薄熙来案、令计划案、周永康案,等等。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在纳闷:既然反腐措施如此严厉、果决,那为什么腐败事件依然层出不穷,甚至越反越腐、前“腐”后继?
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标本兼治”、“从源头抓起”,最高决策层提出的这个反腐口号,或者称之为经验,已经指出了症结所在。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行使权力的过程也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从源头上减少或消灭腐败现象,因而就出现了“一个贪官倒下去,千百个贪官冒出来”的无奈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新近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确实有其必要性。因为现在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不只是打击腐败的力度是否足够大,而更在于如何消除各级掌权者滥用权力的机会。除了党纪国法的震慑作用之外,完善各级政府部门的内部监督机制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因为这是预防腐败的第一道关口。如果这道关口形同虚设,不能够实质性地介入反腐阵地,那就无法解决腐败问题。就近来的一系列反腐举措和动作而言,主要是党的纪检部门站在前台,其他专门机构还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反腐败部门并不少,但腐败却照样蔓延。这说明,反腐的关键不在于部门的多少,而在于反腐行动是否真正独立。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201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立案、结案、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多项指标均达到了纪委恢复组建以来的最高值。仅201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数就比2013年同期增长三成多。*何韬:《恶竹应须斩万竿——2014年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工作综述》,《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1月9日。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崇尚综合而不是分析;崇尚宏大叙事而不是细致入微;喜欢大发宏论而不是具体实证。在治理腐败问题上,同样如此。我们谈论反腐败和政治清廉,喜欢从大处着眼,不屑于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其实在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大步迈进的时候,完全可以先行扎紧制度的篱笆,完善法规,落实制度细节。英国在19世纪末发展出一套严格制度,它的技术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复式记账法的发明,这是西方制度文化的土壤。美国虽然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宪法只是一个大构架,它的一套适应自己国家的具体监督制度,也是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在此之前,虽然美国的新闻自由可以由记者对官员腐败现象任意揭露,可是,只要具体的制度细节有漏洞,其结果就还是不断腐败、不断被揭露、官员不断受处罚,然后,不断有官员钻制度漏洞继续贪腐。直到20世纪初以后,科层制度、财务财政制度完善,腐败案件才得以锐减。西方国家是民主的原生地,其之所以能长出这棵大树,是因为有其适宜的土壤。这个土壤包括与自由经济同步、与市场经济匹配的制度细节,其前提是有完善制度细节的强烈自觉意识。这也是移植民主制度的国家,往往长期不成功的原因。它们没有这个土壤,没有这个自觉意识,轻视甚至有意规避政治之外的制度细节安排。结果是政党政治大话过多,制度细节安排不足,使移植的制度之树无法健康生长。*林达:《反腐可从政治之外的制度细节入手》,《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17日。
比如说,“公权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就是个“细节”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公权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进行法律限制意义上的界定,导致整个社会不能有力地行使对官员的监督。必须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和最大的法律限制,这为限制其滥权所必需,因为他们的行为在原则上影响到全体公众。
二、集中体制的非生态性——政治腐败的深层原因
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很不适应,一直是中国改革过程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权力体系的运作、监督、制约、平衡机制的缺失,是腐败问题的根源所在,而腐败问题,又是当前很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有效制止腐败,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和发展进程,从长远来看,政治体制的改革是无法回避的。
由于权力的相对集中,公民的个人权利缺少法律保障,尤其是弱势群体,在群体权利遭受不法侵害之时,处于集体失语状态。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可以举全国之力,高效率地“办大事”;但是,由于个人权利的缺失,意味着在这样的时候,底层社会的真实反应往往被歪曲甚至无视。当时高效率地办成的大事,经过历史的过滤,回过头来看,可能就是“大错事”。这样的体制,呈现的是单向的、发散式的权力运行状态,因为缺少生态回路而不能形成回馈。权力运作因其单向性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回馈。即使有所回馈,也因体制的向上负责性,使得下级在多数情况下,选择报喜而不是报忧,底层的真实声音从而被彻底消弭于无形。
相反,在民主体制下,公民个人及其代表拥有体制上话语权,公民个人是体制及其决策的“回音壁”,而不是“消声器”。从政治生态理论*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的角度看,民主体制是个完整的闭环形生态回路,政策或者决策,能够沿着这个回路,不间断地形成反馈,从而持续地校正和修正着政策与决策。所以,任何重大决策,都能得到各个环节的及时且真实的回馈,而不至于造成社会性的重大失误。
权利最大的伤害来源于权力,人权保障的要害是政府权。这不仅是指威权体制的政府,极权体制的政府,甚至连民主体制的政府也包括在内。权力,只要是权力,无论来自君主抑或来自民主,更无论来自武装革命的暴力,对权利一般具有侵害性。人权障碍在此,怎么办?体制问题应从体制解决。扼其要点大致有:首先,权利必须来自民主。不民主,权力伤害权利,权利却无能力更换它,只有不断受荼毒。其次,权力分配必须制衡。即使民主权力,也会自身做大,而在既定空间内,权利大则权力小,这是简单的加减法。所以,仅仅民主还不够,更必须以宪政的方式制约权力而保障权利。*邵建:《人权的障碍在哪里?》,《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6日。不过,宪政前提下的制衡,也有个前提,就是政治公开。没有政治公开,何谈宪政与制衡?2009年5月爆发于英国政坛的“报销门”,之所以被披露,也正是源于政务信息的公开。*《英国政坛爆出骗补门 议员报销项目无奇不有》,新华网,2009年5月15日。英国《议会绿皮书》明文规定,政府官员和议员的报销制度属于信息公开法案管理之列。所以,从“报销门”事件,我们既可以看到所谓民主制度的缺陷,同时又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自我纠错机制对制度缺陷的弥补能力。所以,对预防和遏制腐败,我们应当有足够的信心。社会的协同进化和体制的不断完善,自会对腐败予以节制。
一位生物学家曾比喻说:“如果经济是一张大网……是否是这个网本身的结构,决定并推动网的变化?果真如此,我们就需要寻找一种理论,解释经济网络的自我转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创造出变动不止的生产技术网络。新技术的出现(如汽车),会促使别的一些技术消亡(如马、轻便马车和马具生产),同时创造出适于更新的技术生存的小生境(如公路、汽车旅馆,交通灯)。这种变动不已的经济体系,听起来有点像变动不已的生物圈……如果存在这种普遍适用的规律,不应该太出乎我们的意料。生物进化及共同进化,和技术进化及共同进化是非常类似的过程,都和小生境的创造以及组合优化有关。”*[美]斯图亚特·考夫曼:《宇宙为家》,李绍明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338-339页。小生境又称小栖息地,是生物生活或居住的微小范围的环境。它常决定一种生物的存在与否,如林地生境中的不同树冠层、树干、枯枝落叶层、土壤腐殖质层、林下的灌木层、草本层及活地被层等。生态学上的这种“小生境”理论,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就是,这种小生境,既存在于社会的经济领域,也会存在于社会的政治领域,我们可以称它为“政治小生境”。具体到腐败问题,以小生境的观点看,有腐败,就会有反腐败。但在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指望这种“政治小生境”的自然发育,似乎太过漫长。这一“政治小生境”的发育,需要外力的协同促动,以期大大缩短这一过程。而这一进程,就是针对腐败现象的制度创新过程。
当然,这一制度创新过程,绝然离不开生态化的政治理念的指导。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它的公平,而公平的实现,本质上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它最终归结为各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平行四边形的斜线。力量不对称,表达不充分,制定不出合理的制度。因此,实现力量的均衡,表达的充分,是我们当下在制度制定前首先需要确立的理念。*赵平之:《当下,理念比制度更重要》,《社会科学报》2006年11月9日。扩而言之,社会的和谐,取决和体现于社会构成的生态平衡,阶级、阶层间发展的生态平衡。美国政治机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始终保持平衡中的稳定。美国政治机制的稳定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两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同一部宪法和同样的机构平衡体系。
同时,我们也相信,良好的领域界分,也是减少腐败的一项政治生态机制。因为领域之间的界限,就像一堵牢固的墙,能够有效地阻断权力的盲目扩张。正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确界分,确保公共权力只能限于公共领域,而不能够将其触角伸向私人领域,捞取非法的利益。这已经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腐败现象逐渐减少的实例所证实。在西方工业国家,经济活动是由私人企业来进行的。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容易受到政治腐败的侵袭,正是因为“在这些社会中,公共机构起着巨大的和中心的作用,常常左右着经济活动”*[南非]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控制腐败》,杨光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页。。中国的公共领域恰恰也存在此类问题。比较典型的“管理性腐败”的爆发,正是因循计划性的监管大权而生。有监管就有反监管,而反监管往往是通过权钱交易等不同形式的大小腐败来通融和实现的。甚而至于,如果没有体制对监管机构的有效制约,监管本身就是腐败的陷阱,前些年揭开的国家药监局腐败窝案的盖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近期“莆田系”腐败案件的爆发,背后恐怕也有监管部门的责任。
在世界范围内,社会政治结构的演变轨迹也证实了领域分区化、结构扁平化、权力分散化且相互之间互为限制的趋势。“常见的自上而下的集权化组织形式不再时兴。组织结构变得越来越在一个平面上,越来越非集中化。……这样做,是为了能够提高适应性和竞争优势。为什么更平面化的、非集中化的组织结构,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其他领域的,可能会更灵活,更能提高整体的竞争优势呢?存在一些涉及许多可变因素和互斥制约因素的困难问题。如将整个问题分成不相重叠的小片来考虑,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美]斯图亚特·考夫曼:《宇宙为家》,李绍明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296-297、319页。而且,这些制约因素之间的冲突越严重,分片方式就越有用。虽然这些结论都是新的,尚需扩展,但分片方式会被证明为一种强有力的解决复杂难题的办法。事实上,在生态系统、经济体系和文化系统的适应性进化过程中,类似分片的解决问题方式,可能是一种最基本的机制。果真如此,分片逻辑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另外,它也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管理复杂组织以及改进复杂机构等方面的一个新理念。*[美]斯图亚特·考夫曼:《宇宙为家》,李绍明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319页。
当下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抉择,是在制度层次和决策高度上进行自觉的领域界分,然后以此为依据,对社会发展诸运行规则和机制进行职能归位,让不同领域的不同运行规则及其职能各归其位,各行其职,各负其责。这就像一台新计算机,使用前必须进行格式化分区,区域不同,运行准则和功能不同,因而有条不紊。即使遇到病毒攻击,也只是对局部区域造成影响,无碍大局。当然,如果不首先进行格式化分区,一时也不会影响计算机的运行。但由于体系庞杂,不同准则和功能共处一域,难免紊乱无序,甚至相互冲突,久而久之,随着内存负荷的增加,就会不堪重负,自乱阵脚;一旦遭遇病毒,甚至造成系统瘫痪。计算机遭遇病毒,无非是引起系统瘫痪;社会体系因缺乏领域界分而造成的病毒侵袭,引发的是整个社会的严重的腐败。这个例子间接地说明,与集中化背道而驰的分散化的领域界分,之于预防腐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恐惧生态学”——黄石公园的狼群与小白杨
白杨树是一种落叶阔叶树,到秋天树叶会变成金色,是美国西部最典型的树种,但它的数量长期以来却一直在减少。不过,自从1995年狼群在绝迹70年后重返美国最著名的国家公园,小白杨树50多年来首次开始重新生长。显然,将狼群重新引入黄石国家公园对那里的环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园的生态平衡又开始恢复到50年前那种比较自然的状态。难道狼群和白杨树之间还有某种神秘的内在联系吗?
原来,虽然狼群本身对白杨树的生长没有直接作用,但它们却通过科学家所说的“恐惧生态学”发挥了作用。
近些年来,这种食肉动物的回归使公园内麋鹿的数量减少了一半,剩下的麋鹿不再在它们感到特别危险的区域吃树的幼苗。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更多的树苗能够长大,有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不会再被麋鹿或其他食草动物吃掉了。科学家说这种现象显示了一个顶端为狼等食肉动物的完整自然食物链,如何使整个生态系统受益。自从狼群回来以后,柳树、棉白杨等其他树木就恢复了活力,白杨树也有了活力。*《狼群重返公园,生态平衡恢复》,《参考消息》2007年7月31日。
好一个“恐惧生态学”!正是得益于“恐惧生态学”的作用,小白杨树50多年来首次开始重新生长,公园的生态平衡才又恢复到50年前那种比较自然的状态。
难道自然界的“恐惧生态学”,不能给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以足够的启发吗?看看政治生活中不时爆出的贪腐丑闻,不正是发生于政治生态链产生断裂或者根本就无从构建的政治环境中吗?诚然,有政治生活的地方,就不免有腐败。但就腐败发生的几率和程度而言,政治生态链完整与否,与政治腐败发生的几率和程度,显然是成反比关系的。从人性的角度看,人都有趋利本性,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往往会忘记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本质,不免会权为己谋,权为私谋。这时候,就需要制度性的“政治恐惧生态学”发挥阻吓与制约作用,约束权力拥有者的私欲意图。
世界上有两种人性观:性善论与性恶论。总体上讲,中国文化崇尚性善论,代表性的言论是孔子的“人之初,性本善”;西方文化崇尚性恶论,基督教的“原罪说”就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性善论的预设,无疑限制了人们制度和规则意识的萌发,阻碍了一国一族的制度与法制建设;性恶论的预设,则无疑促进了人们制度和规则意识的生成,推进了一国一族的制度与法制建设。笔者既不认同性善论,也不赞同性恶论。前者把人看得太过美好,所以我们在日常交往中有时不免上当受骗;后者又把人看得太过丑陋,所以我们在日常交往中又不免时时有戒惧心理。我认为,从中庸的角度看,人性既不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丑恶,“人性本私”。为何在中国人的文化场域里,时不时会见到对“大公无私”的强调,而不是反过来,要求人们“大私无公”呢?这一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它说明人天生就有自私性,但私并非恶。一个人,自从在其成长过程中有了“人——我”认知的界分,就产生了私欲性,就有把身边的东西“据为己有”的私性意识。但“自私”不能说是个完全坏的东西,保护和利用得当,“自私”就是生产力,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以,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保护人们的合理合法的私性权利和私有财产,但同时又限制人的私性的越界膨胀,以免伤及他人的合法利益;而不是像我们曾经天真地相信和实践的那样,试图去消灭人的私有天性,消灭私有制,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侵害了人的基本生存权。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在基本理念或者是宗旨上,对于公民及其所属团体的法律权利,它是以保护为原则的;而对于公共权力及其行使者,它是以限制和引起恐惧为原则的。
为何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腐败案件发生较少,且程度较轻?盖因这些国家经历数个世纪的现代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的洗礼,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针对公共权力的“政治恐惧生态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着政治腐败现象的发生。
所谓“政治恐惧生态机制”,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完整的、环环相扣且相互制约的政治体系生态链的稳定存在。这一生态链的稳定存在,能够满足政治系统的健康运行,进而使整个政治系统受益。在这一生态系统中,诸子系统或要素在客观上互为负有监控责任的“第三方”,监控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近些年,笔者一直在从事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这一理论试图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论原则,揭示和把握政治现象及其本质。我们把“政治恐惧生态机制”看作是政治生态学所研究的“政治生态机制”之一。
《黄帝内经》有言:“不治已病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已变防渐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亦即要求人们不但要治病,而且要防病,不但要防病,而且要注意阻挡病变发展的趋势,并在病变未产生之前就想好能够采用的救急方法。就是说,治病的原则应立足于积极的预防,防患于未然。否则,等病入膏肓,再手忙脚乱地投医,就晚了。治理腐败亦同此理。只有通过制度化的机制积极预防和阻吓,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魏文王问扁鹊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於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闾。若扁鹊者,鑱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於诸侯。”*《魏文王问扁鹊》,《史记·鹖冠子》世贤第十六。这说明,治病救人,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防腐治腐也应学习采行扁鹊长兄之医道,对腐败“未有形而除之”,而不学扁鹊“鑱血脉,投毒药,副肌肤”,事倍而功半。
因此,中国机构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独立的政治、经济监管生态体系,建立体制内与体制外并举的政治生态恐惧机制,实现权力组织架构的生态化设置,阻吓腐败于萌芽状态。
四、政治生态恐惧体系的构想
政治生态恐惧体系包括体制内政治生态恐惧体系和体制外政治生态恐惧体系。
从肌体的生物学存在角度看,某一肌体的生存,取决于其良好的免疫力。良好的免疫力,使肌体清楚地识别“自己”与“非己”抗原,对“自己”抗原形成天然免疫耐受,对“非己”抗原排斥攻击。因此,免疫作用的对象是具有抗原性的异物。具体而言,免疫具有三大生理功能:防御——抵抗病原体的侵袭;自稳——及时清除体内衰老、损伤的细胞(自稳功能紊乱,会导致过敏及自身免疫疾病);监视——及时识别、清除体内突变细胞。免疫系统由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组成。
良好的免疫力,就是肌体的“自净力”。但是,这种免疫力和自净力,往往因为肌体的结构原因而受损。此时,就需要来自肌体外的“他净力”,帮助肌体行使免疫功能,完成自净力不能完成的任务。当然,这是以肌体的生态开放性为前提的。开放性建立起肌体与外部环境的信息沟通和能量交换关系,使他净力得以通过这种关系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就任一肌体而言,其生命力的长短取决于其开放程度,以及其自净力与他净力的平衡程度。政治生态学无疑是把政治体系看作一个类似于肌体的有机开放系统,在其自身体系与外部环境保持持续而稳定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过程中,通过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构建起良好的政治生态恐惧体系。
(一)体制内政治生态恐惧体系的构设
1.改革执政党的内部监督机制,实行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并赋予纪委体系以相对独立性。
党代表大会是同级党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是实施党内民主的重要机制和场所。因此,只有改革现行党代表大会的非常任制为常任制,使党代表的职能得以连续性、持续性、稳定性地发挥,才能够更好地限制党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主要成员的权力,落实对权力执行机关的日常监督。
相对而言,纪委体系架构的改革更富成效。党章赋予纪委以“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能。党的七大、八大和十一大党章规定,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1980年2月,中央批准地方纪委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但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十二大党章规定地方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不再沿用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表述。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规定:“加强上级党委和纪委对下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健全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常委的经常性考察和定期考核机制。加强常委会内部监督,主要负责人要自觉接受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加强同级纪委对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探索建立同级党代表大会代表、全委会对常委会工作进行评议监督的制度。”但是,在现行的纪委在人事和财政上对同级党委与政府有关联关系的状况下,上述规定怎么落到实处,还有不少亟待解决问题。纪委系统在人事和财政上的垂直化运作,是强化其监督职能的唯一出路。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会分工负责”的要求。根据这一精神,从2006年1月开始,在省级党委换届过程中,省委副书记这一层级便开始削减,新任命的省纪委书记不再像过去通常所安排的那样担任省委副书记,而是只担任省委常委。 从表面上看,这一变动似乎使纪委又回到了2001年之前的状态,降低了纪委的地位,但实际上由于中央掌握了省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削减了地方党委对地方纪委的影响,使得纪委书记的独立性和分量得到加强,其实际效果也许会大于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的横向管理模式。况且在常委分工负责的情况下,减少省委副书记这样一个层级,对于提高纪委的监督检查效率,优化纪委的工作环境,是有利的。但这一规定还没有上升到法规的层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36条强调,“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作为其实施路线图,首先给出了改革的“第一落点”,即“建立健全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报告工作制度”,并明确提出了“五项制度”,即定期报告制度、专题报告制度、即时报告制度、约谈制度、处置反馈制度,以要言不烦的方式基本覆盖了纪委工作面和主要业务链,进一步明确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工作的知情权、话语权和指导权。尤其是,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基础上,《实施方案》明确了领导干部任免的垂直架构:“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就在组织人事制度上,界分和渠化了纪委的隶属关系,对于其政治生态制约职能的正常发挥,意义非凡。
2.改变人大代表的构成成分,强化代议机关的监督职能。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和监督机构,人大代表人民依法监督政府工作,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监督政府对于行政权力的行使。但是,它的监督职能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与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不相匹配。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大代表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官员,这种组成结构自然削弱了代议机关对政府的监督力度。这就像是在足球场上,踢球者既是球员又当裁判,一身二任,等于是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其效果可想而知。从反腐败的角度看,人大的职能是代表人民行使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因此它属于“异体监督”,就好像医患关系,医生给病人看病,因为病人是“他者”,医生才能客观诊断,针对病势果断下药;行政官员变身人大代表,一身二任,就成了“自体监督”,就好像医生给自己看病,怎能客观诊断?又怎能针对病势果断下药?从最大程度上发挥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与监督机关的职能的要求出发,必须改变代表成分的构成,在法定层面,按照社会各界别、职别的人口比重,设定各界代表的比例数目,并大幅减少官员的成分。
与之相关,目前人大的监督力度的不足,还体现为行政问责制问责主体模糊的问题。我国《宪法》第3条、第128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当然,各级人大要通过立法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它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手段的运用,如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罢免等权力。但遗憾的是,目前的问责主体仍主要是行政部门,行政问责主要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在监督性质上仍属于自体监督,而不是法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这无疑大大削弱了问责的力度和公信力。从权能归属上看,人大无疑应强化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面对一些社会影响恶劣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对直接相关的行政责任人,人大应启动其监督职能和机制,依法行使质询权,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否则,人大就有不作为之嫌。但是,正如上述,人大代表构成成分的官员化,无疑束缚了其法定权能的正常行使。
相比之下,政协委员更多地来自民主党派、无党派和民营经济人士,顾虑较少,没啥负担,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什么就说什么,批评往往一针见血和切中时弊,似乎更接近监督的本义。而政协委员一般都是每个界别中的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体育精英、科技精英、学术精英,精英参政议政,这种相对强势的身份就给了他们参政议政相对强势的理解,意识到自己是被推选出来监督政府的,也就不会有下级心态,不会总是看领导脸色说话。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的他们,有勇气为本群体利益代言;整体的高素质,也使他们有能力做出一些批评和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曹林:《委员为什么比代表更敢言》,《山西晚报》2009年3月10日。
3.改革行政监察体系,改变一府两院的现行权力架构,赋予两院以相对独立性。
在打击腐败方面,没有什么比透明、舆论和不偏不倚的第三方执行者更有效。典型的例子是新加坡的反腐经验。从1959年政府成立,新加坡就在腐败没有蔓延之前予以根绝。他们加强了反腐败法律的制订,赋予贪污调查局强大的权力,对在薪水之外拥有不明来源资产的官员进行调查。在法律面前,官员必须证明自己的财富并非贪污所得。我们的腐败问题日趋严重,从司法体制角度看,就在于缺乏一个类似新加坡那样相对独立的、健全的、因而强有力的司法制度。目前的司法制度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主要集中于司法机关的双重隶属关系——业务上以及人事上由上级机关指导、监督和管理,同时,地方政府负责财政保障。这种体制,使得司法权地方化的趋势日益严重,这是亟待解决的司法痼疾。此前有很多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地级和县级法院的财政都由同级政府承担,由于财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司法公正。建议将地方法院的财政统一交由省财政来承担,省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财政由国家承担。
完善司法制度,提高法院的威望和独立性至关重要。因为法律层面的反腐败措施及其效率,都取决于司法体系的独立性。这还是前面所涉及的领域界分的问题。诸多司法腐败属于权力占有者之间缺乏制度性区隔的体制性腐败。如本该作为第三方公正审判的法官,同替当事人说话的律师之间缺乏制度性区隔,从而形成了法官、律师间的相互利用状态。在法律诉讼中,律师处于弱势地位,而很多时候法官的裁判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就给了法官上下其手的机会。律师乃至当事人都会明白,案子的胜负并不取决于法律和事实上的规定,在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法官个人的偏向或者是更高权力官员的干涉。
当然,司法机关相对独立,也会出现司法机关滥权的腐败问题。所以,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设计来监督司法机关。比如说,完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受理、交办、核查、督查、终结机制。大力推广涉法涉诉非正常信访案件公开听证制度,完善涉法涉诉案件的错案纠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反映执法人员徇私枉法、失职渎职的突出问题,建立检察机关核实调查制度。
4.行政系统制度体系的垂直建构和垂直运作。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一直执行的一项战略就是,依赖快速的经济增长维持稳定。然而,这种战略有着巨大的延时成本。这一战略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它阻碍了法治进步和文明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稳定的沉迷大大削弱了管理部门的能力,使之难以管理更具活力、更复杂的经济,而且无法监督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人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却不对公众负责。
让问题变得更糟的是,这种管理模式让地方官员拥有了太多的权力,而剥夺了一些关键性管理机构的自主权。所以,理论上说,我们拥有无数旨在让其食品、药品和消费品更安全的法律和法规,管理机构可能也有名义上的权力和授权。但事实上,此类监管机构很多是无效的,因为它们的关键人员都是由地方上的官员任命的,因而自然为地方上的利益服务。
这种局面造成了两个冲突。从制度上来说,一个监管机构的任务就是确保产品的安全,但地方官员更关心当地的经济增长,因为他要借此来升职。所以,地方官员更愿意允许他管辖范围内的公司——纳税者和就业机会的创造者——从事监管者认为有害的活动,例如污染和生产不安全或者假冒的产品。由于地方官员和监管者之间存在不平衡的政治权力,所以这些地方官员通常更易为所欲为。
当地方官员能够从这些经济活动中获利时,就出现了第二个冲突。为了寻求保护,企业主会用金钱和公司股份贿赂地方官员。结果,公司生产的有害产品对于地方监管人员来说,就成了碰不得的产品。
不解决廉政建设的制度缺位问题,或者是设计出了廉政制度,设若这一制度不能够实现垂直运作,地方政府就会基于自身利益,以及其对相关部门人、财、物的掌控而形成的干预,使廉政制度陷入尴尬境地。
5.完善民主机制,实现决策公开和决策民主。
上述几个方面的体系构设,每一项都与民主机制息息相关。民主才是根本和前提。民主就是约束公共权力、保护公民的利益和自由权利的制度机制。民主对于政府是治理方式,对于人民是现代政治生活方式,标示着生活品质。没有民主以及相应的法治保障的生活,很难说是一种安全的、有尊严的生活。
民主制是社会与人性自然进化的逻辑结果。比较而言,传统专制政治是赖于有限的个人理性,以专制者的个人喜好,借助高压态势,自上而下管控众人之事;现代民主政治,则是集合相对无限的众人的理性,众人制定游戏规则,然后委托代理人,依法律规则管理众人之事。前者,权力“天赋”;后者,权力民赋。前者,权力单向运作;后者,权力双向互动。因此,后者更富科学性和人文性,内含纠错机制,更具生态可持续性,而为现代社会所信仰和追求。但即使是民主制度,也离不开监督与制衡。凡是政治权力,不论其来源如何,无不具有扩张性,被滥用以谋取私利。因此,必须设计和构建起一个相对完善的政治生态系统,以形成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这是政治生态学的民主观。*刘京希:《如何看待民主的困境及其前景——基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期。就此而言,民主决不是给少数权势人物锦上添花,安排他们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那不是发展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对权力进行监督、制衡,因此,人民应该有“知”的权利,知情而后才谈得上参与。
腐败问题同其他诸多政治问题一样,要得到彻底解决,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发展政治民主的根本环节上来。从某种层面上看,目前的腐败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只要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和条件不除,而只是忙于革除腐败的毒苗,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效果未必佳,就只会是“腐风吹又生”。 其实,找到腐败的源头并不难,难的是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堵住这一源头。因此,制度性腐败,还得要靠制度性对策才能根除。这就需要把对干部的选拔和监督置于阳光之下,众目睽睽之中,以改变和消除产生腐败的制度环境与条件。
(二)体制外政治生态恐惧体系的构设
1.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形成来自民间的自组织社会监督力量。
假如一个国民,生下来就只有被动接受的权利,而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没有建议、讨论、质疑和监督的权利,没有作为社会之主人的主体性权利,这样的国民对国家是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相应地,这样的社会就是专制社会。与之相反,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会提供让社会精英与具有自觉意识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各类政治团体也踊跃拉拢这样的精英和公民,吸收新鲜血液。只有这样,社会才有活力,国家才有凝聚力,执政者才有认同度。而专制社会总是排挤、打击精英,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怀忧丧志、遁入空门,甚至走上偏激或者对抗的道路。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注重经济建设向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的方向转变。但这种转变,更多的是从强调经济效率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转变,但在公民的社会与政治权利建设方面,仍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缺憾,有时社会个体的公民权利残缺不全,甚至遭受公权力的侵害。
公民权利建设,既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上切实解决公民权利的落实和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问题,应尽快纳入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的议事日程。我们过去一直对权利和权力的性质、运行机制、变化趋势研究不够,以致两方面落实得都不好,现在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权利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于公民权利建设,其中的要害,是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的无障碍运作和实在的司法保障。在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往往形成矛盾甚至对立关系,政社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且,在这种矛盾关系及其博弈中,公民的个人权利往往成为社会发展和政府权力的牺牲品。面对强大的政府权力,失去司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可以想象,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与之相关,在社会体制的层面,公民及其组织——社会团体,还远未成为监督与制约腐败行为的自组织社会监督力量。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或者说忽视了社会团体作为体制性力量进入监督与制约体系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说,公民及其团体作为社会监督的力量,还远远未被视为独立的第三方力量。寻找一种制度机制,并通过这一机制,把民间社会团体组织与整合起来,使之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以第三方的立场,对政府行为进行评估与监督,无疑会大大增加政府的诚信度和政策的执行力,大大减少腐败行为发生的几率。这里的前提,是从法律角度对民间社会团体的赋权。权力与权利构成一对矛盾,公民及其团体手中的权利扩大了,政府手中的权力相应地就变小了,就受到了更大的制约,其滥权与腐败的可能性,自然就会大为降低。在制度环境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要求权力做得越多,我们付出的权利也就越多。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公共事务留给以权利为主体的公民社会,交给第三方,以减少政府的事权,进而减少其行政腐败的机会呢?
2.在法律层面保护网络政治生态恐惧机制。
有统计显示,在内地每天有大约3000个新网站诞生,每月有600多万新网民涌现。由于网络正在成为民间反腐的有威力的阵地,因此网络反腐越来越普遍,网络反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官员们借“考察”名义出国观光、公款消费,到抽名烟戴名表,再到公款按摩,不一而足,都是由网民揭露的。网络的无处不在,网民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不凡表现,以及网民作为一个群体的不断壮大,显然已经使之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甚至有的地方,网民被选为地方人大代表。自由摄影师张晓理就被选为河南省洛阳市人大代表。这表明,政府注意到了他在网上所做的事。
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网络监督力量已经超越报纸、期刊等纸媒,也正在超越广播、电视等视听媒体,成长为最令腐败分子惧怕的体制外反腐机制。怎样巩固和扩展这样一种新型的民间反腐力量呢?从政府的角度看,首先要对网络力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识到它是一种健康的社会力量,是清除政治肌体上的有害细菌、保障政治肌体健康运行的“啄木鸟”,啄的时候感觉有些疼,但过后会让肌体更康健。基于这样的正确认识,其次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网民对于政治运行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之更加合法地、有的放矢地行使监督权,而不是像时下通过“小道消息”等非正规渠道,无序地行使监督权,如此呈现的民意状态,对执政者及其政府形象的认知和塑造,有百害而无一益。
那么,网络作为一种政治生态恐惧机制,其最令滥权者恐惧之处在哪里呢?
首先是它的无处不在。它是“看不见的战线”,腐败分子无以防备。有调查资料显示,88%的受调查者通过网络密切关注各种事件的后续发展,近82%的受调查者认为互联网是民主建设的一条新途径。从南京高价烟局长被免职直至被司法调查,到“雷公”雷政富被立案调查,一系列反腐案件的曝光,无不拜网络力量所赐。而今,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反腐的利器更是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举报贪腐、收集证据的利器。
其次是它的无时不在。它是“实时监控”,到处都是反腐的网民“电子眼”,腐败分子无所遁形。把要寻找的特定人物的个人信息公布在网络上的所谓“人肉搜索”,就是网民的“电子眼”。“人肉搜索”已经让一些腐败分子如坐针毡,食不甘味,寝不安梦。这些移动终端不仅方便公众进行实时监督,也使贪腐行为无所遁形。政府官员的许多违规违纪行为,比如公车私用、会所聚餐等,多是公众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予以曝光的。
再次是它的全员动员。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951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0.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3.9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 10.1 个百分点。网民个人上网设备进一步向手机端集中,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手机网民规模已达 6.20 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com.cn/hlwfzyj/hlwxzbg/201601/P020160122469130059846.pdf.因此,在以移动终端为主体所构设的网络环境下,说网络反腐是“全民皆兵”,丝毫不为过。此时,每个网民都变身为斗士,每人一块“板砖”,每人一口唾沫,足以让腐败分子身败名裂。网络虽然是虚拟世界,但其从现实到虚拟再到现实的双向互动性和沟通性,对腐败分子而言,却是足以令其现形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但是,网络反腐也暴露出它的局限。首先,受限于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不足。政府信息公开是践行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这是民主体制的通则。在民主体制下,不管是直接民主如公民表决式民主、直接选举式民主,还是间接民主如代议制民主——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公民进行政治参与,行使民主权利,必得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前提条件下方可进行。而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更加离不开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尽管该条例所称政府信息,仅限于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并不包含一届政府的产生过程的相关信息,但我们不得不说,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制度性进步。只是,由于制度属于条例性质,而不是法律条文,存在强制性不足的缺憾,“应当”的成分多于“必须”的成分,所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选择性公开”的现象。对于事关反腐的公务人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虽然已经实施,但由于缺乏跨行业、跨部门的统一的网络平台,以及个人隐私的界定难题,使得这些申报和内部公示,并未达到社会性的信息公开的程度,公民无法通过相应的平台确认其真实程度,这也就严重削弱了公民参与网络反腐的力度。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女总理默克尔2007年访华的时候,在南京期间,她没有入住南京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层四千多平米、可以尽览南京全景的总统套房,而是住在面积只有七百多平米的普通套房。一个堂堂富国的总理如此俭朴,不仅让中方接待人员、酒店员工颇感意外,也让那些乐于公款吃喝玩乐的中国官员汗颜。《澳门日报》就此指出,德国总理不住总统套房而住普通套房,除了个人原因,更重要的是制度使然。在德国,公务消费奉行“零容忍原则”,任何铺张浪费都不可容忍,都可视为腐败。德国对官员的公务消费有着严格限制和监督,总理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德国官员的消费清单是公开的,公众随时可以查询。如果有官员大肆挥霍公款,那他面临的将不仅仅是舆论的质疑,很可能因此丢官甚至锒铛入狱。*中新社:《制度使默克尔不住总统房 让中国官员汗颜》,《澳门日报》2007年8月31日。
其次,网络反腐权缺乏法律保护。网络作为信息时代最伟大的发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还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场域。公民网络参政议政,既是政治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新变化,也是公民行使宪法权利,参政议政的新途径。近年来,公民通过网络发表意见,不仅直接导致了个别事件的正确处理,还不断推动着社会文明的进程,带来了政治生态和法治环境的改善。但是,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因网言获罪的消息也时常见诸媒体。从“高唐网案”到“王帅帖案”,再到“王鹏错案”,等等,说明在一个深具“官本位”传统的权力化社会,完成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使命是何等艰巨。我们所指公民网络反腐权利缺乏法律保护,不仅仅是指缺乏部门法的保护,如反腐法规不完善,尤其是网络反腐法规付之阙如;根本上说,是指宪法权威一直没有得到公共权力的应有尊重。而个中原由,在于缺乏一个护宪机制,来维护宪法的神圣权威。
我们之所以强调对公民权利的司法保护,是基于以下的事实与思考:在宪法和法律的层面,当下中国公民并不缺乏基本的公民权利,像生存权、发展权以及必要的自由权利,宪法和相关法律都有明确界定。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这是公民网络表达权的最高法律保障。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公民权利被国家权力侵害的事件?盖因在具有深厚官本位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权为谁所谋、权为谁所用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在权与法的较量中,宪法与法律在政治权力面前,缺乏文本上所强调的权威;面对政治权力的挑战与侵害,因为缺乏制约机制,宪法与法律显得有些无助。既有的司法体系,因为体制结构上的原因,面对政府权力在事实上所形成的对宪法和法律的侵害,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也显得无能为力。甚而至于,在公共权力包括司法权力的行使者看来,法律不过是权力的护持,而不是对权力的限定。如何扭转这种尴尬状况?建立独立的护宪与司法审查机制,是唯一的可行之途。或可改革现行司法体制,赋予其护宪与司法审查的职能,相应地,强化其组织结构及人、财、物供给体系的独立性,切断其与政府权力体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真正成为有独立的赋权的、具有明确的权力监督职能的司法体系,使之形成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力量,进而起到平衡政治生态环境的作用。
五、结语
无论是社会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凡是集中体制,都具有非生态性。而正是其非流动性和集权状态,易导致腐败。权力相对集中而强势,当公民个人应有的法定权利遭受公权力的侵害时,难以找到秉持正义的后援力量,这使得社会在各个方向都有走向极端的可能。权力集中让社会可以迅速地朝着某个方向迈进,但是个人权利的缺乏,意味着在这样的时候,听不到社会作出的反应,因而就不清楚这样的方向性选择是否与社会的总体期望相吻合。这样的体制,所呈现出的是单向的、发散式的权力运行状态,因为缺少生态回路而不能形成对权力的相应制约和及时回馈。即使有所回馈,也因体制的向上负责性,使得下级在多数情况下,选择报喜而不是报忧,底层真实的声音从而被彻底消弥于无形,体制性的腐败也在所难免。
相反,在民主体制下,个人拥有体制上的话语权,个人是体制及其决策的“回音壁”,而不是“消声器”。从政治生态理论的角度看,民主体制是个完整的闭环形生态回路,政策或者决策能够沿着这个回路,不间断地形成反馈,从而持续地校正和修正着政策、决策与公务人员的公务行为。同时,民主体制的权力分散本性,还使政治决策等权力行为,总是处于“第三方监控”的状态,很好地避免着体制性腐败的爆发,而不至于造成社会性的重大失误。
当然,有政治生活的地方,就不免有腐败。但就腐败发生的几率和程度而言,制度性政治生态链完整与否,与政治腐败发生的几率与程度,显然是成反比关系的。从人性的角度看,人都有趋利本性,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往往会忘记政治权力的公共本质,不免会权为己谋,权为私谋。这时候,就需要制度性的“政治恐惧生态学”发挥阻吓与制约作用,约束权力拥有者的私欲意图。此时,制度性的第三方的独立而权威的存在,对于遏制腐败,就显得尤其重要。而以发挥“第三方”社会责任为己任的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建构,无疑是“政治恐惧生态机制”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根本上说,完善民主制度,赋予民主的主体——公民——以“第三方”的社会责任,利用公民及其代表手中所掌握的选举、罢免、弹劾、质询、听证等公民权利,约束权力代理者的权力行为,阻吓与制约权力代理者的越权言行,当是“政治恐惧生态机制”建构的最高境界。
责任编辑:李宗刚
Constructing a Perfect Political Ecological Chain System:On the “Fear Ecology” of Corruption
Liu Jingx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Where there is political life, there is corruption. But in terms of its probability and extent, the integrity of the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logical chain, occurrence probability and degre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are of inversely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obviously. Man is with an interest tendency in nature, those in power often forget its public attribute, and they inevitably use it for their own personal and private ends. For this, there needs to be a system of “political fear ecology” to play a deterrent role and to constraint the private desires and attempts of the dictator. The existence of independence and authority of the third-party is “the ecological mechanism of political fea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judicial system playing the “third-par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its own responsibility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litical fear ecological mechanism”. Fundamentally speaking, a perfect democratic system, entrusts the subject of democracy——the citizen——with the “third-par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at is, by making use of election, recall, impeachment, inquiry, hearing and other legal rights in the hands of the citizen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to constraint the behavior of the power agent, and resist and restrict their unauthorized actions. And this should be the highest stat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fear ecological mechanism”.
political corruption; political ecology; the third-party; judicial system; civic rights; democratic politics
2016-05-01
刘京希(1959—),男,山东齐河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重点项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变迁研究”(13AZZ002)、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构建完善的政治生态环链体系”(02520828)的结项成果。
D621
A
1001-5973(2016)03-008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