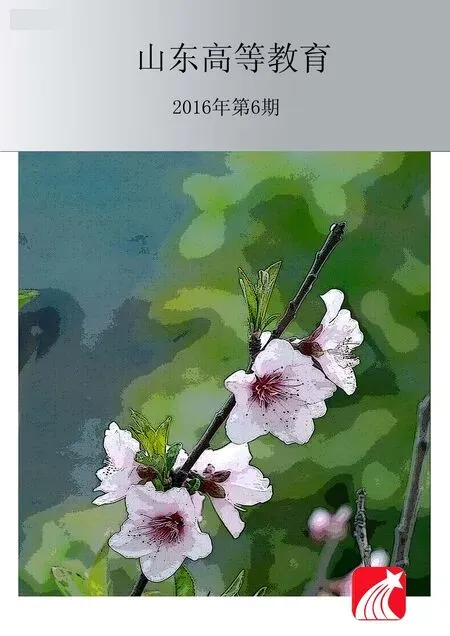大学校长要努力成为政治家与教育家
——朱九思的实践探索
陈运超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7)
经过百年探索,尤其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艰难发展,在颇具得失的经验中,我们越来越感到,对于大学发展来说,政治家与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是稀缺的宝贵资源——要实现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一定离不开大学校长的独特远见、坚毅胆魄与务实作为。因此,研究那些取得突出成绩并得到实践检验的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对于大学的发展以及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新中国诞生后,20世纪50年代的院校调整改变了许多大学和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发展高等教育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包括朱九思先生在内的一批经历血与火考验的革命家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们的实践探索成为我们今天的宝贵财富。研究他们治校办学的成功经验、研究大学校长的成长,对于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原点式启发价值。
1953年,朱九思受命筹组华中工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紧密黏合在了一起——他在华中工学院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任职达31年,长期致力于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与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治校成就,“为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其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现了华中工学院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变,使这所在新中国旗帜下成长的大学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被誉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1]。他赢得了海内外校友和师生的爱戴、全社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尊重,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锐意改革的先锋与卓绝探索的代表,给我们面向未来的办学留下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给高等教育研究留下极其重要的成功案例。
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大学应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大学校长应努力成为政治家
大学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而历史与文化总是地域的,地域的又总是政治的。地域是大学的基因,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大学的发生与发展是不能超越政治而存在的,总是受制于举办地的体制与举办者的意识导向——意识形态的决定力量。无论是意大利、法国与英国,还是德国、美国与前苏联,他们的大学都打上了他们的烙印,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既给大学插上了发展的翅膀,又给大学拴上了历史的枷锁。大学校长的治校办学必须首先适应、然后引导大学在政治约束与思想自由的关系中获得空间,跋涉蠕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并建立新中国。中国的高等教育必然会刻上中国共产党的烙印,新中国的大学必然不能超越政治体制的规制。新中国的大学校长必须遵从意识形态与教育规律的制约。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者,便能取得治校的成效;反之,便可能顾此失彼,得不偿失。举凡新中国的优秀大学校长无一例外,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因此,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大学应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大学校长应努力成为政治家。
政治家并不总是政治、政党人士的专利。凡是在一定政治体制下,有所作为的事业家都须努力成为熟悉政治、理解政治、并能娴熟运用政治力量的政治家。大学校长作为工作于具有较强政治色彩之大学的领导者,要实现治校理想,只有努力成为政治家才有可能。
自然,大学校长成为政治家与政治等方面的领导人成为政治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共性是都必须研习政治规律,善于运用政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建立并探索不断完善的政治体制与机制。但是,大学校长成为政治家总体上还是处于执行层次,且重在能够于熟悉的政治构架下,自如地运用政治方针与有效策略,拓展办学空间,获得治校自主;重在运用有效的政治机制与手段,推行办学主张,实现治校目标。同时,还必须结合高等教育规律,在适应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政治对高等教育的规约,并通过政治在高等教育中的运用对政治以适时反馈,通过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来推动政治的变革与发展。因此,大学校长成为政治家必须遵循政党政治的体制,熟悉并熟练运用政治运行机制与优势力量推动大学的发展,把意识形态的规约转化为治校办学的积极要素,并在治校实践中予以贯彻和落实,运用政治的力量,获得政体的支持,为大学发展提供政治导航与和谐环境。
朱九思作为大学校长, 30余年的时间一直致力于在新中国举办高等教育的伟大实践探索。他在办学实践过程中,经历了新中国全面苏化、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但是,无论在任何时期,朱九思始终以革命家的胸怀和政治家的气魄,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不动摇,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丝毫不能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培养“四有新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保证了正确的办学方向,保证了政党意志在办学与人才培养实践中的切实贯彻与落实。
与此同时,得益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体制机制的洞悉,朱九思在全国大学几乎停办、最难以看到希望的阶段,依然在毛泽东一句“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①的昭示下,看到了曙光与希望。因此,当“文革”仍在大江南北轰轰烈烈展开的情况下,朱九思漫步于偌大而空荡的校园里,主动思考如何办好大学,毅然推动相关部委,筹划新办包括激光、通信、计算机等一批新技术工科类专业,使得华中工学院的专业不像其他大学那样急剧减少甚至被肢解、撤销,反而由“文革”前的18个增加到“文革”结束后的36个。与此同时,他大胆地从全国各地大量罗致被政治遣散的“臭老九”充实师资,教职工人数由1970年的3249名(其中教师1138名)增加到1977年的4419名(其中教师2005名)。[2]这为华中工学院在“文革”后的迅速崛起以及后来的发展奠基了理工学科框架、奠定了发展的人才基础。获得这样的办学空间,既是朱九思主动运用政治智慧进行综合判断的结果,也是他因多年革命锻炼所铸就的政治胆略而采取的先手举措。
在中国举办社会主义大学还必须是中国的大学,必须打上中国的烙印,具有中国特征的情愫,而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大学的模式。大学校长成为政治家就是要在面向世界的同时,探索中国的创新元素,力推中国的大学出特色、上水平。如何实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学治理?如何在绝对执行与主动作为间寻找平衡?如何把政治意识形态化为治校办学的创举?如何协同不同学科、不同工作性质人员的行动与利益?如何在借鉴他人、继承传统中创新思路、超前发展?这既是中国大学校长对政治的重要贡献,也是对世界高等教育的有力丰富。
朱九思他们那一代大学校长注定要在学习中借鉴,在选择中探索,在扬弃中建构。新中国成立之时,苏联模式成为大一统之后,如何突破?改革开放之时,美国经验成为新宠之后,如何实践?这些既是大政治,又是大教育。难免忽左忽右,考验着他们的政治智慧。不过,改革开放营造的大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大机遇。朱九思在搬用苏联体制下的执行与反思,在借鉴美国体制下的学习与探索,都反映出大学校长要努力成为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实践理性。无论是他突破体制与思想禁锢举办新专业,实现学科综合化与研究型的转型;还是大举收罗与培养、重用“老九”,寻找并奠基大学发展的人才支撑,无一不是政治探索,无一不是治校智慧,无一不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学、对中国大学实现政治与教育有机统一的丰富与实践。他在长期的治校期间,先后分别担任书记、校长,并曾书记、校长一身兼任,也为我国大学书记、校长间的分工、分设,合作、合并,以及党委与校长间的关系,书记与校长任期与考核等方面,提供了值得研究的实践案例。
中国大学应该是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须有中国传统与文化的印记,这是基本的政治要求。朱九思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好理解,对近现代中国发展建设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他始终强调在虚心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办学经验的同时,必须强化中国特质,要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烙印,要与中国问题和学校、学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他倡导和研究、推动文化素质教育、重视举办哲学、文学、经济学等文科、社会科学专业,并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课程和讲座,培养有中国心的中国人。
二、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应该始终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大学校长应努力成为教育家
大学校长应成为教育家乃天经地义,没有争议。之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并呼吁大学校长要成为教育家,是因为我们的时代不幸缺乏这样的大学校长,我们现有的许多大学校长不幸缺乏教育家治校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关于教育家方面的研究,文献丰富,本文不再赘述,想强调的是,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必须以教育规律、学术规律为遵循,要具备以下两种素质:第一,在既有传统与体制下,善于发现并捕捉机会;第二,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善于面向未来并开创未来的胆魄与能力。
第一方面是大学校长如何运用现有体制的力量,活化办学机制,在规束的框架下,发现机会,获得别人没有的资源。这是教育家的胆识与机敏。另一方面,大学校长须保持开放的学习心态,借鉴他校、他人的经验,综合判断未来走向,按照规律,突破现态的桎梏,探索新的模式,开创新的路径,实现新的目标。这又是教育家的谦恭与自信。
回顾起来,无论是意大利、法国,还是英国的古典大学,其校长无不是在有效利用并大胆突破宗教的禁锢、国家的管束、传统的制约,从而实现大学的生存、发展与转型。现代大学之所以能够在德国开花,得益于洪堡运用国家力量举办大学,并根据教育与研究的发展走向,适时推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在大学落地生根,建构教学与研究有机结合的现代大学制度。同样,吉尔曼作为美国19世纪中后期杰出的教育家,学习并借鉴德国大学的先进办学经验,在大胆探索的基础上,于1876年成功创立了霍普金斯大学,创办起美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开创了研究生教育的新纪元,并坚持以人为本、科研为首、学术自由的办学原则,很快成为众多高校学习的榜样,开创并带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体系逐渐形成。[3]1904年,范·海斯(Charles R. Van Hise)出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在担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的15年间,他把英国住宿学院和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所有优点结合在一起,把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发扬光大,并使威斯康星大学的办学模式的影响扩展到全国甚至国外。[4]直接运用大学的资源和能力解决公共问题、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威斯康星理念”因此逐渐发展成为大学的三大职能之一,推动并丰富了美国赠地大学的发展。作为教育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在大学的发展史上写下精彩的乐章,为大学校长的研究留下宝贵的案例与实践借鉴经验。他们都是运用体制、变革体制的高手。
回到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我们无不为政治体制的约束而感叹,另一方面又无不为政党推动大学实现大发展而兴奋。作为新中国的大学校长,他们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高歌猛进,以及极左路线的一统天下、右倾思潮反复冲击、改革开放的大快人心。但无论何时,他们都始终注意思索和探究大学的特点,按照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治校办学,从而使新中国的大学能够经风雨、见彩虹,奠基并成就了今天的大学。
同样,朱九思在华中工学院的实践就是体制动力与自身竞力相激荡的结晶。他在当时的时局下,能够敏锐发现并捕捉发展机会,认识到并坚持人才是大学第一资源的基本规律,即使是在知识分子被视为“牛鬼蛇神”的背景下,也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始终清醒一贯。无论是在“反右倾”运动期间,还是在“文革”期间,他都不遗余力地保护他们,收留他们,支持他们。朱九思成为我们党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并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先进代表和基层实践的化身。“深挖洞、广积人”成为第一大“九思标识”。在那一段极其特殊的动荡时期,他毅然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从全国网罗各类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到学校工作,诚聘知名学者来校讲学、著述、担任学科负责人,为学校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奠定了最重要的师资支撑,留下来最重要的崛起财富。
认识到现代科学的综合化趋势,以及高等教育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规律之后,即使在苏联式专业化办学思想处于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朱九思也坚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推进学科综合化。新中国成立后,在全面苏化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以专业化办学为指导思想,纷纷建立起了像华中工学院这类学科单一的一批专业性、专科性大学。这种办学思想指导下的人才培养直接与职业需要对口,好处是人才培养的效率很高、实用性强。但是,朱九思认识到这不符合高速变化的时代需求,也不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专业面向太窄、发展性不足,不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综合的需要。同时,大学学科单一也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综合、交叉的发展。因此,朱九思大胆冲破苏联模式的禁锢,克服重重体制的阻力,在考察美国、加拿大、日本等现代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上,在深入思考和研究他们的办学经验与规律的基础上,学习借鉴现代大学治校路径,变革并突破体制的规约,运用行政的强力,大力推动学术生态的优化。他在全国率先提出并推动大学学科综合化,为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学科架构,也为后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系列改革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探索。学科综合化成为第二个“九思标识”。
认识到现代大学必须发挥研究职能,大力推动学术发展这一规律之后,即使在大学只是教学机构这种狭隘认识的历史背景下,朱九思也要推动高校的科研发展。多年来,我国学者在大学职能的认识和把握上是有分歧的。但是,朱九思通过不断反思与研究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认识到研究工作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建校初期、“文革放大假”的阶段,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只开展单一教学的现象比较普遍的情况下,他都艰难地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并在实践中大胆提出了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认为科研也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与教学之间是源流的关系。“科研走在教学的前面”这一实践理念成为第三大“九思标识”。主张研究走在教学之前,既是对洪堡思想的继承,也是对该思想的大胆突破。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科学春天”到来的时候,他才能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学校接过少数几张来自国家的表彰奖牌。
在认识到尊重学术和学术自由这一现代大学特征之后,朱九思无论是在行政至上的体制下,还是在从严治校的背景下,都倡导和坚持学术自由。他以治校严格著称,“从严治校”是又一“九思标识”。这主要是指他对行政管理的严格。虽然,他并无力改变现有体制下的大学行政管理架构,但他却认识并积极运用了行政体制的集中力量与效率,坚持治校要严的理念,强调行政的运行活力与效能。他治下的学校办事效率很高,无论是在推进突破政治性、体制性障碍诸如广纳人才这样的难事大事,还是直接指挥诸如植树等具体而细微的易事小事,都能说了就办,并尽可能办成办好。对行政管理队伍的严格要求成了华中工学院的习惯。但是,朱九思并没有因此推行大学的行政化,而是减少官僚主义,减少行政对学术的干预,学术上的事情交由老师,行政只是服务于学术的工具罢了。所以,在对待教师时,给予的是尊重和相信;在对待学术时,鼓励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争辩,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坚持对真理的探究学风,主张“学术自由是大学生命的真谛”[5],凡是学术上的事情由教师主导,行政只是提供条件的支持和宽松的舞台。
三、中国大学校长急需成为政治家和教育家,大学校长须具有政治胆识与教育风范
大学校长成为政治家主要是基于现实的发展,成为教育家则主要是源于内在的动力。然而,检验二者是否有机结合、是否相得益彰,只能是经过大学校长治校实践检验并给大学留下具有历史价值的、激励后人继续前行的精神财富,以及得到历史检验的、可实现持续发展的办学业绩。这是精神与思想化为传统与实践的结晶。历史上,凡是受到尊崇的大学校长无不如此。蔡元培留下的兼容并包思想依然启迪着我们,办学业绩仍然让我们称道。
同样,朱九思在建设新中国的大背景下,始终以政治家和教育家为己任,努力践行,体现出革命家治校的胆识、教育家办学的风范,为大学校长以及高等教育工作者流传下宝贵的精神财富,给大学校长治校办学以重要启示,给华中科技大学留下“敢于竞争,善于转化”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推动着大学的不断变革与快速发展。
这样的大学校长体现出高超的政治胆识与治校风范,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敢。这是尊重规律的政治胆识,也是办学治校始终如一的精神状态。在我们今天看来,前人所取得的成绩、留下的思想已经显得不那么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如果回到这些大学校长治校的历史背景,我们看到的是艰难而有力的突破,体会到的是敢于变革的超人胆识。能不能先人一步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希望、能不能捕捉到见微知著的机会、敢不敢在微弱曙光的引导下抓住机会并大胆付诸实践,成为大学校长是否可以铸就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分野。
今天看来,朱九思过去所探索并实践的很多事情都已经变得很平常,比如揽人才、建学科、搞科研、筑围墙、育树荫等等都是今天的办学常识。但是,回到当时浓烈的政治氛围、僵化的思想观念、严重的体制束缚、过弱的办学自主权和过少的办学资源,没有“敢于竞争”当先的胆魄、“善于转化”担当的能力,是不可能去冲击苏联体制的桎梏、冲击一统天下的计划体制牢笼的;没有放下自我一切利益的大无畏的政治家与教育家胸襟是不可能违上地去设计、去推动大学校长必须推动的现代大学综合改革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的。
是。这是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能力,也是办学治校始终如一的精神力量。举凡成为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大学校长,无不潜心于政治规律与教育规律的认识与研究,无不是把握并运用这些规律为实现治校目标服务的高手。毕竟,“不失其所者久”,违反规律的时代、违反规律的事情总是短暂的,都不可持续、都不可长久。
认识规律难,按照规律办事更难!实事求是难,在极左路线浓厚氛围的笼罩下、在集中统一的体制下,坚持实事求是就更难!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能否从本国、本校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按照高等教育的自身规律办学,而不是唯书唯上、急功近利地搞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也不是千篇一律、崇洋媚外地搞拿来主义和形式主义。办出中国特色和学校优势永远是大学校长的治校追求。
朱九思正是善于思考和研究政治与教育的规律,并能够把两种规律融合于一起加以有效运用。他在“文革”的空闲时间里,就在思考、总结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得失;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利用出国访问、跟老师交流得到的信息、阅读翻译有限的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有了对规律的把握,才能在极左思想的禁锢下看到曙光,当政治强制地胁迫教育规律时,也能迂回地从教育规律出发,判断未来走向,并大胆出手办专业、搞研究、引人才;有了对规律的认识,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迅速出击,培养人才、搞学科综合化。因为这才符合规律,符合规律才能持续发展。
爱。这是大学校长成就事业的内在支撑,也是办学治校始终如一的精神源泉。凡是成功者无不热爱自己的事业,无不把事业作为毕生的追求。如果大学校长有了对教育的热爱、有了对大学的挚爱,就会潜心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与发展,就可能全身心而不是三心二意地办学治校。只有有了对教育的真诚热爱,才能不顾一切地献身教育,热爱学生,尊重教师;才能不顾利益的诱惑和权力的吸引,专心办学,潜心治校。
大学是一个需要沉心静气,慢工出细活的地方。凡是有所成就的大学校长,无不任职时间长、醉心研究多、痴心实践好。朱九思先生从进入大学开始,一辈子没有离开,也不愿意离开他心爱的大学,一生沉醉于高等教育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把爱教育、爱华工融入了自己的血液直至天堂。
注:
①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做出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参考文献:
[1]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各界人士深情送别朱九思同志[EB/OL].(2015-06-17)[2016-04-05].http://news.hustonline.net/article/94409.htm.
[2]陈运超.大学校长治校之道:一个个案的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2002:52.
[3]黄镇.吉尔曼的办学理念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成长[J].继续教育研究,2006,(4):57-59.
[4]刘宝存.威斯康星理念与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J].理工高教研究,2003,(5):17-18.
[5]朱九思.大学生命的真谛[J].高等教育研究,200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