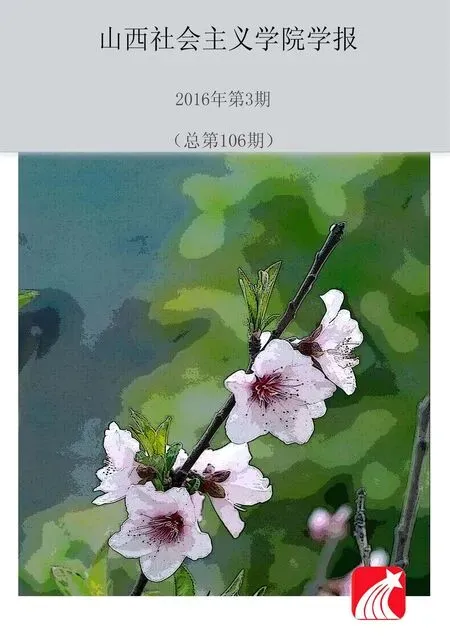明道待躬行 正学须复性——明儒薛道学人生的文化诠解
郭万金 赵寅君
(山西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06)
三晋人文
郭万金赵寅君
(山西大学, 山西太原030006)
明儒薛,山西河津人,明代继承程、朱的理学大师,明道躬行与正学复性构成了其道学人生的主要部分。薛毕生读书论学,一意以“履而行之”的“为己之学”为宗,既无著述传世的意图,更恪守述而不作的准则,以躬行明道的实践方式践履程、朱之学,传承道统。
薛;道学;人生;诠解
“权势利达无以动其心,死生利害无以移其志”①,薛一生正行,出处进退,辞受取与,莫不合乎礼义规范,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人格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无论是安贫乐道的恬淡怡然,还是入狱临刑的无畏坦然,抑或是仗义执言的气节凛然,儒学理念的信仰与秉承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浩然元气,亦正是这脉坦荡淋漓的浑然正气造就了一代醇儒,光明俊伟的仕宦生涯、刚直耿介的夫子品格、正道亢行的处世原则莫不折射出这位儒者对儒学道义的人生诠释。而此,亦即这位理学大师对儒学道统的核心理解。《明史》称“(薛)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斯道已明,直须躬行,寥寥数字,却大致标明了薛于理学史中的自我定位与历史选择。
一、明道待躬行
自孔子开创儒家传统以降,儒学的发展实在算不得履道坦坦,周秦诸子的鼓舌争鸣,焚书坑儒的极端政策,黄老玄学的无为清谈,佛学大盛的举世谈禅,以及兵戈并起的战事频仍,乃至儒学体系中经学诠解的繁琐沉闷,都对儒学的传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至有宋一代,周张二程,朱熹诸儒,直承尧舜孔孟之道,倡明理学。元初,经许衡、吴澄、郝经诸儒提倡,理学渐为统治者认可,明代“以理学开国”,太祖朱元璋诏示:“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②成祖朱棣下令辑成《性理大全》,颁行天下,程朱理学成为独尊的正统,更成为科举考试的经典教材,朱注《四书》被定为开科取士的规程和科试答卷的标准,诵读《六经》,亦“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击之”③。国家政策的干预使得明初思想变成了朱学的诠释,“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④。薛无疑则可算作“述朱”的典范,其不止一次称道,“濂洛关闽之书,一日不可不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学,则非矣”(《续》卷四),极端的推崇中虽有“卫道者”色彩,却已旗帜鲜明地标出了自己的学术旨归。其对朱熹功业的定位则在排斥邪说,阐明圣学,其称:“尧舜之道,非孔子无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无以发;周子程子张子之学,非得朱子为之发明,后世纷纷莫知所定论矣。”⑤(卷九)
“春秋之时有孔子,斯道大明;战国之时有孟子,斯道有寄。自秦汉以降,世儒以知谋功利相高,不知道为何物。故韩子曰,轲之死,不得其传。程子曰,退之必有所见,不知所传者为何事。窃谓,天命之性,道也。圣贤明此道,行此道,是以道得其传;不明不行,则天命之性虽未尝不具于人心,然人既不明不行,则道失其传矣。”(卷一)
道学传授的源流追述中正暗含着“明道”、“传道”的职责自勉,薛对程朱理学的笃信源自对圣学道统的信仰与珍重,由之萌生的则是对道学的自觉维护与传承,“道之失传”则是其最不愿也不能接受的。因而,宋儒之后的道学谱系中,元代大儒许衡成为薛眼中的道统承继者。对于许衡,薛评价极高,“许鲁斋,余诚实仰慕。窃不自揆,妄为之言曰:其质粹,其识高,其学纯,其行笃,其教人有序,其条理精密,其规模广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为浮靡无益之言,而有厌文弊从先进之意,朱子之后,一人而已”(卷一)。“朱子之后,一人而已”的定位实已将许衡置于道学传承的链条中,然其中亦隐含着以道学延续的使命继任。“鲁斋学徒,在当时为名臣,则有之,得其传者,则未之闻也”(卷二),薛对许衡之后“未闻传道”者的慨叹中既有担心圣学失统的焦虑,更可感受到其欲以明道传学的继统精神。元儒许衡正是明儒薛于道学谱系中引为楷模的典范。许衡亦言“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⑦,又称,“先务躬行,非止诵书作文而已”。其于四书的遵从信服,正与薛相通,亦是道学传承者们的共同心理。作为圣人志意载体的四书,是他们心灵深层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源泉。作为朱熹之后的道统延续者,许衡、薛的儒学实践大抵皆可称作朱学范式下的道统延续,同时,继任者的基本定位亦决定了他们“恪守宋人矩”的学术旨归,“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之法,潜心体认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卷一)。身体力行地循着先儒的经验法则体会圣人心意,以躬行实践的务实态度继承道统,恢明圣学。
“圣贤之书所载者,皆道理之名也,至于天地万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实也。”(卷一)书本知识仅是世间经验的反映与提炼,“绝知此事须躬行”,从文字到文字的理解实践并没有太大的益处。“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间,圣贤之书不过模写其理耳;读书而不知实理之所在,徒滞于言辞之末,夫何益之有!”(卷十)在薛看来,仅停留于文本层面的读书学习,很大程度是一种虚妄之学,因此“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见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以为口耳言辞之资,非实学也”(《续》卷三)。“实学”的提出正是其躬行主张的理论表现,其中更继承、发扬了儒学传统中的务实主张。
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安国曰:“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为己”之学的目标在自身修为的提升,躬行践履,于己实有所得;“为人”之学的目标则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徒以空言虚论炫耀于人,实无裨益之处。二程亦言:“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朱熹赞曰:“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⑧“为己”成为儒学正统的切要所在,薛更是以为治学之本。他主张读书,为学务要务实、求实,就是切实“体贴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卷二),“必欲实得而力践之”(《续》卷一一),方为“实学”,或叫“本领之学”(《续》卷一),“本领工夫”(卷二)。否则,“溺心于文字之间”,“徒事于记诵辞章之末”(卷九),“用于己全无干涉”(卷一),只能是“词章之学”(卷三)、“文章俗学”(卷九),也即所谓“为人之学”,“皆非本领工夫”(卷二)。“为己”之学原是循着“内圣外王”、“修己以治人”之宗旨而延伸的儒学训练。
“学优则仕”虽是被认可的实现“修齐治平”之人生理想的途径,但明代“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⑨,科举成为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与功名利禄紧密绑缚在一起,一般士人死读经书,习作八股,背诵词章,空谈性命,一心以科第博取功名,于国家大事、生民利病略不留意,科举之学自然随之沦为利禄之学。“十七岁始厌科举之学,慨然以求道为志”(《年谱》)的薛于此自然深恶痛绝,尤其他遵从父命,获得科名后,于科举之弊有了更深的体会,“科目进身者,有一第之后,四书本经悉置而不观,则身心事业从可知矣”(卷二)。科举弊端直接导致的是士风日下,道学不明,而此正是薛所最为关注的。对此,薛的批评更为激烈,“科举之文盛而理明者,间有之;因而晦者,尤多矣”(卷一),“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卷八)。更立足“为己”的古学传统抨击科举之弊,“朱子注《四书》,明圣贤之道,正欲学者务为己之学,后世皆藉此以为进身之阶梯,夫岂朱子注书之初意哉”?“圣贤专以为己之学教人,而犹有为人者,况以科举为人之学教人乎”。科举之学“其坏人才也甚矣”(卷四)!八股科举自实行之日起,就不断有人指出其中的弊端,薛的批判自然也是制度之中的弊端纠正,然而,他的批判立足于对科第弊端的实际观察,所秉持的是先儒“为己”的立学传统与明道动机,因此,薛于躬行主张下的科举批判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振聋发聩,而鞭辟入里的针砭中更有着务实对策的积极思考和履行实践。薛在任山东督学佥事时,即以“致知而力行,居敬以穷理,由经以求产”为宗旨,考察诸生,“必先询其力行,而后及于文艺”。削官归籍,设教河汾时更是“不事语言文字,而必责诸躬行之实”。
明代,科名功利驱使下的“俗儒”或“章句之徒”,背弃“圣人之言”、“先儒之义”,“或剿拾成说,寓以新名,炫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卷一);或醉心于“注脚之注脚”,“经文不过数语,而小注乃至数千百言”,“不惟有与经注矛盾处,亦以起学者望洋之叹”,“使人愈生枝节,莫知其本”,由之导致的恶果则是“后学者转相剽窃,但资侥幸利达,而无以资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卷四)!世风败坏,士行日下,学术空疏,成为明代科举八股于社会思潮、士人操行、学术品格的最大负面影响。科举虽有弊端却非十恶不赦,但由于制度缺陷与社会不良习气绾结,才造成了明代学术虚妄的恶果。薛倡言实学、标举力行,正有着裨补时弊的深刻意义。对“无烦著作,直须躬行”的薛而言,身体力行的践履、体会经典中所承载的圣人心意,以不贵言语的实践态度昌明道学方是正途,至于文字著作却非有心为之。其“所著,……盖惟体验身心,非欲成书也”⑩。“阅先生《读书录》,多兢兢检点言行间,所谓学贵践履,意盖如此”⑪。乔宇《薛文清公行实序》更称,“平生所著述,若《续读书录》诸书,咸明白简易,力挽末学词章之陋。盖其践履精纯,言与行相顾,匪若立异奇高无补于世者所可论也”。平实文风中所贯穿的正是一以继之的务实趋向与“述而不作”的传道准则。“孔子述而不作,学圣贤之道,不述圣贤之言而自立新奇之说,去道远矣”,又曰,“或者谓,立言当求先儒所未言者。夫以孔子之大圣,犹述而不作,况后学不述古圣贤之言而欲创立己说乎”(《续》卷四),孔子的圣人典范成为薛著述的模板。“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力行何如耳”,“为学无别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动,一身皆天理;事不妄为事,事皆天理”(卷四),恪守圣贤矩的述而不作,但顾力行成为薛的述学特色。至于其无心而成的著述,虽然“谓先生一生事业,包举于斯录可也”1②,但札记式思想记录并无严密精心的结构意图,大抵于“读书至心有所开处,随即录之,盖以备不思而还塞也”,其对这些思想实践的记录并无藏之名山、传于后人的著述意识,以至他晚年《读书续录》书成后门生阎禹锡向他索要,回答却是:“《读书续录》但余老自备遗忘耳,亦何足观也。”(《年谱》)
二、正学须复性
理气关系涉及事物规律与事物本身、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诸多问题,是理学家的首要命题。薛“理在气中”“理不离气”的观点虽然略不同于朱熹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朱子语类》卷一),认为“理气不可分先后”(卷二),“理气二者盖无须臾相离也”(卷三),但又以“气载理,理乘气”(卷三)来描述理气的动态关系,又称“天地之初,都无一物,只有此理”(卷六)。显然以朱熹“理在气先”、“理生万物”为宗。当然,薛之论作为读书札记,一时有所触发即记录,不过是薛当时阅读儒家经典时的思想轨迹,并无系统整理,更无意流传后世。前后矛盾只是一般思辨的体现,并未有更深入的论证阐释。又如薛所论天地阴阳,称“天地之开阖,世运之兴衰,日月之往来,昼夜之变化,寒暑之推移,万物之始终,皆阴阳之气屈伸消息为之主”(卷十)。用意则在以“阴阳相胜相根”的一般规律批判佛道所谓“鬼神”、“神仙”、“生死轮回”的谬说,为儒家正统辩护。但综观所论,多守成旧说,阐述前儒理论,略少发挥。
“致知格物”作为儒家人生修养的第一课,有着重要的基础意义。薛认为,“就万物万事上求实理,格物致知之要也”(《续》卷四),延续了“以实学求实理”的一贯路径,对于讲求“躬行”的薛而言,“以行为本”毫无疑问成为其知行观的基本认识。程颐明确主张“知在所行之先”的“知先行后”。朱熹承认“知之为先,行之为后”,但又强调“行重知轻”、“知行相须互发”(《朱子语类》卷九)。薛继承了前儒知行并重的思路,认为“知行两得”(《续》卷二)、“知行贵乎兼尽”、“知行虽是两事,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卷一)。但是,务实的薛更主张以行为知之本。“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偏废,而居敬又穷理之本也。”(卷六)居敬是“力行”,穷理是“致知”;“居敬为穷理之本”,就是“行为知之本”。更从实践检验的求真角度来肯定“行”的意义。“凡事必有微验之实乃可,不然即妄言者多矣。”(《续》卷二)“见得理明,须一一践履过”(卷四),才能叫做“真知”;强调“真知其理而实践之”(《续》卷二)。“重行”的主张落足于问学之道则体现为循序渐进的知识累积。“格物”功夫全在“逐物逐事上穷至其理”,“致知格物,于读书得之者多”(《续》卷一一);“学有所得,必自读书入”(卷五)。因为薛对道学的最大阐释乃是在其身体力行的实践中。
“圣贤万世所传之道,只是天命之性。”(《续》卷三)“盖先圣之心,虚灵洞彻,万理咸备,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但其寂然不动之时,初无声臭可闻,无涯可测。”(《敬轩文集》卷十九)孟子“人皆可为尧舜”的论断则为常人可以达于这样的“内圣”境界提供了理论辩护,“存心养性”、“学以至圣人之道”成为道学传承中极富感召力的立学目标,“尽性者,圣人;复性者,贤人。至于圣人圣人相传之道不过于此”(《续》卷五)。“复性”成为与圣人对话的途径,而“性”亦成为薛理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以客观万物万事的最高本原和主观认识追求的最高客体统摄一切。“性者万物之一原”(《续》卷五),“性为万理之枢”(《续》卷二),“性者,人所受之天理,仁义礼智也”,而天理人心的合二为一,天理即存在于常人的固有本性中,只需回到自己天赋本心就可以臻于“内圣”的境界,而此亦即道学相承的关键所在。在薛看来,“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曾、思、孟相传之道,又岂外乎性哉!”(《续》卷九)“然则自孟子没,道失其传,只是性不明。”(《续》卷一二)宋代理学诸君子使得“‘性’之一字大明于世”(卷三),有着“使圣晦而复明,大道绝而复续”(卷五)的万世之功。以道学延承自任的明儒薛,一生躬行明道,更是一以复性正学为宗,以昌明圣学,延继道统。
“千古为学要法,无过于敬,敬则心有主,而诸事可为”,“程子挈敬之一辞,示万世为学之要。程子之主敬,周子之无欲,皆为学之至要”,“程子曰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为学之要也”。“主敬”是宋代理学诸儒力主的修身要法,为学一本程朱的薛对于“敬”这一“要法”更是奉为圣典,兢兢检点。除所号为“敬轩”外,并作《持敬箴》以自警,“一刻之谨,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内之枢机,养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继孔学,开示迷,敬为要约。其曰主一无适者,欲人必专其念而不杂于多岐;其曰整齐严肃者,欲人必极其庄而不失于怠隳,斯实内外交养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甚至于“为学时时处处是做工夫处,虽至鄙至陋处,皆当存谨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时,手足不敢妄动,心不敢乱想,这便是睡时做工夫,以至无时无事不然”。薛每时每刻的定心涵养中,敬诚专一,更有着动静合宜的思辨,“为学之要,莫切于动静,动静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静而敬,以涵养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动而敬,以省察喜怒哀乐中节之和,此为学之切要也”。力主践履躬行的薛更以一生的品行磨砺实践着内外兼备的笃敬涵养,“内则惺然其心,不使有一尘之蔽;外则肃乎其容,不使有一体之惰,以至接乎物则必主于一,而无他适之扰”,“近而屋漏无所愧,而天地无所怍”,成就了有明一代儒臣第一的“河东薛夫子”。
论者称,“文清之学,端亮严峻,俗士不敢入,邪说不得乱,居然一代之宗”1④,所谓的“端亮严峻”,正在薛一生的检点言行,躬行明道,以其一生德行完成了儒家经典的哲学诠释,不以文字为念,循着前贤楷模道学传承之路,履行着理学规范下的道德实践。科举考试是封建士人的头等大事,薛主持会试,作序略曰:“切惟为治莫先于得贤,养士必本于正学。正学者,复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复,则明体适用,负经济之任,厘百司之务,焉往而不得其当。”有同考官对薛说:“‘正学复性’数字,久不言,恐非时文。请易之。”薛正色答道:“某平生所学,惟此数字而已。”以居敬为功,以复性为宗,正学以延续道统,薛一生之学,正在于此。
注释
②陈鼎:《东林列传》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9页。
⑦许衡:《鲁斋遗书》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5页。
⑨张廷玉:《明史》卷71,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68页。
⑩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页。
⑪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
⑬冯从吾:《薛文清先生全书序》,见《少墟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王怡敏)
K825.1
A
1008-9012(2016)03-0067-06
2016-08-25
郭万金(1979-),男,山西阳曲人,山西大学国学院教授;赵寅君(1986-),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