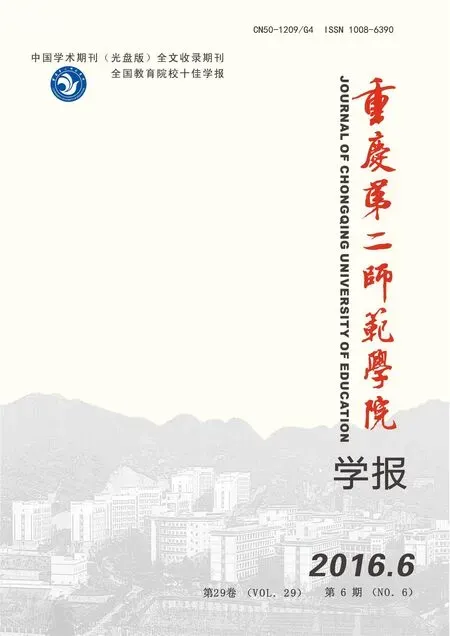铁凝“三垛”小说中的“垛”意象及其符号意义
赵 蕾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铁凝“三垛”小说中的“垛”意象及其符号意义
赵 蕾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铁凝“三垛”系列小说中的“垛”意象蕴含着多重符号意义。它不仅是承载女性生命力之奔突与奇遇的“欲望之垛”,象征女性生存依赖与现实物质的“生存之垛”,更是未来以微妙的方式在女性生命和内心永存的“风景之垛”。“垛”所隐含的复义在小说中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铁凝以其超性别的视角既在人性与历史的时代遇合中窥破了女性作为“他性”的生存本相,也在对多元人性及其生存图景的深刻揭示中展现出历史本质。
“三垛”;欲望;生存;风景
铁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陆续发表的“三垛”系列小说(《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以独特的超性别视角关注于农村革命、政治、经济变革历史中的女性命运。其中“垛”这一意象在小说中蕴含着多重符号意义,它不仅是承载女性生命力之奔突与奇遇的“欲望之垛”,象征女性生存依赖与现实物质的“生存之垛”,更是历史的见证者,悲剧的衍生地,未来又以微妙的方式永存于女性生命和内心的“风景之垛”。“意象不仅仅是装饰,而且是一种直觉的语言的本质本身。”[1]作为一个承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意象,“垛”在人性与历史的时代遇合中窥破了女性的生存本相。
一、“欲望之垛”:女性“生命场”中的欲望与力量
“垛”这一意象首先象征着女性生命力的在场与悸动,女性欲望的彰显与合理性认同。长期以来,在男性菲勒斯中心文化的统治之下,女性面临的生活写照不仅是隶属于男性并作为其欲望载体的“第二性”客体,在自我展现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生命也在男性的宰制下失去了活力与能动性。新时期文学对个人主体的表述一贯渗透着男性身体的到场、女性身体的缺席、被剥夺与被奴役的性别政治。铁凝则有意打破这一躯体话语方式。她在“三垛”中着重突显女性“生命场”中最原始最自然的状态,通过描写女性在原欲世界里开始采取的主动者姿态,展现一直以来女性被压抑的生命力之奔突与奇遇,以此来确立女性的欲望主体身份,探究女性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健全人性的建构。
《麦秸垛》一开篇就呈现出一堆堆坚挺挺地戳立在麦场之上、跳跃着光芒与生命色彩的麦秸垛,挺拔而不失柔和,丰润圆满而饱含生机,使整个原野骚动起来。当原野上的女人们出场时,麦秸垛便以某种潜在方式唤醒女性内心的悸动与生命力的勃发:
黄昏,大片的麦子都变成麦个子,麦个子又戳着聚拢起来,堆成一排排麦垛,宛若一个个坚挺的悸动着的乳房。那由远而近的一挂挂大车频频地托着她们,她们呼吸着黄昏升腾起来,升腾起来,开始在柔暗的村路上飘动。[2]
人类的欲望像麦秸垛一样生生不息地繁衍和生存,铁凝以清丽、真淳的笔致赋予麦秸垛以女性特质。在麦田劳作的下乡知青杨青感应到麦秸垛对她的召唤,被唤醒了内心从未苏醒过的部分,全身蓄满精力,更坚定了对陆野明的爱情和驾驭幸福的信念。同是对陆野明,沈小凤被唤起的爱更加炽热和浓烈,麦秸垛如同一个个沉默的热团诱惑着她,使她内心对男性的渴望迅速燃烧成欲望。沈小凤作为欲望行为的发起者,她牵引着陆野明,他们在村边场上一个硕大的麦秸垛中野合,人的体温融合垛的体温,女性原始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理欲望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棉花垛》中米子靠钻窝棚挣得棉花,虽是出卖肉体以维持生计,但她积极热情并乐在其中,因为在此行为中她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话语和行为主动权,男人仿佛成了她玩弄于股掌中的物品,由她的意志操纵和摆布,而窝棚外那一堆堆白得耀眼的棉花垛便是她欲望升腾的导火索。她钻窝棚也想着自己的将来,攒下体己钱,她要寻人和生儿育女,不愿意只带着一张穷嘴走。下一代女性小臭子和乔从小耳濡目染男女间身体的差异与交往行为,对此充满好奇,便有了她们逼迫男孩老有参与她们模仿“淫乱”的童年游戏,女性的生理欲望在少女心中就开始隐隐萌芽和悸动。《青草垛》中十三苓和冯一早青梅竹马,从五岁起他们每年都在家门外的青草垛中搭建一间“房子”,“结婚”、“睡觉”、“过日子”,沉迷于建立一个“小家”的幸福,热切地盼望长大,在青草的净洁与清香中演绎着生命的精彩。经历了大城市生活的蹂躏之后,混合着青草味的童年幻成了十三苓一生永恒的念想。在这里,“垛”成了女性蓬勃生命力和生理欲望厚积薄发的媒介和符号所指。
女性欲望与生命力的奔突最终回归于母性,这是女性身体在喷薄之后最神圣的皈依。回归母性,打破父权制建构的完美母亲形象,也是女性感悟人格的完整和尊严的重要途径。《麦秸垛》中的大芝娘、《青草垛》中的大模糊婶都是具有地母般情怀的女性。大芝娘刚结婚三天丈夫就参军走了,回来的目的就是因在城里提了干、找了城市姑娘而来跟大芝娘结束包办婚姻的。大芝娘毫无怨言地跟丈夫离了婚,只要求丈夫跟她生一个孩子,让她没有白白结过一次婚。大芝娘以勤劳和坚韧的品性独自抚养女儿大芝长大,当丈夫在城里遇到困难时,她还主动把丈夫一家四口接到自己家里收留。大芝娘身上无处不散发着母性的光辉与善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她最强盛的生命力的体现,她的生命真切实在地贴着端村的大地,震慑了端村的每一方田野。后来,她平静地接受了女儿大芝的早逝,抚养失去母亲的孩子五星,对下乡来的知青杨青、沈小凤更是给予母亲般的疼爱与关怀。只是每到深夜,大芝娘屋里的纺线声和被窝里那个磨得发亮的枕头,诉说着漫漫长夜中其内心深处无尽的孤独和凄楚。当杨青回城之后,她常常看城里街上的女人,尽管她们有着和大芝娘同样丰满的乳房,却不再有大芝娘式的背负、真淳与博大的母爱、坚韧的生命力,大芝娘始终以“缺席的在场”姿态在她潜意识中永存。《青草垛》中的大模糊婶也是集无私无畏的爱与蓬勃、坦荡的生命力于一身,倾尽全力对从小失去母亲的一早给予母爱的滋养,展现出从容、坚韧的生命底蕴与女性本色,并以无所顾忌的性器官展示作为对文明无言的拒斥与抗衡。
女性“生命场”中被激活了的欲望与力量彰显出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与自在性,是对女性身体作为性主体身份的合理化认同,更是对男性霸权不动声色的挑战。在这片“欲望之垛”中,她们首次从“铁屋子”中挣脱重重枷锁,恢复了最原始的生命活力,展现出一段无遮拦的、自由而自然的生命历程,在对爱情的永恒守望和对母性的赤诚皈依中体现女性“人”的情怀。铁凝有意识地通过“身体的掌声”来建构女性健全的人性,“在从人性的角度去反思和批判历史的‘原则’时,她是把女性身体视为人性觉醒的重要契机”[3]。对女性生命意识的审视与张扬,对女性欲望坦然地承认与突显,都将女性的历史生存由遮蔽带向了敞亮。
二、“生存之垛”:与女性生存境况密切相连的物质依赖
“垛”也是作为与女性生存境况密切相关的现实物质与生存依赖而存在的。“三垛”中描写的三个村庄各自以“垛”为生:端村拥有大片的麦田,麦秸垛是麦收时节端村人辛苦劳作的成果;百舍村的棉花地和大庄稼并存,村民大多靠种花、卖花维持生计,一堆堆棉花垛是花主们财富的象征;在茯苓庄,割草是祖辈传下来的事业,家家房前屋后都有一两个青草垛,烧火、铺炕、喂牲口乃至盖房都需要草。但村庄里的年轻女性往往不能通过劳动获取这丰硕的生存之本,她们自愿或被迫靠出卖肉体的方式换取衣食资源,女性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不断因生存依赖而被“物化”。
《棉花垛》的故事发生于抗日战争前后,米子年轻时不像百舍村的其他姑娘那样靠替花主摘花赚钱,她凭借着姣好的容颜和身材靠钻窝棚和花主睡觉挣得棉花,衣食无忧,心安理得。她的女儿小臭子长大后也步其母之后尘,与能给她毛布大褂和呢面皮鞋的汉奸秋贵勾搭在一起;为救自己的“衣食父母”秋贵,她还不惜出卖了一起长大的女革命者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封建思想和男权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她们并无冲破封建枷锁的意识,身体成了她们唯一的生存资本;她们善于利用这一生存资本做交易满足自我需求。到了《麦秸垛》所涉及的解放后知青上山下乡时期,女性意识初露端倪,但农村妇女仍摆脱不了因对生存物质的依赖而任由男人摆布的命运。年轻的四川姑娘花儿怀着身孕被人贩子以两千五的价格卖到端村,在和善良、朴实的小池结婚后她终于吃饱了饭,有了作为一个女人的气色。小池和家人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花儿的孩子,但不久花儿的前夫又从四川找到端村来强行带走了她,她走时身怀着小池的孩子。女性对自己的命运毫无选择和支配的权力,只能像物品一样任由男人根据需要交易和摆布,为了一口活下去的食粮她们只得听之任之,宛如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进入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在传统伦理与现代观念的融合与冲突之中,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无明显的改观,《青草垛》中十三苓有着改变命运的决心,一心想要在城市中立足,可在经历了城市生活的重重劫难之后只得沦落到社会最底层,依靠性交易维持生计:
十三苓一走三年。开始给我写信,说在京城一个大人物家“帮忙”;不久又来信说,给韩国一家公司推销商品;不久又来信说,在一个服装学校学剪裁;不久又说是一个大款的“关键人物”。最后一封信上说又换了工作,工作说得不具体,只说,即使如此,她也决心要混一混,她不信这天下竟没有她的位置。再后来就没有了消息。[4]
除了生理性别之外,女性在都市中无从演绎自己的社会角色。通过十三苓这一女性形象,小说表达了女性在城市中的生存焦虑体验,引发读者对女性生存价值的思考。小说写到“黄米店”这一从封建社会延存至今的组织机构,通过“小黄米”给过路的运煤司机提供性服务,来换得司机车上的煤,以卖煤来维持全店的开销。十三苓就曾是店里备受热捧的“小黄米”。这里直接以被物化了的女性身体与男人之间进行物与物的交换,直言不讳地袒露女性在都市中作为“空洞的能指”而存在的卑微与奴性。
铁凝之于女性体验大胆直露的书写,与其说是在控诉社会,不如说更多地是在解构女性自我,“是对女性的历史与现实境遇的深刻的、近乎冷峻的质询,一种对文明社会中女性位置的设问”[5]。这些女性的经济附属地位是由男人支配的,她们只是男性生活的一个因素,而男人是她们的整个生活依赖。她们不能通过正当劳动获取生存资料,只能在对男人的依附之中以身体做交易换得苟且偷生,逆来顺受,身陷囹圄而不自知,失去了独立的勇气和自主的尊严,最终只得经受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摧残。
三、“风景之垛”:窥破女性生命本相
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作为村庄里一处处亮丽的风景而存在,“垛”象征着丰盈和富足,它们喧嚣涌动,宛如甘露般滋养着庄稼人的身心。与此同时,“垛”也以一种隐忍的悲悯封存女性内在的自我,以一种温婉的原宥环绕、触摸、记述作为“风景之风景”的女性生存本相。“风景之风景”原是柄谷行人在评价日本写实文学时所使用的词汇:“现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很明显是在风景中确立起来的。因为写实主义所描写的虽然是风景以及作为风景的平凡的人,但这样的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外部的,而须通过对‘作为与人类疏远化了的风景之风景’的发现才得以存在。”[6]“三垛”通过对风景之“垛”与平凡女性的书写,从而实现对本质性地存在于“风景”背后的“风景之风景”——女性在历史沉浮中的生命本相的窥破与发现。“垛”这一村庄中特有的风景也因对女性生命本相的见证而在女性生活和内心中永存。
“三垛”分别呈现了抗日战争前后、建国后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的女性命运,女性从被压迫在“铁屋子”里蒙昧无知到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以及对蓬勃生命力和生理欲望的张扬,突显了女性在历史境遇中的心灵成长。但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又延续着女性千古不变的生命形式与人类共性,女性在精神和物质上始终未彻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试图冲破以男性为中心的尺度,在突显差异的基础上作“女人”时,又深深陷入对生物性的强调,难免走向性别本质主义,陷入男性中心传统对女性角色的预设,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因此,在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不是男性,而恰恰是女性自身。女性被动地或主动地沦为男性菲勒斯文化的帮凶,与这个菲勒斯一起残害自己的灵与肉。《麦秸垛》中沈小凤对陆野明狂热的爱恋一步步演化为无处投放的悬置的自我:
“那以后,我还是你的吗?”
“不是。”
“我是,就是,就是!”
……
“你是你自己的。”陆野明到底推开了她。[2]57-58
沈小凤不是通过主动的征服,而是想把自己推诿给一个男人,通过在男人的手里变得被动和驯服,而为自己开创未来的。遭到拒绝后她竟也想重复上一辈女性大芝娘的命运,求他跟自己生一个孩子。沈小凤的身心总要投靠到一个地方,而从没有想过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依靠自己去丰盈和完善自我。附属性在她身上已经内在化了,即使当她以表面的自由行动时,她其实是奴隶。《棉花垛》中作为现代女性的乔在对国的仰慕和爱恋中走上抗战道路,在恋爱的过程中她对照榜样,寻找差异,自我规训。正如福柯所言:“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他在权力关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他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7]可是国一旦离开,她却失去了生活和事业的方向和目标。她早已在追随国的自我征服中逐渐丧失了独立的意志,成为内在匮乏之下毫无行动力的虚无化自我;她从根本上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革命与改变女性地位之间的本质联系。小臭子也对抗战事业满怀一腔热血,乔和国给她任务她从不推脱,她靠和汉奸秋贵的关系帮助八路军过日伪的封锁沟,传递抗战情报,却在对抗战现实勇敢的奉献、热情的盲从之后无知无觉地泯灭、消融自我而成为汉奸,从根本上她仍摆脱不了对男人的依附性和被支配的从属地位。不论是新女性乔,还是因袭传统重负的小臭子,最终都殊途同归地逃脱不了被男人先奸后杀的性别牺牲。“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15这些女性的内心被男性意志掏空和消融,滞守于身体的惶惑之中,失却了完整的人格和尊严。国家、民族的苦难掩盖不了女性性别的苦难,当她们在民族战争中充当男性操控权力的载体或发泄欲望的工具被利用尽之后,只能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女性身体在民族战争中承受着双重的挪用和挤压。
铁凝在人性与历史政治的时代遇合中窥破了女性作为“他性”的生存本相,在对多元人性及其生存“风景”的深刻揭示中展现出历史本质。值得注意的是,“三垛”中对男性命运的书写也别有用意。《麦秸垛》中回城后的陆野明虽和杨青走到了一起,但和沈小凤苟且的那个麦秸垛之夜“仿佛留给了他永远的怯懦”;《棉花垛》中奸杀了小臭子的国虽因“战功”得到了一生的优待,但四十五年后和老有在火车上偶遇的他目光呆滞,精神萎靡,靠几瓶子药维持生命;《青草垛》更是以死去了的冯一早的魂魄为叙述者讲述十三苓和茯苓庄的故事,最终冯一早的灵魂也随着青草垛一起被烧成灰烬。这里以女性身体的被蹂躏和枯萎对应男性大脑的枯萎,深刻地暗示了男性中心文化不仅造成对女性生命的深深戕害,同时也使男性遭受无形的精神阉割,使他们同样失去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独立的人的本质内涵。
四、结语
《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中的“垛”所隐含的复义“表达出一种关系或者一个过程”,“一个解剖的过程”,“所表达的东西会在思想里作为一个整体”[8]。这一象征性的符号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生命力与生理欲望的勃发和与生存境遇密切相连的物质依赖之间隐含的矛盾自我,以“垛”中“风景之风景”的发现解构女性自身,窥破女性生存本相,探寻普遍的人性意义。铁凝曾在自述中谈到,她在把握女性题材时力求摆脱纯粹的女性目光,而用一种超性别的视角力图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境况。因此,“三垛”中并没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痕迹,而是在对女性心灵史和生存本相客观清醒地挖掘过程中,在敏锐却又含而不露地洞察男性中心社会文化以及笼罩在这一文化场中的两性关系的同时,表现了铁凝对人性、人的本质和欲望的深层探寻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的体贴关注,其终极关怀是建立一种更合理的人类生活方式。
[1]T·E·休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1915)[G]∥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
[2]铁凝.铁凝文集[M].第1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6.
[3]贺绍俊.铁凝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36.
[4]铁凝.铁凝文集[M].第1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53.
[5]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48.
[6]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9.
[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27.
[8]威廉·燕卜荪.复义七型(选段)(1930)[G]∥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10.
[责任编辑 于 湘]
2016-06-21
赵蕾(1992— ),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7
A
1008-6390(2016)06-00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