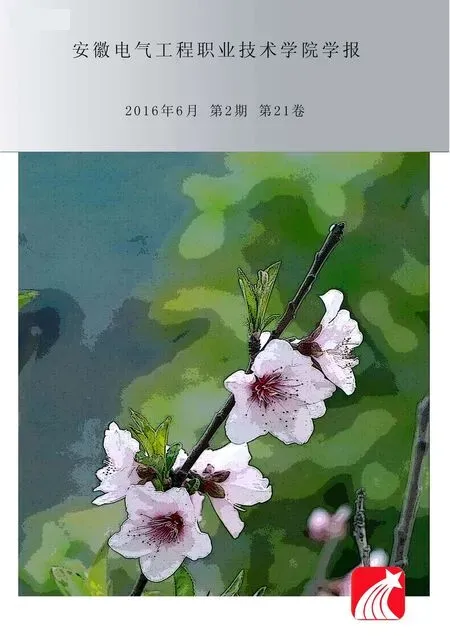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政策关系
——从李斯特鸿沟至罗克辛贯通
张耀文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北京 100088)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政策关系
——从李斯特鸿沟至罗克辛贯通
张耀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北京100088)
摘要:法治化的推进,刑事政策在司法工作中的作用愈加突出。但刑事政策在介入刑法后,实践中出现了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一方面是刑事政策有超越刑法界限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在具体适用刑事政策时,把握限度出现了错误。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原则,其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的联系,在立法以及司法过程中,应坚持两者互相完善、互相补充的关系,共同推动法制化的进程。
关键词:刑事政策;罪刑法定原则;相互贯通
罪刑法定原则从初期的排斥刑事政策,到如今充分发挥刑事政策的作用。这是因为刑事政策的灵活性为刑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铁律,又为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划定了界限。刑事政策的适用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应是一种共存共进的关系,共同为法治社会的实现作出贡献。
一、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刑事政策”由费尔巴哈所提出,随后李斯特对其进行了细致的阐释。讨论的初期,由于刑事政策和罪刑法定原则在适用中所产生的矛盾,一度认为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可贯通的。后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学界普遍认识到了刑事政策对于罪刑法定原则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政策的分离:“李斯特鸿沟”
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一直以来受到极大的关注,李斯特曾提出过自己经典的主张“刑法仅需要在实在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进行概念的分析和得出体系上的结论。刑事政策则包括刑法的社会内涵及目的,就不属于法律人探讨的事情。”[1]10基于这样的立场,李斯特提出“罪刑法定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将刑法与刑事政策割裂的理论就是著名的“李斯特鸿沟”。李斯特认为,为了完成自由和人权的维护,有必要只从规范法学的角度去为刑法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不允许刑事政策等外在元素侵入其中,必须保证其自身的封闭性。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在于保障了罪刑法定原则的不可侵害性,保证了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至于偏离刑法立法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但是一味的强调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分离,会导致以下两方面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对刑法体系(刑法教义学)的刚性坚持容易造成精巧的刑法体系与现实的脱节;另一方面,对刑事政策的极端化推崇则容易使对犯罪行为的惩罚走向偶然与专断,背离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1]6罪刑法定原则从最初的渊源上进行分析,其制定的目的是限制君王的权利,让法律不再仅仅为特权阶级所掌握,真正实现“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但是罪刑法定原则自身的僵硬性和滞后性也在对法律的公平正义进行着冲击,社会生活总是千变万化的,而立法总是滞后于法律,并且法律也不可能穷尽犯罪情况。毒驾是否入刑,网络犯罪是否应该单列罪名,这些现实问题都在不断地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质疑。这时候刑事政策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刑事政策“具有意向性,具有灵活性,具有动态性,具有开放性”,“而罪刑法定以及罪刑法定规制下的刑法强调的是稳定性,强调的是明确性”,[2]刑事政策的灵活动态性对成文法的僵硬和滞后性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在成文法限定的基础上,去根据具体现实去实现灵活性和法定性的统一。
(二)“李斯特鸿沟”之消弭:罗克辛贯通
李斯特的理论,过度强调了刑事政策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分离性。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罗克辛教授重新梳理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罗克辛称刑法教义学为刑事政策导向的刑法学,“建立这个刑法体系的主导性目的设定,只能是刑事政策性的。刑事可罚性的条件自然必须是以刑法的目的为导向。”[1]133罗克辛将刑事政策引入到了刑法当中,认为两者之间的鸿沟是可以架构的,从而使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罪责目的化,使刑事政策和刑法的关系清晰化。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在刑事政策和教义刑法学相协调的背景下,可以推论出刑事政策和罪刑法定原则也是一种相互共存的关系,这种共存关系不仅仅表现在文字单纯字面含义上的连贯性,而且从立法的价值取向上也是共存的。
罗克辛主张打破李斯特时代刑法体系的封闭性,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刑法体系”。这个体系需要满足三个要求:一是概念性的秩序及明确性;二是与现实相联系;三是以刑事政策上的目标设定作为指导。[1]20由此可知,罗克辛所主张的刑事政策不是一个明确限定的概念,而是包容了犯罪论体系的各个阶层。不仅指向刑法的价值、目的、实质,更是涉及到司法、立法各个环节。在确定了刑法体系的特征之后,罗克辛又将构成要件该当性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特征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和违背社会功能性构成要件该当性。
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李斯特鸿沟”的产生,是因为中世纪刑法过度严酷和随意性。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可以加强刑罚的规范化弱化随意性,从而呈现出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执行化和绝对化。“罗克辛贯通”产生于法治水平的较高阶段,这时过于刻板的刑法阻碍了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无法应对社会出现的新状况,因而需要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正确的引导刑法的价值取向。
二、罪刑法定原则深层解析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法治的核心,其“明文规定”的主要特征为人权保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法律条文一旦确定,立法和司法机关必须在条文规定的限度内活动,超出法律本身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违法。古时国家滥施刑罚、任意入罪就是因为成文法律由特权阶级所保有,普通民众不能清楚地了解法律规定,从而处于一种极度恐慌的状态。罪刑法定原则实现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契合,这也是刑事政策所应追求的目标。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理性分析
罪刑法定主义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在整个刑法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禁止习惯法,禁止类推,禁止溯及既往,禁止不定期刑。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理性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禁止习惯法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首要要求,具体反映到我国法律的是《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类推制度主要是限制有罪类推,因为它超越了民众的法感情,更严重的是会造成社会的恐慌;溯及既往原则因为超越了人们的可期待性而被否认;禁止不定期刑主要是禁止绝对不定期刑,它因为赋予了法官过大的司法裁量权而受到批判。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理性分析
“罪刑法定并不是单纯的形式原理,而有必要作为实质的处罚限定原理加以理解”[3]。罪刑法定原则随着法治的推进,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形式理性。它的实质理性是指:刑罚法规的明确性;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
罪刑法定原则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刑法的首要原则的原因,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障人权等人类的普是真理。“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略”[4]。刑事政策的立法之初,立法者就是想利用刑事政策来指引刑罚的实施,以期能更好的实现刑法预防的功能,因此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从法治国要求的体系性处理方式出发,并不能得出刑法和刑事政策存在对立关系的观点”[5]137。
三、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刑事政策和罪刑法定原则如同一根树的两个枝干,从产生的初期就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两者不仅有共同的目的,在限度原理和价值目标上都是极为相似的。
(一)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共同点
共同的目的:预防和矫正。刑事政策的首创者费尔巴哈,其理论就是以心理强制说为标志,主张以法律威吓为内容的一般预防。费尔巴哈作为刑法理论的大师,其刑法理论也是以一般预防为目的,由此可见两者在创立之初目的就是共同的。其次从我国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中来看,刑事政策注重社会秩序的维护,同时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充分考虑了价值内容的判断。因为在我国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体系中都是以社会危害性为判断标准的。
共同的限度原理:刑法的谦抑性。以我国刑事政策为例,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死刑政策、“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坚持少杀慎杀”、“对未成年犯教育感化”,都是在贯彻刑法的谦抑性。罪刑法定在中世纪产生之初就是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防止刑罚的滥用。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依然在行使着自己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作用,闪耀着理性的光芒。
共同的价值目标: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根本原则,其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6],在现实的制定过程中,刑事政策虽然是政治的需要,但国家的每一个刑事政策其出发点都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同一的,都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更好的去实现人权。
(二)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天然联系
“我们必须在符合社会公正与合理的原则之下实现对功利性的追求,这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现代刑事政策中毫无疑问应当成为规范和制约刑事政策实践的不可动摇的基石。”[7]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的联系,共同为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发挥着重要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为刑事政策划定了固定的界限,一切越线行为都是违背立法原意,都是应被废弃的。“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这是一条铁律,任何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不能打破它。贯彻刑事政策必须在刑法的罪刑法定框架内进行,既不能法外施恩,也不能法外施威。因为一旦刑事政策离开罪刑法定原则,就不能保证它的公正性。徇私枉法、机械操作等事件就会接踵而至。最高检《关于在检查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规定,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现政策指导与严格执法的有机统一,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宽和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做到宽严合法,于法有据。
“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并不能否定掉法条本身的价值选择,而这样的价值选择可能在立法时就受到了刑事政策的影响。而对于已经确定存在的法条而言,对法条原意的发现也常常需要借助于刑事政策价值判断的融入。”[5]138“罪刑法定原则要求遵照法律,但法条的解释是存在困难的。只要刑法内容由文字表述,以普通用语为基础,就有解释的必要。”[8]许多法律条文制定之初和刑事政策是会产生交集的,因为两者的目的都是起到社会预防的目的。因此如果需要从深层次去分析法条的立法原意,刑事政策的研究是一条很好的路径。而且从人类语言的习惯上说,任何文字都难以逃脱解释的必要,因为受众不同,理解的能力也是不一的,如果想让文字更加清楚明白,必须进行后天的解释加工。
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统一的角度,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满足于对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和定罪量刑最低限度的形式合理性这样一个诉求方面,并且进一步派生出国家行使刑罚权、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还要满足实质和理性的要求”[2]如何理解和实现实质合理性的要求,刑事政策提供了解的途径。刑法法律条文的刚性和滞后性决定了法律条文不可能完全适应社会生活。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程序区分于成年犯的审判程序,因为刑法不是以惩罚为目的而是以预防为目的。这时刑事政策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充分运用刑事政策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完善和引导作用,弥补法律原则固有的缺陷。
(三)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完善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足见刑事政策对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什么关系,储槐植教授提出了刑事一体化的概念,此后储槐植教授又对刑事一体化和刑事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为观念的刑事一体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它要求良性刑事政策为之相配,同时在内涵上又与刑事政策兼容并蓄,因为刑事政策的基本载体是刑法结构和刑法机制。”[9]这是刑法理论界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阐述,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自然适用二者关系的理论。刑事政策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如果相关的刑事政策已经很完善和成熟了,那就可以直接依据相关的刑事政策去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实现刑事政策的法定化。但是如果相关的刑事政策还很模糊笼统,其价值取向还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则不适宜立刻进行法律的转化,应注重在司法实践中去践行相关的政策价值。因为刑法的立法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频繁的对立法进行修改和废止,会严重影响到刑在实践当中主要还是从定罪和量刑两个角度去把握。
从定罪方面来说,以未成年人犯罪为例,“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在制定刑事政策过程中,应当对未成年人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思想。一旦定罪就会对未成年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过多的定罪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悔改。
从量刑方面来说,对犯罪人一定要进行全面考察,全面把握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对那些有悔改可能的罪犯,给予宽大处理,促使罪犯悔过自新,促使其更好的回归社会,实现刑法的目的。以许霆案为例,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制下,需要按照盗窃罪进行定罪,而且应适应数额特别巨大条款进行量刑。但是本案的发生是由于ATM机故障肇始的,从社会的影响、刑罚的预防目的、许霆个人的人身危害性等多角度考虑,是不适宜按照无期徒刑进行判处的。“承办与宽大相结合”历来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法院秉承着这一刑事政策理念,呈报最高法院予以酌定减轻处罚,实现了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的完美结合。
刑事政策虽然要求达到一定的成熟性才能进入刑法,但是不意味着刑事政策要达到完全规范化的程度。刑事政策有着灵活性的天然优势,绝对规范化的刑事政策意味着与刑法无异。而且德国刑法学者认为法律不可能太过明确,甚至提出刑事法律的明确性早就消失了。*[德]洛塔尔·库伦著:《罪刑法定原则与德国司法实践》,黄笑岩译,2011年9月16—18日中德刑法解释语境下的罪刑法定原则发言稿,第6页;[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的法律明确性原则》,黄笑岩译,2011年9月16—18日中德刑法解释语境下的罪刑法定原则发言稿,第4页。现代刑法早已从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过渡到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过强会导致刑法的僵硬性,难以适应社会的变迁,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刑事政策的灵活适用留出一定的空间。
刑事政策在指导刑法立法和司法时并不是不加限制的。相反,适用刑事政策时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如果适用刑事政策不加限制,规范刑法将会被刑事政策任意改变和废止。罪刑法定原则将会被架空,刑事政策因为受政治的影响,过度的适用刑事政策将会有被强权利用之虞。而且,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产生。国家刑事政策的重心还是落在犯罪化,非犯罪化的比例较少,此时如果不有选择的适用刑事政策,会导致人权的践踏和社会的不安。成文刑法固然有一定的僵化性,但却也保证了刑法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因此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保持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依然是目前最合适的选择。
四、结语
刑事政策是由国家制定的,带有政治性。但政治和法律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刑事政策也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的规制下去制定和运行。“李斯特鸿沟”反映的刑事政策和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仍会出现在一些地方。但这不能否定我们可以去架构二者,使之更好的为我们服务。
法律条文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对于它的权威性,任何执法活动都必须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度内进行。刑事政策应充分发挥其罪刑法定的辅助作用,明确量刑幅度和刑罚执行的方式方法。现阶段我国将继续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基础上,对情节轻微的案件把握好诉与不诉的限度,对证据的标准、未成年人的保护起到更好的指引作用。通过刑事政策的指引,刑法条文本身的正义性将会得到丰满,有助于实现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M].蔡桂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梁根林.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J].国家检察学院学报,2008(4):152-160.
[3] 山口厚.刑法总论[M].蔡桂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
[4] 杨春喜.刑事政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7.
[5]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一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6] 张明楷.罪刑法定对现代法治的贡献[J].清华法治论衡,2002:180-255.
[7] 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05.
[8]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2.
[9]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
[责任编辑:朱子]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and Criminal Policy——Liszt Gap to Claus Roxin Perforation
ZHANGYao-wen
(CriminalLawSchool,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Criminal policy plays a vital role in judicial work in the advance of legalization. But in practice, after the criminal policy with the criminal law, the criminal policy conflicts with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On the one hand, the criminal policy is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criminal law;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policy, the grasp limit has the mistakes. As a basic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has a natural connection to criminal policy, and in th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they should keep the relationship of improving each other and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to promote the legislation process.
Key words:criminal policy;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mutually connected
收稿日期:2016-04-20
作者简介:张耀文(1992-),男,山东省青岛市人,刑法学硕士研究生,中国刑法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06(2016)02-00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