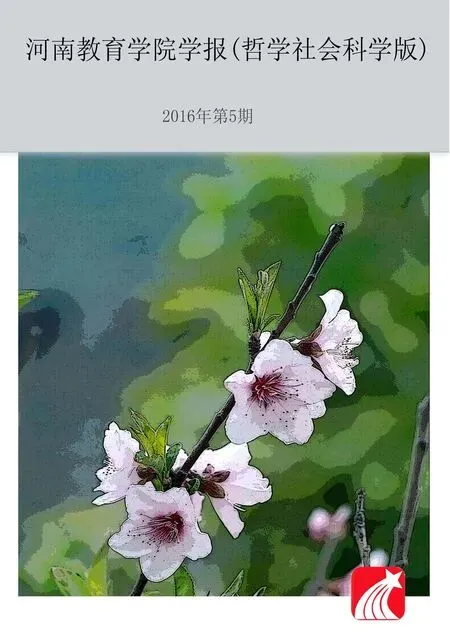浅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中之“善意”
赵亦婕 张锋会
浅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中之“善意”
赵亦婕张锋会
针对登记对抗规则下第三人的“善意”问题,学界出现了“单纯善意且不问过失”“单纯善意且无过失”“单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三种理论界定。比较三种理论的得失,“单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比较适合用于界定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之“善意”。
善意;恶意;过失;重大过失
我国《物权法》对物权变动及效力做了不同的规定,不动产一般采取登记生效规则(第十四条),动产一般采取交付生效规则(第二十三条),对于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准不动产则采取登记对抗规则。*《物权法》第二十四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登记生效与登记对抗本是针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立法规则,在登记生效规则下,很少考虑善意第三人问题。在动产交付生效规则中,一般也很少考虑善意第三人问题。善意第三人的问题一般发生在采用不动产登记对抗规则的法律体系中,我国《物权法》将登记对抗规则引入准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中,必然要考虑善意第三人的问题。但是,何谓“善意”?我国现行法对“善意”缺乏界定,学术界也众说纷纭。不解决“善意”的界定问题,《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适用就会产生很大的分歧,不利于实现立法初衷,不利于《物权法》发挥定纷止争、保护当事人权利的作用。
一、善意与过失的关系
善意,拉丁文bona fides的意译,与“恶意”(或者“非善意”)相对,其渊源可追溯于罗马法,普遍见于民法学领域。一般地说,善意是行为人对其实施行为及后果的主观心态,指不知存在足以影响法律效力的事实而为一定的行为。
单纯的善意,即作为主观心态的善意相对容易判断。民法学界对此有两种理论: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前者要求第三人相信其交易行为有法律依据,或出让人权利合法,而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此时善意无法与“怀疑”并存;后者则要求第三人不知、无法知或不应知其交易行为无法律依据或出让人缺乏合法权利。比较而言,消极观念说在当下更易被接受,从而成为通说。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道德伦理学范畴的概念,善意的认定具有极大的主观性,通常为判断其知或不知,不知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变动自然是善意,但是知晓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却不一定是恶意。[1]这就涉及善意判断的另一问题,即第三人对自己的“善意”是否存在过失,法律需要不需要对这种过失予以关注的问题。作为登记对抗主义立法例代表的日本学界提出了众多的理论构造,主要有债权效果说、相对无效说、不完全物权变动说、第三人主张(出现)说、制裁失权说、信赖保护说等。[2]通说认为,善意应并不单纯指知或不知的心理状态,还应包括对受让人(第三人)知与不知合理性的法律评价,即包括对过失的要求[3]39。笔者认为,善意第三人制度本身就是对正常物权变动规则的例外规定,我们不能仅因为第三人主观上的“不知”就必然予以保护,第三人对知与不知的合理性评价必须考虑在内。这样,界定第三人的“善意”,就必须考虑两个因素:单纯善意,有无过失。
二、常见的善意界定理论
(一)单纯善意且不问过失
该理论模式的结构与日本“善意恶意不问+背信恶意者排除”的结构方法类似,认为当事人甲乙的物权变动未登记而该物权又在甲丙之间进行二次交易,为保护第三人利益,丙有权对甲乙的物权变动提出否定。依据该说的反向解释,只需要判断丙是否为单纯恶意即可,无须计较其过失,不论是一般过失抑或是重大过失。我国《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一十一条也有类似规定: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台湾部分学者认为:“所谓善意,系指不知让与人无让与的权利,有无过失,在所不问。”[4]8当然,单纯善意且不问过失,必须排除恶意的情况。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2款规定:“受让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不知物不属于出让人的,视为受让人非出于善意。”[5]220学者也认为,如依周围之情事,在交易经验上,应可得让与人之无让与权利之结论者,应认为恶意。[6]564但是,恶意与重大过失是不同的,恶意的范围比重大过失的范围小得多。
(二)单纯善意且无过失
主张该理论的主要依据是信赖保护说。该说认为甲乙之间第一次交易后,物权变动并未采取登记为公示手段,故原物权人甲依旧保持着该权利外观,丙出于对甲这种权利外观的信赖(误信)而与甲进行该标的物的第二次交易,原则上法律要保护丙的信赖利益。由于理论结构和对第三人加以保护的要件不同,该说又分为限制的信赖保护说和权利外观说。限制的信赖保护说认为,在受让人乙与第三人丙的物权变动皆未经过登记时,乙丙均取得相同地位的不完全物权(“有排他性而无对抗力的物权”),两物权可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对第三人的信赖保护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若受让人乙具备可归责事由,第三人丙只要善意就会得到保护,不需要考虑其过失;二是当乙不具备可归责事由时,丙只有单纯善意且无过失才能受到保护。[2]权利外观说主张,受让人乙和第三人丙的物权不能同时存在,第三人丙经过登记后,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方可获得该物权,同时乙丧失该物权。[2]笔者认为,限制的信赖保护说中的第一种情况属于广义的善意,即不知、不应知、不能知且不问过失;限制的信赖保护说中的第二种情况与权利外观说中对善意的界定是相同的,皆为最狭义的善意,即不知、不应知、不能知且无任何过失(即尽到注意义务)。该善意界定理论产生于日本较为特殊的背景下,在日本立法例里有体现,例如,《日本民法典》第192条规定:平稳而公然地开始占有动产者,如系善意且无过失,则即时取得行使于该动产上的权利。
(三)单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
该理论认为,出让人甲与受让人乙之间进行第一次交易活动,但物权变动未经过登记要件,此时甲又与第三人丙就该标的物进行二次交易,当丙为单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时,依据法律应保护第三人丙的合法权利,丙可对甲乙之间的第一次物权变动行使否定权,并通过登记取得该物权;而当丙有重大过失时,则其无权否定甲乙之间的物权变动。其中,重大过失一般是指第三人出于疏忽或过于自信而对该物权的相关情况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注意义务却盲目相信该权利外观,如丙购买甲的船舶时没有认真核对该船舶的登记等相关材料或实际占有情况,或对于一些涉及常识性错误的权利外观的误信,如甲将一辆轿车以远低于市场价的白菜价销售给丙而丙欣然接受。
三、《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中“善意”的界定
民法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制度(如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物权变动登记对抗制度)皆有平衡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和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目的,因而要求受法律保护的行为人(表见代理之相对人、善意取得之受让人、已抵押动产的受让人等)依诚信原则尽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方为公允。[7]
“单纯善意且不问过失” 将“善意”定义为非恶意,即不知、不应知、不能知且过失与否不论,虽然在实务运作中容易操作,对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要件反向强制力增强,但犯有重大过失、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的第三人也受到该条款的保护,违背公平原则,导致法律本身的公信力受到减损,亦不能非常有效地保护交易安全与公平;同时,恶意者排除理论是混乱暧昧的,有将“善意”“过失”双重标准不加区分混为一谈的嫌疑,在法理上很难解释清楚。“单纯善意且无过失”将善意局限在一个过于狭小的空间中,分离善意与过失,对于第三人的保护限制过大,因而受让人获得的未经登记的物权不可对抗的第三人范围大大缩小,导致登记必要性下降;同时,它又赋予了第三人过于繁重的注意义务——调查权利外观下的真实,容易使得调查成本高于登记成本,造成不经济、低效率的结果。“单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将“善恶意”与“有无过失”相分离,充分考虑到主客观判断依据,将重大过失排除在善意之外,将“善意”定义为不知、不应知、不能知或一般过失,扩大了善意的界定范围,即未经登记的物权不可对抗的善意第三人范围扩大,反向制约当事人进行物权变动登记,促使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维护动产交易市场的稳定发展;同时,又课以第三人适当的审查注意义务,将其注意成本尽量控制在登记成本的范围内,高效、经济,可以更加有效地维护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平原则。
将善意界定理论适用于我国,应当回归《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立法目的与背景。首先,该条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要件的条款要求登记作为对抗要件,主要目的在于遏制当代市场经济生活中一物多卖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交易行为,维护交易安全;其次,通过督促当事人对物权变动进行登记,减轻受让人对同一物权变动情况的审查注意义务,降低交易成本,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同时,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价值高,流动性强,特殊动产的登记制度尚不完善,需要法律对其交易过程的每一细节进行更为细化恰当的解释。综合考量上述三种理论界定,笔者认为以基于第三人限制说与消极观念说之上的“单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理论比较适合用于界定《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中的“善意”。
[1]郭志京.也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J].比较法研究,2014(3):95-113.
[2]龙俊.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J].法学研究,2012(5):136-153.
[3]刘亚荣.论机动车买卖中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2.
[4]张练.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之再探讨:以“善意”与“合理价格”要件为视角[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3.
[5]德国民法典[M].郑冲,贾红梅,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史尚宽.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7]王荣珍.论物权变动未登记不得对抗之善意第三人范围[J].太平洋学报,2009(5):52-61.
(责任编辑孟俊红)
1006-2920(2016)05-0084-03
10.13892/j.cnki.cn41-1093/i.2016.05.017
赵亦婕,清华大学法学院学生(北京 100083);张锋会,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濮阳 457000)。
——从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3020号判决切入
——以受让人权益保护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