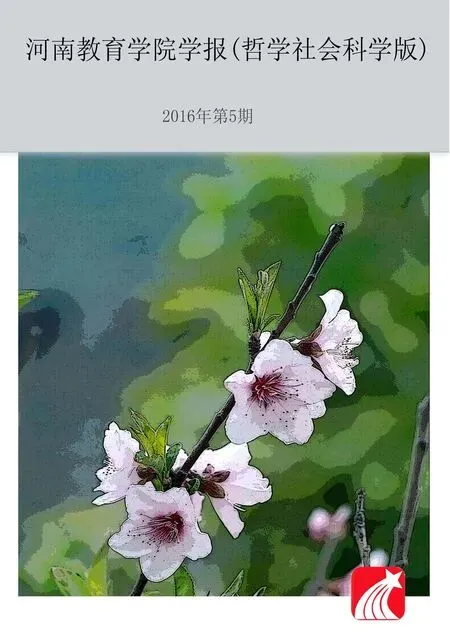横看成岭侧成峰
——清代小说的批评与鉴赏
欧阳健
横看成岭侧成峰
——清代小说的批评与鉴赏
欧阳健
王成勉教授邀我来“中央大学”座谈,我感到非常荣幸。“中央大学”是研究型的顶尖级大学,这里有一流的专家,也有非常棒的青年才俊,能来和大家交流,是非常荣幸的。我在南京工作了15年,从1980年到1995年,对南京的几所大学都比较熟悉,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是“中央大学”的前身。我们在南京工作,也学到了江浙一带的学术传统,比较重视文献,比较重视基本功。“中央大学”的校训是“诚朴”二字,今天就想按你们校训的指导,用“诚朴”的态度来谈一谈我的想法。王老师给我的题目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清代小说的批评与鉴赏》。我是很忠实地按照这个题目来讲,命题作文,尽量做到不跑题。但很惭愧,卑之无甚高论,不当的地方,讲错了的地方,务请王成勉教授、康来新教授与诸位才俊不吝指教。
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诗无达诂。”*出自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7页。诂,就是训诂。诗,没有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解释,诗歌的鉴赏,可以超越字词的训诂,在想象的意境中飞翔。诗的篇幅短小,小说可不一样了,它的容量很大,对小说的解读,有无限丰富的空间。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读起来容易,教起来就不容易了。一首唐诗,一首七绝,你可以讲两节课,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倒过来讲,颠过去讲,串起来讲。但小说怎么讲,请问《红楼梦》两节课怎么讲?小说好懂,但不好讲;即使好讲,也不好研究。所以小说研究,可提供发挥的潜能是非常大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千古名句,是极富哲理的;但不应该反过来说“要识庐山真面目,必须置身此山外”。正确的态度是:既要深入其中,对文献、文本做充分的把握;又要超乎其外,“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要把握这门学问的总趋势,把握它的来龙去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问题之所在。
“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旨趣,就在于自然景象会随你的观察点的转移而改变。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或者鉴赏,如果换一副眼光,换一副心肠(我没用流行术语的“角度”“立场”),对于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与前人不一样的发现。这个问题,前人已经讲过很多的话,如果换一副眼光,换一副心肠,说不定会有新的见解、新的发现。当然,新发现不一定必然超越前人,不一样不等于高明,但毕竟是不一样了。不是讲多元吗?你在多元诠释中增添了一元,这就是对学术研究的贡献;至于各元之间,不是平等的,会有精粗高下之分,到底谁精,谁粗,谁高,谁下,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有待于历史的检验、历史的去取。这是我对正题“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诠释。
至于副题“清代小说的批评与鉴赏”,清代小说太多了,通俗小说就有六七百部,不可能都讲,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儒林外史》,一个是《红楼梦》。《儒林外史》作为陪衬,讲得简单一点;《红楼梦》作为重点,讲得多一点。
先讲《儒林外史》。大家读文学史都知道,它的定位是讽刺小说,这是鲁迅先生提出来的,好像两岸的学者都没有表示不接受。支撑“讽刺”说的,有两个著名的细节:两茎灯草,一个虾丸。
严监生生了病快死了,伸着两个指头,就是不咽气。众人猜度心事,皆未说中。他的妾赵氏是服侍他的,最知他的脾气,问道:“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你们大概没有看过灯盏;过去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点的是菜油,在灯盏里放灯草,吸了油,点着就亮了。如果想亮一点,就点两根灯草;想再亮一点,就点三根灯草。往前拨,往后拨,就可调亮度。严监生快死了,围了一屋人,点了两根灯草,亮度高一点。严监生觉得太浪费了,死不瞑目,挑掉一根灯草,他方点点头,咽了气。这个细节立刻被研究者抓住了,说严监生是“小气鬼”,严监生也就成了和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齐名的“悭吝人”的典型。如果换一副心肠,不苛求人,这样节省一点能源,减少一点污染,又有什么不对呢?为这点事抨击严监生,好像有失厚道。
范进中举,是有名的故事。他去广东高要县拜见知县汤奉,这个老师是很不错的。听说范进母亲见背,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吃饭用的是银镶杯箸,很考究,范进退前缩后,不举杯箸,知县忙叫换了磁杯象牙箸;范进又不肯举动,直到换了竹子的才罢。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后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虾丸子,方才放心。范进于是成了“虚伪”的典型。如果换一副心肠想想,遵制尽礼也要看环境,在老师的席上,可以要求更换杯箸,却不好要求重办素酒。我在南京15年对虾丸没有印象,到了福建才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虾丸小小的,白白的,应该算是清淡的了,在贵重的燕窝中拣了一个虾丸,表明他确能节制尽礼,“情伪”云云,实难服人。
想要解决《儒林外史》的定位,首先要从大处着眼,问一问为什么题名“外史”,答案是:对应于正史之《儒林传》。正史自《史记》起,即设有《儒林传》,传主是“以儒学登用,林立朝右”者,事略是明其“专门经训授受源流”。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说: “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参见吴敬梓著《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吴敬梓“以《史》《汉》才作为稗官”,将“儒林”群体作为描写对象,继承史家“不虚美,不掩善”“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对善的旌扬和对恶的鞭笞,构成了《儒林外史》的两极。书中对至善之人如王冕、虞育德、杜少卿、沈琼枝的旌扬,是读者所不应忽略的。为此,我写了《试论〈儒林外史〉“善善恶恶”的整体构成》(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史外之史,传外之传——从小说和历史的关系看〈儒林外史〉的真义》(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两篇文章,今天就不展开了。
说到《红楼梦》,“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情况就更加突出了。不但众说纷纭,而且肝火甚旺,“几挥老拳”的事,从古到今,层出不穷。过去研究生做论文,我都劝他们不要研究《红楼梦》,为什么呢?第一难做,第二很难过关。答辩的时候,你说别人不对,他不高兴;你说别人对,另外一些以为他不对的人不高兴。但我搜索台湾的网站,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大约有一千七百多篇,说明台湾的年青学子还是很有勇气的。
如要厘清红学之纠葛,吵了一百年,百年红学,吵了什么?关键在什么地方?不妨询问一下:都读《红楼梦》,都讲《红楼梦》,“红楼梦”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是睡在“红楼里”做了一个梦?还是做了一个“有关红楼”的梦?
前人的答案,多半倾向于后一个:《红楼梦》写的是一个“有关红楼”的梦。对象,梦的内容是红楼。下面问题就来了:“红楼”的寓意又是什么呢?有两位大名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第一个大名人是胡适先生,他的答案是:“红楼”是富贵人家之所居;作者曾经历过繁华旧梦,后来潦倒了,他就怀念过去的日子,把它写出来,《红楼梦》是他的自叙传。
第二个大名人是潘重规先生——潘先生仙逝的时间并不久。我当年在南京做《明清小说研究》主编的时候,潘先生还给我投过稿。我没有见过他,但知道他是台湾很有名的红学家。他的答案是:“红楼”是“朱楼”,《红楼梦》就是《朱楼梦》。红就是朱,明朝的皇帝又姓朱,因此作者是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红楼梦》是“红楼血泪史”。
我们换一副眼光,换一副心肠,对他们的观点作一点评论。我这个评论,是按“中央大学”的校训“诚朴”的态度来做的,如果我评得不恰当、不准确,欢迎当场批评,不要客气。我们要尊重前人,要尊重学术,要诚诚恳恳、朴朴实实。朴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不故弄玄虚,不耍花枪,把道理讲明白了,就是朴。有些人要叫别人看不懂,他认为这叫学问,我们不敢恭维,我们还是朴素一点比较好。
胡适1921年作《红楼梦考证》,他这个考证本身不怎么样,但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八字箴言,被后人推崇得不得了。想想也对,你思想不解放,胆子很小,不敢去想,当然不行。我过去也非常赞同这个说法。后来一想,胡适的假设,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又算什么“大胆”?如果说明天是世界的末日,或者地球就要倒塌了,这当然算得上“大胆”。那么胡适的假设“大胆”在哪里?当他拿到《红楼梦》的时候,还没有对《红楼梦》做深入研究,还没有搞清楚《红楼梦》作者是谁的时候,就假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了。
什么是自传?作者写出自己的生平,还原一个活生生的自我。《红楼梦》作者生平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敢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呢?《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确有吴敬梓的影子,说《儒林外史》有自传因素,就会令人信服。胡适是怎么证明的呢?他采用的是类比法:曹寅有个亲生儿子曹颙,又有个过继儿子曹。曹颙无子(有人说曹雪芹是他的遗腹子),曹有没有儿子?不清楚。胡适却说有,并且就是曹雪芹。曹算是曹寅的次子(严格说是他抱来的),做过员外郎;《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做过员外郎。二者对照也就得出结论,贾政即是曹;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之子。曹雪芹“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所以,“《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则是当日曹家的影子”。*参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他的“小心求证”,就是如此的简单!
在胡适考证《红楼梦》30年之后,“第一次有人否定他全部的学说”(这句话我打了引号,它是潘重规先生的原话),他就是在台湾红坛上,继新红派代表人物胡适之后,“堪称一大家”的潘重规教授。他批评由“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员外郎”,从而推定贾政即是曹、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的逻辑说:贾政还任过学差,主管一省科举,员外郎的官职远不及学政之高贵清华,但遍查清代史料,从无曹任学差之事,自传说不是一个大漏洞了吗?我还想到,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朝,做到员外郎的有哪些?他们的次子又有哪些?在数字化技术异常发达的今天,只要稍稍搜索一下,立刻能得出上千的人选,难道都是《红楼梦》作者吗?尤为要紧的是,曹家的极盛时代,是在曹寅江宁织造之任上,而号称曹之子的曹雪芹,他生下来的时候曹寅已经死了,家里很快就被抄没了。根本赶不上曹家的富贵繁华,怎么可能“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呢?
“自传说”的最大弊端,在于其无助于对《红楼梦》的诠释。胡适由此推定“《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天天吃饭,作诗,闹别扭,发脾气,固然很煞风景;“自传说”的继承者们,竭力强调家庭衰败,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内在驱力。我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在台湾,胡适先生的弟子很多,但他们并不都赞同胡适的观点;大陆是批胡适的,但百分之九十的红学家是胡适的忠实信徒。但出身“包衣下贱”的曹家,因充当皇室耳目而“饫甘餍肥”,并无多少令人羡慕的光辉;曹家这样的家庭被抄没,更算不上真理和正义的失败,不值得为之洒下同情之泪。
潘重规先生认为红楼是朱楼,《红楼梦》就是“朱楼梦”,有没有根据呢?有。我这次到台湾来,在师大旧香居买了潘重规先生的《红楼梦新辨》《红楼梦新解》《红学六十年》,他的《红楼血泪史》在大陆出版过,这三本书是我来台湾以后才读到的。潘重规先生的看法,有没有根据呢?有。第五十二回有真真国女子“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的诗。《红楼梦》就是“朱楼梦”,不是潘重规先生杜撰的。他的研究方法,是将《红楼梦》看作运用“隐语”抒写亡国“隐痛”的“隐书”,它是民族血泪铸成的。如宝玉说“除明明德无书”,而不说“除四书无书”。潘重规先生从文字狱的角度考察,表示明朝才是正统;贾宝玉代表传国玺,林黛玉影射明朝,薛宝钗影射清室,林、薛争取宝玉,即是明清争取政权,林、薛的得失,即是明清的兴亡;贾府指斥伪朝,贾政指斥伪政。结论是:《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全书不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后四十回也不是高鹗续作。三个结论,掷地有声。
潘重规先生讲这话的时候,还是年轻人,而胡适却如日中天。他敢于这样讲,是有勇气的。他的意见立刻遭到胡适先生的强烈反驳,给他两个回答,一个是“还是索隐式的看法”,一个是“还是猜笨谜的方法”。他的反驳对不对呢?
第一条,“还是索隐式的看法”。“索隐派”在红学界是很大的帽子,给你戴上这顶帽子,就意味着你的主张是谬论,你是错误的,你是不科学的。胡适先生把这个帽子抛出来,以为潘重规先生接不住。其实,索隐是传统文化的正宗,不是坏东西,而是好东西。司马贞有《史记索隐》,与裴骃的《史记集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三家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索隐是科学的、学术的,不是荒谬的。对于《红楼梦》来说,作者明确宣示“真事隐去”。如果作者说:“我是现实主义,我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那就没有必要索隐了。既然是“真事隐去”,将隐去的事象“钩索”出来,不是很对头吗?考证派也好,索隐派也好,探研的都是小说“本事”,即素材来源。作家、版本、本事,是小说文献考证的三大支。我写过《古代小说作家简论》《古代小说版本简论》,却没写过《古代小说本事简论》。由本事考证的歧义,方派生出作家考证与版本考证的歧义。胡适研究《红楼梦》作家与版本,就是为了证明它是作者的自传;潘先生研究《红楼梦》作家与版本,就是为了证明它是“朱楼梦”。作家考证与版本考证是为本事考证服务的,而小说研究的最后指向就是文本,只有把本事搞清楚,明白本事到文本之间的飞跃是怎么完成的,对我们的研究才有意义。“索隐派”的鼻祖蔡元培早就指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元培不是凡人,他于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五岁时就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他是清政府的精英,是那个阵营出来的,他的感受应是有迹可循的。不像我们,隔了一百多年,好些事情是想当然的。刚才和王先生在中大门口照相,我说过去的校徽都是三角形的,他感到很惊讶。王先生德高望重,但比我小了几岁,就没有见过三角形的校徽,这就是经验在起作用。
王成勉教授送给我他的大作《气节与变节——明末清初士人的处境与抉择》,书中对南明史实有精辟的论述,如谓南明朝廷厚待武人,武人提出了政权上的要求,遭到东林复社派文官领袖的拒绝,武人就和皇族、宦官、阉党合作,两派争斗使朝廷失去政治家来主政,也失去民心的支持。*参见王成勉著《气节与变节——明末清初士人的处境与抉择》,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50~51页。联想甄士隐解《好了歌》:“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大家都知道《桃花扇》,戏里有忠臣,有良将,也有奸臣,有坏蛋。他们都在忙什么呢?阮大铖想投靠复社君子,侯方域等却拒之门外,把他弄得很狼狈。你出了一口闷气,你伸张了正义,但结果呢?“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史可法、左良玉,乃至马士英,都为清军南下“开辟”了道路。不管主观动机如何,不管道德品质如何,最终的结局就是这样。荒唐就荒唐在这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试体会一下,以《桃花扇》人物的立场,这种懊悔会出自何人之口?阮大铖的?还是侯方域的?我以为是后者。所以我赞赏潘重规先生的意见,《红楼梦》是由民族血泪铸成的。
第二条,“还是猜笨谜的方法”。恰如胡适先生所指责的,“旧红学”确有穿凿附会之弊,将《红楼梦》形象与情节弃在一边,说林黛玉影射明朝,薛宝钗影射清室,怎么影射法?说不清楚,因而走向了文学的反面。我赞同潘重规先生对作者政治态度的判断,却不赞同简单地从字里行间去“破译”。
回到正题上来,《红楼梦》的“红楼”,到底是指什么呢?它不是“富贵人家之所居”,说“朱楼”也只对了一半。“红楼梦”指什么呢?要从《红楼梦》书中去找。这三字出于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其《红楼梦引子》曰:“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就点出了“红楼”与“风月情”的内在联系。大观园的少女,除了林、薛、史,余者不是姊妹,就是丫鬟,宝玉和她们之间的感情,是不能称作“风月情”的。还要注意一个史实:在书名改定过程中,题为《金陵十二钗》的,恰是曹雪芹本人。“十二钗”的典故,见《情史》卷七“情痴类”明末名士王百谷的一段话:“嘉靖间,海宇静谧,金陵最称饶富,而平康亦极盛。诸姬著名者,前则刘、董、罗、葛、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青楼所称‘十二钗’也。”*参见冯梦龙编《情史》,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6页。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亦云:“赵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时曲中有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先后齐名,所谓‘十二钗’也。”*参见朱彝尊著《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3页。从“金陵十二钗”或“青楼十二钗”,可知红楼就是青楼,《红楼梦》就是有关青楼的梦。
这样的判断有没有根据呢?还是来看《红楼梦》作者的申说:“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试想,“我之负罪固多”与“闺阁中历历有人”,是不同性质的事,为何说“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原因就在于二者确有内在联系。作者之负罪,恰在“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沉湎于狭邪之游。作者若不绸缪北里平康,何能结识“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呢?如果出于“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的考虑,将此事隐而不言,岂不使“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的“当日所有之女子”,一并泯灭了吗?
那么,“青楼十二钗”,与“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民族之感,又有什么关系呢?
王成勉教授在其书中提到,清人入南京时,明朝共有23个总兵、47个副将、86个参将游击,以及238 300多明军投降,其中包括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侯方域等名士胜流。相形之下,与之交往的曲院诸姬,如马湘兰、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顾横波、卞玉京、寇眉、陈圆圆等“秦淮八艳”,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气节。《红楼梦》,充溢着作者强烈的自谴自责和对“所有女子”的敬佩之情。作者郑重回答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亦即小说的所取题材问题:《红楼梦》写的是“当日所有之女子”“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作者的创作意绪发端,并不起于家庭败落后对“繁华旧梦”的怀念,而起于“历过梦幻”后对“所有之女子”的追忆。如果写的是家庭生活的经历,以“当日所有之女子”称呼自家姊妹亲戚,显然是不恰当、不适宜的;“一一细考较去”,尤不像是对待朝夕相处的亲人的口吻。
那么,为什么在《红楼梦》中轻易看不出青楼的痕迹呢?
第二是净化。《红楼梦》将秦淮旧院的所有痕迹统统抹掉,虚构了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贾府者,“假府”也。宁国公贾演,长子贾代化,长孙贾敷,隐含“演化”、“敷演”(衍)、“敷化”之意。大观园只是秦淮旧院的变形,无非多了一堵墙而已。潇湘馆、蘅芜院、秋爽斋、缀锦楼、蓼风轩、稻香村所构成的女儿王国,如众星捧月般拥着宝玉一人,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或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这就是青楼格局的写照。贾府中的女儿,皆按年龄排次,是从旧院“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沿袭来的;男子却各房另排,且多称“二爷”,贾琏为“琏二爷”,他哥哥是谁?书中并未说明,可知亦是旧院习俗。贾府既喜欢过生日,又常将生日记错。如薛宝钗生日是正月二十一日,凤姐错记为二月二十一日,探春又说“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但贾母的生日却是八月初三。如果了解“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过寿是最好的宴请借口,就不会对生日的混乱发生疑问了。
至于《红楼梦》书中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情绪的宣泄,包括潘重规先生“破译”的“隐语”,但最主要的却是“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自怨自愧,日夜悲哀。明清鼎革,时人称作“天崩地坼”。《红楼梦》作者补天无望,却写了勇补孔雀裘的晴雯,以寄托自己的情思。孔雀裘后衿上烧了一块,能干裁缝、绣匠都不认得,更不敢揽活;唯独晴雯看出是孔雀金线的,抱病将里子拆开,用界线之法依本纹来回织补,又用小牙刷慢慢地剔出绒毛来,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嗳哟”了一声,就身不由主睡下了。这么一位好女子,却因“高标见嫉,闺闱恨比长沙;贞烈遭危,巾帼惨于雁塞”,作者怎能不一掬辛酸之泪?“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就让我们慢慢地去解其中味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今我之所言,不过立于庐山一侧之孔见。时光有限,只能就此打住。我带来两本书:《红楼诠辨》与《红谭2014》,所论或者较详,留赠“中央大学”,诸公如有兴趣,聊供暇来翻阅核查。
康来新教授是当今台湾红学界的领军人物,我们于1990年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相识;1997年武夷山国际小说史研讨会又同游天游峰,畅谈红学研究、“发迹变泰”、神怪小说、民间信仰;2005年我出席嘉义大学国际小说戏曲研讨会,讲《清初三大小说家(陈忱、丁耀亢、李渔)合论》,康来新教授以“讨论人”身份评论说:“能分享欧阳先生的研究心得,非常高兴;这么尊重钱穆先生,我很感谢。”今天是我第二次在台湾讲坛发表谬见,尤望不吝赐教,也恳请王成勉教授及与会老师、同学提出宝贵意见。
(欧阳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范富安)
1006-2920(2016)05-0011-06
10.13892/j.cnki.cn41-1093/i.2016.05.002
*此文系根据2016年2月24日在台湾“中央大学”的讲稿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