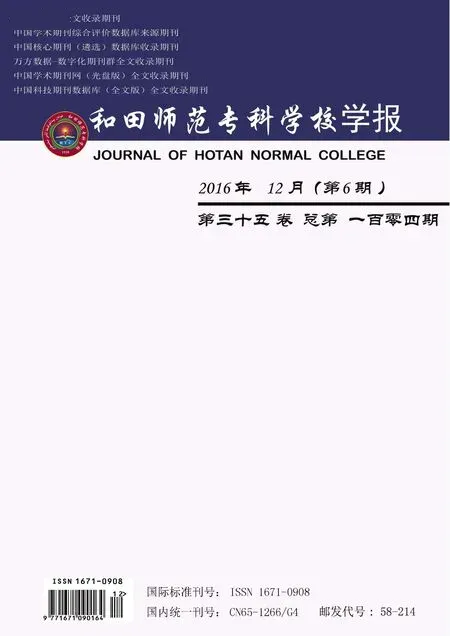福柯对话语、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述
李 婷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福柯对话语、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述
李 婷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其研究很多,但他对话语、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探讨尤为经典。通过对福柯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他认为话语与知识的关系需要在话语实践中讨论,话语是知识得以产生的基础性条件,知识在形成后也进入话语实践之中发挥作用,成为话语的一部分;知识和权力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表现在权力控制知识,知识给人以权力;在三者的关系方面,福柯认为话语、知识与权力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在话语是知识和权力的存在条件,知识和权力建构话语。
福柯;话语;知识;权力;关系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继萨特之后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对话语、知识和权力的研究是福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福柯并不是话语概念提出的第一人,但其话语分析的方法以及将权力贯穿于话语理论中,建构了系统的历史分析的话语理论。
一、话语与知识的关系:话语实践中的关系
传统认识论研究的角度是从主客体关系出发,与此不同,福柯切入知识的视角是话语实践。福柯认为,没有脱离话语实践而存在的知识。
“什么是话语”,“为什么话语是一种实践话语”,是需要明确的两个问题。在《词与物》中,福柯谈到,话语的任务就是“说出所是”[1],“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2]。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3],其所谓“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精神病学话语”等都是基于这个定义上使用的。话语不仅是一种陈述方式,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的符号,更是一种实践话语,即福柯所说的“系统形成的话语谈论之对象的实践”。对于福柯来说,知识的形成既不决定于话语内部也不决定于话语的外部,而只能决定于话语间的实践运动。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指出,“这个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种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知识是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4]在他看来,研究思想史或知识史应该先考察知识赖以存在的规则,即考察知识存在的前提条件——话语实践的总体要素及其规律。话语形成有四个要素,分别是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使用以及策略选择。这四个要素共同组成了“话语形成规则”,并由话语实践所确定的。换句话说,话语以陈述的形式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知识性的实践行为,而知识是在话语实践中构建起来的。因此,知识与话语的关系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话语是知识得以产生的基础性条件;二是知识在形成后也进入话语实践之中发挥作用,成为话语的一部分。知识就是这样在话语实践中产生和运转。
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相互利用的关系
福柯写道:“当我读到——我知道已经归属于我的——‘知识就是权力’或‘权力是知识’的命题时,我开始发笑,因为研究它们的关系正是我的问题……我提出它们的关系这一事实,清楚地证明了我并没将它们二者等同起来。”[5]由此可见,学术界将权力与知识等同起来的观点违背了福柯本人的思想。在福柯看来,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是互利关系,体现为权力控制知识,知识给予人权力。
(一)权力控制知识
在《词与物》中,福柯将知识概括为朝三个方向敞开的空间区域。第一个方向放置的是数学和物理;第二个方向是语言、生命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等科学;第三个方向是哲学。[6]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认为知识是由话语实践按照规则构成的要素整体。他所指的知识是广义的知识(savoir),而不是科学或规范的知识(connaissance)。换言之,福柯研究的知识是包括自然科学、经验科学及哲学在内的知识。为什么福柯要考察广义的知识,而不去探讨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那种规范的知识?也就是说,是否存在纯粹的知识?在福柯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柏维尔曾指出,传统的知识研究总是以探索知识的认识论基础为主,并将知识当成一种脱离政治统治行为的认识活动的产物。[7]而福柯指出了不存在纯粹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知识,知识都是为历代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所控制,为赋予不同社会阶层及其社会成员身份、权利和行为方式服务。正如福柯所说,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无处不在,权力也无处不在。“……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能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8]“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必须从真理与权力,而不是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9]从福柯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权力是一种知识化的权力,知识是一种权力化的知识。权力要对社会大众进行支配就必须建构各种理性主义和知识编码。
(二)知识给人以权力
知识给人以权力表现为知识本身具有权力功能。福柯指出,“如果把科学仅仅看成一系列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可以对命题进行证伪,指明谬误,揭穿神话的真相,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科学(知识)同样施行权力,这种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10]知识给人以权力还表现为,知识为权力的合理性辩护。福柯指出,“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知识)为功能的话语,以此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并获得特定的权力”[11],“如果没有真理(知识)话语的某种经济学在权力中,从权力出发,并通过权力运行,也就不能行使权力。”[12]权力的运转需要知识,权力的合理性必须通过知识来加以论证。如果没有知识的传播、保存,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
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研究上,福柯不仅考察了权力对知识的作用,而且考察了知识对权力的作用。福柯曾经无情地揭露道:“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13]在福柯看来,权力和知识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谁拥有权力,谁就决定知识的有效性;谁拥有知识,谁就决定权力的统治策略。
三、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相互依存的关系
福柯认为,上帝的死亡也预示着人的死亡。换言之,元话语的死亡代表了传统话语叙述主体的死亡。在他看来,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客观真实”等待主体陈述,所有的知识最终都是话语实践中隐而不现的权力和知识的相互利用。此时,“话语与知识”关系、“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向“话语与知识-权力”关系开始转变,使得话语、知识、权力三者的关系更加清晰明确。
(一)话语是知识和权力的存在条件
从话语的功能性层面来看,权力自身无法建构知识,必须以话语为前提条件,并利用话语形成知识;而知识若不进入话语之中,或者说不成为话语的一部分,也将无法产生权力形式。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对于“性倒错”问题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性话语是如何成为权力和知识的前提和条件的。所谓性倒错,在福柯看来,其实正是当代性话语的产物。“通过如此众多的话语,人们增加了对一些小小的性倒错的法律判决,人们把不合法的性行为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人们给从儿童时期到老年的性发展提出一套规范,精心地规定了所有可能的性异常的特征,人们还组织了各种教育控制和医疗方法,围绕着那些最微小的怪诞念头,道德家们、特别是医生们收集了一套有关可憎事物或行为的夸张语汇。”性倒错者由于破坏了西方社会的两大规范性体系——“婚姻的法律”和“欲望的秩序”,时常受到社会上控制性话语的打击。在打击的过程中随之相伴的是权力的关系,而且“控制性经验的权力必须紧贴着身体,注视着它们,强化它们的各个部位,它激活它们的皮肤,夸大它们的错乱。它把性的身体揽在怀中。无疑,这意味着它的效能得到了提高,控制的范围扩大了。”性话语通过对性倒错者进行判断和整合,制定出约束性倒错者行为的一套规范,从而实现了对某个群体的分类,使得权力关系的对象更加明确。
(二)知识和权力建构话语
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收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16]。在一定条件下,话语可以转化为权力,而作为权力的一种的知识则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须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17]。福柯在《何谓作者》一文对“作者”一词的阐释清楚地表明知识和权力是如何建构话语的。作者“AUTHOR”词源是权威“AUTHORITY”,也就是说,作者实质上就是统治者。作者在话语中掌握着话语权,实则是统治权。在一定意义上,这个“AUTHOR”就是国王。AUTHOR在中世纪指的是对精神的支配。然而对精神的支配是上帝所拥有的,这就说明在中世纪,统治者即是活的上帝,他对人们的精神进行统治,致使我们的信仰也交给了他们。因此国王才是真正的“AUTHOR”。福柯明确指出,任何人的言说和书写都无一例外地深受“话语形成”的规则支配。所以,从话语论来考量,任何作者都不过是在履行某种“作者-功能”。以前的作品并不是在表达作者真正的意图,而是揣摩并阐释、表达统治者的意图。一部作品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代表作者“死了”,因为一旦作者的思想形成文字,就必定会有各种解读。就如国王一样,他的命令和意志一旦下达,经过传话人的传达、阐释,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本经典会出现很多阐释本。从这个意义上,就如福柯所说的,作者并没有权威性,而是他的话语被滥用,被知识和权威工具化。
“谁在说话”、“在哪里说话”、“以什么身份说话”、“话语被谁用”、“话语有什么用”等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权力问题。福柯在话语形成的分析中也清楚阐明了权力和知识对话语的建构作用。对象、陈述形式、概念和策略共同组成了“话语形成规则”。福柯指出,这四个要素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四个要素依次形成一个垂直的等级系统,即上下行的关系,前面的层次制约着后面的层次,低级层次不能独立于比它们高的层次。这四个要素无不受权力和知识的影响:话语对象不是自为自在,它是知识和权力选择的结果,以知识和权力允许的方式确定、分析、分类、解释它们所掩盖构成的关系网络;话语陈述形式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建制确定的,并按照权力的规则行事,否则便会遭到排斥、歧视;概念的使用必须符合连续形式、共存形式以及涉入程序,话语才能获得理解、认同和接纳;话语策略的选择会受到知识和权力意志的影响,还要满足所属话语群的要求。
从探讨话语与知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到考察话语、知识与权力三者的关系,福柯摒弃了传统的认识论研究框架,独树一帜地从话语实践的视角指出,话语与知识的关系需要在话语实践中讨论,知识和权力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话语、知识与权力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福柯的话语理论让我们时刻对“知识”或所谓的“真理”保持警惕,不被权力所控制的知识所蒙蔽。
[1][2]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M].New York: Routled, 1989:48,121.
[3][4]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18,203.
[5] 王治河.福柯[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85-186.
[6] 参见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452-453.
[7] 参见杜以芬.浅谈福柯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知识与社会权力的控制[J].济南大学学报,2005(03):64.
[8][12]米歇尔·福柯. 钱穆译.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33-234、23.
[9] 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446.
[10][11][13]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2、37、31.
2016-10-10
李婷(1993-)女,广东梅州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