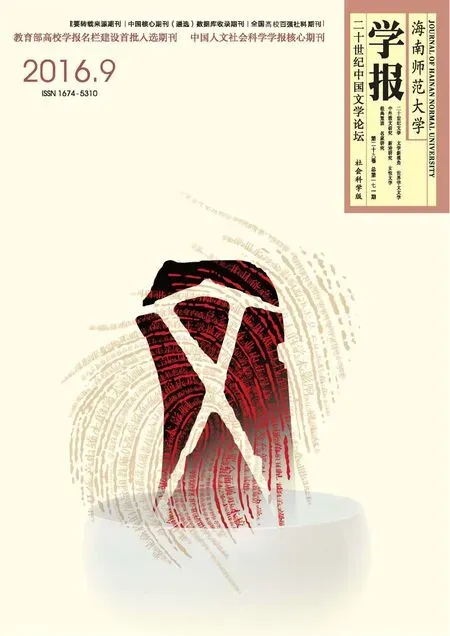行动政治:卢卡奇和齐泽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
孟 飞
(1.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2.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哲学与文化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46)
行动政治:卢卡奇和齐泽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
孟飞1,2
(1.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2.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哲学与文化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46)
卢卡奇和齐泽克所生活的世界图景和政治状况都不尽相同,但是对历史主义的批驳、反对资本主义的线性发展观、对行动政治的高扬等论点却非常切近。可以说,卢卡奇和齐泽克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充满了崇敬,但是又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卢卡奇;齐泽克;反历史主义;革命;行动政治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对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最普遍的共识是:广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政治经济的广泛论著提供了基础。①[美]B·A·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王加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60页。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历史哲学的建构日益成为显学。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中的旗帜性人物,而齐泽克是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最具爆发力的思想家,虽然他们所处的历史境遇和革命状况不尽相同,不过我们发现二者在对马克思历史观念的理解上惊人地相似。卢卡奇式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先在语境就是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是其哲学的逻辑起点和原初本体论。他用历史重构去针对当时第二国际理解马克思和观察资本主义现实的双重“伪图像”②②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意在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面相。历史概念幽灵性地出没于《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论文集中。卢卡奇断言:只有引入历史,才能希冀解决那些被察觉了的困境。齐泽克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溯中,不仅批判了历史主义连续进化的错误逻辑,而且找到了在现存秩序中寻找历史断裂、激发革命潜能的方式。卢卡奇和齐泽克的共同政治意图是,坚持一种行动主义的政治方式,即对欧洲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遗产的继承。
一、反历史主义,均质历史的谬误
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渊源由来已久,发轫于黑格尔,历史编纂的批评话语转向现代模式——尼采的系谱学,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柯林武德的“构成性想象”,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等等。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不把历史作为停滞的过去,而是发挥分析工具的作用。
卢卡奇指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异质于以往的虚假哲学,最显在的理论旨趣在于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科学批判理论的逻辑架构。这种批判哲学首先表示了历史的批判。《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历史”概念批驳了以往一切的超历史的叙事话语。卢卡奇梳理了经维科《新科学》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历史概念演化,就本质而言,以往的历史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精神的自我超越史,现实感性生活世界的“历史性”维度被“历史主义”所遮蔽。传统历史主义成为匀质空间里的线性发展轨迹,历史的差异性被暴力擦除,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时间概念的抽象性和齐一性解释。卢卡奇首先针对“物化时间”的谬误来抵达对资本主义时间史的揭露。卢卡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物性化的结构”。资本主义咒符不仅使历史过程中的客体物性化,并使物性化过程强加于主体。这种结构性的物化在当代已经被“无名化”或内化为了一种“自我认识”。所以任何无批判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理论都跳脱不出在各自不同的层次上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循环论证,确切地说,历史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内部繁殖生演。历史只会客观地流逝,成为没有获得真正发展的“福山式幻觉”。卢卡奇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框架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找到了对自明性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路径,也形成了科学认识社会历史本质的客观前提。古典经济学把商品和交换的发展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有其规律的古典国民经济学类比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可以看出,就其特征和对象结构来说都十分相近,于是古典国民经济学研究经济体系的本质和规律也被伪造成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那种自然界。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所谓“社会关系”是把人的主观存在排斥在外的,人“仅仅作为抽象的数量、作为某种可归结为数量、可归结为数量关系的东西”而结构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人的历史性生存以一种自然存在的形式呈现,社会历史规律被置换为社会自然规律。《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摒弃了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它揭示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的变化的,因此也必定要历史地走向灭亡的。”*[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页。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即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这个报告中甚至提出了“重写历史”的号召。卢卡奇借此抵抗非历史的自然性规定,以反对一切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出现的“自然法则”、“自然秩序”和“似自然性”。由此,批判理论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历史恒定命题的批判。
虽然齐泽克没有直接援引过卢卡奇的相关论述,不过就对历史主义的批驳来看,他们的思想原质颇有些家族类似(维特根斯坦语),当然,齐泽克的理论阐发是建立在拉康主义的精神分析地基之上的。齐泽克的论文《历史反对历史主义》同时批驳了历史相对主义和简单的反—历史相对论(历史主义)。通过本雅明的杰作《历史哲学论纲》,他揭露了官方编纂的连续的、空洞的同质性时间的反动本质。齐泽克认为,反对“解释学”的和“权力意志”的压迫就需要历史唯物主义“阻止、固定历史运动的能力,以及从历史整体中分隔细节的能力”*[斯]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历史唯物主义是建构的流动过程,而不是叙述性的过去,具有创新意义的当下用它的本真瞬间打断了历史匀质空间里的线性发展轨迹,并从历史的同质化流变过程中逃逸出来。联系到现实的反资本主义革命斗争,齐泽克坚持“彻底历史性”的标靶应是消解以往父系霸权的历史肌质和胜利肌质,通过一次次失败获得过去模态命题评估的补偿,这个关键时刻就是辩证运动的机理——开头处繁复的回溯性重构。这样就涂改了统治阶级空洞介质的“大文本”,闯入本雅明意义上的弥赛亚时间,以新的“大文本”去展示终将实现的本身。哲学的抽象论证的最终目标是寻找现实难题的克服途径,针对今天的左派面对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及自由民主制度的不同回应方式,齐泽克认为这些政治学意义上的不同的否定性模式遵循了精神分析中拒斥创伤性真实的不同形式。由于这些构想都依赖于最小限度的“非历史的”形式的框架来定义理论地平,因而并不能真正提供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本雅明式“弥赛亚”的“中止的辩证法”要求我们询问资本主义自身所产生的边界,暴露其创伤性“非历史”内核。
二、生成与革命潜能,资本主义的自我消解
对纯粹自然样态的伪历史书写的批判,消解以往父系霸权的历史机制和胜利机制都必然将卢卡奇和齐泽克的理论逻辑引入主体思维的架构之中。这一点来源于黑格尔的启发,但是《精神现象学》的主客体同一图式仍是超历史的。黑格尔虽然也试图寻求具体的、历史中的“我们”,但是“我们”在他的唯心主义概念体系中是找不到还原点的,因为黑格尔主义的“我们”是抽象的、精神的我们,是被历史主义体系框定的“我们”。绝对精神的大全和历史永恒创造性寻求历史的终点,而终结或者完成态扼杀了主客体作为“历史性”统一体的现实性与批判性。
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本体论,这里的历史是实践性的历史,历史的主体是人们的创造世界的行动。真实的主客体辩证关系必须建立在感性实践活动这一生存着的“历史性”的主体之上。于是历史成为真正的行动者、创造者,成为了对现实的批判和真正的当下。我以为,“生成”归纳了所有卢卡奇对历史概念判断的核心。从古希腊哲学到尼采,生成已然不是时髦的概念,但卢卡奇通过“生成”,继续了自维科以来经康德、赫尔德、黑格尔而由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所阐释了的“历史性”话语的内涵。历史本质上具有主—客交互作用的生成性建构力量,生成不是无内容的时间形式,而是我们当下生活的现实性。历史是我们生活的历史,随着我们现实生活实践的延展,历史过程向我们不断地生成。历史如果展现其本质,它就是我们的生活实践本身;历史又无法透露本质,因为它处在时时生成中、创造中、更新中。我们说,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就是自然不断向人的生成,同时又是人不断创造着他们复杂的、自由的社会关系以及不断生成着它们作为人的崭新本质的具体的统一过程。《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这篇论文指出资本主义物化的生存境域中,目的合理性被“祛魅”了,而工具理性成了统治的力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的关系所遮蔽。卢卡奇的观点是,要从根本上移置认识的拘于部分的直接性,只有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够把捉。“生成就不是一种纯粹普遍变化的抽象的飞掠而过,不是内容空洞的实际渡过的时间,而是那种关系的不停的产生和再生产。”*[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68页。在历史性语境中,现实不断生成,事实世界在我们的关注下就摘除了恒定不变的假面,丧失了它那似乎独立自在的性质。一切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并为人的现实生活的种种关系所中介过的存在,在时间中的存在,在历史中的存在。因此这个生活世界的一切所谓的“事实”存在都只不过是具体的、历史的、暂时的。事实僵化的界限、一切固定不变的“规律性”在对时间性的领悟中消失了。由此可见,卢卡奇对资本主义永恒化的批判找到了现实的出口,资本主义只是历史过程的一个暂时的过度性的环节而已。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资本主义并非永恒之物,有其具体的、历史的形成和界限。“我们的导师的遗嘱”*[波] 罗莎·卢森堡著、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4-377页。明确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造成社会内部的对抗性结构,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然。
与“生成”的概念发生文本互文的是齐泽克的“革命潜能”观,齐泽克把本雅明的“革命潜能”看作对象,它只作为自身的缺失而产生;只以它自身缺失的形式而存在。其结论是:“(革命潜能)与其说是被置入历史而现实化的东西,还不如说是使我们可能通过把任何东西置入历史而实现某种缺失之物的东西。”*[美]瑞克斯·巴特勒:《齐泽克宝典》,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8页。借用黑格尔的术语,齐泽克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在创造和完成自身的部分之同时也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即排斥的部分——那些阻止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自身的对抗,这种对抗将提供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的历史性批判。如同主体的形成本身便表征着一种不可能性一样,植根于资本主义逻辑之内的冲突与对抗将动摇资本主义的结构原则。而为了逃避与实在界相遇,仅仅在同一形式框架内进行偶然性的替代游戏是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的。尽管当代资本主义较之维多利亚时代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齐泽克在反对“自然化”、“永恒化”问题上仍然坚持绝对历史性的批判态度。资本主义的出现当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过去便已存在,也将永远存在下去。
三、行动政治,从历史中显现
卢卡奇和齐泽克提醒我们,请铭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伟大论述:资本主义的唯一界限是资本主义本身,能够毁灭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是资本本身,它必须从内部爆炸。所以,“生成”和“革命潜能”等概念中透露出的根本用意是全球的、大量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环节的联结,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如果无法还原到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模态中,那是不完整的。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有一段精彩陈述:“生成同时处于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中介,但是是处于具体的,也就是历史地过去和同样是具体的,也就是同样是历史的将来之间的中介。当具体的‘这里’和‘现在’溶化过程时,它就不再是不断的、不可捉摸的环节,不再是无声地逝去的直接性,而是最深刻的、最广泛的中介的环节,是决定的环节,是新事物环节。”*[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8页。我们认为,生成作为一种当下的建构,是一种将过去造就新质的创化,并且这一当下的创造也是走向未来的环节。历史的生成作为一种时间,不是平滑的持续流逝,而是一种过去—现在—将来的三维同一的历史性生存时间。卢卡奇指出:“只有人能把现在把握为生成,在现在中看出了那些他能用其辩证的对立创造出将来的倾向时,现在,作为生成的现在,才成为他的现在。”*[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01页。在他看来,历史没有永恒的事物而只是活生生的过程,因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不断生成和敞开,这种生成是现实性的“倾向”或者说是现实的“将来”,因为生成永远在敞开着未来,“生成的真理就是那个被创造但还没有出世的将来,即那正在(依靠我们自觉的帮助) 变为现实的倾向中的新东西”*[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99页。。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生命活动的生成之中统一起来。它的现在是在过去的必然性中生成的并且孕育着作为它的理想的将来趋向,它的将来只是在现实性的根据中才生成其为将来。卢卡奇旨在向无产阶级宣扬历史的、革命的辩证法,比如阿格尔评论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把资本主义的恶危机趋势所决定的工人阶级的客观状态同从‘阶级意识’的角度说明统治和解放的工人阶级的主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加]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4页。。这是不错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基本反映了卢卡奇投身革命早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这部著作可以理解为卢卡奇对1920 年代初政治革命危机的紧急反应,它是与革命实践相联结的战斗文本。
齐泽克极其推崇这种在历史转捩点的行动主义政治方案,他不由地回溯到卢卡奇同时代的革命实践中,他高度赞扬了那些随时准备接手基层工作并敢于负责的人,而列宁则是这些人的原像。“他总是负绝对责任,绝对不会妥协。如果你在掌权,掌握真正的权力,那就意味着非常激进的东西,这意味着你是没有借口的。”*[斯]斯拉沃热·齐泽克、[英]格林·戴里:《与齐泽克对话》,孙晓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页。他不断强调,绕开列宁也就没有可以直接接近的“本真马克思”。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对历史时刻显示出自身意义的把握能力是惊人的。列宁的判断是:临时政府的优柔寡断为跳过民主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并连接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机会。齐泽克认为,列宁并没有悖逆普遍规律的知识,因为列宁的主张只存在节奏上的缓急而已,革命规划的第二阶段紧紧跟随第一阶段。“必然发展阶段”的客观逻辑是不存在的,复杂化进程的环绕总是破坏事件的生成。所以列宁主义者的坚定立场是,实现骤变,在形势的辩证矛盾中即使条件不成熟也要不畏惧行动,不畏惧即使不愉快的后果,不畏惧实现其政治工程。亨廷顿对其赞词是:“二十世纪最具有意义的政治创新。”*[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307页。齐泽克论述了当时俄国同时存在的两种反对冒险革命的声音。第一种只强调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适性。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他们认定俄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就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事情,社会主义的介入会导致历史的跳跃,会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第二种声音来自对道德—政治后果的担忧,比如考茨基等人在议会中幻想可以建构一种结盟政府,他们试图在民主合法程序中寻求革命的正当性。这类对行动深渊恐惧的实质是:既然每一项行动都冒着偶然性的危险,那么无人有权将他的个人选择强加于人。所以,民主与其说是对正确选择的保证,不如说是对付可能的失败的机会主义保险——人人都负责。齐泽克认为这两类抵抗冲动实际上都是寻找某个大他者的先验保证。而列宁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用另外一个大他者来反驳对立的意见。即是,没有大他者,“我”承担起了行为的责任。这就好像拉康指出的精神分析师只能投身到没有任何外部保证的自身授权一样。拉康认为,只有通过行动才有效地假定了大他者的不存在,“我”扮演了不可能性,也就是既存的社会符号秩序坐标中作为不可能出现的东西。用齐泽克的话来说,“政治调停本身不会发生在某个潜在的全球矩阵的坐标中,因为政治调停的结果正是这个矩阵的‘改组’”*[斯]斯拉沃热·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宋文伟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页。。在《今日列宁主义》、《呼唤列宁主义的不宽容》等文章中,齐泽克高扬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的果敢和决绝。齐泽克由此引申出他所认为的左翼政治的主要特征是行动的政治,是把反资本主义主题付诸于行动的政治现实主义。
结语:卢卡奇和齐泽克,政治的浪漫派
卢卡奇的历史理论指出:“如果我们可以把全部现实看作为历史(即看作为我们的历史,因为别的历史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实际上使自己提高到这样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上,现实可以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3页。如果做一点言辞上的转化,那么卢卡奇呼唤革命的行动主义,正如《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明确的:要由行动来证明和指出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行动使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的历史的统一中得到了实现,毅然投身于行动应该被视为将无可避免的命运坦然接纳下来,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措施。卢卡奇思路的当代表述是:对抗性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而这种对抗是同行动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是对抗得以确立的条件。行动实现了那些在给定的象征世界中似乎“不可能”的东西,它是为自身创造可能性的行为。
同样,齐泽克也把行动当作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重要指针,他通过“行动”概念的阐发把他的政治理想与当今左翼政治实践的各种形式明确区分。从拉康到齐泽克,当代学界对“行动”的解释是玄奥和艰深的。瑞克斯·巴特勒给我们提供了通俗的解释:“它们(行动)都打破了现存的符号性惯例。它们并没有停留在可以接受的可能性的范围之内,而是积极探索并发展这些可能性。伴随着行动,总是存在着一种意料之外的、无法预言的要素,它们是在现有视阈中不可预见的某种东西的因素。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行动必然发生在旧的符号秩序中,那么就不能在这一秩序内完整地命名或评判它。它的目标恰恰是重新定义什么是可能的,并且改变理解它的标准。在这一意义上,只有行动成功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以其自身条件来谈论它。它转变了符号语境,继而才使自己看起来的确是可能的……只是行动本身使发生的事件有了成功的可能,而这些事件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可能性的实现。”*[美]瑞克斯·巴特勒:《齐泽克宝典》,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页。齐泽克认为,全球左派意志消沉的大背景下思考应对全球资本的新模式,首先就要反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倒退到消极的对灾难性结局的浸淫中——反叛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积极行动以寻求共产主义宏图伟业的教义。我们应该将行动视为无可避免的命运坦然接纳下来,同时回溯性地置身于过去的有可能发生的可能性中,我们现在就要按照这样的可能性采取措施。
但是,学界对于卢卡奇和齐泽克的诟病主要也来自于他们历史方法中的总体化革命观,即把历史彻底历史化的方法——把“历史”抛进行动的领域。这是与把所谓的历史辩证法先验化和神秘化联系在一起的,卢卡奇和齐泽克思想的理论特征是跟在一定迷惘的时代建构乌托邦的救世希望的理论努力的本性有必然的联系。高扬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行动表征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卢卡奇和齐泽克浪漫主义的冲动和主体性逻辑的出发点。我的看法是,与其把这种乌托邦性当成卢卡奇和齐泽克思想的某种局限,不如说,如果当代批判理论还有什么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话,那就是乌托邦。列斐伏尔的观点是,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更甚,没有任何思想中不存在乌托邦。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干脆是乌托邦本体的。在政治的洪流中英勇斗争如果泯灭了乌托邦情结,那么连我们行动的借口不也被阻止了吗?乌托邦是当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继续行事已不复可能的时候,某种我们为了生存而被推入其间的事物,这与左派解放政治的迫切愿望是息息相关的。
(责任编辑:袁宇)
Action Politics: Lukacs’s and Zizek’s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View on History
MENG Fei1,2
( 1.SchoolofMarxism,SoutheastUniversity,Nanjing210096,China; 2.TeachingandResearchDepartmentofPhilosophyandCulture,PartySchoolofNanjingMunicipalCommitteeofCPC,Nanjing210046,China)
Despite differences in their respective world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Lukacs and Zizek are rather similar in their views as to their critique of historicism, their objection to the capitalist linear development notion, and their compliment of action politics. As it were, Lukacs and Zizek were fully reverent towards Marx’s view on history, but with a strong flavor of romanticism.
Lukacs;Zizek;anti-historicism;revolution;action politics
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外语类重点课题“齐泽克文艺批评的哲学原质”(项目编号:15jsyw-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6M591751)
2016-05-20
孟飞(1983-),男,江苏南京人,东南大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博士后,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B089.1
A
1674-5310(2016)-09-0098-05
——回望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