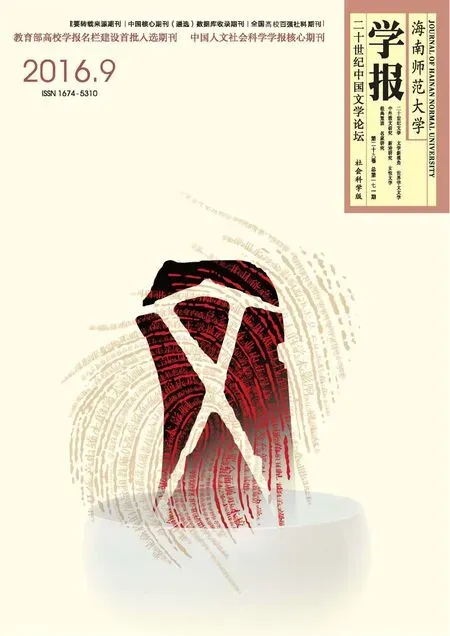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梳理及辩证解读
莫焕然
(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广东 珠海 519000)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梳理及辩证解读
莫焕然
(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广东 珠海 519000)
生态女性主义在同一理论范式下思考人类、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寻求三者的和谐共存,在多元纷争的今日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追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渊源并分析其内涵与特质的基础上,澄清对该理论的误解,为其理论和实践困境寻求出路,是一种颇具价值的努力。
生态女性主义; 理论梳理;辩证解读
一、引言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无度索取与肆意破坏,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人们开始反思自然界之于人类的价值。20世纪后半叶,哲学伦理界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理论,生态中心主义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判断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准则。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在经历了自由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后,也打着解构的旗帜,向主流文化中心推进。在此背景下,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自然而然地汇流成生态女性主义。
本文追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渊源,分析其内涵与特质,并在此基础上澄清对该理论的误解,试图为其理论和实践困境寻求出路。
二、理论梳理
(一)渊源追溯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最早见于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埃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的代表作《女性主义·毁灭》一书中。此后,众多学者的真知灼见丰富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也拓展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疆野。
生态女性主义不断地从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大理论系统中汲取养分。生态主义是其第一个思想源泉。其中“土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又是生态主义的代表思潮。1949年,美国新环境理论创始人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年鉴》一书中提出“土地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认为土地是一个由人和其他非人物质共同组成的彼此依存的整体,每个成员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人类应抛弃土地征服者的姿态,努力维护这个共同体的健全。①[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舒新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8页。1973年,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斯(Arne Naess)创立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把自然科学范畴的生态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世界观结合在一起,关注整个自然界的福祉,追问环境危机的社会、文化和人性根源,以人类和自然的协同发展为起点与归宿,自觉承担起尊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责任。②Naess, A,The Ecology of Wisdom: Writings by Arne Naess, New York: Counterpoint, 2010, p.73.
生态女性主义的另一个思想源泉是女性主义。部分女性主义者在原有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拓展新的疆域。他们发现远古时代的人类视自然为母亲,对其充满敬畏之情。这样的有机论哲学观对人类的行为具有文化强制力和道德约束力,因为戕害母亲的行为是为社会道德所谴责和禁止的。同理,女性繁衍后代的能力受到推崇而与男性平等。但萌发于十六七世纪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却使有机论哲学观让位于机械论哲学观。在这样的语境下,人类以自然的主人自居,视自然为被动的、机械的物质实体,利用自身掌握的科技驾驭自然,造成一系列的生态危机。同时,在机械论哲学观之下的男权制社会中,女性与自然一样受到男性的控制与压迫。溯源让女性主义者确信自然和女性的命运息息相关。于是,他们把生态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熔于一炉,将远古的模糊意识发展为现代清晰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体系。
(二)内涵与特质分析
1.兼收并蓄,熔生态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于一炉
生态女性主义熔生态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于一炉,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理论体系。首先,生态女性主义者视自然为一有机整体,人类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因此,人类与自然应紧密相连、协同发展。其次,生态女性主义者重视社会生态中女性的地位与权利,批判男尊女卑,提倡两性平等。此外,生态女性主义者还强调自然与女性的联系,主张从女性角度去寻求解决自然生态环境失衡的良方,站在生态整体性的高度去探寻实现男女平等的良策。正如美国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凯伦·沃伦(Karen Warren)所指出的那样,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压迫是相互联系、相互强化的,因此,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开展离不开生态学的介入,而生态问题的解决也必须借助女性主义的推动。*Warren,K,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p.99.
2.破立结合,重理论的解构与重构
生态女性主义另一特质是破立结合。它在解构掠夺自然和压迫女性的压制性观念体系的同时也构建“和谐”观念体系。
生态女性主义拆解掠夺自然和压迫女性的根源——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男权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把人的利益视为价值原点和道德尺度。它的形成可以溯源至基督教和西方哲学。《圣经·创世纪》里描述了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赋予其治理大地和管理万物的权力。基督教教会进一步指出,地球只是人类通往天国旅途的临时居所。自然一旦被去神圣化和世俗化,人类便无所畏惧地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视世界为一个按理性能力高低排列的等级结构,作为理性能力最高的人类自然是主宰。可见,人类中心主义鼓励了人最富掠夺性与破坏性的本能。男权中心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派生物,是男权社会中一整套为男性霸权服务的权利话语体系。它把男性定义为社会的主体,女性定义为附属并服从于男性的客体。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借助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实现它们对自然和女性的奴役。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我们应当提倡生态中心主义,构建“仁爱伦理”。在生态学揭示出人类和自然的其他成员具有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关系的基础上,生态中心主义提出我们应该考虑整个生态系统,而不是把个体与母体分离。生态中心主义努力构建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伦理范式,以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为依据,来衡量人类思想和行为的道德价值。“仁爱伦理”承认并尊重事物之间的差异,认同中间状态,指出“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动机的核心是对他人和自己的爱的能力”*Warren,K.,Ecological 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08.。
3.流派丛生,纳多元观点于一体
吉蒂·纳罕娜格(Jytte Nhanenge)将生态女性主义概括为“一个立场多样的伞状术语”*Nhanenge, J, Ecofeminism: Towards Integrating the Concerns of Women, Poor People, and Nature into Development,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11, p.207.。可见,流派丛生、观点多元是其重要的特质之一。这些流派相互交汇,使生态女性主义在不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中向前发展。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揭示男权统治者以自然不具灵性、女性具有异于男性的生物机制、女性与自然有着本源的联系为理据,将自然女性化,女性自然化,并将对两者的压迫视为具有同源关系的自然现象。他们在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in)和瓦尔·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等人的带领下,通过构建关爱伦理(Ethics of care)和弘扬女性文化,确立生态有机体的观念。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判定源于于父权制的精神信仰,如犹太教和基督教,使压迫自然与女性的罪魁祸首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成为主流价值体系而充斥于世。因此,只有肃清这些旧的精神信仰,树立以大地为基础的新的精神信仰,才能解决危机。代表人物查伦·斯普瑞特耐克(Charlen Spretnak)就认为复兴女神宗教理念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
以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为代表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要削弱自然与女性的联系,因为自然与女性的联系本身就是社会构建和意识强化的结果,只能将男性社会构建的女性生物学意义上的弱势扩大化,而不利于女性的解放。*Merchant, C.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One, 1990, p.253.他们指出,生态危机和性别失衡的根源是父权制概念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需要构建一个无统治制度的社会。
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肯定自然与女性的联系,但他们并没有囿于一隅,只进行性别思考,而是对自然、女性、有色人种、下层阶级等社会弱势群体均给与伦理关怀,批判所有不公正统治及不公平主宰。该流派的领导人物范达娜·西瓦(Vandana Shiva)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只不过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策略。它使财富和权力集中到发达国家和精英阶层,而第三世界国家和下层民众则备受压迫剥削。西瓦提出恢复能动的、整体的和可持续的女性原则。*Shiva, V. & Mies, M.,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1993, p.308.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从哲学层面揭示出父权制是自然和女性被压迫的根源。父权制通过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给自然和女性套上枷锁。因此,哲学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非二元的基于联系的概念框架。如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就针对男性中心主义中被边缘化的“他者”,提出了“另者”(an-otherness)的概念:任何异于“自我”的个体均是与“自我”有别却相互平等、相互依存的“另者”*Murphy,P. Literature, Nature, and Other: Ecofeminism Critiqu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 p. 152.。“另者”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消解“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用“仁爱伦理”化解“自大伦理”。
三、辩证解读
生态女性主义与批判和质疑相伴而生。笔者认为有些批判是误解,需要予以澄清;而有些质疑则道破生态女性主义的困境,有助于出路的探寻。
(一)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
有学者曾指出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与“女性主义”两个角度是一个悖论。因为生态是一个整体视角,而女性主义却是一个强调男女两性相区分的视角。*孙丽君: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困境与出路》,《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为了调和这一悖论,我们是否要摒弃女性主义这一视角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生态主义本身并不排斥视角。事实上,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切入问题的途径。再次,女性主义视角恰恰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独特之处。但以女性主义作为切入点,就意味着生态女性主义者必须警惕女性视角中强调区分与批判的倾向,坚持不管女性还是男性都是生态链中的一个结点,这一结点的生存发展依赖于生态系统这一整体,又反过来影响着这一整体。换句话说,生态女性主义者可以立足于女性主义的视角,但他们的视域内不能仅仅只有女性的身影,而是应延伸至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人类与非人类存在。
(二)二元制
生态女性主义处理二元制问题的方式的确需要斟酌反思。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者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作为掠夺自然、男权中心主义作为压迫女性的根源,有再次陷入二元制窠臼之嫌。而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人类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二元对立,容易抹杀人类与自然的独特性,导致主体的迷失。*陈伟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困境及批判》,《理论与改革》2013年第6期。诚然,如果不坚持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人将成为自然界中消极被动、碌碌无为的“自在物”,根本无法实现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描绘的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持续发展的理想蓝图。事实上,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早已认识到这一理论困境并尝试寻求出路。笔者认为,前文介绍的墨菲的“另者”概念不失为出路之一。因为“另者”有别于“他者”。“他者”是与“自我”不同并因此对立的概念。而“另者”虽与“自我”相异,却与“自我”相互平等、相互依存。如此一来,一方面二元对立得以消解,另一方面主体的重要性也不会被忽视。只有强调人类与自然两者的差异性统一,坚持“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的统一,人类才能一方面合理、适度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以利于自身的生存及发展;另一方面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将人的形象推演至万事万物,促进生命共同体的繁荣。
(三)女性与自然
有学者担忧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结,无异于将女性重新束缚于生育、持家的传统角色中,无法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如珍妮特·比尔(Janet Biehl)认为强调女性生物学意义上所独具的优势是一种倒退。因为女性异于男性的生物特征正是父权社会中男性压迫女性、掠夺自然的依据。*Biehl, J, Rethinking Feminist Politic,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1, p.212.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是让女性撇清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对自然的歧视换取对女性的歧视,是一种残留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这样的女性主义何以能破自然危机之困,何以能取女性解放之道,何以能解人类救赎之谜?而且,我们不能否认,几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体现出女性与自然的联系。首先,这是因为女性特有的孕育生命的体验造就了女性独特的、异于男性的对生命的博爱。正是这样的体验及由此产生的女性特质让女性与同样孕育生命的自然具有息息相通的亲和关系。其次,女性是生活环境的主要使用者,对环境污染更有切身体会。肯定和强调这样的亲和关系并不是“倒退的“,而是“革命的”。这样的亲和关系让女性较男性更能热爱自然并自觉践行生态女性主义赋予自然以主体人格、万物以言说权力的理想。再次,这种亲和关系能赋予女性自然母亲代言人的身份,从而使女性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更能推动人类文明秩序的重建,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实现自然界生命丰富多元,人类文明两性和谐平等。复次,女性的悲悯、包容、关怀等特质并不是女性的劣势,这只是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压迫女性的借口。笔者认为,这些正是所有人应当具备的品质,因为这些品质是利他主义的。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救自然,解放女性,救赎人类。
(四)男性与女性
有的学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有让女性取代男性从而占据中心地位的倾向。这样只会构建另一种“强权话语”。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恰恰说明这些学者并没有真正领会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误将早期的狭隘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混为一谈。的确,19世纪末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次妇女运动都过于偏激地将男女两性置于绝对对立的位置,从而导致女性主义的滥觞。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是男女关系的和谐,不是用女性霸权取代男权至上。不仅如此,生态女性主义还呼吁人性的全面伸张,除了关注女性的解放,也要关注弱势种族和弱势阶级等边缘群体的解放,表现出对人类未来价值的终极关怀。
(五)理论整体性
西瑟·伊顿(Heather Eaton)在其著作《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导论》中指出:生态女性主义跨越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环境学等多个学科。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对多样的声音和不同观点都极具包容性。*Eaton, H, Introducing Ecofeminism Theories, New York: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5, p.336.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多学科性、多领域性和多视角性虽然能吸引不同领域的学者加入,但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难免会削弱其理论的整体性,使其外部呈现出混乱的状态,陷入理论认知的困惑和实践联盟的困境。*陈伟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困境及批判》,《理论与改革》2013年第6期。笔者认为,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流派丛生、观点多元,但事实上,一番拨云见日后,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纷繁的表征之下共同的目标和理论根基:各流派均以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两性和谐共存为总体目标,均强调对“权力范式”的解构与对有机世界观和生态伦理的建构。流派丛生、观点多元不是混乱的表象,而是生态女性主义在迥异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语境中,根据这些不同的因素的组合变化而做出的调整。*Warren,K,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p.287.众所周知,我们对理论的认知应该基于自己所身处的具体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在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多元化反倒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与接受该理论。其次,理论只有具体化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生态女性主义的具体目标是有差异的:可以是保护自然生态,可以是解放女性,可以是结束种族主义,也可以是对抗阶级压迫。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化更能保证目标的实现,从而更能凝聚为此奋斗的各种力量。再者,不同流派观点之间的交融与碰撞更有助于理论的整合和发展。可见,流派丛生、观点多元恰恰是生态女性主义生机盎然的体现。
(六)理论的偏颇
有学者指出,生态女性主义者突出女性与自然的天然联系,指出男性伦理的基调是对自然的仇视。这一定论难免以偏概全,混淆了性别的生理性与社会性,忽视了不同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个体差异。*彭慧洁:《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意义和困境》,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或许某些男性更具备生态意识,更能与自然亲近,与女性共处,而某些女性却沦为男权社会压迫自然和其他女性的帮凶。诚然,这样的差异的确存在。故笔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需要对其中所指涉的男性和女性给予更明确的限定。但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这种差异事实上给生态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首先,除了一些女性的呐喊以外,我们可以听到具有生态意识的男性的声音,这对于实现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极为重要。因为没有达致女性与男性的和解,如何谈得上两性的平等与和谐呢?其次,那些成为男权社会中压迫者同谋的女性,她们和其他男性压迫者一起,正是生态女性主义需要争取的对象。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恰恰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也是其现实意义所在。
还有学者质疑生态女性主义滥用了“人类”这一概念,模糊了不同国家、种族和阶级中不同群体的界限,一方面让受害者被并入“人类”概念而蒙冤,另一方面又没有突出本该承担更多罪责的破坏者,致使社会政治维度被遮蔽。此外,对父权制的批判实际上是以偏概全地将整个人类文化置换成西方文化,忽视了其他地区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因而有失偏颇。*彭慧洁:《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意义和困境》,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笔者赞成这些洞见,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者务必做跨群体和跨文化的思考。
(七)科技观
生态女性主义视现代科技为男性驾驭自然、控制女性的工具而加以批判,忽视了现代科技对自然和男女两性都具有积极影响的事实*李鹭、 殷杰:《生态女性主义的科学观》,《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1期。。笔者认为,科技进步本身并无过错,问题的关键是利用科技的主体。只要科技有进步的人文精神的引领,它是可以助力我们维护生态平衡、实现持续发展之事业的。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应该修正他们对科技过于偏激和盲目的态度,扭转技术悲观主义的倾向,对于能促进自然与社会生态和谐的科技应鼓励发展并大胆利用。
(八)理论与实践
有的学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重理论,轻实践,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泛设想。*关春玲:《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笔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并未忽视实践。首先,理论构建与传播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因为各种专著的问世,各种研讨大会的召开都有助于提高生态女性主义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此外,生态女性主义者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和女性解放的实践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也有迹可循:在印度,她们发起“普契尼抱树”运动,保护即将用作炊事燃料的木材;在中国,她们举办“妇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专题培训;在肯尼亚,她们植树造林,变沙漠为绿洲;在瑞典,她们向国会议员呼吁,禁止在森林里使用除草剂;在英国,她们抗议核导弹对地球生命造成威胁;在美国,她们揭露铀矿开采和危险物垃圾填埋造成的癌症上升和新生儿缺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11月和1981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妇女的五角大楼行动”(The Women’s Pentagon Actions)。在这次集会中,妇女们呼吁维护女性的正当权利,谴责人类为一己之私而肆意掠夺自然资源、毁坏自然生境的卑劣行为。纵观所有的这些实践运动,都是以非暴力的形式出现的,温和理性。此外,平民政治运动这一特点,也说明生态女性主义已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而有具备强大的号召力和持久的战斗力的可能。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态女性主义在实践中确实存在问题。首先,“生态女性主义”容易令人望文生义,误认为支持者必定是女性。这就造成了参与人群的狭隘化。其次,生态女性主义实践活动多是集会、示威,方式缺乏多样性。再者,平民化的运动缺乏政府支持而不能有更高的上升空间。对于这些实践困境,生态女性主义者可以考虑以下的解决途径:首先,要强调“女性”只是视角,不是参与者必须具备的生物特性。事实上,这里的“女性”已成为一种文化隐喻,代表所有受欺辱的弱势群体与和平、眷顾土地家园的阴性气质;而且,生态女性主义要超越性别思考,将关怀延伸至所有受压迫的弱势群体,这样便可争取更多支持力量。其次,实践活动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在家庭,生态女性主义者应采取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对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下一代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消费领域,他们应选择低能耗、无污染的绿色产品,利用消费引导生产以促使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学校,他们应重视环保和平等意识的培养;在科研领域,他们应继续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此外,生态女性主义者必须寻求政策的参与和支持,让决策部门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国家方针政策制定的依据之一。
四、结语
生态女性主义在同一理论范式下思考人类、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寻求三者的和谐共存,在多元纷争的今日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其理论与实践上的困境也是值得大家深入思考,努力解决的。让我们为“一个没有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Gaard, Greta,Ecological Politics: Ecofeminists and the Gree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2-43.的生态社会而奋斗吧。
(责任编辑:袁宇)
Eco-feminism: Theoretical Systematization and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Mo Huan-ran
(ZhuhaiCampus,ZunyiMedicalUniversity,Zhuhai519000,China)
Eco-feminism’s reflections on and probe in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humanity, nature and society under the same theoretical paradigm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oday’s world of multiple disputes. Based on a retrospect of the origin of eco-feminism and an analysis of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some misconceptions and remove dilemmas in theory and practice—a worthwhile endeavor.
eco-feminism; theoretical systematization;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珠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2016年度一般课题“生态女性主义辩证解读”(项目编号:2015YB032)
2016-06-18
莫焕然(1979-),女,广东韶关人,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讲师,悉尼大学TESOL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C913.68
A
1674-5310(2016)-09-01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