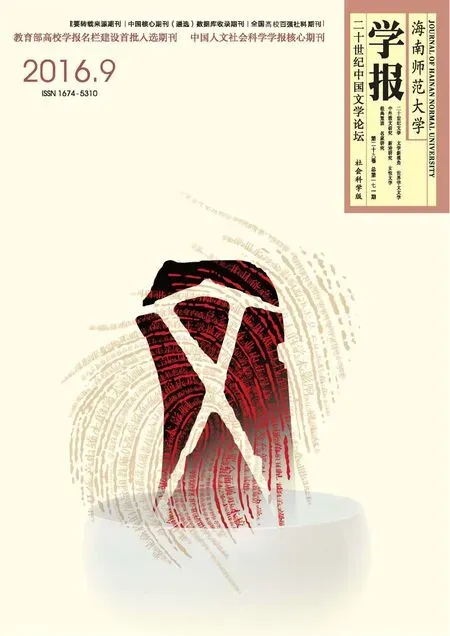利奇Semantics“语义类型”术语群的汉译
——兼谈Leech语义分类的逻辑
张春泉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利奇Semantics“语义类型”术语群的汉译
——兼谈Leech语义分类的逻辑
张春泉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利奇(Geoffrey Leech)的《语义学》(Semantics)关于语义类型的术语形成一个“术语群”,学界关于该术语群给出的汉语翻译分歧较大,在综合考量已有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Leech语义分类的逻辑,笔者倾向于译为:理性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反应意义(Reflected Meaning)、主位意义(Thematic Meaning)。“语义类型”术语群的汉译存在一定分歧有文本内外原因。
Semantics;意义类型;术语翻译
利奇(Geoffrey Leech)的《语义学》(Semantics)在中国语言学界译介较多,影响较大。其中关于“语义类型”的划分尤为精彩,“语义类型”在利奇《语义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者在论述语义的类型和语言的社会功能方面也有他的独特创见。他从理性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等七个方面来分析不同类型的意义如何适从于语言交际的总体效果。”①沐莘:《推荐一部富有创见的语义学书——浅评杰·利奇的<语义学>》,《外国语》1988年第1期。利奇的“语义类型”学说及其《语义学》在中国语言学界影响较大,引用频率较高,译法较多。
利奇《语义学》语义类型术语的汉译,学界有一定的分歧,有的分歧还很大,甚至相扞格。为更好地“拿来”,更清晰地分析、更透彻地理解利奇关于语义类型的论述,我们在此搜集了有一定代表性的12种文献,其中著作和论文各6种,6种著作分别列举如下。陈慰《英汉语言学词汇》②陈慰:《英汉语言学词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这是工具书,其汉译搜集尚全,只作参考,下文相关统计一般不列入;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等译《语义学》③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等译:《语义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是Semantics的中国第一部全译本。其余4种均在参考援引Semantics的意义类型时作出翻译,分别为:束定芳《现代语义学》④束定芳:《现代语义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伍谦光《语义学导论》(修订本)⑤伍谦光:《语义学导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胡壮麟《语言学教程》(第三版中文本)⑥胡壮麟:《语言学教程》(第三版中文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钱玉莲《现代汉语词汇讲义》⑦钱玉莲:《现代汉语词汇讲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论文6篇,其中,周绍珩《利奇的两本语义学著作简介》⑧周绍珩:《利奇的两本语义学著作简介》,《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1期。,仅有效涉及Connotative Meaning的汉译,可作参考,下文的相关统计不列入。其余5篇为:沐莘《推荐一部富有创见的语义学书——浅评杰·利奇的〈语义学〉》*沐莘:《推荐一部富有创见的语义学书——浅评杰·利奇的<语义学>》,《外国语》1988年第1期。,吴颖、张德让《语义类型与“门”的英译》*吴颖、张德让:《语义类型型“门”的英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彭石玉、陈明芳《利奇的意义类型与英汉品牌命名理据》*彭石玉、陈明芳:《利奇的意义类型与英汉品牌命名理据》,《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宋杨《从利奇的意义分类看英语词汇教学》*宋杨:《从利奇的意义分类看英语词汇教学》,《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王东风《语义类型及其翻译》*王东风:《语义类型及期翻译》,《中国翻译》1989年第5期。。以上所列论著一般都把Semantics列为参考文献。
综观上述关于利奇“语义类型”的各种汉译,结果较为一致的是Collocative Meaning,均译为“搭配意义”;其次是Affective Meaning,一般译为“情感意义”或“感情意义”。即“Collocative Meaning”“Affective Meaning”这两个术语的汉译分歧不大,可以采信,二者可译为“搭配意义”和“情感意义”。另五个术语的汉译则均有较大分歧,在我们看来,Semantics所列出的七种语义类型形成一个术语“群落”,在语义上相互对待、相互完足,互为生成和存在的前提,其汉译应充分考虑其作为一个特定“群”的态质。综论辨析如下。
一、Conceptual Meaning:理性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目前学界主要有2种译法:“理性意义”和“概念意义”。据可列入统计的10种文献,译为“理性意义”的共2例,分别是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等译《语义学》和沐莘《推荐一部富有创见的语义学书——浅评杰·利奇的〈语义学〉》。译为“概念意义”的共8例。
我们认为,相对于“概念意义”,将“Conceptual Meaning”译为“理性意义”更为合适,更为接近原作者的原意。理由如下:其一,汉语语境中,“概念”与语词(尤指“词”)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利奇《语义学》所探索的“语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词义,它还包括句义等。利奇在其《语义学》第1章“小结”中指出“在这一章里我提出了研究意义的三个要点”*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等译:《语义学》,第11页。,其中的第二个要点即明确指出:“在辨认句子之间的意义关系以及哪些句子有意义、哪些句子无意义时,知道涉及哪些因素。”*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等译:《语义学》,第12页。利奇的原文为:“to know what is involved in recognizing relations of meaning between sentences, and in recognizing which sentences are meaningful and which are not.”*Geoffrey Leech ,Semantics, Harmondsworth:Penguin,1981.“概念意义”的译法可能会将“语义”误解为“词义”。例如:彭石玉、陈明芳《利奇的意义类型与英汉品牌命名理据》《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参考书目的第1条即是利奇《语义学》英文原著,该文开篇指出,“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利奇(Geoffrey Leech)在他的Semantics这部著作中提出,‘词义’(意义)可以分为七种类型,即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以上后五种又统称联想意义)和主题意义。”*彭石玉、陈明芳:《利奇的意义类型与英汉品牌命名理据》,《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其二,利奇在给出“Conceptual Meaning”这一术语时常常将另一个术语“逻辑意义”(logical meaning)与之并列,二者的联接词是“or”(“或者”),这说明Conceptual Meaning与logical meaning是应该等量齐观的,而译为“概念意义”,则与“逻辑语义”是逻辑上的“包含于”关系,而不是全同等值关系。一般而言,“理性意义”与“逻辑意义”则更为接近(“逻辑”在西方导源于“逻各斯”,后者意为“理性”等)。
二、Connotative Meaning:内涵意义
我们所考察的文献中关于Connotative Meaning的汉译主要有4种,即:内涵意义,联想义,含蓄意义,附加意义。其中将“Connotative Meaning”译为“内涵意义”的共8例。例如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等译《语义学》等。
将“Connotative Meaning”译为“联想义”的共1例。束定芳《现代语义学》指出:Leech把常见的“语义”分成7种类型:概念义、联想义、社会义、感情义、反映义、搭配义和主题义。其关于语义类型的七个术语,与李瑞华等的翻译大体相同,只是关于“Connotative Meaning”的翻译不同。束定芳在《现代语义学》中像是参考了利奇《语义学》的1974和1981两个版本。在关于联想义的解释中,用的是1981年版本:“显然,与概念意义相比,联想义不太稳定,是一种附加的意义,具有开放性和模糊性的特点。(Leech,1981:13)”显然,束定芳是将“Connotative Meaning”译为联想义。其译法盛若菁《比喻语义研究》等征引沿用介绍。*盛若菁:《比喻语义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需要注意的是,在利奇《语义学》中,利奇将Connotative Meaning、Social Meaning、Reflected Meaning、Collocative Meaning、Affective Meaning统一概括为Associative Meaning。而 Associative Meaning这一术语,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等译《语义学》及陈慰《英汉语言学词汇》均译为“联想意义”。如此看来,将“Connotative Meaning”译为“联想义”容易与“Associative Meaning”混淆。
译为“含蓄意义”的共1例。见王东风《语义类型及其翻译》:“英国著名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在他的《语义学》(Semantics)中,把语言的意义分为七种主要类型:即概念意义、含蓄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它为我们正确而全面地认识语言的各种意义、在翻译中端正对‘原意’的认识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该文虽然文题中的“翻译”不是指对“语义类型”自身的翻译,但是在讨论具体材料的翻译时,以利奇的七种语义类型为纲,亦涉及对七种语义类型自身的翻译,将其中的“Connotative Meaning”译为“含蓄意义”。与之较为接近,陈慰《英汉语言学词汇》所译出的3个义项中有一个为“隐含意义”。*陈慰:《英汉语言学词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译为“附加意义”的为周绍珩《利奇的两本语义学著作简介》:“利奇为使语义学成为一门语言的科学,首先给它划出了一个核心部分,这就是把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作为语义学首先要描述的主要对象。”*周绍珩:《利奇的两本语义学著作简介》,《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1期。该文还紧接着指出:“利奇认为这类特征不过是语言的附加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它是随着社会条件和人们的认识变化而改变的,因此是不稳定的,应看作语义的边缘部分。”*周绍珩:《利奇的两本语义学著作简介》,《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1期。
以上“含蓄意义”“隐含意义”“附加意义”似没有“内涵意义”明确,且“含蓄意义”“隐含意义”“附加意义”更容易与“Social Meaning”“Affective Meaning”等其他意义类型在逻辑上形成交叉关系。
三、Social Meaning:社会意义
在我们所考察的文献中,关于“Social Meaning”的代表性的意见是2种,即译为:社会意义,风格意义。其中译为“社会意义”的共7例。例如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等译《语义学》即是。
译为“风格意义”的共3例。例如:吴颖、张德让《语义类型与“门”的英译》指出:“然而最早对语义做出全面概括的是英国语言学家利奇,他把语义分为七种类型:概念意义(理性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社会意义)、感情意义(情感意义)、联想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等。”*吴颖、张德让:《语义类型与“门”的英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有一个注释:“关于七种语义类型的说法不一:括号中为李瑞华、杨自俭等译的《语义学》中的说法。两种说法的实质内涵是一样的,可一一对应,前一种已被普遍接受。为方便解释,本文第二部分采用后者,其余部分皆使用通用说法。”*吴颖、张德让:《语义类型与“门”的英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该文的“参考文献”列举了利奇《语义学》的英文原著,也列了李瑞华等译的《语义学》。
我们以为,利奇所谓“Social Meaning”确实包含有“语体意义”或“风格意义”,但从忠实于原文的角度看,译为“社会意义”更“信”,且“风格”与“语体”等是在社会语境中生成的,二者有先后“派生”关系,取前者似更可靠。
四、Reflected Meaning:反应意义
我们所考察的文献中关于“Reflected Meaning”的代表性的汉译主要有3种,即:反映意义,反射意义,联想语义。其中,译为“反映意义”的共6例。例如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等译《语义学》:反映意义和搭配意义。同为语义类型的术语,贾彦德《汉语语义学》中的“反映义”与利奇《语义学》“反映意义”在意义上区别较大,二者容易混淆。
译为“联想意义”的共3例。例如伍谦光《语义学导论》(修订本):“利奇认为,这是一种能引起听者(或读者)联想的意义,也就是说,有些词具有这样的特点:当你听到或读到它们时,会马上联想起别的事情来。”*伍谦光:《语义学导论》(修订本》,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42页。
就利奇的原意而言,“Reflected Meaning”主要是指“在存在多重理性意义的情况下,当一个词的一种意义构成我们对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的反应的一个部分时”*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等译《语义学》,第22页。,Reflected Meaning与Collocative Meaning “它们包含着语言词汇层次上的一种相互联系”。其原作者英文原文分别是:“Two further, though less important types of meaning involve an interconnection on the lexical level of language.”“First,REFLECTED MEANINGsi the meaning which arises in cases of multiple conceptual meaning, when one sense of a word forms part of our response to another sense.”*Geoffrey Leech Semantics Harmondsworth:Penguin, 1981.
显然,词汇层次上的相互联系,一般不宜脱离语言意义过远。
结合上述英文原文以及作者在同一个纲目并列给出且放在一起讨论的有共性的在汉译上无甚争议的“搭配意义”,可以看出,将“Reflected Meaning”译为“联想意义”有些宽泛。
此外,将“Reflected Meaning”译为“联想意义”还容易在事实上与前文所讨论的“Connotative Meaning”的汉译“撞车”。
译为“反射意义”的共1例。见胡壮麟《语言学教程》(第三版中文本):“利奇(G. Leech)在1974年第一次出版的《语义学》(Leech,1974:23)中则提出了如下七种意义类型: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感情意义、反射意义、搭配意义、主位意义。”*胡壮麟:《语言学教程》(第三版中文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我们以为,为避免与贾彦德《语义学》“反映义”混淆,*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7-108页。“Reflected Meaning”可译为“反应意义”。
五、Thematic Meaning:主位意义
我们所考察的文献中关于“Thematic Meaning”的代表性的汉译主要是2种,即:主题意义,主位意义。其中译为“主题意义”的共9例。
译为“主位意义”的共1例。见胡壮麟《语言学教程》(第三版中文本)。另外,陈慰《英汉语言学词汇》同时收了“主题意义”和“主位意义”。
我们以为,考察利奇《语义学》的原意,将“Thematic Meaning”译为“主位意义”似更合适。其理由是:一方面,利奇所提出的“Thematic Meaning”“主要涉及在不同的语法结构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等译:《语义学》,第37页。,在一定意义上强调的是句法语义,“主位”中的“位”更能直观地体现出“位置”“结构”这些要素。且另一个方面,“主题”更为经常的是属于语用学的一个概念,往往与“话题”等术语直接相涉,在语义学框架下取“主位”意义上更简明。
结 语
以上关于利奇《语义学》所提出的七种语义类型,在综合考量已有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充分考虑其“术语群落”特征的前提下,我们倾向于译为:理性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反应意义(Reflected 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主位意义(Thematic Meaning)。不难看出,利奇《语义学》语义类型是广义的语义分类结果,其分类着眼于语符自身的指称意义、语符之间的系统意义、语符的文本话语语境意义、语符的社会语境意义等。
利奇关于语义类型术语的汉译之所以有些分歧,可能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翻译时对利奇意义类型表述的上下文语境观照得还不太充分,比如可充分关注到“Social and Affective Meaning”“Reflected and Collocative Meaning”等几种术语是成对列出的。第二,所翻译的对象术语是对“语义类型”的考察,而语义本身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和主体性,因而这些术语自身语义有其不太确定性。第三,利奇《语义学》分出的语义类型较为细致,表征语义类型的术语之间的逻辑关联需进一步探究。第四,就译法而言,牵涉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
(责任编辑:袁宇)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emantic Type” Term Groups in Leech’sSemantics——A Concurrent Analysis of the Logic of Leech’s Semantic Classification
ZHANG Chun-qua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In Geoffrey Leech’sSemantics, as regards the term group of the semantic type, there have been some disparitie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ose terms in academia. On the basis of som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existing translations and research result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ends to translate the seven terms respectively as理性意义(conceptual meaning), 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 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 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 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 反应意义(reflected meaning), and 主位意义(thematic meaning) by combining the logic of Leech’s semantic classifications. Moreover, as analyzed, the causes for divergence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emantic type term group involve textual and extra-textual factors.
Semantics;meaning types; term translatio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文科技术语的认知语义研究”(项目编号:13YJC740132)
2016-05-01
张春泉(1974-),男,湖北安陆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语用学、语义学研究。
H315.9
A
1674-5310(2016)-09-01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