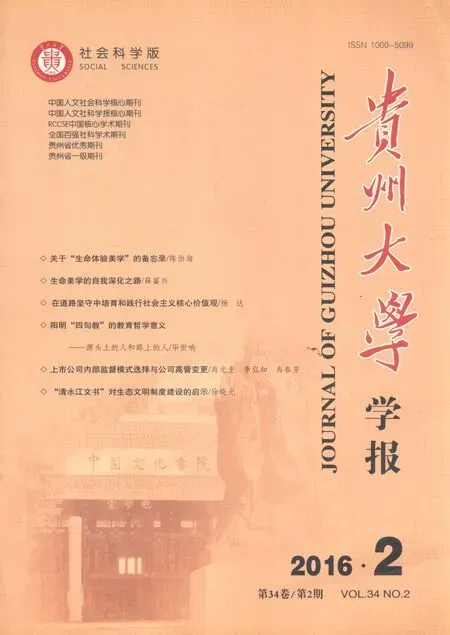生命建基·信仰补缺·境界超越
——潘知常生命美学思想述要
刘 剑
(贵州大学 艺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3)
生命建基·信仰补缺·境界超越
——潘知常生命美学思想述要
刘剑
(贵州大学 艺术学院,贵州贵阳550003)
摘要:潘知常教授的生命美学起始于1984年,30年的学术历程里,他始终在探讨生命如何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以生命活动中的审美活动为逻辑起点,以个体的觉醒和信仰的觉醒为两翼,他已在理论—历史—现状三个层面建构起自己生命美学的理论体系。重估生命美学,是后实践美学时代各美学学派沉寂后应当开展的一项工作。
关键词:生命;信仰;超越;境界
在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的各种论争当中,以潘知常为首倡者的生命美学是其中耀眼的美学学派,在生命美学30年的发展历程中,重新梳理并评估生命美学的学术贡献,这是一件有必要也有意义的事。
一、以生命为美学建基
据潘知常先生多次在不同场合接受问答时说,其生命美学的天启之年是1984年12月12日28岁生日那年,这算是个体生命中重要的美学事件。①*①“在1984年的12月12日,是我28岁的生日。也就在那天晚上,在中原寒冷的冬夜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那个夜晚,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审美活动与个体生命的逻辑对应。美学之为美学,应该是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类个体生命之间的对应的阐释,这就是我所提出的生命美学所要面对的美学问题。后来正是在这一内在生命感悟的基础上,我写就了第一篇美学札记:《美学何处去》,开始关注生命的自由表现,关注生命的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这就是后来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的所谓生命美学。”参见潘知常、邓天颖:《叩问美学新千年的现代思路——潘知常教授访谈》,学术月刊, 2005年第3期。尽管后来学界把生命美学学派的诞生纪年界定在潘先生《生命美学》一书出版的1991年,但真正的潜伏破土却在他生命中的1984年。他在最近的相关论述里也说自己是“生命美学三十年”(1984—2014年)。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个对于宏大历史中微不足道但对个体生命历程如此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于该事件奠定了其生命美学的基调和理路:以个体生命的存在阐释审美活动,探讨生命如何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
“个体的觉醒”是这次事件的核心要义,被潘先生认为既是他本人生命美学研究的开始,也应是中国美学研究走向正轨的关键所在。美学研究长期只关心空洞的人,即使关注到个体性的“自我”,关注的都是“自我是什么”,很少关注“自我怎么样”。“自我是什么”关注的是现象背后的本质性问题,是认识论命题;“自我怎么样”关注的是现象本身的存在性问题,是价值论命题。抛弃生命的真实体验而从美学理论推演美学理论,这是很多美学研究者所走的老路。这类美学研究将“美学”研究成冰冷的知识谱系,忽略了美学研究的意义维度和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学科品性。个体之所以是个体,不是他的本质规定了他的存在,而是存在就是本质。把个体规定为“理性的动物”“符号的动物”等都没有触及到真实的个体,本质不是先在的,存在才是优先的。此在都是因为其不可重复性、独一无二性而具有存在于世的价值。过去的个体是躲避在上帝、理性、普遍、一般、本质的呵护下,但当这些庇护者都缺席的现代社会,在个体被抛的状态下,个体就只能自己面对自己的痛苦、绝望、颓废、孤独、焦虑、荒诞、恐惧,只能自己安顿自己,自己作出自己的选择。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总是表现为自己照料自己的绝对个别的存在物。
说到生命,那生命的真相是什么?封孝伦先生认为,生命的真相就是人具有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这三重生命,并指出:三重生命在根本上都是不自由的。[1]潘先生认为,生命的根本真相就是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就其要义,他们都指出生命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是被规定的存在,特别是时间性的大限划定了生命不可逾越的时限。杜威用“动物祖先”这一说法强调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承续性关系,但是人类最终还是与动物分道扬镳,从蒙昧中醒来。当人类觉醒后,却发现了自己的孤独:一是在人与自然维度上,人类与自然无法完全融洽起来的“人类的孤独”。早期所有民族的神话和史诗里面,自然给人类留下的很少有诗意优美的面孔(优美范畴出现在比较晚的农耕时代),大多都是魔鬼般恫吓人心的恐惧,甚至是荒诞无稽、灾难恐怖的记忆。那是早期人类创伤心理的神话表达,在这些神话中,人类是那样的孱弱渺小,无法再与自然握手言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陌生疏离的我—它关系。诗人海子将火与水交媾的陶器时代认为是人类的首次离别:“我们的嘴唇第一次拥有/蓝色的水/盛满陶罐/还有几十只南方的星辰/火种/最初忧伤的离别”(海子《历史》)。当人与人之间形成人与社会的维度后,并没有因为群体抱团而感到温暖,一种“个体的孤独”更加难以承受,人与人在社会维度形成的是一种我—他关系。正如日本学者山崎正和说:“我突然发现了人的社交尽管有着如此华丽的外表,但其本质是孤独存在的行为”[2]。人与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是先哲们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孔子以“仁”为核心,试图破解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是以血亲之爱推及他人之爱这种方式来解决的。面对“人类的孤独”和“个体的孤独”这双重的孤独,审美活动得以出场。审美以我—你这种亲和的对话关系超越人与自然之间的我—它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我-他关系,给心灵寻找安顿皈依之所。潘先生将美学“基因化”处理,认为审美是人猿揖别时对自身的呵护与鼓励,审美就是人猿揖别后高举的灯塔,为人类生命的茫茫未来导航。人类选择身体直立的同时,就将精神也直立起来,寻求人类生命自身的超越性。
将潘先生“个体的觉醒”事件放回整个1980年代的后景中俯瞰,我们会发现,如此个体性的事件其实是整个时代的个体表达。作为1950年代出生的学者,他们亲历了太多的集体性对个体性的遮蔽乃至伤害。到了1980年代,在上一个时代留下的伤痕与反思中,他们所领会到的是个体生命的苏醒,生命觉醒所唤起的是对于国家政治层面那种宏大叙事的质疑,而在美学领域的体现就是质疑那种意识形态翻录式的美学,那种高高在上的冷美学对于个体生命的当下存在来说,始终抵不过个体生命瞬间最真实的体验:“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这一真实的诉求也成为1980年代生命美学的时代表达。潘知常先生在1984年启悟并在1985年《美学何处去?》一文中提出:“真正的美学应该是正大光明的美学、生命的美学。……应该向人的生命活动还原,向感性还原,从而赋予美学以人类学意义。”[3] 400生命美学的崛起正是得益于个体生命意识的时代觉醒。个体的觉醒看似是个体性的事件,其实是时代性的事件,以个体性生命为根基的美学也必将成为时代性的美学。后实践美学时代,生命美学之所以如此靓丽夺目,就在于它比体验美学、生存美学、生活美学等更有时代性和超时代性品格。
许多美学研究对逻辑起点的设置都没有放在第一逻辑起点上,致使研究体系不彻底。生命美学将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前移至比“实践”更早的“生命”上,大胆强调生命的生物性,肯定感性的合法地位,这是以理性为内核的实践美学不屑于也不能承认的地方。康德说:“美只适用于人类,即适用于动物性的但却有理性的存在物,但这存在物又不单是作为有理性的,而是同时又作为动物性的存在物”。[4]康德在这里强调了美的疆域是人类(这一点驳斥了那种认为动物也能审美的观点),因而强调人的动物性不等于就把人贬低到动物,而是强调了人与动物祖先的承续性关系,这一观点可以给予生命美学最大的学术勇气。“现实性取代更为重要的超越性,从而造成了实用压倒审美、理性压倒感性、现实性挤压超越性的不正常状况。生命美学正是看到了实践美学的这一缺憾,转而坚定地将实践本体论转向生命本体论,让美学真正从人自身的生命去吸饮生命的泉水。”[5]将“生命”作为自身美学的逻辑起点,这将使生命美学的根基更加稳固,也将使生命美学在实践美学之后走得更远。
二、以信仰为生命补缺
潘先生的第二个个体性美学事件发生在2001年的春天,他在美国纽约的圣巴特里克大教堂终于找到了“通向生命之门”。*“2001年的春天我在美国纽约的圣巴特里克大教堂终于又找到了进一步的美学问题。那一天,我在圣巴特里克大教堂深思了很长时间,终于第一次清晰地理清了十五年来的纷纭思绪:个体的诞生必然以信仰与爱作为必要对应,因此,必须为美学补上信仰的维度、爱的维度。在我看来,这就是美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学之为美学,不但应该是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类个体生命之间的对应的阐释,而且还应该是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与人类的信仰维度、爱的维度的对应的阐释。”参见潘知常、邓天颖:《叩问美学新千年的现代思路——潘知常教授访谈》,《学术月刊》, 2005年,第3期。他认为,个体的诞生必然以信仰与爱作为必要的对应,因此,生命美学不应只停留于个体性以阐释审美的主观性,还应是为美学补上信仰和爱的维度以阐释审美的普遍必然性。
生命的有限性注定生命是一场悲剧性的结局,叔本华和尼采对此问题已经作了精彩的分析。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不会就此坐以待毙,他发现了神性的存在,投奔信仰以获得生命的救赎。尼采认为,希腊人洞察到生存的恐怖后,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创造了奥林匹斯山神谱,在神灵的庇护下,希腊人感觉到人生是值得一过的,悲剧艺术由此诞生。“对于生命来源的好奇,对于死后世界的敬畏,美感的追求和符号的思维”是人类早期普遍的思想特征,当人类通过举行仪式与天地通灵后,“就可能被当做是很实用的生活策略而被普遍适用,而背后隐含的一套观念就被当做是天经地义的东西而不必加以追问,人们在这些仪式中获得生活的安定,也从这套制度中获得秩序的感觉。”[6]海子在诗中描述了人类冒险并找到家园的过程:“公元前我们太小/公元后我们太老/没有人见到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但我还是举手敲门/带来的象形文字/撒落一地。”(海子《历史》)正是向着神的怀抱投奔,生命才找到安顿和庇护的家园,超越自己的孤独:“到家了/我缓缓摘下帽子/靠着爱我的人/合上眼睛/一座古老的铜像坐在墙壁中间/青铜浸透了泪水。”(海子《历史》)
信仰谓何?按潘先生的说法,信仰简单说来就是愿意相信。信仰属于无限性领域,因为无限性是无法证实却又存在的,证实不了也不需要证实,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且愿意相信。信仰的出现是因为“未知”的存在。康德已经提出,理智的认识不能抵达本体的信仰领域。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说:“对于能够说清楚的,我们必须说清楚,对于不能说清楚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雨果说:“我们从来只见事物的一面,另一面是沉浸在可怕的神秘的黑夜里。”未知世界是人的世界之外一个更高存在的维度,它要求我们无条件地去信奉它。未知世界的存在导致宗教的出现,宗教的核心就是信仰,罗丹说:“宗教是对世界上一切未曾解释的,而且毫无疑问不能解释的事物的感情,是维护宇宙法则,保存万物的不可知的力量的崇拜;是对自然中我们的官能不能感觉到的,我们的肉眼甚至灵眼无法得见的广泛事物的诱惑;又是我们的心灵的飞跃,向着无限、永恒,向着知识与无尽的爱——虽然这也许是空幻的诺言,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些空幻的诺言使我们的思想跃跃欲动,好像长着翅膀一样”。[7]也就是说,生命本无意义,是虚无的存在,但我们必须赋予它以意义,生命才值得一过。“因为只有在信仰之中,人类才会不仅坚信存在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而且坚信可以将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和终极关怀诉诸实现。”[8]155
信仰与审美的关系体现为审美就是爱的见证。潘先生认为,爱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有限性之后拥有的能力,是人自知自己的有限性后生出的一种绝对责任。惊异于生命的短暂、有限、悲惨,爱才由此而生。爱着眼于一个绝对高于自身的存在,在绝处寻生。因此,“审美活动是人类追求无限性的见证,审美活动也是人类之爱的见证”,[8]185只有在信仰之中,人类才能超越人与自然的我—它关系和人与社会的我—他关系,从而形成一种间性的我—你关系。正如潘先生所言:“审美活动中,美是无限性得以见证的对象。就是说,审美活动所创造的审美对象因为使得人们可以在它身上看到人类对于无限的追求,因而见证了无限性,因此成为美;至于美感,则可以被视为无限性的见证快乐。也就是说,是一种见证到无限时的心理快乐。见证了无限,是美,见证了无限的心理快乐,就是美感。”[8]289没有信仰维度,审美活动的超越性就无法实现。
信仰与美学的一条暗道就在于愿意相信。愿意相信,这是人在进行审美活动时必须达成的一项审美契约,原因在于审美活动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和意义关系,不是反映和认识关系。俗话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只有接受者愿意相信“雪里芭蕉”要表达的是生命的禅意而不是雪的季节性知识与芭蕉的生物学知识,他才能走进审美活动的门槛,否则,审美活动就难以发生。波德莱尔说:“诗歌的最为现实之处,在于它只有在另一个世界才完全真实。”[9]只有愿意相信,我们才能理解艺术真实。
信仰问题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先“照着讲”再“接着讲”而来的。潘先生以“忧世”与“忧生”先讲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两个谱系:“忧世”谱系是一个以现实关怀为己任的传统,是“以文学为生活”的美学传统,从先秦《诗经》到明清《水浒传》皆属于此;“忧生”谱系是一个以终极关怀为己任的传统,是以“为文学为生活”的美学传统,从神话《山海经》到明清《红楼梦》皆属于此。不管是哪一个美学谱系,整个中国美学传统都存在根本的缺憾:“其中有自然生命但是没有神圣生命;有自由但是没有人;有解脱但是没有救赎。它关注的尽管确实是生命,但是却只是生命的盈足而并非生命的负疚,只是通过取消向生命索取意义的方式来解决生命的困惑。”[3]233中国向来缺乏直面生命真相和意义的勇气。但是,审美并非来自现实关怀,不是“忧世”的结果,而是来自终极关怀,是“忧生”的结果。
在“忧生”的生命美学谱系中,应从曹雪芹、王国维和鲁迅那里接着讲历史所缺的信仰问题。从个体生命出发阐释审美活动,王国维为人性补上“欲望”,鲁迅为人性补上“反抗”,但个体的诞生不是美学的全部,他们对于美学事业的未竟之处恰恰就在于未能找到人与世界之外一个更高存在的信仰维度。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也未能同时高举“信仰”的大旗,错过一次历史的选择机会。科学指向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指向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但这两个维度都触及不到人的灵魂维度。百年过去,科学与民主依然没有在中国扎根,其根本原因,在于信仰维度的缺失,因为信仰才是科学和民主的根基。这样,我们发现,“为美学补神性”成为潘先生多年来奔走疾呼的大旗。但是,奇怪的是,对此问题,学界一直缺乏响应。对于这一点,潘先生本人也感到非常震惊!平心而论,信仰问题是必须要补的,但如何补,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如果说第一次美学事件的意义在于“个体的觉醒”,那么,第二次美学事件的意义就在于“信仰的觉醒”。同样地,将“信仰的觉醒”放回潘先生个体生命中发生的2001年前后,甚至放到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来看,信仰问题的提出都非常有现实和历史的针对性。从过往的历史来说,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是“信而不仰”,民众可以信某一个神,但他不敬仰它,这样的信仰是没有神性的。中国宗教是一种世俗而实用性的宗教,只关注此岸和现世,其骨子里缺乏一种超越性品格。从当下的现实来说,本来就缺失的信仰所造成的真空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由领袖人物填补的,但市场经济几乎让国人的领袖性信仰发生空前的滑铁卢,滑向金钱拜物教。这一问题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的当下,越演越烈,上至官员的贪腐让人触目惊心,下至百姓的暴富心理空前膨胀。因此,“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是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信教,但是不能拒绝信仰;我们可以拒绝神,但是不能拒绝神性”。[8]165作为生命美学,作为具有生命美学精神的艺术创造,若无信仰维度以使人超越,这样的生命美学和艺术创作依然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可以说,金钱拜物教时代写诗是野蛮的。
美学应当接着康德讲,接着讲康德的“主观的普遍必然性”,首先要讲清楚的就是审美的“主观性”,其次才能讲清楚审美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如果说,潘知常先生以第一次个体生命的美学事件将生命放置到美学研究的本体性位置以解决康德说的审美的“主观的”问题的话,那么,他的第二次个体生命的美学事件寻求破解的就是康德所说审美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正如他说,“个体的觉醒”是“主观的普遍必然性”中的“主观”的“觉醒”,而“信仰的觉醒”却是“主观的普遍必然性”中的“普遍必然性”的“觉醒”。审美的主观性来自于审美活动中个体生命与对象之间建立的一种价值性关系,他关注的是对象之于自己的意义,而不是客观的认识论关系。在意识形态给美学松绑的今天,我们可以大胆承认审美的主观性,审美不是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获得关于对象的精神愉悦。精神愉悦不是因为“反映—认识”的框架而获得,而是以“价值—意义”的关系而获得的情感。审美的普遍性对于康德来说,来自于无法证实的普遍共通性;对于潘先生来说,审美的普遍性并不是来自于实体对象的自然属性,而是来自于审美活动中生命与对象建立的价值性关系。信仰维度涉及的就是价值取向,这种关系是人类普遍的一种关系。换句话说,审美活动是人类最根本最共同的一种生命需求,生命普遍的需求导致审美的共同性,即“主观的合目的性”注定了“主观的普遍必然性”。可以说,潘先生的生命美学是用存在主义美学精神接着讲康德的美学问题,而跟西方现代生命美学相异,跟中国生命美学传统精神相通。
三、以境界为生命启明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仅要知道生命有限性的真相,更要解决生命的关怀问题。“哲学面向必然现实,解释现实的存在根据和它的局限性,这种一种超越性的否定;美学面向自由、理想,解释存在的本来意义。美的这种非现实性,是一种超越性的肯定。”[10]131生命哲学是对生命真相的揭幕与去魅,而生命美学则是对于超越生命有限性的诉求。美学的迷人之处,不在于我们知道了叔本华、尼采所说的生命是一场悲剧的结局这样的真相,而在于我们要超越真相,通过有限眺望无限,寻找安顿生命的居所。正如萨特认为的那样,人生本是毫无意义的虚无存在,但怎样摆脱虚无却是有意义的。
生命是生成的,未定的,不是先天的,不是先天的本质规定了他的存在,而是他的存在是一种面向将来筹划的生成过程。杨春时先生主张将现代美学的根基建立在意义论哲学基础上,“意义论哲学不探讨存在是什么,也不探讨能否认识存在,而是探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10]123生命是每个人的筹划和意义赋予活动,“此在必须生成为它尚未是的东西本身,这就是说,它必须是这种东西本身”。[11]潘先生认为,审美活动就是进入审美关系之际的人类生命活动,就是一种以审美愉悦(“主观的普遍必然性”)为特征的特殊价值活动和意义活动。因此,美学应当是研究进入审美关系的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研究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生命美学就是一种价值论和意义论美学,探讨的仍然是它的基点:生命如何存在与生命超越如何可能。
依此逻辑,那生命美学的真相是什么?就是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审美所审的就是超越现实生命的那个部分精神生命。生命就是一个成为你自己的过程,它是面向不断超越当下走向各种可能性的生成过程,它是通过对将来的筹划来超越当下。康德由此曾说,“美是对无限的眺望”,黑格尔说,审美具有一种令人解放的性质。“人只有生活在无限的资源里才能够永恒,人只有生活在对生命意义的创造里才能够战胜时间。”[8]220取消美学对有限生命的关怀,美学的学科价值和人文底线何在?依此理路,我们发现,潘先生生命美学的精魂就在于超越性:“超越必然的自由即自由的主观性,超越性问题存,则生命美学存;超越必然的自由即自由的主观性,超越性问题亡,则生命美学亡。”“对于超越必然的自由的追求,堪称生命美学的灵魂。”[8]192终极性和无限性的向往使得人类的审美活动一直走在至善至美的路上。杨春时的超越美学就是从生存本体论的角度把“超越”规定为审美的本质和生存的本质,认为审美才是生存的最高形式,是超越现实和理性的解释方式。有论者甚至认为,整个后实践美学的要义就在于“审美超越”,“这是后实践美学超越实践美学的地方,是中国美学走向现代性的重要一步”,[12]199“也是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学研究中被各种迷雾所遮蔽的理论盲点,更是包括生命美学在内的后实践美学给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建设所做出的最大贡献”。[12]216后实践美学以生存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为灯塔,使审美活动具有超越现实关怀的超验品格,这可以说是美学摆脱意识形态胁迫后的合理归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生命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对话后的重要成果。
审美活动的超越性在结果上就体现为“境界”,潘先生直接就说:“美是自由的境界”。[8]357“境界”是中国美学精华性的范畴,它概括了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只有“境界”才能表达出生命的超越性。在张世英先生关于人生在世的四重“境界”论体系中,第一层是最低的原始的主客不分的“欲求的境界”,第二层是主客二分的“求实的境界”,第三层也是主客二分的“道德的境界”,第四层境界就是“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审美境界统摄并超越了“欲求”“求实”和“道德”三种境界,在审美境界中,人不再受“生理欲求”“求实精神”和“道德义务”的强迫,人与世界完全融合为一,从前三者的“应然而然”的境界进入到“自然而然”的境界,这是一种自由的澄明之境。审美境界的超越性特征使得审美活动之为审美活动的存在根据“就在于它能够‘活出境界’,能够让人在那个‘长得超出了自己’的精神上站立了起来的世界中诗意地栖居”。[8]350“诗意”就是万事万物聚集之中那一点“神性”所发出的光亮,只有诗人才能通过意象性的技艺把那点“诗意”召唤出来,“通过愉悦的澄明,他照亮人的精神以使他们的本性得以对那些在其田野、城市、住宅中的本真者敞开”。[13]
最能满足于生命超越性诉求的是艺术。如果我们仔细窥探会发现,大部分美学家至今对“美”所下的定义其实质上是关于“艺术”的定义。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看出,艺术学学科注定与美学学科之间有扯不断的学术纠葛。尽管这样,艺术之所以是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实在是因为艺术就是澄明之境的显现。艺术是审美活动的超越性品格的物质确认,其携带的超越性功能是与生俱来的。一切艺术活动从源初开始就是一种“让……居”的活动,就是让人的生命得以安顿栖居的活动,它给动荡不居的人们构筑了一个安稳的形式居所。在源初的艺术生成境域中,巫师所操持的仪式过程就是艺术过程,这些艺术并非是对于某个生活的反映,恰恰相反,他们相信那些符号本身就具有魔法,就是对象本身,是仪式和艺术同时给了他们混乱的心灵以安顿,使他们能战胜现实生命的各种际遇。虽然模仿再现艺术观主导西方艺术几千年,但实际上艺术根本就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这种认识论理路是有问题的。艺术从来都不是对生活的反映,相反,则应该说,是生活模仿艺术,否则,我们已经有生活了,还再去反映一遍生活干什么?岂不多此一举?多年来,僵化的反映论文艺观忽略了艺术之所以是艺术的真谛,把艺术打造成为现实服务的工具和操手。那种将作品还原为作家的社会生活的思路是值得商榷并深深反思的。艺术不是返还现实的再现之物,而是指向未来的超越之物。亚里斯多德曾说,诗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不是历史那样讲述已经发生的事,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因为它的可能性,它才以普遍性避免了历史的个别性;因为它的可能性,它才具有朝着无限挺近的超越性。
进入21世纪,在各种暴力事件、自然灾害、宗教冲突、政治博弈、资源争夺等矛盾交织的“风险社会”(吉登斯)中,生命如何创造意义而获得存在,这是美学继续要回答的问题,生命美学所秉持的超越性由此更加具有当下意义。
四、结语
潘先生曾以“一个中心”(审美活动)“两个基本点”(“个体的觉醒”和“信仰的觉醒”)来概括他30年(1984—2014)的美学历程,这也构成了其生命美学的基本构架。审美活动是其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个体的觉醒和信仰的觉醒是其逻辑前提,审美超越是其美学旨归。他的美学研究已经涵盖“理论—历史—现状”三个层面,从“理论”出发向“历史”和“现状”进行生命美学的逻辑展开。*在历史层面,潘先生陆续出版了12本著作(《美的冲突》《众妙之门》《中国美学精神》《生命的诗境》《中西比较美学论稿》《独上高楼——中西美学对话中的王国维》《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红——潘知常导读<红楼梦>》《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说<聊斋>》、《职场<红楼>》);在现状层面,潘先生陆续出版了四本书(《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美学的边缘--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这些著作都是其生命美学的逻辑展开。
可以说,生命美学是无法否定的,唯一可以否定的只是各自对生命本质与内涵的理解不同而已。将认识论美学转向价值论美学,这是生命美学对当代美学的贡献,也是中国美学研究应该接着讲的方向。关于实践美学的批判可以告一历史段落了,关于生命美学的历史评价已经开始。学界不应该在时髦性的“生态美学”和“生活美学”热潮中忘记更为原点性的生命美学。
参考文献:
[1]封孝伦.生命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15.
[2]〔日〕山崎正和.世界文明史:舞蹈与神话[M].方明生,方祖鸿,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91.
[3]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4-45.
[5]刘成纪.生命美学的超越之路[J].学术月刊,2000(11).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39.
[7]〔法〕罗丹.罗丹艺术论[M].沈宝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9.
[8]潘知常.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法〕皮埃尔·布吕奈尔,等.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M]. 郑克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1.
[10]杨春时.生存与超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280.
[12]章辉.实践美学:历史谱系与理论终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9.
(责任编辑钟昭会)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2.003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2-0013-07
作者简介:刘剑(1977—),男,贵州赫章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学与诗画美学。
收稿日期:2016-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