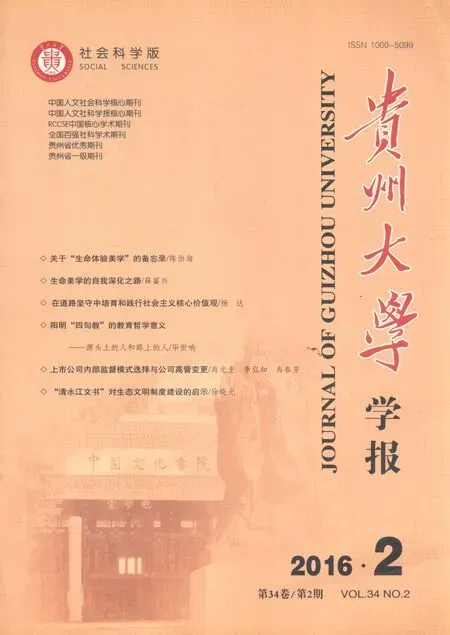“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用法初探
余 珩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用法初探
余珩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2)
摘要:详细梳理了“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的用法,包括真性询问和非真性询问中表示加强疑问语气、警示或反诘义,及在言域范围内引起受话人对某一个话题的思考和关注等功能,进而探讨了“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用法产生、发展的机制以及消亡的动因。
关键词:“毕竟”;疑问语气副词;主观性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毕竟”作为疑问语气副词最早的用例始于中唐时期的诗歌,但并不多见;晚唐时期用例逐渐增多,《祖堂集》中有14例;到宋代疑问语气副词用法成为该词的主要用法:佛教文献《五灯会元》中有85次用例,占“毕竟”语气副词用例的75%,世俗文献《朱子语类》中有26个用例,占“毕竟”语气副词用例的57%;明清时期疑问语气副词的用法逐渐消亡;现代汉语中,“毕竟”已经不能作为疑问语气副词使用,《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均没有“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的用法,《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明确指出“‘毕竟’不能用于问句”。“毕竟”疑问副词用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机制值得探讨。
“毕竟”一词最早以“完成”义同义连用形式出现,汉代语料中已见用例。随后逐渐虚化为语气副词,唐时基本完成虚化过程,可以表达多种语义信息:“最终”义;“到底、究竟”义(用于疑问句中,表示追究某事之最终结果);“必定”义;“坚持”义;“到底、究竟”义(用于陈述句中,表示辩解或者反驳)”。[2]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唐宋时期“毕竟”作为语气副词在疑问句中的用法,虽然孙菊芬[2]、张秀松[3]都提到了这种用法,但并没有对其产生及发展过程进行详细的论述。本文就“毕竟”在唐宋时期的疑问语气副词用法做深入细致的讨论,深究这一用法的来源、演变机制、消亡动因等相关问题。
一、“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用法使用情况
“毕竟”作为疑问语气副词的用法始见于中晚唐时期的诗歌当中,例子如下:
例1哀哀元鲁山,毕竟谁能度?(孟郊《吊元鲁山》)
例2朱门深锁春池满,岸落蔷薇水浸莎。毕竟林塘谁是主?主人来少客来多。(白居易《题王侍御池亭》)
例3风露澹清晨,帘间独起人。莺花啼又笑,毕竟是谁春?(李商隐《早起》)
例1出自中唐时期孟郊为吊唁诗人元德秀所作的诗,这是目前我们搜集到的“毕竟”作为疑问语气副词最早的用例。此例中,“毕竟”加强疑问语气,强调对“谁能度元鲁山(元德秀)”的疑问;例2是中唐时期白居易的诗作,前两句描绘了林塘的美丽景色,先是发出疑问:谁是林塘的主人?之后说明发问的缘由:主人来林塘的次数还没有客人多;例3是晚唐时期李商隐的诗作,前两句描写了春风晨露一片恬静的景象,后两句表现了诗人看到美景时内心因为落寞而发出的感叹:这么美好的春天,到底是谁的呢?
到晚唐五代时期,“毕竟”用为疑问语气副词多见于口语性较强的禅宗语录中。比如,《祖堂集》共使用25次,其中14次用作疑问语气副词,占全部用例的56%。这个比例说明,《祖堂集》中“毕竟”还的疑问语气副词用法相当活跃。“毕竟”还可以用在特指问句和正反问句中,下面分别就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其一,用于特指问句中。共13例,用以询问对方对某一个事件的看法、建议等11例。多用于句首,为真性询问。如:
例4师闻此语,似少惊觉,乃问曰:“弟子浮生扰扰,毕竟如何?”天皇云:“在家牢狱逼迮,出家逍遥宽广。” (卷五·龙潭)
例5问:“祖祖相传,复传何法?”师云:“释迦悭,迦叶富。”僧曰:“毕竟传持事如何?”师云:“同岁老人分夜灯。” (卷九·九峰)
例6报慈云:“什摩年中,向你与摩道?”僧云:“毕竟作摩生?”报慈便打一下。(卷十六·沩山)
例4中,龙潭和尚未出家时对生活状态产生了怀疑,于是询问天皇和尚的看法,以“毕竟”加强疑问语气;例5中,僧徒询问传法之事,九峰和尚的第一次回答并没有使其满意,于是他又重申了第一个问题,以“毕竟”加强疑问语气;例6中,僧徒对报慈和尚的回答并不满意,又重申了一遍问题,以“毕竟”加强询问语气。这3个例子都是传疑的真性询问。
询问方式1例,用于对实现某一个目标状态所必须的工具、途径或方法进行提问的问句中,位于句首,为真性询问:
例7师问诸硕德曰:“行止偃息,毕竟以何为道?”有人云:“知者是道。” (卷十五·鹅湖)
鹅湖和尚问他的得意弟子们,行住坐卧时该以什么方式体现佛家所谓的“道”,“毕竟”加强疑问语气,为真性询问。
询问事物1例,用于对称代提出疑问的问句中,位于句首,为真性询问:
例8过一日后便问:“如何是佛?”室拳手。“如何是道?”又展手。“毕竟阿那个即是?”石室便摆手云:“勿任摩事。”(卷五·石室)
沩山让仰山探访石室和尚,仰山追问石室和尚什么是佛、什么是道,用“毕竟”加强疑问语气。
其二,用于正反问句中,共2例,位于句首,加强疑问语气,都为真性询问:
例9禅客曰:“一切众生,毕竟还得闻无情说法不?”师曰:“众生若闻,即非众生。”(卷三·荷泽)
例10问:“法雨普润,枯木为什摩无花?”师云:“不见道‘高原陆地’?” 曰:“毕竟还有生花时也无?”师云:“若生花则不名枯木。” (卷九·九峰)
例9中,禅客问慧忠国师有没有听过“无情说法”,又继而追问众生有没有可能听闻“无情说法”,“毕竟”加强追问语气;例10中,僧徒问九峰和尚,枯木为什么不开花,下一问继续追问枯木有没有开花的时候,“毕竟”加强追问语气。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毕竟”作为疑问语气副词在晚唐时期《祖堂集》中的用法都为真性询问。
宋代“毕竟”的疑问副词用法达到鼎盛,并出现了非真性询问的用法。《五灯会元》中“毕竟”共出现114次,有85次作为疑问语气副词使用,占全部用例的75%。其中,用于真性询问77次,用于非真性询问8次。以下分别介绍这两种用法。
一是用于真性询问,延续了《祖堂集》中的用法,多位于句首,出现的语境多是追问意味的问句,主观性增强。例如:
例11问:“初心后学,如何是学?”师曰:“头戴天。”曰:“毕竟如何?”师曰:“脚踏地。”(卷第八)
例12僧问:“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师曰:“龙腾沧海,鱼跃深潭。”曰:“毕竟如何?”师曰:“夜闻祭鬼鼓,朝听上滩歌。”(卷第十一)
例13僧问:“不落阶级处请师道?”师曰:“蜡人向火。”曰:“毕竟如何?”师曰:“薄处先穿。” (卷第十八)
例11中,僧徒问隐微禅师发了初心后怎么样学习佛法,隐微禅师的第一次回答并没有让僧徒满意,于是又发出了第二次追问,“毕竟”强调追问语气;例12中,僧徒问纸衣和尚什么是佛法最真实的大意,纸衣和尚的第一次回答并没有让僧徒满意,于是僧徒发出了第二次追问,“毕竟”强调追问语气;例13中,僧徒问法达禅师什么是不落阶级的地方,法达禅师的第一次回答并没有让让僧徒满意,于是僧徒发出了第二次追问,“毕竟”强调追问语气。
以上3个例子都是就第一次问题的答案不满意,进而发出第二次追问。这种追问用法在72次真性询问中有31次用例,占真性询问用例的45%,是常用的形式。这一类用例中,“毕竟”都于追加疑问,意义上大致相当于“究竟”“到底”。既然是追加疑问,“毕竟”的疑问语气程度就相对于没有追问的“毕竟”问句要强一些。
二是用于非真性询问,多位于句首,带有警醒、反诘意味。例如:
例14上堂:“赵州有四门,门门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长安。门门通大道,毕竟谁亲到?路路透长安,分明进步看。”(卷第十二)
例15上堂:“……若是个惺惺底,终不向空里采华,波中捉月。谩劳心力,毕竟何为?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诸人行时,各自着精彩看。”(卷第十八)
例16上堂:“乾闼婆王曾奏乐,山河大地皆作舞……”蓦拈拄杖,横按膝上,作抚琴势云:“还有闻弦赏音者么。”良久云:“直饶便作凤凰鸣,毕竟有谁知指法。”(卷第二十)
例14是智海道平禅师的布道演讲,意为赵州四门通大道,玉泉四路通长安,虽然如此,又有谁亲自走过这些道路?此句意在警告众人,佛法需要亲身实践,“毕竟”问句带有警示或反诘意味;例15是百丈以栖禅师的布道演讲,指出若是保持“惺惺”状态,就不会“空里采华(花)”“波中捉月”,并诘问这样的行为劳心劳力,为什么要做呢?“毕竟”强调反诘,带有警示受话人的意味;例16是荐福悟本禅师在布道中的发言。乾闼婆王奏乐时大地山河都跟着一起舞蹈,继而发出诘问:即便是如凤凰一般的美妙声音,又有谁懂得欣赏呢?
以上3个例子都是禅师的布道内容,布道与师徒之间的问答不同,是对僧徒宣讲教义,重点在于传信而非传疑。事实上,此类“毕竟”强调的并不是疑问语气,而是警示或者反诘语气,这是“毕竟”疑问副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用法。
世俗文献中也有“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的用例,但并不如禅宗语录多,《朱子语类》中“毕竟”共出现228次,作疑问语气副词使用共26次,其中15次用为真性询问,11例用于无疑而问形式,下面就这两种用法进行分析:
一是用于特指、选择问。位于句首,加强疑问语气。例如:
例17问:“‘七十从心’一节,毕竟是如何?”曰:“圣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十五而志于学。……” (卷第二十三·论语五·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
例18问:“‘仁者先难而后获’……”曰:“仁毕竟是个甚形状?”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卷第三十二·论语十四·樊迟问知章)
例19问:“《论语》颜渊问仁与问为邦,毕竟先是问仁,先是问为邦?”曰:“看他自是有这‘克己复礼’底工夫后,方做得那四代礼乐底事业。”(卷四十一·论语二十三·颜渊篇上)
例17中,学生问“七十从心”一节主要表述的道理是什么,朱熹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这里“毕竟”作为加强疑问语气的副词,强调“追根究底”的意味;例18中,学生问“仁”是什么,“毕竟”在句中加强疑问语气,强调“追根究底”的意味;例19中,学生问颜渊先问“仁”还是先问“邦”,这是一个选择问句,“毕竟”加强疑问语气。
二是用于无疑而问。为了使论证深入,在关键性的内容上,用提问形式进行说理,主要起提示下文、表示反诘等作用,例如:
例20“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他也不曾说是仁圣。但为之,毕竟是为个甚么? 诲人,毕竟是以甚么物事诲人?这便知得是:为之是为仁圣之道,诲之是以仁圣之道诲人。”(卷三十四·论语十六·若圣与仁章)
例21又曰:“耳之能听,目之能视,口之能言,手之能执,足之能履,皆是发处也。毕竟怎生会恁地发用?释氏便将这些子来暪人。秀才不识,便被他瞒。”(卷七十四·易十·右第四章)
例22曰:“若是识得仁体,则所谓觉,所谓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说得自有病痛,毕竟如何是觉?又如何是活物?又却别将此个意思去觉那个活物,方寸纷扰,何以为仁?”(卷一百一·程子门人·谢显道)
例20中,朱熹解释了孔子所说的“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是以什么来“为之”,又是以什么“诲人”。这里,朱熹自问自答,因此例子中的两个问句并不是传疑, 而是启发受话者对该问题的思考,为提起下文做准备;例21中,朱熹认为释家(佛教)关于“发处”的说法并不能真正解释“耳、目、口、手、足”是怎么“发用”的,并指出佛家企图用这些说法来“瞒”人,此为无疑而问,带有反诘意味;例22中,朱熹表示谢显道以“觉”来解释“仁”并不妥当,并反问什么是“觉”。此为无疑而问,表示反诘义。
宋代以后,“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用法逐渐消亡,明清的小说中除了用于章节末尾提起下文的用法以外,几乎见不到“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的用法了。
以上我们梳理了“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用法从出现到消亡的大体脉络:始见于中晚唐时期,宋代禅宗语料中使用频繁,世俗文献中也有一定的用例,到明清基本消亡。
二、“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用法形成、发展机制及消亡动因
1. 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的形成、发展机制
史金生[4]、孙菊芬[2]认为,疑问语气副词“毕竟”是由表示“最终”义的时间副词“毕竟”演变而来;张秀松[3]认为,“毕竟3”(按:即疑问语气副词)是在唐代由“毕竟1”(按:即时间副词)的“不因——而不——”转折义从行域投射到言域演变而来。
我们认为,“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的用法是从时间副词演变而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毕竟”疑问语气副词分为加强疑问语气和表达反诘、提起下文两种用法:前者是由于“毕竟”时间副词的“最终”义在问句中进一步发展出“追根究底”的语气,由客观性表达发展出主观性的对疑问态度的强调;后者的用法稍微复杂一些。我们认为,其形成机制是“毕竟”主观性加强,促使句意由行域向知域过渡表示反诘义,又由知域发展到言域表示提起下文。下面我们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
首先是“毕竟”主观性的加强。“毕竟”作为时间副词表示“最终、到底”义时,其主观性并不强,例如:
例23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地藏菩萨本愿经》)
例24我以此法。令一切众生。毕竟快乐。恒自悦豫。身无诸苦。心得清凉……(《大方广佛华严经》)
例23旨在说明世间的男女凡是听闻“宝胜如来”佛名的都最终不堕恶道;例24中,大光王告诉善财童子是以什么“法”来让众生最终得到快乐。两个例子都是客观地描述某个事件进展到最后的状态,“毕竟”不带有主观性。
时间副词“毕竟”用在问句中,最初的主观性并不是很强,以例1来看,句中的“毕竟”可以理解为“最终”义时间副词,“最终”表示某一事件在时间上的终极状态,对终极状态的询问从语用上分析,就是表示说话人对整个事件的“追根究底”的求知态度,这种语用推理引起的语义变化发生使其结构发生了重新分析[4],因此,这一句中的“毕竟”可以重新分析为表“到底”义的疑问语气副词,其主观性强于时间副词用法。
晚唐《祖堂集》中“毕竟”主观性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如例10就两个平行的选项进行发问,并不涉及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因此,这一例中的“毕竟”是加强疑问性的语气副词,不宜再理解为时间副词。
唐以后,“毕竟”主观性不断增强,《五灯会元》中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
例25僧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水天影交碧。”曰:“毕竟是同是别?”师曰:“松竹声相寒。”(卷第十六·南明日慎禅师)
例26僧问:“佛与众生,是一是二?”师曰:“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曰:“毕竟是一是二?”师曰:“唯余一朵在,明日恐随风。”(卷第十六·承天惟简禅师)
这两个例子中,两个问题均是同一个人向相同的对象发问,问相同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比只是多了“毕竟”一词,这表明“毕竟”在交际过程中发挥了特定的功能,即表示说话人追加疑问并且强烈想要获得满意答案的情感态度。此外,樊华[5]认为,“毕竟”的疑问语调比疑问语气词“吗”更能表达使用者的感情色彩,唐宋时期疑问语气词“吗”的前身“磨、摩、么、末、”已经出现,但“毕竟”出现的疑问句大都没有这些疑问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毕竟”出现的疑问句大都表达较强的主观性。
其次是从行域到知域的过渡。“毕竟”在交际中开始发挥强调疑问的交际功能之后,用于非真性询问时,其疑问性质发生了转移,由加强疑问语气转移为表示警醒、反诘等意义。我们以徐盛桓[6]提出的疑问的语用合适性为标准来进行分析。该原则表述为:
将疑问项的设疑抽象为Y,对此的回答为X:
Ⅰ发问人对Y是有疑问的。
Ⅱ发问人认为Y的设疑是合理的。
Ⅲ发问人对X是真心求知的,对X是未知的,对X的期待不存在倾向性。
符合以上3点,疑问项的语用合适性就是充分的,其中Ⅰ、Ⅲ是主要的。以例4来看,龙潭和尚(发问人)对出家前的生活状态(Y)是存有疑问的,认为这个设问是合理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X)是真心求知、未知且不存在倾向性,因此这是个真性询问。
以例15来看,这个例子是布道中的提问,首先发问人对Y是没有疑问的,布道的形式就是对僧徒或大众宣讲教义,发问人的身份首先是主讲人,这就限定了发问人对Y是已知的;其次发问人认为Y的设疑是不合理的,从句意的理解上来看,“空里采华(花)”和“波中捉月”已经被定性为“谩心劳力”的行为,既然已经对疑问项有了定性,那么再进行设疑是不合理的;再次发问人对X并非求知,对X是已知的,对X的期待存在倾向性。发问人作为布道的演讲者,对X必然是已知的,既然是已知,那么X是一个固定值,发问人对X的期待不存在倾向性。如此看来,例15同时违反了原则Ⅰ、Ⅱ、Ⅲ,因此是非真性询问,是一个反问句。
如果问句违反了疑问的语用合适性,就表明该问句在交际过程中疑问性质发生了转移。这种语用合适性的违反是发话人有意为之,是一种主观化的手段,表达说话人对对话中某一话题的否定态度。例14、15、16中,“毕竟”所在的问句都违背了语用合适性原则(至少是最核心的Ⅰ、Ⅲ原则),疑问性质已经消失,“毕竟”不再强调疑问语气,而是表现出反诘或警示的语气,也就是说,“毕竟”的语义功能从行域过渡到了知域。
再次是从知域向言域过渡,表示提起受话者对某一事物或状态的关注。
“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的主观性不断加强,发生了从知域到言域的转变,“毕竟”逐渐脱离了表示疑问的语境,渐渐丧失了表示疑问的功能,而是在言域范围内提起受话人对某一个问题的关注,或是要求受话人就某一话题进行深思。我们以具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例20、21、22中,朱熹为提起弟子对某一个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而提出设问,在问句后紧跟着给出了答案,属于设问形式。设问违反了疑问的语用合适性原则Ⅰ和Ⅲ,设问人对Y没有疑问,且对X有倾向性。但设问并不违反原则Ⅱ,因为说话人是带有目的性的发问,旨在提起受话人对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与老师在课堂上提问学生的行为相似。无论是提起关注还是发人深省,都要求受话者就这一问句进行相应的行为,“毕竟”在这样的设问形式当中,追加发问人对受话人就某一个话题进行“追根究底”思考的态度,其功能已经超越了知域的范围,向言域发生转移。
明清时期的小说中,“毕竟”大量用在章节结尾处作为提起下一章节的结束语,大约就是这种用法的延伸。例如,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毕竟”全部出现在章节末,一共出现22次:
例27毕竟董卓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例28毕竟救张辽的是谁,且听下文分解。
例29毕竟马腾之言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除了《三国演义》,其他的小说如《三宝太监西洋记》《周朝秘史》《水浒全传》《儒林外史》《乾隆南巡记》《施公案》等也大量使用了这一格式。“毕竟”表示非真性询问,有提起下文的功能,属于言域范围。
2.疑问语气副词 “毕竟”的消亡动因
“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用法在明清时期基本消亡,这一时期的文献几乎很少见用于问句的“毕竟”。同时,“毕竟”作为“追根究底”义语气副词,用于陈述句中表示“到底、究竟”的用法越来越兴盛,逐渐接近现代汉语中的“毕竟”。由此可见,“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用法受到了表总结义语气副词这一主流用法的排挤而逐渐消亡;从外部来看,则是受到了同一时期“究竟”“到底”这两个词的排挤(主要是受到了“到底”的排挤),最终导致“毕竟”疑问副词用法的消亡,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部分文献中疑问语气副词“毕竟”的用例数量
三、 结语
“毕竟”作为疑问语气副词使用最早出现在中唐时期的诗歌中,由时间副词用法发展而来。晚唐《祖堂集》中均表示真性询问,用于特指、正反问句中,加强疑问语气。宋代佛教文献《五灯会元》中,“毕竟”真性询问的用例仍然活跃,用于非真性询问表示提起下文或反诘意味的用法也逐渐成熟。世俗文献《朱子语类》中“毕竟”疑问语气副词用法呈现衰退的趋势,与其他用法相比用例减少,主要用于设问句中,表示提起下文或表示反诘的作用。明清时期“毕竟”疑问副词用法受到“毕竟”的总结义用法以及同时期并存的“到底”“究竟”的排挤而趋于消亡。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虚词例释[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2]孙菊芬.“毕竟”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演变研究[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3).
[3]张秀松.“毕竟”的词汇化和语法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5(1).
[4]史金生.“毕竟”类副词的功能差异及语法功能[C]//吴福祥,洪波.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5]樊华.汉语疑问语调使用分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
[6]徐盛桓.疑问句探寻功能的迁移[J].中国语文,1999(1).
[7]沈家煊.复句三域行、知、言[J].中国语文,2003(3).
[8]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
(责任编辑钟昭会)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2.024
中图分类号:HO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2-0167-06
作者简介:余珩(1987—),女,贵州遵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汉语词汇、语法及语义演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禅宗语录句法史”(09YJA740087)
收稿日期:2015-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