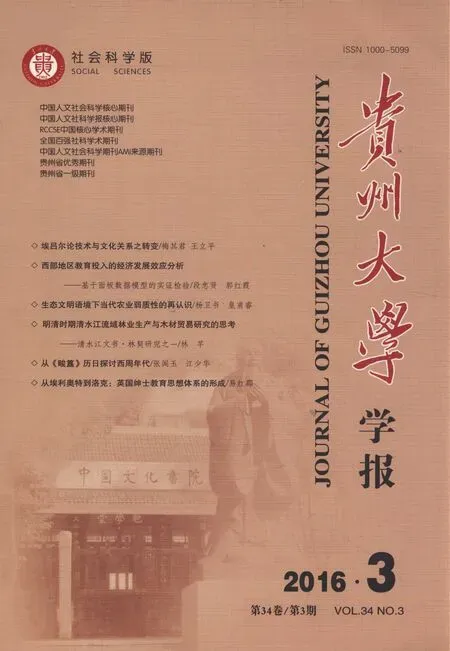论王阳明对“孝”的心学阐发
——以《传习录》为中心的考察
邓 立
(1.贵州财经大学国学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25;2.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论王阳明对“孝”的心学阐发
——以《传习录》为中心的考察
邓 立1,2
(1.贵州财经大学国学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25;2.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明代大儒王阳明不仅为躬行孝道的典范,而且在理论上独取蹊径从心性哲学的视角对儒家核心范畴“孝”进行理论阐发,从包涵丰富哲学思想并充满伦理意蕴的《传习录》可以窥见其由“心即理”的形而上理论预设到“知行合一”的主体性情感自觉,再到“致良知”的本体性伦理建构的运思历程。“孝”既是一种先天的道德情感又是源于“心”的道德主体,以此存在方式其所凸显的是:人的价值由主体意念向外在客体的无限扩展,因其与“心”同构的缘故又暗合了“孝”为“天经地义”的自然之“理”。
关键词:孝;心;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独特的伦理表征,对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形成及中国国民性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历代儒家学者都极力予以阐释和弘扬。明代大儒王阳明不仅为躬行孝道的典范,而且在理论上独取蹊径从心性哲学的视角对儒家核心范畴“孝”进行理论阐发,从包涵丰富哲学思想并充满伦理意蕴的《传习录》可以窥见其由“心即理”的形而上理论预设到“知行合一”的主体性情感自觉,再到“致良知”的本体性伦理建构的运思历程。
通过对“孝”的先验预设,由“心”为主体到外在事物的理论延展,是对传统道德历史审思、哲学诠释、伦理建构的一系列尝试。特别是对“孝”心性定位的深化和心学阐释的独特理论,蕴涵着儒家传统仁爱、亲亲、尊尊等伦理精神,体现出儒家“良知”“良能”教化思想的人文情怀,形成颇具特色的阳明心学孝道伦理观。于此而言,阳明心学对传统道德“孝”的阐发匠心独具,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谨以《传习录》为中心展开。
一、心即理:“孝”的形而上理论预设
从历史上看,儒家思想极为重视孝德,“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①《孝经·三才》。“孝”是天道自然,万物运行的规律,依据人的本性而生。王阳明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的根本价值取向出发,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尤其是孟子的心性论及陆象山“心即理”的理论体系,并延展到对“孝”的阐释和发挥上。其把孝、忠、信、仁都视为心内之事,心外无求,是“天理”的自然之性。“理”即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定和存在形态,又是道德的终极价值及伦理上的至善,所谓“天理在人心,互古互今,无有终始。”②《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心”既是本体,又表现为用,“体、用一源”。而“孝”的焦点往往在“心”上,阳明在论证“心即理”的思想时,常常以孝悌、忠信、仁义等道德规范为立论依据展开,由他与徐爱的对话可窥一斑: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
对于至善只在“心”中探求的质疑,以侍奉亲人“温清定省”等人伦事理为例,阳明认为,“孝”应从本心出发,在“去人欲、存天理”上下工夫。无论是“冬温”还是“夏清”,都必须“讲求此心”,不能有私心杂念,只有用发自内心的真诚敬爱父母,尽心尽力奉养父母,才算得上“孝”。这亦是“人子之礼”②《礼记·曲礼上》。。做到“心”中无欲,纯粹是“天理”,能拥有这样孝亲的诚意之心,自然会寻求“温清”的方法,冬天思量父母的寒冷,夏天考虑父母的酷热,理当如此。“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③《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因此,孝亲源于诚意的“心”所发,有了“心”这一本体,孝亲的“理”自然存在。“心”的本体就是自然之“性”,有孝敬亲人的“心”,就存在孝敬亲人的“理”。
依此逻辑,“心”的本性使然,遇到父亲自然就表现为“孝”,遇到君主自然就表现为“忠”。于是,善与不善关键在于“心”,善良的人以“心”为本体,罪恶的人“心”失去其本体。阳明讲:“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悌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④同③。换言之,“仁爱”为人心自然之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就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天理”。要达到“仁”,首要的是“孝”,以“孝”为本,才能做到“仁民而爱物”。从亲亲、尊尊开始,然后达到“明明德”、“亲民”之仁,正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⑤《礼记·中庸》。仁爱之心就是“孝”的本体,“工夫”不离本体。那么,“孝”与“心”之间是如何彰显出内在的同一性呢?
常言道,“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依阳明之见,也可以逻辑地理解为“孝由心生”“孝”就是形而上的自然之理。阳明曾说:“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⑥《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究其原因,佛家逃避父子、君臣、夫妇关系,害怕社会人伦所牵累,身与心分离;而儒家用心对待父子、君臣、夫妇关系,身心合一,这个“心”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就是孝悌、仁义、礼让。在阳明的语境中,“佛氏遗外而重内,遗弃人伦物理,自然以虚灵养心;儒家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其养心修己,自然不能离却事物。”[1]从这个义理上看,佛家心生逃避反而“著相”,儒家尽心人伦却“不著相”,表明“孝”即是源于事物自然之理,尽心孝亲离不开人伦事理这个对象,“孝”与“心”都是以“理”的形式而实存,二者必然不可分离。
与此同时,阳明看来,孝顺父母就是心外无物,穷尽孝顺的“天理”。“孝”的“天理”不在亲人身上,而在“心”中。“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⑦《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中》。换言之,万事万物的“理”在“心”中,到事物中去求“理”,就如到父母身上去寻求孝道、到幼童身上去寻求“恻隐之心”一样不可行。“心即理”,“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⑧同⑦。“理”来源“心”,若没有“心”,便没有“理”的存在可言。与朱熹所谓的“理”是客观的存在,有客观的“理”,才有孝亲的“心”一分为二不同的是,阳明认为,“心”只有唯一,“心”即是“理”,孝亲、尊亲成为最高的“理”,也就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孟子讲良知、良能是人的先天善良品性,“亲亲,仁也;敬长,义也。”⑨《孟子·尽心上》。“孝”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天然生发的美德。阳明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孝”是人的自然本性,即自然而然之“理”,而这种本性源于人心内在生发的“良知”。由“孝”所表现出的“良知”具有道德感化功能,以至让纠缠于孝慈而准备对簿公堂的父子明白其道理后“相抱恸哭而去”。
阳明给他的学生解释其中的缘由时说:
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今何不曾豫悦我,不知自心已为后妻所移了,尚谓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只是我不能尽孝,日思所以不能尽孝处,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时,又不过复得此心原慈的本体。所以后世称舜是个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个慈父。①《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
易言之,孝慈源于“本心”,需要从自己的内心之中去寻找,才能发现孝慈之“理”。舜对“孝”的认知从“本心”出发,不断反思自身的行为,所以越来越孝顺;其父瞽瞍不知本心已被转移和遮蔽,认为自己对儿子慈爱有加,事实并非如此。而瞽瞍只有心情愉悦的时候,他心中的本体恢复才能表现得更为慈爱,舜为古今大孝之子与瞽瞍是慈父构成了因果关系。阳明说舜自认为是不孝之子,而瞽瞍却是慈爱的父亲,是从“心为本体”的预设论据出发对孝、慈逻辑的推理和反证。孝道与慈爱都是源于“心”之自然,“孝”是爱的根本,“孝”的关键又在于心诚,诚意之心对“慈”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人子事亲,当以诚心尽孝,自可悦亲。”[2]在阳明看来,作为本体的“心”是“孝”生发的本源,“心即理”,“孝”亦是自然存在之“理”,认识到“孝”由“心”所发,就可以避免对孝、慈的理解失之偏颇。
由是观之,“心即理”的理论给予“心”形而上的本体规定。具体到“孝”而言,即是对传统孝德进行先验的理论预设,“孝”既是一种先天的道德情感又是源于“心”的道德主体。于是,“孝”以一种道德的主体性存在方式其所凸显的是价值由主体意念向外在客体的无限扩展,因其与“心”同构的缘故又暗合“孝”为“天经地义”的自然之“理”。由此推论,以“心”为本体的内在道德主体可以关照外在世界的客观事物,万事万物在“心”的统摄下而获得存在的价值。不仅如此,以“心”为本体的形而上先验预设形成的宇宙论与价值观,表现为“自然之理”与伦理规范的渗透和交融,是阳明心学对生命自然充满情感的道德考量以及由宇宙世界到社会秩序之间价值转换的逻辑推理。
二、知行合一:“孝”的主体性情感自觉
不难分辨,“知行合一”源于“心即理”的形而上预设,知与行都来源于“心”。用阳明的话讲,“心”不需外求,自然会知,且“知之真切笃行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②《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中》。知行一致,内外统一,须在孝悌、忠信等人情事理的学习上下“工夫”,才可以达至“仁义”。人情事理与“仁义”是知与行的合一,“这个合一并不是指知行两者指涉同一对象、二者完全是同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是不能割裂的,知行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3]阳明认为,“行不著”“习不察”就不能明白为学的宗旨,如“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若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③《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换言之,只有躬行实践才能出“真知”,知孝必定是已经用心行孝,才可称为“孝”。可见,知识必须付诸实践,也就是道德践履需要通过身心去真切体悟,才是“知行合一”。阳明对此作了详尽而独到的阐释: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就是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④同③。
显然,私欲是遮蔽认知的关键,源于私欲的存在导致知行脱离其本体。知与行犹如“尊德性”与“道问学”,它们是相互存养与共生的统一体,是知行并进、内外本末、一以贯之的修养“工夫”。也即是说,知与行都源于“心”这个本体,只有切实行孝、行悌后才会懂得什么是“孝”,什么是“悌”。“懂得孝悌并且有孝悌的意向,无疑表现了善的德性,但这种德性又必须实际地体现于行孝行悌的过程:正是行孝行悌的德行,为主体是否真正具有孝悌的德性提供了外部确证。”[4]阳明认为,知与行的工夫不可剥离,例如:为学与孝亲之间并不矛盾,“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至不真切耳。”①《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子女侍奉父母,是发自内心和源于本性,“良知真切”,则“不为心累”,与为学立志的宗旨具有一致性。在学习孝亲的事情上,知与行本是一体,阳明讲得非常清楚:“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而后谓之学;其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②《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中》。于是,学习就必须实践,不去实践则不能穷尽天理,当然就不能尽心、尽性,也就无所谓尽孝。进一步讲,只有笃行的“工夫”持之以恒才能实现心中的“良知”,才能做到孝亲,这就是客观存在之“理”。
阳明指出:知、行二字,即是工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落实尽孝而已,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③《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
有鉴于此,“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三者需要下的“工夫”是有区别的,在“孝”的问题上,须谦逊、谨慎地对待,才能依此“良知”来尽孝。阳明始终认为,从意念开始就应符合道德规范,“一念发动处”便是行,知与行本身是一件事,是完满的、统一的整体,如果存在恶的意念,就需要在“克己”上下工夫,做到“思无邪”,才能达到“知行合一”。而且,存养德性是“知行合一”的“工夫”,德性、良知源于本心,无论是“静处体悟”,还是“事上磨练”,都是存心养性的修养“工夫”。因此,在“温清”奉养父母的事情上,一定要按照“良知”中应该如何“温清有节”、“奉养得宜”的方法去实践,不要被任何私欲所遮蔽,通过意念去实践,才能实现奉养的“良知”,这就是“孝”的根本体现。毫无疑问,阳明看来,道德行为是通过道德修养来实现的,首要的道德行为就是“孝”。正如其在教约中明确要求教师每天要询问学生:“在家所以爱亲敬畏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乎?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④同②。视学生践履“孝”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曲加诲谕开发”,来达到“蒙以养正”、“知行合一”的道德教化目标。
如前所述,阳明把知、行看成一件事,知与行是相互包含、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知是行的开始,而行是知的完成,知、行为统一的工夫。正如冯友兰先生指出:“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吾人必致良知于行事,而后良知之知,方为完成。”[5]同样,“孝”源于心的本体,由“良知”所发,顺此推导,“孝”就是“应当”,为一切道德的根本,知孝(心中有孝)就知道如何去躬行孝道。那么,孝道也就成为道德规范与道德践履的统一体,人的道德品质、社会道德规范由“孝”而生,道德修养、道德教育都以“孝”为出发点。这是阳明心学对“知”的先验规定,知与行自然而然构成内在逻辑上的一体化,“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则反映出阳明心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的能动性,是道德意识的主体性情感自觉。
三、致良知:“孝”的本体性伦理建构
阳明心学聚焦于“致良知”,而根本指向是“良知”。心中的“良知”是人的先天禀赋,亦是一种本体性存在,实现心中的“良知”即“致知”;作为“心”的表征的“良知”在事物中得以实现,就是“格物”、“致知”。也就是说,“孝”的实践“工夫”就是达到心理合一,即“致良知”。孝、忠、仁、义与“良知”一样为人心所固有的存在,是“心”的本体,是“天理”的彰显,又是内心的主宰。阳明认为,年幼的时候,“良知”没有被私欲遮蔽,人人都知道孝顺父母,可以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与天地合德”的至善境界;而普通成年人,因物欲所限而不能遵循,则需要“格物”来实现“良知”,才能更好地做到“孝”。“良知”与私欲此消彼涨,于是,只有通过对心中的“天理”细微之处精确体察才能“明明德”,即“致良知”。
如果“良知”是“本心”,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与天然的表现方式,那么,孝悌之心与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一样就是人的自然情感的真情流露,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阳明云:“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真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真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①《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中》。用“致良知”的“真诚恻怛”去侍奉父母就是“孝”,再次表明,“孝”是源于“良知”的自然本心,从“心”上下工夫,才能真切笃实地躬行孝道。所以,阳明强调:“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②《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而且,人的心灵具有自然的灵性,“虚灵明觉”的“良知”所产生的感应称为“意”,知是“意”的本体,“意”以物为对象,“意”用在孝亲上,孝亲则为事物。当然,“意”只是一种意念、愿望,还不能称为“诚意”,在“温清”、奉养父母的事上用功,按照“良知”中所内在的方法去付诸实践,做到“自慊而无自欺”才可以算得上是“诚意”。可见,“‘孝’的本质在于内心的真诚,而不仅在于外在的繁文缛节。”[6]
阳明看来,“舜不告而娶”“武不葬而兴师”等典故所反映的关于忠孝、节义等伦理冲突,须应时应事而变。如纠结于这些特殊境遇中的事情,而不下“工夫”去“致良知”,“悬空讨论”这些变化无常的问题,将与为学、处事的宗旨相去甚远。阳明有云: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③《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中》。
换言之,在不同的时代针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要掌握灵活应对的方法,明白人伦事理,懂得“权变”,就能领会古人如何通过诚意之心“致良知”。因此,孟子认为,舜不告而娶,是合乎情理的,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不孝,“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孟子·万章上》)我们可以看出,阳明采用连续反向追问的方式,推论出“良知”所发的缘由和根据,以此证明古代圣贤以“本心”存在的“良知”为价值判断依据具有的合理性。也即是表明,在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交织时,“良知”可以为道德选择提供本体性依据;在应对道德主体与道德规范之间产生冲突时,“良知”成为“权轻重之宜”的关键,即道德困境中坚持“良知”优先原则。
与此相应,用阳明的话来讲,“良知”存于人心,“良知”是“无方体”“无穷尽”,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人心一点灵明”,又是一念“真诚恻怛”,在“孝”的问题上下“工夫”即是“致良知”。那么,天下之事都可以通过孝亲、从兄的“真诚恻怛”即“良知”的意念去应对和发挥,所以“良知”就成为“孝”的“明镜”,是对孝悌之心的印证,又是对外在事物善、恶的再度确认。在《传习录》中,阳明有这样一段精到的论述:
孟氏“尧舜之道,孝悌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于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④同③。
虽然“孝悌”为“尧舜之道”,但是对于“良知”本身而言,“事亲”之“孝”与“从兄”之“悌”相比,“孝”必定是第一位的。而且,以由内而外的扩充理论来看,“良知”之“孝”是根源又是起点,这也符合“孝”为天经地义以及“百善孝为先”的逻辑。进一步分析,“良知”固然只有一个,却是可以不断扩充、拓展的,而万事万物取决于人的“良知”,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这无疑是心学对“良知”内涵的显性延展。而且,阳明认为,“良知”如至善一样是天性,没有私欲的存在,是心之“本然”,即天性的本源,“道心”与“人心”“自然无不是道”。“‘道心’与‘人心’既不能分,‘心’与‘身’又不能分,这样,‘理’与‘天理’也就愈益与感性血肉纠缠起来,而日益世俗化了。”[7]于是,“真诚恻怛”地侍奉父母的“良知”可以从爱亲孝养的世俗人伦中扩充到万事万物,达到“工夫”与本体的合一,这是所谓“惟精惟一”的学问,即“致良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理”。依此而论,“致良知”是从内心的本体向外在的事物展开,即“复其本体”,那么,孝悌也即是由“心”而发,以“心”为道德主体,扩充为世间中的万事万物恒定不变之理。这即为阳明心学以“致良知”的“工夫”所呈现的具有直觉主义特征的本体性伦理建构思路。
四、余论
阳明心学是对儒家传统心性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从“心即理”的形而上预设到“致良知”的本体性建构来看,“知行合一”的主体性自觉既是其搭建的为学立旨的桥梁,又是“天理”到“良知”的逻辑转换渠道,亦是理性与情感的价值平衡并实现其心学融会贯通的关键所在。从历史的境遇中讲,阳明对“孝”的心学阐发正是由“圣人之学”向“圣人之心”与“至孝之心”之间转换的现实写照,亦是其矢志不渝地追求与天地万物一体之“心”,期望“致良知”学说昌明于天下,进而实现国泰安民、天下大同的人文情怀。
通过《传习录》中阳明对“孝”的心学阐发的考察,归纳起来,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阳明心学沿袭儒家“道统”,对儒家传统道德的诠释、发挥及儒学本体论建构的哲学审思和理论推进有积极的价值,是儒家思想的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是阳明心学以“心”为主体向客体外在认知展开的致思路径具有理论的深刻性,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评价的那样:“阳明说心即是理,说理无内外,这就性理而言,本是如此;但在表诠的次序上,及实践的程序上、结果上,不能不承认这种由主观向客观展开的意义。”[8]
三是阳明心学对传统道德的抽象化、绝对性的定位和阐发,仅从“良知”上去找寻道德的价值依据,把“心”预设为一切道德的主体,对事物本来之理的选择性忽略所形成的理论缺憾以及个人存在的价值迷失,似乎成为阳明后学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或许,通过《传习录》中阳明对“孝”的心学阐发初步探讨所呈现的问题,能唤起学界进一步研究古代道德文明,以此更为深入、全面地体认传统中国。
参考文献:
[1]张祥浩.王守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400.
[2]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63.
[3]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9.
[4]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3.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23.
[6]杨明.个体道德·家庭伦理·社会理想——〈礼记>伦理思想探析[J].道德与文明,2012(5).
[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59.
[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6.
(责任编辑 周感芬)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3-0029-06
DOI编码:国际10.15958/j.cnki.gdxbshb.2016.03.006
收稿日期:2016-04-2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中国公民道德发展研究”(12&ZD036)。
作者简介:邓 立(1981—),男,贵州福泉人,贵州财经大学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儒学与中国传统伦理。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①《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