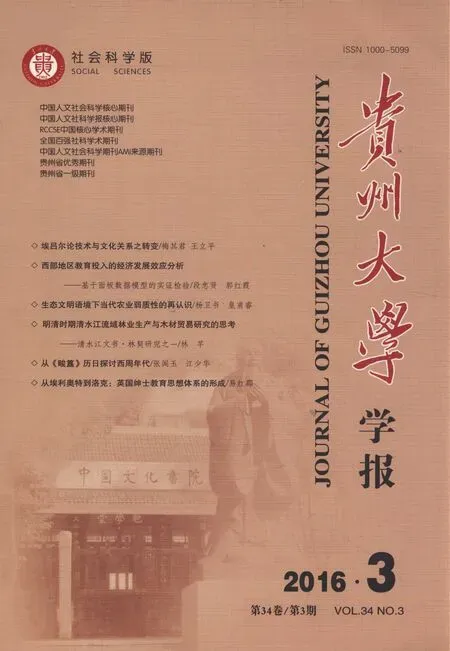埃吕尔论技术与文化关系之转变
梅其君 王立平
(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埃吕尔论技术与文化关系之转变
梅其君 王立平
(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埃吕尔认为,传统技术被束缚在文化之中,而现代技术是一种自主的技术,超出了文化的限制,并反过来决定文化,对文化构成威胁,而造成这一转折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的绝对效率,即技术的效用性战胜了一切价值。
关键词:技术;文化;埃吕尔
关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人类学家习惯将技术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有的哲学家也认为技术嵌入在文化之中,是“一种文化过程”。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把文化分为三个亚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但他认为,这三个亚系统在作为整体的文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技术系统起着主导作用,它决定社会系统的形态,并与社会系统一起决定思想意识系统。[1]日本人类学家石田英一郎等人也将文化的内容分类为技术文化、价值文化和社会文化[2]。法国哲学家多洛认为,“工艺技术与文化艺术一样,都归于文化之列”[3]。
与上述观点不同,不少哲学家认为,技术发展到现代已开始强烈地冲击乃至决定文化。德国技术哲学家盖伦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急剧变化的技术化的社会,为适应这样一个社会,人类在几千年漫长的文明史中形成的基本上稳定的、常规的种种制度、习俗、规范、思想乃至感情和心态,被迫不断地改变自身以迎受挑战,“人类文化生活在这些方面的改变,却远远赶不上且适应不了技术社会的迅猛发展”[4]。法国技术哲学家拉特利尔指出,现代技术与科学对构成文化的一切方面产生决定性影响,使文化刻上特殊的印记。科学技术一方面“日趋毁坏使文化统一的因素”,另一方面“揭示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客观的历史的可能性”。[5]海德格尔、斯宾格勒、罗宾斯、韦伯斯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
在后一种观点中,埃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阐述具有代表性。埃吕尔是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和神学家。他的技术哲学与马克思、海德格尔、杜威的技术哲学一起被称为四大技术哲学学派。埃吕尔以工业革命为界将技术分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与之相应,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被称为传统社会或前技术社会,而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则是现代社会或技术社会。埃吕尔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技术被束缚在文化之中;而在现代社会,技术超出了文化的限制并对文化构成威胁。
一、自主性: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
埃吕尔把技术定义为“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通过理性获得的(在特定发展阶段)有绝对效率的所有方法”[6]XXV,他所讨论的技术是一种广义的技术。埃吕尔提出,若要明晰技术的定义,必须对“技术操作”和“技术现象”进行区分。“技术操作包括为达到特定目的而依据一定方法进行的所有
埃吕尔所探讨的现代技术实际上就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埃吕尔认为,现代技术已发生本质性变化,它和传统技术之间并不存在公分母。在前技术社会中,技术的应用范围还十分狭窄,传播速度相当缓慢,它基本上只是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其地位并非是至高无上的。自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传播速度愈来愈快,它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大,已经渗透到世界的各个领域,成为各个领域发展的主导力量,成为社会中最具影响的因素。
埃吕尔认为“自主性”是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主要区别。技术并非自始就是自主的。在传统社会,技术只不过是一种人们使用的工具,它的发展进步依赖于文化和社会,并被牢牢地限制在人类文化和生活的总体框架之内。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关注的是工具的使用,而非工具本身。重点是使用工具之人,而非人使用之工具。人使用工具的技巧、才能才是首要的”[6]67-68。只有在技术社会,技术才是自主的,或者说只有现代技术才是自主的。埃吕尔从三个层次详尽剖析了现代技术的自主性[7]。
现代技术自主性的第一层次是指技术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则。这种内在逻辑和规则又主要表现为技术系统的自增性、技术前进的自动性和技术发展的无目标性。首先,技术系统的自增性也称技术系统的自我增长,是指“通过内部固有的力量而增长”[6]209。埃吕尔认为,技术在进化过程中性质发生了改变,它的发展几乎不再受人的决定性干预。技术根据自身之内在逻辑不断发展,并不回应人之需要,人在技术发展中并不扮演重要角色。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强制改变其所触及的一切,使得一切必须遵循它,使所有进入技术范围者都必须采纳技术原则。技术系统的自增性还主要体现在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上。技术发明是之前技术要素的组合,本质上是之前技术增长的内在逻辑产物。简而言之,整个技术系统的自我增长可以被表达为两条规则:“(1)在某个社会文明之中,技术进步是不可逆转的;(2)技术进步是按几何级数进行的。”[6]89其中,技术的几何级数增长是说,一项技术发明不仅对作为整体的技术系统的一个分支产生影响,很可能同时对多个分支产生影响。其次,技术前进的自动性指技术仅仅依赖于自身向前发展,而不依赖于人和其他外在力量,它受之前技术所引导,被技术理性所规定,但不意味着没有人的选择。“技术包含了某些它本来意义上的后果,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结构和要求,引起人和社会做特定调整,这种调整是强加于我们的,不管我们是否喜欢。”[8]155技术前进的自动性包括技术活动的自我定向、技术间的自动选择、环境对技术的自动适应和非技术活动的自动消除。再次,技术发展的无目标性指技术发展漫无目的,存在各种可能性,它并不按照人为其预先设定的目标发展。“不管人类为任何给定的技术手段所定的目标是什么,它总是将必然的结局隐藏在自身之中,并且在技术这种固有的结局与人类为之计划的非固有的目标之间的竞争中,总是前者获胜。如果技术与人类的目标不太相符,如果一个人企图让技术去适合自己的目标的话,一般可以立刻看到,修改的只是目标,而不是技术。”[6]141第一个层次的自主性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技术发展的相对自主性。显然,这种自主性并不是现代技术所特有的,它甚至不是技术所特有的。于是,埃吕尔进一步从社会的技术化和人的技术化生存两个方面来阐述现代技术的自主性。
第二个层次的技术自主性,即社会的技术化,是指技术自主性要通过它与社会诸因素的关系呈现出来。对于一切社会因素而言——如政治、经济、科学、道德、文化等,技术是自主的,不受其支配,相反,一切事物皆被技术改变。可以说,人类社会现在几乎不存在可以用来抑制技术之物,几乎没有什么能与技术相匹敌,社会中的一切皆是技术的奴仆。
第三个层次的自主性,即人的技术化生存,重在强调人与技术的关系。在技术化的社会之中,技术已无孔不入,它几乎不允许任何不能融入技术之人存在,甚至不能容忍逃避技术化的念头存在。埃吕尔认为,技术已经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一种环境,他称之为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是人所创造的将人自身完全包围的一种环境,它不仅是技术得以产生并适应的一种环境,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作为生活环境的技术不仅直接改变人的生活,而且改变人的思维,它“强迫我们把任何问题都视为技术问题,同时,把我们锁在封闭的已成系统的环境之中”[6]48。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人都将无法使自己脱身。技术社会中,人可以判断、选择,但严格受到技术限制:“人只能在技术所建立的选项系统之中做出选择,只能根据技术所指定给人的范围对技术进行指引”[8]325。因此,人已经技术化,他无法逃避技术而只能适应技术。
总之,“自主性”是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本质区别,是现代技术所独有的“特殊力量”。“这不是一种没有方向,没有特性或没有结构的中性力量,而是一种具有特殊力量的权威。它按照自己特有的感觉折射人类利用它的意志和人类为它预设的目标。”[6]141当然,现代技术的这种自主性绝不是指外在于人的自主性,相反,它恰恰是由人的选择和行动来支撑的:“所有人都致力于技术,在一切领域,每个人都寻求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本质上就是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6]85正是在这种共同努力中,个人或某些组织的特定选择对于整个技术系统而言,已变得无关紧要。由于现代技术的自主性,人类的生活、文化发生彻底变化,它就像“弗兰肯斯坦怪物”一样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并且要求愈来愈多,愈来愈苛刻。它要求重塑人类生活、文化和技术自身框架,因为现存框架已不适应技术环境。
二、文化的技术决定
技术社会之前,技术首先受到古希腊关注存在、真理和注重人自身认识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控制。人们不重视技术,对技术持审慎态度,甚至鄙视技术。因为他们认为,手工艺和工具是奴隶所从事的职业,手工艺和工具不可能使头脑变得更加智慧,更加高贵。中世纪,技术受到基督教的约束。例如,12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二世严格限制弩弓的使用,并禁止使用致命的弩弓攻击基督教徒,违抗者将被清除教门。到16世纪,人们依旧认为,“技术进步并不总是意味着社会进步,并将技术之力量牢牢地限制在社会和文化之中”[9],技术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约束。总之,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的传统社会,传统技术与自身所处时代的文化密切相关,它从属于生活,依赖于文化。
在技术社会中,技术与文化之关系已经截然不同。原本受到文化限制的技术已挣脱缰索,打破一切限制技术的界限,延伸到所有领域,与文化产生冲突。到现在为止,那些曾经被共同认可的观点,即技术发展所依赖的相适应的文化是必不可少的观点,几乎不再被多数人所肯定。现在,无论在何种环境之中,技术发展仅仅依赖于其自身,以至于它迅速带来文化各个领域的塌陷,使“世界上所有人都生活在由技术与文化相冲突所导致的文化衰败的时代”[6]122。现代技术在一切文化领域实施垄断,一切文化活动——智慧的、艺术的、道德的——仅仅是现代技术的一部分,任何事物都必须臣服于它。换句话说,目前已不存在能够与技术抗衡的文化,文化也已不再是曾经所是。
价值观念、信仰、心理等文化方面在现代技术的入侵之下也发生转变。现代技术既不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加入新内容,也不是用“旧瓶装新酒”,而是彻底打破旧瓶,也就是说,技术彻底打破传统文化的原有结构,使传统文化发生动摇、改变,甚至面临没落的危机。因此,埃吕尔担心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将被技术所摧毁,担心文化的瓦解——包括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传统心理、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瓦解。由于现代技术的冲击,“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一种宗教的消失——作为一种技术的结果:在原子弹被投放到广岛之后,日本天皇崇拜的衰落。我们正在目睹中国藏传佛教在舆论压力下的败落。根据目前的调查,由于技术而非舆论思想的影响,佛教正在逐渐衰败。”[6]121在埃吕尔看来,现代技术创造的世界自始就仅仅有利于它自身。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必然存在到处机械地复制自身,致使社会文化形式分离,文化戒律被推翻,道德遭到破坏,最终人和事物非神圣化。
现代技术标准是国际性的,它要求与之不相符的文化被迫修改自身的标准以适应技术的标准。埃吕尔指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程度无论如何,都被迫倾向于应用同样的技术程序。“过去的文化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且发展道路亦不一样。然现在,一切都与技术结盟,沿着相同轨迹发展,可以说,技术使不同文化趋同。”[6]117尽管目前不同地域、民族之间依然存在某些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残余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会完全消失。譬如说,现代技术虽然已取得了对宗教的胜利,但人的文化、生活方式仍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全改变。不可小视的是,现代技术的文化入侵具有某种欺骗性,它令人误以为现代技术带来了多样性和差异性。其实,“不同地区的文明差异是表面的,本质上是同一的,即都是技术的。这种差异来自于技术人员冷静的计算,而不是来自于人类深层的精神和物质的努力。不是人之本质表达,而是技术之意外事件。”[6]131这就是说,表面上会造成一定的文化多样性的现代技术,实际上必然导致同一化。
可见,现代技术日渐控制文化的所有要素,逐渐成为文化的核心力量。也就是说,现代文化是技术主导的文化,亦可称之为“技术文化”。“技术文化”意味着技术不再只是简单的工具和庞大的机械装置,而是具有文化的特征。这种“技术文化”并非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种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技术文化,而是拥有文化功能成为以技术决定为特征的文化。“技术文化”取代传统文化,并与传统文化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埃吕尔认为:“技术文化取代传统文化的形式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突然间全部毁灭,亦不是另起炉灶重新建造新的文化,而是逐渐地侵蚀、改变传统文化。”[6]125现代技术文化的此种特性使得正在被毁灭的传统文化被恢复、重建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因此,现代文化被现代技术所构造,文化仅仅成为它的服从者。换言之,文化的一切领域从属于现代技术,现代技术主宰一切文化领域。
三、技术的绝对效率
埃吕尔认为,现代技术带来的文化危机与技术的绝对效率是分不开的。现代技术将绝对效率放在真善美之上,使艺术、道德和宗教臣服于技术力量。对于技术的绝对效率而言,一切价值相对于技术价值都变得不重要。也就是说,现代技术所依赖的原则使任何价值皆被还原为技术效率和技术的有用性。现代技术将自身展现为绝对效率的方法的总和。绝对效率之所以是“绝对的”,可以在两种意义上理解:其一,它用最有效的方法达到目的,即是绝对有效的;其二,它是绝对的,是因为其他一切价值必须都从属于它,即效率是绝对的。[10]于是,一切价值皆被还原为技术价值,这意味着技术使用者依据技术标准进行价值判断。埃吕尔认为,现代技术的绝对效率概念远远背离了原始性意义上的技术有用性概念,原始意义上的技术概念已经被狭义化。“一切技术的发展都是人类智慧思维和创造的最高贡献。但是一旦技术超越了某个点,技术的有效性原则就变得极其突出”[10],以至于文化的限制条件对技术有效性原则的束缚力越来越小,最终文化的限制条件不再对技术起作用。
埃吕尔认为,技术的历史就是不断寻求绝对效率的历史。技术社会之前,尽管寻求最大效率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仅仅是美、宗教、道德和政治等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技术不能提出适应的问题,因为它牢牢地陷入文化和生活的整体框架之中,效率和作为最有效达到任何目的的非技术价值融为一体,与非技术价值相和谐的效率是有效的,与非技术价值相冲突的效率除造成人类的损失和自然的破坏之外,将不会达到任何目的。然而,自工业革命起,“社会产生了独断的理性技术,这种技术唯独考虑效率”[6]73,技术作为绝对效率的方法总和的特征才显现出来。技术的绝对效率原则动员起整个社会,超越和凌驾于任何文化之上,支配一切人类文化。人们曾用美学和道德等文化价值与之相抗争,但最后,美学和道德等一切文化价值附属于技术效率,不得不服从于技术的绝对效率。现在,技术的进步“除自身的效率之外,不再受任何其他限制”[6]74,技术的绝对效率压倒一切。
技术的绝对效率取得胜利之前,美学的考虑在技术活动中至关重要,美学的限制是必不可少的,并且美学的限制允许“无用”进入到技术有用性和技术效率之中。技术有着基于美学等其他价值考虑的多样性,例如,16世纪瑞士武士所用的剑至少有9种形式。但19世纪起,技术从美学的限制之中获得解放,并使美服从技术有用性和技术效率。现在,美似乎仅仅被理解为“技术之美”:“一种不美的技术是不可能的。因为,自技术效率取得绝对优势之后,人们普遍形成一种思想:美是技术的有用性,即最适合使用的就是最美的。很显然,现在几乎已经不再存在一种指向过去的美学思想。”[10]例如,在自动化的过程中,生产流水线是最美的,但这种现象仅仅是现代技术绝对有效性的最初原形之一。
道德同样不能避免类似的遭遇。埃吕尔认为,现代技术不再接受任何道德限制,也从来不关心道德问题。相反,它倾向于建构一种技术道德,使一切必须依据、遵循技术道德进行判断。“道德判断道德问题,至于涉及技术问题,它没有什么可说。只有技术标准是相关的。……既然技术已经超出了好和坏,那么它无论什么限制都不害怕。”[6]134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生产的快速增长,以至于道德限制不再对蒸汽机的使用起任何作用。武器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人们发现更具创造性的自我防卫策略。技术的绝对效率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成了道德的裁判者和新道德的创造者。
现代技术为了更好地在不同环境发挥其有用性和自身效率,产生了新的多样性。例如,军事坦克依据其被运用在山区地形还是平原地形而被设计为不同的外观。但无论如何,在现代技术显而易见的动态的、多样性的表层下,完全是一个凝固的追求绝对效率的技术系统:在其强制性的绝对效率状态中自我推进。
在埃吕尔看来,技术的绝对效率导致现代技术现象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合理性。合理性是指一切技术活动都可以被精确地计算、推断,亦即技术活动的理性化。“一切都被精确地计算和测量,以至于从合乎理性的观点看,所决定的方法近乎完美;从适用的观点看,所采用的方法明显是迄今为止所使用的所有方法中最有效的。”[6]79-80二是人工性。人工性是指技术控制、消除、毁灭自然、文化等非技术活动,依自身规则构造世界,但它所构造的世界根本不同于以往的世界。“技术活动自动地消除非技术的活动,或者将非技术活动转变为技术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意识的努力或定向的意志。技术活动之所以能将非技术活动消除或使之转变为技术活动,是因为技术的有效性。”[6]83现代技术的绝对效率不仅决定了与自然的交往,而且也深深地铭刻在人之文化创造上,占领一切领域,以至于从技术的绝对效率上来考虑,尽管存在自然、文化领域的差别,但已不存在自然和文化展现的区别。可以说,世界之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形式。
不管现状所强加的文化束缚如何,现代技术的绝对效率总是能够将其同化,将其纳入自身框架。所以,现代技术已经成为理解文化成长与发展的钥匙,它彻底地突破文化的干预和控制,实行极权的技术垄断。埃吕尔认为,传统社会中,不存在人不能反驳的约束,因为不存在对一切都是绝对好的东西。“技术形式的多样性和模仿的缓慢性使得人之行动是决定性的。譬如,当几种技术形式都可付诸实施时,人可以根据很多理由进行选择,而效率仅仅是众多的理由之一。”[6]75但现在,技术绝对效率的存在使我们面临丧失有效的人类决定的危机,面临技术构造文化的危机。
四、结语
从分析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区别入手,埃吕尔提出了技术与文化关系历史变迁的观点。埃吕尔关于技术与文化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思考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特别是现代技术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埃吕尔的分析也并非无懈可击,技术的效用性如何能战胜一切价值仍需要追问。
参考文献:
[1]〔美〕L·A·怀特.文化的科学[M].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351-353.
[2]〔日〕石田英一郎,等.人类学[M].金少萍,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51.
[3]〔法〕路易·多洛.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M].黄建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1.
[4]〔德〕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人类的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中译序)[M].何兆,武何冰,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
[5]〔法〕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吕乃基,王卓君,林啸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7:9.
[6]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Trans:John Wilkinson.New York:Alfred A.Knopf,1964.
[7]梅其君.技术在何种意义上自主[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 (6):54-58.
[8]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ystem[M].Trans:Joa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m,1980.
[9]Rudi Volti,William F.Ogburn,Social Change with Respect to Culture and Original Nature[J].Technology and Culture,2004,45 (2).
[10]George Teschner,Alessandro Tomasi.Technological Paradigm in Ancient Taoism[J].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2009,13(3).
(责任编辑 方英敏)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3-0001-05
DOI编码:国际10.15958/j.cnki.gdxbshb.2016.03.001
收稿日期:2016-03-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技术视域下的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传承”(10XMZ033);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科技传播与文化变迁”(GDZT2011009)。
作者简介:梅其君(1972—),男,湖南汉寿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技术哲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民族区域发展。操作”,“方法是技术操作的基本特征,它的有效性有大有小,复杂程度可高可低,但其本质一样”。[6]19任何操作都需要一定的技术,技术行为的特征是寻求最大的有效性。当理性判断和意识进入操作领域之时,先前尝试性的、无意识的、自然的活动变为明确的、有意的、理性的活动,于是,就出现了技术现象。技术现象在这个时代备受关注,它可以被描述为:在任何领域都寻求最有效的手段,最有效的手段即是建立在计算基础之上的技术手段。技术手段逐渐进入到一切领域,使其自身被推崇为至高无上的法则,从而产生了技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