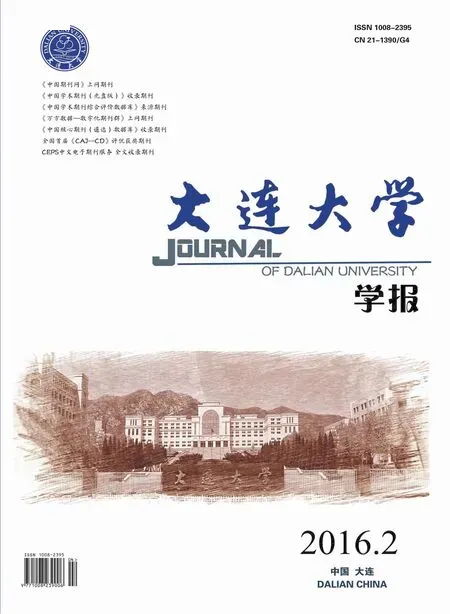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的现代重述
——以郑振铎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为中心
张 岩(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的现代重述
——以郑振铎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为中心
张 岩
(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重要形象,也是中国现代作家最为关注和喜爱的希腊神话形象之一。随着西方神话学的引进,普罗米修斯神话中的“盗火”情节以及其中蕴含的启蒙意识、殉道精神和反抗意志为中国现代作家所关注和高扬。郑振铎作为古希腊神话的重要研究者,曾对普罗米修斯神话作出系统的研究和翻译,并以《取火者的逮捕》为题创作了系列小说,高扬了普罗米修斯大气凛然的英雄气概以及威武不屈的坚韧意志,集中表现出中国现代作家对这一“盗火”神话的价值诉求和精神追求。
关键词: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现代重述;《取火者的逮捕》
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在希腊神话和整个西方的文学世界中都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形象内涵和价值标尺的角色。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西方神话学和文学中的神话传统逐渐进入到中国作家的视野之中。而在诸多古希腊神话形象中,普罗米修斯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作家最为偏爱的希腊神话人物。
一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名字代表着“先知者”。在以宙斯为主神的这一代希腊神话谱系中,普罗米修斯是作为有功之臣而登上神殿,因为他曾经帮助宙斯推翻上一代天帝克洛诺斯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神界和新的世界秩序。当宙斯要求人类永远停留在蒙昧阶段时,普罗米修斯持着火种来到人间,让人类逐渐摆脱蒙昧,走向光明和智慧的生活。在希腊神话中,宙斯最终的胜利既标志着神与人之间关系的绝对法则,也是古希腊文化精神中对于权威和力量的推崇。而普罗米修斯也并未被赋予巨大的牺牲精神,则更多地强调其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反叛精神。这种精神经过了世世代代文学作品的传颂,逐渐凝炼为一种普罗米修斯精神,一种从古希腊到现代社会一直努力追求的人性自由的民主精神。
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要对这种影响的来源脉络简要梳理的话,可以发现在现代作家有关“普罗米修斯”神话的陈述中,有两个主要的来源:其一,是对古希腊神话的译介和西方早期的文学作品;其二,来源于以雪莱的戏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为代表的近代以来改编自盗火神话的西方文学作品。
郑振铎在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的序言中,详细介绍了他创作之初所查阅的《神话集》(阿波多洛斯)、《神谱》(赫西俄德)、《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雪莱)等记载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的资料。这篇序言虽说是对于小说内容的来源作出的解释,然而却极为鲜活生动地描述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转变轨迹,从而为现代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背景。赫希俄德在《农作与时日》和《神谱》中讲述了普罗米修斯的生平,与正义的宙斯相比,普罗米修斯代表了试图欺骗权威的阴谋家,从而歌颂了权威的不可撼摇。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所塑造的普罗米修斯是一位具有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理想人格的民主战士形象。在普罗米修斯的身上洋溢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坚韧的斗争意志。茅盾、郑振铎都是通过翻译和介绍希腊神话而了解普罗米修斯这样一个英雄形象。茅盾编译的《希腊神话》,书中首篇就是《普洛末修偷火的故事》,颂扬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好朋友”“人类的恩人”。郑振铎在其翻译作品集《希腊神话故事》的序言中提到:“这故事,很早的便在Hesiod的《神谱》(《Theogony》)里叙述着。其后大悲剧家Aeschylus更取之而写成《Prometheus the Fire—Bearer》《Prometheus Bound》及《Prometheus Unbound》伟大的三部曲。这伟大的三部曲虽仅存了中间的一部(即《Prometheus Bound》),而我们读之,却是怎样的感动!”[1]1933年7月,上海文学社编辑的《文学》月刊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便印上普罗米修斯取火的油画。郑振铎在其译作《严加管束》附言中说将这篇小说“献给为光明而争斗的青年勇士们”,反动派的镇压“不过造成无数象Prometheus般的伟大的人物而已。”[2]神话题材小说《取火者的逮捕》从第三期开始在《文学》月刊发表。
第二个来源是直接来自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作品。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和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都表现出狂飙突进运动强烈的反抗意识。特别是雪莱摒弃了希腊神话结尾中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和解,最终在冥王的帮助下第一次彻底地战胜了宙斯。这个极具冲击性和颠覆性的结尾,以及雪莱这部诗剧所颂扬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启蒙精神和价值追求。郑振铎认为:“在革命诗人雪莱所写的《Prometheus Unbound》里,却以为反叛者的柏洛米修士和暴主宙斯之间是没有重归和好之可能的。惟其表现柏洛米修士的反抗精神及其背景,当然也很受着Aeschylus的启示。”[3]192在雪莱的诗剧中,最终“大地、天空和空气以及宇宙间的一切势力,欢呼的颂扬这和平友爱的新的统治的出现。而全剧也在欢呼声里闭了幕”[3]193。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最终宣告了普罗米修斯的胜利,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叛逆的情调”,不仅是对之前诸多普罗米修斯故事的极大突破,而且对后代作家、学者而言展开了另一重值得激昂振奋的意义空间。正如凯伦·阿姆斯特朗在《神话简史》所言:“英雄神话并不热衷于提供令人敬拜的偶像,而是为了触动每个人血管里的英雄主义因素。神话必须导向积极的参与或模仿,而不是消极的冥思苦索。然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却早已遗忘,该如何以一种精神挑战和转变来把握我们的神话生活。”[4]146
二
1933年至1934年间,郑振铎创作了题为《取火者的逮捕》《亚凯诺的诱惑》《埃娥》和《神的灭亡》的四篇短篇小说,并结集出版。其中,第一篇《取火者的逮捕》基于郑振铎的翻译小说《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以宙斯在神殿等待审讯普罗米修斯开场,浓墨重彩地刻画了神殿之上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对峙与批判,最终宙斯恼羞成怒地下令对普罗米修斯残酷的惩罚。第二篇《亚凯诺的诱惑》描述宙斯为了知道未来的命运,而使海神亚凯诺劝说普罗米修斯认罪,与宙斯和解。第三篇《埃娥》在情节上与之前两篇并不产生明显的连贯关系,更像一个插叙。讲述天帝宙斯荒淫无度的暴行,他用欺骗的手段霸占了人间的女子埃娥却始乱终弃,没有给予埃娥相应的保护,而使得天后赫拉因嫉生恨,将埃娥变成白牛,受尽屈辱,宙斯却怯懦地逃之夭夭,寻找新的玩物和乐趣了。这个插曲的设置一方面表现了宙斯腐朽没落的统治,为人类的反抗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据,另一方面引出了普罗米修斯的解放者——赫拉克勒斯。而对于第四篇,是原有神话中所没有的,即便是雪莱的诗剧也并不与此相同的。在之前的诸多版本中,无论是普罗米修斯向权威低头,或是普罗米修斯与宙斯和解,又或是宙斯因为不知道自己灭亡的秘密而最终实现了普罗米修斯的复仇,人们对于希腊神话中这个故事的反抗意识逐渐加强。在郑振铎的笔下,这个故事的结局呈现出进一步的发展,郑振铎说这部分是“最架空无据”[3]195,“离开了那古老的传说而骋着自己的想象的奔驰”[3]189的产物。这与郑振铎在五十年代提出“英雄传奇”的概念颇有一脉相承之意:“讲史或演义,只是据实而写,不容易凭了作者的想象而驰骋者;又其时代也受着历史的牵制,往往少者四五十年,多者近三五百年,其事实也多者千百宗,少者也有百十宗;作者实难于收罗,苦于布置,更难于件件细写;而其任务也往往为历史所拘束,不易捏造,更不易尽量的描写着。至于英雄传奇则不然,人物可真可幻,事迹若虚若实。年代也完全可不受历史的拘束,如此作者的情思可以四顾无碍,逞所欲写,材料也可以随心做造,多少不拘。作者很容易见长,读者也更易感到趣味”[5]721。在这篇作品中神的灭亡体现了作家彻底的反抗意志。总的来说,这部神话题材小说集的创作既是郑振铎多年以来翻译和研究希腊神话的成果,更以昂扬激越的情感表现出作家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
(一)启蒙精神的延续
《取火者的逮捕》虽然创作于三十年代,但是却秉承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小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以他强大的意志力、坚韧的反抗精神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面对危难,先知英雄最为伟大之处是能够坚持真理,即便被误解、被打压、甚至遭受迫害却依然坚持历史的发展方向。被捕后的普罗米修斯临危不惧地承受宙斯施加给他的种种酷刑,表现了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郑振铎没有将“普罗米修斯”直接定为作品集的名称,而是选取了“取火者的逮捕”,从而将讴歌的对象从古希腊神话中的特定的神延展至整个革命者的和启蒙者的群体,“取火者”的身份确认强调了普罗米修斯的启蒙价值和革命身份。
在东西方远古神话中,关于“火”与人类的记载都非常地详尽与生动,许多神话学者认为火的神话在整个神系故事中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至此,神话所讴歌的对象由“神”转向了“人”。火能够带给人光明与希望、勇气和力量,对于前路茫茫、急切地寻求前进道路的现代中国而言,“火”的启蒙价值被极大地高扬。火在希腊神话中的确属于神的技艺,是“神们的独得之秘,是神的权威的代表,它只能放光明于神之厅与室,它只能供神作种种的利用的工具”。有了火,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便足以夸耀于下等的人类之前,足以为他们永久的主宰而不虞其反抗;人们是在永久的龌龊卑污的生活中度过去的;那么可怜,那么无告”。普罗米修斯将火传播到了人间,隐喻人民在茫茫黑夜中终于寻到了曙光。漫漫的长夜被这一星星的火光所代替,人类不再蒙昧地在黑暗中摸索。在郑振铎的小说中,“火”既能够点亮人类的生活,也能够点燃人类的心灵与智慧;既能够带给人们御寒的温暖,也能够引燃革命的熊熊烈火。当“众神之王”宙斯带着赫尔墨斯周游的时候,发现人类竟然学会了使用火,在人间发现草屋中放射出火光,特别是铁工场里的熊熊炉火映照“严肃、自尊与自信”的打铁汉子的脸面。失去火的专有权的宙斯,感受到人类即将摆脱他的奴役,预感到神的世界倾危的征兆。文中,普罗米修斯热情地赞扬火:“‘火’将不再是个人的装饰品,将不再是神阀的工具,将不再是阴谋与个人主义的奴役。它变换了千万个式样,为全人类而服务,为向全人类的光明、幸福的生活得建立之目的而服务。”[3]-211普罗米修斯给人类文明和反抗种下的火种点燃了人类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最终发展成漫山遍野的燎原大火。反叛者们气壮山河地攻占了奥林匹斯山。这场人与神之间的斗争,“‘人’是终于光辉地得到最后的胜利了”[3]213而诸神们的栖身之所,那象征着神圣与权威的神庙“在自己的雷矢之下倒塌了。亚灵辟山裂开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就在神道们所站的地方”,随着“神之族整个的沉落在这无底的最黑暗的深渊里去”[3]302,这首“神之终曲”也落下了帷幕。
(二)强烈的现实感
“真实地反映生活”是郑振铎重要的文学主张和创作理念。在《血与泪的文学》里,他主张:“记住!记住!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6]391-392在《文学与革命》里,郑振铎高呼“伟大的文学永远是和伟大的时代相合奏的”[7]322,因此,他主张现代作家有责任和义务“把现在中国青年的革命之火燃着”[8]334。这样的一种文学思想和文化思考使得郑振铎在创作中坚持文学不应该只反映个人的情绪,而更应该侧重于对现实和时代的反映。
在三十年代初郑振铎译述希腊罗马文学时,已不仅仅从文学意义角度着眼,而且还具有社会学、美学的新的目光。他在《取火者的逮捕》的序中指出:神话里“记录着真实的古代人的苦斗的经过,以及他们的心灵上所印染的可能的争斗的实感与其他一切的人生的印象的”[3]187。所以,所谓神话的“美”,“并不是象绿玉白璧乃至莹圆的珠,深红的珊瑚般的只供欣赏赞叹之资的,而有着更深入的社会的意义”。[3]187而对普罗米修形象地喜爱也正是产生于社会意义的层面上,郑振铎在《取火者的逮捕》的序言中对于普罗米修斯的殉道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远在这一切之上,弹奏出永远的反抗的调子的,乃是预知者柏洛米修士(Prometheus)的故事。”[3]188“那伟大的为人类而牺牲的柏洛米修士,便是一切殉教者的象征。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墨翟,都是这一型式的人物。在个人主义的自私的空气,若烟雾腾腾,黑地昏天似的弥漫于一切之时,能不有感于这!”[3]188基于这样的认知,郑振铎在选取普罗米修斯神话作为创作题材的原因,主要也在于感慨于这一形象所表现出的坚定的反抗意志与悲壮的殉道精神。
在《取火者的逮捕·新序》中,郑振铎说:“题材只是一个,那就是:描写‘神’的统治的横暴与歌颂‘人’的最后胜利。虽然写的是古代的希腊神话,说的却是当时当地的事。”[9]185在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王瑶先生已经关注到这部小说强烈的现实感,认为这部小说“从人类对神权开始斗争到神权的趋于灭亡,指出了人类的必然胜利与神权的命运没落,根据旧文而渲染得异常壮美,随处都流露着作者自己的热烈的正义感。黑暗的惨绝,光明的渴求,残酷的神权高压,悲壮的牺牲者的歌声,终于使神权没落,正义重显。这正是反映了中国现实情况的作品,虽然写的是希腊神话。”[10]340在小说中,“人”与“神”的关系,既代表了人权与神权的对立,又代表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宙斯的形象被改造成“暴中之暴”“专制者中的专制者”,他以自己的力量自恣,“倚傍着权威与势力以残横加人而自喜!以他人的痛苦来满足你的心上的残忍的欲望!”[3]205他的对立面是一切被压迫者,神与人之间的矛盾便转化为压迫者与反抗者之间的斗争。当郑振铎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质问诸神:“你们的一部《神谱》,还不是一部蹂躏人权的血书么?”[3]208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鲁迅《狂人日记》中书中写满了“吃人”一般强烈的愤怒火焰,小说将原神话中的神反抗神的矛盾演化为借助神与人之间的矛盾普化为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焦点,具有明显的现实指涉性。
(三)殉道精神的升华
《取火者的逮捕》设置了一个极具震撼性和思考性的结尾:普罗米修斯和以宙斯为代表的所有神族一起被人类和其他反抗者投入到无底的深渊之中。作为救赎者的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推翻神的统治却最终也同他所推翻的众神一样的命运。作者在五十年代再版时对初版本的结尾做了删改,“现在看来,取火者的柏洛米修士,人类的好朋友,是不应该和‘神’之族一同被消灭的”[9]186。所以在新修改的版本中,郑振铎删去了“连柏洛米修士在内”的字样,“以及其他有关的辞句”[9]186。这修改后的新结局,是出于郑振铎对于普罗米修斯命运的重新思考,还是更多地基于对时代背景因素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最初的版本似乎更加符合郑振铎创作的初衷,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神来之笔,使得整篇小说的悲剧意蕴得以升华,整篇作品的思想价值得以彻底地呈现。
作为“先知者”的普罗米修斯可以预知人类和诸神的命运,必然也能够知晓觉醒的人类将会推翻神的统治,整个神界包括其自身终将面临落幕的结局。然而面对这样的结局却依然坚定地将象征着启蒙与革命的火种投向人间,帮助人类推翻了神的统治,无畏地走向毁灭。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在《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类学文集》中说:“我们必须用研究结尾的同样方法来研究小说世界:必须把它们正视为一个完整的意味深长的总体存在。”而“作品自身就是回溯性的,它同时是对精神蜕变的叙述和报偿。”[11]20《取火者的逮捕》的结局体现了以普罗米修斯为代表的英雄人物面对“生存还是毁灭”的命运抉择时付出生命的代价反抗暴虐的统治,在他们的身上凝聚了强烈的悲壮美。
朱光潜曾言:“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12]206在普罗米修斯身上体现的正是一种令人慨然的高尚的悲剧精神。而这种悲剧精神是建立在对可能发生的结局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彰显出悲剧精神的崇高美感。如果说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是一位呼唤自由与正义的文化英雄,那么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延伸了埃斯库罗斯和雪莱笔下的“殉道精神”和牺牲意志,体现出大气凛然的英雄气概以及威武不屈的坚韧意志的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最终超越其命运悲剧而提升到人类的崇高人格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郑振铎.希腊神话·序[M].上海:生活书店,1935.
[2] 郑振铎.严加管束·译者附言.文学[M].上海:上海文学社,1937.
[3]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序.郑振铎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4] [英]凯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5]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6] 郑振铎.血与泪的文学.郑振铎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7] 郑振铎.我们所需要的文学.郑振铎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8] 郑振铎.文学与革命.郑振铎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9] 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新序.郑振铎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0]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M]//王瑶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1] [法]勒内·基拉尔.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类学文集[M].刘舒,陈明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2]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Restatement of Prometheus "Stealing Fire"——With “The Arrest of Fire Stealer” by Zheng Zhenduo as Center
ZHANG Y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Prometheus is an important image in Greek mythology, and the image for modern Chinese writer. When introduced to China, Prometheus "stealing of the fire" contains the enlightenment consciousness, martyrdom and resistance As a researcher of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Zheng Zhenduo researches Prometheus myth and created a series of novels with the title of "The Arrest of Fire Stealer" which praised his heroic spirit and tenacious will by concentrating on “stealing Fire” in its value demands and spirit.
Key words:Prometheus; stealing fire myth; modern restatement; “make fire's arrest”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6)04-0065-05
收稿日期:2015-08-02
基金项目: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青年项目: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作家的神话意识(201307)
作者简介:张岩(1979—),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