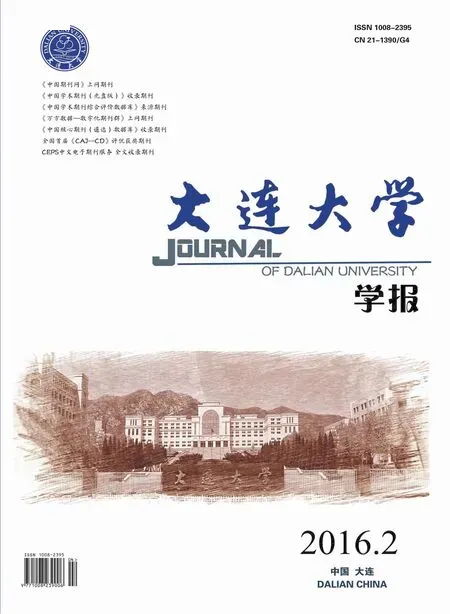解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悲剧本质
——人的生存困境与冲突
屈荣英,刘利翔(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解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悲剧本质
——人的生存困境与冲突
屈荣英,刘利翔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是一位具有美国南方特色的伟大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带有哥特元素的南方小说。小说是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通过他人的回顾间接对艾米丽小姐进行叙述,暗示了艾米丽小姐悲剧的一生。作品从人的外在生存真实困境和内在生存真实困境角度展现了人与自身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人与观念的冲突。
关键词:悲剧;生存困境;冲突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创作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带有哥特式特点的南方悲剧小说。小说以旁观者的口吻进行叙述,并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通过客观环境和叙述者的主观猜想向读者暗示了艾米丽小姐悲剧的一生。这部小说以时间倒错叙事手法对悲剧本身重构,还通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对艾米丽进行分析。小说中的象征隐喻把这部充满悲剧色彩的哥特式南方小说与西方现代化悲剧本质相联系。
希腊式悲剧“涉及人类命运的人的痛苦、灾难、死亡是与上天统治的宇宙的混乱紧密相关”[1]46。而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悲剧“把爱国主义与拓展人的生存的自由空间这一根本方面紧密结合”[1]84。可是福克纳笔下的悲剧从本质上来看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现代工商文明在南方的崛起和对南方的侵袭所带来的个人的生存困境。“现代社会悲剧的中心主题是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异化是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困境。”[1]109正如奥尔在谈到悲剧发展时所说:“希腊模式基本上是神性的,文艺复兴模式主要是贵族的,而现代模式根本上是社会的”[2]。
福克纳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通过描写人的生存外在真实处境和内在真实处境展现出人与自身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人与观念的冲突和经济上的冲突。反过来这些冲突起到了悲剧增强的效果。南方出身的威廉·福克纳在小说中充满了对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憎恨和对故乡往昔的怀念,但是他深知南方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从这个层面来看,作者本身所具有的矛盾冲突也或多或少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体现。
一、社会和艾米丽的外部冲突
小说一开头就叙述了“艾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3]99,这是作者一种悲剧暗示,“在悲剧的两个基本观念即牺牲与死亡方面,是古今相同的”[1]107。并以此为序通过“无名的叙述者”一步步对艾米丽的死因展开探索,同时也是对悲剧性的生存困境做出预表。作者看似不经意地对艾米丽的住宅进行描写,实际上是想借此展示艾米丽小姐周围环境上的客观困境。而艾米丽小姐可以称得上是贵族气派的房子是往昔南方奴隶制繁荣的缩影,但与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格格不入。更进一步的生存困境在现代工商业体制和旧奴隶制体制的冲突中显现。“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轮形花纹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它们涂抹的一干二净。只有艾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3]99汽车间和轧棉机无疑代表了现代工商业,而艾米丽小姐破败的木屋毫无生气,却还依然存在,表达了南方奴隶制虽然已经被北方文明的工商业化打败,但并不服输,想要用自身的存在表明自己的高贵和等级性。这种时代的反差产生了现实的冲突,而历史大环境的冲突也体现在艾米丽小姐身上。另一方面,冲突还产生于南方人情社会和北方竞争社会的反差。当艾米丽小姐父亲去世的时候,当时镇上的人为了照顾艾米丽小姐,精心编造了一个谎话,谎称她的父亲曾经为镇子做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免除了艾米丽小姐的税。而之后“等到思想更为开明的第二代人当了镇长和参议员时,这项安排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满。那年元旦,他们便给她寄了一张纳税通知单。”[3]100在大环境的转变中,从前具有人情味的社会在老一代人的渐渐离去和新价值观的侵袭之下,逐渐变得冷漠和毫无同情心。究其本质“随着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迅速推进,高度技术化,物质化,非精神化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在心与物的关系方面,心与物的对立越来越严重。”[1]146人为了物质忘却人的本性。
二、观念冲突
此外,艾米丽小姐生存困境的外部因素,还包括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对她思想上和行为上的桎梏,这种冲突也是造成艾米丽小姐一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艾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3]100。从这里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小镇人们的观念里,艾米丽小姐对于人们来说,只是保留下来的一个传统,只是一套南方旧社会体制的代表和象征和用来纪念的一个牌位,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追求幸福,有血有肉的人。而人们也只愿意相信,艾米丽小姐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人们心中的传统和观念而活,一切和人们想法不符合的行为和想法如果在她身上出现,即是打破传统,违反人们的意志,包括后来人们对她恋情的评论。但是,艾米丽小姐作为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也想要追求自己的幸福。艾米丽小姐心中向往着爱情,也向往着能有自己的幸福,但是来自父亲的专横独权使自己在大好年华却不能有正常人享有的恋爱权利。后来父亲去世之后出现的北方工头的背叛,对追求幸福的艾米丽小姐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最后为了挽留自己的爱人和对抗小镇人们异样的目光不得不将爱人以一种变态的方法留在自己的身边。这种观念的压制和自身的需求最终导致了无可避免的冲突。
三、环境冲突
对于艾米丽小姐来说,对她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那位只在画中出现而从未真正出现的父亲。这位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但他对于艾米丽的影响却从未消失过,始终如诅咒一般不肯离去。正如画中描述的:“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腿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着艾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门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3]104从画中可以判断,艾米丽父亲生前死后都掌握着女儿的命运,完全是一副专横的暴君的嘴脸。他手中的马鞭正是父亲在家庭中地位的体现,不仅用马鞭来维护自己家中的地位同时也用它来赶走艾米丽小姐的追求者,并认为所有的追求者都配不上自己的女儿。从另一面表现出她的父亲只把艾米丽小姐看做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并没有真正关注艾米丽是否能得到幸福的婚姻。地位和等级始终是她父亲最为关心的事情,并在生前死后一直影响着艾米丽。这种像君主一样的父亲造就原因是由于南方庄园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和美国南方保守的加尔文主义。父亲是庄园主同时也是家庭的首脑,是家中无可争辩的主宰者,这就使艾米丽的父亲对女儿拥有绝对的权利,而她丝毫没有反抗的可能。另外,基督教加尔文教义也从宗教角度维护父亲作为家长的统治地位。这就使艾米丽小姐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传统因素方面,都无法对父亲做出的决定做出反抗。环境的影响注定了她的悲剧一生。从表面看来这只是单方面的压制,不具有冲突,但是,艾米丽小姐毕竟是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没有感情,一方面只能顺从父亲的安排,另一方面心中的矛盾和纠结的情绪最终在父亲去世时完全崩溃了。“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女们都准备到她家拜望,表示哀悼和愿意接济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习俗。艾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他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他们,她的父亲并未死。”[3]104能看出她对父亲的爱和恨在她父亲死亡之后变成了一种绝望和崩溃。这种冲突是一种隐性的冲突,作者没有直接在小说中道出原因,但通过以上描述可以分析出来艾米丽小姐对父亲感情的复杂性和内心的挣扎。无论爱还是恨,都在她父亲死的时刻彻底爆发,神志变得不正常。
四、经济冲突
如果说社会、环境、观念上的生存困境是有关生存方式间接的影响,那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经济原因。由于父亲去世的时候没有给艾米丽给下任何财产,使得她在生活上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对于一个上流社会的小姐来说,自身基本上没有谋生的本领,一旦没有了经济支柱,生活基本上无法保证,但又不可能放下身段去自谋生路,这和她的贵族身份不符。这种贫困还体现在她“连人带马”打败了那些想要收税的官员一样,如果经济上不是处于困境,艾米丽小姐也不会不付清税。她经济上的拮据也体现在小镇人们对她的同情。“在楼下的一间房里,她临时布置了一个画室,沙多里斯上校同时代人全都把女儿,孙女送到她那里学画,那样的按时按刻,那样的认真精神,简直同礼拜天把她们送到教堂去,还给她们二角五分钱硬币准备放在奉献盆子里的情况一模一样。”[3]109-110对于小镇人心目中的“大家闺秀”和“纪念碑”,由于经济上不能实现自足,镇上的老一代人是非常清楚的。之所以把女儿和孙女都送到她那里去学习绘画可能并不是因为她的画技有多高,可能只是类似于“沙多里斯”那个时代声称她的父亲曾经为小镇做出过贡献的善意谎言,因为人们知道一个真正“贵族”是不会接受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即便是已经没落了。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来,艾米丽小姐生活上是拮据,因为人们都知道她父亲“除了房子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而人们都不愿意看见这个“纪念碑”因为贫困失去仅有的贵族标志,卖掉自己的房产。在福克纳的另一部约克纳帕塌法县小说《喧哗和骚动》中,杰森最后因为经济上的困境,不得不不把自己家的庄园卖掉,以至卖掉之后这一有名望的贵族从此彻底消失了。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艾米丽小姐一直没有结婚,致使经济上没有依靠。
五、自身冲突
虽然福克纳在整部小说中,并没有对艾米丽小姐进行心里描写,但并不代表艾米丽自身并没有想法。通常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南方妇女基本上是“没有本体,没有独自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只是被别人所确定、所描绘、所解释、所拥有、所热爱、或者被别人所仇恨。”[4]最能体现艾米丽自身冲突的情节,是从她的情人荷默·伯隆开始。在这之前父权在艾米丽身上压制是冲突的根源。由于父亲赶走艾米丽所有的追求者,致使她在正当妙龄却无法拥有正常人的权利,心里被极度地压抑着,反而更加激起了艾米丽想要获得自己爱情的渴望。当荷默·伯隆出现时,艾米丽觉得自己的幸福即将来临,但这只是她悲剧的开始。在摆脱了父亲的桎梏之后,艾米丽开始了自己的爱情之旅,虽然作者没有直接叙述艾米丽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但读者从其中能隐约感到,艾米丽终于可以过上正常不受压抑的生活,可以自由享受爱情了。但之后冲突便达到了最高点,首先是从外到内,然后是内心中激烈冲突。“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艾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因为妇女们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3]105-106这些“无名的叙述者”的间接叙述,告诉了读者人们对于艾米丽小姐家族传统的猜测以及镇上老一代人们对这场婚姻的看法。“可怜的艾米丽,她的亲属应该来到她的身边”[3]106。这些叙述很明显地表达出来人们对这位“大家闺秀”和“纪念碑”的身心和情感并不感兴趣,只在意这位传统和义务的代表不能够也不应该和一位令他们憎恨的北方佬在一起。这些外部的力量和那位死去多年的父亲一样,时时刻刻告诫艾米丽小姐应该是一位高贵的“大家闺秀”。而艾米丽小姐内心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决心不再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决意追求自己的幸福。随后这种冲突不断加大,首先是浸礼会牧师在小镇妇女的要求下拜访了艾米丽,但收效甚微,紧接着便搬来了两个堂姐妹过来劝阻,希望能够借此机会使艾米丽放弃这段恋情以保住家族的名誉,而这些压力对艾米丽小姐造成的压力并不足以使冲突爆发。使艾米丽小姐自身冲突爆发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荷默在众人面前说自己喜欢男人而且无意结婚。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这里,艾米丽小姐彻底崩溃了,自身的冲突到达了顶点并且爆发了。她一直以来所坚信的幸福再次破灭了,并且也是永远的破灭了。她知道,自己即将永远的失去自己的情人和生活的希望,因此内心充满无限绝望。如果不做出一些行动,就不可能留住荷默,而活着的荷默一定会再一次离开她。所以最后,她选择了永远留住荷默——用毒药杀死他。让情人活着,情人便离他而去,留下的只有无限的悲伤,而让情人死去,起码可以拥有他的尸体,这便是在外界生存困境和内部生存困境双重重压之下的混乱而疯狂的逻辑。冲突的最终形态以精神上的病态和疯狂展现。艾米丽小姐是各种冲突之下的牺牲品,这也恰恰符合了现代社会悲剧要求,既牺牲和死亡。
六、结 语
艾米丽小姐悲剧的一生通过对比的手法展现了内心的痛苦,即使是在各种冲突和那样的环境中仍然顽强地渴望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同时还表现出她的人性一面。而这部小说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玫瑰”是对艾米丽小姐悲剧一生的诠释,既美丽和枯萎,是一种对南方女性的同情和钦佩。在此作者福克纳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送出“玫瑰”以祭逝人。
参考文献:
[1] 任生名.西方悲剧论稿[M].上海:上海外国语出版社,1998.
[2] John Orr. Tragic Drama and Modern Society[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89:12.
[3] 威廉·福克纳.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4] 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196.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gic Nature of A Rose for Emily: Human Life Plights and Conflicts
QU Rong-ying, LIU Li-xia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American writer William Faulkner is a great writer with southern traits. There are Gothic elements in his short story A Rose for Emily which sets in American Civil War period. The story indirectly narrates the life of Miss Emily by people’s reminiscence and implies the tragic life of Miss Emily. The story displays the conflicts between man and self, man and society, man and environment and man and outlook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uter life plights and inner life plights.
Key words:tragedy; life plight; conflict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6)04-0057-04
收稿日期:2015-10-12
作者简介:屈荣英(1971—),女,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刘利翔(1983—),男,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