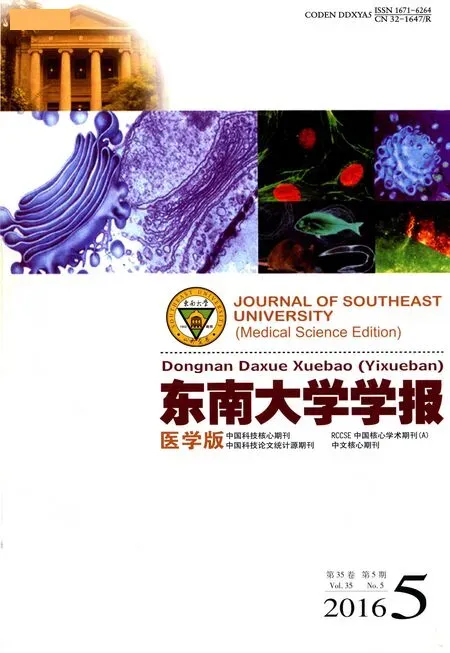细菌-脑-肠轴理论体系的建立
白宇,胡云霞,陈俊伟,于希忠,方南元
(1.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中医药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综 述·
细菌-脑-肠轴理论体系的建立
白宇1,胡云霞1,陈俊伟1,于希忠2,方南元2
(1.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中医药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肠道菌群可以经脑-肠轴对大脑产生影响,因而形成了细菌-脑-肠轴这一概念。细菌-脑-肠轴的作用在代谢性疾病、精神性疾病、功能性胃肠病等疾病中均有体现,所涉及的途径包括肠黏膜屏障、神经信号通路、5-羟色胺和色氨酸代谢通路、免疫应答反应、胃肠激素、细菌代谢产物、基因调控、HPA轴等。本文作者就菌-脑-肠轴这一理论的形成和理论基础作一综述。
细菌-脑-肠轴;肠黏膜屏障;胃肠激素;短链脂肪酸;综述
脑-肠轴是大脑和胃肠道之间紧密连接的双向神经体液交流系统。过去对脑-肠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状态与胃肠道功能的互相影响方面。然而最新的研究证据表明肠道菌群与大脑之间可以通过脑-肠轴进行沟通并调节大脑的发育和改变宿主的行为。这一发现重新定义了肠道菌群与脑-肠轴的关系,表明肠道菌群可能通过脑-肠轴改变脑功能影响神经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进而形成了细菌-脑-肠轴这一新的概念体系[1]。细菌-脑-肠轴理论体系的建立重新阐释了众多疾病尤其是代谢性疾病和精神异常性疾病的发生机制,也为其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
1 肠道菌群对大脑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不仅可以影响肠道生理,而且还可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首先,临床研究表明肝性脑病可以通过抗生素治疗来达到治愈的目的;而炎症性肠病的患者,除了肠道菌群的结构异常外还常常伴有精神障碍[2]。其次与正常动物相比,无菌小鼠在焦虑行为、自主控制和记忆力方面均有显著差异。第三,肠道菌群能干预宿主早期的脑部发育情况并对宿主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实验发现,与正常小鼠相比无菌小鼠能自主活动较多而焦虑样行为较少,但是较早暴露于有菌环境中的无菌小鼠行为更趋向于正常的SPF小鼠[3]。基于宏基因组学研究结果则显示,焦虑、抑郁、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和肠易激综合征等精神行为异常的患者与健康人相比均存在菌群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最后,益生菌治疗已被证明可以改变大脑的行为。例如,双歧杆菌str.NCC3001能改善中度结肠炎小鼠所表现出的焦虑样行为,而益生菌治疗也可以不同程度改变因母鼠与子鼠分离或实验性心肌梗死诱导出的抑郁样症状,增加小鼠之间的群体互动。
上述证据不仅表明细菌-脑-肠轴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对中枢神经功能和宿主整体行为具有强烈的影响。目前用于肠道菌群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用抗生素干预、粪便细菌移植、益生菌治疗和无菌动物模型[4]。尽管上述的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但是仍然取得了很多可喜的进展。细菌对人中枢神经产生影响进而改变情绪和行为的能力也在逐渐被研究人员所重视。
2 肠道菌群与脑-肠轴的互通途径
肠道菌群之所以能对大脑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有赖于肠道菌群和大脑之间互通的信号通路。肠道菌群和大脑之间的沟通途径是一个复杂的网络,中间涉及免疫、神经、内分泌等多个系统的相互交叉作用,而确切的机制尚不明确。
2.1 肠黏膜屏障
肠道是人体与肠道菌群接触最直接的器官,而肠黏膜更是与肠道菌群接触最直接的组织,因此肠黏膜屏障是细菌和脑-肠轴之间互通的第一站。在肥胖症中,肠黏膜通透性的增加能导致内毒素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LPS)通过肠黏膜屏障进入宿主血液或组织当中引起内毒素血症[5-6]。在肠易激综合征、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身上同样也发现了肠上皮通透性改变的情况[7-8]。反之,肠道菌群对肠屏障功能亦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例如在肥胖症和2型糖尿病中,肠道菌群和益生菌可以经由内分泌细胞改善内毒素血症,减轻炎症反应。肠道菌群对肠黏膜屏障的保护功能很可能是通过一些内分泌细胞分泌的内分泌肽来完成的,例如胰高血糖素样肽-2(glucagon-like peptide-2,GLP-2)可以通过3种途径维持肠黏膜屏障功能[9-10]:(1) 诱导肠上皮细胞增殖,从而影响肠营养作用;(2) 上调肠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增加上皮细胞的连接程度;(3) 控制潘氏细胞生成抗菌肽来参与免疫调控,而抗菌肽则涉及到宿主菌群的分离,从而维持肠黏膜屏障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GLP-2抑制剂之后,益生菌虽然还能引起肠道菌群结构的改变,但是肠黏膜屏障的改善作用却完全被抑制。这一系列实验说明在肥胖症和2型糖尿病中,L细胞和肠道菌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改变肠壁黏膜的通透性和炎症反应程度。
2.2 神经信号通路
消化道黏膜下具有丰富的神经网络结构,其拥有的神经细胞与头脑的神经细胞数量相当,因此肠黏膜神经丛又被称为“肠脑”或“第二大脑”。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和肠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s,ENS)之间的交互作用主要是经由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ANS)和外周神经系统来实现的。益生菌、乳酸杆菌可以作用于肠道感觉神经的离子通道上,从而影响肠道的运动和疼痛感知。在无菌小鼠的肠管内,感觉神经元的肌间神经丛的兴奋性明显降低,但是对无菌小鼠的肠管移植了正常的肠道菌群后,后超极化的感觉神经元的兴奋性又会逐渐增加[11]。有报道显示,鼠李糖乳杆菌(JB-1)种植到空肠后可以导致交感神经的传入进一步被激活,主要表现为自发性的兴奋频率增加[12],而长期予以鼠李糖乳杆菌L治疗可以引起脑内GABA受体的区域依赖性表达,并且可以经由小鼠迷走神经信号通路降低应激诱导的皮质酮水平,减轻焦虑和抑郁样症状。因此脑-肠轴可能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机制轴,而是一个长久的动态系统,调整内外环境和因素,干预生理和心理事件。
2.3 5-羟色胺、色氨酸代谢通路
5-羟色胺是人体内一种具有神经功能的生物胺,在中枢神经系统和胃肠道中均有表达。5-羟色胺主要参与肠道内分泌和肠蠕动的调节以及疼痛的感知,对情绪与认知的调控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故而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已被广泛应用于情感和胃肠道疾病如肠易激综合征的治疗中。色氨酸是一种必需氨基酸,必须在饮食中充分供应。微生物与色氨酸代谢之间关系的证据已经在无菌小鼠的研究中得到体现。在生命早期缺乏菌群的时候,会导致血浆色氨酸水平的升高而犬尿氨酸/色氨酸的比例降低,并且诱导增加成年后海马区5-羟色胺水平,这些现象即使是将无菌小鼠断奶后置于有菌的环境中依然存在。益生菌双歧杆菌则可以影响色氨酸代谢的代谢,例如在高血氨症时,摄入瑞士乳杆菌的治疗方法,可以明显降低大鼠炎症标志物水平,减少血清素代谢,恢复认知功能,改善焦虑样行为[13-14]。
2.4 免疫应答反应
肠道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是外来的病原体和内部的生理环境之间的一个重要的防御屏障,与肠道相关淋巴组织一起组成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动物体上,免疫系统可以通过识别感染性微生物,激活中枢免疫应答的方法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改变宿主行为,引起食欲减少和疲劳等精神症状相关的疾病行为。空肠弯曲菌在亚临床剂量给药时可导致小鼠焦虑样行为;在外周予啮齿类动物的促炎细胞因子则可以诱导出动物如抑郁、睡眠障碍。目前肠道菌群对局部和远端免疫系统的影响已被逐渐发现,在健康个体中微生物会不断校准并强化免疫系统以对抗潜在的感染。众所周知,抗生素治疗则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15],这种由抗生素引起的菌群失调也被发现可参与远端免疫系统的初始启动环节。口服人类婴儿双歧杆菌-35624可以增强人外周血中IL-10的表达水平[16-17],而无菌小鼠单核吞噬细胞产生I型和II型干扰素(IFN)的能力较有菌小鼠减弱,这也直接导致了无菌小鼠抗病毒免疫缺陷,这也从侧面说明应用微生物信号在远端的免疫系统中的地位[18]。免疫系统受损的患者常常伴有因抗生素治疗引起肠道微生态失调的情况,这种治疗会降低患者的免疫功能并可能引起致病菌数量的上升和转移,反而增加全身性感染的机会。
2.5 胃肠激素
肠道也可以经由激素信号通路参与肠内分泌细胞释放的肠肽与大脑进行沟通,而后者能够直接作用于大脑。基于无菌小鼠和益生菌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也参与到了肠道激素调节机制当中。NPY就是一个被认为参与了细菌-脑-肠轴相互作用的目标激素,它对于微生物的调控作用非常敏感,且同时具备了作为神经系统和内分泌信使的双重功效。在细菌-脑-肠轴沿线上的多个部位均可以发现NPY的表达,并且NPY具有调节情绪、应激复原和调节胃肠运动的广泛功能[19]。肠道菌群和激素分泌的影响是相互的,例如去甲肾上腺素浓度应激性升高可以刺激共生的大肠杆菌等革兰阴性菌的生长,而NPY也被发现对包括大肠杆菌、粪肠球菌、嗜酸乳杆菌在内的多种肠道细菌具有直接抑制作用。胃肠道激素在细菌-肠-脑轴反应中的作用是一个要求更多关注的全新研究领域,然而关于胃肠激素参与细菌-脑-肠轴沟通潜在机制的研究依然非常有限。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很有可能为脑-肠轴紊乱性相关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思路和靶点。
2.6 细菌代谢产物
大肠内的细菌在厌氧条件下会将未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发酵成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SCFAs是细胞代谢中的一个主要的能量来源,特别是在早期的大脑发育阶段。研究发现,短链脂肪酸信号在肠道的受体有游离脂肪酸受体-2(FFAR2)和游离脂肪酸受体-3(FFAR3),这些受体参与的控制食欲的激素包括PYY和GLP-1等,而FFAR3同时还存在于大脑中。这也提示我们很可能存在一条潜在的通路影响短链脂肪酸的形成和食物摄入。SCFAs参与脑肠轴调节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是它可以穿过血脑屏障。血液循环中的短链脂肪酸如丁酸和丙酸可以通过单羧酸转运蛋白进行远距离转运,穿过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一旦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它们依旧可以通过单羧酸转运蛋白转运至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口服天然果聚糖作为SCFA供体后大鼠脑组织中丙酸受体FFAR3表达升高也从侧面说明这一问题[20]。短链脂肪酸与FFAR3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对脑组织引起深刻的反应,例如脑室内直接注射丁酸钠可引起额叶皮层和海马区短暂瞬时的组蛋白乙酰化,同时引起BDNF表达的动态变化,从而导致小鼠产生抗抑郁样行为反应[21]。虽然短链脂肪酸到达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的影响可能是相当微小的,但是由肠道菌群慢性转运至中枢神经的短链脂肪酸是可以慢性累积的,因此短链脂肪酸有可能对大脑产生持久而稳定的作用。
2.7 宿主基因调控
人类的肠道微生物是出生后从环境中获得的,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环境因素与宿主基因相互作用去塑造遗传表型,同时也是一个由宿主基因决定的属性。人类微生物群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已取得众多成果,新一代测序和相关的组学技术也逐渐应用到其中[22]。这些成果不仅提供了人类健康和疾病状态下微生物组成的相关重要的信息,同时也为研究其对宿主代谢和生理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基础。不同成人之间肠道菌群可以出现明显的多样性差异,而家庭成员之间检测到的菌群谱往往比无关的人有更高的相似度[23-25]。目前认为肠道菌群的家族相似性主要是由共享环境因素如饮食的偏好等来决定的。一些针对性的研究方法为宿主基因对微生物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例如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相比产甲烷的史氏甲烷短杆菌一致率更高[26],而在特定的基因位点层面比较研究不同人群所含微生物指纹的特异性也显示宿主基因和微生物之间存在相互的作用[27]。对于人类,肠道微生物的遗传性是通过有效的双生子研究来评估的。这一研究在单卵双生和异卵双生间做出对照,辨别出了最易遗传的菌群类目-Christenswnellaceae。Christenswnellaceae同时与具有遗传性的细菌以及产甲烷古生菌都构建了网状系统,多见于较低体重指数的人群中[28]。潜在于肠道微生物遗传之下的宿主等位基因点一旦被发现,我们就可以去了解这些健康相关的细菌的性质,并最终利用其促进人体的健康。
2.8 HPA轴
肠道细菌和HPA之间的直接联系来自于2004年的一项研究,实验人员发现无菌小鼠和正常SPF小鼠相比,在面对束缚应激时表现出夸张的皮质酮(CORT)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水平。这一跨时代的发现使得神经学家开始重视细菌在对中枢神经产生影响的重要性。在随后几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细菌不仅在生命早期对HPA轴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能在随后的生命过程中持续发生作用。HPA轴在生命的初期尚未发育成熟,需要在产后继续发育,而这段时间正好和肠道菌群开始定植的时间重合,使得两者在时间上有了相互影响的机会。母婴分离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新生儿压力应激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组成的长期变化,这很有可能是导致大鼠后来长期出现异常应力反应和压力相关性行为的原因。而在早期的应激时期予以乳酸杆菌属益生菌治疗被证明可以正常化基础皮质醇水平,而母婴分离之后皮质醇水平又再度出现升高,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之前研究结果。人在压力应激的情况下肠黏膜的通透性会增加,也给了肠道菌群透过肠黏膜直接接触免疫细胞和肠道神经元细胞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在应力条件下微生物通过免疫系统和肠神经系统影响中枢神经的潜在途径。在这一设想的指引下,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提前予以大鼠益生菌嗜酸乳杆菌治疗可以改善由于压力引起的肠道通透性升高,并且能够抑制HPA轴的高反应性[29]。
3 总结与展望
肠道菌群对人类生理病理的影响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还发现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脑-肠轴来影响大脑的功能之后。尽管肠道菌群对脑-肠轴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针对其机制的研究却未能取得预期的快速进展。这是因为脑-肠轴与肠道菌群的分子信号通路研究取决于精确的高通量鉴定技术来取得肠道菌群的微生物构成。第二代测序技术(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是目前较为先进的基因测序技术。虽然有利有弊,但是在这一技术的支持下宏基因组学技术、宏转录组技术、16S rDNA等测序技术目前已广泛用于肠道菌群结构的分析中。在此基础上,终有一天肠道菌群经脑-肠轴调节人类行为的机制将被彻底阐明。
不同微生物在胃肠道不同部位的富集程度不同,因此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特定位点的肠道菌群有可能对脑肠轴产生特定的影响,因为胃肠道的每一个位点不仅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吸收不同种类的营养物质的能力[30-31]。肠道菌群在特定位点对宿主是否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是一个研究的难点,也许只有通过肠镜在肠道不同部位收集粪便和组织样本的方法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1] de PALMA G,COLLINS S M,BERCIK P,et al.The microbiota-gut-brain axis in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stressed bugs,stressed brain or both?[J].J Physiol,2014,592(14):2989-2997.
[2] COLLINS S M,SURETTE M,BERCIK P.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and the brain[J].Nat Rev Microbiol,2012,10(11):735-742.
[3] DIAZ H R,WANG S,ANUAR F,et al.Normal gut microbiota modulates brai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J].Proc Natl Acad Sci U S A,2011,108(7):3047-3052.
[4] BUROKAS A,MOLONEY R D,DINAN T G,et al.Microbiota regulation of the Mammalian gut-brain axis[J].Adv Appl Microbiol,2015,91:1-62.
[5] BRUN P,CASTAGLIUOLO I,di LEO V,et al.Increased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in obese mice:new evidenc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J].Am J Physiol Gastrointest Liver Physiol,2007,292(2):G518-G525.
[6] AMAR J,SERINO M,LANGE C,et al.Involvement of tissue bacteria in the onset of diabetes in humans:evidence for a concept[J].Diabetologia,2011,54(12):3055-3061.
[7] CAMILLERI M,MADSEN K,SPILLER R,et al.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in health and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J].Neurogastroenterol Motil,2012,24(6):503-512.
[8] JULIO-PIEPER M,BRAVO J A,ALIAGA E,et al.Review article: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orders,a controversial association[J].Aliment Pharmacol Ther,2014,40(10):1187-1201.
[9] LEE S J,LEE J,LI K K,et al.Disruption of the murine Glp2r impairs Paneth cell function and increases susceptibility to small bowel enteritis[J].Endocrinology,2012,153(3):1141-1151.
[10] CANI P D,POSSEMIERS S,van de WIELE T,et al.Changes in gut microbiota control inflammation in obese mice through a mechanism involving GLP-2-driven improvement of gut permeability[J].Gut,2009,58(8):1091-1103.
[11] FOSTER J A,MCVEY NEUFELD K.Gut-brain axis:how the microbiome influenc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J].Trends Neurosci,2013,36(5):305-312.
[12] PEREZ-BURGOS A,WANG B,MAO Y K,et al.Psychoactive bacteria Lactobacillus rhamnosus(JB-1)elicits rapid frequency facilitation in vagal afferents[J].Am J Physiol Gastrointest Liver Physiol,2013,304(2):G211-G220.
[13] DESBONNET L,GARRETT L,CLARKE G,et al.The probiotic Bifidobacteria infantis:an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antidepressant properties in the rat[J].J Psychiatr Res,2008,43(2):164-174.
[14] LUO J,WANG T,LIANG S,et al.Ingestion of lactobacillus strain reduces anxiety and improves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hyperammonemia rat[J].Sci China Life Sci,2014,57(3):327-335.
[15] DESHMUKH H S,LIU Y,MENKITI O R,et al.The microbiota regulates neutrophil homeostasis and host resistance toEscherichiacoliK1 sepsis in neonatal mice[J].Nat Med,2014,20(5):524-530.
[16] KONIECZNA P,AKDIS C A,QUIGLEY E M,et al.Portrait of an immunoregulatory Bifidobacterium[J].Gut Microbes,2012,3(3):261-266.
[17] KONIECZNA P,GROEGER D,ZIEGLER M,et al.Bifidobacterium infantis 35624 administration induces Foxp3 T regulatory cells in human peripheral blood:potential role for myeloid and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J].Gut,2012,61(3):354-366.
[18] ABT M C,OSBORNE L C,MONTICELLI L A,et al.Commensal bacteria calibrate the activation threshold of innate antiviral immunity[J].Immunity,2012,37(1):158-170.
[19] HOLZER P,REICHMANN F,FARZI A.Neuropeptide Y,peptide YY and pancreatic polypeptide in the gut-brain axis[J].Neuropeptides,2012,46(6):261-274.
[20] BONINI J A,ANDERSON S M,STEINER D F.Molecular cloning and tissue expression of a novel orphan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from rat lung[J].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1997,234(1):190-193.
[21] SCHROEDER F A,LIN C L,CRUSIO W E,et al.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of the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sodium butyrate,in the mouse[J].Biol Psychiatry,2007,62(1):55-64.
[22] COTTER P D,STANTON C,ROSS R P,et al.The impact of antibiotics on the gut microbiota as revealed by high throughput DNA sequencing[J].Discov Med,2012,13(70):193-199.
[23] GOODRICH J K,WATERS J L,POOLE A C,et al.Human genetics shape the gut microbiome[J].Cell,2014,159(4):789-799.
[24] Structure,function and diversity of the healthy human microbiome[J].Nature,2012,486(7402):207-214.
[25] QIN J,LI R,RAES J,et al.A human gut microbial gene catalogue established by metagenomic sequencing[J].Nature,2010,464(7285):59-65.
[26] HANSEN E E,LOZUPONE C A,REY F E,et al.Pan-genome of the dominant human gut-associated archaeon,Methanobrevibacter smithii,studied in twins[J].Proc Natl Acad Sci U S A,2011,108(Suppl 1):4599-4606.
[27] FRANK D N,ROBERTSON C E,HAMM C M,et al.Disease phenotype and genotype are associated with shifts in intestinal-associated microbiota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J].Inflamm Bowel Dis,2011,17(1):179-184.
[28] GOODRICH J K,WATERS J L,POOLE A C,et al.Human genetics shape the gut microbiome[J].Cell,2014,159(4):789-799.
[29] AIT-BELGNAOUI A,DURAND H,CARTIER C,et al.Prevention of gut leakiness by a probiotic treatment leads to attenuated HPA response to an acute psychological stress in rats[J].Psychoneuroendocrinology,2012,37(11):1885-1895.
[30] SIMREN M,BARBARA G,FLINT H J,et al.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functional bowel disorders:a Rome foundation report[J].Gut,2013,62(1):159-176.
[31] NAGPAL R,KUMAR M,YADAV A K,et al.Gut microbiota in health and disease:an overview focused on metabolic inflammation[J].Benef Microbes,2016,7(2):181-194.
2016-05-11
2016-07-06
国家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1403376);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BK20130955)
白宇(1988-),男,江苏南京人,医学博士。E-mail:512538869@qq.com
方南元 E-mail:lionlog@126.com
白宇,胡云霞,陈俊伟,等.细菌-脑-肠轴理论体系的建立[J].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6,35(5):781-785.
R333
A
1671-6264(2016)05-0781-05
10.3969/j.issn.1671-6264.2016.05.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