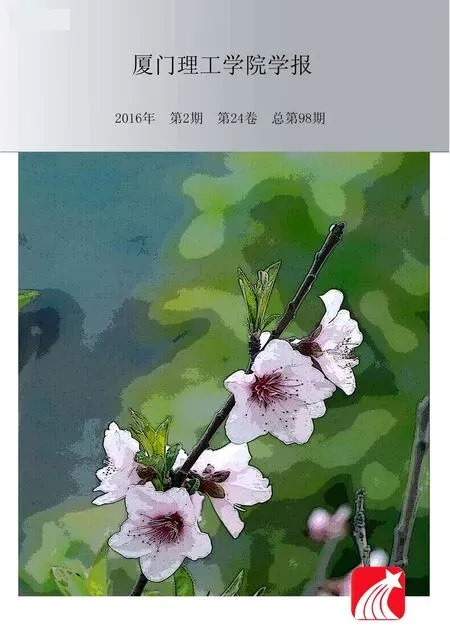论苏童《黄雀记》的逃亡意象
孙媛媛,韦丽华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论苏童《黄雀记》的逃亡意象
孙媛媛,韦丽华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逃亡”作为苏童小说人物一以贯之的行为特质,在《黄雀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黄雀记》以“梦”“绳子”“水塔”“魂”为核心意象丰富了逃亡者的形象内涵,以3位主人公逃亡的命运轨迹展现了逃亡者因对现实的焦虑和愤怒而走向自闭、隐忍、漂泊的逃亡生活和宿命的悲剧结局,以贯穿人物命运的逃亡动作和欲望机制诠释了逃亡者的悲剧本质——主体通过逃亡获得短暂的安稳完满后,因现实缺失的不可抹灭,他们最终依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悲剧色彩。结合拉康的欲望辩证法探讨人物逃亡悲剧的成因,不难发现主体逃亡表象背后欲望追寻的实质。
[关键词]苏童;《黄雀记》;逃亡;意象;欲望辩证法
苏童是当代作家中富有才子之气且成就颇丰的一位。以多变的叙事技巧以及颓靡的抒情风格享誉文坛。而学界对其小说内容和主题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苏童小说内容和主题的研究,主要可分为逃亡与还乡,童年与成长、红颜与悲歌、历史与宿命四大类。”[1]逃亡作为其小说的主题之一,现有研究主要从现实、社会、文化三个层面进行解读。在现实层面,主要表现为“对固有现实生活的摆脱。”[2] 13在社会层面,“更主要地表现为对既定生活轨道的和既定命运的恐惧、拒绝、与反抗。”[2] 14在文化层面,分析逃亡是“一种文化逃亡,一种人类在灾难和死亡困境中力图精神得救的图景,一种人类自己制造灾难和从灾难中逃亡的情景。”[3]本文从哲学层面解读苏童小说的“逃亡”,结合拉康的欲望理论,探讨现代社会主体的逃亡走向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一、苏童式的“逃亡”
“《黄雀记》的‘香椿树街’是苏童和他成长的南方建立起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文学想象。从《桑园留恋》开始到《黄雀记》,苏童已经花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去经营他的‘香椿树街’。”[4]“香椿树街”作为苏童文学想象的一块记忆园地,在向我们呈现了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身上所具有的不安定的情感世界和混乱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展现了在那条狭窄的南方老街里,暗涌着流淌不息的少年血和他们在潮湿的空气中发了芽又溃烂了的年轻的生命成长。在这种轻车熟路的创作想象中,使我们在《黄雀记》里依然能感受到似曾相识的冰冷气息。正如苏童自己说的那样,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香椿树街。而“逃亡”作为苏童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人物姿态,在《黄雀记》也得以充分体现。在这里,“逃亡”从人物的形而下的行为姿态提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姿态,从而具有哲学性的普遍意蕴,丰富了其“逃亡”主题的哲学内涵。
在《黄雀记》中,从三人间的作恶游戏,演变成一起令人发指的强奸案,又悄无声息地转换成冤狱案,最后变成一桩令人振聋发聩的杀人命案。在看似关乎罪与罚的青春成长的一桩桩事件背后,影射的却是个人在波谲云诡的时代洪流中,与现实命运的反抗与逃亡。而主人公们在反抗与逃亡的过程中伴随着对欲望的追寻,逃亡过程实则也是欲望膨胀的过程。根据拉康的欲望理论,欲望本体从一开始就是处于缺失状态,主体所追寻的欲望不过是欲望本体的一个能指而已。欲望是拉康思想的中心概念,因此,本文首先通过分析意象与人物的对应关系,展现逃亡者的逃亡动作;其次分析个体逃亡的命运轨迹——无一例外地走向悲剧结局;最后结合拉康的欲望辩证法揭示逃亡者的普遍处境——主动逃亡表象下掩藏的是被抛弃的实质,从而得出他们逃亡悲剧的本质原因。
二、逃亡者的形象表现
作者在描写“逃亡”和塑造逃亡者形象时都离不开意象的运用。《黄雀记》中的梦、绳子、水塔以及魂这些意象形象且艺术地表现了文本中人物的逃亡姿态,丰富了主人公们作为逃亡者的形象内涵。
(一)梦之于保润
文本中故事一共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保润的春天。春天是一个做梦的季节,文中的保润曾多次在梦中幻想仙女的模样。所以梦之于保润是一个感知“美好”世界的窗口。梦同时也是沉淀于保润内心深处愿望的反映,而这种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却又是一种被抑制的状态。在文本中,现实的困境——保润与仙女的落差使保润追求仙女的愿望被抑制。保润向往着仙女的“爱情”,可在仙女看来这是一种不可能。我们在保润身上看到一种“够不着”的落差。这种落差表现在保润偷偷地拿了家里的80元,带她去看电影,滑旱冰。保润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一味地迎合和满足仙女的要求,而当他看到旱冰场里人的穿着,才发现自己的过时,这其实就是保润与仙女之间的格格不入。而这场爱情的开始就是因柳生的欺骗,他将保润的“身份”提到一定高度以至于后来遭到仙女的不屑和无视。这其中虽然看起来很搞笑,荒诞,但实质是够不着产生的落差感。而大落差的悲剧是人自身往往无法扭转命运给他带来的这些影响,是一种无奈的悲剧。
所以爱情的幻想只有在梦中才得以实现,梦使保润因现实的无奈所造成的焦虑得到了缓解。“这种梦成了一种逆向补偿,一种获得平衡的方式。”[5]梦实际上成了保润在现实困境中的自由地,在梦境中保润满足了自己的爱情想象。所以“梦”意象无疑为我们寻找逃亡者的逃亡迹象找到了突破口,为我们探寻其内心的情感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梦里的“狂欢”恰好反映的是现实里的失落与悲哀。这种失落与悲哀,究其实质是现实的局限性对个体自由发展的限制,它是个体无法突破现实无奈而陷入的一种悲哀境地。既然无法突破,个体飞向梦的自由高地就成了逃离现实的不二之选。
(二)绳子之于柳生
文中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意象——绳子,它虽与保润的手息息相关,与祖父的身体合二为一且与仙女也有过两次身体交接,但切切实实受到身心束缚的却是柳生。自保润进了监狱、仙女离开香椿树街之后,夹着尾巴做人就成了柳生的真实人生写照。在柳生的日常生活中,母亲的善意提醒如影随形。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担心保润出狱后不领情。在一次与柳生的对话中,母亲透露出她的担心,柳生却对此怒不可遏。而他的这种“怒”恰恰是来自于他心中的担心和恐惧以及从未消失过的罪恶感。当他带头在水塔上修庙宇时,师傅的一句话无意间挑起了他当年的“事迹”,他立刻就觉得羞耻难耐。所以绳子对其身心的束缚从未松懈。绳子意象揭示了柳生在所谓的现实“自由”中其实是步步为绊的生活困境。所以,他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却依然活在生活之牢中。这种非正常的生活姿态,不外乎是对正常生活的一种游离,而且他的隐忍的生活方式,也坐实了他是个生活的逃亡者。
(三)水塔之于仙女
对于仙女来说,水塔是她青春罪恶记忆的发源地。水塔作为被封存的记忆存在,是仙女不可也不再愿意触及的青春创伤。她两次在水塔,两次被捆,对她来说都是一种屈辱。作为女性,这是一种个体命运的无法掌握的无奈。水塔从而成为一种意象,是青春罪恶成殇的一种象征。所以文中仙女的出走就是对象征着罪恶的水塔的逃离,也是对于罪恶渊薮的香椿树街的逃离。但这种逃离是无望的,就如她在水塔里的遭遇一样,不管是她主动闯入还是被迫进入,她从来都没有成功逃离过水塔的“黑暗”。 当她离开香椿树街那一刻,她的身份变成白蓁,她的身体成为了她个人欲望的表达渠道。她对欲望的不停止的追寻,带来的结果就是无休止的空缺和失落。身体的破碎不堪加上精神的忧伤记忆,仙女注定是一个悲剧的存在。她外在的无根漂泊正是内在的精神无处安放的真实写照。封闭式的水塔结构藏匿了无数个青春的罪恶,而她对自我及他人罪恶的逃离却又最终陷入欲望的泥沼中。
(四)丢魂之于祖父
就祖父“丢魂”延伸出一系列荒诞可笑的行为——寻找尸骨来说,显得滑稽无比。但祖父的“丢魂”的缘由却是头上的一块“文革记忆”,这是一个时代的创伤。时代的记忆和伤害,虽然没有以本来面目示人,但是辗转至今,却依然清晰可见。不论是外在的时代创伤——刀疤,还是内在的精神创伤——丢魂,都显示时代的罪恶给人带来永不泯灭的伤害。丢魂在文中是一种精神意象,它不单单指向祖父,也反映了香椿树街上少年们的精神状态。作者通过历史雕刻当下,以历史的“丢魂”映衬当下人们内在的精神缺失。所以丢魂显示的则是祖父因历史伤害的延续而对现实世界的精神逃离,也是香椿树街上人的内在精神无所依附的焦虑状态的表现。
作者借助意象的表现手法展现了逃亡者各自的“逃亡”的动作。而“逃亡”动作虽各不相同,但人物的“逃亡”都是规避和搁置现实困境的一种方式。保润面对无望的爱情、柳生面对内心的罪恶、仙女面对欲望的沟壑以及祖父面对时代的精神创伤,当这一系列现实困境扑面而来时都无一例外地引发了人物的逃离反应。而文中除了运用意象的表现手法丰富逃亡者的形象内涵之外,更是将人物的逃亡意识贯穿于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之中。因此,人物的逃亡原因以及选择何种形式逃亡到最后结局如何这种情节发展,都是在人物的逃亡意识结合个体命运的运动轨迹中展开。
三、逃亡者的命运轨迹
文本中保润、柳生以及仙女三人间的情感纠葛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主线,他们彼此的逃亡生活看似各不相干,互不相扰,但实则是阡陌交错、纹理相通。因此,从他们的逃亡生活中分析他们的逃亡原因、逃亡方式以及逃亡结局可以进一步展开逃亡者的命运轨迹以及论述在人物的逃亡意识所主导的情节发展中个体命运走向悲剧的必然性。
(一)逃亡的原因
不难看出,改变三位主人公各自生活轨迹的起因就是由少年们内心的青春骚动引发的一起强奸案。从此以后,大家都走向了“逃亡”的命运轨迹。而他们内心的骚动正是源于他们对现实的一种焦虑,而焦虑的根源是他们对“仙女”的想象。仙女对青春懵懂的少年来说是一种诱惑,这诱惑在现实中作为一种欲望对象存在,是少年们心中的欲望实现的替代品。而仙女之所以成为替代品是因为拉康将诱惑之因看做是对象a,而对象a在现实中是无法获取的,因此仙女成为替代对象a的欲望存在。对于保润来说,在与仙女的追逐怒骂同时,其实是他在追寻内心欲望的幸福过程。正如他去向仙女讨要80元债款时无意中看见仙女的脚趾虽然面露羞愧之色但内心又顿生喜悦之情。这“正是在主体与对象a既包围又发展、既联合又复杂关系中,他获得了一种虚幻的充实、完满的幸福体验。”[6] 198对于柳生来说,尽管他继仙女之后依然驰骋情场,但他迟迟没有结婚恰恰是因为他没有忘怀“水塔里的仙女”。他记忆中无法忘却的仙女是他的欲望对象,当他满足自己的欲望并带来短暂的幸福体验后随之而来的是更大欲望缺失。根据拉康的观点,欲望本体的缺失导致主体是无法满足内心的欲望。因此,这种想象本身就是一种无法满足幻想。所以,他们对这种想象和诱惑的追寻,必然是一种失落且悲剧的结局。仙女作为少年欲望实现的替代品的同时,自己也是欲望的追寻者。她听信柳生的片言与本该达不到要求的保润约会,保润是她在欲望实现的过程中的错误对象,相比而言柳生更符合仙女对欲望对象的要求。所以,柳生、保润都不过是仙女在欲望表达时的一个能指而已。拉康将能指看做是欲望对象,但并不是欲望本体。因此他们在各自的欲望表达时,尽管有欲望对象的存在但是依然无法满足真正的欲望,拉康将这种欲望表达归结为是内心焦虑的一种表现。
他们内在的骚动和外在的欲望表达都源于他们内心的焦虑,而伴随焦虑存在的还有青春少年时期特有的愤怒叛逆的情绪。保润天生愤怒的目光,与仙女傲骄愤怒的眼神不期而遇,加上柳生那颗骚动不安的灵魂,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与叛逆就必然导致青春悲剧,悲剧一旦发生,逃亡就会如期而至。他们小小的身体无法承受悲剧所带来的现实恐惧感,对现实的逃离似乎就成了一种不选之选。
(二)逃亡的方式
当悲剧发生后,保润进监狱、柳生“夹着尾巴”地生活、仙女离去,他们各自导演着自己的“逃亡”轨迹。监狱无疑是隔离保润与香椿树街的一道现实屏障,我们从保润的几封家信中不难看出监狱生活的无聊与重复。这种非正常封闭式的生活状态对于保润来说虽然是一种被动选择,但与他在香椿树街上孤僻自闭的存在方式——宁愿去井亭院,也不愿去学校似乎形成了某种对应关系。他出狱归来,在香椿树街也没有掀起多大波澜。香椿树街的遗忘、祖父的失忆、父亲的逝世、母亲的抛弃,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重回正常生活的保润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当生活以一种拒绝的姿态迎接他的时候,他在生活中找不到任何情感寄托以及归宿感的时候,自闭式的逃亡实则是对自己的一种另类保护。
柳生小心翼翼地怀揣那份罪恶感夹着尾巴地生活了十年,这种非正常的生活姿态,隐忍的生活方式,不失为对生活的另类逃亡。这不是对既有的生活环境的摆脱,而是对所处环境的固守。仙女归来后对其颐指气使,他也毅然保持俯首称臣的姿态以及当保润回来时,只有他为其接风洗尘。他的种种表现在看似赎罪的背后,其实是对现实真实的某种逃离。
与其他两位逃亡者不同的是,仙女以最直接了当和决绝的姿态离开了罪恶渊薮的香椿树街,这种逃离不仅包含她对现实的不满和抗拒,同时逃离的过程也是她自身欲望的填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的是能指的不断转移,从马处转到老阮最后是庞先生。能指所指的就是欲望对象,因此能指的移动其实就是欲望的表达过程。于是我们可以说能指的不断变化,一个能指转移到另一个能指的这种持续流动、逃逸的现象是仙女的某种欲望表现。但能指的丰富却永远无法满足她内心的愿望,因为这种丰富是建立在欲望本体缺失的基础上,能指只不过是欲望的替代品而已。所以仙女欲望表达的自由虽然被物化,但丰盛的背后依然掩盖不了精神的贫瘠和心灵的孤独。在仙女的欲望表达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无根漂泊的生存状态,漂泊正是她无处安放的精神的真实写照。
保润的自闭,柳生的隐忍,仙女的漂泊,不同的逃亡方式并没有带来新的希望,只是逃亡者以不同的逃亡姿态演绎着各自不同的悲剧人生。
(三)逃亡的结局
辗转十年,过去的过不去。保润在柳生的婚宴上杀了柳生,白小姐生下一名“耻婴”亦或“怒婴”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这种无望的挣扎与逃离最终走向依然是苏童式的宿命死亡。
首先是无望的挣扎。白小姐,尽管能指——欲望对象是丰富的,但她对于爱的需求却是贫乏的。能指越是快速地转移,主体的恐惧空虚感就越强烈。而空虚和焦虑会迫使主体不断追求新的欲望对象来弥补。这是主体对爱的完满的欲望的一种追寻,而主体渴望爱的完满恰恰是因为在现实中爱的需求的贫乏和缺失。文中颇有姿色的仙女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主体,身体是其欲望表达的手段。但是身体在突围现实的困境时却又陷入被包围的怪圈,包围身体的正是主体的欲望。所以她的逃离带来的后果不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解放,而是身体的“围困”——怀孕与精神的空虚和焦虑。最终从城市落荒而逃,返回香椿树街,回到了原初的起点状态。
其次是宿命式的死亡。死亡在苏童小说中其实是逃亡者很好的一种解脱方式,且具有一定的宿命意蕴,宿命里包含着某种必然的可能性。首先,“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7]监狱并没有消灭犯罪,犯人因为不公正而受苦,继而衍生出冤屈感导致杀害的行为。其次,保润最后杀死了柳生,这一简单粗暴且残酷的报复行为,并不仅仅是保润心理极度压抑和冤屈而产生的冲动结果。十年成长的终止,出来后,社会的不认同,亲人的抛弃,保润的心理成长还永远停留在十年前,他心理的愤恨有增无减,过去的过不去,恰恰是因为过去的创伤从来都没抚平过,十年的监狱生活,就是在每分每秒地提醒他受过的冤。所以与十年自由的生活相比,保润的精神创伤显然更为严重,他始终不明白,仙女为什么要诬陷他?这是他的一个心结。而柳生对于保润而言,其实就是一面镜子,柳生的存在就是说明保润的羞耻。在仙女面前,似乎永远都有一个柳生,而他是作为一个被忽略的存在。他的清账就是与仙女跳一曲小拉,后来换成贴面舞,这一舞是他用十年的牢狱生活换来的。他在贴面时流下的一滴眼泪,或许是悲哀或许是满足。仙女其实就是他青春年少时,内心的一个欲望,然而当他欲望满足时,随之而来其实是更大的失落。当他得知,柳生穿走了他父亲的衬衣时,他又流下了一滴眼泪,这是失落的眼泪。所以只有柳生消失,他才能找到自我。然而他并不知,柳生的死亡,带给他的并不是社会的认同,而是更永远的抛弃。
个体在逃亡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自我价值也没有摆脱现实困境,而是确证了其悲凉、荒诞、吊诡的人生处境。这是因为个体的逃亡看似是对现实的生存环境的一种拒绝,然而实质是被个体所依附的生存环境的一种抛弃。这种抛弃必然使个体的逃亡终归走向失败或是自我毁灭的悲凉处境。
四、逃亡者的悲剧意蕴
“逃亡”是贯穿苏童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譬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的陈宝年——他的逃亡与还乡、以及后来《逃》中的五龙——他的逃亡与城市欲望。在其新作《黄雀记》里,苏童驾轻就熟地将逃亡融入在人物对生活的态度以及对命运的思考中。保润的自闭,柳生的隐忍、仙女的漂泊,祖父的丢魂,每个逃亡者以不同的姿态演绎着各自的逃亡生活,而他们在寻找新的希望的生活中走向的却是无望的悲剧结局。从文本中人物一系列的形而下的“逃亡”归结出一种形而上的关乎逃亡的哲学内涵,探究人物逃亡的悲剧结局的本质原因。
众所周知,让祖父丢魂的那个“伤疤”指向的是对历史的反思,历史对人情人性的压抑、对是非黑白的颠倒导致了诸多关于人的不幸。而社会在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丢魂也成了现代人的精神象征。时代的发展导致人的思想的转变,时代使人的情感在得到释放的同时欲望也得以膨胀。苏童巧妙地将时代的成长与人物的成长结合在一起,从80年代开始,香椿树街上的三个少年承载着时代的欲望气息,辗转十年,时代的发展与个人的成长相互映衬。从人的身上反映出时代发展所显现的诟病,譬如郑老板的弟弟因财发疯,老板与官员的争病房之战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权色欲望的追求。所以,不管是压抑还是释放,在过度的情况下都会导致人性内在恶的滋生。而拉康认为从镜像阶段中自恋认同的那一天起,人的行为中就有了侵凌性因子,而“梅拉尼·克兰所谓的‘内在恶物’不是什么别的,正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侵凌性的种子。”[6]73霍布斯也认为人生来是自私的,残酷的,人对人是恶的。这种恶物驱使人不断与外界认同,并在认同的过程中,“引起了禁忌和逃离的反应。”禁忌实则是自我欲望的压抑,逃离则是自我保护。人们在逃离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伴随着欲望的压抑,但压抑所导致的结果不是欲望的疏离而是欲望的膨胀。
所以,文中三位主人公在逃亡的过程中实则也是欲望追寻和膨胀的过程。保润从幻想到跳一曲小拉,柳生从强奸到追忆曾经的仙女,仙女对于物的执着追寻,但追寻的结果却不是满足而是无法满足。三位主人公所呈现的就是三重人生悲剧,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主体总是千方百计地对欲望进行追寻,而结果却是永不满足。对于拉康来说一般意义上的欲望其实不叫欲望,它只是真正欲望的替代品。人们对一般意义上欲望的追寻得到的不过是短暂的欲望满足,但此欲望实现后又必然奔向下一个欲望。就如保润跟仙女跳一曲小拉之后又要求再跳一曲贴面舞。所以欲望的无穷尽导致欲望满足的无止境。然而欲望满足的无止境带来的必然是主体的痛苦。但又正如拉康所说,“欲望指向的对象作为缺失者不在现实世界,但正因为他作为缺失而不存在,才被渴望。”[8]158
对于保润来说,他的欲望就是渴望成为他者的欲望对象,以及得到他者的承认。在文中他者指的就是柳生和仙女,拉康认为,“人因消灭在他者的欲望之中,而发现了自己的欲望,并对侵夺自身权利的他者流露出嫉妒的感情。”[8]160他者的欲望在这里指的就是柳生因对仙女的存有欲望而实施了强奸,保润却因此承受了十年的牢狱之灾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这种消失对于保润来说就是一种生存意义的消灭。但保润也因此发现了自己的欲望,“主体因自身的欲望重叠在与自己非对称的他者欲望中而被告自己的欲望。”[8]161所以当他出狱后,所谓的“报复”就是重回水塔与仙女跳一曲小拉。这正是因为保润在柳生的欲望中发现了自己的欲望,更重要的是保润想要以此获取他者的认同——柳生可以他也可以。“主体又提出相互承认的原则,热切盼望着自身被自己欲望的他者所欲望。针对他者,主体为了作为我所欲望的主体生存下去,必须确认自己是被欲望着的事物。”[8]161但是在这种认同的过程中,当保润因柳生的侵犯而被剥夺了欲望的权力后,保润对作为他者的柳生来说必然流露出一种嫉妒的情感。更甚的是,“两个个体间围绕着在他者中被欲望的相互承认的纷争,最终将走到其中哪一方让步或死去的极限地步。”[8]162所以保润最后在柳生的新婚之夜杀了他,而酿成悲剧。
仙女在文中是典型的物质拜金女,她的拜金思想从与保润约会开始就初露端倪。她对异性的择友观是英俊潇洒且条件优越。虽然长相帅气,物质丰富的男人对一般女性来说的确极具吸引力,我们不否认这种憧憬的普遍性,但是对于仙女而言,她并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她是一个孤儿,被人收养长大。在她成长的过程所留下的创伤就是对于父爱和母爱的缺失。所以她的欲望其实不是对金钱物质的崇拜,而是完整的爱。所以在拉康那里,“他的幻想不是一般意义上拜金主义的幻想,而是对完满的欲望,对那从来不曾拥有就永远失落了的原初快感。”[6]204而她对“物”的执着寻求也必然是失落的,因为“物”在拉康那里就是一种既不能看也不能听、又不能触摸的欲望。
保润欲望着他者的欲望,仙女欲望着爱的完满,他们在欲望表达同时都具有祖父“丢魂”的特质,而祖父在文中实则是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在拉康看来是无法完成的主体建构。因为主体的建构从想象界到象征界有一个飞跃,有一个质变的过程。精神病患者既没有处于镜面的完整自足之中,更没有完成从想象界向象征界的转换,他们只是停留在镜像初期阶段。所以文中最后祖父与婴儿在相处的安静中形成一种对比,他们是彼此的一个镜像。文本中婴儿的怒与耻反映了成人世界里的光怪陆离,祖父在异化与自我确证的过程中实则是停留在一个婴儿的状态,他代表着主体的破碎不堪。就好比那张合家福,其他人都残缺不齐,只有祖父完好无缺。但照片里的完整反衬的却是现实世界里祖父主体性的破碎,这种破碎还表现在保润、柳生以及仙女等欲望主体身上。祖父的丢魂找魂等一系列具有重复性的动作表明的也是现代社会主体欲望表达的重复与相似。
所以在逃离与禁忌反应中,主体的欲望因欲望本体的缺失和欲望主体的破碎而无法通过欲望表达得到真正地满足。在拉康的欲望辩证法中,欲望之因是对象a,“拉康将对象a定义为某种残余,需要进入象征时候留下的残余。在主人话语中,一个能指试图为所有其他能指表示主体,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某种剩余;这种剩余就是对象a,就是剩余意义、剩余快感。”[6]187但剩余快感是不可获得的,就好比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剩余价值,工人自身是无法获取的。而文中,保润逃到最后还是坐牢、柳生逃到最后还是被杀、仙女逃到最后还是抑郁离开、祖父始终被搁置在井亭院,他们对生活的逃离都是失败的。因为在看似主动逃离的背后,透露出他们其实是被抛弃的对象。它预示着逃亡者的一种普遍处境:人们在逃亡的过程中,伴随着欲望的膨胀,而欲望的表达无法满足欲望,但“为了获取那一点点剩余快感,主体又总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逃避、甚至破坏这象征秩序。”[6]192而当主体对其生活的坏境逃避或者是破坏时,其实是被其抛弃,因为他在被拒绝的同时,他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也被颠覆了,最后他所逃避所毁灭的不是其所处的环境,而是自己。文中的保润、柳生以及仙女无一例外,而作为精神症患者的祖父也是如此。“象征秩序是牢不可破的,精神患者的疯癫不是主体对象征秩序的胜利,而是被象征秩序抛弃;因为精神症患者在被象征秩序拒绝的同时,他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也被颠覆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毁的不是象征秩序,而是他自己。”[6]192在逃亡的过程以及欲望的表达过程中,主体会暂时获得一种自由和快乐的假象,这种假象掩盖的恰恰是生活现实中的真正缺失。因此,在苏童的小说中逃亡是一个无法逃脱的逃亡。在《黄雀记》中,主人公们在获得逃亡带来的短暂的安稳完满后,随之而来的是现实生活里的缺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人物彼此间的命运走向,因为缺失的不可抹灭而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悲剧色彩。
五、结语
苏童不管是书写历史还是辗转当下,他的作品始终是贯穿着逃亡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创作就是作家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苏童迷恋逃亡,把它作为人与社会不合作的一种姿态,人只有拒绝那种生活姿态时,才会逃,人在逃亡的过程中实现或毁灭着自己的某些生命价值,这也是人生悲剧性的体现和写照。”[9]“逃”是人固有的一种心理情结,它是对现实枷锁的一种本能的或者是正常的反应。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让我们去思考逃亡的人以及让人逃亡的现实世界的“不正常”。
保润、柳生、仙女、祖父在文中以逃亡者的形象存在,但不论是以自闭、隐忍、漂泊还是疯癫等逃亡方式生活,依然摆脱不了苏童小说中逃亡所带来的宿命式结局。与其以往小说不同的是,苏童的“逃亡”涵盖的可能是作者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以及社会转型期焦虑的表现,但在《黄雀记》中,人物的逃亡伴随的是主体欲望的释放。而人物在逃亡过程中,因欲望本体的缺失以及欲望主体的破碎而无法通过欲望表达满足主体的真正欲望,欲望表达满足的仅仅是真正欲望的一个能指。主体逃亡的表象伴随的是对欲望追寻的实质,最终无一例外地走向悲剧。这让我们对“逃亡”的思考由对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转向对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思考。
[参考文献]
[1]程桂婷.苏童研究综述[J].扬子江评论,2008(6):32.
[2]摩罗,侍春生.逃遁与陷落:苏童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8(2):12-20.
[3]徐肖楠.中国先锋历史小说的神话过度[J].南方文坛,1997(2):18.
[4]何平.香椿树街的成长史,或者先锋的遗产[J].小说评论,2015(4):29.
[5]张丽.论苏童小说的逃亡主题[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10.
[6]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00.
[8]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9]李清霞.论苏童历史小说的生存意识和逃亡意识[J].扬子江评论,2008(4):60.
(责任编辑马诚)
Image of Escape in the Story of the Yellow Bird by Su Tong
SUN Yuanyuan, WEI Lihu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Escape as a recurring behavioral trait for Su Tong’s fictional characters is well presen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Story of the Yellow Bird.The core images of dream,rope,water tower and the soul in the story add to the full connotation of the runaways.Out of anxiety and anger of real world the three protagonists run away onto an isolated,suffering and drifting way of escape until they meet their destined end of tragedy.The act of escape and the mechanism of desire that runs through the fate of destiny interprets the tragic nature of the runaways:the subjects may get brief peace when they run away,but they can’t escape their tragedy eventually because one can’t get away from reality.A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towards the cause for the tragedy of the runaways suggests that pursuit of desir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escape.
Key words:Su Tong;the Story of the Yellow Bird;escape;image;dialectics of desire
[收稿日期]2015-12-03[修回日期]2016-03-24
[作者简介]孙媛媛(199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通讯作者:韦丽华(1971-),女,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sisterwlh@163.com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432(2016)02-008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