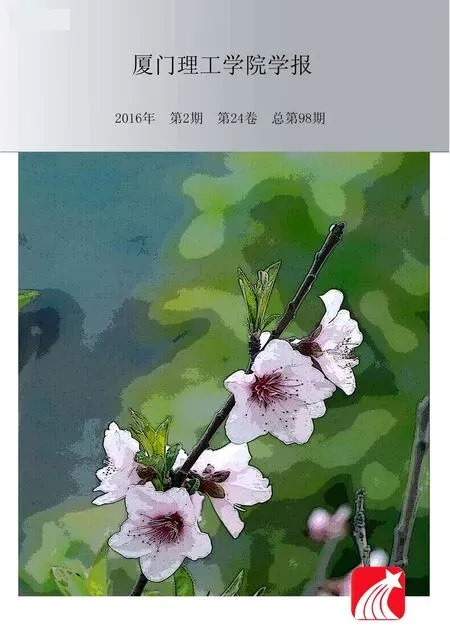在历史与文化背景下演绎的爱情传奇
——论袁雅琴的长篇小说《陪楼》
苏晓芳
(厦门理工学院文化发展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24)
在历史与文化背景下演绎的爱情传奇
——论袁雅琴的长篇小说《陪楼》
苏晓芳
(厦门理工学院文化发展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24)
[摘要]厦门作家袁雅琴的小说《陪楼》,讲述的是婢女阿秀与侨商家的私生子二龙之间曲折浪漫的爱情故事,作品将故事放置在鼓浪屿百年历史与闽南地域文化背景上展开,使小说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作为颇具闽南文化意蕴的小说,作品侧重从“人文资源根基”上展现地域特色,具体表现为对于以鼓浪屿为中心的闽南日常生活习俗的精心描绘和一系列富于闽南地域文化性格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陪楼》既反映了作家对于鼓浪屿历史与文化的深刻理解,也是作家对于闽南地域文化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陪楼》;地域文化;鼓浪屿历史;人物形象
厦门作家袁雅琴的小说《陪楼》讲述了一个流落到鼓浪屿的婢女阿秀与侨商龙家的私生子二龙之间缠绵一生的爱情传奇。作品在历史与地域的双重维度上展开故事,历史跨度大,视野恢宏,上起鼓浪屿沦为万国租界之后的1920年代,下迄经历近3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新世纪之初,叙事重点则在抗战爆发、厦门沦陷、日军占领鼓浪屿之后的历史阶段,着重展现在民族危难面前,鼓浪屿人的苦难、忍辱与抗争。同时,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不仅注重以鼓浪屿为代表的闽南人日常生活场景与民间风俗的描绘,更成功塑造了阿秀、维娜、安韵珍、地瓜等一批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性格的人物形象,小说处处散发着迷人的闽南风情。本文从作品的历史与地域文化背景的挖掘、闽南人文风情的描绘和独特的人物形象塑造等三个方面剖析其艺术价值。
一、爱情故事背后的历史沧桑与地域文化
所谓陪楼,是指鼓浪屿别墅的附属建筑,小说中说,它“紧挨着主楼,就像佣人站在主人身边一样,敛声敛气的。从外形上看,陪楼与主楼浑然一体,可内部装饰、用料却全然不同”[1]P3,而在居住功能上,主楼与陪楼的区别也有主仆之分,小说中龙家的主人是住在主楼的,仆人则住在陪楼。阿秀是一个来自东山岛的渔家女儿,流落到鼓浪屿,曾被人贩子拐卖为婢女,受尽残酷虐待,后为婢女救拔团救助,被善良宽厚的龙家收留,又因曾对龙家小姐龙维娜有救命之恩,维娜的母亲安韵珍让她住进主人居住的主楼,维娜对她也以姐妹相待,但阿秀始终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龙家仆人,因此主动要求从主楼搬进陪楼居住,并在陪楼度过了漫长的一生。因此,陪楼是人格化的阿秀,陪楼的故事,也就是阿秀的故事,而阿秀的人生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她与二龙之间的曲折坚韧而不失浪漫的爱情传奇。
二龙是龙家少爷龙博山与婢女阿彩的私生子,当年的新派大学生龙博山在接受父母包办的婚姻,与厦门望族之女安韵珍完婚之前,已与温柔贤淑的阿彩相好,并珠胎暗结。这原本是类似于曹禺的话剧《雷雨》中的桥段,但剧情并没有向戏剧化的极端发展,因男女双方本性的善良与容忍,包办婚姻虽无激情,却也能各尽本分,相安无事。而阿彩在生下儿子之后,因血崩死于陪楼,产下的私生子二龙则被送到教堂,由威约翰牧师抚养成人。二龙与龙家的再次相遇是因为阿秀。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厦门沦陷,公共租界鼓浪屿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岛”,难民纷纷涌进鼓浪屿,日军一边从经济上封锁鼓浪屿,一边飞机轰炸,龙家陪楼不仅成了龙家收留、安置难民的避难所,也在暗中变成了二龙等抗日志士的栖身之所。在这纷乱动荡的时刻,阿秀与就读于厦门大学的二龙相遇,两人之间萌生了患难中的真情,这乱世中的爱情弥足珍贵,然而命途多舛,二龙在陪楼短暂停留之后,就被日军抓捕,在经历严刑拷打之后死里逃生,远走香港,从此与阿秀分离。待到二人再次相见,二龙素未谋面的孩子龙隆都已二十岁。在龙家的操持下,两人举办了迟到的婚礼,但因为各自的承诺与责任,又不得不再次分开,阿秀让二龙将龙隆带走,自己则继续留在陪楼,照顾着对于她来说既是亲人也是恩人的龙家老小。几年后,二龙在香港离世,而阿秀则一直呆在陪楼,直到静静地走完自己的人生。
就一部长篇小说而言,二龙与阿秀聚少离多的爱情故事并不复杂,爱情的华彩处也只如惊鸿一瞥,无尽的岁月在无望的等待中流走,二龙与阿秀的爱情的动人之处是离别中的守望,而这种守望甚至是超越生死的,正如作品中所说“有一种爱,是离别”[1]268。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简单的充满悲情的爱情传奇是放置在一个非常宏大的背景上展开的。这个背景犹如一个既有深度又具广度的舞台。从纵向背景来看,小说时间跨度近百年,从1920年代阿秀流落到鼓浪屿,讲到21世纪初阿秀离世之后,其中涵盖了鼓浪屿的百年沧桑,包括公共租界、抗战、国共内战、文革、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阶段。作为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组成部分,鼓浪屿因其美丽的自然风光、舒适的气候条件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在20世纪初沦为了西方列强竞相争夺的公共租界,但也因此而获得了更早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契机,至今仍随处可见的西式建筑与钢琴岛的美名显然与此相关。
鼓浪屿公共租界是清末到民国时期仅有的两个公共租界之一,另一个是上海公共租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割让台湾后,为避免日本进一步觊觎厦门,清朝政府为寻求“国际保护”,请求列强“兼护厦门”,于1902年1月10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清朝福建省兴泉永道台延年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丹麦、荷兰、瑞挪联盟、日本等9国(或联盟)驻厦门领事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不久后续签《厦门鼓浪屿续订公地章程》及《厦门鼓浪屿租界中田地章程》,划定鼓浪屿全岛约1.78平方公里为公共租界[2]。跟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样,抗日战争时期,鼓浪屿也经历了被日军包围、封锁的孤岛时期,只是各类文艺作品大多更关注上海孤岛,鲜有描写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因此,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相对较少。鼓浪屿公共租界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为日军占领,直到1945年,鼓浪屿公共租界才由国民政府正式收回。
在成为公共租界之前,就已有十多个西方国家在鼓浪屿上设立了领事馆。成为公共租界之后,这里聚集了更多的外国人,主要有三类:传教士、水手和商人。四十多年公共租界的历史,对于鼓浪屿独特人文环境和文化风貌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至今尤存的旧领事馆、教堂、别墅等具有中西合璧特征的建筑很多都带有那个时期的历史烙印。作为背景描述,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公共租界时期鼓浪屿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外国俱乐部的灯红酒绿,侨商家庭的日常生活,教堂、新式学校的西化气息……其中,既有外国水手蛮横凶残、欺压国人,也有像威约翰那样友善仁慈的外国传教士真诚地传播着上帝的福音,并尽其所能地帮助中国人。日军攻陷厦门之后,沦为难民避难所的孤岛生活也被描绘得生动传神。
小说涉及到一个定居于鼓浪屿的侨商家族,这又使作品拥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广阔的横向视野,《陪楼》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家族小说,虽然30万字的篇幅足以承载一个完整的家族故事,但是作家用了一种做减法的方式叙事,不仅避免了因人物线索繁多而造成的叙事枝蔓缠绕,使作品的主要人物命运和关系得以凸显,也在保留其家族叙事框架的同时,营造了浓郁的闽南地域文化氛围。原本龙家应是一个人口众多、关系复杂的大家族,龙家第一代即二龙的爷爷早年下南洋经商,攒下家业,在鼓浪屿上建成凤海堂别墅,龙家第二代似乎不只有小说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龙博山和龙博绵,而龙家第三代,则除了二龙及安韵珍的两个儿子和女儿龙维娜外,还有他在海外经商期间与外国女子生下的孩子。依照通常家族小说的写法,仅就这些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各自命运都可以延伸出若干故事与线索来。但作家对于主要人物之外的人物和关系做了淡化处理,龙家第二代仅提及博绵在厦门银行工作,博山继承家业,下南阳经商;而第三代的故事则聚焦于二龙与维娜,二龙是阿秀的恋人,维娜是阿秀的姐妹。次要的人物关系被淡化,而文化背景依然存在,因地缘关系,隶属闽南文化的鼓浪屿人是最早主动走到外面世界去打拼的一群人,像龙家这样的侨商家庭则是其中的代表,通过侨商家庭的日常生活,作家将笔墨集中于地域文化氛围的渲染,使小说的文化意蕴得到自然展现。
这个爱情传奇背后的两重背景非常清晰:纵向的背景是鼓浪屿百年历史,横向的背景是以一个侨商家庭为中心体现的闽南文化。这个原本纯情简单的爱情传奇巧妙地立足于历史与文化的交汇点上,既拥有历史的深度,又富于文化的浓度,个人与历史、个人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交汇点上得到凸显。
二、兼容并蓄的文化自信与浓郁的地域风情
人总是历史性地生存于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之中,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对生存于该地区的人们的文化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关注特定地域的文化性格,并在作品中予以展现,形成了中国文学中极具魅力且延续已久的小说创作传统,即地域文化小说。有研究者指出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间接体现为人文基础的历史性,即进行人文地理开拓,来提供必要的人文资源根基以促进区域文学的形成;另一方面间接体现为民族特征的体系性,即进行民族语言的发展,来提供必要的语言表达符号以推动区域文学的出现。从人文资源根基到语言表达符号,都有着地方性的基本内容,表现为人文性的语言运用所产生的群体影响作用。”[3]依照这样的论述,地域文化小说主要从“人文资源根基”和“语言表达符号”两个方面来表现地域文化特征,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前者体现为特定的地域自然景观、人文习俗的描绘和特定地域文化性格的塑造,而后者则是方言或特定民族语言写作。《陪楼》的作者袁雅琴并非土生土长的闽南人,对于闽南方言的纯熟运用亦非她所长,因此,除了少量的亲属称谓,作品基本上没有使用方言写作,这部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集中于“人文资源根基”的表达。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闽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磨合,并由东南沿海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所逐渐造就”[4]。闽南地域文化除了表现为独特的自然环境外,还有与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相关的人文环境。小说除去引子和尾声,共15章,章节的题目全由厦门地名或闽南独特的建筑名称组成,如黄家渡码头、日光岩、人民体育场、骑楼等,这些名称除了提示所在章节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外,还用相关地域场景的细致描绘渲染出浓郁的人文氛围。如小说第14章题为《骑楼》,骑楼是近代传入中国福建、两广等地的一种沿街建筑形式,特点是商住合一,上楼下廊,厦门的骑楼兼有欧陆风格和东南亚地域特征,楼下的长廊既可遮挡风雨侵袭,又能掩避炎阳照射。厦门现存最著名的骑楼就是中山路步行街骑楼群,小说这一章的情节正是以中山路为背景的:
步行街并不见得有多现代奢华,相反,她比较古典,不过这种古典是洋气的,怀旧的。步行街的洋房有点原汁原味,没有大的改造,立在街的两旁,安静地让时光从身上流过,刷新,置换。特别是入夜,LED夜景灯亮起来的时候,步行街身着晚装。光影变幻,穿越时空,动静之间,诠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魅力。沿街的人文古迹将军牌坊,闽台文化宣传阵地讲古角,闽南特色石刻的休闲桌椅,绿化组合、古迹指示牌、街区图,当然还有定期演出的歌仔戏、布袋戏、南音、闽俗服饰等形式的闽南民俗文艺表演,都是个性化的文化元素[1]286。
这一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将传统符号与现代气息熔为一炉的中山路街景。人文场景的描写是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鼓浪屿地处闽南文化圈,但其文化因历史与独特的地理位置又具有特殊性,由于曾有沦为万国租界四十多年的经历,又聚集了许多曾下南洋打拼的侨商家庭,鼓浪屿文化在传统闽南文化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文化和南洋文化的元素,因此,鼓浪屿文化带有复杂多元的特点。正如杜维明所言,“没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文明不包含各种价值”[5]。然而,各种不同的价值在此碰撞,却并未带来文明的冲突,巨大的文化包容力让闽南文化、西方文化、南洋文化等看似相互抵牾的多种文化因子甚至不同的价值观彼此共存,并毫无裂隙地融合在一起。比如,龙家的家庭成员信奉着不同的宗教,龙老太太笃信佛家,她的儿媳妇安韵珍则信奉基督教,佛祖与基督在此并不矛盾对立,作为第三代的龙维娜则拜完佛祖拜基督,他们似乎找到了不同宗教的相通之处,那就是人性的善良与宽容,回归到一种单纯的理想状态。小说中还有一个动人的细节:维娜教阿秀弹钢琴,阿秀最先弹熟的曲子是闽南歌曲《望春风》,西方的音乐载体与源于古典戏曲《西厢记》的闽南曲调水乳交融。小说中还提到了来自鼓浪屿的钢琴家殷承宗率先用钢琴伴唱现代京剧《红灯记》,这种中西融合的思路是有传承的,这也正是鼓浪屿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个神奇岛屿的文化先天地具有一种包容的力量,不仅能将不同来源的文化容纳于其中,更能将它们彼此结合,熔铸为一个新的生命。这种文化包容与融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坚守传统与接纳新质并非矛盾对立,在以开放的胸襟接受外来的事物与观念的同时,若能保持文化自信,就能既吐故纳新,又避免自身传统的全面丢失。
随着小说中主要人物的行踪流转,作家还将笔触伸展到厦门周边同属闽南文化圈的泉州一代,作品中对于泉州蚶江镇端午习俗的描绘犹如一幅生动的民俗风情画:
……这时只见那“火鼎公”上身反穿羊羔黑裘,下着宽筒黑裤,裤管下端紧束绷带,脚穿圆口软底男布鞋,腰束长绸巾,手执竹质长烟管在前;“火鼎婆”身穿镶边大襟红衫,下着镶边宽筒大红裤,头顶盘起高高的发髻,脚穿高底绣花软底布鞋(闽南俗称“大公鸡鞋”),手执大圆蒲扇在后;一口内燃木柴的火鼎(即铁锅),架在两根竹竿中间绑着的“四脚架”上面,两人用绑在竹竿两端的长绸巾抬起火鼎;“女儿”身穿青色镶边大襟衣和镶边宽筒裤,脚穿绣花软底鞋,一根软竹扁担两头挑着装有一小捆木柴的小竹篮,紧随两老之后。这一家三口踏着民间小调《十花串》,悠闲自得,“火鼎公”一步一撅臀,“火鼎婆”一步一摆腰……[1]65
作家不但描述了戏台上“火鼎公火鼎婆”表演、“公背婆”、“送王船”、海上泼水等民俗节目,还不厌其烦地介绍茯苓糕这样一种闽南民间传统手工食品的来历。在一部叙事节奏明快、矛盾冲突激烈的小说中,加入这样巧妙的闲笔,不仅让浓郁鲜活的闽南风情扑面而来,也在小说相对沉郁压抑的情调中增添了几分谐趣。
作品中的闽南风情还体现在随处可见的对于鼓浪屿人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上,鼓浪屿别墅的精美建筑、内部的装饰、海边的碉堡、院子里的绿树繁花,还有中西合璧的生活方式、家庭音乐会、中秋博饼等特有的风俗。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精彩纷呈的地域文化越来越为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的局面所取代,民俗、民间宗教信仰、方言等那些曾经植根于先辈生活的元素,现在正面临着裂变、崩溃的危机。而在文学作品中让这些文化元素得到重现,无疑能唤醒我们的文化乡愁,有助于这些曾经鲜活的文明得以重生。
三、精彩传神的地域文化性格的塑造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陪楼》的人物并不多,人物关系也不复杂,大致算来是以阿秀、二龙为中心的四代人,由于小说在结构上做了减法,涉及到的四代人中凡是与阿秀和二龙的命运没有直接关联的人物都淡化、虚化了,所以呈现在台前的人物就为数更少。小说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是阿秀、维娜、安韵珍这三位闽南女子。
同为闽南女子,阿秀、维娜、安韵珍是有区别的。三人之中,安韵珍居长,她出身厦门望族,知书达理,温柔娴淑,遵从父母之命嫁入鼓浪屿龙家,虽然也为得不到丈夫的爱情而感到委屈,但她孝顺公婆,待人宽厚,以宽容大度的心胸对待丈夫的私生子二龙。在处理各种矛盾时既有原则又懂得适当妥协,比如她非常看不惯家中花匠地瓜的品行,常直率地指出他的问题,令其有所忌惮,但又顾及龙老夫人的颜面而有所包容。身为虔诚的基督徒,她慷慨仁慈,尽自己的力量关怀弱小,收留阿秀,安置难民,常年在教堂做慈善。在她身上,闽南传统女性的坚忍与基督徒的慈爱体现得淋漓尽致。
维娜是安韵珍的女儿,是出身于既恪守闽南传统文化又拥抱西方现代文明的侨商家庭的大小姐,优渥的物质条件,使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中西文化熏陶,她既擅长中国古典文学,又精通西洋音乐和英文。她是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鼓浪屿的女儿,生长于鼓浪屿,嫁人也未出鼓浪屿,直到优雅地老去,她都未离开这个迷人的岛屿。与其母亲相比,她性格率真,在追求爱情幸福时显得更为勇敢,这表现在她反对父亲给自己安排的婚姻上,但维娜的反抗仍是温和的,在她的反抗中并没有我们在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惯常见到的那种青年一代为寻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而表现出的对于旧家庭、旧伦理的决绝与叛逆,因为维娜毕竟是个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闽南女子,从小接受的闺阁教育养成了她柔顺的性情。
阿秀与维娜同岁,出身底层,身份由东山岛渔民之女到婢女,然后被龙家收留,又因为与二龙的姻缘,而成为龙家的媳妇,但她本人却一直把自己当作龙家的佣人,因此,她一生坚持住在陪楼,而不肯住进象征主人地位的主楼,她“安分守己,知足而乐,待人真诚,为人友善”[1]293。初读小说,读者大多会为阿秀与二龙重聚并补办婚礼之后依然选择分离而感到遗憾与不解。如果对作品进行细读并对闽南文化有更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就不难解答。小说中的闽南女子,从安韵珍到维娜,均是如此。当龙博山去马来西亚经商、向子豪去海外求学、工作时,他们的妻子安韵珍、维娜都没有随行,而是留在家里。小说中借龙老先生之口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男人在国外打拼那是应该的,……不要忘了闽南本土文化是我们的命根子,女孩子更应该在国内读在家里学。”这就是闽南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像许多以下南洋而开启家族发展并聚集财富的侨商一样,鼓浪屿人也都有着不同于内陆农耕文化安土重迁的海洋文化性格,即使是富裕之家,男子长大之后都会离家出外闯荡,而女子则守望家中,相夫教子。这种闯荡与守望,或为家,或为国,无怨无悔,代代相传,表现出海洋文化开拓、进取、务实的一面。阿秀在嫁给二龙之后就是龙家的媳妇,她必须选择留在龙家,照顾长辈,料理家务,尽一个闽南媳妇的职责。
如果问小说中最美的角色是谁,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阿秀、维娜、安韵珍皆有可能;但若问谁是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角色,则非地瓜莫属。地瓜在小说人物关系中是一个次要角色,他是龙家的花匠,因为与龙老太太的一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小小年纪就从泉州乡下来到龙家,他本名阿昌,因说话腔调有些杂,说一口不伦不类的闽南普通话,有人笑说他一口地瓜腔,于是被叫做“地瓜”。地瓜在龙家做花匠,却总想跟主人平起平坐,他先一心想让阿秀嫁给他,在看到阿秀与二龙两情相悦之后,因爱生恨,向日本人出卖二龙,沦为汉奸的地瓜最终也落得了一个可耻悲惨的结局。地瓜在作品中虽是配角,但着墨不少,甚至让人觉得有抢戏之嫌,然而细细考量,这个角色的安排其实是颇具匠心的。从故事结构来看,地瓜是一个结构性人物,他是戏剧冲突的缔造者,因为他既充当了二龙与阿秀爱情中的一个骚扰者,也是二龙坎坷命运的制造者。同时,就作品的风格而言,他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他是调和作品忧郁沉重氛围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他言语的饶舌幽默,使作品时不时有了一点轻喜剧的亮色。这个角色的设计犹如闽南地方戏曲高甲戏中的丑角行当,有戏曲研究者指出,“在闽南乡村随处可见高甲戏,有高甲戏演出几乎就有‘丑’行当的展示”[6]。尽管从故事叙事本身来说,作为“丑角”的地瓜并非主角,但就作品整体而言却意义非凡。小说中的少量的方言描写也集中在地瓜的身上。巧合的是在泉州蚶江镇端午的民俗表演中,地瓜扮演了“公背婆”中公的角色,由于他是本地人,从小看着这些演出长大,在龙家也时常会露一手给大家逗乐,所以他演得驾轻就熟,十分精彩。这段表演其实就是地瓜这个角色在整个小说中的角色定位。
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塑造也各具特色,二龙如鼓浪屿海边碉堡般坚固顽强、绝不妥协的性格,“无论海风、潮汐如何改造、侵蚀”,都不可改变的执着与坚守;作为家族家长的龙老先生殉难时宁折不弯的气节,龙老先生这样温文尔雅的老绅士,在日军要抢占他的家园的时候,也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龙老夫人的仁慈与颟顸;阿敢的侠义与担当;向子豪的内秀与儒雅……正是这些姿态万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将闽南人性格中那些既复杂又单纯,既开放又保守,既柔顺又坚强,既吃苦耐劳又享受生活的性格特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闪耀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四、结语
《陪楼》演绎的是大时代中闽南儿女的爱情传奇,其背后却潜藏着一部百年鼓浪屿的人文志。透过小说看鼓浪屿文化,会发现隐身在美丽的自然风光与略带小资情调的人文景观背后的一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这既是鼓浪屿文化本身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作家对于以鼓浪屿为代表的闽南地域文化的独特体悟。
作为一个外地人,作家袁雅琴书写闽南文化,有其天然的劣势,也有其优势,劣势显而易见,主要是对鼓浪屿乃至整个闽南文化的生疏;而优势则在于,任何一个外地人,在面对在地文化时,总是先天地带有一重比较的视野,从而能更为敏锐地感知其文化的独特之处,而不会有久处其中、司空见惯的漠视与迟钝,或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遮蔽和无视。袁雅琴不但以深入而细致的案头准备与田野调查克服了自身的劣势,还以一个“新闽南人”对闽南文化的挚爱,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从而书写出这样一部潜藏着深厚历史与地域文化魅力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袁雅琴.陪楼[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2]何其颖.公共租界鼓浪屿与近代厦门的发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31.
[3]靳明全.区域文化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66-167.
[4]林枫、范正义.闽南文化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
[5]杜维明.对话与创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7.
[6]陈炳聪.丑的魅力[J].福建艺术,2005(1):59.
(责任编辑马诚)
Yuan Yaqin’s Attached Building:Legend of Love in South Fujian
SU Xiaof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Studies,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men 361024,China)
Abstract:Attached Building,a novel by Yuan Yaqin,an authoress of Xiamen,tells a love story between Ah Xiu,a maid and Erlong,illegitimate son of an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an.The novel,set in Gulangyu in south Fujian rich for a colorful history and a unique overseas culture,describes the vivid daily life of south Fujian and impressive characters with typical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ulture of south Fujian.It also reflects the writ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Gulangyu,and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e of the region.
Key words:Attached Building;regional culture;history of Gulangyu;character
[收稿日期]2016-01-19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新世纪人才,JAS14218);厦门理工学院引进人才项目(YSK12017R)
[作者简介]苏晓芳(1971-),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E-mail:xfsu@163.com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432(2016)02-00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