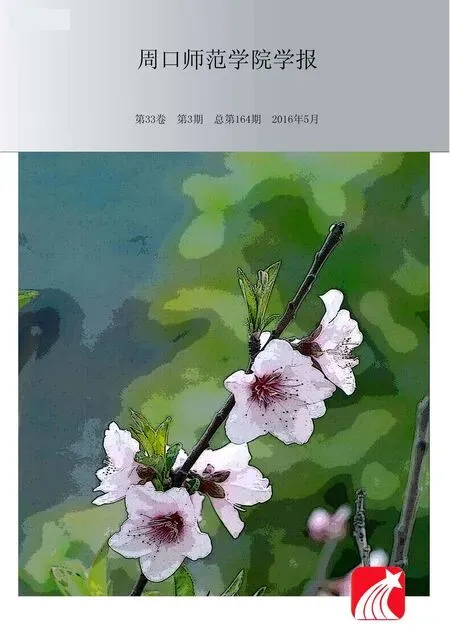性、道、教三位一体:论韩愈《原道》内圣外王的国家治理学说(上)
——兼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比较
刘真伦
(浙江大学 人文高等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8)
性、道、教三位一体:论韩愈《原道》内圣外王的国家治理学说(上)
——兼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比较
刘真伦
(浙江大学 人文高等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8)
摘要:性、道、教及其相互关系,构成治道亦即政治经济哲学的基础。韩愈用《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纲维《原道》全篇:以“仁义”为天命之性,“正心诚意将以有为”为率性之道,“礼乐刑政”为修道之教,构建出一套性、道、教三位一体、内圣外王的国家治理学说。无独有偶,千年以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同情、合宜、仁慈、正义的理论体系与韩愈的学说高度近似,印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通规律。
关键词:韩愈;原性;原道;原教;亚当·斯密
传统文化中的“道”存在着多重内涵,韩愈《原道》所推原的究竟是什么道?《原道》一文的主旨是什么?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程、朱认定《原道》所推为“道之大原”亦即宇宙的本根本体,并据此指责“《原道》只是见得下面一层,源头处都不晓”,以为《原道》只涉及“用”的层面,没达到“体”的高度。其影响延续至今,唐君毅谓“《原道篇》与他文之辟佛之说,若只就其所及之义理而观,正如其诗所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1]401,就是明证。实际上,韩愈乃至孔、孟儒学的“体”,指的是博爱之仁;程、朱乃至老、庄的“体”,才是自然之道、先天之理。韩愈将“博爱之仁”设定为人类本性,正是“道之大原”。韩愈所说的,何尝不是“上面一层”。《原道》所谓“由是而之焉之谓道”[2]1,“道”只是由“性”趋“教”的途径。性体道用,韩愈交代得明明白白。所以,《原道》所原的不是天道而是治道,亦即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之道。韩愈推原天道亦即人类本性的文章,是《原性》而不是《原道》。
明杜希元《新刊正续古文类钞》分析《原道》云:“其言模仿《中庸》首章、《孟子》卒章。”[3]5所谓“模仿《中庸》首章”,约略接触到《原道》的义理结构。《原道》以《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4]1625纲维全篇:“博爱之仁”即天命之性,“礼乐刑政”即修道之教。前者确立了道统的形上本体,后者明确了治道的形下实体。“正心诚意将以有为”即是率性之道,是沟通“性”“教”的理论桥梁。《原道》的创作宗旨,是为即将由中世纪向近现代转型的中唐社会寻求社会治理之道,构建一套符合理性原则的政治经济新秩序。新秩序的基础,是人类共有的先天道德理性,即博爱之仁;新秩序的路径,是社会各阶层的“相生相养”;新秩序的价值准则,是合宜,亦即“行而宜之之谓义”。无独有偶,千年以后的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以构建理性的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宗旨,以先天道德理性即“仁爱”作为人类所禀赋的天性,以“同情”沟通自爱与爱人、利己与利他,以“仁慈”“正义”区分道德教化,以“合宜”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与尺度。二者的高度近似,印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通规律。
一、原性:动物性与人性的辩证统一
人性抽象而玄奥。但简单一点说,人性就是一个人的资质、品类、精神特性,或者说人格类型。前者为形上,后者为形下;前者为隐性,后者为显性;前者为未发,后者为已发。韩愈的人性论,是善性与恶性的辩证统一,动物性与人性的辩证统一。
(一)性:资质、品类、精神特性与人格类型
《说文》“性”字从心、从生,指人生来就具备的先天禀赋。告子曰:“生之谓性。”[5]737《庄子·庚桑楚》:“性者,生之质也。”[6]810成玄英疏:“质,本也。自然之性者,是禀生之本也。”[6]811董仲舒《贤良三策》:“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7]24告子、庄子的说法,强调人性的先天性质;按董仲舒的说法,则“人性”的形成,也不排斥后天的作用。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孔子的说法。《论语·阳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8]240皇侃《义疏》:“性者,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具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及至习,若值善友则相効为善,若逢恶友则相効为恶。恶善既殊,故云相远也。”[8]240又引范宁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斯相近也。习洙泗之教为君子,习申商之术为小人,斯相远也。”[5]240又引旧释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8]240孔子将“性”“习”并列,并以之作为“相近”“相远”的依据,谓性使之相近,习使之相远。这里的“之”,即指人的资质、品类。意思是说,先天的禀赋使得人的资质、品类差距不大,后天的熏习会让人的资质、品类越走越远。资质、品类,指一个人的基本精神素质。它决定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也左右着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按孔子的说法,决定一个人资质、品类、精神特性的,既包括先天的禀赋,也包括后天的熏习。庄子与董仲舒的说法,都只是发挥了孔子说法之一端。
按现代学界一般的说法,人性,也就是人类天然具备的基本精神属性。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基本人性的映射。这个问题,理论的演绎抽象玄奥,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却简单而朴素。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资质、品类、精神特性,或者说人格类型,取决于他的过往经历,尤其是这些经历遗留在他大脑皮层的记忆。这些记忆五花八门、纷繁复杂,但可以简化为两大类:爱恋与恐惧。母腹中的胎儿记住了妈妈的心音,所以刚出生的婴儿特别依恋妈妈的左胸,这里是爱的温床、安全的港湾。这类记忆积淀在人的大脑皮层里,赋予人爱与被爱的本能。母腹中的胎儿,同样也会遭遇饥饿、冷热、颠簸、惊吓;妈妈的惊慌、恐惧、愤怒、绝望,也会传递给他,使他感受到生存的艰辛、无助。这类记忆积淀在人的大脑皮层里,赋予人生存竞争的本能。出生之后的婴儿、幼儿阶段,类似的记忆进一步强化大脑皮层中的心理积淀。同时,这些心理积淀开始左右他的行为方式,并一步一步逐渐固化为他的行为模式。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人的记忆是可以遗传的。所以,上面所说的记忆,不仅仅指个人的记忆,还包括他父辈、祖辈,乃至家族、族群的记忆,这就是人性的由来。人性保存在基因信息中,无法选择、无法改变,所以它是先天的;人生的所有记忆都来源于自身的经历,所以它又是后天的。还应该指出,人的记忆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决定着人生的路向。人人都享受过人生的温暖:妈妈的爱抚、家庭的呵护、师长的理解、朋友的关怀。记住这些,你就学会了感恩、关爱、谦让、宽厚;忘记这些,你就变得冷漠、自私、忌刻、狭隘。人人都经历过人生的挫折:生活的艰辛、学业的艰难、职场的争斗、情场的失意。记住这些,可能有助于你保持旺盛的斗志与进取精神;但对此念念不忘或者纠结不休,也有可能阻碍你前进的步伐,甚至将你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上面的说法很容易让人推导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富裕家庭的子弟比较容易养成仁慈宽厚的性格,贫困家庭的子弟比较容易养成偏狭残忍的性格。表面上看,这样的结论颇有阶级歧视尤其是歧视劳动阶层的味道,但却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人性的形成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得到多少爱,就会储存多少爱;得到多少恨,就会储存多少恨。心理的积淀,最终固化为人格类型。反过来,记住了多少爱,就会回馈社会多少爱;记住了多少恨,就会回馈社会多少恨。人格类型,最终外化为行为模式。以中唐社会而论,最凶残的社会群体有三个:宦官、牙兵、游民。唐代宦官大多是来自边远山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家子弟;唐代的牙兵,一开始就以内迁的六州胡为主体;唐代的游民,无论是内使诸司小儿还是黄巢、朱温等盐枭乃至《新五代史·伶官传》中那些伶人,无一不是贫苦出身。儿时的可怕经历储存在他们记忆深处,积淀为残忍暴戾的基因。不过有必要指出,这些人与劳动者阶层毫无关联,他们属于无业游民。真正的工人、农民,有家有业,是不会参与这种玩命游戏的。当然,富家子弟未必都能成长为仁人,贫家子弟也未必都会成长为暴徒。根本的差异,还在于自己的选择:选择记住什么,选择遗忘什么。尧、舜、禹、汤与桀、纣、厉、幽,同样出身于贵族家庭;特蕾莎修女与希特勒、武训与马加爵,同样出身于平民家庭。前者养成了仁慈宽厚的人格类型,后者养成了狭隘忌刻的人格类型,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韩愈人性论:善性与恶性的辩证统一
先秦人性理论的四个主要流派: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两汉时期由性无善恶论发展而来的扬雄人性善恶混论、由性有善有恶论发展而来的董仲舒、王充、荀悦的性三品论,韩愈都有所借鉴。
《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4]1625,郑注:“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孝经说》曰:‘性者生之质命,人所禀受度也。’”[4]1625孔颖达疏:“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无名,强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刚柔好恶,或仁,或义,或礼,或智,或信,是天命自然,故云谓之性。”[4]1625
韩愈的人性论以性三品为理论外壳,以孟子的人性本善为内涵实质。具体说来,孟子以先天道德理性作为人类与生俱生的本性,以“存”“养”“放”“弃”区分现实社会的人格类型,认为人人本性都有善端,但存之、养之则为善,放之、弃之则为恶。韩愈《原道》以“博爱之仁”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原性》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人性的内涵结构,同样将人性归结为道德理性。至于现实社会中善恶的分化,是因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2]47,认为上品的“善”是五常完备的结果,下品的“恶”是五常缺失的结果,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以道德理性的完备与缺失来区分人性的善恶,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现代人格心理学有关人格缺失的理论正是这样诠释人格类型的差异,和韩愈的理论方法非常接近。这一部分内容,笔者已经有专文详细阐述,参见拙文《韩愈性三品理论的现代诠释》。和韩愈相似,亚当·斯密同样以仁慈或仁爱作为人类所禀赋的神性,亦即先天道德理性:“在神的天性中,仁慈或仁爱是行为的唯一规则,神的行为所表现的全部美德或全部道德最终来自这种品质。美德存在于仁慈之中,这是一个被人类天性的许多表面现象所证实的观点。”[9]395-396同时,亚当·斯密将“仁慈感情的缺乏”视为“道德上的缺陷”[9]397,也和韩愈的观点相当接近。
以下,试为检讨韩愈对性恶理论以及其他人性理论的吸纳或扬弃。
韩愈对荀子的性恶理论有深刻的领会。人本来就是动物的一分子,动物所具有的禀性,人类也都一一具备。举凡趋利避害、贪生怕死、好逸恶劳、沽名钓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自傲自大、自暴自弃、懈怠、懒惰、贪婪、忌刻、阴贼、残忍,种种丑恶现象,人类社会并不少见。《荀子·性恶篇》列举的人类种种恶性,生而好利、生而疾恶、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实际上都是人的真情实性,属于人的动物本性。作为动物人本能的生存要求,它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无所谓好坏,无所谓善恶。荀子所谓“性恶”,相对于礼义而云然,指人类天性中不符合礼义的自然缺陷,并没有邪恶的含义。所以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0]434,杨倞注:“伪,为也,矫也,矫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故为字‘人’‘傍’‘为’,亦会意字也。”[10]434从总体上讲,韩愈对荀子的性恶论是肯定、接受的。《原性》所谓“得其一而失其二”,就荀子而言,所“得”的,就是性恶。正因为如此,他也就同时接受了荀子的劝学。如同荀子将《劝学篇》置于全书之首一样,韩愈也将学习置于化性起伪之首,“学”与“不学”决定“移”与“不移”,就是明确的证据。韩愈讨论人性,从来都不避讳人性的缺陷。他不讳言自己早年为了生存“求禄利”“争名竞得失”“为利而止真贪馋”,也敢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甚至包括他本人直接侍奉的三位皇帝的性格缺陷。他的《原毁》就专门剖析人性中的“怠与忌”。他也知道,人性的缺陷来自于天性,《天之说》对天、人同样自爱自利就有深刻的认识。这一些,都来自于荀子的影响。归根结底一句话:人类的生存要求,包括其中不符合礼义的自然缺陷,都是动物人生存竞争的本能,无所谓善恶。即便是人类公认的美德,如爱人、利他,也来自于自爱、自利。自爱是爱人的基础,自利是利他的基础,二者并非水火不能相容。《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4]1629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恻隐之心”,就是通过推己及人,由“亲亲”推演而来。韩愈的“博爱之谓仁”,正是“恻隐之心”“仁者爱人”的升华。而且退一万步讲,在由个体集合而成的社会群体中,没有个体,又哪来的群体?没有“仁者”,又哪来的“爱人”?人类社会由中世纪向近现代转型,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是必不可少的大前提。“求禄利”表达自我生存的要求,“行道”表达自我完善的要求。韩愈明确地将“求禄利”与“行道”并列为人生的两大目标,原因即在于此。和韩愈一样,亚当·斯密并不一般性地反对自爱与自利,他认为,“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是恰当和正确的”[9]101-102。“自爱是一种从来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一方面成为美德的节操。当它除了使个人关心自己的幸福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后果时,它只是一种无害的品质。虽然它不应该得到称赞,但也不应该受到责备。”[9]399同时,由于人人都具备自爱的本性,所以推延开来,人人都能够理解他人的自爱,亚当·斯密把这样的本性称之为同情(sympathy):“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9]5通过“同情”,亚当·斯密把自爱与爱人、利己与利他联系到一起。当然,自爱与自利在前,爱人与利他在后,这就是亚当·斯密先做《道德情操论》后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的根本原因。简而言之,构建现代思想体系,必须以人格独立、个性解放为基础;构建现代社会经济秩序,必须以个体权利保障为基础。没有完善的个体就不会有完善的社会,二者的序位不能颠倒。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和韩愈的义利观也有相通之处。
归纳起来讲,韩愈高度褒扬孟子人性本善的理论,实际上是着眼于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特殊性;韩愈接受荀子的性恶理论,实际上是着眼于人类与动物相通的共性。无论是共性还是特殊性,都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另外,“性”属形上,“善恶”属形下,二者并不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11]225。性无善恶、性有善有恶,才是性三品的逻辑前提。所以,韩愈的性三品并非前人的性三品,性善、性恶、性无善恶、性有善有恶,都包含其中。但从根本上讲,性善、性恶的对立统一,才是韩愈人性论的核心内容。性善、性恶、性善性恶的对立统一,构成了韩愈人性论的三位一体。换言之:人的动物性,集中体现了人类的生存需求,人类的聪明、才智、勇敢、坚毅、进取精神、冒险精神、探索精神、理性精神,都来自于这里,柳宗元将其归结为“明”与“志”,今人统称为功利理性、工具理性、科学精神;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特殊性,集中体现了人类自我完善的需求,人类的群体意识、团结、合作、秩序、相互关爱就来自于这里,荀子将其归结为“群类”“纲纪”“礼法”,孟子将其归结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韩愈将其归结为“博爱之谓仁”,今人统称为道德理性、价值理性、人文精神。韩愈倡言博爱,同时并不排斥积极进取的理性精神;二者的辩证统一,才构成了韩愈人性理论的全体。程、朱不承认“性恶”,其所以排斥韩愈,根源正在这里。今天我们还有必要讨论韩愈的人性理论,其原因也在这里。
二、原道:反身而诚的正道与急疾为治的邪道
《礼记·中庸》“率性之谓道”[4]1625,郑注:“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谓道。”[4]1625孔颖达疏:“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违越,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义行义之属,不失其常,合于道理,使得通达,是率性之谓道。”[4]1625
《原道》云:“道有君子小人。”[2]1君子之道,即仁义之途,但怎样走上仁义之途,也存在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至于小人之道,同样是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
(一)道:大道与小径
“道”,其本义为道路。《尔雅·释诂》:“道,直也。”[4]2575郭璞注:“道无所屈。”[4]2575《说文》:“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12]73段注:“首者,行所达也。道人所行也,故从辵。《释宫》文:行部偁‘四达谓之衢’,九部偁‘九达谓之馗’。”[12]73《释名·释道》:“道,一达曰道。二达曰岐,三达曰剧,四达曰衢,五达曰康,六达曰庄,七达曰剧。”[13]18所谓“一达”,相对于“二达”“九达”而云然,谓指往一个方向的道路,也就是直路。道、路,又有大义。《诗·大雅·皇矣》:“帝迁明德,串夷载路。”[4]519毛传:“路,大也。”[4]519冯衍《显志赋》:“遵大路而裵回兮,履孔德之窈冥。”[14]988《后汉书》章怀太子注:“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泛兮。”[14]989王安石《洪范传》:“路,大道也。”[15]691元吴澄《无极太极说》:“道者,大路也。”[16]卷4
与大路对应的是径、蹊,指小路、小径、邪径、捷径。《老子》五十三章:“大道甚夷,而民好径。”[17]203河上公注:“夷,平易也。径,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从邪径也。”[17]203王弼注:“言大道荡然正平,而民犹尚舍之而不由,好从邪径,况复施为以塞大道之中乎。”[18]141《礼记·祭义》:“道而不径。”[4]1599孔颖达疏:“道而不径者,谓于正道而行,不游邪径。正道平易,于身无损伤。邪径险阻,或于身有患。”[4]1599《吕氏春秋·孝行》:“舟而不游,道而不径。”[19]308高诱注:“济水,载舟不游。涉行道,不从邪径。”[19]308《说文》:“径,步道也。从彳,巠声。”[20]36徐锴《系传》:“道不容车,故曰步道。”[20]36《释名·释道》:“步所用道曰蹊。蹊,系也,射疾则用之,故还系于正道也。俓,经也,人所经由也。”[13]18《史记·高祖本纪》“前有大蛇当径”[21]347,索隐引郑云:“步道曰径。”[21]348《玉篇》:“蹊,遐鸡切,径也。”[22]133朱熹《楚辞集注》:“捷,邪出也。径,小路也。”[23]8
将大道、大路的概念引申到社会领域,指人生的正道、正路,《尚书》已经如此。《书·洪范》:“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4]190孔传:“言无有乱为私好恶,动必循先王之道路。”[4]190孔颖达疏:“无有乱为私好,谬赏恶人,动循先王之正道。无有乱为私恶,滥罚善人,动循先王之正路。”[4]190曾巩《洪范传》:“作好作恶,偏于己之所好恶者也。好恶以理,不偏于己之所好恶,无作好作恶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径,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异辞也。”[24]163明王守仁《送宗伯乔白岩序》:“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奕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25]228
将小路、小径的概念引申到社会领域,指人生的邪径、捷径,《论语》已经如此。《论语·雍也》:“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4]2478皇侃义疏:“言灭明每事方正,故行出皆不邪径于小路也。一云:灭明德行方正,不为邪径小路行也。”[4]2478邢昺疏:“此言其人之德也。行遵大道不由小径,是方也。”[4]2478《管子·短语》:“令之以终其欲,明之毋径。”[26]893房玄龄注:“行令所以终人之欲,使之明识正道,不从邪径也。”《易林·鼎》:“阴雾作匿,不见白日。邪径迷道,使君乱惑。”[27]246
将“道”“路”与“捷径”对举,用以区分正、邪不两立的不同人生路径,《楚辞》已经如此。《离骚》:“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28]8王逸章句:“路,正也。言尧舜所以能有光大圣明之称者,以循用天地之道,举贤任能,使得万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称近以及远,明道德同也。捷,疾也。径,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纣愚惑,违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暇及带,欲涉邪径急疾为治,故身触陷阱,至于灭亡,以法戒君也。”[28]8洪兴祖补注:“路,大道也。”[28]8《书·大禹谟》:“侮慢自贤,反道败德。”[4]137孔安国传:“狎侮先王,轻慢典教,反正道,败德义。”[4]137孔颖达疏:“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谓自得于心。反正道,从邪径,败德义,毁正行也。”[4]137
(二)邪道:急疾为治、施行惶遽
大道悠远而漫长,所以《离骚》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8]27君子之道指仁义之途,上文已详,此处不再重复。以下讨论小人之道。
小道为捷径、近路,凡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者,大多难逃其诱惑。所以“急疾为治”“施行惶遽”八字,写历代暴君“欲涉邪径”的急切之态,可以说是入骨三分。盖历代暴君大多并非昏君,而多为雄才大略之辈。其所以暴,大多是为了一个宏图大业,比如修长城、修运河、治理黄河之类。而一统天下,或抵抗游牧部落入侵,如抗匈奴、抗鲜卑、抗突厥、抗女真、抗蒙古、抗后金等,更是荫及子孙的千秋大业。这些事业本身关系到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系到百姓的安居乐业,其合法性不成问题。秦代的长城工程、隋代的运河工程、元末的治黄工程,从工程技术设计以及工程技术效益的角度讲,都不失其合理性。他们受到后人的质疑,不是因为他们的目标,而是因为他们实施这些工程的手段,或者说为实现目标而选择的路径。现代武侠小说笔下的正派武功、邪派武功,二者的武功高下并没有多大区别,甚至二者的道德人品也同样各有良莠。他们的区别,就在练功的方法上。正派武功无论少林、武当,强调的是日积月累,穷数十年岁月以达到功力的炉火纯青。邪派武功则讲究速成,无论是吸星大法还是逍遥神功,都是瞬息之间将他人功力据为己有;或者咬破舌尖,将自己一生的潜能在瞬息之间爆发出来。正派武功与邪派武功的目标是一致的:成为天下第一人。二者的成就也相去不远,大多都能完成自己的理想,一战成功。但最终的归宿,却相去甚远:正派人物功成名就,飘然隐退;邪派人物功成名就,或走火入魔终生癫狂如欧阳锋,或血竭气尽生命凋零如厉胜男。走邪道的暴君与邪派武功高手一样,追求的都是一夜暴富、一蹴而就。穷数十年岁月以达到功力的炉火纯青,大道、正道实在是太过漫长了。一万年太久,他们实在等不起。
不管什么宏图大业,急需的都是人力、物力。所以尽管历代暴君的花招五花八门,最终选择的都是见效最快、效率最高的手段:聚敛。而集中财力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利用政权暴力实施经济垄断。这一招,周厉王的宠臣荣夷公已经发明了。荣夷公“好专利”,厉王用为卿士。《易·说卦》“震为专”[4]94,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姚云:“专,一也。”[29]65所谓“专利”,即“专百物”,也就是王室一家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反对的意见也不是没有,芮良夫就劝谏过厉王:“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30]13-14韦昭注说得更明白:“专利,是专百物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将取用之,何可专其利也?”[30]13聚敛之臣所“专”的“百物”,其实就是普通百姓的身上帛、口中黍。其后虢石父“好利”,周幽王用之,看来传统已经形成了。这一传统的理论概括,最早的应该是管仲。《管子·国蓄》:“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26]1262安井衡曰:“出于一孔,专出于君也。二孔,君与相也。三孔、四孔,则分出于臣民矣。”[26]1263继承这一传统并取得成功的应该是商鞅、韩非。《商子·弱民》:“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31]155《商子·靳令》:“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用。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31]108《韩非子·饬令》:“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32]473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这一传统居功厥伟。这就是近道,这就是捷径。不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取之于民,用之于国,快捷而便当。而且“用之于国”“为国理财”,堂皇正大,理直气壮。自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33]4227,富国强兵就成为一面旗帜。从汉武帝盐铁官卖到德宗两税法,从王安石青苗法到张居正一条鞭法,捷径、近道,一帆风顺。近代中国康有为、严复乃至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只要看看“原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最终被统一翻译为“国富论”就可以知道了。对于聚敛之臣的捷径、近道,儒家先贤一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4]2499《礼记·大学》:“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4]1675孔颖达疏:“盗臣损财耳,聚敛之臣乃损义。”[4]1675对于富国、利国,孟子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5]35所谓“利吾国”“利吾家”“利吾身”,其实质都是利己。上下交征利,不篡夺君位不足以餍饱其欲,则国危矣。对儒家而言,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不是上下交征利,而是提高人的文明素质,尤其是提高那些掌握着国家权力与社会资源的君主与权臣们的素质,以降低权力肆虐的风险。韩愈明确反对“速化之术”[2]731,对唐德宗专制独裁、聚敛搜刮的批判,对宫市的抨击,对钱重物轻的批评,对张平叔盐政的批评,都集中体现了他对捷径、近道的态度。
(三)正道:反身而诚、修身正心诚意
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也就是人自身一步步得到解放、得以完善的过程。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生活在大自然的强力统治下,没有丝毫的自主能力,生活在上天的阴影之下,人人都是上帝的奴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开始组织起来,用群体的力量对抗外来的暴力。而群体的组织者奴隶主最早觉悟到了自己的力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最早摆脱了对上帝的依赖,最早得到了解放。王族、部落酋长,就是第一批获得解放的自由人。到了封建社会,王与马,共天下。皇族的统治必须得到世家贵族的支持,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这一时期,拥有土地的贵族也拥有了一份自信,《仪礼·丧服》“君至尊也”[4]1100,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4]1100就透露了其中的信息。世家贵族,成为第二批获得解放的自由人。到了中唐,随着两税法取代均田制,土地买卖更加自由。和均田制分得国有土地不同,买来的土地产权自有,有产的农民开始有了自信,也开始有了自由。与此同时,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的劳动者也得到了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他们可以自主地选择居住地,选择职业,选择老板。用脚投票,就是他们的自由。韩愈笔下的王承福,柳宗元笔下的郭槖驼、宋清、杨潜,就是其中的代表。读书人也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们开始尝试摆脱官场的束缚,寻求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隐居盘谷的李愿、试大理评事王适以及韩门孟郊,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原道》“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2]4,就透露出他们的自信。可以说,士、农、工、商,平民百姓,开始成为最后一批获得解放的自由人。尽管他们的上进之路还铺满了荆棘、充满了艰辛,但只要“民焉而事其事”,而且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还没有完全堵塞,他们都能够生活在希望之中。以一个普通平民的成长为例,或读书,或种地,或做工,或经商,青少年时期,大都贫困艰难。中年以后,或学业有成,或技术进步,或日积月累,终于成为官员,成为能工巧匠,成为豪商巨贾。即或不至,也小有所成,衣食无忧。那么,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个体的历时态发展与群体的共时态分化,就构成了社会分层的动态均衡。这就是等级,这就是秩序。就个体而言,决定自己社会位置的只有自己,“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34]1011。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就是个性解放、个体至上的时代精神。
对于刚刚获得解放、获得自由的人们而言,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权威,而是来自于内在的惶恐。摆脱了神的控制,同时也就失去了神的庇护;摆脱了长上的控制,同时也就失去了权力的庇护。孤独与不安,让他们试图逃避刚刚得到的自由。弗洛姆《逃避自由》,就反映了这样的惶恐。其实,孤独与不安之外,对自我的茫然无知,才是人们最大的惶惑。他们不了解自己能力的边界,也不了解自己欲望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就成为时代的迫切课题。启蒙时代的西方思想家选择了这条道路,中唐时期的思想家同样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当然,这条道路悠远而漫长,不可能吹糠见米、立竿见影,宋元新儒学、现代新儒学,都还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而导乎先路的,正是中唐儒学复兴运动,正是这一运动的旗手韩愈。
韩愈为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开出的药方,是身心修养,是《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内圣之学,其核心是一个“诚”字:“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4]1632郑玄注:“言诚者,天性也。诚之者,学而诚之者也。”[4]1632在韩愈看来,《孟子·尽心上》“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礼记·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4]1632是讨论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答侯生问论语书》以“反身而诚”为“践形之备”,为宋明道学转向内在开辟了先路。同一时期,思考这一问题的还有欧阳詹、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人。欧阳詹《自明诚论》:“自性达物曰诚,自学达诚曰明。”[35]6041柳宗元《天爵论》:“夫天之贵斯人也,则付刚健纯粹于其躬。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35]5877刘禹锡《赠别君素上人并引》:“曩予习《礼》之《中庸》,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悚然知圣人之德,学以至于无学。然而斯言也,犹示行者以室庐之奥耳,求其径术以布武,未易得也。晚读佛书,见大雄念物之普,级宝山而梯之,髙揭慧火,巧镕恶见,广疏便门,旁束邪径。其所证入,如舟沿川,未始念于前而日远矣,夫何勉而思之邪?是余知穾奥于《中庸》,启键关于内典。会而归之,犹初心也。”[36]389韩愈、李翱主张自诚而明,欧阳詹、柳宗元主张自明而诚,其说相反相成,相互补充。《中庸》所谓“诚”,“天之道也”[37]31,朱熹释为“天理之本然”[37]31;周敦颐所谓“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38]436,即人类本性。由天之道到人之性,“诚”之性质已有重大变化。其间转换枢纽,即在韩愈、李翱。《答侯生问论语书》以“反身而诚”作为“践形之道”,合孟、荀为一。二程“尽人道”、杨时“尽则”、王夫之“尽性”“即身而道在”[38]93即出于此,尤堪注意。
《省试颜子不贰过论》:“所谓过者,非谓发于行,彰于言,人皆谓之过而后为过也,生于其心则为过矣。故颜子之过,此类也。不贰者,盖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2]529以“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不能无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于外”为“不贰”,将“言行”的根源追溯到“始萌”“未形”之先,追溯人的行为方式背后隐藏的心性本源,追讨形下事物的形上依据,这样的思路,同样来自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4]1625郑玄注:“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4]1625未发之中,形上也;已发之节,形下也。“始萌”即“未发”,“言行”即“已发”。“已形”“未形”,“已发”“未发”,开宋人心性之学。
由个体的心性修养到群体的社会责任,亦即由“性”到“教”的路径,也就是“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关注的就是“性”“道”“教”的关系问题。韩愈以《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4]1625作为《原道》全篇的义理结构,以“仁义”为天命之性,以“礼乐刑政”为修道之教,作为联系二者的路径,韩愈选择了《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4]1673并特别强调其“将以有为”的性质。儒家的修养以“有为”为目的,与佛道二家空谈心性截然不同。
陈寅恪先生特别重视《原道》的这段文字,称之为“吾国文化史中最有关系之文字”[39]228。其云:“退之首先发现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39]228
《原道》首先将“博爱之仁”提升为人类的本质属性,选择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系统的价值本体,为道统确立了自己的形上依据;然后通过揭示人类社会相生相养之道,明确百姓日用与礼乐刑政之间的本末关系,为道统确立了自己的践履方向;再向前推进一步,《原道》在形下的日用践履与形上的心性修养之间构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这就是大学之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4]1673从“正心”“诚意”到“治国”“平天下”,个体的自我实现与群体的社会责任,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礼记·中庸》开篇即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4]1625上天赋予人类特有的本性,乃是仁义之性;人类社会礼乐刑政的根本依据,是百姓的生存需求;而沟通这“天命之性”与“修道之教”的桥梁,则是遵循仁义本性的修齐治平之道。“性”“道”“教”三位一体,《大学》《中庸》亦由此贯通。《大学》《中庸》流传千年,群儒莫窥其奥。《原道》首次将“性”“道”“教”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将儒家的内圣与外王贯通为一体,将个人修养的心性之学与社会治理的经世济民之道融合为一体,其理论价值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2]刘真伦.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杜希元.新刊正续古文类钞·卷一七[M].明嘉靖四十年自新斋刊本.
[4]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7]董仲舒集[M].袁长江,等校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8]论语集解义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9]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0]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曾枣庄.三苏全集:第3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1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3]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吴澄.吴文正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7]河上公.老子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8]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0]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2]顾野王.宋本玉篇[M].北京:中国书店,1983.
[23]朱熹.楚辞集注[M].听雨斋雕版.
[24]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6]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7]尚秉和.焦氏易林注[M].北京:光明出版社,2005.
[28]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9]黄焯.经典释文汇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0]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1]高亨.商君书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2]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3]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4]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5]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6]刘禹锡.刘禹锡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8]中国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3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DOI:10.13450/j.cnki.jzknu.2016.03.001
中图分类号:I2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476(2016)03-0001-08
作者简介:刘真伦(1947-),男,重庆奉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
收稿日期:2016-02-16
——“原道”传统与刘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