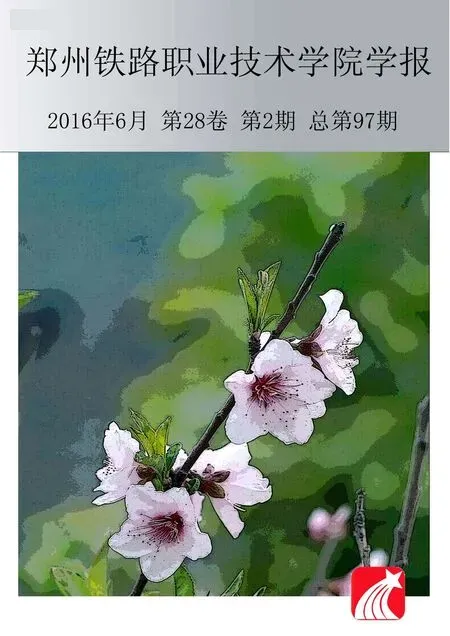鲁迅笔下的国民性问题解析
荆煜君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鲁迅笔下的国民性问题解析
荆煜君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450052)
摘要:从贫穷愚昧、精神胜利法、尊崇势利、麻木冷漠、自私俭啬贪便宜五个方面分析了鲁迅作品中的国民性弊病,其不仅具有“老中国”的时代特征,而且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的人性特征。
关键词:鲁迅作品;国民性;人性
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为了“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出自《<自选集>自序》),即国民性弊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在当时深深震动了国人的灵魂,而且在此后的漫长岁月、广阔地域中引起人们的思索。例如,《阿Q正传》于20世纪20年代在报纸连载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阿Q写的是自己”,甚至到了现代社会,北大的“日本、韩国、美国、欧洲很多地方的留学生都说他们国家也有阿Q”。这说明鲁迅先生笔下所揭示的国民性不仅具有“老中国”的时代特征,而且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的人性特征。就这一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析。
一、贫穷愚昧
贫穷和愚昧如孪生兄弟,常常同时出现。
《药》里的华老栓,是开茶馆为生的城市贫民,家里点的是“遍身油腻的灯盏”,盖的是“满幅补丁的夹被”,听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的传言,花了大笔积蓄为生病的独子买人血馒头治病,最后儿子还是不治而终。
《阿Q正传》的主人公阿Q,没有家,没有固定职业,在村里靠给人打短工维持生计,最终被举人老爷和把总当作抢劫犯抓了起来。阿Q糊里糊涂地接受了一次讯问,懵懵懂懂地在供状上画了一个很不满意的圆圈,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祝福》里的祥林嫂,在失去了家人和房子后来鲁镇做工,因为嫁过两个男人而备受歧视。一个吃斋念佛的女人告诉她:“你将来到阴司去,阎罗大王要把你锯开来分给两个死鬼男人。”这话带给祥林嫂极大的恐惧,她听信那个女人的建议,以历来积存的工钱为代价,去土地庙捐了个门槛,希望赎了这一世的罪名。但人们依然嫌弃她,她后来成了乞丐,倒毙在祝福的前夜。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自己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出自《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们生活在旧中国闭塞、落后、贫困的乡村市镇,极少识字,无知无识,基本不能脱离社会底层,往往成为盲从迷信、任人宰割的羔羊。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在那些文化素质极低的人身上,仿佛还能看到这类人的影子。
二、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标签,也是当时中国国民性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妄自尊大。阿Q虽然穷到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但他却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他跟人口角的时候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虽然娶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却想: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他在祖上和后代虚拟的荣光里自豪着,支撑着他现世可怜可悲的生存状态。
阿Q还很自大。他称之为“长凳”的,城里人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他生活的未庄煎鱼用葱叶,城里人却用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但同时他又鄙薄未庄人是不见世面的乡下人,“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这段精彩的描写令我们想到生活中一些唯我独尊的人。
二是失败后的自欺。阿Q经常沦为闲人们玩笑殴打的对象,失败之后的阿Q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心满意足的得胜似地走了”。曾经他自认是“虫豸”却依然被人揪着黄辫子在墙上碰了五六个响头,他也不过10秒钟就又“心满意足的得胜似地走了”,这回他评价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那简直是同状元一般的荣誉啊!只有那次赌钱,他赢得的一堆很白很亮的洋钱被人趁乱抢走了,他确乎有些沮丧。但擎起右手用力地打了自己两个嘴巴之后,他就心平气和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阿Q每次失败之后都能很快地在精神上获得胜利,用的是自欺的法儿。
三是失败后的遗忘。阿Q在受辱后还有一件祖传的宝贝叫“忘却”。比如那次因为挨了王胡的打,正忿忿之际瞧见了假洋鬼子,他不意中将骂语说了出来,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在他头上啪啪啪了几下,但这“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还有那场悲催的恋爱事件,阿Q因为向赵府用人吴妈求爱,被秀才大爷拿大竹杠痛揍一顿,然而“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便照常做工,听得外面吴妈哭得热闹,他还要凑过去看,想打听缘故。他实在是太健忘了!
四是将失败归因于命运。无辜的阿Q作为抢劫嫌犯被抓进牢里,“倒也并不十分懊恼”,因为“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最终他被押上囚车,游街示众杀头,鲁迅都套用了阿Q“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的逻辑来描绘他的麻木心境。
许多学者都指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自清末以来,备受屈辱的背景下,自上而下的一种弱国弱民的自慰心态,沉湎于此的民族是不思进取没有未来的民族。此言不谬!然而在今天,我们仍然能从沉沦在挫折中,寻找种种借口而不能奋起的人身上看到阿Q相;反观自身,在某时某刻,是不是也产生过如阿Q般的逻辑呢?
三、尊崇势利
尊崇势利就是对于权力、财力、武力、智力等方面强势的一方给予格外的尊敬和崇奉,同时对于弱势的一方给予相当的鄙薄和轻视。
在阿Q生活的未庄,赵太爷之流格外地受到尊敬,首先是因为有钱。当阿Q信口说自己和赵太爷是本家,被太爷一个嘴巴一顿怒骂剥夺了姓赵的权利后,大家自然地认为错在阿Q,“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其次是因为有文化,他们“都是文童的爹爹”。当然,正因为有钱有文化,他们才有机会结识城里更有势力的举人老爷,才能在革命大潮到来的时候投机到革命阵营中去,屹立于上层而不倒。
观之阿Q,他在未庄打短工,又穷又乏的时候,是众人欺侮的对象。当他进城回来,穿着“新夹袄”,腰间“挂着一个大褡裢”,手里“满把是银的铜的”,这时候人们对他就给予了未曾有过的尊敬。当阿Q大嚷着“造反了!造反了!”,自认为做了革命党的时候,一向威风凛凛的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他叫“老Q”,“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地和气,请他喝茶”。人们对阿Q的态度,是随着他运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药》中,当那个代表权势武力、满脸横肉的康大叔出现时,众人是怎样的卑躬屈膝啊!“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花白胡子的人更是走上前,低声下气地请教。对他的讲话,众人也是应声附和。
在《孤独者》中,人们的势利也表现得格外令人心酸。当魏连殳有钱时,房东的孩子和他亲热且不客气,他的客厅里常有几个“不幸的青年”或者“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待到他失业的时候,客厅里“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没有了“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甚至房东的孩子连他的东西“也不要吃了”。再到他为了“活几天”而给杜师长当顾问时,他的曾满布灰尘的客厅里又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
尊崇势利的心理衍生的最坏恶果是欺软怕硬。你看阿Q,在赵太爷、假洋鬼子面前表现的是如此卑怯畏缩;在衙门大堂见到“一脸横肉”的把总,“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一副奴才相,但在无权无势的小尼姑面前却是强者,恣意调笑凌辱。《风波》里的七斤嫂,面对赵七爷“没有辫子,该当何罪”的质问,气急败坏,不顾邻居八一嫂解劝的好心,把一腔怒火转嫁到这个可怜的寡妇身上。这种“爷爷面前装孙子,孙子面前装爷爷”的剧目,在现代社会还经常上演。
四、麻木冷漠
读过《<呐喊>自序》的人都会记得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也会记得先生对此的评价:“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可以说,麻木冷漠的看客现象是鲁迅心中挥之不去的痛,他在作品中多次做过辛辣的嘲讽和冷峻的抨击。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喜欢无聊地围观。《阿Q正传》中,闲人们顶喜欢围观热闹场面。阿Q欺侮小尼姑,“酒店里的人大笑了”,使得阿Q更得意更卖力地表演。阿Q和小D互掐,看的人“好!好!”地煽动。《示众》里,巡警牵了一个罩白背心的男人在街边示众,“刹那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其中有丢下包子摊不顾的胖孩子,秃头、红鼻子的胖大汉,抱孩子的老妈子等人。老妈子“旋转孩子来使他正对白背心,一手指点着,说道:‘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究竟有多好看呢?小说没有讲,总之就是无聊地围观!围观!
第二,喜欢鉴赏别人的痛苦。鲁迅先生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
《孔乙己》中,咸亨酒店的人围观哄笑孔乙己,这个说:“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那个说:“你一定又偷了人家东西了!”还有“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他们在孔乙己狼狈的窘态中获得许多快乐。
《药》里面,革命志士夏瑜被杀,早有“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他们在等待;犯人带到行刑,他们“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他们在鉴赏。
《阿Q正传》里,阿Q上城回来,唾沫横飞地对未庄人描绘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待到阿Q被抬上车游街示众,“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从中不时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喝彩声,事后“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
《祝福》里的祥林嫂,儿子惨死的故事成为大家咀嚼鉴赏的材料,有些老女人甚至专门寻来听她讲述。她反复地讲,反复地哭,终于被大家厌倦了。后来,他们又对她再嫁时额上撞出的伤疤发生了兴趣,纷纷引逗她开口。麻木的祥林嫂,也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知道再无搭话的必要。
这种毫无恻隐之心的、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卑劣行径,在鲁迅作品中多有体现,可见先生有多么深恶痛绝!
第三,对他人命运的漠视。比如孔乙己,他曾是咸亨酒店的欢乐之源,但小伙计说:“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只有掌柜的时不时会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因为他关心的是“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酒店里知底细的人讲到孔乙己被打折了腿,“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的不再问。
同样语气的对话还出现在《祝福》和《伤逝》中。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问。‘老了。’‘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怎么死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
“‘……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罢,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我惊得没有话。‘真的?’我终于不自觉地问。‘哈哈。自然真的……’‘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
同样的淡漠!同样的冰冷!一个生命的逝去激不起他们心中丝毫的涟漪!我们从字里行间能看到鲁迅先生难掩的悲哀。
说到人性中的麻木冷漠,恐怕不是旧中国民众独有的。二战后有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牧师写过一首忏悔诗:“纳粹杀共产党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这首诗被镌刻在一座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
在极权统治的压迫下,在愚昧落后的环境中,对他人的冷漠终将回报到自己身上,就像阿Q一样。
五、自私、俭啬、贪便宜
自私是人性中最天然的部分。人类自有文明以来,总是把它纳入法律和道德的轨道内,免得它恣肆横行。但有时却约束不住,未免酿出些大大小小的故事。
《长明灯》里,吉光屯的头面人物四爷的侄子,口口声声要熄灭大家视若命根的社庙里的长明灯,被大家看成疯子,要将他关起来。四爷处心积虑地想趁机占据侄子的房产,于是绕着弯儿地提到“舍弟也做了一世人”,“香火总归是绝不得的”,但侄子“单知道发疯,不肯成家立业”。而自己的儿子“秋天就要娶亲”,“生了儿子,我想第二个就可以过继给他。但是——别人的儿子,可以白要的么?”自然地绕到了房子这儿。话虽然曲折,可是自私的嘴脸还是昭然若揭。
《伤逝》里的涓生,在冲破封建的阻碍同子君同居之后,受到生活上的一系列打击:失业,经济困顿,小家庭难以为继。涓生这时认为,“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最终决然地向子君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样绝情的话,导致子君回到父亲家里,不久抑郁而终。涓生的作为令人想到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的话,“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重要,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俭啬,即是俭朴到了吝啬的程度,当然,它不包括贫穷的因素。与之相连的往往还有贪便宜的行为。大概是《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临死前那两茎灯草太有名了吧,鲁迅先生写人的俭啬喜欢从油灯写起。
《风波》里的七斤,“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锄头柄了”,在村人里面“已经是一名出场人物了”,但傍晚回家太迟,吃饭要点灯,还是要被女人骂的。他的女儿不小心摔破了饭碗,七斤就直跳起来,一巴掌打倒了女儿。后来,他将碗拿到了城里,花了四十八文小钱补了十六个铜钉,让女儿接着用。
《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因为有钱格外受人尊敬”,但他家晚饭后“定例不准掌灯”。例外的情况不多,其一“便是阿Q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我们推测,这不会只为了阿Q舂米方便,十之八九是为了缩短工期少算工钱的缘故。再有就是赵家想从阿Q手里买点儿便宜的赃货,“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在《恋爱的悲剧》这一章,地保和阿Q定了五条赔罪条件,其一是一斤重的红烛一对、香一封——其后赵家并未用到为吴妈祓除缢鬼的场合,而是“留着了”,“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其五是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阿Q“调戏”赵家用人,被克扣工钱倒罢了,那布衫本是阿Q逃离赵府时丢下的,后来“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以赵太爷的身份地位,居然也贪图这微不足道的便宜!
再说《故乡》里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她伶牙俐齿地对“我”说:“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她不是“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就是“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活脱脱的一副贪利小人模样!
六、结语
而今,鲁迅笔下的这些“老中国”的国民性弊病并未根除,它依然存在于广大民众身上,就像网络写手描述的,“孔乙己复活了,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抱着膀子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在我们周围,有时也会听到杨二嫂刻薄的笑语,会看到阿Q倏忽而过的身影。其实,鲁迅先生也并未走远,他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含着烟斗,冷峻地看着我们。
参考文献
[1]孔庆东.正说鲁迅[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7.
[2]刘泰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上册)[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3]鲁迅.鲁迅小说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赵伟]
收稿日期:2015 - 09 - 15
作者简介:荆煜君(1969—),女,河南郑州人,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811(2016)02-0070-05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People in Lu Xun’s Works
JING Yujun
(Zhengzhou Railwa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Zhengzhou 45005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fects of Chinese people in Lu Xun’s works from five aspects: poverty and illiteracy, spirit-satisfied method, snobbery, numbness, parsimony and selfishness, which not only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ld China” but also reflect the seamy side of humanity.
Key words:Lu Xun’s works; national character; huma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