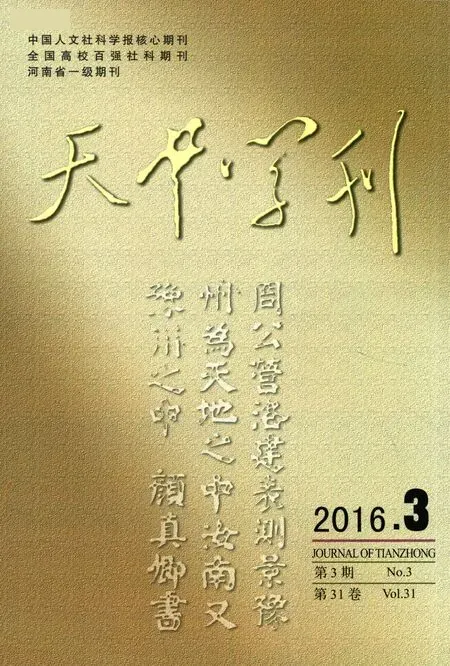家族记忆和民族战争
——《红高粱家族》的战争记忆书写
李保森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家族记忆和民族战争
——《红高粱家族》的战争记忆书写
李保森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对于被侵略者而言,民族战争是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对它的反复书写既是建构不能遗忘的记忆,也是凝聚民族认同、唤醒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红高粱家族》在家族记忆与民族战争的互相映照下,通过对民族战争背景下的乡土、乡民、家族和战争本身的书写,实现了家族记忆的个人化建构,同时以新的历史观念观照和叙述民族战争,起到了建构、延续和传播集体记忆的作用。
《红高粱家族》;民族战争;集体记忆;家族
在新时期小说的百花园中,莫言的《红高粱家族》[1]是一朵盛开着的奇异的花,惊艳、豪放而又充沛。这部小说以狂放不羁的叙事语言,碎片式的叙事情节,充满原始野性且重情重义的人物形象,调用多种感觉器官所传达出来的微妙感受以及一系列繁杂精密的隐喻意象,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在艺术手法上实现了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陌生化,并由此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红高粱世界。从此,高密东北乡成了当代文学版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红高粱家族》用两条线索来支配其内容的复杂性:一条是高密东北乡的同胞们对日本侵略的英勇不屈的反抗,连着这条线的有惨无人道的侵略、勇往直前的反抗、沉痛悲惨的牺牲、钩心斗角的争斗;一条线是“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的爱恨情仇,和这条线连着的是充满原始意味的、富有野性的生命力,是对大胆泼辣、自由勇敢的渴望与追求,是先人的敢爱敢恨、质朴强悍和无所畏惧。这两条线索的交叉勾连,建构了一个独特、神秘、紧张、充满野性的文本世界,刻画出了鲜明、生动、活泼、大胆的人物形象,同时借助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艺术手法使文本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的新面貌。
小说内容的复杂性、艺术的创新性为我们进入小说提供了多种途径,而《红高粱家族》的成就不仅仅在它的文学性和审美性方面,更重要的是它用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叙述过往,以个人化的方式呈现家族的记忆。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红高粱家族》是作为新历史小说潮流的代表之作而被定位的。新历史小说的“新”不是指题材的拓新或重新整合,而是指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历史意识、新的历史观念、新的历史精神和新的历史叙述方法。因此可以说,《红高粱家族》在新的历史观念的框架下重新叙述了家族记忆和民族战争,而家族记忆和民族战争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关于家族的记忆因为战争而充满了更加壮丽的色彩,而战争则通过个人化的家族记忆可以从新的角度被认知、被看待。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记忆是和其他心理活动密切联系着的基本的心理过程,是过去经验在头脑中的反映。所谓过去的经验,是指过去对事物的感知,对问题的思考,对某个事件引起的情绪体验,以及进行过的动作操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留有过去经验的因子,在对往事的追溯中完成对此时此身的确认。可以说,记忆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然而,学界最初对其所进行的研究是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领域开始的,这些领域的研究是以个体记忆为主,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记忆理论探索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从该理论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就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角度与分析工具。”[2]112
对记忆的学理性探讨为我们分析《红高粱家族》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角度,一个新的视野和途径。当然,对记忆的学理分析不应该脱离记忆的具体内容而如空中楼阁般脱离地基,尽管记忆的建构过程可能蕴含着更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些价值和意义的判断必须建立在记忆的内容之上,否则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瓦布赫曾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连续性。”[3]335从这个定义来看《红高粱家族》,我们会发现,小说中关于故乡、家族、战争、乡民的记忆都带有较为浓厚的集体记忆的特质。因此,《红高粱家族》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文本,它是立足于当下的、对集体记忆的一种重新建构,是对由现在指向过去的一种主观心理经验的重新组合,是对过去的再想象和再创造,并在建构过程中饱含着记忆主体的深厚感情。
翻开《红高粱家族》,我们首先看到这样一段卷首语:“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1]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重怀旧的气息,这里有作者对故乡历史的回眸,对家族往事的追忆,对昔日英雄的礼拜,对当下时代和自身的反思。
在更为具体的文本里,叙事者立足于当下,以追忆的方式遐想着、讲述着:故乡高密的光荣与伟大、失败与耻辱;日本侵略者的凶狠和残暴、野蛮和荒诞;故乡同胞们的英勇与牺牲、无畏与无私;党派之间的争权与夺利、狡诈与自私;家族的往事与足迹、祖辈的风流与坚强,等等。这些具体的内容不仅是一段段曾经鲜活过的历史,也是记忆里最为关键、最为可靠的所指。这些记忆不仅塑造着家族,也塑造着历史,“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精髓,既是个人和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又揭示着记忆模式生成中权力结构的运作”[4]。因此说,记忆理论的介入,为重新辨析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和有效的理论视角。《红高粱家族》在对历史的梳理中,再现了远去的家族和乡民的背影,也在对家族形象的刻画中完成了对历史的新的书写。
一、战争记忆中的乡土
在《红高粱家族》一开始,作者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1]2
这段文字奇崛、壮丽,传达了复杂的内容和情感。首先,表达了对故乡的复杂感情。一组组对立的形容词,既是对家乡的一种描述,又是自己对家乡感情的渲染。其实这些语义相互对立的形容词在立意指向上是相通的,都表达自己对在这块土地上所演绎过的生命形态的由衷的崇敬和怀念,差异性的解读只是因为理解方式和角度的不同。其次,通过描绘红高粱的壮丽和辽阔,象征了生活的宁静与平和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之上的人们的豪爽和坚韧。特别是“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则会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抒情话语:“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站在今天,回想脚下土地的历史,得到的是一种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知足与安稳。再次,由先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来对照、反思自身和同时代的人,不免感叹人种的退化。这种感叹由现实引发,同时又在与父辈的对照中得到确证。
哈瓦布赫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3]24这里显然是在强调集体记忆所具有的形式化表现特点,是在借助某一物质客体或精神符号来指代集体记忆,这和英国文学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红高粱家族》的文本,显示出哈瓦布赫所说的“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的是遍布家乡、壮丽而又浪漫的红高粱。它作为一种具体的风物来指代家乡,同时又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寄寓着某种独特的精神。“象征能以压缩的方式保存大量的文化信息,它具有的这种高度凝结能力是人类文化记忆的绝妙之处。”[5]对红高粱的反复渲染、修饰和描写,使其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而是一个充满意味的符号,浸染了写作主体的丰富寄托意味,暗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蕴含着“我”对家乡的浓烈情感。
在“我”对家族记忆的追溯和书写中,与其说红高粱是一种地方农作物,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是一个具有多重指向的能指。因此,文本中处处都有红高粱的色泽和芳香:“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1]66“最后一丝与人世间的联系即将中断,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的打在高粱梢头。”[1]69“爷爷踉踉跄跄地在路西边的高粱地里穿行着,父亲紧跟着爷爷走。他们脚踩着残断曲折的高粱和发出微弱黄光的铜弹壳,不时弯腰俯头,看着那些横卧竖躺、龇牙咧嘴的队员们。”[1]87“河里泛上来的蓝蓝的凉气和高粱地里弥散开来的红红的暖气在河堤上交锋汇合,化合成轻清透明的薄雾。”[1]89“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1]361红高粱作为一个客体,是人们的活动空间;作为一种主体,它目睹了乡民的喜怒哀乐、生死悲欢。“我奶奶”在这里实现了生命的盛放,得到了欲望的满足,展现了生命的活力,也在这里结束了短暂而又惊艳的一生,留下了“我”对她的无限想象和无比崇敬。“我父亲”“我爷爷”和“我”的乡民在红高粱的掩衬下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了保卫家乡而勇敢地战斗,也光荣地死在无比熟悉的高粱地里,尸体被红高粱包裹着。红高粱见证了战争的激烈与残酷,见证了乡民的反抗和牺牲。
因此,红高粱在这里不再仅仅是作为观赏的壮丽景物,也不仅仅具有提供食物以果腹的意义,它因为连着这些神圣且无法忘却的记忆而成为一种神圣的象征物。因此,这里对红高粱的描写,就不再是以客观的角度对其进行描绘,其对乡土的指代,使其包含了更多更浓的主观因素。红高粱的意象,是个体进入家族历史的中介物,是子一辈对父辈想象和怀念的象征物,也是记忆主体置放情感、安放怀念的有效形式。
二、战争记忆中的乡民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强调了环境对乡民性情的影响,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我”的记忆中,家乡是顶可爱的,但是更鲜活的是那些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乡民。故乡具有的各种品性和精神,既因这些乡民而得以形成,也在这些乡民身上得到具体体现。如果说家乡是一种“能指”的话,那么乡民则是更为具体的“所指”,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勤劳、朴实、创造、勇敢和韧性造就了这块土地的传奇。因而,作者对家乡的无比热爱是和对乡民的无比崇敬紧密联系着的。《红高粱家族》表达了“我”对乡民的仰望和敬意,展示了他们的美好品性。这种表达和展示最集中地体现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飞机下了一蛋,落在王文义家院子里,把三个孩子炸得零零碎碎,弃置房脊,挂树梢,涂之墙壁……余司令一树起抗日旗,王文义就被妻子送去……”[1]61战争带来的是可怕的伤亡,是人与人的生离死别,是亲历者梦魇,是刻在历史里的伤疤,是久久难以驱走的恶魔。而战争激起的则是被侵略者的勇敢反抗,是守卫家园的迫切意识,是前赴后继的共同使命,是命运的紧紧相连。一场准备好的反击战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清扫战场掩埋尸体的时候,“全村父老,齐齐跪倒在一片新坟前,一时哭声震动四野。火把奄奄欲熄。一颗硕大的陨星从南边的天空坠落下来,一直触到了高粱梢头才消失灼目的光芒。”[1]126
乡民们在战争中勇敢地反抗侵略者,誓死捍卫美丽的家园。他们英雄般的壮举和悲剧般的结局,使他们在捐躯赴国难的同时完成了个人的历史化书写,成为令后人敬仰的一代,并以沉淀的方式活在后人的记忆中。因此,对民族战争的记忆,不仅仅是民族被侵略、国家被践踏、人民被侮辱,还有战争中所凝聚起来的爱国之心,所激起的奋起反抗,所经历的枪林弹雨、生死考验……对两者的记忆,是一个互相强化的过程,对民族、国家、人民所经历的不幸的喟叹,加深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即对民族战争的憎恨;而对战争的反复书写,则同时也加深了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记忆。
哈瓦布赫认为:“一些记忆总是会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因为许多社会活动都是因强调群体的某些群体记忆,以延续并巩固该群体的凝聚而举办的。”[3]68在《红高粱家族》中,对乡民的记忆既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也是通过对胶高大队、冷支队等其他不同群体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来突出的。与乡民由对美丽家园的眷恋、对和平度日的渴望所激起的自发的反抗意识不同,胶高大队、冷支队等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谋划,他们总是出现在激烈的反抗之后,借着清理战场的名义,用各种理由为自己的“缺席”进行推脱,并且一再用言语表明各自的抗日决心和意志,却行争名夺利之实。甚至为了扩大势力,不惜“窝里斗”,在民族内部互相残杀。因此,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对他们的刻画隐含着对历史叙述的反拨,他们的狡诈、圆滑与萎缩更突出了乡民的勇敢、坚韧与伟大。
三、战争记忆中的战争
和对乡民的无比崇敬连着的是对战争的无比憎恶,二者以一种互动的方式出现在集体记忆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日本侵华战争无疑是深刻的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在那一时期所经历的屈辱与惨重,是历史中无法抹去的沉重的真实,也是每一个渴望和平的人必须勇敢直面的事实。
《红高粱家族》在对这段历史的书写中强化了这一集体记忆的深刻性,同时从中长出了和平的种子,表达了对战争的憎恶。“傍晚时,村里百姓往无枪声的村南‘出水’,遭到日本机枪疯狂扫射,数百名男女死在高粱地里,辗转翻滚的半死的乡民,压倒了无数的红高粱。鬼子撤退时,点燃了村里所有的房屋……那天晚上的月亮,本来是丰厚的、血红的,但由于战争,它变得苍白、淡薄,像艳色消褪的剪纸一样,凄凄凉凉地挂在天上。”[1]155一场扫荡让这些猝不及防和无能为力的人的生命如浮萍一样,瞬间被打碎。战争让这些侵略者丧失了人性和底线,他们滥杀无辜的平民,摧毁平静的家园。侵略者的“狂欢”写下了无法原谅的罪恶,给他人带来了无以复加的痛苦。
文本中有许多被侵略者残酷洗劫后的悲惨场景的描写:尸体横陈、断壁残垣、还在燃烧着的战火、一片狼藉的村庄、麻木发呆的幸存者。这样的书写,看似一片空白,其实却蕴含着丰富的想象生成空间,是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并强化战争的残忍:从萧瑟的画面中可以想象到过程的惨烈,想象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恶劣行径,想象普通老百姓的痛苦与饱受摧残。张志扬在论述有关抗日战争的创伤记忆时曾经指出:“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对于20世纪中如此巨大的‘创伤记忆’,以为不靠文字像碑铭一样建立的反省、清算、消解而生长、置换、超越的能力就可以在下一代人的新的生活方式中悄悄的遗忘、抹去,这除了不真实和不负责任,还说明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已在历史的惰性中无力无能承担他自己的遭遇从而把无力无能追加在历史的惰性中作为欠负的遗产弃置给了下一代。于是,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就这样自己注定了自己一再重复的命运。”[6]69-70对于抗日战争的反复书写,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曾经饱经忧患、屡遭侵略的民族无法忘却的一段“创伤记忆”,更重要的意义则是通过文学记录一段屈辱的岁月,通过文学展览曾经的伤疤,通过文学加深记忆的刻骨,通过文学表明敢于直面的勇气,通过文学表达对战争的憎恶和对和平的珍重。这个意义就如同西方那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而忘掉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
《红高粱家族》仅仅是众多对民族战争记忆的书写中的一种,却因为对战争的独特呈现方式而让人印象深刻。它记录的虽然只是一个地区、一方乡民的反侵略记忆,但由于深刻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引发了人们对共同的民族历史的重新审视,并再次张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的信念,而这自然是民族共同体得以凝聚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说,《红高粱家族》在书写中完成了集体记忆的建构,而建构过程无疑具有延续记忆和传播记忆的双重功能。
四、战争记忆中的家族
在《红高粱家族》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家族记忆也被建构成型。家族记忆是民族战争记忆的重要构成部分,而民族战争记忆也因为家族记忆而染上了传奇的色彩,更加动人,更加缠绵。
在家族记忆中,最为浓墨重彩的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其间所经历的跌宕起伏都是精彩的传奇。他们爱得深爱得真,也恨得深恨得真,而爱恨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性情与豪气足以成为动人的传说。他们的故事随着“我奶奶”的死亡而悄然结束,但是却随着红高粱被不断提起,叫人不忍忘却。
“我爷爷”是个土匪,在给人抬花轿的时候,爱上了坐在花轿里的“我奶奶”,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缠绵悱恻、爱恨交加的故事。由开始在红高粱地里的凤凰和谐,到一把火带去了单家父子的生命后,“我爷爷”实现了由雇工到当家人的身份转变,从此他们“鸳鸯凤凰,相亲相爱”,之后又有花脖子的打劫,“我奶奶”与铁板会黑眼的插曲,“我爷爷”与二奶奶的爱恋……在“我”看来,他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而且每一段都可以成为“我”家族记忆的素材。
他们的爱情在水里泡过,在火里烧过,有甜蜜的滋味,也有黯淡的色彩。两个自由奔放的生命在相遇之处,就预示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的开始。后来生活的展开,是两颗不羁的心互相碰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最主要的还是“我爷爷”和“我奶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难舍难分。无论是“我奶奶”与他人的插曲,还是“我爷爷”与二奶奶之间的故事,看似是彼此的互相报复,却只能作为他们爱情和生命的一段注脚,无法取代他们两个人在彼此心中的重量和意义。他们两个人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是无法分离的一对,是两个生命的相互依赖。而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原始、野性的生命力以及他们在这段惊天动地的爱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世俗的傲视、对自由的渴望,是这段具有传奇性的爱情里最鲜明有力的色彩,也是“我”在建构家族记忆的过程中最着力想要表达的内容。
他们传奇般的爱恨纠葛发生在战争之前,是风暴来临之前平静生活中不平凡的经历。战争之后,生活被打碎,所有人都被卷入这场突然而至的灾难,他们和他们的爱情也难以逃离。和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品性一样,他们也以同样的品性和乡民们一起参与反抗侵略者的战争。“我爷爷”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我奶奶”全心全意支持,并且用自己的聪明禀赋出谋划策。他们的爱情在动乱的岁月中一样动人,尽管结局不无悲壮的色彩。
当“我奶奶”在温暖的红高粱中慢慢闭上眼睛,当生命里曾经出现的面容再一次一一浮现,30年人世间的生活,让她留恋不已,“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1]67这不仅仅是临死前的呼喊,也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我奶奶”告别了这个她无比认真地活过、爱过的世界,把她那短暂而又饱满的人生留给“我爷爷”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咀嚼。而他们的那段往事也为同时代人和后来人所瞩目。
对于“我”而言,在今天只能追溯先辈的往事,在记忆中回味先辈们对生命的尽情演绎。“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主要是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3]106集体记忆是一个对往事进行不断追述的过程,但是始终立足于当下,具有类似于“移步换景”般的变动,因此它自然而然地把此时此身的某种观念和想法灌注其中。《红高粱家族》在民族战争记忆和家族记忆的建构中,所立足的当下便是不忍目睹“种的退化”。作为一种隐喻性象征的存在和指向,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就是纯种高粱的消失和杂种高粱的遍布。由此,作者想要表达的或许就是对逝去的一代的钦慕和尊重,是对那一代人所具有的原始野性生命力、质朴强悍的美好品质的向往和追求。
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历史的张力反复呈现,并构成了千姿百态的历史图景。对于文学而言,描绘历史图景,即是重新建构一段记忆,而这不仅是为了再现过去,也是为了启示当下。民族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但其印痕仍然刻在每一个经历过的个体身上,其余烬偶尔还会闪烁出一丝火星,提醒我们历史并未走远。在民族战争的书写中,建构家族记忆,既能够显示出前者的具体性,也可以突出后者的深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高粱家族》在家族记忆与民族战争的双重互动中,实现了文本的表达意图。就文学本身的意义而言,它充满了艺术上的新的质素;就民族战争记忆的文学书写而言,它为新时期的民族记忆书写提供了一个经典性的文本。
[1] 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 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3]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 李莉.文学与记忆的关系探析[J].社会科学家,2009(12).
[5] 康澄.象征与文化记忆[J].外国文学,2008(1).
[6] 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责任编辑 杨宁〕
I206.6
A
1006-5261(2016)03-0112-05
2015-11-27
李保森(1991—),男,河南武陟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