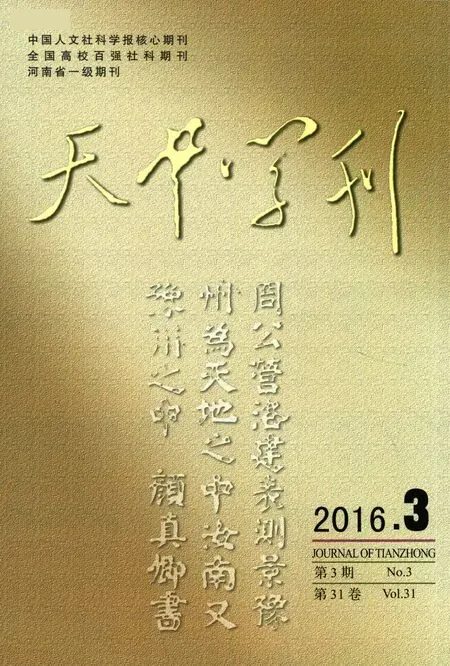切尔卡斯基的汉学研究置喙
侯海荣,宋绍香
(1.吉林师范大学 博达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2.泰安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切尔卡斯基的汉学研究置喙
侯海荣1,宋绍香2
(1.吉林师范大学 博达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2.泰安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切尔卡斯基对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新诗的研究成为海外汉学界的一座高峰。切氏以其鲜明的比较、开放、建构、批判、整合意识对中国文学展开文化理解与文化想象。缘于意识形态、文化心理、诗学观念、时空距离、先在结构、思维范式等诸多差异,切氏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探寻为中国学界打开一重要窗口。在中国当代学术建设生成与敞开的参照系中,理性的态度是以反思的姿态关注汉学一隅的批评话语,在“视界融合”后形成创生张力,进入双方文化对话和重建的主流。
俄罗斯汉学;切尔卡斯基;域外文化交流;中国新文学研究
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出现了两位堪称“双子星座”的世界顶级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和切尔卡斯基(1925—2003年)博士,他们将其对中国文学与文化情有独钟的热忱贯穿于汉学研究的始终。切尔卡斯基凭借丰赡的学术论著成为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研究的权威学者。然而,正如俄罗斯汉学文艺理论家热洛霍夫采夫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人们对俄国文学的认识由来已久……但是俄国对中国的文学文化的研究成果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反应,这不禁令我国的学者对自己工作的真正价值产生怀疑。”[1]汉学作为中外文化的“混血儿”,既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亦是反观自身的“文化之镜”,因此,对切尔卡斯基的学术轨迹进行历时考察,将其对中国文学的翻译、研究搜罗裒辑并加以公允评析,尤为必要。
一、切氏之学术成果要览
切尔卡斯基中学毕业时恰值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因视力欠佳不能入伍而进入军医学校,曾任炮兵营副军医。战后因其母亲的努力他得以进入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学习汉语,该院乃俄苏汉学的重镇,切氏汉学之路由此开启。他以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作为研究的客体,以本土文化语境为基点,辅以来华进修的优势,探骊得珠,成果颇丰。纵观切切尔卡斯基的汉学成就,其治学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发端期(20世纪50—60年代)
1951年,切尔卡斯基被派到西伯利亚赤塔市苏军司令部任职,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点燃了汉学研究的星星之火。50年代末切氏考取了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师从汉学家艾德林,规定课题是曹植研究。切氏真正的汉学研究就是以研究曹植为肇始的,1963年他在汉学界崭露头角,写出了成名作《论曹植的诗》。该著专题论述了曹植诗歌与乐府民歌的有机联系,尤其对《洛神赋》及曹植诗歌的典故作了精辟考辨,阐释曹植诗歌的创新特质及审美价值,并通过对曹植创作道路的剖析,展示了以汉朝末代皇帝年号命名的建安文学的成就及其对后世诗坛的影响。切氏认为,曹植作为“建安之杰”,他的辞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之一,“在公元2—3世纪,这种诗体正由铺叙事物的叙事诗转向抒情诗(短赋)”,“在民歌基础上创立乐府诗体,极具研究价值”[2]。切氏初试锋芒,跨越了中国古汉语的瓶颈,可以说《论曹植的诗》是其汉学里程中首部标志性著作,具有界碑意义。此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这块学术阵地,锲而不舍,钻之弥坚,将学术重心转移到了中国新诗的编译、著述、诠释、阐论方面,力作迭出,见表1。

表1 切尔卡斯基20世纪50—60年代汉学成果汇总
(二) 高产期(20世纪70—80年代)
切尔卡斯基从20世纪70年代起奋力垦拓,其汉学研究臻至巅峰状态。这一阶段切氏对现代新诗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开掘与广度覆盖,翻译与研究平分秋色,堪称切氏学术生命的黄金期与学术成果的丰收期。从翻译总量来看,切氏译诗歌千余首,涉及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包括不同社团、不同流派代表诗人的代表作品,选译诗歌之广、诗人之全、诗篇之准、质量之精,堪称世界之最。《雨巷》《五更天》《蜀道难》三部译作含编选并作序,组成一个年代系列,勾勒出诗歌演进的嬗递动态,共选入95位诗人的434首诗歌,提供了中国20世纪20—80年代现代诗歌创作的概貌。《中国新诗论》《中国战争年代的诗》《艾青:太阳的使者》,实现了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点面结合”的一种描述。《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和《俄罗斯文学在东方:翻译理论与实践》是切尔卡斯基别开生面的一类著作,作者从翻译学的视角提出了制约文学翻译的文学传统、翻译心理、原文形象、民族传统诸多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问题。切氏这一时期的汉学成果见表2。

表2 切尔卡斯基20世纪70—80年代汉学成果汇总
(三) 平歇期(20世纪90年代至2003年)
众所周知,以发生在1991年12月25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为标志,长达69年的苏联政权解体。俄罗斯国内政治风云的动荡变幻,亦殃及汉学家的命运。自20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汉学界逐渐萧条,汉学研究随之落潮。切尔卡斯基身为犹太人,1991年移居故国以色列,任教于耶路撒冷大学,由著述转向讲学,以另一种方式传播中国现代文学,延伸着汉学研究。1993年,他的专著《艾青:太阳的使者》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而其专著《徐志摩:在梦幻与现实中飞行》则成为遗作,在俄罗斯一直没有发行,直到2015年才出现中译本,由中国知名翻译家宋绍香完成。由此可见,切尔卡斯基的汉学成就一方面受到作者自身学术历练的规约,同时与国内政治环境和苏中关系起伏(蜜月期——冰封期——解冻期——升温期)密切相关。切氏这一时期的汉学成果见表3。

表3 切尔卡斯基20世纪90年代后汉学成果汇总
二、切氏的现代学术意识
海外汉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认识框架与多元的学理空间,此乃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层面。“正因为‘汉学’在知识谱系上属于‘东方学’,能够‘全息’地舶来外缘文化观念,才反而更值得好好研读,以便既取其具体结论又取其具体方法为己所用”[3]。切氏以其执着的学术个性形成了自身汉学研究的独特格局。观其特点,兹举荦荦大端。
(一) 比较意识——中俄互鉴
作为称职的汉学家,切尔卡斯基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中国的文学文本,而且包括其文化背景。比较文学是以跨国度、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内部、外部的透视与汇通。切氏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他在中俄两种异质文化间总能寻捕到某些牵系、耦合与启发。譬如,徐志摩创作的《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去罢》《灰色的人生》等,在切氏看来,这些作品中流露的人性与情感具有同义性,如同屠格涅夫的作品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一样[4]。再如,在《中国战争年代的诗歌(1937—1949)》中,他不仅着墨于诗歌的形式、风格、审美,且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诗歌与俄苏诗歌的关系;在《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中,他对中国诗人如何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中国文艺界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论争以及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等做了全面论述。事实上,比较研究对汉学家来说不啻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只有对比较对象有深层的理解,才能产生真正的比较话语。对此,国内学者钱中文认为“所谓发言权,就是你真正研究过你所要比较的对象,本国的、外国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现象,在对中外的某几个作家、某段文学史的研究中,你确有心得,有见解”[5]305,否则这种所谓的“比较”就会陷入隔膜与肤廓。
(二) 开放意识——内外贯通
其一,切氏对西方文论与世界文艺学理论倾心研读,关注艺术方向、文体形式、传统与创新等问题。他指出,中国诗歌是世界文学交往中的积极参与者,它与东西方各国文学间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在扩大、深化。譬如,切氏在《中国20—30年代的新诗》第一部分“五四时期的诗歌”中,不仅阐释了五四时期诗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且从模仿与借用西方形象、歌颂西方伟人等视角厘清了中国新诗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并且在第八章把中国的小诗与日本的俳句、印度泰戈尔的短诗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外国作品对其的影响等。李福清认为,该著“是首次运用世界文艺学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人创作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特色的开山之作”[2]。再如,切氏在《徐志摩:在梦幻与现实中飞行》中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诗集中,已经显示出借用西方题材的痕迹。中国诗人不是简单地“重复”外国作品的思想和形象,而是超越它们,有所创新。西方浪漫主义通过海涅、雨果、裴多菲、米茨凯维奇等作家的作品引入中国后,以某种方式发生了变形。所以,中国的浪漫主义较之西方,“批判的”比重增加了,导致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均衡发展。西方诗人的思想和诗艺如哈代、斯温伯恩、罗塞蒂使徐志摩的诗歌具有勇猛的反抗精神。爱情抒情诗具有“赞美爱情”与“毁灭爱情”两个极端。其中,拜伦和雪莱诗歌的感情与灵感在徐志摩的心中鸣响并发出回声,阅读徐志摩的诗歌《去罢》与拜伦的鸿篇巨制长诗《唐璜》,会感到二者之间内在的血缘关系等。切氏的以上结论是足以成立的,因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它不是传统文学自身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新质文学”[6]。
其二,中国新诗作为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锋,引发了海外汉学界的瞩目。切氏绝非画牢自囿,既不唯我独尊,又能在同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不仅揣摩中国学者的态度,而且以犀利的学术眼光、开阔的学术视野、求真的学术品格在国际学术呼应中敢于争鸣。譬如,切尔卡斯基认为苏霍鲁科夫在《闻一多论》中对闻一多唯美主义的批评过于偏激;对于英国海罗鲁德·艾克顿的《中国现代诗歌选本》,培恩认为该本很出色,而切尔卡斯基则觉得该本序言中某些评论不够精准,从而使得全书黯淡。在切氏心目中,对中国新诗研究不乏佳作,法国路易·米歇尔的《墙上芦苇·西方眼中的中国诗人》、美国许芥昱的《二十世纪中国诗选》和林明晖的《中国新诗导论》皆为珍本。切尔卡斯基称许芥昱的选本是“西方第一本,也是比较完整的一本中国新诗集”[7]195,同时切氏对书中关于诗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理解表示不满,因为“编者显然把表达细腻情感的文学同粗糙简单的‘喇叭式’文学对立起来”[7]198。
(三) 建构意识——译研相融
切尔卡斯基青年时代辗转学习汉语的动机,就是为了翻译中国诗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仅中国新诗选集,切尔卡斯基凭借一己之力就翻译出版了十余种。费德林曾指出,苏联汉学家们将翻译视作一种艺术,是运用祖国语言准确转达原作的思想和艺术表现力,翻译不是“原作的反光”,这一点与欧洲(英、法、德)翻译原则不同。远不是所有汉学家—翻译家都同时掌握原文语言与俄罗斯文学语言的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段[8]。这一点上,切尔卡斯基的翻译水准无人比肩。譬如,切氏在《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中,指明了俄译汉的诸多问题,有曲解原意、前置词缺省、形象毁坏、成语错位、同音词变异等。他在《俄罗斯文学在东方: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为国际译介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切尔卡斯基的中国新诗研究与其翻译同步进行,他的每部译集序言,都是一篇很精致的研究论文。“虽然他翻译了许多中国现代诗歌,但是翻译决不是他的最终目的,目的是研究中国现代诗歌”[9]。在翻译的同时,切氏潜心学习诗学理论,以真正了解和把握中国诗歌史的发展脉络。他对中国20世纪20—40年代的诗歌,不是一般性介绍,而是评析各流派的代表诗人及其代表作,揭示诗人的创作道路、艺术特质与价值,非常到位和深邃。
(四) 批判意识——赏评共参
切氏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并没停留于感性层面,而是对作品、作者加以定性、定位,核心质素数语破的。一方面,切氏对作品本身给予恰当的评判。譬如,在《太阳的话》中,他评价艾青“《北方》里虽然不见战争场面与士兵冲锋,然而战争氛围真实可感,战争漩涡中惶惶不安的人民生活被大规模地呈现出来”,“1979年之后,作品的主题、语调发生了变化,作品中出现了带有哲学潜台词的冷静观察”,“艾青诗作贯穿着一个信念:总有一天祖国大地上的水和人民的眼泪将失去自己的苦涩”,这样的点评精当至极[9]。切氏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新诗作了详尽分析,既肯定了诗歌创作的不俗成就,也阐明其“公式化”倾向与艺术上的粗糙;另一方面,他也对诗人创作主体给予凝练恰切的总结。在《艾青:太阳的使者》中,切氏认为艾青是一位“平民化”诗人,是“太阳的歌者”与“光的代言人”,“是祖国文化、东西方优秀文化的继承人”,“是与希克梅特、聂鲁达并驾齐驱的世界级大诗人”[10]。切尔卡斯基在《徐志摩:在梦幻与现实中飞行》一书中称赞徐志摩是“中国的雪莱”,他的诗不受约束,“满腔热情而又充满智慧,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感”,“徐志摩是爱情与风景抒情诗的大师”,“他是较早传递苏俄消息的人之一”,“徐志摩与闻一多全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最有天才的代表人物”,同时认为“他是一位理想的浪漫主义者,但他是圣洁的,尤其不是恶魔……有‘七情六欲’,也有缺点”[4]。
(五) 整合意识——宏微并进
切尔卡斯基不仅有译著、合著,还有研究专著。譬如,切氏抓住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战争年代这两个新诗发展的重要时期,凸显了其研究架构的宏巨性和时代性。随着对中国新诗研究不断深化,他逐渐走向微观研究,即对有代表性的诗人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学理研究,他选择了两位诗人:一位是革命诗人艾青,一位是唯美派诗人徐志摩。切尔卡斯基说:“艾青作为艺术家出现时,我写了评论他的著作。而现在,我将把评论徐志摩的历史性的新著推到读者面前加以评判。”“很多年以来,我都企望写出一部评论20世纪中国的这两位最杰出、最耀眼的诗人的著作。从我孤陋寡闻的‘信息’土丘,我想冒昧说出下面的话:艾青的生活之路是悲惨的,而命运是美好的;徐志摩的生活之路是美好的,而命运是悲惨的。”[4]20世纪80年代欧洲科学基金会编纂大型学术书《中国文学精选指南(1900—1949)》时,特约切尔卡斯基执笔该书的《现代诗歌卷》。由此,他把艾青、徐志摩等中国诗人推向了世界。
毋庸讳言,汉学家缘于自身认知的“原初格局”、心理图式、价值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干预,在对域外文学的体认与参悟中势必存在某种天然的局限与障壁。譬如,《论曹植的诗》尽管是切氏“第一次向苏联读者和学界介绍了这位伟大的诗人及建安文学”[2],但论者的学术水平尚难恭维。该著共设四章:建安文学、民歌与曹植、曹植的诗歌遗产、诗人生平[11]。总体来看,切氏认为曹植的作品饱含仁爱精神,抒情色彩浓郁,诗中充满作者的思想矛盾、建功豪情、愤懑忧思、渴求失望等。这样的说法并没有任何新的学术生长点,仍为步尘之语,或者说只是切氏把中国学界的观点进行了一下异域移植与符号转换。切氏还有一篇论文,将奥维德与曹植加以横向解说,二位确有相似点:出身名门,学富五车,穿梭于皇家诗人之间;奥维德遭遇流放,忧郁而死,年寿六十;曹植被逼徙封,英年早逝;奥维德写下《哀歌》,曹植著有《七哀》;奥维德写有《哀愁集》等恳求皇帝奥古斯都宽恕,曹植也写下许多类于“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这样的诗句向曹丕表露心迹。乍看这样的视角似别出心裁,事实上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与曹植生年相距两个世纪,他们生活的国家制度相去甚远,秉承的文化“元气”迥然有异,如此低层的比较论说,学术意义似乎不大。
再如,切尔卡斯基更多地看到了中国新诗现代转型中与西方诗歌千丝万缕的关联,而没有看到或显豁或隐秘的中国古今诗学的“纠缠”。事实上,中国新诗发展是中国古典诗歌、西方诗歌传统与现代诗人的个性追求合力作用的结果。另外,切氏认为中国战争年代的诗作存有“脸谱化”倾向,这一观点并无新意。他在对中国诗歌进行整体特征的归纳,一方面会让读者抓住作品的类型,另一方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简化历史。那么能不能在文学生态中还原诗歌的精神真相,在新诗强调政治性,弘扬“大我”,推崇“炸弹”与“旗帜”的社会功能中,进一步阐发它的历史合理性?如在《中国50—80年代诗歌选》中,苏联、“文革”题材占据比例较大,此种筛汰机制是作者以作品思想性为本位的思维惯性使然,旨在使文学作品的解读成为窥视、搜集中国信息的渠道,此种翻译意图使得许多优秀作品不能入围。诗歌乃作者以一种特别的语词样式呈现出来的言说,倘若逡巡于诗作外部而没有真正进入诗本体,没有在“诗之所以为诗”的意义上触摸诗歌的质地与灵魂,是否弱化了诗歌真正的艺术精神、美学内蕴、中国味道?
诚然,指瑕并非苛责,更不意味着否定。切尔卡斯基的汉学著作在俄罗斯曾经一度洛阳纸贵。《中国20—30年代的新诗》《中国40诗人诗选》在当时印数创下峰值,各为1万册,《为了寻找一颗明星》印数2.5万册,《蜀道难》1万册,这些译本炙手可热,短时售罄,侧面反映出切氏茹苦治学付出的巨大艰辛。切氏的《中国20—30年代的新诗》与《中国战争年代的诗》体大思精,两部著作计50余万字,中国社科院的李聃曾立志翻译,但该著一直没有与中国读者见面。《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是一部典型的有关学术交流的著述[12],译成中文也似乎遥遥无期。这既是切氏自我的遗憾,亦是中国的损失。
切氏之所以如此投入地去翻译研究中国文学,是因为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翻译与弘扬中国文化,既是他的追求又是他的归宿。平心而论,任何人都无法超越自身所处的历史现场与文化语境,对“他者”的完全理解无异于一种美好的学术期待。故此,顾彬指出:“互相之间不能理解无论如何都不是个灾难,我们习惯性地缺乏理解才是真正的灾难。”[3]汉学文本的开放性也正是在阐释者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统一中得以达成。正视汉学偏见存在的正当性,以包容的姿态去“指点”汉学家的“亮点”与“盲点”,去“看见”他们的“洞见”与“不见”,去“理解”他们的“曲解”乃至“误解”,此种良性互动恰恰是推进学术前行的动力。汉学作为中国学者的外在视点,呕心沥血的汉学成果实在不应遭遇放逐与遗弃的命运。切尔卡斯基“希望自己的著作不只俄国读者能读到,更希望中国和世界读者都能读到,目的是将中国新文学推向世界先进文学之林,加强中俄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交流”[2]。汉学研究梯队青蓝相接,这既是汉学领域的学术期许,也是本文的立意起点。
[1] [俄]热洛霍夫采夫.评李明滨的《中国文学在俄苏》、《中国文化在俄罗斯》[J].中国比较文学,1996(11).
[2] [俄]李福清.车连义及其中国现代诗歌翻译与研究[J].泰山学院学报,2007(1).
[3] 李雪涛.论汉学研究的阐释学意义[J].国际汉学:26辑,2014.
[4] [俄]切尔卡斯基.徐志摩:在梦幻与现实中飞行[M].宋绍香,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
[5] 钱中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总序//钱中文文集:4卷[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
[6] 汪介之.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2014(8).
[7] 然理.中国新诗在国外[J].诗探索,1982(7).
[8] [俄]费德林.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在苏联[J].岱宗学刊,2000(4).
[9] Черкасский Л.Ай Цин.Слово солнца[С].М.Радуга,1989.
[10] Л. Е. Черкасский.Ай-Цин-поданный Солнца:Книга о поэте[С].Москва,1993.
[11] Л. Е. Черкасский.Поэзия Цао Чжи[М].Москва,1963.
[12] Черкасский Л. Е.Маяковский в Китае[М].Москва,1976.
〔责任编辑 刘小兵〕
H35
A
1006-5261(2016)03-0001-05
2015-07-29
吉林省2015年高教学会教育科学项目(JGJX2015c112)
侯海荣(1971—),女,吉林长春人,副教授,博士;宋绍香(1936—),男,山东泰安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