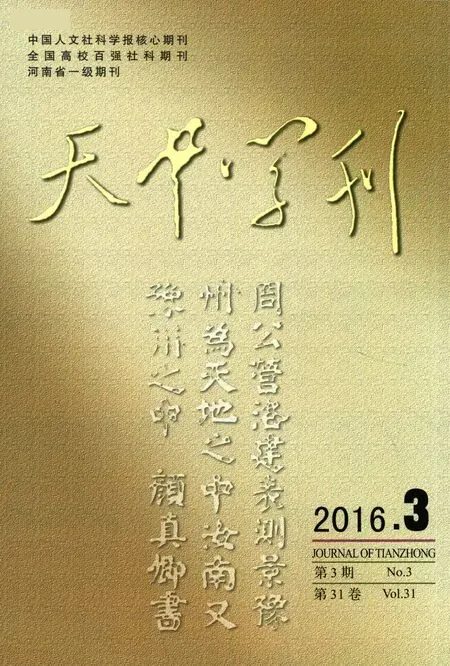苏秦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许中荣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苏秦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许中荣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苏秦作为战国时期合纵家的代表,其读书人的身份定位、“落魄—发迹”的传奇经历以及世态炎凉的体验,在其后底层文人那里引起强烈的共鸣,而被代代演绎。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思路对苏秦故事进行梳理,不仅可以发覆这一故事的演变轨迹,更能透过故事的演变一窥挣扎在底层的读书人的“心史”,为寒士文化的探究提供一个新的案例。
苏秦;故事演变;中国叙事文化学;寒士文化
作为战国时期合纵家的代表人物,苏秦从“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崛起而“扶轼撙衔,横历天下”[1]25的传奇经历赋予其故事极大的发挥空间。苏秦的读书人角色、变泰发迹与后世寒士的身份定位和期许形成强烈的共鸣,常被后世文人作为自况的对象。另外,苏秦发迹前后炎凉世态的强烈对照也深深地触动着士人的心灵。其中,苏秦故事最具特色的就是对作为读书人的寒士命运的关注,而这一主题也构成了苏秦故事的内核。所以,梳理苏秦故事的流变对于我们探讨寒士心态及其文化的递嬗和其所独有的美学品格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苏秦故事贯穿战国迄今的两千余年,遍布史传、诗文、笔记、小说、戏曲诸种文类。本文试图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思路,细致地爬梳历代苏秦故事文本,从叙事演变轨迹中探求寒士在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面目各异的彰显,从而深化对苏秦故事的解读。
一、苏秦故事的文本演变
苏秦故事最早出现于《战国策》,在该书卷三有对苏秦发迹前后几个关键情节较为细致的记载。其后,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辟《苏秦列传》与《张仪列传》,在这两篇列传中,司马迁并未对《战国策》已有苏秦故事予以较大改动,仅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苏、张二人师事鬼谷子、智激张仪、知恩图报以及遗计报仇等诸多情节,形成苏秦故事“师事鬼谷—落魄返家—家人冷落—发奋读书—六国拜印—智激张仪—衣锦还乡—知恩图报—遗计报仇”的基本框架。另外,此时期存世的还有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著录的苏秦游说诸侯的15篇说辞。
西汉中期到魏晋南北朝,苏秦故事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此时期涉及苏秦故事的作品除京房《别对灾异》《汉书·严助传》以及傅干《谏曹公南征》、西晋左思《咏史诗八首(其八)》、北周庾信《拟咏怀诗二十七首(其二)》等诗文从《战国策》《史记》中苏秦故事载记取典外,还有对苏秦多讥刺语的作品开始出现,如汉诗《箜篌引》、魏曹丕《煌煌京洛行》、西晋傅咸《纵横篇》等①。此外,南北朝时期神鬼之说与佛教的盛行,也在苏秦故事的流传中留下烙印。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良书。”[2]103另外,还有鬼谷子梦中授书苏、张的故事,载于五代杜光庭《录异记》以及北宋晁载之《续谈助》、南宋陈葆光《三洞群仙录》等书,明代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及其改编本均受其影响。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也有关于苏秦冢(卷二)、苏秦金(卷三)的记载,都是在前代史传记载中师事鬼谷子、千金拜相故事基础上神鬼、因果的附会增饰。
唐宋时期,据粗略统计《全唐诗》《全唐诗补编》至少存诗46首,《全宋诗》《全宋词》也至少存诗59首、词6首涉及苏秦故事。上述诗词几乎都是以苏秦自况心迹,或为对苏秦落魄的喟叹,或为对六国拜相自我期许的高吟。在史籍方面,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记载苏秦故事,皆以《战国策》《史记》为本。
元代中期出现《冻苏秦衣锦还乡》杂剧,该杂剧对人物身份做出调整,把苏秦、张仪定位为农家子。另外,该杂剧对苏秦故事最大的情节变动为逆用历史记载中苏秦智激张仪入秦事,而为张仪“冰雪堂”智激苏秦入赵[3]242-268。据《全元戏曲》所载,有6篇杂剧提到“冻苏秦”之典,可作为苏秦故事在当时传播情况的注脚②。可能出现于元末明初的尚有南戏《苏秦衣锦还乡》,或已佚,明成化年间有据之改写而成的《冻苏秦》传奇,亦不见。今存《冻苏秦》传奇的改写本《金印记》。该传奇以浓重笔墨突出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并把苏秦落魄归结为公孙鞅的妒贤嫉能。其后,高一苇改编《金印记》重订为《金印合纵记》,根据史传插入智激张仪情节[4]。此时期苏秦故事在小说中亦有演绎。嘉、隆间,余邵鱼编纂《列国志传》以及明末冯梦龙据之修订为《新列国志》均涉及苏秦故事;乾隆年间蔡元放增删润色为《东周列国志》,整合史传、传说,说部中的苏秦故事于此定型。其后不久,杨庸“取冯梦龙《新列国志》要删为书”而成《东周列国志辑要》。嘉庆间还有杨景淐参考《列国志传》增饰而成的《鬼谷四友志》,集中演绎鬼谷子四位弟子孙庞、苏张故事,此书多从前代史传、小说杂合情节,并未出离《东周列国志》的故事框架。
综上,由于苏秦故事的典范性,历代史传、诗文、笔记、戏曲、小说等对之都有或繁或简的记载,实难以尽数统计。据不完全统计,记载苏秦故事较为完整的史书有5部,笔记3部,戏曲存3部、佚2部,小说有5部。另外尚有散见于诸种文类的难以计数的苏秦故事典故。史传及其“典故”对苏秦故事起了维稳故事内核的作用,主要在大传统层面接受与传播;戏曲、小说则从小传统层面对苏秦故事进行变形与再创作,大大丰富了苏秦故事的文化内涵。不过,苏秦故事在这两个层面的接受与传播历来共享着同一故事内核,即诉说着寒士苏秦的心声,这也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中心。
二、战国到西汉初期:知识阶层的兴起与苏秦故事的生成
在战国到秦汉时期,由于文献散佚等诸多原因,今日可见的苏秦故事主要记载于《战国策》《史记》两部史传中。我们在上述历史叙述中可注意到二者之间明显的承继关系,司马迁在承袭《战国策》历史叙述的同时又增添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想象③。在《战国策》中苏秦落魄归家后家人对其不予理睬,而在《史记》中则增添了“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5]2241的细节描写。除此之外,在衣锦还乡情节中,我们也可找到相似的历史叙述,《战国策》中苏秦感慨:“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1]25而到了《史记》中,司马迁却在此处之后又缀上“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5]2262一句,进一步凸显苏秦依靠“游说”而发迹的自负心态。
从《战国策》“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的史家论断中,我们可注意到苏秦故事于其时代的象征意义。战国时期,社会阶层出现较大流动,表现为上层贵族的下降与下层庶民的上升两种趋势。对庶民而言,一条上升的途径是依靠军功;另一条就是凭借知识、学术而仕进。此种情况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多有案例。《论语》中子夏所说“学而优则仕”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另外《史记》里李斯所说的“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可作为这一时代风气的生动注脚。类似于苏秦、宁越、李斯等凭借“知识”而改变命运的,还可举出张仪、范雎、虞卿等人。及至汉初这种现象也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史记》记载主父偃“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5]2961,与苏秦、李斯等人的心态如出一辙。这种以知识谋求上升的社会风习给庶民提供了竞争的平台,但同时也造成了读书人之间残酷竞争的局面。现实中的“上升”也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简单,毕竟能够脱颖而出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
如果对比此时期诸多凭借知识而发达的历史人物故事,我们会发现他们人生经历有惊人相似之处。而这些人之中最具传奇性的当属苏秦,从落魄至极的“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经过“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的刻苦攻读,终佩六国相印。落魄与发迹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突出的正是知识改变人生的动力。可以说,《战国策》和《史记》对苏秦故事的记载,尽管在细节上有一些差异,但其核心理念却表现得相对一致,即对于“游士”现象导致的这种社会阶层变动的生动涵括。
三、西汉中期到魏晋南北朝:苏秦故事的转向、低潮及其文化成因
从西汉中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苏秦故事的文本留存可见,这一时期苏秦故事的出现频率相对偏低,且对苏秦的态度与《战国策》《史记》有相当大的差异。东方朔在《答客难》中向往苏秦时代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时异事异”的现实。其实这种现实的变化并非从汉武时期才始现,只是此一时期该现象更为凸显而已。《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载秦昭王踌躇满志之时已有“厌天下辩士,无所信”的举动,可见这一“时异事异”与政治背景的密切关系。秦统一六国,“处士横议”就已不适合大一统君主政治的需要,而且“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的位置”[6]80,统治阶级从而对游士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汉初采取的“封建”制度给游士现象提供了回光返照的机会,但不久后,汉武帝元朔二年下“推恩诏”削藩,游士现象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统治阶级从大政方针上对游士采取高压态势,这种政策情随事迁就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集体无意识,如汉诗《箜篌引》“甘言无忠实,世薄多苏秦”,京房的《别对灾异》“内为苏秦之行,外似夷齐之语”以及魏曹丕《煌煌京洛行》“苏秦之说,六国以亡。倾侧卖主,车裂固当”等都对以苏秦为代表的游士采取了贬抑态度。
东汉末,荀悦鉴于党锢“处士横议”的现实,在《汉纪》中痛斥“三游”(游侠、游说、游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某一部分人对“游说之士”的心理,作为“游说之士”典型的苏秦在此种社会思潮下难逃指摘。另外,魏晋南北朝为政局极不稳固的时期,渴望太平的心态又不自觉地放大了对“游说之士”的反感。所以苏秦在该时期多呈现为“无信”“巧佞”形象,发愤苦读的苏秦形象很大程度上被遮蔽。
苏秦故事在此时期陷入低潮或还受到门阀制度的影响。随着王朝的政治稳固,西汉中后期的士人已不同于战国至汉初的“游士”而成为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士大夫”。虽然西汉中后期仍推行“不辨士与庶族”的选士制度,但这种新兴世家大族的出现无疑会对其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观念到东汉更加深入人心,据史传记载,光武帝就已表现出不甚重视单身士人转而倚重有宗亲势力者的倾向[6]268。东汉中后期此种观念更加普遍,“选士而论族姓阀阅”(《意林》卷五引《昌言》)已成俗例,“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寒门”(《后汉书·文苑传》),虽未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程度,但其形成的社会心态无疑对苏秦故事的创作与传播造成影响。在这种社会心态中,接近“寒士”身份的苏秦往往作为企图突破这一现状的“野心家”出现,避而不谈或者贬抑之就很容易成为苏秦故事在此时期不得不面对的两个选择④。
另外,我们还可注意到该时期苏秦故事的另一转向是仙佛观念的渗入。《洛阳伽蓝记》记载苏秦金、苏秦冢即已沾染佛家色彩。东晋王嘉《拾遗记》中记载一则鬼谷子梦中授书苏、张的故事,《全宋文》卷44收录袁淑《真隐传》一篇,与《拾遗记》所载故事有一定承接关系,尤可关注者为遗书责备二人的叙述,表现出出世态度的逐步增强。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现状,此类苏秦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其原因不仅与门阀制度造成的庶族士人积极进取心态的低迷、政局动荡杀戮之风大盛有关,也与士人受到玄学影响,“抑志身退”,转而追求山林之乐的心理有关。
四、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推行与苏秦故事的润色
唐宋时期,士人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科举制度的推行为寒士出将入相提供了可以期许的舞台,所以由寒门而发迹的苏秦就与此时的士人跨越时空产生了心灵的共鸣。
以唐人为例,高适《九日酬颜少府》“苏秦憔悴人多厌”;李白《别内赴征三首(一)》“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薛令之《草堂吟》“君不见苏秦与韩信,独步谁知是英俊。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男儿立志需稽古,莫厌灯前读书苦。自古公侯未遇时,萧条长闭山中户”。诸多诗作大都表达了类似“读书当许万户侯”的心声。唐代仕途的开放为“大量处于文化边缘的、出身低微的士人进入现实政治生活参与权力与利益的角逐”提供了机会[7]93。李白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高度自信,正可作为盛唐士子入世热情的脚注。士人之入世热情反映在苏秦故事的创作与传播上,便是对苏秦拜印、衣锦还乡的文学想象。
科举虽为士人提供了参与权力与角逐利益的机会,但相对及第、发迹而言,更多的却是落第、不遇。“怀抱利器,郁郁适兹”的自我期许与“不得志于有司”现实之间的反差,却仿佛大多数士人难逃的宿命。因此,苏秦故事的“落魄”以及“衣锦还乡”无疑给士人提供了最好的自况模板。
与唐代士子张扬、极端化心态相比,宋代士人更多了一份成熟的内敛。如果说唐代士子在“不遇”之时尚且不忘“腰间各佩黄金印”的话,那么宋人对苏秦故事侧重点的书写则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对苏秦落魄的书写不再如唐人那样充满奋发的激情,而是呈现出低迷的情调。如苏轼《浣溪沙》“谁怜季子貂裘敝”;吴礼则《鹧鸪天》“自怜季子貂裘敝,来与机云相对闲”;张榘《贺新郎》“季子貂裘尘渐满,犹是区区羁旅”;刘辰翁《金缕曲》“风雨断魂苏季子,春梦家山何处”等,大都弥漫着凄凉悲楚的音色。在宋人诗词中突出了苏秦故事“怜”及“二顷田”两个要素。“怜”字的强调无疑表达了宋人现状与苏秦故事的“同情”,是现实心境的托古。“二顷田”的强调则凸显出宋人追求稳定、保守的价值取向,前引张榘、刘辰翁、陆游等人的诗词都把苏秦故事中的旧貂裘情节与“家”“羁旅”联系起来,这与《战国策》《史记》等早期文献中苏秦羞于回家的情节大相径庭,即使在唐代“旧貂裘”也多是强调“不遇”而未如此凸显其与“家”的联系,可见这是宋人对苏秦故事的新创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晁补之《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中的“苏秦不愿印,乃在二顷田”,直接颠覆《史记》中“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的苏秦形象。
当然,唐宋时期苏秦故事主要存在于诗词的“用典”之中,呈现出片段化、碎片化的特点。不过,如把这些零散于唐宋诗词中的苏秦故事的遗存融会起来,可注意到在充满个性的诗词创作中也呈现出一种时代的共性。唐代苏秦故事多关注苏秦故事的“落魄”与“衣锦还乡”情节;宋代苏秦故事更多关注苏秦故事的“落魄”与“家”“羁旅”的关系,甚至凸显了“二顷田”在苏秦故事中的意义。虽然用典多根据的是大传统中的史传叙述,发挥空间有限,但是唐宋诗词对苏秦故事的频繁引用维持了苏秦故事作为“俗典”的传播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唐宋士人融合己意与时代普遍心态对苏秦故事中的某些前代未曾强调与凸显的情节要素反复皴染,形成了新的叙述语境。这一叙述语境一方面来自大传统中的史传叙述,另一方面也与小传统中的民间话语有着若干微妙的联系,元明时期苏秦故事的编纂与想象就是顺承这一思路而来并发扬光大的。
五、元明清时期:民间语境下的苏秦故事及其逐步定型
元明清时期诗词文章中的苏秦故事多沿袭大传统叙述中的苏秦形象,并未出现较大变化。然在作为俗文学的戏曲、小说中,苏秦故事却基于民间话语的改编与增饰而有了质的飞跃。苏秦故事较早出现于元代中期的《冻苏秦衣锦还乡》杂剧,该杂剧上承苏秦、张仪为同学以及“智激”情节的史传叙述而又有较大变动。凸显“世态炎凉”是该剧的主线,情节的改编也主要围绕其展开,突出了伦理亲情在苏秦故事中的位置。除了紧紧围绕苏秦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展开故事,该剧还基于前代苏秦、张仪为同学关系的载记,大胆想象其为“异姓兄弟”,并逆用苏秦智激张仪的情节而创“冰雪堂”一事,这正是建立于民间话语中对结拜兄弟之间关系思考的再创作。
《冻苏秦》杂剧建立了其后苏秦故事的基本框架与故事主线,元末明初有《苏秦衣锦还乡》南戏以及之后据之改编的明传奇《冻苏秦》,以上两种均佚,今存改自《冻苏秦》传奇的《金印记》。该剧承《冻苏秦》杂剧所建立的“醒炎凉世态”[8]1主旨,进一步凸显苏秦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从叙述结构来说,《金印记》在周氏、苏秦双线结构的运用上受《琵琶记》影响较大,“一年奉亲,一年奉君”的“忠孝”妥协或许也与“全忠全孝”的蔡伯喈有着某些联系,表现出戏曲“俗”的底层士人心态的真实的充满矛盾的一面。其后据之改编的《金印合纵记》对《金印记》情节又有所变动,按照史传记载增加了张仪的戏份,融入苏秦智激张仪的情节,以及或受朱买臣故事的影响而设置苏秦拜相后着敝衣归家以增饰其戏剧性的情节。
从上可见,苏秦故事戏一直围绕家庭矛盾展开叙述,突出“世态炎凉”,剧作者紧紧扣住苏秦“读书人”的身份,以苏秦自况心迹,为读书人吐气。这是元代科举不兴,落魄书会才人所具有的挣扎于“百无一用”与“皇天不负读书人”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苦闷心态的折射。
与戏曲中苏秦故事的尚“俗”有所不同的是,明清小说中的苏秦故事受到复古文学思潮的影响,从嘉、隆年间余邵鱼的《春秋列国志传》到明末冯梦龙修订的《新列国志》,再到乾隆年间蔡元放增删润色的《东周列国志》,呈现为一步步接近史实的趋于“文雅”倾向,这一倾向把苏秦故事所彰显的寒士气息又打回史传原形。不过,打回原形的苏秦故事不管怎样也早就沾染上了演变过程中浓厚的苏秦形象寒士化的气息,以及围绕家庭矛盾展开叙述的故事结构。
总之,元明清三代是苏秦故事趋于稳定的时期,在戏曲领域苏秦故事趋向于小传统的民间化叙事,在诗词文章中依旧维持着稳固的大传统叙述,而小说则杂糅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双向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叙述格调。不论如何,至此,苏秦故事以读书人的命运为故事核心,围绕家庭矛盾展开叙述的故事框架却趋于定型,其后的苏秦故事几乎再也没有越出这一故事模式的。
概言之,作为历史人物的苏秦,其故事在《战国策》《史记》中虽为“事实”,但其传奇性的经历为后世苏秦故事演绎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尤其是作为发愤读书者形象出现的苏秦,在历代故事演变过程中和底层读书人的现实处境与自我期许产生共鸣,被赋予寒士文化的内涵。苏秦故事在演变过程中受到政治环境、宗教渗入及科举制度的影响与制约,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表现底层读书人心理诉求的故事,其内核为文人代代相传并赋予新的文化意蕴。对苏秦故事进行梳理,不仅可以发覆这一故事的演变轨迹,更能透过故事演变一窥挣扎在底层的读书人的心史,为寒士文化的探究提供一个新的案例。
注释:
① 对苏秦持贬抑态度的论断,在《荀子·臣道篇》即已出现。归其为“态臣”者流,盖缘于作为游士身份的苏秦“巧敏佞说”的特征与儒家“信义”观念不同之故,这也说明苏秦身上本就存在两个矛盾面。在治世中,作为苦读发迹的苏秦容易成为接受主流;在乱世中,其巧佞无信的一面则更容易遭到关注。
② 这6篇杂剧为金仁杰《追韩信》、萧德祥《杀狗劝夫》、高文秀《谇范叔》、无名氏《风雪渔樵记》《张千替杀妻》以及作者有争议的《裴度还带》。
③ 裴登峰《士人“精神胜利法”与〈战国策〉的娱乐性质》(《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冬之卷)一文通过细读“托拟苏秦合纵、张仪连横《策》文”对《战国策》的“自我情结”予以发覆,足以成说。从这个角度看,其与《史记》编纂过程中司马迁的“自我感情投射”相通,说明苏秦现象是当时有一定代表性的现象和心态。
④ 本节以上论述多有参考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的相关论断处,特此说明。
[1] [西汉]刘向.战国策[M].贺伟,侯仰军,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
[2] [晋]王嘉.拾遗记[M].齐治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王季思.全元戏曲: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 孙崇涛.《金印记》的演化[J].文学遗产,1984(3).
[5] [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2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8] [明]佚名.金印记[M].孙崇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责任编辑 刘小兵〕
The Textual Evolution of Su Qin's Story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XU Zhong-ro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ombined vertical faction, Su Qin's identity of a literati, the legendary “down-up” and the experience of sweetness and bitterness in his life are interpreted by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combing Su Qin's story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we can find the evolution track of his story, and have a glimpse of the “heart history” of a literati struggling in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It can be a new case for the study of the poor scholar culture.
Su Qin; story evolution;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poor literati culture
I206
A
1006-5261(2016)03-0020-05
2016-03-10
许中荣(1988—),男,山东聊城人,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