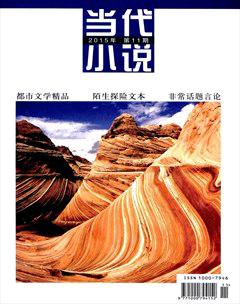花局
阮家国
这个春天好像与我无关,我已经退休了,但说退休又不对,准确说,我是退居二线,就是不再担任实职,不再当一个不起眼儿的副局长。县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副科只能做到五十岁。本来,我想跟妻子一路外出打工,多少挣点钱,补贴一下家用,但我们单位的局长又找我做工作,要我为单位写部门志。当然,如果我能答应下来,局里还是要另外再给我发一点辛苦费的。我跟妻子商量,妻子说,既然给你多发钱,那你就给局长一个面子。
早春时节,妻子就外出了。妻子的单位是个事业单位,内部规定可以请长假,但工资基本不算少。妻子也不是要出去打工挣钱,是要减肥。妻子身高一米六八,年轻时体重一百二十斤,生下孩子后奶水不足,不得不发奶,但一吃发奶的东西,就把身子发胖了,体重一下子长到一百五十斤。等她过了四十岁,体重就又长了十多斤。这两年,她一直在坚持靠运动减肥,但作用不大。去年她就说,今年要想办法减肥。有一天睡觉,我们亲热过后,她说,明年我一定要出去打工,下苦力减肥,不然就连搞这事都搞不起来了。她下了很大决心,要找回苗条,找回青春。
妻子一走,我的生活就难过起来。我不会做饭,吃饭就成了我每天最头疼的事,因此,能在外面吃,我就尽量在外面吃。
清明前,我进山回老家踏青祭祖,给祖坟挂青,悬挂寄托哀思的清明吊。给自家祖坟挂了青,我又去妻子娘家的祖坟挂青。其实,岳父母已去世好多年了,也就是说,妻子娘家那边也没妻子的亲人了。
岳父留下来的老房子,二舅子住过,后来二舅子也不住了,搬到了城里。岳父的老房子现在仍有人住,是岳父的一个本家兄弟寄居。我一个人来给妻子的父母跟爷爷奶奶挂青,好像就有点孤单。去岳父的老房子里找了一把砍刀,先顺着小路上山,又走进路边的树扒(树林),给妻子的爷爷奶奶挂青。这两座坟在树扒中间,紧挨着,坟堆上也都成了小树扒,挤满了茅草、竹子跟荆刺,乱蓬蓬的,看着叫人心寒。不把坟上收拾利索,挂青就是不敬不孝。我开始拿砍刀砍除妻子爷爷坟上长的东西。等把这座坟上的东西砍利索,我就出汗了。我脱掉外衣,又砍妻子奶奶坟上的东西。坟上的东西都砍干净了,这儿就好看多了。我找了两根我刚砍下来的青竹条子,用来挂青,给两座坟的坟头都挂上了清明吊。本来,我还想为妻子的爷爷奶奶烧点纸,但我又怕失火,没敢烧。
离开这里,我又去给岳父挂青。没想到我会遇到一个叫我姐夫的姨妹子,在去岳父坟上的半路上。叫我姐夫的人亲热地叫我姐夫,我差点就忘了答应,因为我有点吃惊,不敢相信对面走来的一个好像还年轻的女人还是我的一个姨妹子。姨妹子穿着朴素的青色衣裳,但岁月好像并没带走她苗条的腰身,看上去,她就像路边刚发出来的一蔸嫩嫩的小草。还有两个字,我不想说出来,那就是好看。我在想,她到底是我的哪个姨妹子。妻子娘家是个大家族,这么一来,我就好像有好多既认不完全又记不清楚的姨妹子,也不晓得这个姨妹子是我的叔伯姨妹子,还是叔伯的叔伯姨妹子,但我又不便问她。因此,我写这个蹩脚故事,还只能把她称做姨妹子。
话说回来,从我一看见姨妹子起,就觉得她对我好热情,好像就是我的亲姨妹子。我注意到,她好像一直在笑着,她脸上还有两个小酒窝儿,酒窝儿好像也在笑着。特别是她的眼神,好像就是晴天夜空里的星星,叫人一看心里总会产生一点想象。看上去,她好像是个嘻嘻哈哈嬉皮笑脸的热闹人。真没想到,我还有这样一个姨妹子。姨妹子说,姐夫,你年年回来给老的挂青尽孝,可不容易。我说,有时候我也没回来。姨妹子说,姐夫,你莫抠字眼儿,就是偶尔一两年没来,还不是年年来?姨妹子笑了起来,我也笑了。我问姨妹子到哪儿去,姨妹子说,春上还没吃到笋子(竹笋),想去扳点笋子尝新。我说,笋子应该是才发出来,正好吃,你快去扳。姨妹子说,扳笋子还不简单?眨个眼就能扳一大捆,我先陪你去挂青,不是你一个人还怪孤单。孤单?姨妹子说我孤单,我孤单不?我也不晓得自己孤单不孤单,她这么说,我也不好说不叫她去。我们就一路去挂青。
岳父的坟在地边上,这儿倒是不怕失火,能烧纸。姨妹子也从家里拿了火纸跟清明吊来,我说,这些都有,你就不用拿了。她说,各是各的心意,到伯父伯母他们坟前来,不烧点纸,心里会过不去。她这话说得倒也有理。她先陪着我给岳父岳母烧纸,又给坟头挂上清明吊。
给岳父岳母坟上挂了青,我的事就做完了,可姨妹子又要我跟她一路去扳笋子。想到她陪我挂青,礼尚往来,我就陪她去扳笋子。到了要扳笋子的地点,她说我,你没扳过笋子吧。我说,好像还是小时候扳过。她说,我就晓得你没扳过,树扒里难得拱,你就莫去扳了。扳笋子,我还是想扳,但我又怕别人看见我跟姨妹子往树扒里钻,会说闲话,就没进树扒。
姨妹子进路里边的树扒去扳笋子,我就在路外边的树扒里找笋子。长竹子的地点才长笋子,找啊找,可我也没找到好多笋子。我又钻进一处竹子更多的树扒,才看见不少笋子。听见姨妹子在上边叫我,我也没答应。不知咋的,我想跟她开个玩笑,叫她一时不晓得我在哪儿。她又在喊,姐夫姐夫,你在哪儿。我仍然不吭气,这时,我又听见她猛地惊叫起来说,哎哟,蛇,好大一条蛇。听见她说蛇,我就浑身一掣,打了一个大激灵。再看我身边,树扒里每一根竹子的竹蔸边上,还有好多枯枝败叶里边,好像就都有蛇要出来。有一条大蛇好像就看见了我,正吐着长长的蛇信子。我自小就怕蛇,怕得要命,就再也不扳笋子了,就连已扳的笋子也不要了,连滚带爬地朝树扒外跑,要快速甩开大蛇对我的威胁。
我还没上路,姨妹子就格格格地笑了起来。等我上路,她说,姐夫,看把你骇的,你好笑人,笑死我了,笑死我了。我抱怨她说,你还笑?她这才不笑了,说,你放心,蛇还躲在洞里呢,到热天才会出来。我说,一听见蛇我就怕,哪儿还顾得想会不会有蛇?她不说蛇了,问我,你扳的笋子呢?我说,还在下边。她抿着嘴笑,又进路下树扒里去拿笋子。过好一下,她才上来,又多扳了一些笋子。见我坐在路边上,右脚没穿鞋,她说,哎哟哎哟,看我看我,这玩笑可开大了,害你把右脚皮鞋都蹬坏了。她搁下笋子,拿我右脚皮鞋看。我的右脚皮鞋,右边的鞋帮子豁了,肯定是刚才抢时间上来时,哪一脚没踩好,一脚就把皮鞋右边的鞋帮子蹬豁了。她说,姐夫,对不起,我明儿给你买一双皮鞋。我说,哪个要你买?这鞋帮子找修鞋匠还能补起来。她说,那算不行,补过的皮鞋不把你穿丑了?现在你没鞋子穿了,咋搞?要不你在这儿等着,我回去给你拿一双鞋来。我说,没事儿,就是不穿鞋也能走。
见姨妹子把扳的笋子都捡到挎箩里,要走了,我站起来,右脚把鞋趿着,想将就着走。她叫我等一下,说,这挎箩背带上恰好绑着一条布条子,好像就是给你准备的,来,把鞋绑到脚上,就能走了。我用布条把皮鞋绑到脚上,果然就能走了。
到她家里,她给我找了一双布鞋,叫我换上。布鞋是新鞋,倒也还合脚,我说,这布鞋好像就是给我做的,布鞋养脚,还是穿布鞋舒服。她说,你在城里就没穿过布鞋?我说,上班不穿,回家才穿。她说,这双你先穿着,我明儿再给你做一双。我随话问话说,这鞋是你做的?她说,咋的,你还不信?闲的时候,我也做布鞋卖。我这才注意到,我脚上穿的是一双胶地子、灯心绒鞋面的布鞋,跟从店里买的布鞋差不多。我说,没想到你还有做鞋的手艺。她说,啥手艺不手艺,还不是想摸几个钱?我再次看我脚上穿的布鞋,没想到我这次回来挂青,倒把皮鞋踩坏了,又穿上了一双姨妹子做的布鞋。
她洗手给我泡茶,开始剥笋子。见她忙着,我也去帮忙。她说,你们城里,笋子早就尝新了吧?我说,笋子是有人在卖,不过我倒还没尝新。她说,那好,中午我们就炒笋子尝新。杯子里泡的茶不烫嘴了,我喝两口茶说,还是春天好,又能吃椿芽儿(香椿),又能吃笋子,新茶马上又要出来了。她说,茶场马上开园,又要忙着摘茶叶了。我说,给茶场摘茶叶,多少钱一斤?她说,头一茬儿单芽茶,一百元一斤。我说,那要是摘自家的茶叶,卖给茶场呢?她说,那又不一样了,一斤多三十元。我问,你家有茶叶没?她说,有一点,不多,不像茶场那边的人,家家都有不少茶叶。我说,茶场的新茶不好买吧?她说,茶场开园头几天,等着买新茶的人多,不晓得有好多。我说,明儿去看看新茶能买到不。她说,茶场一开园,我先摘自家的茶叶,拿去请茶场先做出来给你。我说,这两天茶场能开园不?她说,说不定明儿天就开园了。
姨妹子家门前院坝边上有一棵桃树,桃花挂满枝头,红艳似火。我正在观赏桃花,姨妹子喊我吃饭。
姨妹子三儿两下就把午饭做好了,炒了个笋子腊肉,还有个椿芽儿炒鸡蛋,看起来好像也并没把我当客待,其实像这样遇饭吃饭最好。要是她把饭菜做得太丰盛了,我心里还会有负担,但吃饭只有我们两个人吃。后来我才晓得,她男的外出打工去了,她家在城里买了房子,要装房子。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给我打电话,说茶场今儿开园,叫我先到她家。我一看时间,才五点过一点,还真有点后悔昨儿天不该给她手机号。我说,太早了。她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不起早,摘茶叶还能挣到钱?一日之计在于晨,理是这个理,但我仍不想起早。她说,你赶紧起床,我骑摩托来接你。看来我就是再不想起早也不行了,还只能起床。
来到她家,时间还不到六点。见她把摩托朝屋里推,我说,不到茶场了?她说,先摘自家的茶叶,再到茶场,请技术员把茶叶做出来。我说,你今儿就想把新茶喝到嘴?她说,是呀,春上不喝新茶,又缺味儿又差劲儿。我说,你说话也好有味儿。她哈哈笑着说,有没有味儿我不晓得,我只晓得今日有酒今日醉,人要及时行乐。我说,所以你今儿就要把新茶喝到嘴。她说,就是呀,不瞎说了,我们赶紧抢时间摘茶叶。现在,我好像又发觉,她又像个心直口快、有口无心的人。
她家门外有自来水水龙头,锁上门,她去洗手,还叫我也洗手。她说,摘茶叶,手要干净。我说,我可没摘过茶叶。她说,摘茶叶还不简单?一看就会。我说,摘茶叶好像就不是男的做的事。她说,你怪说,等我们到了茶场,你看有没有男的摘茶叶。
她家的茶园离家有两里路,有三四分地。我们来到茶园,天才亮。茶叶才发出来,只发出一个嫩芽芽儿来,摘单芽茶,正是摘的时候。清明前后,茶场要做一芽一芽的芽茶,摘茶叶要摘单芽。她边摘茶叶边说,摘单芽茶,要摘得匀净,选稍大一点的芽茶摘,不能拿手指甲掐芽茶叶根儿,拿两个手指逮住,轻轻一拈一拽,一个芽茶就摘下来了。我摘了几下,她笑着说,摘茶叶就是这样摘的,看来你倒还怪在行,我说一看就会嘛。这是我头一回进茶园摘茶叶,也是头一回看她摘茶叶。手脚快的人,不拿一只手摘茶叶,拿一双手摘。姨妹子就是一双手摘茶叶,两个手刷刷刷地摘。
由于摘茶叶摘得早,我们只用了半早上就把她家的茶叶摘完了。我们又骑车赶往茶场。
一到茶场,我就看见,茶场满山遍坡的茶园,处处都站着摘茶叶的人,果然也有男的在摘茶叶。茶场场房的茶叶加工车间正在忙着加工今年摘得最早的茶叶,有好多人在这儿等着拿新茶。我就遇见了好几个从县城来等着买新茶的老熟人,见我骑车带个女的来,有人还不怀好意地看我。
等姨妹子把才摘的茶叶交到技术员手上,我们又到茶场的茶园摘茶叶。路上,我问她,茶场能帮你做茶叶?她说,你想得倒美,人家自己加工茶叶都忙不过来。她前后看看,见没人过来,才说,有个技术员是我一个老表,我给他衣裳荷包里塞了包烟,他才勉强答应下来。我说,看来喝点新茶还不容易。她说,当然,你说哪个不想先尝新呢?
为抢摘茶叶,茶场给摘茶叶的人管午饭。午饭前我们只摘了个把小时茶叶,我手笨,摘的茶叶少得可怜,好像还没盖住篮子底,不好意思过秤,我把我摘的茶叶倒到了她的茶叶上面。她说,你摘的也不少,下午你攒劲儿摘,看能摘好多。
下午是我头一回摘茶叶挣钱,我摘了足足五个小时茶叶,挣了五十元钱。她说我,行啊你,挣了不少。我说,我挣的钱还不够你的一半。她说,也不少了,你没想想?你一只手就摘了这多。我说,这倒是的,但我只能一只手摘。她说,明儿天再摘,争取挣一张大票子。我说,你摘,我不想摘了。她说,摘茶叶多好,又不出力气又能挣钱,你就把这当做下乡体验生活。把摘茶叶当做体验生活,我没想到她还会这样说。我说,我又不是大作家,还要体验生活?她说,那大作家又是啥人?听说你就是个大笔杆子,大笔杆子难道就不是作家?我说,莫言你听说过没?他就是大作家。她说,电视上看过,好像前不久还得过世界大奖,拿了好几百万奖金。我说,我只是个能将就着写个材料的人,跟他比,他在天上,我在地上。她说,也不能那样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她请茶场帮忙做的茶叶还拿不到手,也就是说,今儿天还喝不到新茶,但我们一到她家,她就从身上拿出一点新茶来。新茶用一个小塑料袋装着,只有一点点,大概只能泡几杯茶。我说,哪儿来的新茶,是不是你老表悄悄给你的。她笑笑说,新茶总算能喝到嘴了,还真是的,是他悄悄给我的,熟人总能多吃四两豆腐嘛。
她拿两个玻璃杯泡新茶,叫我喝茶,她去做晚饭吃。刚泡的芽茶漂面,过好一气,芽茶才会在淡青色的茶水中下沉到杯底。这时,茶叶不烫嘴了,正好喝。这是我今年喝头一杯新茶,我先把茶杯拿到鼻子前闻闻香气。新茶的清香味儿好诱人,我抿了一点,再抿一点,慢慢品尝新茶的清香。
我叫她来喝茶。她喝下一口,说,香,好香,只有清明前喝新茶才香。我说,过了清明喝新茶就不香了?她说,也不是不香,但节令不能错过,等过了清明,你再喝新茶,就又是一个味儿了,少了一种清明前才有的鲜味儿。
吃过晚饭,她带我去卡五星。昨儿天她就留我卡五星,但昨儿晚上我回老家有事,没玩成。
卡五星是现在这边正流行的一种麻将牌的新玩法,据说是从诸葛亮生活过的襄阳那边传过来的。卡五星三个人比输赢,只打条饼万三种牌中的条饼两种牌,外加红中、白板、发财三种字牌,不准吃牌,只准碰牌杠牌,牌路活,大和多,可规矩也多。手中有四六条、四六饼,停牌五条、五饼,赢牌就叫卡五星。最小的和叫“屁和”,屁和不能逮炮,只能自摸,晒牌(亮牌)自摸才能翻一番。卡五星赢钱,一般是屁和的四番,跟清一色、小七对赢钱一样多。像“杠上杠”、“杠上开花”、“手抓一”、“海底捞”,赢钱都翻一番。最大的和叫“满的”,赢钱是屁和的八番。像清一色卡五星、清一色中有四张同样的牌、有两对同样对子的“龙七对”,还有有三句字牌的“大三元”,都是满的。
现在是个吃喝玩乐的时代,县城里除了人多房多,就是麻将机多。可以这样说,卡五星让麻将馆儿跟麻将机都翻了好几番。城里大街小巷处处都是麻将馆儿,麻将馆儿还蔓延到了乡下。在岳父家老屋后边的贡维平家,就有一台麻将机,今儿晚我们就去那儿卡五星。
在贡维平家卡五星,打一场牌收台费十元。我跟贡维平也是老熟人,跟他说几句客气话后,我们就去卡五星。我们还没在麻将机边坐下,我见姨妹子就递给贡维平二十元。贡维平对我说,我哪儿能收你台费?我说,人亲财不亲。姨妹子说,就是,老表是老表,萝卜还是三分钱一斤。贡维平咧着嘴笑,还是把钱接了。贡维平打开麻将机开关,说,哪个跟你是老表?姨妹子说,黄泥巴打灶,各喊各叫,我今儿就把你喊老表,咋了?贡维平说她,你是个热闹人,咋说咋好听,老表就老表吧。贡维平叫我先做庄家,我推辞一下,只好按色子拿牌。要说起来,贡维平把我岳母喊姑太婆,在辈分上他比我还矮两辈。
卡五星,五条五饼最烫手,晚打不如早打。头一把牌,我手中有三个五饼、三个八饼,天生停和,停四七条,抓头一张牌,我抓到一个八饼,开杠,杠到一张四条,屁和自摸,但我却嫌和小,把五条打了出去,过一圈,上家贡维平碰三条,打出一张五饼,我又开杠,竟又杠到一张五条。我们玩的是屁和自摸输家一人给五元的麻将,这把牌,我杠开卡五星,赢了个满和,满和封顶四十元,加上一个暗杠、一个点杠,贡维平给我六十元,姨妹子给我五十元。这把牌我只用了分把钟就赢了一百一十元,而我今儿天摘大半天茶叶,才挣了五十元,难怪好多人都眼热卡五星。要说魅力,能赢钱才是卡五星的魅力。
玩物丧志,说起卡五星,我怕上瘾,平常也不大玩,可牌逢生手,这晚我火儿冲,牌运好得出奇,手上要啥牌,就能抓到啥牌,或碰到啥牌,隔三岔五总要摸个满和。有好几把牌,我还得感谢姨妹子,是她给了我碰牌的机会。
牌打到后来,她说不打了,没钱给了,再说明儿天还要起早摘茶叶。她掉了三百多元,贡维平也掉了百把元,我上场就没掏本儿,赢了将近五百元。她掉得最多,我说把她掉的钱退给她,她说,看你,姐夫,说到哪儿去了?钱是身外之物,挣不完也花不完。看来,她倒还真是个豁达人。
这晚我就在贡维平家睡觉。第二天一早,我跟姨妹子又去茶场摘茶叶。这天,我在茶场买了一斤不带包装的新茶,她把请茶场做的新茶也拿回来了。晚上,我们又在贡维平家卡五星。这晚,她又输了两百多元,把她今儿天摘茶叶挣的钱掉了个精光。
睡觉起来,我看见天在下雨。下雨自然就摘不成茶叶了,难怪姨妹子没过来。下雨也好,我正好回去。昨儿天局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回去帮忙搞个材料。
我洗漱用的东西随身带着,本来,我可以不到姨妹子家,可我的脚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她家。
我说要走,她说,莫走,下雨正好陪你卡五星。我说,十赌九输,我看这卡五星玩不得,你最好也莫玩了。她说,愿赌服输,卡五星哪儿有不输钱的?我说,你还是早点进城装房子。她说,等茶叶一摘完,我就进城。见我真要走,她把请茶场做的新茶拿出来给我,我说,你留着喝,新茶我买了。她说,你买的是你买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嫌弃就拿着。她这样说,我就只好拿着。
我要去乡上搭车,可雨下得大了一点,我又没带伞。她给我找了一把伞,叫我等她一下。我打开伞,走过她家院坝,走到桃树边看桃花,我发觉两天没看,这棵桃树上的桃花开得更艳了。桃花太好看了,我有点恋恋不舍的,好像舍不得离开这棵桃树。
她说到乡上有事,就便儿送送我。我说,看来这雨是慢上劲儿,得下一天,那你就便儿给你女儿送把伞。她说,就是,今儿天星期五,女儿要回来。我说,你女儿在上几年级,学习不错吧?她说,在上三年级,好像还行,我还想把她转到城里去上学呢。我说,这当然应该。她说,可又怕进不了县实验小学,我还想请你帮个忙,看能不能把我女儿的户口转到你家。我说,到县实小上学,是不是一定要看户口?她说,是这样,县城十字街、北大街、东门街的户口才报得上名。呃,姐夫,给我女儿转户口这事,你要给我姐说吧?我说,这事肯定要跟她商量,我把她电话给你,你直接跟她说吧。她说,我才不跟她说呢,我就找你。我说,这事你等我想想再说。
我没想到,姨妹子要我帮这个忙,也不知道这个忙我能不能给她帮到。回家后,我一直在犹豫着,这事跟不跟妻子说,又该咋跟她说。妻子每隔几天就会发短信,说她打工的辛苦,说她有多累,当然,也说她的减肥,说她体重下降了八公斤。每次跟她发短信,我都想说说姨妹子女儿转户口的事,可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我还真怕妻子不仅不答应,还会犯疑,怀疑我的动机,为啥要给一个原来我都不认识的姨妹子帮忙,给她的女儿转户口。
谷雨过后,有一天下午,姨妹子打来电话,叫我到公园东头儿的小广场去。这时我在家里刚把单位一个材料修改完,一看时间,我在电脑前已坐了两个多小时,正想出去走走,活动活动身子骨。
县城有一条小河,河北是老城,河南是新城,公园就在新城河边。我家住在东门街,从这儿到公园不远,过河就到了。公园建成有好几年了,据说曾规划在公园南边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三馆”,可后来原计划建“三馆”的土地却变成了一栋栋电梯楼。一大片电梯楼把公园南边的视野都堵死了,看起来,公园又好像成了电梯楼的院坝。
河上有座大跃进时建成的跃进桥,过了跃进桥,往西边走几步就是公园东头儿小广场。小广场的北边下面是河,边上有栏杆,姨妹子正站在栏杆边上,手扶着栏杆。我过桥时就看见她了,她也看见了我。一看见她,就见她在笑。我好像有好久都没看见她笑了,看见她脸上的两个酒窝儿,我心里竟咯噔了一下。
她带我去看她买的房子。她买的房子就在公园小广场南边路外,是一楼,不大不小,有一百一十多个平方。我说,这个点好,离学校、菜市、县医院都不远,办事就是方便。她说,最好能赶在秋季开学住房子,两三个月装得完不?可我现在就连装修工都没请到。我说,算你运气好,我这儿就有装修公司老板的电话,我马上给你找装修工。
我一打电话,装修公司的人马上就来看房子,说明天就派人来装修。装修公司的人一走,我发觉姨妹子的脸上简直就笑成了一朵花,她又叫我到她住的地方去。
我没想到她还租了住处,她租了两小间房子,隔她买的房子不远,也是一楼。一进屋,我就看见屋里搁着不少笋子、椿芽儿。我说,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来。她说,我还给你带了一些,走时你带回去。我说,我不要,又不会做饭。她说,你不会做饭,姐姐也不会做吗?我说,忘了给你说,她出门去了。她说,那也好办,在她回来前,你就在我这儿吃饭。她洗手给我泡了茶,又开始择菜做饭。看来,晚饭只有在这儿吃了。
她这次进城,给我带了一双她亲手做的布鞋。我喜欢穿她做的布鞋,把布鞋拿了回去。晚上,洗脚后,我就把新鞋穿上了。穿上前,说不清是为啥,我还把一只鞋子拿到嘴前,叭叭地亲了两口。
头两天,装修工在她的毛坯房里给墙打排电线的槽子,做敲敲打打的事,我们就去采买先要用的装修材料。她没装修过房子,也不晓得咋买材料好。材料只有看了才有比较,才能选择,我就带她先看材料,找卖装修材料的商店一家家地看。我们差不多看了整整一天,可她还是拿不定主意,该买哪种档次的材料好。我说,装房子不能太爱好了,你就是花百儿八十万元装修,十年后看起来跟人家只花十万元装的房子也没好大差别,倒不如图简单。她说,你说的我懂,就是不能花大价钱装房子,可也不能买太差的材料,那就买中不溜儿的中档货。我说,还有,我觉得最好不铺地板,一铺地板,一来客,人家就要换脚,穿鞋套,多麻烦?她说,倒也是,铺不铺地板,等我问问你挑担(连襟)再说。
在她那儿一连吃了几天饭,我就不好意思再吃下去了。这天下午,她又留我吃饭,我说,晚上有人约我吃饭。她看看我说,你哄人,看你一下,我就晓得你在说假话。我说,我总不能白吃白喝,咋好意思在你这儿长期吃饭?干脆这样,以后我来吃饭,每顿给你二十元生活费。她说,看你,又说到哪儿去了?你一直在给我帮忙招呼装房子,按说,我又要管你饭,又要给你开工钱。这话听起来顺耳,听她这样一说,我就觉得她真会说话。我心里又不能不说,她这话说得不是没道理。
妻子走后,我就像个没家的人,但自从姨妹子进城后,到她那儿去,我能吃现成儿的饭,我就又像个有家的人了。既然她这儿好像是我的家,我就得顾家。第二天,我就买了几根莴笋跟两斤嫩豌豆米过去,她却说我不会买菜。她说,菜倒是好菜,可就是太老了。我说,这菜看起来多嫩,明明不老。她说,你看,是你看走眼了,你哪儿有眼睛劲儿?你根本就不会买菜,以后就别再买菜了。
有一天上午,她见我没过去,又打电话叫我去吃午饭。我说,今儿天中午真的有事,要参加人家婚宴。她倒没说啥,这时,我正准备拿刀削两个洋芋,煮油盐面条吃。
我在电脑上又处理一段文字后,起身准备做饭。我才开始削洋芋,就听见门响。自从妻子走后,我家房门还没被人敲过。我在想,敲门声是不是来自我家房门,我是不是听走耳了。再听,是有人敲我家的门,门又不轻不重地被敲了一下。
我万万没想到敲门的人会是姨妹子,她却又不进屋,说,我就晓得你又在说假话。我只好又过去吃饭,看来,我只有在她那儿把便宜饭吃下去了。
天不觉就热了起来,有一天,我又下乡。这次在乡下多待了一天,一共待了三天。昨儿天她还给我打过电话,但今儿天她就不打电话了。我打她的电话,她又不接,我就觉得有点怪。回城已是晚上了,我想先到她那儿去看看。
她的租住处屋里没开灯,我又去看她正在装修的房子。这儿有灯,装修工正在忙着,却不见她。我问她呢,装修工说,她还是早上来过,后来就不来了。
我觉得不对劲儿,她有可能就在屋里。我又到她的住处,看见门上并没挂锁,可门却推不动。她肯定在屋里,我在门外打她电话,听见她的手机在屋里响着,可就是没人接听。打电话没用,我又开始敲门,重重地敲门,大大的敲门声把房东都引来了。房东说,今儿一大天都没看见她了,是不对劲儿,该不会是出事儿了吧?经房东允许,我把房门撞开了。
她在床上,脸上滚烫,人事不知。房东帮我把她搀扶到我背上,说,你赶紧送她上医院,屋里你放心,我照看着就是。
我背着她一路小跑,直奔县医院急诊科,先办住院手续,安排床位,给她打上吊瓶儿。
快到半夜了,她才醒过来。她一醒就笑,有气无力地说,这是哪儿?我说,你还行,还笑得出来。她说,我也不晓得是咋搞的,下午觉得浑身没劲儿,就睡觉,哪儿晓得一觉就睡成这样了。我扶她坐起来,拿湿毛巾给她擦嘴。她嘴干得厉害,都干起壳了。我给她拿了一个喝水的杯子,杯里已倒了小半杯开水凉着,我又倒一点开水进去,让她喝温开水。她肯定渴得厉害,看,一杯开水她一气就喝完了。我说,我去给你买点东西吃。她说,不想吃,也不饿。我说,我还是回去给你煮点稀米汤喝。她说,稀米汤也不想喝,真的,有你在这儿陪我,我简直一点都不饿。我不晓得她咋要说这话,这话说得我心里又咯噔了一下。可等吊瓶儿打完,她又叫我回去睡觉。这间病房没有空床,想到明儿天早上还要过来帮她看病,我只好回家休息。
好在第二天,经检查诊断,她只是得了重感冒。
她出院的第二天,我们没吃晚饭,她约我出去吃烧烤。我说,咋想起来要吃烧烤?她说,想吃,还就想潇洒一回。
我们到河堤烧烤一条街吃烤鱼,找了一个有空调的小单间。天热,我们在喝冰冻啤酒,这是我头一次见她喝酒。她好像能喝酒,已喝了好几瓶儿啤酒。我发觉,她喝酒上脸,她的脸红了起来,看起来艳若桃花,我好像就又看到了老家她家门前那棵桃树上的桃花。我说,你是不是很能喝酒?她说,才不是呢,我只能喝一点点。我说,是不是脸上有酒窝儿的人,特能喝酒?她说,我不是说了,没酒量吗?呃,你跟哪些有酒窝儿的人喝过酒?我说,也就跟你喝过。她说,谁信?不行,谁叫你这样说?要罚你,从现在开始,你喝两杯,我喝一杯。我说,这咋行?我又没多大酒量。她说,好久没喝酒了,今儿酒一定要喝好,你就给我个面子吧,二比一,我才有劲儿往下喝啊。我这人心肠软,只好牺牲自己,让自己吃亏。我们又喝了不少啤酒,才走。
她好像喝多了,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我们顺着河堤走,要走过南大桥南桥头,往公园走。在桥头,我们还站了一下,看河上的夜景。这两年,城里在河上修建了拦水蓄水的橡皮坝,流过县城的小河好像变成了波涛滚滚的大河,又在河两边的河堤上搞夜景建设。每到夜晚,南大桥上下一河两岸,总会布满装点夜色的彩灯。现在,在我们眼里,河上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的彩灯好迷人,看起来简直就像天上的银河。看眼前的天上的银河,我们都有点激动,她说好美好美,我也跟着说好美好美。
走到公园,她说,我差点就忘了问你,那天我是咋到医院去的?我说忘了,她抓着我的胳膊,摇着说,我要你说。我说,当然是坐车去的。她说,不对,好像不是的,你说出来呀。我只好说,是背她到医院的。她说,那你现在也背背我,我喝多了,走不动了。说着,她就趴到了我身后,看来,不背她好像又拗不脱,我只好背她。她在我背上说,长大后还从来没人背过我,叫人背着真好。说着,她身子往上一纵,两腿就把我的身子夹得更紧了。这时,她哪儿晓得我身上有多难过,说心里话,我都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当然晓得,自己要是控制不住,后面就会做出啥事来。
好不容易,我才把她背到屋,可她又不愿意下来开门,还赖在我背上。她给我钥匙开门,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把我背到床上。我又背她进屋,到床边,把她放到床上,但我又放不利索。她人溜到了床上,但她的两条胳膊却还在缠着我,又在拽我。我放在裤兜里的手机,好像又贴着我的大腿,振动了一下,这叫我打了一个激灵。我说,啤酒喝多了。她这才丢手。我不说要去解手,又哪儿走得脱身?
实际上,刚才在公园,我们就都上过厕所。一出门,我就赶紧溜了。我当然明白,再不走,自己就肯定走不了了。
过了桥,我的心才放下来。一看手机,妻子给我发了好几条短信,还给我打过电话。这时,我就是给她打电话,也根本解释不清,我也懒得跟她解释了。她今年走后,一直怀疑我,怕我出轨,怕我有外遇。我多次向她保证,她好像还不信。实际上,在我心里,她根本就没离开过我,一直还潜伏在我身边。一想到她这多年来对我跟我们家的付出,我就不能对不起她。再说,我还向她保证过,就更不能对不起她。起码,我要像个男人,说话算话。
奇怪的是,这之后,姨妹子就不再联系我了。
回想起来,我们吃烧烤喝啤酒那天晚上的事,我可能没处理好,弄得我们双方都无比尴尬难堪。看来,只有让时间来慢慢淡化我们的记忆。
不知不觉,热天又往前走了一截,学校就放暑假了。
实际上,我心里还一直在等她的电话,但我就是等不到她的电话。有一天,我去她那儿看,房东说,她退房了。
她的房子当然也早就装好了。在她装好了的房子前,我给她打电话。她的手机提醒我说,你的电话已转入来电提示。我给她打电话,不是想见她,是要给她说个事,就是她女儿转学的事。尽管自从在老家她跟我说过一次后就一直没再说过,可我还是没忘记这事。我想不给孩子转户口,看能不能把这事办成。也是事有凑巧,我大学毕业头几年曾在县教育局工作过,原来的一个老同事后来一直在县实小工作,是财务主管。财务主管是内当家,我就找他帮忙。我跟他说,不管你想啥办法,你都要保证帮我把这事办成。学校放暑假前,他给我打电话,叫我一开学就带孩子来报名。这两天,我就急着要给她说这事,可现在又打不通她的电话。难道她是跟我说着玩的,又不想给女儿转学了?我打算既不等她的电话,又不再给她打电话了,只当自己没事找事,做了一次蠢事。
妻子在江苏张家港一家工厂做工,说要到年底才会回来。
有一天凌晨,我从敲门声中醒来。天还没亮,我走到门边,却又不敢开门。这时,放在床头的手机又响了,我又进卧室去接电话。是妻子打来的电话,我问她在哪儿,才晓得她隔着门板给我打电话。妻子突然回来,我差点都认不出她了。她黑了瘦了,但看起来倒好像更年轻了。我说,你回来也不打个电话?她说,就不打电话。
这天,妻子说起她一个叔伯妹妹请我帮她的女儿转学的事。我说,我搞不清你有好多妹妹,你说的是你哪一个妹妹?她说,就是清明前你进山挂青时,请你帮她女儿转学的那个妹妹。我说,这我倒是想起来了,是有这事,但这事又不大好办,还没办好。她说,不会吧,你是不是在哄我?我说,你晓得,我素来不哄人的。她说,那你赶快去办,看不给她女儿转户口行不行。我说,你咋晓得这事?她说,我那个妹妹,她男的在我做工的那个厂管事,最近她下去玩,跟我说的。我说,呃,你那个妹妹,我的姨妹子,她到底叫啥名字?妻子却说,我也不晓得她的名字,咋的,你到现在也还不晓得?顿时我就一愣,我不晓得妻子是不是说,我跟姨妹子交往时间不短,应该知道她的名字。看来,妻子还是知道一些我跟姨妹子交往的事。那么,妻子是不是早就有心,才让姨妹子在她去张家港后照顾我的生活?这又是不是就是妻子为了考验我才给我做的一个局呢?还有,我那个姨妹子,其实她早就晓得她姐姐外出,起初,她只是想试探试探我,但后来她是不是就春心萌动,也想尝试一下呢?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不晓得姨妹子的名字。后来,我也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就有这样一个姨妹子,她山里老家门前有一棵一到春天就开满桃花的桃树?我们是不是真在一起扳过笋子,摘过茶叶,打过麻将,还喝过酒呢?那晚喝酒后,我是不是就趁着酒兴,还背过她呢?而这一切又好像根本就不存在,我越想越糊涂,好像正从一个开满桃花的桃色梦中醒来。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