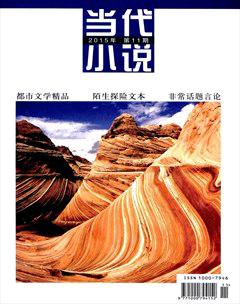活鸡宴
阿航
傅献勋
教堂的钟声敲响五下,傅献勋摸摸索索地从床上起来。其实教堂钟声还没敲响时,他就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了。街边路灯折射进来的光亮,犹如一柄大刀。傅献勋曾多次想到过,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形状呢?他到底没再去深究。巴黎的冬天寒意浓郁,特别是他住的这种居住房,夹在高大的房楼间隙,如同茂密森林里的一株小树,那阳光与它几近于绝缘。
今天礼拜二,是他们这帮老家伙吃活鸡的日子。在十六年前,那位叫留忠青的老乡,从巴黎郊外的农场买来六只活鸡,按老家的做法红烧了,然后盛于脸盆里端上桌面。当时在场的诸位乡亲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留忠青说,咱们大伙一条命落在了法兰西,清一色光棍,有子女等于没子女,没子女不用说绝后代了,日后就得靠大伙儿互相间照料着了。留忠青此话一出,大伙不由得一阵哆嗦,身上冷飕飕的。是啊,原先大伙儿青壮年时,有没有家室、有没有子女,那不是甚么大事。反正都已认命了,同时也习惯成自然了。要解决性的问题,巴黎的红灯区里有的是妓女。手头宽裕时就睡个高档点的白种女人;手头紧时凑合睡个非洲黑妹,照样都能起到消防作用的。如今岁数渐大,不去想时倒也浑然不觉,每日里搓个小麻将,隔半月一月逛趟红灯区,日子过得还说得过去。今日经留忠青这么一提,大伙儿便有些发慌了,心头沉重了。陈生根说,刚才忠青的提醒没错的,我们都是黄土埋到肚脐眼的人了,趁现今大伙还时常聚聚的得想个办法。朱岳琴说,今天忠青请大伙吃活鸡,依我看他是有用意的,我的猜度不知对不对……反正在我看来,这是个好方式,日后就每礼拜吃次活鸡好了,轮流做东。连云发说,岳琴的提议我赞同,既能吃鸡又能会面,还能晓得谁有个头疼脑热,一箭三雕的好事儿嘛!
那天为礼拜二。
今天轮到傅献勋做东。他提上那只经过“乔装打扮”的鸡笼从家里出来。由于巴黎城里是不允许活的家禽进城的,所以他得乘坐巴士去巴黎郊区的农场里买活鸡。
路上一共要换三次车。对于这条线路,傅献勋是闭着眼睛也能走了。其实,他们中的每一位从自家家里出发去郊外那家农场的路,谁都轻车熟路的。毕竟已十六个年头了啊。
本来,巴黎的地铁系统这么发达,如这些老人们乘坐地铁去郊区农场的话,要便捷得多,舒适得多,时间也要大大的节省。但这些老人们十分的顽固,顽固到了怪异的地步。当年,在他们从上海乘坐洋轮抵达巴黎时,巴黎的地铁尚未成气候的。他们因此就一辈子不去乘坐地铁。他们对新生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怀疑态度和排斥心理。他们称地铁为地洞车,嘲笑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巴黎地铁是老鼠嫁囡、地鼠钻洞。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地面上跑的,才是可靠的,安全的。依此类推,他们中除个别人乘坐过飞机外,其余的人均没有乘坐过那像大鸟一样的玩意儿。因为他们从中国出来时,乘坐的是轮船,他们对飞机连概念都没有的。
老人们抽的纸烟,是他们年轻时代的产品。淡蓝色的烟壳上印着个长翅膀的齿轮,海绵嘴自然是没有的。这法国的烟草公司应该说是做到以人为本了,多年来一直小批量地生产这种“工业革命”时代的香烟,以满足从那个时代过来、又跟不上现今时代步伐的老烟民的需求。
……
太阳刚刚露脸,郊外的田野白茫茫的,昨夜的霜冻还未融化,还是它们的一统天下。傅献勋从巴士上下来,兜头一股冷风扫过,他连着打了三四个喷嚏。里头的暖和,外头的干冷,傅献勋这架老牛车经不起折腾啊。傅献勋走在乡间土道上,步态迟钝,一团团的白汽从他的肩膀两边散发开去,远看如一台小型蒸汽机似的。傅献勋走着走着,又咳嗽开了,鼻涕、眼泪糊了半脸,他不得不抱住路旁一根电线杆儿呼哧呼哧喘粗气,取出手拍擦拭脸面。
农场主是位脸膛红润的汉子,他和这批中国老头混得很熟。农场主瞧着傅献勋的脸色说道,我愿意把自己的健康秘诀告诉你,你爱不爱听?傅献勋连点头、摇头的气力都没了,就近坐在了一张椅子上,胸脯一起一伏拉风箱似的。农场主是位饶舌之徒,他不顾现实情况还只管往下说道,我的健康秘诀是每天喝适量自酿的红葡萄酒。你如听从我的劝告,我就免费送你一瓶我自酿的红酒。
临走时,傅献勋对农场主说,见一面少一面啦……他伸出三个手指头不再往下说。农场主说,你今天怎么啦,老是拿手说话……你这三个手指头又是什么意思呀?傅献勋说,顶多三次……来你这儿买鸡……农场主说,你们中国人不是喜欢讲吉利话的吗?你今天怎么不遵守你们的传统习惯了呢?傅献勋说我感觉到了,我今天来你这儿……一路上都在想这件事儿。
农场主黯然。
其实农场主这人除了多嘴多舌一点,其他方面都还不错的。十六年前,十七位中国老人设了一个“活鸡宴”的饭局。那些用餐的鸡从一开始便是从他农场买的。轮到做东的老人们,每每起了大早,乘坐早班巴士从巴黎城里来到他农场。农场主熟悉他们中每一位的脾性、嗜好,他还将他们轮流的次序给排列出来,并根据他们每人的喜好,或招待红酒,或招待甜点及水果。三年后,他的次序表开始变动。本来轮到的那位没来,来者是下礼拜做东的人。
现在,农场主根本无须再排列他们之间的次序了。剩下的五位,谁先谁后,一目了然,傻瓜都分得清楚的。
傅献勋提上鸡笼走向巴士站。去李岳树家。当年留忠青死后,“活鸡宴”的地点转换到了陈生根家;陈生根死后转换到了张炳康家;张炳康死后转换到了如今的李岳树家。
连云发
牙齿痛了一夜。俗话说牙痛不算病,痛起来要你的命。这个夜晚、或者说这个阶段以来,连云发算是深刻领教了这句话。一个晚上的折腾,致使早上起床的连云发精神萎靡,情绪低落。
连云发想,像这种烂牙,像这样子脸肿如馒头,还如何吃得动鸡呢?
连云发同时又明白,所谓的“活鸡宴”,那“吃”是无所谓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能够走动一下;能有几个人说说话。况且说的还是家乡那土得掉渣的方言话。在这法兰西,在这番邦的地界,再没有什么语言能比得过老家的土话了。老家的土话,亲切,具有亲和力,而且还能让人浮想联翩呢。连云发每每听到老家的土话,他脑屏上便会映电影一样地一幕幕展开,老家的山,老家的江流,老家的舴艋船儿,老家的父亲、母亲,还有一位……连云发想到她时,免不了又得脸臊心跳。他和她,曾经在老家村口的香樟树下拥抱过、抚摸过。
连云发吞下几片止痛药,牙痛的症状稍许缓解。他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流通进来。这时他看见了楼下邮递员的身影,那邮递员骑上摩托车时也瞧见他了,他向他友好地笑笑,并指了指门楼边的邮箱。
至少已有二十多年了吧,连云发没有接收到过信件了。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煤气单、电费单之类的公函。那位他熟悉的邮递员今天冲他笑着指了指他的邮箱,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连云发忍着牙痛、拖着虚弱的身子走下楼梯。他的手很不听使唤,稍稍抬高一点就抖动得厉害——他总算将邮箱给打开了,里头果真躺着一封国际航空信。
信是从中国大陆寄来的,来自他的老家。写信的是一位叫连成彬的人。连成彬在信中说,他早就听父辈人说了,他的伯父连云都和他的关系,除了那层堂兄的亲戚关系外,更是一对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他这次是通过多方打听才获得他的地址的。连成彬在信中接着说道,现在大陆搞改革开放了,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海外跑,要去赚外汇啦。他们家很无奈,因为他们的伯父连云都在去国外的途中就死了,所以那根华侨的脉络也就断线了……连成彬扯到正题:他希望堂伯父看在他伯父连云都的面子上,能给他办理出国手续、并负责一定的经济负担。连成彬最后说,我是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如果您愿意,我就做您的儿子好了!读完信,连云发苦笑。巴黎实在是太具诱惑力了。然而,生活在巴黎的他们,又是怎样一种情景啊。
连成彬的来信,勾起了连云发对往事的回忆。连云发的老家——或者说在整个欧洲大陆占大多数的老华侨的老家——是在浙江南部的一个山区小县城青田。青田县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人多地少,且无其他出产。由于穷则思变的缘故吧,这个地方的人从很早以前就把去番邦、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去海外作为一条谋生的出路。
诚然,那个年代跑到番邦去的均为年富力强的男丁。
连云发是和他的堂兄连云都一道结伴去番邦的。时年连云发十八岁;连云都十九岁。连成彬信中所说的没错,他与堂兄连云都的关系情同手足。当年,他们两家为了凑足他们去番邦的盘缠,都卖掉了家里仅有的几亩薄田。他们两家的父辈们,把改变家庭命运的所有希望,一古脑押在各自的儿子身上了。
在上海时,连云都身体即有不适症状,上吐下泻。临到签证手续办下来时,连云都的身体仍然未见好转。连云发说,堂哥,你现在体格这么虚弱……乘船能吃得消吗?连云都笑笑说,我们穷人命贱,没什么关系的。连云发说,那轮船可得在海上漂一两个月呢,万一你的病好不了,又没药吃……那如何是好哇。连云都说,别说了堂弟,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出来,不赚到番邦钱是回不去的。
他们上了那艘从上海驶往巴黎的轮船。他们买的是最差等级的船票,睡在最底层的船舱里。空气浑浊,吃得又差,这样的条件哪怕是个身体健康的人也免不了要生病的。连云都的病情越来越重,几近于奄奄一息。轮船上有位翻译,连云发跑去找他,让他找医生来给连云都看病。那番人医生捂着鼻子下底层船舱,只远远看了一眼连云都就赶紧走了。连云发从翻译手上拿来了几片药丸,如同得到了仙丹般地让连云都立马吞服下去。可毫无效果,躺在床上的连云都除了吐和泻,好像其他的功能全都丧失掉了。
连云都还没完全断气,就被几位凶悍的番人水手拿担架给抬走了。连云发呼天抢地扑过去,可他哪有什么力气啊……连云发被一位人高马大的番人水手一掌打晕过去。待他醒过来时,他的堂兄连云都早已被抛进大海喂鱼了。翻译对连云发说,他得的是传染病,如果他不喂鱼,那么我们大家都得喂鱼。连云发双目空洞地望着洋面,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心如一块石头。
……
这样子磨磨蹭蹭,一个下午眼看就剩下一截尾巴了。连云发沉溺于往事的泥沼里,他忘记了做饭——他只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喝过一杯牛奶。连云发心想,干脆就上李岳树家吃好了,不管吃得动吃不动的,喝点鸡汤也行啊。
李岳树
礼拜二,这于李岳树的生活来说,是个须认真打理的日子。李岳树早早起了床,他将房间和客厅都收拾、打扫了一番。李岳树本来就是个爱清洁的人,他的家比起其他老人的家来,最为干净。但李岳树还是每逢礼拜二,必早早起床将本就干净的房子再清理一遍的。李岳树对那些老人解释说,大伙儿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礼拜二这一天,我总要想尽法子给大伙创造一个良好环境的吧。
李岳树从橱柜里搬出那套平日里没机会用的茶具,泡进水槽,逐个清洗、擦拭;茶叶是有的,但在巴黎是不可能喝到新茶的。这些从中国货行买来的茶叶,隔年的就算新茶了。但有茶叶与没有茶叶,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儿。试想想,几片茶叶漂浮在茶杯里,映着绿意,散着清香,再说说老家土话,叙叙旧人旧物,那份惬意也就可想而知啦!
在他们这个老人群体——包括最初时的所有老人中,套用今日的一句流行语——李岳树属于“另类”。李岳树年纪最小,而且并非是相差无几的“小”,是小十多岁。李岳树还有三点与众不同之处:其一,他是老人们中惟一一位乘坐过飞机的人;其二,他当过兵;其三,他最晚来到巴黎。
李岳树当的是国民党的兵,拿今天的话来说,属国民党老兵行列。1949年前夕,李岳树跟随国民党的大部队撤退到了台湾岛。小小的台湾岛一下了蜂拥而至如此之多的男壮丁,其男女间的比例严重失衡。在当年,台湾宝岛上的外省人——当今讲的老兵们,个个为讨老婆的事儿愁眉苦脸,一筹莫展,很多人打了一辈子光棍。李岳树仗着自己面目清秀、又多少会点识文断字的本钱,几经出入,总算捞到了一位本地姑娘为妻。只是好景不长,他的一位光棍上司打起了他老婆的主意。这事儿拖延了一两年,李岳树备受折磨与痛苦的煎熬,最终他的老婆背叛了他投入上司的怀中。
李岳树办妥前往法国的探亲手续,预订了机票。离上机前数小时,李岳树潜入上司和他老婆居住的房间,将他们俩双双给杀了。
李岳树现今每每想起那一幕时,恍然如梦。他不敢相信……自己犯下了如此深重的罪孽。他是深爱着他的妻子的,至今依然如故。李岳树从台湾逃出来到巴黎,他身上所携带的最重要的一件东西,便就是那女人的一张照片。那位他曾经的妻子,风情万种,靠在一棵椰子树上,其背后似乎拂动着热带的海风。李岳树将这张照片摆在床边的床头柜上,睡前看上几眼;醒来后的第一眼,不用说也是面对着她了。
李岳树一生生活在赎罪的痛苦之中,晚年愈益加重。不过李岳树是个心理素质良好的人,他心中的苦闷,一般是不会外露于表面的。在其他老人们看来,李岳树是个乐观的人,一个善于替别人着想的人。
李岳树将几盆盆景搬到阳台上。太阳已经升老高了,冬天的阳光实在是贵如金子啊,李岳树感觉到浑身上下暖洋洋的……这时,他瞧见傅献勋从前面的街道上蹒跚过来,提着那只经过装饰的鸡笼,样子显得有几分滑稽。
李岳树进厨房烧开水去。
孙祖芳
孙祖芳还和前数日一样,一起床便跑出去大肆采购。他采购的东西主要是粮食,如进一步细化来说,则是大米和面粉。那阵子刚好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电视新闻、报纸新闻,以及街头巷尾,到处沸沸扬扬。孙祖芳的消息来源,主要是通过火车站候车室那块大屏幕电视上看来的——他家没有电视机,而火车站离他家则近在咫尺。他由此知道了有一个叫伊拉克的小国家正被美国人打,还有许多强国帮着美国人打呢。这个小国家的领导人萨达姆是个狂人,越打越不服输,还在那儿叫嚷要以牙还牙、以血偿血。这一来事儿就闹大了,针尖对麦芒了。于是街头巷尾就有人预言道,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开战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根本不晓得“世界大战”意味着什么,或者至少来说认识不足的吧。像他这种人,曾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就晓得世界大战可不是好玩的,那是要饿肚皮的,会把人逼到绝境的。
世界马上就要爆发第三次大战了,作为一个小民百姓,他的当务之急便是要深挖洞、广积粮了。中国人作为在饥饿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民族,太知道粮食的重要性了。民以食为天——已不仅仅是一条说理的古训了,而是已沉淀到这个民族血液里的东西了。
李岳树家里是有电话机的,孙祖芳那天在电话亭里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他的意思是让他也赶紧采购粮食,做好充分的准备。没料到的是李岳树拿他的话根本没当回事儿,非但没当回事儿,还差不多以讥讽的口气说道,祖芳你是不是又想重温旧梦了呀……可是,你现在这岁数,恐怕就是仙女下凡躺在你怀里都动弹不了了吧。孙祖芳直想冲着电话筒骂上两句,但他没有。李岳树平时的为人,是有口碑在的,他不能因为他的一两句话语,就把脸皮给撕破了呀。
本来,孙祖芳是还要和其他那几位说说的,劝说他们赶紧采购粮食以防不测。但他在李岳树这儿碰了壁——再说啦,他们几位家里均没安装电话,他一家家地跑也嫌累。孙祖芳想,反正自己是无论如何都要多采购了。只要家里有粮,哪怕外头的世界打得天昏地暗吧,他都可以高枕无忧的啊。
李岳树那天在电话中所说的话,是有特定意思的,是有所指的。这是一个老华侨们的共同“典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兵荒马乱,巴黎的市民们如无头苍蝇,不知干点什么好。在这个关节眼上,中国人就显得训练有素。他们这些老华侨——当年的青壮年华侨们,什么都不干,专干采购粮食一桩事儿。他们每天如蚂蚁搬家般地往自己的窝里搬运粮食,将所有的法郎都换成了一袋袋大米和一袋袋面粉。而番人们,就没有这个算盘了,他们依然有条不紊地吃多少买多少,全然没有今后要闹饥荒的远见。也许,那是由于他们的祖宗挨饿的日子没有我们祖宗多的缘故吧。
战争的序幕拉开——一打就是持久战。饥荒像秋天里的枯叶一样纷纷飞舞,落在了每个人的头上。街上开始出现大量的饥民,他们成堆成片地靠在城市建筑物的边角,睁着一双双死鱼般空洞的眼睛。
第一位尝到甜头的是陈生根。陈生根是位好事者,有事没事喜欢上街乱逛。他那天走着走着,就在一堆饥民面前徘徊不前了。不雅观地来说,他像一摊鼻涕一样地粘那儿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那十数位被饥饿折磨着的大多为年轻的姑娘们。陈生根因家中有粮,肚子里有“货”,勇气陡生。陈生根试探着问道,如果……我能让你们吃饭……你们中……谁愿意做我老婆?陈生根这句吞吞吐吐的话,没料到效应却出奇的大。那些姑娘们先是不敢相信;或者说是她们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吧,反正一时间她们全懵懂了。然而很快地,她们就反应过来了,她们的眼睛中流露出企盼的光斑,并纷纷将手举起来。
陈生根喜出望外。
陈生根以粮食换取法国姑娘做老婆的事儿,很快就在华人圈中一传十、十传百地铺开来了。手头掌握着粮食的华侨们,个个喜形于色,眉飞色舞,他们纷纷涌上街头,面对一大群一大群饥肠辘辘的法国姑娘们,由着性子地挑肥拣瘦,百里挑一。
孙祖芳挑选来的老婆同样很好看,个子比他还略高一点呢。孙祖芳觉着她最大的好处是比中国人丰满,肤色白嫩。他们平安无事地过了三年半可称之为幸福的夫妻生活,她替他生下了两个混血儿子女。
战争结束后,这种不对等的夫妻关系随之瓦解。而且,无一例外。
那段日子所留给孙祖芳的纪念品是两双小孩的鞋子,一双是他女儿的;一双是他儿子的。孙祖芳将那两双小鞋锁进箱子里,寂寞难耐的时辰里,他就取出那两双小鞋子放在掌心把玩,怎么玩都不腻的。
今天采购完后,孙祖芳心血来潮又打开了那只箱子,捧宝贝似的捧出那两双童鞋。想起这对儿女,他们在尚不懂事的年纪里就跟随他们的母亲走了,从此杳无音讯。
他们是两只小鸟啊……孙祖芳泪眼模糊地嘀咕道。
孙祖芳沉沉入睡,睁开眼时天已擦黑。孙祖芳猛一个激灵坐起来,心想今天又要迟到了,又得挨那几个老家伙的骂了。
王正仁
“双十节”那天,王正仁他们这些仍持“中华民国”护照的老华侨们,受台湾驻巴黎的有关机构邀请,前往某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王正仁本来是不想去的,他的一条腿在头一年里被汽车撞伤,至今还得拄拐杖,行动起来颇为麻烦。但最终他还是去了。一年中也就这么一回热闹,错过了可惜啊。
在礼堂外头熙熙攘攘的大厅里,王正仁没费多大工夫便就找到那几位老家伙了。他们这批人,如从头算来,在巴黎这个地方已相处五十多个年头了。拿俗话来说,那是烧成灰都认得了。王正仁拄着拐杖,却能悄然无声地来到傅献勋身后站定。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将一张小纸条塞在了傅献勋的衣领里,让他走动时身后飘着一点白。其他几位老人心照不宣,气定神闲地谈论着来演出的都是哪几位艺人,说看节目单上有几个名字眼生得很呢。
他们的票是连一块儿的,他们五人肩挨肩一排坐着,倒也显出了某种统一性来。此时他们的脸面是舒展的,眼睛东张西望忙不过来。
演出的高潮部分是摸奖。有位长官模样的男人从那个摸奖箱里摸出一张小纸片,他将其递给一旁的礼仪小姐,让她念。礼仪小姐那张樱桃小嘴读出了一串阿拉伯数字。李岳树提醒道,大伙看看手上的票,会不会轮到我们这些老家伙中彩呢。王正仁说我中啦!王正仁由于过分激动,靠在他身旁的那副拐杖哐啷一声倒在地上,引得许多人扭转过脖子来瞧他们。但老人们浑然不觉,争相嚷道,我们中啦!我们中啦!那位长官模样的人从礼仪小姐手中取过话筒说道,中奖的先生请听好,等晚会演出结束后,请您到后台与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今天的奖品是——长官先生卖关子,他故意停顿下来,笑眯眯地眼睛朝台下扫来扫去。整个礼堂里鸦雀无声。长官先生的声音如一声春雷——是一台24寸的彩电!
今天,两位小老乡要过来帮他把那电视机给安装上。那台电视机,至今还寄放在靠街面的老乡餐馆里。故此,两位小老乡首先得跑到那家餐馆把电视机给搬运回来。当两位小老乡抬着电视机上楼时,王正仁早已敞开房门、拄着拐杖站楼梯口等候他们了。王正仁颤巍巍地说道,你们两位……是我居住这里三十年来的……第一回客人啊……两位小老乡听了这话,差点没失手把电视机给掉地上。是啊,这太不可思议了!一个人的家,居然有三十多年没人来往?而且,讲白了是从未有人来过他的家!
王正仁的房间里,满鼻子闻到的都是药水味儿,比诊所里的味儿还要浓烈多多。两位小老乡很不习惯,连呼吸都觉着困难。王正仁一脸歉意地说道,我是久病成医了……那针都自个儿给自个儿扎的,从消毒到大小注射器,一应俱全……不好意思让你们闻气味了……小老乡自然说没事的。
电视安装、调试妥后,小老乡又耐心地告知王正仁如何使用遥控器。王正仁按着遥控器的按键,像个孩童似的乐呵呵。王正仁突然想起什么来,他说你们俩千万不要马上走,今天无论如何都得给我个面子。王正仁拄着拐杖,从贮藏室里找出一瓶布满灰尘的瓶装酒。因那瓶酒已整个儿灰不溜秋的,两位小老乡一时无法辨识出那是一瓶什么酒。王正仁说,我因身体不好已戒酒二十多年……这酒就一直没喝掉,今天你们来最好了……麻烦你们拿水槽洗洗,厨房里有起子。盛情难却,两位小老乡在水槽里洗了半天,才让那瓶酒露出庐山真面目,是瓶老牌子的法国白兰地。他们好不容易将已腐烂的瓶塞打开,对着两只不对称的玻璃酒杯倒入一点点呈棕黑色的酒。王正仁拄着拐杖站于一旁,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两位小老乡如喝中草药一般地喝下那杯里的酒,因那酒显然已变味、变质了。
一个下午,王正仁皆春风满面,沉浸在幸福的光照之中。房间里突然有了人的声音;有了跑来跑去的人影子,这实在是件让人兴奋不已的事儿啊!王正仁拄着拐杖在房间里不停地走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那屏幕上的画面,他觉得各有千秋,都很新奇、很精彩。王正仁在心里忖度,今天就晚些过去了,要是那帮老家伙责怪起来,那我就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谁叫我摸奖得了个大彩电呢,谁叫我偏偏今天又安装上电视了呢,我多看会儿电视总不算罪过吧?
咖啡吧
孙祖芳跨进门时,还未喘顺了气,就受到连云发的攻击了。连云发说,我这样子一个病人,一个晚上牙痛没睡觉,来得都比你早,多多少少也帮上了点忙,你倒好,健壮得像头牛的人,倒学会吃现成的了。孙祖芳说我靠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发觉天都黑了,凭天理良心讲,我不是有意的。李岳树接话道,你是累坏了吧,那样子每天背大米,就是铁铸的人也吃不消的呀。孙祖芳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他觉得李岳树他没道理老是挖苦他的。傅献勋和连云发俩听李岳树如是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急匆匆问道,背大米?祖芳他背大米干吗?难道家里办食堂啦?李岳树说,这说明你们俩的脑子都没用了嘛,吃过馍馍忘了香味了嘛。傅献勋和连云发面面相觑,还是搞不明白。连云发转过脑袋问孙祖芳,你说嘛,怎么背起大米来了?孙祖芳气呼呼地说,到时候你们饿肚皮时别来求我!
犹如一盏灯,照亮了傅献勋和连云发记忆的深处。他们俩豁然开朗,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傅献勋嬉皮笑脸地说道,原来是这样呵,祖芳兄这回是要做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的行为喽?连云发一本正经地说道,祖芳兄哪,我们这帮老不死,说什么都是同患难的难兄难弟了吧,你怎么可以吃独食呢?孙祖芳脸憋得如一片猪肝,他没好气地嚷道,我花的是自己的法郎和力气,轮不到你们风言风语!李岳树适可而止地将话题给带住,他说祖芳兄他早就把话给我了,本来还想分头动员你们的,是我给他泼了冷水他才没跑到你们家去的。因为我经过分析了,这一回的仗,只是局部范围打打的,根本形成不了世界大战的,这对打的双方力量相差太悬殊了,伊拉克肯定会被美国人吃掉的。
如果俄国人看不下去呢?看问题要有发展的眼光嘛!孙祖芳仍然不服气。
李岳树说,俄国人他再看不下去也不会动手,也不会出兵,这是个大局。好了好了,我们这些老家伙顶多没几年饭吃了,就别操这份闲心了……咦,正仁怎么到这个时辰还没来呢?他这个家伙平时都是早早就到的呀。
一小时过后,王正仁平日坐的那个位置仍然空着。桌子上,那盘红烧鸡的热气渐渐稀薄,每人面前的碗筷码得整整齐齐,未动。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要还有一人未到,谁都不能先动筷。李岳树发话了,他说大伙不能再坐着干等了,要不我和祖芳去趟他家……他该不会是摔倒爬不起来了吧,他如人在家里最好,如不在家……那就得赶紧报警了。
王正仁家的住址,李岳树的小本本上有记的。李岳树将小本本上所写的地址递给的士司机看,让他找去。
他们爬上楼梯,廊道里回响着电视机发出的声音,震天价响。李岳树和孙祖芳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王正仁耳朵失聪已多年,他能听到一点声响的时候,在他人听来无疑如五雷轰顶了。李岳树说,看来这家伙叫人把电视机给抬回来了,看入迷了。孙祖芳说,看电视能当饭吃?肚子饿都不晓得了?!
他们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先是小声敲,后来越敲声响越大;李岳树和孙祖芳轮流喊,正仁!正仁!……嗓子都喊哑了。旁近的邻居受惊动,跑来一位老头。他说别再喊了,你们这样子喊椅子都听见了,没用。李岳树说,那叫我们怎么办呢?老头说撞门呀,这门不结实的。
破门而入后,他们看见王正仁一动未动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正面朝了电视屏幕。孙祖芳粗心,他以为王正仁这家伙当真还在看电视呢,正要大骂他几句,但他那张开的嘴巴立马就僵硬在那儿了——种种迹象表明,王正仁他已死了。
王正仁患有心脏病,以及名目繁多的病。过分的兴奋和刺激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王正仁的尸体被运走后,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他们四人一道打的去了那家咖啡吧。那是一家脸面极窄的咖啡吧,坐落的地段相当偏僻。
他们鱼贯而入,面无表情。咖啡吧老板娘是位白发苍苍的法国老太婆,由于长年累月的坚持劳动吧,瞧她的腰板还是挺结实的,手脚也不算迟钝。老板娘抬头时看见了他们四人,她的眉宇之间似乎细微地牵动了一下。她默不作声地打了四杯对威士忌的咖啡。这种喝法,他们已经喝了五十多年。当年他们均为活蹦乱跳的小伙子;而她也是一位情窦初开的迷人小姑娘。老板娘多年来遵守着一条原则,她不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谈情说爱,但她的“情”她的“爱”,却又无微不至地沐浴着他们每个人的心房。从这一点上来理解,说她是他们的“大众情人”并不为过。
老板娘端着威士忌走过来坐在他们身旁,点上一根烟。她徐徐吐出一口烟,说,人都是要见上帝的。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