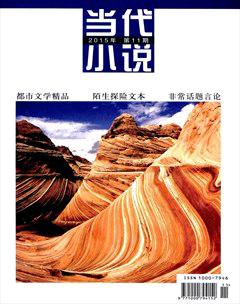撕裂
周齐林
1
深夜,老张开着车在人迹稀少的马路上疾驰起来,他大声嘶喊着,像是发了疯一般。后面一辆车跟上来,骂了一句神经病,紧接着油门加速,疾驰而去。这一骂,老张心中的火气一下子冲了上来,他一脚油门踩到底,车轮飞转,车子一下子往前飞去,很快就追上了刚才那辆车。
现在,他们几乎并驾齐驱。老张飞速看了右边车窗一眼,放慢车速,故意冲着对面车窗又大喊大叫起来,像是示威一般。夜风透过车窗灌进车里,发出呼呼的响声。老张继续嘶喊着,喊几声便摇头看对方一眼,面红耳赤,横眉怒目的样子。就怕不要命的。老张的样子吓坏了对方,对方很快就作出了让步,在下一个狭窄的路口,对方主动让行。老张见状,他心底的那股怒气顿时消减了许多。他又嘶喊了一声,而后一脚油门,蹿上前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张把车开到了一个烂尾楼前,这里空旷无人,他走进去,站在烂尾楼中央,鼓足气,提起嗓子,冲着苍茫的夜歇斯底里的嘶喊起来,啊——啊!老张使劲喊着,尾声拖得很长,喊声在回音的衬托下,显得粗犷无比。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喊得全身乏力,嗓子沙哑,老张才停了下来。最后朝天狠狠地骂了句操她姥姥,狠狠地踢了一脚烂墙面,老张才返身回到车里。夜风拂面,老张顿觉神清气爽了许多。
老张不老,今年才四十刚出头,不过就是因前额头发稀少,面相比较显老,单位里的人就都叫他老张。起初叫老张的人只有单位的党组书记,也就是一把手李馆长。后来大家就都跟着李馆长叫了起来,左一个老张,右一个老张,前一个老张,后一个老张,叫的人多了,老张也就默认了。无论谁叫老张,老张都笑着,像一个不倒翁一般。
在公司在单位,谁在老张面前都是一个爷。这是实话,单位的保安队长小刘,前台小红,细究下来,可都是有背景的,你千万可别被表面现象给遮了眼。老张在市文化馆上班,负责给馆长写材料,弄各种各样的方案,还有其它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他都得干。这十多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聪慧,老张写的材料在市直单位圈里,可是出了名的。就这样,在这十多年的煎熬之下,近几年,老张终于受到领导的青睐,入了编,有了亲戚朋友眼里羡慕的一个铁饭碗。老张始终记得,自己入编的那一年那一天那一晚,妻子好好犒劳他一番,表现得很温柔,各种姿势都任他来。一连几日,老张都面色红润,心底美滋滋的。
一步一个脚印从下面爬上来,老张很珍惜。虽然一不小心成了领导眼里器重的角色,但老张始终提醒自己得夹着尾巴做人,处处低调为人,不可张扬。老张深知,单位虽小,水可深。领导表扬他,他红着脸,羞涩地一笑,像一个羞涩的姑娘;领导骂他,他都点头听着,不吭声不顶撞不反抗。无论领导骂得多厉害,老张始终赔笑着。
再怎么低调谨慎,也总有马失前蹄之时,更何况老张头顶除了伺候一把手李馆长之外,还有一个副馆长要伺候,他得夹着尾巴小心翼翼鞍前马后地给她端茶倒水。这个副馆长是个女的,姓王,近五十,正处于更年期的年龄。更年期妇女所具有的心烦气躁等典型症状,老张看在眼里,苦在心里。这些更年期所带来的苦果几乎都辐射到了他身上,让他苦不堪言。老张现在极其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就像一只形影相吊的猴子,深陷在如来佛祖的手掌心,任怎么腾云驾雾翻筋斗云也逃脱不了。
王馆长这几日似乎对他很有意见,她手掌一握,他便顿感头顶乌云密布。老张把车开进小区的地下室,停好车,刚上电梯,一条短信就跃入他的眼中:别跟我玩阴的,我踩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是王馆长的短信。王馆长的意思是老张就像一只蚂蚁,蚂蚁搞大象,岂不是不自量力?这条短信仿佛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水中一般,顿时起了阵阵波澜。老张久久地看着,咬着牙心底狠狠地骂了一句臭婆娘,使劲摁了下删除。
这段时间,老张心情抑郁,几乎处于崩溃的状态。虽然上个月刚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但老张现在却丝毫也不兴奋。晚上躺在床上,老张思来想去,辗转难眠,觉得王馆长之所以这段时间一直针对自己,主要还是因为自己跟李馆长走得太近了。李馆长几乎把他当成了心腹,而且也是从底层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上来的,如此一来便有了惺惺相惜之感,自然很器重他。老张孤身在外打拼多年,身边能有这样一个领导器重自己,自然十分珍惜十分感恩。老张和李馆长一走近,王馆长自然看在眼里。更重要的是王馆长一直想扶正,但眼见没几年就要退休了,挣扎不过,也想跟李馆长搞好关系,好为日后退休谋个更好的砝码。眼见自己手下跟李馆长这么热乎,王馆长自然十分看不惯。
老张经常在内心深处哀叹,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条狗一样活着,甚至还不如一条狗。老张觉得自己就是王馆长手下的一条狗,这么多年一直被一条无形中的绳索拴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任何行动,无论大小,都得听从主人的指挥,稍微擅自行动,就得被臭骂一顿。现在,掌握在手中多年的一条狗忽然挣脱锁链,跟了新的主人摇尾巴,老主人见了,自然会咬牙切齿,愤愤不平。这样想着,老张不由悲从中来,他直感觉眼前一片阴霾,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其实老张也不想升官发大财,只想踏踏实实工作,好好把生活过好。老张感觉自己就像一艘帆船,在海上漂着,稍有海浪翻滚,便颠簸不已,更要时刻担心翻船的危险。
事情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老张虽然跟李馆长走得近,但工作还得归王馆长管。李馆长一度想把老张调离出来,工作上直接对接他,但王馆长始终没答复,默不吭声,不置可否,跟他玩起了踢皮球。虽然是单位的一把手,但王馆长市里有人,如此一来,李馆长平时做事便有了一些顾忌。
在上周举行的新年度工作方案审核会议上,王馆长提交的一个方案,当场被李馆长否决,老张觉得在理,也跟着附和了几句。但老张一说完,就后悔了,王馆长拉长着的脸像一根苦瓜一样,一直悬挂在头顶,恍惚之间,苦瓜就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刀,随时会砸在他头上。祸从口出,老张还是后悔了。贪图一时的口舌之快,现在却落得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下场。但老张心底还是咒骂着,这个老女人简直是一窍不通,这个项目其实去年已经弄过一回,但收效甚微,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今年再提交这样的方案,岂非浪费国家财政?但老张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自己太幼稚了,这个女人之所以重提这个方案,其中的猫腻他稍微动动脚趾头就知道。
2
老张开门,见客厅里的灯还亮着,时间已是晚上11点。妻子见他进门,赶紧迎了上来,给他取公文包递上布拖鞋。老张他妻子有个好听的名字,陆小雪,人也长得漂亮,比老张小七八岁。老张坐在沙发上喘息的片刻,小雪把锅里热着的饭菜端上了桌。老张任小雪忙碌着,他不吭声。过来吃饭吧,今晚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排骨玉米汤,血鸭,红烧猪蹄,都是老张爱吃的菜,而且是家乡味。见老张坐在沙发上不动,小雪走过来紧挨着他坐下,手挽着他,小鸟依人般靠在他肩膀上。老张适才悲凉的内心开始回暖了一些,他看了妻一眼,妻子见状,又撒娇似的说,去吃一点嘛,尝一下,我和老妈忙活了一个下午呢。老张被妻子拉着起身坐到了餐桌前,吃了几口,布满阴云的脸上终于露出几丝笑容。
已经五六天,老张没回家吃饭睡觉了,下了班他在单位附近吃个快餐,独自在寂静的河边走走,然后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直至看书看累了,倒头就睡,办公室有一个小隔间,里面放着一张简易床,供他休息。这一般都是主任才有的待遇。眼睛一直盯着书本看,但却看不进去,到最后老张通常都是一边用电脑放着格调低沉忧伤的音乐,一边把整个身子凹陷进沙发里,面无表情地发着呆。老张内心抑郁,他感觉自己像无路可逃的人,被两拨敌人逼到了一个无人的死胡同里,胡同边是一堵高墙,要想突出重围,必须翻上高墙,一跃而下。有几次,老张心底起了一跃而跳的决心。
在家里,老张感觉自己像一个外人,110多平的房子,却住着岳父岳母小舅子以及老张他自己一家人。虽不拥挤,却也宽敞不到哪里去。这些年,老张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在领导面前夹着尾巴做人,处处小心翼翼,谨慎得很。近几年,家里经济条件大有改善,老张却感觉越活越累,甚至有时心底起了跳楼杀人的歹意。有时老张恨不得把岳父岳母全部毒死,但这毕竟只是梦里的想法,早上一醒来,面对板着脸的岳父岳母,他甚至连赶他们出去的勇气都没有。
今天是老婆陆小雪三番五次要求之下,老张才回来。老张想起这些事情就气不打一处来,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全靠着他一个人支撑着,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道理整个家庭都应该理解心疼他。但事情却大大相反,岳父岳母住在这里多年,每天饭后把碗一丢就去打麻将遛狗,连碗筷有时都得他来洗。更让老张一肚子火气的是他们时不时还拉长着个苦瓜脸给老张看。老张在心里忍不住咒骂,你们在这里吃我的住我的喝我的,现在却还反客为主,使脸色给我看。这算哪门子道理?老张曾把这些苦水吐给关系好的铁哥们,几个哥们听了都纷纷为老张叫屈,他们纷纷为老张出谋划策。最后他们得出一个比较一致的建议:必须逮着机会灭灭他们的威风。其实总结到底就是一句话,男人必须硬起来,你硬他则软,就是这个道理。几个兄弟让老张哪天得着机会把饭桌掀个底朝天。老张频频点头称是,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他一咬牙,还是忍了下来。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几番劝勉下来,老张的几个兄弟们也算是心凉了,不再对他抱什么希望。
这段时间,老张一下班就看见岳父岳母和小舅子在电脑前搜索房产信息,饭也做得晚。老张看在眼里,苦在心里,忍着没发火。买房是好事,但关键是小舅子没钱。小舅子毕业五六年了,才存了不到四万块,买个一百平左右的房子,在这个二线城市,首付得将近三十万。剩余的缺口,他们都把求助的眼神投向了老张。岳父岳母和小舅子不敢开这个口,最后这个借钱的任务便落到了老张他老婆陆小雪的身上。第一次开口,老张看了妻子一眼,没吭声。第二次,老张看都没看妻子一眼。第三次,老张想发火,但还是忍住了。老张愤愤地说,你到底是跟谁过日子?你下半辈子要是想跟他们去过,你就尽管借给他。说完,老张甩门而出。银行卡和存折虽然都在陆小雪身上,但陆小雪是不敢轻易动这个钱的,毕竟这些钱都是老张辛辛苦苦挣来的。她陆小雪挣的几个钱都花在了自己身上,最近这几年在老张的默许下做了点小生意,不赚反亏了一把。反正就一句话,老张没点头,陆小雪丝毫也不敢轻举妄动。
小舅子不争气,有点好吃懒做,要是这样帮他就等于是在害他。更重要的是,老张一想到小舅子买房这个事情,他脑海里就浮现出爸妈一脸苍老的样子,他的心就隐隐地疼。老张他爸妈从老家出来已经五六年,却一直住在老张他大哥的出租屋里,平时大哥大嫂上班,爸妈就帮着给他们洗衣做饭。老人两个一把屎一把尿拉大他们兄弟姐妹五个不容易,老来应该享福。老张一直想把爸妈接到自己这边来住几天,他这里的小区环境不错,里面有个老年活动中心,饭前饭后,跟父母差不多年纪的老人都会在里面唱歌跳舞。虽然这样想了多年,但老张的这个想法一直未能如愿。岳父岳母一直在这边住着,他说也不是赶也不是,只能平时逢年过节,多给父母一点钱来弥补。但老张给的钱,父母亲舍不得用,他们省吃俭用留下来存着,或者拿出来买菜交房租,给大哥大嫂们贴补家用。有一次,老张给了父母亲一万块生活费,第二天,父母就瞒着他去邮局,把钱打给了正在乡下盖房子急着用钱的三姐。老张理解爸妈的心,他没怎么责骂他们,只能咬着牙铆着一股劲,更加卖力地工作。市里平常有什么采风和评奖活动,他都会忙里抽空去参加,得来的评委费和采风的酬劳,他就都给父母当做生活费用。
老张是这样想的,与其把钱借给好吃懒做的小舅子,我还不如在自己单位附近的小区给年老的父母买个小点的房子,简单装修一番,让他们老两口住,平时自己下班还可以去他们那里吃饭,有烦心事什么的,可以跟爸妈吐吐苦水。这样想着,老张坚持不借的心就硬了起来,他不能亏了自己的父母。小舅子想买房就得靠自己的真本事,年轻的时候不吃苦,那还等到何时吃苦?
吃完饭,洗漱一番,老张进书房看了一会儿书,顿觉倦意,便起身进房睡觉。四室两厅,他们夫妻俩住在最里面的一间,中间隔着书房,对面是女儿住的,这样一来便有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晚上他们夫妻俩人亲密一番,心里也不必顾虑太多。
老张进屋躺下没一会儿,妻子就穿着薄薄的睡衣,水气缭绕地进来了。陆小雪把屋里明晃晃的灯调成了暗暗的淡黄色,一抹光晕迅速在整个房间里弥漫开来。妻子穿着薄如蝉翼的睡衣在他眼前来回走动着,时而娇媚地看他一眼,显得意味深长。透过单薄的睡衣,老张看见妻子胸前高耸着的那对小白兔。老张顿觉整个身子炸裂了一般,顿时有了反应。你这是在挑逗我吗?老张笑着说。陆小雪见老张笑了,心底也跟着一笑,脸上便生出一丝少见的妩媚来。陆小雪这次明显是有备而来。老张一把把陆小雪抓在怀里,把她扑在床上,剥了个光溜溜。
一番折腾下来,老张已是气喘吁吁,他瘫软在床。妻子陆小雪温柔地从后背环紧抱着他,老张抽出一根烟,缓缓抽着,一圈圈的烟雾缠绕着,纠缠在一起,而后又缓缓散去。陆小雪紧抱着老张,轻咬着他的耳朵说,老公,那钱就借给我弟弟,好吗?老张抽烟的手在半空中,忽然又停了下来,他没吭声。妻子又撒娇似的推了推他的肩膀,说,他是我亲弟弟呢。老张咳嗽了声,说,借可以,但最多只能借五万。陆小雪一下子踢开被子,闷声闷气地说了句,没劲。原本弥漫着甜蜜幸福的气氛顿时又变得充满火药味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老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到凌晨两点多,起来在客厅抽了根烟,窗外是静谧的夜,他的内心却阵阵波澜,难以静下心来。一直晃荡到凌晨三点多,老张才入睡,却又早早地醒了。
3
早上近10点,老张去了一趟馆长办公室。李馆长递给他一个文件,说明天一早要参加市里的一个重要活动,要作一个报告,让他赶紧加班加点务必在下午下班前把这个报告赶出来。老张笑着点头称是。快出门时,馆长又把他叫住了。你眼圈怎么这么红?昨晚没睡好吗?馆长一脸关切地说。馆长这么一说,老张心头一热,赶紧说没事没事。
有这样的领导,虽然忙点累点,老张还是觉得值得,毕竟有奔头。放下手中的一切杂事,老张静下心来,忙着手中的这个报告。但刚理出个头绪,下笔不到一千字,内线电话又响了起来。老张歪头一看座机屏幕上显示的内线号码,眉头不由紧皱。你过来一下。王馆长在电话里说道,说完,啪的一声就挂了。听语气,好像一肚子火。正常情况下,她有什么事找老张,她都是客客气气的。即使是装出来的,老张听着也舒服。老张有些慌张地上楼,满是忐忑。他敲了敲门,那边应道,进来。老张看了眼前这个女人一眼,堆着一脸的笑容,叫了声,王馆长,你找我。老张还没坐稳,一本杂志啪的一声甩在他面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给我早点滚蛋。王馆长盯着老张,仿佛一副要置他于死地的神情。老张拿着工会主办的这本内刊杂志,翻看这期刚印刷出来的封三新闻,看见一个领导的名字赫然画上一个很大的红色圆圈,老张认识这个领导。领导的名字叫汪佳,杂志上却写成了汪假。老张盯着这个字,额头上顿时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来。佳写成假,你是要给人家打假吗?王馆长张着嘴大骂道,嘴张着,几乎要一口把老张给活吞了。对不起,馆长,对不起,下次再也不会这样了,我下去好好跟他们开下会。老张始终堆着笑脸,战战兢兢地赔着不是。下次?还有下次?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就直接卷铺盖走人。老张一边频频点头,一边识趣地退了出来。
重新回到2楼的办公室,一进门,老张就一肚子怨气地把门边的垃圾桶踢了个底朝天。回到电脑前,他索性把电话座机的线给拔了。但稍微平息片刻,老张又自动把电话线给接上了。名字写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话说回来,这本杂志说白了是本内刊,发行量很小。此外,汪佳就是一个小副科,连离正科都还差一截,更别提七品芝麻官了。老张感觉自己被活生生地羞辱了一番,自己四十多岁的人了,却被骂小孩一样狠狠地骂了一顿。关键是那边劈头盖脸地骂着,他却不吭一声,还面红耳赤不停地赔着笑脸,老张顿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他靠着墙,紧握着的拳头狠狠地砸在墙上,洁白的墙壁上顿时溢出一个血印。老张重新回到座位,一番自虐,他稍微平静了一些,心底却萌生出一丝绝望感。办公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是老婆陆小雪的。我去取钱给我弟弟了,老公,好吗?老张面无表情地扫了短信一眼,又重新把手机放回了桌上。陆小雪明显是征求的语气,几分钟后,见老张不回短信,陆小雪又打过电话来,老张没接,摁掉了。没几秒,那边又打了过来,老张又摁掉。最后,老张关掉手机,伏在桌上,默默地凝望着窗外的世界。
4
接下来的两周,王馆长要去北京出差学习,老张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倍感轻松,身上压着的那块巨石仿佛卸掉了一般。为此,老张还特意开了一瓶法国红酒,干了一杯。一整天,老张的办公室静悄悄地,座机电话很少响起。老张忙完手头的工作,便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窗外那一片绿油油的菜园子,几个当地的农民正提着水桶在地里浇水施肥。已经有许多年来没有下地了,老张想着读小学初中时,酷热的天气,毒辣的太阳高悬在天空,他们哥俩跟着父母在干裂的稻田里收割稻谷,汗水浸湿了整件衣服,有时他们熬不住了,便逃似的躲到村口那棵巨大的梧桐树下乘凉。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想着这些往事,老张感叹不已。他们哥俩已经长大,也跟着时间的步履走向苍老,而父母早已苍老下来。
这天即将下班时,老张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老张他母亲说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这周六回去。母亲说着要回去好多天了。老张深知母亲最终选择回老家的原因还是不能融入大哥他们一家的生活,前段时间侄子带着刚怀孕的女朋友来到这座城市,原本宽敞的房子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他们六个人挤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老张他大哥张华见儿媳妇怀孕在身,便主动把自己住的房间腾出来,让他们住了进去。他们两口子则在客厅里搭了一个简易木板床,晚上11点把床板铺好,第二天早早起来就去上班了。客厅比较小,放下一张简易床,就没地方了。老张他父母俩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心底总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住在这里碍手碍脚。老张他大哥张华心思缜密,一眼就看出了父母心中的疙瘩。晚上吃饭时,便劝他们安心在这里住着,不要想太多。张华说,爸妈,你们就安心住着,你们要是回老家,身体有个磕磕碰碰,我们怎么能照顾到你们?大儿子虽然这样说了,老两口看着他们夫妇俩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回来连个躺的地方都没有,心底还是过意不去。老张想出钱在大哥附近再租个房间,让他们老两口住下来。但老两口执意不肯,倔强得很,老张他老爸晚上还冲着老婆子发火了,说家里山清水秀的不好好呆着,偏偏要跑到这里来凑热闹。
放下电话,老张决定让父母在自己家里住几日再回去,第二天一早再送他们去火车站。当天晚上老张早早地回去了,一进屋,饭菜刚好端上桌。妻子看了老张一眼,说,回来啦,吃饭吧。岳父岳母,老张一家三口,还有小舅子和他女朋友,七个人上桌,各吃各的,陆小雪不时往女儿碗中夹菜,时而笑着说一些公司里发生的趣事,陆小雪想调节下气氛,但收效甚微,她说笑了几句,附和的人少,顿感无趣,便不再言语。众人都低着头。老张他岳父岳母眉头紧皱,脸紧绷着,似乎时刻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老张心里有事,他有话说。饭吃到大半,老张抬头看了众人一眼。海风啊,你明后两天去公司住一下,我爸妈他们要过来住两天。老张话还没说完,只听见对面碗筷啪的一声甩在桌上,他岳父的脸一下子黑了,小舅子听了老张的吩咐,头几乎埋到了碗里,闷声说了句好。好什么好,你就在这里住着。老张他岳母涨红着脸,母夜叉似的在老张面前张牙舞爪着。老张握着碗筷的左右手微微颤抖着,一股莫名的怒火顿时蹿到他嗓子眼。老张,你逮着机会就得把碗砸了,把饭桌掀个底朝天。不然你得永远受欺负。这几句话一下子从老张的脑海里冒了出来,他仿佛就看见自己歇斯底里地嘶喊着,一下子把饭桌掀了个底朝天,桌子上的碗筷在地上翻滚着,发出喀嚓的响声,菜汁流了一地。这些场景只在老张面前一闪而过,他憋红着脸,没吭声,忍了下来。饭后,老张就独自去散步了,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回来。走在晚风轻拂的江边,老张心底却阵阵撕痛着。一股强烈的受辱感慢慢在他心底蔓延开来,他顿时感到十分后悔,没把握住刚才那个复仇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早已不再。他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摔碗掀翻桌子的动作,两只手在暗夜里手舞足蹈着,整个人变得异常激动起来。在无数次这种臆想里,老张内心的不安和屈辱感仿佛得到了一丝解脱。
重新回到家里,整个房间静悄悄地,妻子陆小雪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看电视。见老张回来,陆小雪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他一眼。自从老张否决了借钱给小舅子买房的事情之后,陆小雪和老张的关系又重新回到了原点,他们彼此之间不冷不热的。老张闷声在客厅里坐着,陆小雪看了一会儿电视,啪的一声又把电视关了。老张算是明白了,陆小雪明明是站在他们那边的,在整个家里,他成了彻底的外人。
一直到12点,老张才拖着一身的疲惫倒在床上,妻子陆小雪已经睡熟,发出细微均匀的鼾声。看着妻子熟睡的样子,老张心里感到一丝悲凉绝望,陆小雪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老张躺在床上,却丝毫睡意也没有,他瞪着黑漆漆的天花板,心底却被那阵汹涌的屈辱感给淹没了,它们像蚂蚁般啃食着他。无数的思绪纷纷涌进老张的脑海里,他感觉自己的头都快要炸裂开来。时间已近两点,明天还要上班,老张头脑依旧十分清醒,他咬着牙逼着自己不要再想什么东西,那些思绪却愈加翻滚起来。凌晨三点,老张迷迷糊糊地睡去,再次醒来时,时间才是早上六点一刻。老张再也睡不着了,他起床穿衣服,站起身子,头却一阵眩晕,整个人直感觉天旋地转。老张扶着墙,缓缓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缓解片刻,整个人才稍微有所好转。
一整天,老张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办公室的电话线老张来了个干脆,一狠心,也拔了个断。门关着,电脑上循环播放着略显阴沉忧伤的音乐,老张面无表情地躺在沙发上,心情跌到了谷底,就像股市暴跌了一般。老张在沙发上躺着,快睡着时,手中的电话忽然尖锐地响了起来。老张懒得去搭理。但很快,打电话的人似乎固执得很,电话立刻又响了起来。老张歪着身子去取桌子上的手机,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拿过手机一看,整个身子忽地就变得笔直起来。老张弓着腰,几乎颤抖着双手拿着手机,说了声,喂,王馆长,你找我。
“你在哪里?座机怎么一直打不通?”电话那边,王馆长劈头盖脸地逼问着。
“馆长,我在办公室呢。”老张嗫嚅着,解释着说。
“在办公室?你骗谁呢!在办公室怎么座机一直打不通?你又去外面乱搞什么了?”王馆长几乎不给老张喘息的机会。
老张拿着手机,老老实实地听着,那边讲到30分钟,忽然啪的一声就挂了。王馆长给老张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老张放下电话,一阵恍惚,他突然猛地把手机甩了过去,嘴里大骂着,妈的,操你娘。手机摔出去,撞击在墙壁上,摔成了两半。王馆长虽然身在外面出差,但依旧要紧紧地把老张握在手掌心里。老张满心悲凉地走到墙脚,捡起摔成两半的手机。老张心情抑郁地倚靠在椅子上,好友成辉在QQ上给他发来一个消息,见他久久未回复,抖动了一下聊天窗口。老张俯身点开链接一看,一条本地基层公务员自杀的真实消息映入他的眼帘。成辉又发来一个消息,说,你可千万别自杀啊。说完,又发来几个搞笑的表情。
老张一口气看完本地公务员长达万言的遗书,面无表情地倚靠在沙发上。他微微闭上双眼,那个基层公务员自杀的场景就浮现在他脑海里,老张仿佛看见他精神恍惚步履蹒跚地爬到了17楼,而后纵身一跃,飞了起来。他正站在万丈悬崖边,脚下是云雾缭绕的云端。办公室外忽然砰的一声,不知是谁把一包垃圾扔了下来,发出一声巨响,一下子把老张从恍惚的思绪中拉了回来。
这一天,老张一直在办公室呆到晚上十点才回到家里。家里的气氛依旧压抑不已。老张独自一人在沙发上坐到了十二点,抽着闷烟,才进屋。其间,妻子陆小雪出来只看了他一眼,却没说话。
凌晨三点一刻,陆小雪被一阵霍霍的声音惊醒。她伸手一摸,床的另一边空荡荡的。她穿上衣服,走到门外,见清凉的月光之下,一个人,光着膀子,正手持一柄长刀,弓着腰,在阳台那块细长的磨刀石上,霍霍地磨着。陆小雪凑上前去细看,见是老张,神情却很陌生。陆小雪叫了一声老张,老张一脸寒气地看了她一眼,她顿时吓得退后几步。眼前这个人紧咬着牙,两只手持着刀柄,霍霍地磨着手中这把细长的钢刀,刀刃在光线的照射下寒光闪闪。而眼前这个人在月光的映射下,全身也裹着一股寒气。陆小雪再叫了一声老公,没应答。她再次叫时,门外磨刀之人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嘴角隐约露出一丝冷笑。
老公,是你吗?陆小雪看着眼前这把散发着寒气的刀柄,全身禁不住一阵冷颤。她迅速擂响了爸妈的房门,喊着,爸,爸,你快开门。陆小雪显得一脸惊慌,仿佛眼前这个男人不是她老公,而成了一个陌生的局外人。很快,岳父岳母披着睡衣,紧握着女儿陆小雪的手,他们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客厅中央。小舅子则从门后拿出一根铁棍,貌似很勇敢地护在前面。
小张,你千万别乱来,有什么事我们好好商量。老张他岳父语气明显软了下来。眼前的这个磨刀人只顾磨着刀,刀声霍霍,他仿佛完全沉溺于磨刀的世界里。不时地,他抬头张望一眼,嘴角溢出一丝冷笑。
老张他岳父使劲掐了老婆子一下,老张他岳母啊的一声尖叫起来。老人终于确信这不是一个梦。转瞬之间,他们便陷入无声的对峙之中。这是一场有声的对峙,刀声霍霍,抑扬顿挫,像是在拉着一曲幽深而又悲愤的调子。
正当众人手足无措时,霍霍的磨刀声忽然停了下来,老张,这里且称呼为磨刀人,磨刀人手持钢刀,大拇指缓缓地从闪着寒光的刀刃上一滑而过。老张赤裸着上身站了起来,他缓缓把刀放进刀盒里,刀在月光的映射下,散发着一股阴森森的寒气。
磨刀人提着刀,旁若无人地穿堂而过,进了房间。此刻已近凌晨四点。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老张,久久地呆站在客厅中央。
老张把刀紧握在手,躺下,缓缓进入了梦乡。而屋外,灯火辉煌。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