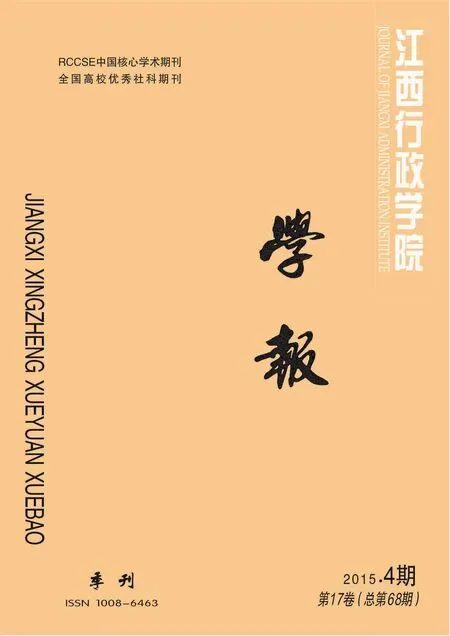村级财务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图景——以D村财务收支变化(1973-2003)为例
村级财务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图景——以D村财务收支变化(1973-2003)为例
尹利民,钟文嘉,万立超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31)
[摘要]本研究旨在通过D村30年村级财务收支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基层治理变迁的轨迹,进而把握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图景。个案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家政权建设以行政集权的方式渗透国家权力,村民过着集体生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国家政权建设开始呈现自主性与行政放权的特性,村民的经济生活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在收支关系上却出现了失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国家政权建设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公共权力借助于各种手段向社会提取资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现象开始出现,村民的经济生活在提高的同时也承受着重负。由此,国家政权建设变迁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了一个“加强-松动-再加强”的过程,这一过程透过村庄的收支关系变化微观地呈现出来。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基层治理;村级财务

一、研究背景
用国家政权建设(state-building)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学界惯有的研究进路,曾引起了一批著名学者的广泛兴趣[1]。从财政社会学的角度看,国家财政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演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财政体系是理解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关键[2]。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过程。国家财政对国家政权建设有着实质性的影响[3]。同理,由于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不同时期和阶段,其渗透的方式存有差异,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从而国家权力的渗透方式会对国家财政产生很大影响。由此,国家财政成了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纽带,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图景可以通过国家财政体系的变化得到体现,而在基层社会,则可以透过村庄微观的财务收支变化来展现。
那么,国家政权建设会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何种后果?中国乡村社会又是通过何种图景来呈现国家权力渗透的过程?基于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以D村为研究对象,试图透过D村从1973-2003年的村级财务收支变化的轨迹,来考察国家政权建设对中国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理解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图景。
当然,从村级财务收支的变化这一微观视角来窥视国家政权建设这一宏观制度变迁的企图带有很大的风险,但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并最终与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的过程,它的确在乡村社会留下了影子。因此,尽管这种努力可能并非全面,但却可以让我们从这种独特的视角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二、国家政权建设:已有的研究路径
我们知道,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著名社会运动研究专家查尔斯·蒂利,在研究西欧国家形成时所提炼出来的一个分析框架,其核心观点是: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通过政权的官僚化、合理化和结构化,并提高渗透性的努力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4]。这一理论解释因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被学者广为借鉴,并用以分析中国的国家构建过程。
从20世纪开始,中国就一直尝试着国家的政权建设,但效果却不尽人意。正如杜赞奇所言,在中国20世纪前半期,由于不能消除赢利型经纪体制的影响,国家政权试图进入乡村社会的企图遭到破灭,阻碍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扩张[5](P52)。传统国家内部的裂变性,致使其国家机器可以维持的行政权威非常有限,从而使得传统国家出现“有边陲而无国界”的格局[6](P63)。可见,从总体上看,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不成功的。进入20世纪后半期,新兴的国家政权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实现了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强渗透,国家认同观念的输入直达基层,并以集体化的方式扩大生产单位,从而降低了公共品供给中的协调和交易成本,其结果是:一方面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大规模完成;另一方面却破坏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权力文化网络”传统。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效果也不是很好,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历史课题[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推行,国家逐步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和治理[8],凭借“政党下乡”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将一个“一盘散沙”的农民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通过政党对农民进行组织与动员,把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9],推动了中国乡村政治或基层治理的变迁。
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把国家政权建设看作是因变量,视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为自变量。当然,这种把国家政权建设看作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前提的假设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比如,张静就认为,国家政权建设是否可以解释中国基层社会现象?在她看来,具有强大权力的现代国家其实是完成了向公共服务角色的转换,是与公民身份联结在一起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权建设并非只涉及权力扩张,而且还包括国家—公共组织角色的变化、与此相关的各种制度和治理方式的变化以及公共权威与公民关系的变化[10],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均衡[11]。也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之,重点研究财政供给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所带来的影响。该研究认为,由于国家财政供给的不足,影响了基层政权的监控效果[12]。当然,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不仅仅表现在中国乡村社会,其努力同样发生在城市,尤其是城市的社会管理体制变迁,比如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就是一种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13]。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学界对国家政权建设理解的一个共同点是:国家政权的官僚化、对下层的汲取、国家权力的扩张或整合、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笔者也认同这一理解。学界有关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讨论国家政权建设是如何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尽管也有文献从基层干部文化的视角来解读乡村国家政权的变化[14],从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来分析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变化[15],但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变迁图景如何展现?尤其在中国乡村社会是如何展现?
基于此,本研究力图通过D村30年村级财务的收支变化来透视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变迁图景,以一个个案的事实来呈现30年的变化。D村位于赣南一个小山村,被誉为“交通便利、通讯畅通、班子精干、民风纯朴、群众安居乐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明星村”。该村是单姓村,男性村民都姓邓。所辖有11个村民小组,7个自然村,截至2012年12月,有512户,人口2106人。耕地面积1434亩,其中水田1000亩,旱地434亩;山地面积3000亩,其中宜果山地230亩。该村经济主要来源是杂交稻制种和外出务工收入。2011年制种面积达700亩,年制种收入达100万元,是村产业支柱,2012年该村农民的人均收入2500元左右。笔者在D村田野调查,一次偶然的机会获得了该村从1973年至2003年完整的账本资料。
关键词本研究的视角以D村的收支项目作为,分三个阶段来叙述其变化,即1973-1978年、1978-1992年以及1992-2003年。中国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而1992年,我国又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显然,这两次政策调整是影响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变量,故以此为依据。
[中图分类号]F302.6
[收稿日期]2015-07-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作者简介]尹利民(1969-),男,江西永新人,政治学博士,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地方治理与信访问题研究;钟文嘉(1991-),女,江西峡江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万立超(1992-),男,江西南昌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三、集体性、行政集权与国家政权建设(1949-1978)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看作是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主要借助于国家对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等方式来推动。比如,在经济基础方面,国家通过土地改革,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最终建立起了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16](P52),从而实现了国家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展现出了集体性的特性。在意识形态方面,国家凭借有效的政治动员,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力,使官僚体制延伸到基层社会,进而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展现出了行政集权的特征。因此,这一阶段国家政权建设的特性可以概括为“集体性与行政集权”,故可称之为集体性与行政集权的国家政权建设。
那么,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建设图景是如何在微观村庄展现?我们以D村1973年至1978年村级收支结构来理解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图景。
从内容上看,公积金、公益金、往来款、生产性收入与支出等是这一时期D村财务的主要项目。从量上看,虽然D村的收支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总体上还是较低,反映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
村里的公积金是村级收入的重要来源,主要包括集体财产的一些收入、罚款收入、私人建房交款以及从事副业和手工业的村民的缴入等。比如,在D村1976年的公积金收入中,就有D村的杉树樟树款、出售烤烟房等收入。而生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农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工业与手工业收入、渔业收入、副业及其他收入,共计5293元,其中农业收入1590元,林业收入2289元。公益金收入则是按比例提取,一般从各生产队(村小组)中提取,主要用于该大队社员(村民)的福利支出。如,烈军属、五保户、困难群体等费用,合作医疗费以及电影费等方面的支出。这一时期上级财政投入非常少,在1977年之前,投入资金仅为1060元,1978年也只有3926元。可见,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国家对乡村的财政投入非常有限,乡村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尽管这一时期的村级财务收入水平比较低,但总体上还能保持收支的平衡。因此,这一时期的村级收支结构可以概括为集体性低水平的收支平衡结构。
集体性低水平的收支平衡结构首先具有集体性的特征,集体性意指村级事务以集体为单位,村民缺乏自主性,村民的经济生活甚至经济往来都是通过大队或生产队来实现的。比如,D村的往来款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往来款是指村里各生产单位资金的相互拆借,主要发生在各生产队之间,村民间的经济往来非常少(见表1)。由于村民缺乏自主性,经济生产仅限于大队、生产队之间。即使有村民可以外出从事一些手工业,如木工、泥工等,但都需要向村民所在的生产队缴纳一定的资金。比如,D村1973年、1975年村民的投资款实际上就是村民外出从事手工业向生产队缴纳的费用。这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民从事经济生产的机会,也限制了个体性的经济活动。

表1 D村1973-1978年财务收支结构 (单位:元)
资料来源:D村村级财务账本(2013)
经济活动的集体性与行政集权性互为因果。因为国家权力的延伸与对社会的控制是在自觉的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经济活动的集体性需要行政集权来强化,而行政的集权又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失去自主性。
当然,行政的集权特性在政治上强化了国家权力的渗透,是依靠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来完成。我们知道,“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既可以帮助基层政权控制乡村经济资源,又可以很方便地完成向基层社会提取经济资源的任务。因为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在政治上几乎垄断了所有的资源,凭借阶级身份和严格的户籍制度来限制农民的流动,将其纳入高度政治化的管理网络,并通过阶级话语的建构和政治运动式的治理来不断形塑乡村社会[15]。经济上,通过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来限制农民的自主性的经济活动,从生产分工到生产成果的分配均实行计划供给制,甚至农民间的经济往来都是以集体为单元。从D村的财务收支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有学者指出,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政权建设任务的完成是以降低农业经济效益和确立政治全能型控制的威权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它可能只是暂时的和非稳固的[18]。

表2 D村1979-1992年财务收支结构统计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D村村级财务账本(2013)
可见,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图景表现在: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组织,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经济活动方面,以集体为行动单位,村民缺乏自主性。在意识形态方面,国家凭借有效的政治动员,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力,使官僚体制延伸到基层社会,进而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展现出了行政集权的特征。
四、自主性、行政放权与国家政权建设(1978-1992)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始启动,并首先从农村开始。那么,这一制度变迁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如何?或者说,农村改革使得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表3 D村1976年与1992年公积金、公益金收支比较 (单位:元)
资料来源:D村村级财务账本(2013)
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两个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农民的生产领域与行政领域。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民在生产领域有了很大的自主性,生产单位也开始由生产队转为家庭,“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瓦解,从而使农村的合作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行政领域的变化主要是中央开始尝试性地进行行政放权的改革,扩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权力。这方面的改革措施主要有:1980年和1982年的收入分成制,1983年到1986年的利改税,1988年的财政承包制以及1993年的分税制。那么,这些变化是否可以从微观的村级收支结构中反映出来呢?
从D村的财务账本中,我们随机选取1979年、1983年、1988年和1992年四年的收支情况(见表2),发现与上一阶段相比,D村在收支结构上明显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表现在量上,大多数收支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表明中国乡村的经济水平在不断提高。其次,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收支项目。比如,从1983年开始,出现了田亩税,不过量还比较小。从1992年开始,出现了承包和内部往来款这一新的收支项目,并且出现了村级投资基金,比如,1992年D村的投资基金达到865270元,这表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与行政放权的改革开始影响到农村。与此同时,经济活动也开始由过去的生产队转变为家庭,村民的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经济单位也不单纯是村集体,个体也可以成为经济活动单元,这些都可以从D村的收支项目上反映出来。我们以公积金和公益金为例来进一步说明。
公积金和公益金是村级财务收支的重要内容,这一项目从1973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以1976年和1992年为例,来比较这两项内容的收支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公积金的收支前后没有太大的变化,收入主要依靠村集体,支出也主要用于村公共事业,但在收入的项目上有一些不同。比如,1976年,各种罚款收入、外出从事副业村民缴纳的公积金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收入;到了1992年,公积金收入主要依靠集体经济, D村的过桥费收入是村收入的主要来源。《江西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第5条规定,集体提留的使用项目只限于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其中公积金可占集体提留总额的40%,管理费不得超过集体提留总额的40%,其余用作公益金。公益金的收入主要是按照比例提留,是各生产队(村小组)上交款项。1976年与1992年在支出的项目上就有了很大的不同。1976年公益金的支出主要是民生支出,比如敬老院、五保户等生活费,但到了1992年除了这些之外,村干部的养老金保险支出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其次是招待费。这些项目的支出与公益金关系不大,但却成了支出的主要部分,农民的负担及政权的内卷化倾向开始出现。
其实,关于农民的负担问题,国家有明确的规定。比如,《江西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农民上交集体提留和乡镇统筹费的数额,以乡镇为单位计算,控制在上年当地人平均纯收入的5%以内,其中集体提留和乡镇统筹费各占一半。第4条规定,农民上交集体提留可以按家庭经济收入分摊,也可按承包土地面积或劳动力分摊。乡镇统筹费按不同产业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购建生产性固定资产、兴办集体企业等。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对特别困难户的补助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支出。管理费用于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村民小组负责人的合理报酬和补贴及其他管理开支,而这一切又与国家的行政放权改革有很大关系。换言之,国家的行政放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但却为地方政府吸取社会资源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以公益金支出为例,D村的公益金支出在1988年达到顶峰,而后则开始下降,1992年的支出水平竟然与1973年相当。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向社会吸取资源的能力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却出现减弱。政府的财政能力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控制能力,也取决于农村社会的承受能力及征缴成本。过度的资源吸取最终会导致乡村衰败。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方式不仅取决于政府社会控制的需求和能力,同样也取决于为此支付的管理成本[17]。经济领域的相对自主性,行政领域的放权,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进一步说,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围绕农业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利益分割关系。相比较而言,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的某种松动,意在为社会资源的成长提供可能空间,为将来更多的社会资源的提取创造条件。因此,无论是经济的相对自主性,还是行政领域的放权,都不会以降低国家对社会资源提取能力为代价。
可见,这一时期的村级收支结构表现出了自主性低水平的失衡收支结构。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仍然比较低,经济发展的层次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且开始出现收支失衡的财政结构。这一变化也揭示出了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图景: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政治的集权向分权过渡,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松动。国家的资源吸取能力在不断增强,但公共服务能力却在下降,开始出现政权的内卷化倾向。
五、政权内卷化与国家政权建设(1993-2003)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而在农村,税费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不断提取资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前一阶段村级收支结构中,就开始出现了“三提五统”的内容,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三提五统”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负担大幅度增长。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构成了“三提留”的内容;而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和民办教育方面构成了“五统筹”的内容。提留款归村级组织收取,统筹款由乡一级组织收取,所以又称“村提留,乡统筹”。提留统筹收入是村级组织的重要收支部分。而在公积金、公益金、上级投资及收缴、生产队基金和大队基金、银行贷款、税款、管理费、计划生育、提留统筹收入等9项收支中,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三项由村里直接向村民收取,并不上缴国家,其主要用途也是用于村中事项的处理。公积金主要用于村中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电站等;公益金主要用于民兵训练、军属津贴、教师工资、五保户补贴等公益性事业的建设,部分年份将“计划生育”纳入了公益金的范畴;管理费来源于村级管理过程中的罚款、收取的建房费等方面,而村干部工资、办公费用、会务费用、伙食费、差旅费主要在行政管理费中支出。

表4 D村1993-2002年收支结构统计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D村村级财务账本(2013)
与前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收支项目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一是村民上缴的各种费用增加了,且开始以个体为结算单位。比如,仅在1993年上缴的村提留、乡统筹两项就达50672元,还出现了农林特产税。各种集资也是明目繁多,比如公路集资等。其二是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而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当然,由于国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决定,行政分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深化,因此,村民经济活动的自由有所增强(比如鱼塘承包活动),村集体也有些生产经营性的活动。这些都可以从D村的村级生产经营性收支项目中反映出来。但由于D村地处中西部农村,集体经济非常弱,因此,经济活动也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性方面。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来看,如果说前期开始出现政权内卷化的倾向,那么,这一时期政权内卷化的特性比较突出。学界虽然对黄宗智借用格尔茨有关“内卷化”的概念颇有争议[18],但大多同意杜赞奇的“政权内卷化”的内涵及使用,即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权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5](P51)。
政权内卷化特性的彰显首先可以从D村行政费用增长得以说明。比如,1993年的行政管理费为31565元,到了2000年则增加到42654元。据调查,D村的行政管理费用不包括村干部的工资,而主要用于接待和村干部活动的日常支出。因为,这一时期正处于中国农村税费时代,村庄向村民征收各种税费的压力很大,在非常时期甚至还会聘用一些非正式官僚来充实征收队伍,以完成上级下达的税费和罚没任务[12]。行政管理费用的增加,意味着政府职能和权力在逐渐扩大,也表明国家权力的渗透在逐渐增强。除此,政权内卷化的特性亦体现在各种集资摊派上。如表4所示,D村的公路集资,1997年为10944元,2000年为21168元。虽然总量上不是很多,但对于经济发展非常落后的D村,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些摊派,经纪体制被延伸到村庄,这些村庄“经纪”在征收过程中,上下伸手,以饱私囊。
可见,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图景集中体现在基层政权的内卷化特性。由于基层政权借助于经纪体制,使得村庄财务收支结构达到空前的失衡。一方面是村庄债务高筑,比如,1997年D村向银行借款高达128591元,这些钱主要用于完成上级下达的税费任务;另一方面则是村庄行政支出增加,如D村的往来款在2002年达到了31528元,而往来款中很大一部分支出是村干部间的人情往来。
从另一侧面也可以反映,国家借助于各种方式来加强与基层社会的联系,或正式或非正式。“正式联系”是国家与个体村庄发生的在政治架构内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双方以各自特有的政治身份与对方发生关系的。甚至说,很多“正式联系”是对预先设定好的政治程序的履行。“正式联系”是能够用法律、制度来解释,是“有章可循”的,比如税费的提取比例、计划生育实施等方面。国家与村委会之间各自的职权是明确的,关系是固定的。“非正式联系”则是国家与个体村组织在法定的政治架构以外的联系。这种联系“无章可循”,双方并不是以正式的政治身份与对方接触,缺乏“政治色彩”,比如,账本中所记录的双方发生的借贷关系。这种借贷不同于前面所讲的上级拨款,也不同于村里缴纳给国家的各种费用。前面两者都是双方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履行各自的职能。而普通的借贷关系的发生,国家与D村是作为市场内最普通的经济个体而发生关系的,这种借贷不一定具备“政治色彩”,也不具备从属或支配的性质。比如,1998年,D村借乡政府10000元,有的年份乡政府会向D村借钱。像这种借贷关系并不具备政治效应,只具有经济上的约束力,等同于最普通的借贷关系。
可见,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国家借助于各种手段,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虽然在形式上出现了多元化,个体的自主性也大为增强,但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更加有效,而在这种强渗透下,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六、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政权建设变迁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了一个“加强-松动-再加强”的过程,这一过程透过村庄的收支关系变化微观地呈现出来。
从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来看,上述国家政权建设变迁的历史图景,只是反映了这个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特性。从长时段来看,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控力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国家更容易渗透到社会中,强化其监控力,因而国家政权建设的效果将会越来越好。然而,这并非说明在现代国家社会无成长的空间,也不是说经纪体制趋于盛行,相反,社会同样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成长,并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制约政权的内卷化和经纪体制的不断重复。
2003年以后,随着“村财乡管”体制的推行,税费改革的完成,政权内卷化的趋势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国家权力也因为载体的丧失有所缓和,但向底层渗透的努力却没有停止,只不过在方式和手段上更加策略化,“服务下乡”“政策下乡”和“政党下乡”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策略。然而,国家权力在向下渗透的同时,社会也在自我成长。各种民间组织在乡村社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遏制政权内卷化的有效力量。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政权建设的步伐将会向良性方向迈进,国家政权的服务职能将会强化,而吸取能力将随之而下降,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Joseph S.The Crisis of Tax State[M]. In Richard Swedberg(ed.). Schumpeter J.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马骏,温明月.税收、租金与治理:理论与检验[J].社会学研究,2012,(02).
[4]Tilly C.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Introduction[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6]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
[7]龙太江.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未完成的历史课题——兼论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集权与分权[J].天津社会科学,2001,(03).
[8]吴理财.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J].学习与探索,2002,(01).
[9]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J].学术月刊,2007,(08).
[10]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J].开放时代,2001,(09).
[11]王德福,林辉煌.地方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实践与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04).
[12]黄冬娅.财政供给与国家政权建设——广州市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研究(1949-1978)[J].公共行政评论,2008,(02).
[13]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4]张乐天,陆洋.新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解读——兼谈乡村社会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J].南京社会科学,2012,(06).
[15]韩鹏云,徐嘉鸿.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与现代国家建构方向[J].学习与实践,2014,(01).
[16]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7]项继权.中国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兼论当前乡村体制的改革[J].开放时代,2008,(03).
[18]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J].社会学研究,2004,(05).
责任编辑李业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