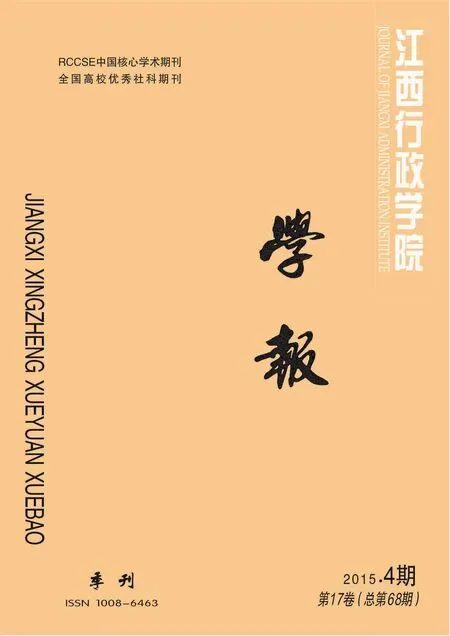仪式实践与村庄社会整合——以江西省泰和县东塘村的“上灯”仪式为例
仪式实践与村庄社会整合——以江西省泰和县东塘村的“上灯”仪式为例
罗士泂1,张世勇2
(1.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
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摘要]“上灯”主要以祭拜祖先、喝“灯酒”为活动内容,是江西省泰和县东塘村仍然实践着的宗族仪式。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来看,“上灯”仪式对宗族认同的产生和维系具有重要作用,并再生产着村庄公共性。“上灯”仪式所产生的这些社会功能已经社会化在人们的“叶落归根”和集体行动等日常观念和行为中。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村庄共同体面临解体的当代中国农村,保护和传承类似于“上灯”仪式这样的村庄传统文化资源,对乡村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仪式;社会整合;宗族认同;村庄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K892.26
[收稿日期]2015-06-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及社会应对机制构建研究”(12CSH018)。
[作者简介]罗士泂(1991-),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张世勇(1977-),男,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农民流动和乡村治理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仪式与社会整合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仪式通常被界定为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是特定群体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1](P1)。仪式不仅在神话传说和宗教生活中,而且在世俗生活中也具有实际功能。注重仪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全方位表现以及“功能-结构”的整合能力,是有关仪式研究的重要方面,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和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为仪式的功能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2](P18-26)。涂尔干认为凝聚是仪式的重要功能。这是因为,仪式的最基本特征是实践,仪式在实践过程中具有公共性,具有维系群体所共有的价值体系和集体意识的功能。在涂尔干那里,在“集体意识”产生的过程中,人们通过仪式强化了个体对于集体或者群体的归附关系,将个体微弱的力量与强大的集体力量相勾连,从而达致社会团结、凝聚和强化集体力量的效果。这个过程就是社会整合的过程。显然,社会整合是仪式的重要功能之一。
“结构-功能”主义强调从整体的视角分析微观社会中仪式的功能,通过仪式行为和活动来分析“社会”以及社会现象。“结构-功能”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可以对现实生活中仪式的社会整合功能这样来分析:一方面可以指出社会整合的价值体系和集体意识是什么,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指出这些价值体系和集体意识是怎样与社会整合相联系的来解释任何仪式[3](P37)。
本文试图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剖析江西省泰和县东塘村的“上灯”仪式的社会功能。相比于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祠堂、族谱及其他宗族事项,“上灯”仪式的参与度较广,对村民的现实生活影响深远,其社会整合功能尤为凸出。在当代中国农村人口频繁流动,乡土社会发生巨大转型,村庄共同体面临解体的时代背景下,分析“上灯”仪式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对于乡土社会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村庄概况①
东塘村隶属江西省泰和县的一个自然村,距县城约50公里。全村户数143户,518人。与中国的许多村庄一样,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东塘村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多,常年外出人员逾150人左右,绝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都处于典型的季节性流动状态,即在春节后外出至次年的春节前夕返家。东塘村是一个典型的宗族性村落,罗姓始祖生于明永乐年间,与其他两兄弟分居后在本村一口大塘东面立基,故得名东塘村。自罗姓始祖开基至今,村庄历史已逾600余年。明嘉靖年间,曾孙们计议为始祖修建祠堂一座,以作后人怀念,取名为友恭堂。友恭堂有4大房派,分别为晴江堂、远门堂、承德堂、亮子堂。其中亮子堂人数最多,约占东塘村总人口的60%。
自20世纪初开始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农村宗族在国家的主流政治话语中完全丧失了合法性,宗族被表述为一种落后、封闭、愚昧的封建糟粕。经历过多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许多农村地区的宗族组织瓦解,族权被废除,族产被充公,谱牒、祖宗牌位、菩萨等实物被销毁,宗族的各种活动和仪式被限制或禁止。但是“与其他地区不同,泰和农村中的宗族传统一直没有真正中断过”,即使是在建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如土改和文革初期的“扫四旧”运动,“泰和城乡也从未对宗族的历史传统进行过分严厉的‘清算’”[4](P24)。这方面在东塘村有充分的体现,如东塘村至今仍保存较好且一直在使用的友恭堂、精心保存的重修于光绪年间的族谱以及每年一次的“上灯”仪式。
三、实践着的“上灯”仪式
目前的东塘村,除了祠堂、族谱、祖坟等宗族事项之外,“上灯”仪式是目前村庄中唯一的、仍然实践着的宗族活动。下面对“上灯”仪式的内容与过程作一详细介绍。
(一)仪式简介
“上灯”[4](P263),是指为庆祝新生男婴以及男子“满旬”(年满20、30、40、50、60岁)而在祠堂举行祭拜祖宗、喝“灯酒”②的宗族性仪式。所谓“灯”有“新灯”和“旧灯”之分。新灯即是指新生男婴,也被称作“鸿丁”灯③,旧灯则是指“满旬”者。添丁即意味着宗族生命力的延续,“上灯”的主要目的是向祖先报告“香火有续”,并感谢祖先有灵。“上灯”作为一种宗族仪式被赋予了象征意义,通过“上灯”仪式向外部展示宗族强大的生命力。
东塘村人从何时开始“上灯”仪式,可以追溯到罗姓祖先在此开基,其间经历过怎样的历史变迁已不可考。最近的变化只能追溯到文革时期。据调查,1960年代初期之前“新灯”和“满旬灯”分开进行,并不统一操办。喝“灯酒”的菜品讲究“八碗八碟”,每户上灯人家都必须置办两桌。四碗是热菜,“新灯”以鱼、肉等荤菜为主,“旧灯”则更多的是以素菜为主,如豆芽、豆腐之类。但这四碗之中必须有一盘红酱肉,红酱肉要是没有吃完主人必须将剩余的带回家。另外四碗是点心干果,如状元红、花生等。196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条件困难,“新灯”“旧灯”都无力独自承担举办上灯的费用支出,族人便对上灯形式进行改革:“新灯”与“旧灯”合在一起共同操办,仪式的所有组织工作由“新灯”负责,这样的规矩一直延续了下来。
文革期间,“上灯”活动曾中断过几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全村办了持续几天的灯酒,一则为文革期间没有参与“上灯”仪式的男婴重补仪式,二则为了庆祝“上灯”仪式的恢复。从此,“上灯”仪式每年都会举办。2004年的“上灯”,是近几年最为热闹的一次,当时邀请了舞龙队助兴,还对整个过程录了像。
(二)仪式地点
“上灯”的地点在友恭堂,友恭堂始建于明代嘉靖丙寅年(1547年),宗祠坐东向西,前后三栋,长50.52米,宽12米,占地603平方米,砖木结构。庭院地面两侧用砖铺修,中间道有5米宽,全用鹅卵石铺修,造型美观精致。走进宗祠,正厅上悬挂“友恭堂”的堂匾,居中有天井一口,左右两边为游廊。祠宇友恭堂专设列祖列宗神位龛(不过目前已经没有了,只是在上灯当天会悬挂始祖夫妇像)。龛前有一个四方大龛桌,重有千斤,主要用于族人祭拜时安放香烛、香火等。仪式当晚在祠堂庭院里燃放烟花鞭炮,之前也在这里放电影。
(三)仪式过程
1.仪式的组织与准备
上灯前需要一系列的准备活动,这些活动单纯依靠一两个家庭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这也是同族人互助以及集体行动能力的体现。每次“上灯”主要由“新灯”家庭操办,每年“新灯”中辈份最高、年龄最大者的父亲作为仪式的主管,全面统筹仪式的组织与准备活动。
每年大年初一,主管会将所有“新灯”家庭的代表召集在一起,商讨仪式的具体事宜。从这些代表中选出会计和出纳各一名。仪式的开销来自“上灯”家庭的集资。“新灯”集资较多,一般根据大致预算除以当年“新灯”的总数来确定其集资多少,近年来普遍在1000元以上。而每个“老灯”家庭集资较少,只需10元或20元即可。
聚餐用具也由“上灯”家庭来准备,“旧灯”家庭一般只需要提供一套桌凳(八人座)、一套餐饮用具(八人用)和一个酒壶,“新灯”则需准备两套甚至更多。此外酒水也是由各个“上灯”家庭提供,在正月初八或者初九上午,主管会安排专人到各个“上灯”家庭中收集。所有“上灯”家庭在仪式开始之前都必须买好香烛、鞭炮等祭祀用品。
在正月初九的当天早上,上灯的家庭都会在自家“香桌”(用于呈放香炉、菩萨等用于祭祀的桌子)上摆放一碗白米饭,同时还要燃放“小边挂”(很短的一串爆竹),在中午和晚上还需各举行一次。村民可以据此判断哪家今年会“上灯”,特别是那些“旧灯”,因为谁到“满旬”村民很难确切知道。初九上午,主管还必须把村中的老先生请到祠堂为恭贺“添丁”“满旬”之喜书写横幅、对联并将其张贴于祠堂内的柱子、门襟等处。类似的对联有:“放手擎明月,开心闹花灯”“灯前共饮新丁酒,酒后同观福禄灯”,尽皆喜庆之辞。
2.仪式前奏
正月初九傍晚,“上灯”家庭各自把备好的餐具、桌凳、爆竹等带往祠堂,等待仪式开始。桌凳此时并不摆开,只需倚靠在墙边或者祠堂的柱子上。这时,所有的村民以及来村作客的外甥、姑丈等客人都陆续来到祠堂庭院等待仪式的开始,众人齐聚一堂,交谈甚欢。特别是那些常年外出务工的村民,更是珍惜这样的场合,因为这是他们一年到头与村民相聚的不多的机会。
过去,仪式当晚还会请戏班在祠堂唱戏、舞龙灯。后来改为在祠堂放电影,随着电视的普及,电影也不放了。不过,每次举行“上灯”都要雇请吹鼓手。在仪式开始之前,祠堂里已经是欢聚一堂、热闹非凡。
3.集体祭拜
“上灯”仪式的四个主要环节由四通鼓来引导。有专人负责击鼓,用一根大竹杠击打祠堂大厅北边墙上挂着的大鼓。击鼓有一定的要求,先是三声慢节奏且特响的“砰砰砰”,紧接着就是九声快节奏的击打,重复三次即可。
随着第一通鼓声响起,“上灯”仪式正式开始。所有“上灯”家庭都必须派1名代表(除却“新灯”是由男孩的父亲代替外,“旧灯”除特殊情况一般是本人)前往神龛插上香烛、香火,随后是集体祭拜。所有代表依次排开,具体顺序是,前几排是“新灯”家庭代表,第一排中间是“新灯”中辈份最高、年龄最大者的父亲(即当年仪式的主管),后面几排是“满旬”者,依照60岁、50岁、40岁、30岁、20岁的顺序一排排站好,在斯文先生的主持下行三跪三拜之礼。
4.鸣炮
第二通鼓敲响后,便是鸣炮。在祠堂庭院等待的人听到第二次击鼓后,一起燃放鞭炮。鞭炮燃放完之后放烟花。放烟花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的,之前以鸣放火铳为主。炮竹和烟花烘托出热闹喜庆的气氛。观看完烟花之后,第三通鼓声响起,开始喝“灯酒”。
5.喝“灯酒”
所谓喝“灯酒”就是聚餐,也在祠堂里进行。此时,桌凳业已摆好,在上菜的过程中,斯文先生(图1西席1号)会起身面向众人介绍本次“上灯”的情况,同时祝福本村(即本宗族)人丁兴旺。斯文先生讲话完毕即可开怀畅饮。餐桌上的菜一般得补充三次,第一次加菜时,斯文先生会首先打“阐”④,对着头席说道:“今晚乃本房云灯之喜,前辈、外甥、姑丈、席上列客,一杯薄水,席上简单,敬献各位。”此时,头席上的前辈便回应道:“今晚乃贵房云灯之喜,祝添丁者长命富贵,满旬者添福添寿,一起喝个鸿杯,敬献各位。”如此云云。当第二次加菜的时候,前辈这时又先打“阐”,然后再说些酒食已够之类的客气话。斯文先生则以天气和暖,慢坐一时等话语回应。整个喝“灯酒”的过程一般会持续两个小时左右,由斯文先生宣告灯酒正式结束。随后第四通鼓响起,标志着此次“上灯”仪式结束。
图1友恭堂席位安排简图

(四)与“上灯”有关的其他事项
1.酒席的规模和菜品
自从1960年左右的改革之后,喝“灯酒”的菜有“四湿四干”之分,“四湿”指的是:鱼、肉汤、豆腐等主菜,“四干”则是指红鸡蛋、状元红等干货。上菜的顺序先是红鸡蛋、状元红等干货,其次便是豆腐、鱼等,肉汤是最后上桌的。现如今,对于已经贫富分化的族人来说,因为各家经济水平不同,酒席的规模有所变动,但幅度不大,总体上维持在30至40桌之间。菜品的总数量不会有变化,都是八个菜。不过有些较为富裕的家庭如果“上灯”,单个菜的菜量会有所增加。关于菜量的多少,族里的妇女在上灯结束后会议论,比如会说“xxx家今年吃得好,菜也够量”。也就说,酒席的规模和菜品的种类不会因村民贫富分化而有很大的差别,避免了炫富等恶性竞争。
2.喝灯酒的席位安排
喝“灯酒”时席位安排很讲究,不“上灯”的村民一般都和本家(本房)人坐在一起,而本家没有人家“上灯”的人则可以随意坐,但不能乱了长幼和辈份。有8个席位是不能随便坐的,也就是村民口中所说的“上座”“西席”等(参见上图1)。上座中也有先后之分,图中上座1号为头席,头席是由主管优先考虑邀请村中本年度没有获得男丁的某房的前辈(前辈是按照年龄、辈份来确定的,一般超过60岁以上才可能被称得上前辈)。前辈此时是作为客人被邀请参加并向“上灯”者贺喜。来村中做客的外甥、姑丈都分别有一个席位,外甥、姑丈的选择主要按照辈份来进行,年龄并不重要,即使让年龄小的男孩坐在这个位置上也无所谓,其中上座2号为姑丈,上座4号是外甥。西席则是邀请斯文先生。除了主持仪式,斯文先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招呼客人”,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说话有水平,一般都是通过与前辈打“阐”的方式进行。
3.上草谱
“上灯”仪式的第二天上午(正月初十),是一年一度上谱的时刻。此时的上谱是上草谱,作为正式修谱时的依据。每隔30年才正式修谱一次。
上草谱也有严格的次序,主要是按照添丁、娶进、嫁出、死亡的顺序进行。添丁者,即将其姓名、具体的出生年月日记载在草谱之上。对于娶进者,详细记录女方居住地、生辰八字、其父亲的姓名等。嫁出者,记录其嫁出地、配偶姓名。对于死亡者,记录其死亡的具体年月日、埋葬地点、坟头朝向等。
上谱的完成代表着新生男婴正式加入宗族,成为宗族认可的一个新成员。他在族谱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就被赋予本族人的身份,更体现了祖先血脉的绵延。
四、“上灯”仪式的功能分析
吉日祯吾认为,仪式可以传授或者表达某种东西,具有再生产和再塑造的特性[5](P53)。从上述仪式的程序、过程、场合以及氛围可以看出,“上灯”仪式至少表达了两个方面的集体意识:其一,“上灯”仪式维系和再生产着宗族认同,巩固了村民的同宗关系;其二,“上灯”仪式再生产着村庄公共性和道德秩序,凝聚了村庄的共同体意识。
(一)宗族认同
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宗族性村落农民的意义世界是建立在祖辈身上的,生养男孩是延续祖宗血脉的责任。在“上灯”仪式举行的过程中,村民可以体验到一种从祖宗到子孙后代血脉绵延的历史感[6](P31)。这种历史感内涵着对宗族认同的集体意识。宗族的后代子孙唯有生养了男孩,尽到了传宗接代的责任,才能够体验到这种历史感,宗族成员个体的生命意义正是以这种历史感作为载体而实现的。正如参与“上灯”的族人所说上“新灯”目的在于“沾了祖宗的光,生了儿子,要拜谢列祖列宗,对祖宗表示感谢”。新丁的诞生,使得宗族血脉的延续成为可能,也正因为此,生者才会有感激祖先的动力与理由。如果不去上灯也就不可能有资格上族谱,就会被排斥在宗族之外,个体的生命就可能失去了意义。
“旧灯”参与“上灯”仪式,可以解释为“满旬”者向祖宗报告生存状况,同时也祈求祖先能够提供更多的庇佑,确保生活平安幸福、子孙有出息。他们也是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通过追溯、思念、感谢祖先的过程体验祖宗血脉绵延的历史感。显然,无论是“新灯”还是“旧灯”对“上灯”仪式的自我解释,都体现着对宗族的认同。需要说明的是,族人对于宗族的认同并非仅仅只是由仪式达致的结果,当然还有其它宗族性事项,比如祭祖、葬礼、日常生活交往等。但是,“上灯”是目前东塘村唯一存在的、周期性的全员参与的宗族仪式,其对宗族认同的维系的重要作用是其他宗族事项无法替代的。
(二)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
村庄的公共性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基础之上的,然而伴随着乡村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变迁和文化基础的削弱,村庄原有的公共性也日渐衰微。而在东塘村,“上灯”仪式在村落中年复一年地举办,已经成为村庄中不可或缺的公共活动,再生产着村庄公共性。在乡村社会巨变的背景下,这一点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作为村庄中的公共文化活动,“上灯”仪式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使得村庄的公共性的再生产和维系有现实的载体。“上灯”仪式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祠堂举办,为族人体验祖宗血脉绵延的历史感提供了具体化的场景,同时这也是一个公共性再生产的过程。在宗族性村落中,宗族成员的出生、结婚、葬礼等重要的生命仪式都要在祠堂里举行,“上灯”仪式是关于宗族成员出生和身份确认的生命仪式。祖宗的牌位画像供奉在祠堂里,“上灯”仪式的举办使得祖宗和子孙后代象征性地共聚一堂。这对于所有的宗族成员(包括已经逝去的祖先)来说是一种共享的欢愉,对于现世的族人来说,则体验着共有祖宗的心灵“共振”, 再生产着村庄的社会团结。
第二,在“上灯”仪式所提供的这个公共空间里,一种以共同祖先为纽带的公共关系得到了再确认和强调。通过对这种血缘关系的强调,宗族共同体(同时也是村庄共同体)得以延续。族人在此期间通过一起聊天、看烟花燃放的壮观场景、喝灯酒等方式进一步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特别是那些常年在外漂泊的村民,通过参与“上灯”仪式,维系了与其他村民的社会关系。
第三,仪式的举办建构了一种共同的美好记忆。当仪式活动结束之后,仪式现场的热闹逐渐淡去,重归日常生活的族人依然反复品评与回味仪式的过程。当有人问及“上灯”仪式时,族人都显得格外兴奋并且会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一一告知。“上灯”仪式俨然已成为一种美好的共同记忆。正如大专毕业后已经在外工作5年的应强说,“感觉通过这种形式,全村都拧在一起,有氛围。同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聚一聚,问下自己村庄中的好友外出情况。这种感觉很好!而且一年到头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以前上学不曾有这感觉,只是觉得好玩,现在出去后,才发现这个很有家乡味道。更何况每年只回来一次,这样的机会更加珍惜”⑤。
第四,仪式的举办过程重申了公共道德和秩序。“上灯”仪式中的按照长幼次序祭拜、酒席座位的安排仍然讲究房派和辈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宗族长幼道德的重申。对于每一个“添丁”者来说,他都必须参与上灯仪式并且在祠堂置办“灯酒”。就像人们所说的:“我喝过别人家的灯酒,作为礼尚往来,我也应该让别人喝我的灯酒。即使我没有喝,我的祖辈曾经也喝过。”正是在这样的习俗约束之下,族人之间的人情往来的网络也就绵延不绝而未曾断裂。很显然,这些习俗和规矩是公共秩序的重要基础。
五、“上灯”仪式的社会化表现
族人通过“上灯”仪式与祖先沟通,向祖先汇报生者的生存状况,不仅再生产了宗族认同和村庄的公共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集体意识已经社会化在村民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中,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秘而不宣”的行为动因。我们可以从外出务工人员对仪式的积极参与、村民建房行为所体现出的“叶落归根”观念以及村民的集体行动中窥其一斑。
(一)积极参与
仪式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是“强制性”的活动,这种“强制性”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转变为参与者不加反思的“应该”行为。这在人们对“上灯”仪式的肯定态度和积极参与中有充分的体现。
现年30岁的亮廉则认为,“上灯很热闹,一大家族的人聚得比较齐,一年也就只有这么一天看的人比较多。而且在外打工后,难得见到一次面,一起喝酒聊天,也算一次聚会”⑥。他的表达实际上透射出这么一个信息,即“上灯”仪式的举行将外出村民的心凝聚在了一起。当“游子”归来之后积极参与仪式体验到仪式现场的视觉震惊与心灵震惊,当他们一起坐在祠堂之时总能体会到一种“家乡的味道”,乃至于使他们有一种“不参加就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的感觉。当人们在回答“有没有人不去上灯”这一问题时,回答道“没有人不去上灯,不去就是笨蛋”。东塘村中有一人已经是外村的“上门女婿”,却仍然坚持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在本村(东塘村)“上灯”“上谱”。 可见,必须参加“上灯”已经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
(二)叶落归根
近年来东塘村在建以及新落成的房屋特别多。这也许是因为近年来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村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有所增加,有了改善居住条件的经济基础使然。但25岁的宾明对自己建房的解释,说明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宾明看来,“即使没有多少积蓄,仍借钱建房,有钱可以在外买房,但在家里有个安身地,叶落归根嘛!在家总得有个落脚点,老了年纪大了,回来有个地方住。自己也不可能打一辈子工,始终还是要回来,现在在家建好房。即使发达了,家里还有亲戚朋友”⑦。现年65岁的梅师同样表达了这么一种看法,“在家建房后,以后老了回来能有个落脚地”⑧。不仅他们两人,许多在外工作并安家落户的村民,也一定要返修或重建自己的房子,以备“叶落归根”。当地的经济、交通条件并非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在外边已经买了房子顺利实现了城市化的村民依然想着要“叶落归根”,可见宗族认同已经内化在村民的思想观念深处。这种认同已经超出了“生我养我的地方”的简单内涵,具有祖宗血脉绵延意义上的超脱性,对常年在外打工的族人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拉力。
一定程度上参与仪式也是一种关系的确认,即对宗族成员身份的认定。如果有人在年老之后不返回村庄,他就无法亲自在祠堂向祖先汇报自己的生活状况,一旦他不是在村域内死亡,那么就连在祠堂举办丧礼的资格都将丧失,某种程度这不啻于是对其族人身份的否定。与此相反,如果他年老之后居住在村庄的范围之内,就不存在上述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族人所说的建房是年老之后能够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更深层次原因是他们在乎认祖归宗,因为这是他们生命意义的价值所在。
(三)集体行动
2005年东塘村的28位村民在县政府的办公室将本镇的书记打了。事情的起因是东塘村与邻村的集体资产纠纷。东塘村与邻村院村本是同一个祖先,历史上分家析产时,院村得到面积小、平坦、肥沃的耕地,而东塘村分得面积大、地势不平整的山地。2005年林权改革时,为了得到更多的林业补贴,院村对东塘村的一半的林地提出要求。当时镇书记偏袒院村,在山权证、林权证都在东塘村手中的情况下,仍坚持要将一半的林地分给院村。最后东塘村召开村民大会,选出代表,并要求村委主任和书记必须与大家一起去县政府讨要说法。临行前威胁道,如果不去,便将他们逐黜族籍,不让他们的子孙进祠堂上灯,不能上谱。在一番内心挣扎之后,村委主任和书记最后还是赶过去了。并且说道,“得亏我们去了,把他们劝开了,不然还不把他(镇书记)打死啊”⑨。
这件事情,至少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为了集体利益,村民可以组织起来并集体行动;其次,对宗族身份的强调已经深入人们的观念中。村干部的身份具有两重性,一是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一是作为宗族成员,这两重身份使得他们在上述集体行动中产生了角色冲突,其处境颇为尴尬。村干部想在宗族成员(村庄共同体的一份子)与国家治理者身份之间取得平衡,不想参与集体行动,但族人以“如果不去,便将他们逐黜族籍,并不让他们的子孙进祠堂上灯和上谱”相威胁。作为国家“代理人”要求他们不能参与集体行动,而作为宗族成员以及村庄的一份子却又不得不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矛盾和纠结中,他们最终选择了后者,抱着“硬着头皮过去,要是解职也没办法”的心态参与了集体行动,虽然他们嘴上说是扮演了调解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逐黜族籍乃至自己的子孙都不能进入祠堂上灯和上谱,这将意味着“断绝与宗族祖先的联系纽带,失去了宗族成员的身份”[4](P160)。村干部如此重视宗族成员这一身份,并在有可能影响到自己国家代理人角色的情况下参与村民的集体行动,是宗族认同在个体行为上的最好表现。
六、结论和讨论
通过上文对东塘村“上灯”仪式的详细描述及功能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仪式所发挥的社会整合功能是依循两条线索:其一,宗族成员身份这一社会认同;其二,对村庄共同体的维系。
“上灯”仪式举行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一种社会关系的再确认,这种社会关系通过与祖先象征性的沟通与交流而获得,即族人对于自身宗族成员身份的确认、强调与认同。对于新生男婴来说,通过“上灯”仪式向祖先汇报自己降生于世,通过在族谱上书写上自己的名字等出生信息,从而在宗族谱系中拥有自己的位置,正式获得宗族成员身份。无论是对仪式的积极参与和认可,还是建房现象所凸显的“叶落归根”观念,乃至于村庄中的集体行动都是宗族认同在个体行为上的体现。
“上灯”仪式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一种共享的社会记忆,村民之间长幼尊卑的道德秩序和村庄公共秩序再次被强调。在这个空间里以血缘为纽带的人情往来得以可能,超越家庭和一般亲友的欢聚在这个空间里举行。这对于那些常年外出务工的村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们外出只是为了获取更好经济收入,但其社会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只有在宗族、村庄才能实现,“上灯”仪式为他们实现这些价值和意义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场域和实现这些价值的机会。他们参与“上灯”仪式不仅维系与祖宗的关系,而且现实生活中与族人的关系以及在村庄中的社会资本也得以再生产。对于处于流动状态的村民来说,虽然他们身体在外,村庄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之网,而且是一种价值意义之网。当他们结束流动状态返回家乡之后,就可以从容地回到这种社会关系中,为其适应村庄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而言之,无论是仪式所产生的宗族认同抑或是公共性的维系,这两个仪式的整合功能都是村庄社会关系和共有价值的确认、维系和再生产,区别之处在于前者是一种纵向的与祖先联系的身份确认与认同,后者建构着横向的村庄社会关系网络。村民通过对这种社会关系的经营,自然而然地构筑出一个结构相对稳固的村落共同体。这是“上灯”仪式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所产生的重要社会效果之一。
在当前中国农村,伴随着大量中青年外出务工,农村人口流动增强,村庄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进一步打破了村庄社会封闭性。外出务工在改变村庄原有的经济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缓解村庄人口和资源的压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频繁的人口流动不仅导致村庄人口过于疏化,农村的人口结构亦发生了巨大变化,村庄社会生活乃至农民的家庭生活不完整,村落共同体也面临解体。东塘村的“上灯”仪式所具备的村庄社会整合功能无疑对于这些消极方面具有消解作用。当人们基于共同的信仰、追求或利益,借助仪式的表达与实践,从而建立了一个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社会关系网时,对于维系他们自身的生活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能促进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和整合。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实际上仍然存在诸多类似东塘村“上灯”仪式这样的传统文化资源,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如何发掘和保存这些传统资源,对于重建乡村社会,让人们记得住乡愁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依据学术规范,文中的地名、人名都已做过相应的技术处理。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张世勇、罗士泂、卢云龙子、张婉杰2014年4月在东塘村为期15天的调研,东塘村是罗士泂的家乡,部分资料也来自于罗士泂的日常观察。
②近人娄子匡在《新年风俗志》载广东海丰新年“灯酒”习俗云:元宵节,家家要备牲醴去祭神祭祖,大街小巷中的人家,凡是在去年养了男孩子的,他们就在这天设筵欢宴;要是族中有公产的人家,那就由公众来办酒席,在祠堂里宴饮,这就叫“灯酒”。不过本地的喝灯酒与其所描述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③本文将其称作“鸿丁”,而不是“红丁”,可能是由于钱杭所调查的地方与当地叫法差异所致。泰和地区方言甚多,发音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而在东塘村一般将“鸿”念作“féng”。
④打“阐”主要是指敬酒一方起立,端起酒,向对方表明敬酒的意思,然后再说些敬酒之类的话语。此时,所有的喝灯酒人员都会放下手中的筷子,观看打“阐”双方。
⑤2014年4月13日上午,在其家中访谈。
⑥2014年4月15日上午,在其家中访谈。
⑦2014年4月11日晚上,在其家中访谈。
⑧2014年4月12日晚上,在其家中访谈。
⑨2014年4月15日下午,在当地村委会办公室访谈,村委主任、书记以及会计在场。
参考文献:
[1]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英]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M].夏建中,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5]吉日祯吾.宗教人类学[M].王子今,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6]杨华.绵延之维:湘南宗族性村落的意义世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李业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