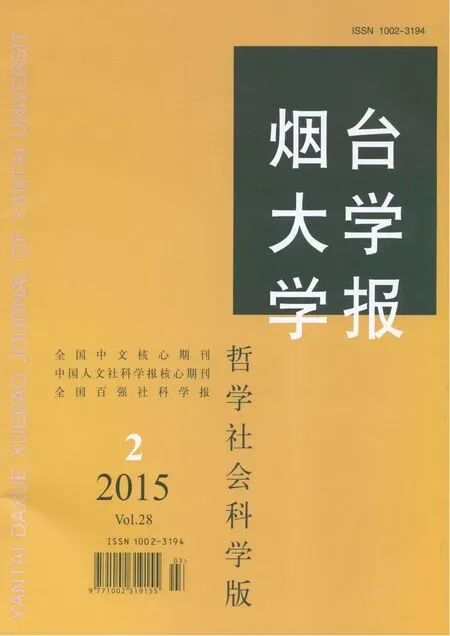“他者”想象中的种族书写
——论卡森·麦卡勒斯作品中“隐蔽的东方主义”倾向
尚玉翠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他者”想象中的种族书写
——论卡森·麦卡勒斯作品中“隐蔽的东方主义”倾向
尚玉翠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美国南方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对美国南方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与现实冲突非常关注。在其作品中,她力图超越自身所处文化中的种族主义狭隘观念,真实地展现黑人、菲律宾人和犹太人等少数族裔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困境,但也存在着“刻板化”黑人、“女性化”菲律宾人和“神秘化”犹太人的倾向,为他们烙印上或显或隐的东方主义特征。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可以解读麦卡勒斯对黑人、菲律宾人和犹太人等少数族裔形象的东方主义想象,揭示其作品中“隐蔽的东方主义”倾向,并探讨这种“他者”想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动机。
卡森·麦卡勒斯;他者;种族书写;隐蔽的东方主义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2.012
作为美国当代极富个性的作家,卡森·麦卡勒斯以对精神隔绝主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刻揭示而著称。从其第一部作品《心是孤独的猎手》到其最后一部作品《没有指针的钟》,几乎所有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都被烙上了明显的精神隔绝的印记,因而,精神隔绝主题也成为其作品重要而独特的标志之一。她通过探讨阶级、性别和种族等权力等级关系对个人的规训、限定和惩罚,深刻揭示出:正是这些无所不在的隐形权力将每个个体限定在精神隔绝之中,无法超越,也难以超越。在造成人物精神隔绝的众多隐形权力关系中,她非常重视种族这一维度,不断以犀利的笔触真实地刻画出美国南方社会中的种族歧视现象,凸显出对黑人、菲律宾人和犹太人等东方族裔的生存境遇与文化困境的重视和关注。在对身处种族歧视语境中的黑人、菲律宾人和犹太人等东方族裔形象进行塑造时,她力图超越种族主义的壁垒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桎梏,客观真实地展现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的个性特征和生存状态,但是也存在着“刻板化”黑人、“女性化”菲律宾人和“神秘化”犹太人的倾向,将他们作为沉默的“他者”,为他们烙上或显或隐的东方主义特征。
根据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东方主义”首先是学术层面的,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其次指的是一种以“东方”与“西方”之间“本体论与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它认为由于东西方在地理上分别居于地球的东西半球,在其他诸多方面也处于长期的区隔和对立状态,因而双方在政治、经济乃至语言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巨大差异。*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4页。第三,“东方主义”是一种权力话语,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进行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基于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所谓“东方主义”便成了西方人出于对广大东方或第三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以此满足其自身文化、文明发展和殖民扩张的需要。西方中心主义者从既定的特权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人为地设置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先进与落后——并以此对世界加以描述和定位,将东方形象塑造为上述二元对立系列中的后者,认为“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西方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萨义德:《东方学》,第49页。由此可见,这种西方优于东方的神话是西方为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地位而进行的一种强权政治虚设,表达的是对自身的时代关注。
一、对黑人的“刻板化”描写
作为美国南方人数最多的少数族裔,黑人在麦卡勒斯的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出现在她的每部作品之中。她“很同情他们(黑人),为他们被奴役的地位感到抱歉”,并试图像对待同族人那样“自然和公正地处理黑人角色”*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冯晓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32、135页。——既描述他们惨淡困苦的生活困境,又表现他们因遭受种族歧视与不公而产生的孤独与无奈,进而对黑人形象的个性和生存境遇进行了较为客观和人性化的呈现。但她也借用了一些传统美国文学中所塑造的黑人的“刻板形象”,并没有完全走出刻板化描写黑人形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惯性。刻板化描写作为西方在东方化东方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往往通过无所顾忌地贬低和诋毁东方不断将其边缘化,从而达成巩固和增强西方中心霸主地位的目的。在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有意无意地对处于从属地位的黑人进行负面解读,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与想象塑造了许多“刻板化”的黑人,如心智不成熟的“黑孩子”,逆来顺受的“汤姆大叔”和“珍妮大婶”等等。这些丑化和固化的刻板形象既严重歪曲了黑人的应有形象,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公众对黑人群体形成固定呆板的认识,使得他们在美国社会只能处于“他者”的位置,极大地削弱了他们为自我存在进行辩说的话语权力。
首先,对心智不成熟的“黑孩子”刻板形象的借用。心智不成熟的“黑孩子”的刻板形象主要表现为一些没有恶意却有点疯疯癫癫的黑人小孩,他们生性懒惰、疯狂和幼稚,不像正常人。麦卡勒斯作品中的许多次要角色就是此刻板印象的复制与体现。《婚礼的成员》(以下称《婚》)中的哈尼被看作是上帝没有完成的孩子,他无所事事,四处荡悠,最后迷上了大麻,闯入白人店铺实施抢劫。《没有指针的钟》(以下称《钟》)里的黑人男孩“大小孩”,馋嘴且“没有健全的智力”*卡森·麦卡勒斯:《没有指针的钟》,金绍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页。,最终因抢夺食物而惨死于警察之手。这些被“造物主太早撒了手”*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周玉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31页。的黑人男孩,要么做出并非正常人的疯狂行为,要么嘴馋低能没有头脑,既缺乏理性又幼稚不堪,心智十分低下。他们被描述成带有人种缺陷特征的低劣族群,处在种族等级金字塔的最低端。
其次,对逆来顺受的“珍妮大婶”刻板印象的使用。珍妮大婶是黑人奶妈形象的一个分支,往往给人留下温柔快乐、性格极好的印象。麦卡勒斯笔下的大多数黑人女性都是此类刻板印象的延续。她们隐忍温顺,安于现状,毫无反抗意识。《心是孤独的猎手》(以下称《心》)中的鲍蒂娅在米克家做事,既要帮厨又要照看孩子,工作时间长、强度大,但她忠于雇主,认为三个小孩就像她的亲人一样,不是保姆却胜似保姆般地悉心照料他们。《婚》中在弗兰淇家做厨娘的贝丽尼斯更是“极像个保姆,既做饭又充当着替代弗兰淇母亲的角色”,*Yvonne Atkinson, “Mammy”, AMERICAN, Vol.II.Issue 1,(July 2005), p.22.不但在生活上照顾她,还忍受她孩子式的任性与胡闹,帮助她顺利渡过青春期成长为少女。她们都自愿融入主流白人文化,毫无逆反的意识与倾向,即使在亲人遭到白人的不公正对待和迫害时,她们也只是悲伤地接受事实。面对哥哥遭受酷刑而终生残疾的悲剧,鲍蒂娅除了焦急和心痛之外无计可施;贝丽尼斯在哈尼被判处八年刑期后,虽然四处奔走,以致心力交瘁,但都于事无补。正是囿于白人意识形态的局限,这些安分守己的人过于逆来顺受,完全不懂得通过反抗来摆脱逆境,不会对现有的种族秩序带来任何威胁。
第三,将有种族反抗意识的“抗议黑人”塑造得过于极端和偏执。这类形象虽然不同于极端负面的、妖魔化的“黑人暴徒”形象,但他们对白人所持有的反抗、敌视和仇恨态度,却使他们成为过“度”的极端者与偏执者。《心》中的黑人医生考普兰德是一个思想层面上的“抗议黑人”。对于黑人,他充满了拯救种族的使命感,希望用知识和教育来帮助他们成为与白人一样有自尊和尊严的人;对于白人,他秉持反抗态度,自始至终充满着敌对情绪,把他们称作“恶魔”和“压迫者”。但他的这种反抗思想却极端与偏执,不仅使白人视他为“国家的麻烦”,而且也得不到同胞和家人的支持与理解,甚至被家人看作是“愚蠢的胡闹”,最终只能怀着“隔阂、愤怒和孤单”的心情默然离开*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陈笑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39页。。《钟》里的黑白混血儿舍曼是一个行动上的“抗议黑人”。由于刚出生就被抛弃,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但却想当然地认定父亲就是个白人疯子,强奸了他的黑人母亲,因此他恨父亲、恨白人,认为所有南方的白人都是疯子,对白人充满了敌意,并从语言和行为两个方面不断地进行反抗。在与白人进行语言交流时,他会故意违反话语规范,“误用”和瞎编一些词汇,试图通过颠覆语言自身承载的语义秩序,来扭转与之相关联的“错位”的种族秩序。在具体行动上,他十四岁时与同伴撕扯下珍妮大婶的广告牌,抗议白人对黑人妇女进行人为设定的刻板印象;当后来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他产生了与白人“对着干”*卡森·麦卡勒斯:《没有指针的钟》,第237页。的想法,采用暴力手段报复白人对黑人种族的不公正对待,并悍然搬进了象征身份、权力与地位的白人居住区。他这种公然挑战白人尊严和种族等级秩序的“越界”行为,引起了白人的强烈不满与无比愤怒,最终被炸死在家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所做的有意激怒白人的颠覆性举动,虽然表达了挣扎在边缘上的少数族裔群体对主流社会权力的否定与控诉,但也导致了种族矛盾的激化与仇恨犯罪的爆发,极端与偏执得过了“度”,最终遭到了主流社会的强烈压制而走向失败。
二、对菲律宾人的“女性化”描写
在美国传统文化中,当其描述和刻画东方时,会有意识地女性化东方,将亚洲移民建构为温顺、从不闹事和深具女性品质的形象,导致“女性化”的亚裔男性成为美国主流话语中一种特殊的性别形式。身为亚洲移民的菲律宾人来到美国之后,生活在由白人所主导的殖民话语和权力网格中,被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霸权文化所控制和操纵,处于失声和无法言说的被殖民状态,甚至面临着被女性化的尴尬处境。在《金色眼睛的映像》里,菲律宾家仆安纳克莱托便是被女性化了的“他者”形象的突出代表。
西方对东方的“他者”想象首先表现为对安纳克莱托的行为举止和心智等方面的贬损。在对东方进行书写的东方主义话语中,最常见的就是在生活情趣、行为举止和心智等方面对东方和东方人加以贬损。安纳克莱托是艾莉森·兰顿太太的贴身菲佣,他从未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喜欢卖弄蹩脚的法语,经常从嘴里蹦出法语单词。在餐厅用餐时,他居然不自量力地用法语点菜,结果因词汇有限只点了“卷心菜、四季豆和胡萝卜”*卡森·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陈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66页。。这种滑稽可笑的行为使其像小丑一般让人忍俊不禁。除此之外,哨所还流传着很多他与艾莉森荒唐弱智的逸事,尽管大部分都是上尉捏造出来的,是为了伤害和打击艾莉森,但“西方文化中叙述性别‘他者’与叙述种族‘他者’,采用的是同一套话语”*Lisa Lowe, Critical Terrains :French and British Orientalism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reface,Discourse and Heterogeneity: Situating Orientalism.转引自李纯仪:《〈印度之行〉中的印度想象:对〈印度之行〉中“他者”话语解读》,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7年,第25页。。由于身处秉持种族和殖民主义的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他毫无话语权,面对上尉肆意虚构和传播这些流言蜚语,他无法进行舆论的自卫,揭露这些虚假事件,除了生气和激动之外无计可施,但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他根本无力改变充满敌意和蔑视的种族等级秩序。
其次,西方对东方的“他者”想象更体现在女性化安纳克莱托的性格。在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在实践上被描述为女性的”*萨义德:《东方主义再思考》,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7页。,东方被想象、构建为女性化的他者,即使是对东方男性的描述也赋予其强烈的女性化特征。小说起初虽然没有明确暗示出他的性别,但他的生活情趣和性格都被赋予了强烈的女性特征,“自始至终被刻画为女性化和捉摸不定的角色。”*Martin, Robert: “Gender,Race, And The Colonial Body: Carson McCullers’s Filipino Boy, And David Henry Hwang’s Chinese Woman”,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1992.Vol.23 Issue1,p.99.他喜欢鲜花、亚麻、衣服等带有装饰性的东西,更热衷于芭蕾舞蹈,经常独自步态优雅沉着地跳舞,显得过于女性化。而且他不具有男性该有的坚强性格,非常胆小可怜,软弱无能,完全像个孩子似的毫无控制能力。刚到兰顿少校家时,他被其他的小男佣折磨得痛苦不堪,整天像小狗一样紧紧跟着艾莉森。尽管他已经十七岁了,“可是他病态、聪慧、惊恐的脸上分明是十岁孩子的无辜表情”,这种不成熟的幼稚状态使其无法自己生存,只能找寻强有力的白人作为自己的保护者和拯救者,所以当“他们准备回美国时,他哀求她带他一起走,她同意了”*卡森·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第64页。,艾莉森·兰顿太太充当起了菲律宾人遭受暴力后的抚慰者和保护者。在此,菲律宾人这个软弱与令人悲哀的异类,使美国人将其看作是有待帮助或照料的对象,需要进行所谓的人文关怀与扶助。这一情节的设置,象征性地再现了美国在菲律宾摆脱西班牙统治时所扮演的拯救者形象,既契合了美国人乐意颂扬并不断被美化的扩张意识,又在这种施救的过程中完成了拯救东方的“救世主”形象的自我建构。
第三,对菲律宾人的“他者”想象更体现为对安纳克莱托的性别加以女性化。跟随兰顿一家来到美国的安纳克莱托,就像艾莉森那只名叫佩特罗尼乌斯的猫一样,“夏季结束前她不得不给‘他’的名字加上了一个阴性结尾,因为‘他’突然产了一窝小猫”*卡森·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第134页。。他虽然是一个二十三岁的成年男人,但他过于沉湎于女性化的兴趣与爱好之中,整天不是莺歌燕舞就是摆弄水彩,像个女人一般阴柔。为此,兰顿少校多次吓唬他说要把他弄到军队里去,认为美国的军队语境可以强化他的男性气质,“会让他成为一个男人”*卡森·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第133页。。在此,美国人被赋予了成熟、伟岸和阳刚的男性特质,弱小的菲律宾人则表现出了如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女子的性格特征——感性、幼稚和柔弱,在“男性特质”上与西方白人男子不可同日而语。可见,安纳克莱托完全符合西方对亚洲男性“女性化”的认识模式,实现了西方人在东方主义视野中对东方人的期许。而且,这种二元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将东西方放置于一种比较的框架中,以安纳克莱托为隐喻的东方菲律宾落后柔弱,而以兰顿少校为象征的西方美国则文明强大,使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强烈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差异对比中,东方的菲律宾不仅成为美国自我映照的镜鉴,也成为其确认和强化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和民族文化自信的对象,甚至还为东方需要美国征服和救赎的殖民观念提供了合理的历史诉求。
三、对犹太人的“神秘化”描写
麦卡勒斯文学创作的主要阶段正处在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文学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犹太人遭到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和贬抑,在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各个方面都遭受压迫、剥削甚至是迫害,使他们深陷于悲惨的困境之中。面对这种极端和非人道的社会风气,麦卡勒斯声称她谴责“容许这样的堕落发生的社会”*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第243页。,对现实中的犹太人朋友充满了友好与同情。但“不会让现实发生的事情来影响”*卡森·麦卡勒斯:《抵押出去的心》,文泽尔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自己的麦卡勒斯,对独具特质的犹太文化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使其呈现出神秘化的色彩。
首先,她着重突出了犹太人的非凡智慧。麦卡勒斯“以智慧和受难为标志来界定”犹太人的身份,塑造了一系列拥有聪明头脑和超越精神的“喜深思、爱探求”的智者形象。*Hershon,Larry: “Tension and Transcendence:‘The Jew’ in the Fiction of Carson McCullers”,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September 22,2008.p.52,58.《心》中的哈里是正统的犹太人,在语法学校跳过两级,并且是“职业学校数学和历史课上最聪明的学生”*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155页。。在《钟》中,“(马龙)班上有许多刻苦读书的犹太学生。他们的成绩都在年级平均水平之上。”*卡森·麦卡勒斯:《没有指针的钟》,第7页。优秀的成绩成为犹太人头脑聪慧的标识,而勤于哲理性思考和拥有过人的艺术天赋,更成为犹太人富有智慧的象征。《心》中的布瑞农虽然只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但他不停地思考战争、生活以及有关生死的重大哲学问题,使其看起来“像德国的犹太人”*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215页。,带有犹太人喜深思的特有印征。在《神童》中,犹太人海密是一位被称为神童的小提琴家,他才华横溢,十三岁时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不但演奏技巧纯熟,而且能够体悟到音乐本身所蕴涵的精神旨趣,在音乐中实现了精神的超越与升华。这些犹太人所拥有的超常智慧,使他们身上散发出浓厚的神秘气息,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其独特文化的想象空间。
其次,对犹太人饮食习惯的神秘化描写。作为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饮食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浸透着浓厚的社会属性,从最日常最细微的维度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创造精神和文化风貌。犹太人的饮食因受犹太教饮食教规的影响而呈现出禁忌多与规矩多的特点,与非犹太教徒的饮食习惯有着巨大差异,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犹太民族独特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莫里斯范因斯坦与一般美国南方人的饮食完全不同,他“每天都吃发得很松的面包和罐头鲑鱼”*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第7页。,而面包和罐头鲑鱼是美国南方人很少食用的食品。因而,在美国南方人眼中,他的这种日常饮食就显得甚为特殊怪异,而他每天都如此的行为更是让他们迷惑不解,认为他的饮食内容与行为都充满了怪异和神秘的色彩。《心》中的哈里家“吃的是地道的犹太食品”*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254页。,所以当米克与其去郊游野餐时,认为他会带像冷猪肝布丁这样带有东方情调的食物,将犹太人的食品风格赋予了带有异国风情的东方色彩。在对犹太人饮食习惯的行文描述中,作者着重突出的是食物与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的紧密相联性,使日常食物沾染上宗教和民族色彩,成为彰显宗教、民族与文化差异的符号。在此,民族文化的宏观差别通过食物的微观差异而变得一目了然,犹太人的饮食习惯不再是纯粹的日常与普通的饮食习惯,而是承载着宗教、民族与文化特性的特定习惯,不断地散发着独特、古怪与神秘的气息,引发了美国南方人的无限遐思。
第三,对犹太人生活习俗的神秘化描写。当对犹太裔进行文化再现时,麦卡勒斯“以浪漫的笔触赋予了犹太人以超脱尘世的身份特征”*Hershon, Larry: “Tension and Transcendence: ‘The Jew’ in the Fiction of Carson McCullers”, 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September 22,2008.p.57.,将其日常的生活习俗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生活习俗方面,因为《心》中的斯伯尔瑞布斯将道听途说的习俗安置在犹太人身上,以为当一个犹太男孩出生时,家人会在银行给他存一块金条,因而追问哈里金条的事情。米克也很“珍视对犹太人生活所持的浪漫观点”,当她通过窗户看到忙于工作的哈里母亲时,觉得她充满了神秘感,无论何时都是“你看她时,她从不抬头”*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262页。。在此,借助“看”这个动词,米克将看者与被看的对象区分开来,进而建构起自己有别于被看者的身份。通过这种看者的姿态,她站在自身文化立场上对犹太裔加以品评,进行言说和单向诠释,使被看者变成了受限于沉默的“他者”。在她眼中,犹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是迫于生计的忙碌行为都充满了浓厚的异族特质,带给她一种陌生与新奇的情感体验,勾起了她强烈的好奇心与无穷的想象力。
四、“他者”想象背后的深层动机
麦卡勒斯在对黑人、菲律宾人和犹太人等少数族裔进行描述时,既富含同情和赞赏,又深怀恐惧和蔑视,使其话语表现方式充满了张力。但是,她对这些形象的品质断定,却彰显出其创作中“隐蔽的东方主义”倾向,映射出其维护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的深层动机。这种东方主义倾向,一方面是美国试图将东方作为自我映照的镜鉴,反省自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这种对比中进一步确认和强化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和民族文化自信,借以构建起美国拯救东方的救世主形象;当然,这也极大地满足了西方对东方的猎奇心理。
首先,“他者”想象是为了印证美国的自我形象。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南方社会的重大问题,根源在于白人主流意识形态内在价值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它高举人道主义的精神旗帜,宣扬民主、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在现实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却处处设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樊篱,不断对少数族裔进行排斥、限定和迫害。正是由于认识到美国社会的这一顽疾,麦卡勒斯尝试将少数族裔作为反省美国主流文化的一个参照系,力图通过他们的“缺陷”来反省和审视白人自身存在的不足。白人极端种族主义者认为,白皮肤是与生俱来的社会身份,并借此界定了一系列诸如政治、文化和权力等各方面的种族边界,显示出美国南方社会种族伦理的矛盾、狭隘与偏激。作为社会文化的守望者,麦卡勒斯对“各地发生的种族冲突越来越关注”*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第545页。,不断地质疑现存种族伦理秩序的合理性,同时历史地反思产生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深层根源,为探析美国60年代城市权利运动大规模爆发的原因提供了思维路向。
其次,“他者”想象是为了建构起美国作为拯救东方的救世主形象。欧洲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向来将“把落后、野蛮的民族从无知的蒙昧中拯救出来,并帮助他们祛除由于人种缺陷和文化落后所造成的瘤疾”*刘惠玲:《话语维度下的萨义德东方主义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第57页。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即使是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以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居高临下地对东方进行审视,总是把东方看作有待帮助或照料的对象,需要进行所谓的人文关怀与扶助。在麦卡勒斯对菲律宾人的想象建构中,她沿用了西方这一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对东方民族进行解读和审视,将其描述为与美国人截然相反的“他者”存在——完全缺乏自主能力,必须仰仗强大的美国加以救赎,而美国也在这种施救中完成了救世主形象的自我建构。
第三,“他者”想象是为了满足美国对东方的猎奇心理。遥远的东方在美国人眼中充满了异国情调和神秘色彩,在猎奇心理的驱使之下,激发起他们关注和追寻的极大热情,急于将他们捏造出来的知识强加于东方。在这种东方主义想象中,东方被建构成了具有新奇、怪诞和神秘等本质特征的“他者”,被界定为与美国迥然不同的、陌生的存在,这一想象体现了西方对东方、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主体与客体、注视与被注视的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对东方民族的客观认知。犹太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弱小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他们虽然历经浩劫,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涌现出众多杰出伟人,对世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其成为非凡智慧和超越精神的象征,整个犹太民族也因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麦卡勒斯作品中对犹太人精神智慧特征的渲染与放大,以及对其生活习俗的陌生化描写,既是对异域民族文化的浪漫化处理和想象,也是对异域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虚构,契合了美国人对东方的集体想象,有编造风情与附和东方主义神话的趋势。
尽管麦卡勒斯不是一位显在的东方主义作家,也没有显在的东方主义意图,但“在想象文学中都有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体系在较自由的表层下运作”*萨义德:《东方主义再思考》,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第18页。,将人类分为进步与落后的“种族分类就是隐蔽的东方主义的一种自愿合作”*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谢少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5页。,她作品中“隐蔽的东方主义”倾向使其东方主义立场昭然若揭。这种“隐蔽的东方主义”倾向,既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长期涵化的结果,也是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在文学中的无意识表征,体现出了文学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关联特性。因而,对麦卡勒斯作品中“隐蔽的东方主义”倾向的剖析,不仅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其文本进行文学解读,还深蕴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社会思想意义。
[责任编辑:诚 钧]
Racial Writing of the Imagining “the Other”: The Analysis of the Tendency of the Latent Orientalism in Carson McCullers’s Novels
SHANG Yu-cui
(SchoolofHumanities,YantaiUniversity,Yantai264005,China)
American southern writer Carson McCullers focuses on issue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s. Although her project is antinationalist, she describes the black, the Filipino, and the Jew as orientalism othe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rientalism, this thesis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tendency of the latent Orientalism to reveal deeper motives.
Carson McCullers; the other; racial writing; the latent Orientalism
2014-09-20
尚玉翠(1977- ),女,汉族,山东东营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I
A
1002-3194(2015)02-008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