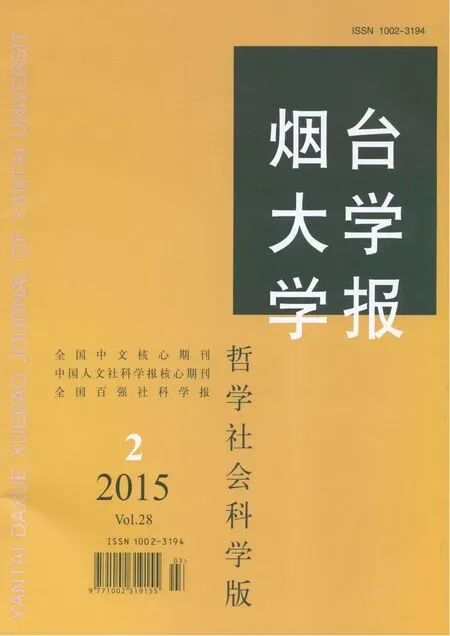“艺术惯例论”:早期版本与晚期版本
乔治·迪基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美国 芝加哥 60612)
“艺术惯例论”:早期版本与晚期版本
乔治·迪基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美国 芝加哥 60612)
在分析美学史当中,“艺术惯例论”给艺术的定义在实践中具有说服力而得到了普遍赞同,但却因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而倍受批评。这就需要面对批评对惯例论进行不断修订,形成了“艺术惯例论”的两个版本。早期版本认为,艺术是:(1) 一件人工制品;(2) 一系列方面,这些方面由代表特定社会惯例(艺术界中的)而行动的某人或某些人,授予其供欣赏的候选者的地位。晚期版本认为,艺术是:(1) 它必须是件人工制品;(2) 它是为提交给艺术界的公众而创造出来的。其中,“艺术家”是理解一个艺术品被制作出来的参与者;“公众”是一系列的人,这些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准备去理解要提交给他们的物;“艺术界”是整个艺术界系统的整体;一个“艺术界系统”就是一个艺术家将艺术品提交给艺术界公众的构架。
乔治·迪基;艺术惯例论; 早期版本;晚期版本;分析美学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2.001
为曼德尔鲍姆(Mandelbaum)的文章与丹托(Danto)的更早文章里的观念所导引,从1969年的“界定艺术”这篇文章开始到1974年《艺术与审美》这本专著为止,我做了艺术惯例论的两种早期版本的前期工作。作为对早期版本的各种批评的回应,我给出了重大的修订,而且我认为,惯例论的看法在我1984年的书《艺术圈》里得到了推进。我将对这两种版本都给予考虑。
传统的艺术理论将艺术品置于简单与狭隘聚焦的关系网络当中。例如,模仿论暂时把在三维网络当中的艺术品置于艺术家与主题之间,而表现理论则将艺术品置于艺术家与作品的两维网络当中。惯例论的两种版本都试图将艺术品置于多维网络当中,它较之各种传统理论所设想的任何东西而言都拥有更大的复杂性。传统理论的网络或者语境太过“单薄”以至于是难以胜任的。惯例论的两种版本试图提供出一种“厚重”的语境,以足以去应对这份工作。一种理论将艺术品置于其中的关系或者语境的网络,我会称之为这种理论的“架构”(framework)。
所有的传统理论都假设,艺术品是人工制品,尽管它们与人工制品的本质有所区分。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惯例的方法就是一种对于传统艺术理论化方式的回归,因为在两种版本当中,我始终坚持艺术品都是人工制品。我所意谓的“人工制品”就是通常辞典的定义:“一个被人所造的对象,特别伴随了一种作为结果而使用的观点。”进而,尽管许多艺术品并不需要是物理对象,例如诗歌就不是物理对象,但是它却是人工制品。再者说,诸如表现之类的事物,例如即兴创作的舞蹈,也是“被人所造”的因而是人工制品。
以任何表面的方式,极大数量的人制艺术品的制品并不存在未解之谜;它被按照各式各样的诸如绘画、雕刻此类的传统方式被人工制造出来的。然而,某些相对晚近的艺术品存在着人工性(artifactuality)的迷惑:杜尚的现成物(readymade),现成艺术(found art),如此等等。有人因而否定此类东西是艺术品,因为他们宣称,它们并不是被艺术家所制作的人工制品。我认为,能被展示出来的就都是,它们就是艺术家的人工制品。在杜尚现成物及其类似物的例证当中,两种版本在如何获得人工性的方面是有差异的。
一、艺术惯例论的“早期版本”
艺术惯例论的早期观点可以用我在1974年《艺术与审美》一书当中的如下定义加以总结:
(1) 一件人工制品;(2) 一系列方面,这些方面由代表特定社会惯例(艺术界中的)而行动的某人或某些人,授予其供欣赏的候选者的地位。*George Dickie, Art and Aesthetic,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4.
在早期版本当中,“授予地位”(conferring the status)是核心的观念。授予地位的最明显与清晰的例证就是合法地位被包含在内的某种国家行为。某位国王授予了骑士爵位,或者见证人宣称结为夫妻的活动,都代表了某一体制(国家)被赋予了合法地位。博士学位是通过大学授予给某人,或者某个人或者某些人通过授予非合法的地位而选举某人作为劳特莱(Rotary)的主席也是个例子。早期的“艺术品”惯例定义所建议的,恰恰就像是两个人能够获得与某个合法系统联姻的地位,并且就像某人能获得成为劳特莱主席的非合法地位一样,某件人工制品在被称为“艺术界”(art world)的文化系统当中能够获得供欣赏的地位。
然而,根据早期的版本,供欣赏的候选者地位是被授予的吗?某件人工制品被悬挂在博物馆当中被当作某一次展示或者戏剧表演的一部分,那么,它就确实是已经被授予了地位的符码。有两个例子似乎暗示出,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在这个问题里被真实授予了地位。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去制造出艺术界的文化惯例(cultural institution),但是仅有一个人需要作为艺术界的代理人而代表艺术界去实施,并去授予供欣赏的候选者以地位。在这个问题里的地位,典型地需要通过“单一的个人将某个人造物当作某个供欣赏的候选者”而得以实现。当然,没有人阻止某一群体的人们去授予地位,也就是像艺术家那样行动,但这通常是被单一的个人所授予的,其中的艺术家就是创造人造物那个人。事实上,许多的艺术品从来都不是被任何人——除非是创造出它们的人——所如此看待的,但是它们仍然是艺术品。
你可能会感觉到,在早期版本的构想当中,艺术界当中的授予地位的观念是相当模糊的。确实,这种观念作为在合法系统当中的地位授予并不是明晰的,在此程序与权威的线索被明确地界定或者整合在法律当中。艺术界的对立面将(没有地方被加以法规化的)程序与权威的线索加以特殊化,艺术界在惯常实践的水平上就实现了自身的事业。仍然存在着一种实践,它定义了一种文化惯例。这样一种惯例并不需要在形式上去建构章程、高级职位与规章制度以获取存在,而且它们拥有了授予地位的能力。某些惯例是形式的,而某些惯例则是非形式的。
现在考虑欣赏的观念。在早期的版本当中,“艺术品”的定义所言说的是供欣赏的“候选者”的地位授予。关于真实的欣赏没有什么可说的,而它所允许的是艺术品不被欣赏的可能性。重要的不是去建构“艺术品”的“分类”(classificatory)意义上的定义,该艺术品拥有诸如真实欣赏的价值属性;这样做是为了让言说非供欣赏的艺术品变得不可能,而且难以去言说坏的艺术品(bad works of art),而这明显是不受欢迎的。任何艺术理论都必须保存特定的核心特征,按照这种方式谈论艺术,我们发现必要的是,某些时候要去言说非供欣赏的艺术与坏的艺术。这也要注意到,并不是某件艺术品的每个方面都包括在供欣赏的候选者当中。例如,某一绘画的黑色通常并不是供欣赏的某个对象。读者将意识到的问题是,某一艺术品的方面是要被包括在供欣赏的候选者当中,这在第一部分当中已经论述。
惯例论的早期版本并不包含某种特殊类型的“审美”欣赏。在第一部分当中已经认定,并不存在特殊类型的审美欣赏,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存在某种特殊类型的审美欣赏。在早期的定义当中,“欣赏”所全部意指的就是,诸如“在经验某物的特质的时候某人发现其值得欣赏或者有价值欣赏”的那些东西。
艺术惯例论的两个版本已在头脑当中有意识地被艺术界之实践所实施——特别是在大约近百年的发展当中,这些艺术实践如达达派、波普艺术、现成品艺术与偶发艺术之类。惯例论与这些发展提出了相当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当中的一些问题在此要得到解决。
首先,如果杜尚能将一个小便器、一只雪铲与一个挂帽钩转化为艺术品,那么,诸如浮木的艺术品不也能同样会成为艺术品吗?如果许多东西当中的任何一个这样做会成为艺术,那么,如小便器这样的对象就能成为艺术品。一件要成为诡计的东西,是从自然物选择出来被带回家并悬挂在墙面上。另一个东西则被选择出来并带入到展览馆中。这就被假定了维茨(Weitz)早期的关于浮木时所参照的是在河滩的一种日常情境且并未被人类的手所触动的判决。请记住,某个东西成为分类意义上的艺术品,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具有了任何真实的价值。根据早期版本,自然物要成为艺术品所依据的是正在被讨论的方式——它是不使用工具而人工化的——人造物被授予为对象,而非人造物制造出了对象。当然,即使这是真的,在艺术品的大多数的例证当中,人工性依据按照某种方式被制造从而得以实现。因而,根据早期的版本,人工性就被实现在两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当中:通过被制造,或者通过被授予。在诸如杜尚的《泉》的现成物的例证当中,一件与水管连接的人工制品拥有被授予的艺术化的人工性,而且这就是一种双重的人工制品。
请注意,根据早期的版本,这两种相当不同类型的东西能够被假定从而被授予了:被授予为人工性与欣赏的候选者。
其次,与艺术观念的讨论相关的经常出现的问题,它似乎特别关涉于惯例论的语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设想诸如贝琪(Bestsy)这样来自于巴尔地摩动物园的黑猩猩”?在此,称黑猩猩贝琪制造了“绘画”并不意味着对其采取歧视态度而它们并不被当作艺术品;这恰恰在于,某些词语需要以它们作为参照。贝琪的绘画是否是绘画的问题,它所依赖的是对它们做出了什么。例如,在芝加哥的自然史的地方博物馆,某次展出展示了某些黑猩猩与大猩猩的绘画。在这些绘画的例证中,我们必须说,它们并不是艺术品。然而,如果它们被在许多公里外的芝加哥美术馆中展出来,它们就“能”成为艺术品——如果在美术馆的某个人,如此这样认为,通过肢体制造出来,那么它就“能”是艺术。这全部依赖于惯例的境遇——某个境遇令人愉悦而成为艺术创造而另外的语境则不能如此(在言说惯例的境遇过程当中,我所参照的并不是诸如此类的美术馆而是一种惯例性实践)。根据早期的版本,使得贝琪的绘画成为艺术品的东西,能被某些执行人进行人工性的授予,并代表艺术界而授予其欣赏的候选者的地位。尽管事实上黑猩猩贝琪并不是在绘画,由此得到的艺术品并不会是黑猩猩贝琪的绘画,但却是并未授权的某人的作品。黑猩猩贝琪并不能被授权,那是因为,它并没有将自己看作是艺术界的执行人——它不能(全面地)参与到我们的文化当中。
维茨认定,艺术的定义或其亚概念无视于创造性。某些传统的艺术定义可能已经无视于创造性,某些传统艺术定义的亚概念也无视于创造性,但是,艺术惯例所考虑的两种版本却都没有无视于此。既然人造性就是创造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对于人造性的需求很少能保护创造性。没有某类被生产出来的人造物,如何能存在一种创造性的例证呢?早期版本的其他需求包含了对欣赏的候选者之地位的授予,却不能抑制创造性;事实上,它激发了创造性。既然几乎所有被用以制造艺术的任何东西都是可能的,这种定义就没有给创造性强加限制。在艺术的某些亚概念已经无视于创造性上面,维茨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的危险在于过去存在的东西。随着对已建立的类型(genres)的忽视和对艺术中新奇寻求的喧闹,对创造性的阻碍可能不再存在了。今天,如果一个崭新的或不寻常的作品被创造了出来,那么,它就同某些业已建立起来的种类(type)是相当类似的,进而它提出会被整合在这种类型当中,或者新的作品与任何存在的作品都决然不同,那么,一个新的亚概念就可能被创造出来。今天的艺术家不会轻易地退缩,他们将艺术类型视为是松散的指导原则,而非严格的详尽说明。
艺术惯例论的早期版本听上去是这样说的:“一件艺术品是某人所说的那个对象:‘我将授命这个对象为艺术品。’”这好像是如此;按照早期版本的假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承认艺术是个简单的问题。就像在教堂的历史与结构的背景当中给个孩子洗礼一样,成为艺术也要有其艺术界的拜占庭式的复杂背景。有人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很奇怪,在被讨论的非艺术例证当中,存在着授予错了的情况,然而,按照这种方式,这种情况却没有出现在包括能被视为无限的生产艺术在内的授予当中。例如,某一份起诉书或许起草的并不合适,但是被告人也不会事实上被起诉。但类似的情况在艺术例证当中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实反映了艺术界与法律体制之间的差异。法律系统去处理的是有严重个人后果的事情,其程序必定反映了这一点;艺术界也应对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是完全不同的那种类型。艺术界并不需要严格的程序;它允许甚至鼓励轻浮与任性,只要不失其严肃的目的。然而,如果在包括生产艺术在内的授予过程当中不可能犯错误,那么,错误就可能通过授予欣赏以候选地位而犯下。在将艺术地位授予某个对象时,某人就假定,在其新的地位上对该对象负有某种特定种类的责任;为欣赏而呈现出来的某一候选者始终面对了这种可能性,亦即没有人欣赏它,而授予地位的那个人将因此而丢脸。某个人可以做出“无米之炊”的艺术品,但却没有必要一定将之做成丝绸钱包。
二、艺术惯例论的“晚期版本”
我相信,惯例论的早期版本因此在某些方面是有失误的,但是,惯例论的方法,我认为始终是切实可行的。在早期版本当中,我宣称,我错误地认定人造性是被诸如杜尚的《泉》和现成艺术所授予地位的。我现在则相信,人造性并不是那类能够被授予地位的东西。
通过转化为某些前存在(preexisting)的物质:通过加入到两种物质里面,通过去除某些物质,通过塑形为某些物质等等诸如此类,一件人造物被典型性地生产出来。这通常所做的是为了转化物能被用以去做某些东西。当物质是能被如此转化的,有人已经清楚了这个例证匹配于辞典里面“人造物”的定义——“一个被人所造的对象,特别伴随了一种作为结果而使用的观点。”其他的例证很少是如此清晰的。假定某人选择了一块浮木而没有将之转化,用来去挖个洞或者在有威胁的狗面前挥舞。再假定这块未被转化的浮木,已经被“制成”了被用以置入其中的挖掘工具或者武器。这两个例证都没有确定去界定“特别伴随了一种作为结果而使用的观点”的非必要条款。因为它们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被制定去提供服务。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并不存在某物在这些例证当中被制成的情况。然而,如果浮木未被转化,它是如何被做成了什么东西的呢?在明晰的例证当中,物质是被转化的,一个复杂的对象被生产了出来:原初的物质是为了当前的目的而成为一种简单的对象,它正在被转为从而生产出复杂的对象——被转化的物质。在这两个缺乏清晰的例证当中,复杂对象已经被制造了出来——木头被用作挖掘工具或者木头被用作武器。在这两个缺乏清晰的例证中,浮木都不会是人工制品;人工制品在这两个例证当中都是被以特定方式制造与使用的浮木。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两个例证,确实都类似于某类人类学家们在头脑中的东西,人类学家们言说,那些非转化的石头被发现是与人类相关的,或者被发现是作为人造物同人近似的化石。人类学家们将这些被按照某种方式使用的石头包括进来,也就是将石头的特定标记,被当作痕迹遗留在石头上被加以使用。人类学家们在头脑中有了复杂对象的同样观念,这些复杂对象通过某一简单(亦即未被转化的)对象的使用而被制造出来的。
在艺术界的语境当中,一块浮木可能是被以一种类似的方式使用的,亦即按照绘画与雕塑所展示的那种方式被选择与展示出来。这样一块浮木就会被用以作为艺术媒料(artistic medium)而加以使用,因而它就会成为更复杂对象的一部分——“被当作某种艺术媒材使用的浮木”。这个复杂对象就会是某个艺术界系统当中的一个人工制品。杜尚的《泉》能按照同样的线索而被理解。小便器(简单对象)被用以当作一个艺术媒材以制造出《泉》(复杂对象),它就是出于艺术界的一件人造物——杜尚的人造物。浮木和小便器会被以诸如此类的方式当作艺术媒体被使用,按照颜色、大理石那种被使用得更为传统的艺术品方式。浮木被用以当作武器,小便器被用以当作成为极少类型的艺术媒材。杜尚并没有去确定人工制品,他所制造的是极少的人工制品。
早期看法的第二个困难是被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所指出的。他观察到了围绕着理论的早期版本中定义的讨论,我将艺术界的特征化为一种“已被建构的实践”(established practice),一种非正式类型的行为。他在形成观点的时候,在引用定义那里,使用了诸如“授予地位”与“代表而行动”这样的短语。此类的短语典型地是应用在正式惯例里面的,这些体制是诸如国家、企业、大学此类。比尔兹利正确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对正式惯例的错误语言使用,它力图描述的是我所设想的艺术界的那种非正式惯例。比尔兹利质疑说:“这意味着去说要代表一种实践的行为吗?地位获得的权威性可以聚焦(于一种正式惯例),但是诸如此类的实践,似乎缺少权威性所必需的资源。”*“Is Art Essentially Institutional?” in Culture and Art, Lars Aagaard-Mogensen, ed.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1967, p. 202.
接受比尔兹利的批评,我已经禁用了太过于正式化的“授予地位”与“代表而行动”这样的观念,同时,也禁用了与这些观念相关的早期版本的某些方面。成为一件艺术品就是占有正确的地位,亦即就是占有在艺术界的人类行为之内的某个地位。然而,成为一件艺术品却并不包括被授予的某个地位,而毋宁是获得了某个地位,在艺术界的背景中或者反对艺术界的背景中,这种地位是作为创造某个人造物的结果而存在的。
早期版本宣称(正如晚期版本所做的那样),艺术品是作为在某个已被建构的实践(亦即艺术界)当中所占据的地位或者地点的结果而存在的。关于这个宣称存在两个关键问题:这是宣称的真实吗?如果这个宣称是真实的,那么艺术界该如何被加以描述呢?
这就是关于人类惯例存在的那种宣称,对其真实性的检验与关于人类组织的其他宣称——对于观察的检验——也是同样的。然而,“观看”艺术界与艺术品被整合在其结构当中,这并不像“观看”某些其他人类惯例那么容易,这些惯例是更被习惯化而加以思考的。
丹托的视觉难以识别的对象(visually-indistinguishable-objects)的观点,展现出艺术品存在于某一语境或者架构当中,但是,它并没有揭示出制造出架构之要素的本质。进而,许许多多的不同架构都是可能的。例如,每一种传统艺术论都暗示出其自身的特殊架构。举个例子,苏珊·朗格(Susan Langer)“艺术是人类情感的形式符号的创造”的观点,就暗示出了(作为做出创造行为的人的)艺术家的某一架构与某一特定类型的主题(人类情感)。然而,朗格的理论与其他传统理论,很容易遇到反例,而结果就是,并不存在它们暗示出能成为正确的那种架构。传统理论容易遭遇反例的理由在于,这个架构通过理论暗示出它太过狭隘地聚焦于艺术家和更具有明显特征的艺术品,而非环绕着艺术品的“一切”架构的要素。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太容易发现艺术品,而这艺术品缺乏被作为普遍性与定义性的某一实践传统理论所捕捉的特质。
传统理论的架构在这一方面指向了正确的方向。每种传统理论都设想,把艺术制成人类实践,这种实践是作为行为的某种被建构的方式。结果就是,每种理论的架构都设想,通过实践及其重复的坚持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我认为,这种对于作为文化实践的某种架构的坚持已经足够了,它使得传统理论自身成为了准惯例的(quasi-institutional)。然而,在某种传统理论当中,并不存在仅仅一种被建构的想象角色,它就是艺术家或者人工制品制造者的角色。而且,在每一个例证当中,艺术家都被视为某一人工制品的创造者,他们作为代表、造就符号或者成就某种表现是适宜的。对于传统的理论而言,艺术家的角色被简单地设想为产生再现、产生符号形式、产生某种表现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艺术家角色的狭隘观念,是对能够被产生出来的容易出现的反例而负责的。尽管传统理论是不足的,对于艺术家角色一定存在着更多不足,较之为传统理论设想所产生出的任何甚至全部这些种类的东西而言都有更多不足。当某位艺术家创造一件艺术品的时候,他所理解与所做的东西,就超出了被传统理论所导致的那种简单理解与所做的东西。
无论艺术家何时创造出艺术,它始终是为了“公众”(public)而创造的。结果就是,架构必须包括为了“公众”的某个角色,而艺术则是呈现给观众的。当然,由于各式各样的理由,许多艺术品事实上并不是呈现给任何观众的。某些艺术品恰恰是不再抵达观众那里的,尽管它们的制作者意在这样做。某些作品通过它们的创造者而从观众那里退出,这是由于,它们以某种低级方式判断这些作品并不是值得被呈现的。事实是,艺术家使得某些艺术品得以退出,因为他们判断作品是不值得呈现的,这种呈现就展现出作品是某“种”被呈现的东西,否则就判断作品无意义而不值得呈现的。因而,即使艺术并不意在为假定面对观众而呈现给观众,因为它可能并不仅仅是为观众而呈现的(正好某些时间所发生的那样),它也是某类具有呈现给公众目的的东西。公众的观念始终盘旋在这个背景上面,即使当被给定的艺术家拒绝呈现他或者她的作品。在这些例证当中,艺术品从观众那里退出,可能存在着被称为“双重意图”(double intention)——存在着一种意图是创造出被呈现的某一类的东西,但是,同样存在并未被事实上得以呈现的另一种意图。
什么是某一艺术界的公众呢?它并不只是人们的集合。某一艺术界公众的成员,他们知道如何去填充角色,这个角色需要知识与理解,这与艺术家所需要的许多方面是类似的。面对不同的艺术存在着各类不同的观众,为某类观众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同于为另类观众所需要的知识的。在所扮演阶段的观众所需要的一些知识,就是要去理解某个人所扮演的那个部分。任何被给定的公众成员都拥有非常多的那一些此类的信息。
艺术家与公众角色是艺术创造的最小的架构,而这两个相关的角色可以被称为“呈现的团体”(the presentation group)。艺术家的角色具有两个核心方面:首先是所有艺术家的普遍方面的特征,亦即意识到被呈现而成为艺术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其二是使用一种或者更多的更广阔与多样的艺术技巧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得某人创造出某一特殊类型的艺术。同样,公众的角色也具有两个核心方面:所有公众的普遍方面的特征,亦即意识到被呈现而成为艺术的东西,其二是能使某人感知与理解到被某人所呈现出来的某种特定类型的艺术所需要的能力与感性。
几乎在每一个现实社会当中,都存在某一艺术制造(art-making)的惯例,此外,对于艺术家与公众角色而言,存在着许多的补充艺术界的角色,诸如批评家、艺术教师、导演、策展人、制片人,还有更多的角色。呈现的团体就是相关联的艺术家与公众的角色,然而,这几组角色成为了艺术制造的基本架构。
在对早期版本的更频繁的批评当中,难以展现出艺术制造是惯例性的,因为这难以展现出艺术制造就是被规则所统治的。对于批评的基础性假设就是它是具有规则统治性的,惯例实践诸如承诺与非惯例的那种诸如遛狗是彼此不同的。真实的是,早期版本并没有带来艺术制造的规则统治性,这就需要被加以匡正。在早期的著作所发展的理论当中,存在着明晰的规则,但遗憾的是,我却没有使得它们变得清晰。在讨论使得艺术制造明晰的规则统治当中,早期理论并没有形成观点,但是,那些呈现使被修订的理论是可以被陈述出来的。早期我认为,人工性并不成为艺术品的必要条件。这种必要性的宣称暗示出艺术制造的一个规则:如果某人希望去制造一件艺术品,这个人就必须通过创造出人工制品而这样做。我同样也宣称,成为被呈现给艺术界公众的某类东西,就是成为艺术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个宣称必要性地暗示出,艺术制造的另一个规则:如果某人希望去创造出艺术品,这个人必须通过创造被呈现给艺术界公众的某类东西而这样做。存在两种相互关联的规则就已经足以制造出艺术品。
问题很自然地出现了:为何这种架构被描述为惯例性的那种,它并不是正确的基本架构,而是某些其他的架构?传统理论的架构很明显是不足的,但是他们的不足并没有证明惯例论当前版本的架构的正确性。证明这种理论正确是相当困难的,尽管证明这个理论错误有时是非常容易的。对于惯例论的当前版本而言,可以言说的是,这就是架构的观念,其中艺术品很明显是被整合在其中的,而没有其他貌似合理的架构是即将出现的。由于缺少更有说服力的论点,惯例论的架构就是正确的那种,我会依赖于对其的描述,我已经赋予了这种论点及其正确性以功用。通过这种描述是正确或者是如此适合的,那么,它就会在听者那里激发起“这是正确”的经验。
在早期版本当中,我谈论到了大量关于惯例的问题及它们是如何被整合在艺术惯例当中的。我尽力区分出我所谓的“首要惯例”(the primary convention)与其他的“次级惯例”(secondary conventions),后者是被包孕在艺术的创造与呈现当中的。举个例子,这里所讨论的所谓次级惯例是西方戏剧惯例隐藏在场景背后的舞台工作人员。西方艺术惯例是与古典中国戏剧的惯例相对而言的,中国戏剧舞台工作人员(被称为道具管理人)在演出的过程同道具与场景的更换过程是同时出现的。这就对同一任务的不同戏剧解决方式,亦即对于舞台工作人员的雇佣,带来了惯例的一种基本特征。任何做出某物的惯例方式,都能够被按照不同的方式做出来。
难以实现的是,正在被讨论成为惯例的这类东西,能够在混淆的理论当中得出结果。例如,西方戏剧的另一种惯例就是,观众并不参与到表演行为当中。特定的审美态度理论也难以实现,这个特殊的惯例就是一种惯例,它包括了观众的非参与就是一种从审美意识而来的规则,这种规则必定是不被冒犯的。此类的理论为彼得·潘所颠覆,潘所需要的是观众成员鼓掌以拯救小仙子小铃铛(Tinkerbell)的生命。然而,这种需要仅仅被算作是对于小孩的新惯例的引入,但是,某些美学家们却并未按照正确方式来把握它。
存在着难以统计的惯例,它们被包含在艺术的创造与呈现当中,但是正如我在早期版本当中所宣称的那样,其中某些并不是“首要的”惯例,而所有其他的惯例则都是次级的。事实上,在早期的版本那里,我所宣称的,不仅仅是存在许多被包含在艺术的创造与呈现当中的惯例,而且整体行为的基础部分都完全是惯例性的。但是,戏剧、绘画、雕塑,诸如此类的东西,都并不是能按照其他方式为之的而做出某物的方式,因而,它们就不是惯例性的。然而,如果“首要的”惯例并不存在,那么就存在着首要的“某物”,难以统计的惯例在其中是拥有某种地位的。何谓首要的,这就对所有被包含在其中的东西加以理解,而在其中,他们致力于去建构行为或者实践,其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角色:艺术家角色、公众角色、批评家角色、导演角色、策展人角色,如此等等。我们的艺术界包含了这些角色的总体,其中艺术家和公众的角色是居于核心的。在某种程度上,用更为结构化的方式加以描述,艺术界包含着一系列的个体化的艺术界系统。例如,绘画就是一个艺术界系统,戏剧则是另一个,如此等等。
于是,艺术的惯例就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规则。存在着的惯例规则,它们来自于为呈现与创造艺术所执行的各式各样的惯例那里。这些规则是反对改变的。存在着支配所致力于的行为中的更基本的规则,而这些惯例并不是惯例性的。人工制品的规则——如果某人希望去制造一件艺术品,这个人必须通过创造出人工制品而这样做——这就不是惯例性的规则,它所陈述的只是致力于某种特定实践的某个条件。
正如我早期所言及的,人工制品规则与其他的惯例规则是不足以创作出艺术品的。而且,正如每一个规则都是必要的,它们都被用以形成“艺术品”定义的公式:
一件艺术品就是那种被创造出来而呈献给艺术界观众的人工制品。
这个定义明确地包括了“艺术界”与“公众”的术语,而且它同时也包括了“艺术家”与“艺术界系统”观念。我现在将这四个要素定义如下:
“艺术家”是理解一个艺术品被制作出来的参与者。
“公众”是一系列的人,这些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准备去理解要提交给他们的物。
“艺术界”是整个艺术界系统的整体。
一个“艺术界系统”就是一个艺术家将艺术品提交给艺术界公众的构架。*George Dickie, The Art Circle, New York: Haven Publications, 1984, pp.80-82.
这五个定义提供了艺术惯例的极少的可能性描述,因而这也是对艺术惯例论的极少的可能考虑。
要预先阻止对“艺术品”定义的反对意见,这让我意识到,存在着被创造出来以呈现给艺术界观众的人工制品,但它们并不是艺术品:例如戏剧海报。然而,这类的东西对于艺术品而言就是寄生的与次级的。艺术品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首要类型的人工制品,戏剧海报与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独立于艺术品的,在这个领域内部,人工制品都是次级的类型。在此定义当中的“人工制品”一词,要依据首要类型的人工制品而加以理解。
早期版本当中给出的“艺术品”定义,尽管并未如此严格地说,我已经意识到它是一种循环论证。“艺术品”定义恰恰也是被循环论所给出的,尽管也未如此严格地说。在事实上,这五个核心术语的定义包含了一种术语链的逻辑循环。
存在一种理想的非循环论证的定义,它假定:在定义中所使用的术语意义,并不会将术语退回到原初的界定那里,但是会成为或者导向更为基础性的术语。非循环论证的理想定义同样假定,我们能达到具有首要意义的术语,这些术语能按照某些非定义的方式而被认知,这意味着,通过直接的感性经验或者理性直觉而得到。存在某些系列的定义满足这个理性,但是,惯例论的对于五个核心术语的定义却并非如此。这难道意味着观念论包含着严格的循环论吗?定义的循环论展现出核心观念的相互支撑。这些核心观念是“屈折变动的”,亦即它们是相互投合、相互假定与相互支持的。定义所揭示出来的就是,艺术制造包括了一种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结构,它们不能按照直接的方式而加以描述,这种线性的方式是通过理想的非循环定义而得以设想的。艺术的屈折变动的本质,通过我们从艺术当中得以学习到的那种方式反映出来。学习有时是通过被教育如何成为艺术家而达到通途的,例如学习如何画出一幅能被展示的绘画。这种学习有时是通过被教育如何成为艺术界观众中的成员而达到通途的——学习如何观看被作为艺术家意图生产而被展出的绘画。这两个通途同时全部教给我们关于艺术家、作品与公众的观念,这些观念彼此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我怀疑,在文化疆域当中的许多领域都拥有与艺术惯例同样类型的屈折变动的本质——例如包括“法律的”、“合法的”、“执行的”与“司法的”观念。
非循环的理想定义也同样把握到了不能提供有用信息的系列循环定义。这可能对于某些系列的定义是真实的,但也并非如此,我认为,这就是惯例论定义的真实性所在。因为这些定义恰恰是相互独立的项目之镜像,这些项目组成了艺术的事业。进而告诉了我们其屈折变动的本质。
近些年来,杰罗尔德·列文森(Jerrold Levinson)、*Jerrold Levinson, “Defining Art Historicall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19 (1979), pp. 232-250; and “Extending Art Historically,”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1 (1993), pp. 421-422.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Noel Carroll, “Art, Practice, and Narrative,” The Monist, 71 (1988), pp. 1140-56;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1 (1993), pp. 313-326; and “Identifying Art” in Institutions of Art ed. Robert J. Yanal,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38.、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s)*Stephen Davis, Definitions of Art,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43.,还有其他人已经提出了他们的艺术理论,或者关于艺术的理论的结论,这是相关于艺术惯例论的一种或者另一种方式。
[责任编辑:刘春雷]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the Earlier Version and the Later Version
George Dickie
(UniversityofIllinois,Chicago60612,U.S.A)
In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aesthetics, George Dickie is an important philosopher, and his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acing the criticism, George Dickie has two versions of the theory. The earlier version: art is (1) an artifact; (2) a set of the aspects of which has had conferred upon it the status of candidate for appreciation by some person or persons acting on behalf of a certain social institution (the art world). The later version: art is (1) an artifact; (2) A work of art is an artifact of a kind created to be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in the art world. An artist is a person who participates with understanding in the making of a work of art. The public is a set of persons the members of which are prepared to some degree to understand an object which is presented to them. The art world is the totality of all art world systems. An art world system is a framework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a work of art by an artist to the art world public.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 the earlier version; the later version; analytic aesthetics
2014-11-05
乔治·迪基(GeorgeDickie,1926-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美国著名美学家,研究方向为分析美学;译者刘悦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史与生活美学。
B
A
1002-3194(2015)02-0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