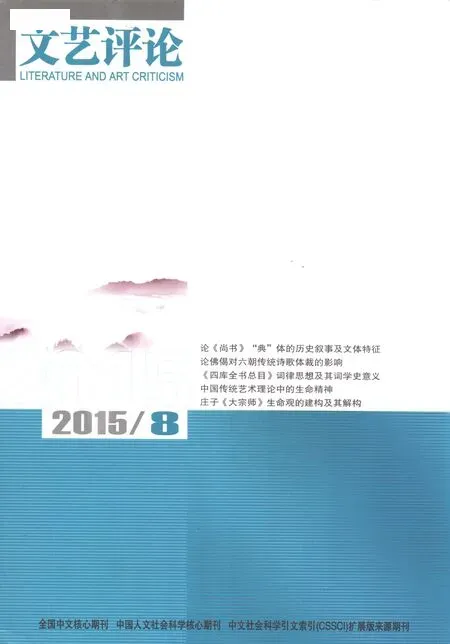儒家心性成长观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卢有志 张澍军
儒家心性成长观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卢有志 张澍军
在当今开放时代,我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对人本身的看法正在经受着多元思潮的冲击和洗礼。近些年,西方思想家提出的等说法,一方面固然是对西方社会生活方式新变化的敏锐揭示,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人的受动性,尤其是人面对资本机器所生产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受动性的无奈。这种现象,可以概略地称为主体的消亡或被塑造的主体。从我国思想界乃至普通民众生活的接受来看,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些思想和看法当作对既定事实的描述,而没有觉察到背后的批判意识,更没有有意识地寻求突破这些困境的出路。事实上,我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人和人的成长有着独特的看法。儒家的心性论和心性的成长说,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套理解人本身的富有启发的概念框架,它不仅可以看作对上述西方思想的回应,而且对当今时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儒家的心性论
在我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传承和积淀中,关于人的看法,最为珍贵的思想资源就是儒家的心性论,以及关于心性的自我成长、自我塑造和自我成就的看法。从根源上看,这套概念框架所肯认的正是人面对外界的影响,具有最终来源于自身或天性的活动性力量。简言之,儒家的心性论就是以“心”和“性”的范畴来界定人的本性。
按照众多古籍的记载,早在上古时代,杰出的政治人物已经用“心”和“性”的范畴来界定人所得之于天的本性,并以这两个范畴来规范人与外界的相接与相处。《尚书·大禹谟》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被后世儒家反复标举和阐释的“十六字箴言”。《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说:“则天之明,因地之性”、“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左传·襄公十四年》有言“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可见按照当时的看法,人的心和性乃是则之天、因诸地的东西,而人在生活和自处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存养天地的赋予而不失。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强调心和性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心和性的“内发论”,这些都是儒家心性说的重要理论来源。
从儒家思想来看,关于心和性的探讨始于孔子。众所周知,《论语》中直接论述“心性”的文字只有两处,其一是《阳货》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其二是《公冶长》中子贡所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当然谈不上是对心性展开的完整论述,但性与仁、性与天命、天道的关系,已经作为隐含问题存在于孔子的思想框架之中。徐复观先生认为,“他(孔子)的知天命,乃是对自己的性,自己的心的道德性,得到了彻底地自觉自证。”①这里强调的就是性的概念与《论语》中其他范畴的关系,尤其是心性与仁、与命的关系。这里所遗留的范畴关系问题在后世儒家那里得到了不绝讨论。
孔子之后,孟子主张心性的内发说而驳斥所谓“外铄论”。《孟子·尽心上》中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又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说法,系统申发在外在的“学”和“虑”之前,人心固有良知和良能的先验能力的观点。《孟子·告子上》中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辱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里所谓“非才之罪也”即强调善乃是人的心性所天生固有,“恻隐之心,羞辱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非外铄而来。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四端”,即是此“四心”的向外展开和表现,这样一来,孟子就为人的外在行为,尤其是善的行为找到了内在于心的发生根据。从儒家思想内部发展的机理来看,孟子的心性说初步为孔子的仁学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因为只有人心固有良知良能,孔子“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说法才有了确定的保障。
大体而言,后世儒家秉承了孟子的观点,并进一步予以发挥和申说。《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即意在阐明“性”来自天之所“命”,这里命就是赋予的意思,而按照天命之性而为,就是所谓道。这里所谓“不可须臾离”,一方面是说人应当按照天之所命行事,另一方面更是强调天所赋予的性乃是人脱离不开的东西。宋明儒者多重视对《中庸》的研究和阐发,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自己的新儒学。不难看出,这是心性内发说的进一步引申。
当然,除上述心性,尤其是其道德性的内生说外,儒家内部还有荀子的性恶论。《荀子·性恶》中说:“然而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者有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那么,既然从儒家传统上说,尤其是在孟子那里,性善论是核心主张,荀子为什么会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呢?按照北京大学王博教授的看法,《荀子·劝学》篇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从学理上看,“‘学’可以看作是荀学的中心观念,并和其他一系列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其次,对学强调,从逻辑上来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人是非自足的或者有缺陷的存在,所以需要后天的功夫来塑造和弥补”,“再次,生命的缺陷决定了生命主体需要借助于他者来改进和完善自己,单纯依赖生命内部的发掘并不能改变问题。”②所以《劝学篇》强调,“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事实上,这里涉及的是人的心性和品格的成长问题,我们认为,孟子和荀子并没有实质上的冲突,性善性恶的分野只是出于从不同的侧面对“学”的强调。本文下一部分将尝试对这个论争提出自己的看法。
总体上看,儒家的心性说强调心或性是人面对生活情境尤其是外界干扰和影响时,所具有的最终的自决和行为选择能力。这种自决能力是一种最终的活动性,它来自天赋,对人所面对的境遇、所受到的或善或恶的影响,有自己的是非判断、监测能力和自我调整的功能。按照多数儒者的看法,这种自我监测、调整和扩充,实际上就是通过学习而自我成长的过程。这其实就是儒家的心性成长观。
二、心性的成长观:可能性与空间
儒家肯定心、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根本,这首先来自最初的生命直觉和生活体验。如果说这种来自原初生活体会的所谓“本体论”是在生命活动中可自觉和可证成的,那么这种证成或自觉的过程就是儒家思想的另一半,即“功夫论”或“修养论”。简单地说,这可以称为儒家的心性成长观。历代儒者用自己的学说和具体生活实践,为心性的成长论证和示范了可能性和空间。
从上文对孔子思想中性与天命、性与仁的范畴关系所内蕴的张力的论述,可以看到,在孔子那里,所思所想达到了仁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扩充和发挥了人得自天的性,人也就完成和实现了自己的“天命”。这也正是孟子明确提出心性论、良知良能说的合法性所在,也正因此,孟子被历代儒者尊为孔子的正宗传人。事实上,孔子也用自己的学说和生命过程,论证和示范了他如何完成了自己的天命,如何践行和实现了自己的心性成长。《论语·为政》中,夫子自道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即可看成孔子对自己心性成长过程的血肉丰满的描述。从《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言行,尤其是孔子对其弟子的教诲和点拨来看,所有关于“学”的言论,其预设的前提也正是心性的成长,尤其是自我成长。所以《论语·述而》中孔子强调的教育观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按照《论语·学而》对人格修养和完善之基本历程的描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际上就是通过诗、礼、乐等来手段和文化积累来完成对心性的陶冶。甚至更广泛地看,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正是立足于人的天赋心性的成长空间和可能性,进行引导和教育,使其“自成”。这也是《论语·雍也》所谓“博学以文”的真实标的。
《论语·为政》中说“君子不器”。关于文中“器”字的理解,历代注家众说纷纭。但在我们看来,“君子不器”说的是人的心性的提升空间问题。从具体的生活技能尤其是《论语》所强调的为政才能上说,我们首先应该对“器”持肯定态度,所以我们也经常说某人在某个领域有所成就,说是“成器”。但《论语》中强调的是成为“君子”,即是说,人不应当像器具一般,只满足于获得有限的才能和用途,而首先应着眼于心性的成长,从不断的自我突破中不断发现自己心性的成长空间,这是比获得具体的才干更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本文第一部分中曾探讨孟子和荀子关于性善与性恶的分歧。从儒家学说的内在理路来看,孟子和荀子的分歧在于对如何“学”以自我成长的具体问题持不同看法,但对心性的成长来说,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荀子强调“善假于物”,通过外物的助益来化恶为善。《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治法度,然则礼仪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这里所谓“化性起伪”,即是化恶为善。相比之下,孟子则主张“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这里则明显强调反求诸己的内省。深层地看,荀子所以反对孟子,即在于他认为孟子主张心性自满自足,从而缺少了自我提升和“学”的维度。但实际上,孟子所说的“四端”用现在的术语表达,应该是一种潜能,其完全的发挥和实现,有待于孟子所说的“扩而充之”。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学”的过程。从学理上说,我们所以能意识到善与恶的分野,能够做出为善去恶的行为,其最终的依据还是在于心性本身的自决能力,这本身就是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孟荀的在“本体论”上的分歧只有表述上的不同。“人之为学”和“扩而充之”都立足于人心的是非辨别能力,心性的成长空间及其“自成”的自决能力。
宋明理学家所特殊重视和标举的《大学》和《中庸》,实际上是将早期儒学关于心性的本体论和关于心性成长的功夫论、修养论打通并结合起来论述的标志性文本。《中庸》主张“天命之谓性”、“修道之谓教”;《大学》标举“明明德”。这里“性”和“明德”就是人所得诸天的心性;而“修”和“明”则是将作为天赋潜能的“性”和“明德”扩充和实现出来的动态过程。具体说来,这种扩充和实现的历程,就是《大学》所标举的“三纲领八条目”。所谓“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首先涉及的就是心和性的修养和砥砺,只有以此为基础,后面的功夫才有了根基。
就宋明儒者自己的学术主张而言,也都有对心性与天、命和道等概念范畴的专门辨析和澄清。二程尝言“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自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二程遗书》卷一八)王阳明则将心性的本体论和心性发挥、扩充和成长的修养论熔为“致良知”一炉。秉承孟子和陆九渊偏向心学一系,王阳明将人天赋的心的活动性界定为“良知”,而“致良知”则是即本体即功夫,推致和扩充心性本然的良知,将之贯彻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成长,也完成了自己的天命。
综上所述,儒家以心和性的概念来界定人最终的活动性。就我们的生活直觉而言,人当然是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乃至侵染的,但人心能够最终意识到这些影响和侵染,具备监测这些影响的是非善恶的能力。用我们日常语言说,人每当陷入某些外界的负面影响和束缚而感到“郁闷”和“悔恨”,其根源即在于人心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状态,知道自己能够改变和走出这种状态但尚未作出实际行动。实际上,这种不断意识到障碍和不断采取克服行动的过程,正是心性的成长。这种不离生活情境而求取觉解的思想和行为框架,也正是中国传统思想不同于西方思想的突出特色。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实践,实际上也正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框架来描述和界定人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活动性因素而予以肯认、发掘和培育,在这里,可以说传统儒家思想的心性观具有天然的用武之地和广阔的开发借鉴空间。
三、儒家的心性成长观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意义
一个国家、民族最初的文化思想对人性的发掘,往往既是对人性诸种活动性潜能的觉醒,又是对这种活动性的强化和培植。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传统思想其实就是民族性格的发展和培育,也是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儒家思想的心性论都既是对我们人性的发现,又是我们人性已经沉淀下来的实质内容,它在我们的言行处世中带有挥抹不去的痕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新时代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认为我国教育系统必须以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精神为己任。在这种视域下,重新思考我国传统思想的优良传统,耐心扎实地回到传统思想家的文本中去发掘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并结合我们真切的人生体验予以利用和创新,是当前迫切需要卖出的步伐。其中,儒家思想的心性论,尤其是其对心性成长可能性与空间的论述和生活示范,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它确确实实应当在我们当今的教育工作中焕发新的活力。我们认为,儒家的心性论、心性成长观对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意义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必须结合传统的心性观念,找到恰切的思想概念框架来描述和界定人的能动性、主动性。如何理解人、怎样理解主体,事实上最关紧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概念框架或思想来理解和观察人的能动性或活动性的来源。无须讳言,我国当前教育界所使用的概念框架大多来自西方教育思想的简单生硬移植。回溯西方思想史,尤其是西方哲学史,近代以来思想家们提出的各种关于人的界定,不论是天赋观念说(如笛卡尔)还是概念能动说(如康德、黑格尔),都无法提出具体地理解人在情境性活动中的能动性的概念框架。因为如果人的概念方式被资本机器所侵染或控制,那么人的碎片化、人的能动性的消逝,就是合逻辑的结论。可以说,这是西方思想界和教育界所面临的主体概念困境的哲学根源。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反省和批判下,西方教育思想对人的活动性的描述和预设的缺点已经暴露无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儒家心性观对人的理解,做出教育通用术语和概念的创新和变革,应当说具有首当其冲的重要性。只有重新界定了人的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才有了施力的标的,才能避免做无用功。
其次,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逐步走向教育过程的情境化,尤其是教育的生活情境化。反观我们多年以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只注重教材的宣读与记诵,而没有渗透到具体的生活情境当中,这其实不利于受教育者对道理的亲身领悟。事实上,儒家的心性成长观,其实现和落实往往就取材于实际生活情境中师生的交流和探讨。我们只要思索《论语》、《二程遗书》和王阳明《传习录》等儒家经典的记载,就不难发现这一点。我们常说教育要“摆事实,讲道理”,其实说的就是教育的情境化。从学理上说,心性的觉解和成长,必须以对自己言行的砥砺琢磨达成,而这其实正是在生活情境中予以落实的。
最后,当今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对受教育者“成己”、“成物”的培育和教导,首先要引导受教育者的“自成”。从根源上说,教育的功能在于唤醒受教育者对自身能动性、活动性的自我意识和觉解,外在的灌输终究无法代替主体自身的领会和证成。在这里,以新的概念体系阐发儒家关于“三省吾身”和“内省”、扩充良知良能的说法,并以此来熏陶和培养学生,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卢有志: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130024),吉林师范大学(136000);张澍军:吉林师范大学(136000)】
①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9页。
②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