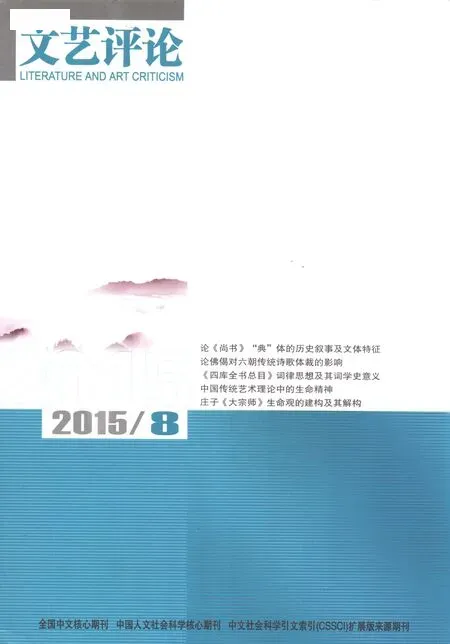明清时期城市生活中的乡村审美情怀
——以李渔《闲情偶寄》为中心的探析
陈莉
明清时期城市生活中的乡村审美情怀
——以李渔《闲情偶寄》为中心的探析
陈莉
一、李渔的城市生活经历与乡村情结
晚明时期江南地域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呈现出由传统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变的蓬勃趋势。商业经济的繁荣使很多人纷纷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促进了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城市的繁荣。李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随着父母离开乡村外出经商的。
李渔(1611-1680),号湖上笠翁,祖籍浙江兰溪夏李村。李渔的父亲李如松是一个药材商人,伯父李如椿是一个医生,他们常年在如皋经营医药生意。李渔从小跟从父辈生长在浙江如皋。可以说李渔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的乡村人,属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的流动人口,类似于现在的城市打工子弟。
二十岁左右,父亲去世后不久,李渔即回到家乡兰溪,继承祖上留下的产业,一度生活在乡村。李渔在家乡建造了“伊山别业”。伊山别业中有燕又堂、宛转桥、打果轩、踏影廊等景观。在《伊山别业成寄同社五首》其五中,李渔写道:“但作人间识字农,为才何必擅雕龙。养鸡只为珍残粒,种桔非缘拟素封。”②在另一首诗《阅耕》中,李渔写道:“五更鸟语催农起,四月乡民愧我闲。”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李渔在乡村生活中并没有直接地参与农业劳动,而是与乡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李渔能以非功利的审美心态观赏着乡村的生活,也使李渔对乡村生活总有着一份美好的记忆。
由于种种原因,三年乡村生活之后,李渔变卖了田产和房舍又回到了城市。先是举家居住在杭州,后又生活在南京,最后又居家杭州,最后病逝于西湖畔自家的园林“层园”。生活在城市,就要遵循城市生活的潜规则,为了生存,李渔过着“卖赋以糊其口”的生活,他非常努力地创作小说和剧本,创作几乎是李渔及其家人在城市生活中唯一的谋生手段,因而市场和观众的喜好自然成为李渔创作追求的目标。《无声戏》、《十二楼》、《肉蒲团》,以及戏曲《李笠翁十种曲》等,都带有迎合市民趣味的特点和较浓的商业色彩。为了维持一家十多口人的生活,李渔还建成了以乔、王二姬为台柱的家庭戏班,常年巡回于各地为达官贵人演出,收入颇丰。在南京生活的二十年是李渔生活最好的时期,他不仅经常携妓出游,在金陵购置了芥子园,并且还经营书铺。身居都市,李渔有不少机会与名人往来,在杭州居住时,就曾与丁澎、陆圻、毛先舒等“西泠十子”多有交往。与名人往来,使李渔的声价大增,吴伟业、钱谦益、丁澎等都曾为李渔的作品写过序,这是商业社会特有的一种名人效应。可以说,城市生活促使李渔发挥了各种潜在才能,成就了李渔的多重角色,使他成为戏剧家、小说家、书商,等等。
如果说写作、演戏、刻书,经营等都是城市生活中的谋生手段,带有为生计所迫的性质,那么,闲暇时李渔的生活则与这些商业经营有着一定的距离,表现出了李渔生活的另一个层面。李渔有一些列雅号,如“伊园主人”、“随庵主人”、“心亭樵客”等,这些雅号表达了李渔对乡村生活的留恋。居住杭州时,李渔还给自己取号“湖上笠翁”,这个雅号表达了李渔对头戴斗笠垂钓湖上的悠闲乡野生活方式的渴望,表达了生活在城市中的李渔浓厚的乡村情结。然而,李渔也指出,虽然人人唤自己为笠翁,但笠翁其实只是一个空名而已。这意味着李渔的雅号都是对乡村生活的诗意想象。
李渔的诗词中有不少交际、应酬之作,但是那些表现真情实感的诗词大多都表达了李渔对大乡村生活的向往。如《山居杂兴》中有“为结山林伴,因疏城市交”,“半生长蹙额,今日小开颜。绿买田三亩,青赊水一湾”③等诗句,表达了快乐的乡村生活体验,而《看红叶》、《茉莉》、《食松菌》、《樱桃》等诗歌都表达了身居城市的李渔对花草树木的热情。这种城市生活中的乡村情结更为集中地被记载在《闲情偶寄》之中。
2005年11月至2014年6月,李青海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虚列工程项目,签订虚假工程合同,以虚开发票入账核销方式,套取项目资金700余万元;2009年8月至2013年6月,李青海以承包镇集体耕地承包户的名义,申报良种补贴,并将部分承包户的良种补贴款截留,共计60余万元;2006年至2017年,李青海通过冒名顶替虚报耕地的方式,套取国家粮食补贴款300余万元。10多年的时间里,李青海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款31笔,共计人民币1100余万元。
二、城市生活中的乡村情结:《闲情偶寄》的美学底蕴
如果说《闲情偶寄》中关于戏剧的理论是李渔适应城市生活,以写作糊口,以演戏为生的城市生涯的经验总结,那么,《闲情偶寄》中关于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是明清士人“尚物”、“玩物”情趣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身居城市中的李渔对自然的呼唤。李渔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市中度过的,城市生活空间的狭小和局促令人感到遗憾,但是在城市有限的生活空间中,李渔却能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城市的生活更加接近大自然,更加富有乡村情调。
在《闲情偶寄》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读到李渔对城市和乡村生活的不同看法,以及城市生活的不得已。如《闲情偶寄·颐养部》中,李渔写道:“追忆明朝失败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夏不谒客,亦无客至,匪止头巾不设,并衫履而废之。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洗砚石于飞泉,试茗奴以积雪;欲食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果落树头,可谓极人世之奇闻,擅有生之至乐者矣。此后则徙居城市,酬应日纷,虽无利欲熏人,亦觉浮名致累。……”④从李渔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第一,乡村生活自由自在,随心所欲,能够亲近大自然;第二,城市生活有着较多的应酬,常常为浮名所累;第三,乡村生活的经历成为李渔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虽然这种乡村的经历只有三五年,但却深刻地影响了李渔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甚至成为李渔评判城市生活时的一个参照系。
在城市生活中,有着更多的商机和更为广泛的社交机会,但生活在城市中,那份裸处乱荷之中,偃卧长松之下的惬意就没有了。这正是明清时期,城市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人们所面临的缺憾,而在城市建造园林就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现象的一种权宜之计。因而,修筑私家园林成为明代后期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尤以江南为盛,如常熟有钱谦益的拂水园、无锡有邹迪光的愚园、山阴有祁彪佳的寓园等。明清士人在喧闹的城市筑起一个个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将山林野趣移入市井隙地,在纤小中寻求隐逸和超脱,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李渔生活的年代。在《闲情偶寄·居室部》中李渔指出:“幽宅磊石,原非得已。不能致身岩下,与木石居,古以一卷代山,一勺代水,所谓无聊之极思也。然能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不得以小技。”⑤在这段话中,李渔非常真切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第一,在城市中建造园林,就是要在狭小的空间中表现无限的自然境界,以一张画卷唤起人们对大山的想象,以一勺水代表大江大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算是对城市生活不足的一种弥补吧;第二,如果真能在城市中复现乡村和山野情景,在有限的城市生活空间中营造出自然景观,这一定是不可小视的高超技艺。在城市生活中有了这些石山,“时时坐卧其旁,即可慰泉石膏肓之癖。”⑥正是为了在城市生活空间中营造这种置身自然之中的感觉,李渔先后参与设计和建造的园林有伊山别业、芥子园、半亩园、层园等。李渔在南京建造的芥子园,只有一丘之地,所以名为芥子,以状其微小。在有限的都市环境中营造广袤的乡村山野的感觉,这就是李渔热衷于园林设计的内在动机和目的。
李渔关于居室的布置同样体现了在城市生活中再现自然的理念。如李渔认为窗栏是一个屋子与外界自然沟通的窗口,所以在游船上要有便面窗,以便坐在船中的人可以看见外面的自然景色,而且恰恰是因为扇面形的窗子的存在,外面的景色被截取成一幅画。这样,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成为船中人的天然图画。而且,随着船的移动,这幅画的内容可以不停地变换,所谓摇一橹,变一像,撑一篙,换一景。而要达到这种如诗如画的效果,人要尽量坐得离窗子远一点,这样才可以使窗框具有画框的效果。此外,李渔还曾设计和制造了“浪里梅”式的窗栏,即用波浪形弯曲的木头制作窗栏,又在层层“波浪”之间镶嵌进木片削成的梅花。这样的窗栏看起来就像一朵朵梅花飘落在潺潺流动的溪水中。这种人造的自然弥补了城市生活中自然景色的缺乏。更为巧妙的是李渔设计的“梅窗”,即将枯树枝稍加斧凿作为窗栏,然后将彩纸剪成梅花形,分红梅、绿萼两种,点缀在疏枝细梗之上。这样的窗栏远远看去,简直就像刚刚开花的扭曲的梅枝。这等奇思妙想,充满了文人的幽情雅趣,将虚幻的自然景色带进身居城市的人的生活中,拓展了人们的想像空间。
园林中对联和匾额的设计理念,也充分体现了李渔“在城市再造自然”的思想。如李渔认为蕉叶题诗是非常富有韵味的趣事,所以园林的楹联可以设计成蕉叶的形状。具体的作法是,在纸上画一个大蕉叶,让漆工刷上绿色的漆,再用黑色漆勾出筋脉,用石黄色写上诗句,然后挂在壁间门上,一个富有自然情调的楹联就完成了。李渔还主张用竹片、石块等富有自然韵味的材料来题写匾额。如竹片制作的匾额,就是用铲子铲掉竹子的结节,然后将其磨得像镜子一样光亮,再用石青、石绿,或者墨汁写上诗句。这些都是可以以假乱真的人造自然,它们表达了生活在城市中的李渔对大自然的深情呼唤。
在《闲情偶寄·种植部》,李渔指出,桃之美要在乡野间去欣赏。“此种不得于名园,不得于胜地,惟乡村篱落之间,牧童樵叟所居之地,能富有之。”⑦李渔能深刻领悟乡村生活的诗意性,指出只有乡间篱落之间,牧童樵叟所居之地的桃花才富有一种乡间的野趣,而喧嚣的城市中是品赏不到桃花的神韵的。但对于生活在都市空间中的人,对于没有条件到牧童樵叟所居之地领略自然美景的城市生活者而言,能够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布置自己喜欢的各种花草树木,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生活的不足。李渔说,春海棠颜色极佳,凡有园亭者不可不备。贫士之家,没有条件种植春海棠的话,就一定要种植一些秋海棠,秋海棠可以通过移根的方法栽种,不需要花钱去买,也容易种植。秋海棠占地不多,性喜阴,墙间壁上的狭小空间,以及别的花草舍弃不用的地方,秋海棠都可以栽种。李渔关于种植秋海棠的种种理解,最终都是因为要在狭小的城市生活空间中营造诗意的感觉。
为了能在夜晚也嗅到花的馨香,李渔想出了一个日夜与花相伴的办法,即在床帐之内建造一个放置花卉的托板,这样就可以时时将各种时令花卉放在床帐之中,人睡在花下,恍惚之间,就感觉到自己似乎睡在鲜花丛中,一觉醒来,更不知自己是否是飞舞在花丛中的蝴蝶。更令李渔心醉的是,“予尝于梦酣睡足、将觉未觉之时,忽嗅腊梅之香,咽喉齿颊尽带幽芬,似从脏腑中出,不觉身轻欲举,谓此身必不复在人间世矣。”⑧这种在朦胧的睡梦中嗅到腊梅馨香的感觉的确令人陶醉,从中可见李渔的闲情逸致,以及对于自然的挚爱之情。在城市生活中获得与自然亲近的机会,这是李渔审美追求的内在动力。
在饮食方面,李渔反复表达了对来自山林、乡野的蔬食的喜好。在《闲情偶寄·饮馔部》,李渔指出蔬食之清洁、芳馥、松脆者,“惟山僧野老躬治园圃者,得以有之,城市之人向买菜佣求活者,不得与焉。然他种蔬食,不论城市山林,凡宅旁有圃者,旋摘旋烹,亦能时有其乐。至于笋之一物,则断断宜在山林,城市所产者,任尔芳鲜,终是笋之剩义。”⑨李渔认为,只有山野间的笋才会有最为纯正的品味,李渔对乡野生活方式和自然情趣的向往溢于言表。
三、城市化与中国文人对乡村的诗意回望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度,几千年来人们居住在人口相对固定、生活相对简单的乡村之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形成了对于大自然独特的认识。同时,乡野中的花草树木、溪流山峦也造就了中国人的诗意情怀,中国的古典诗词简直就是以美丽的花草树木编织而成的“诗的花环”。
随着商业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唐代的西安,已经出现了东市、西市等专门的贸易场所,但是由于市场的相对固定化,以及夜禁制度的施行,所以城市的发展在人们心灵中引起的冲击还不是很大。到了宋代,城市突破了以往的封闭格局,商业交易区和居住区不再截然隔绝,商家沿街设铺,各种商业店铺随处可见,营业时间也扩展到深夜和凌晨,出现了繁荣的“夜市”和“早市”。都城商业繁盛,人口密集,民居、商家、官署不免要争夺空间,因此城市空间显得比较狭促,城市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到了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商品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在物产丰富和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各个商业中心区,如北京和南京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杭州、苏州等成为以商业为主的城市,此外,各地还出现了不少工商业市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生活在城市之中。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⑩但是人们也隐约意识到了在城市生活中乡村诗意景观的消失。“乡村和都市应当是相成的,但是我们的历史不幸走上了使两者相克的道路,最后竟至表现了分裂。”⑪于是,从唐代开始,中国文人士大夫就极力在城市生活中寻求诗意的人生境界,以避免城市生活中乡村诗意性的消失。如白居易就力求在城市生活中寻求山林野逸的乐趣,以闲适、自在的心境化解外部社会带来的烦恼和束缚。司马光在洛阳建造的独乐院,面积虽然很小,但有“弄水轩”、“种竹斋”、“见山台”等景致,呈现出自然趣味。宋代诗人苏舜钦的沧浪亭,三面环水,绿竹环绕,有着江南园林的魅力,体现着主人超然的审美追求。
明清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更是出现了一个回归乡村自然生活的高潮。文震亨《长物志·室庐》开篇就指出:“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⑫,表达了对山野生活的肯定。计成《园冶》中追求的也是“编篱种菊”、“锄岭栽梅”⑬的乡村情趣。
文人士大夫一方面在城市中为生计而奔波,游走于名人官宦之间,以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但另一方面却又对科举、对功名、对商业文化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力求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寻求宁静的乡村体验。正如刘士林所说:“对于古代士人,尽管在理智上他们会选择‘居于城’,但在情感上更向往的还是乡镇与农村生活。”⑭袁宏道的《瓶史》中也提到本希望“欹笠高岩,濯缨流水”,但又为卑官所绊,只有载花莳竹一事,可以自乐。然而,“邸居揪隘,迁徙无常”,自己身居城市,常常迁居,因而没有能力来养花,“不得已乃以胆瓶贮花,随时插换”⑮。再如张瀚虽处城市,但足迹不及公府。张瀚在杭州建有小楼三间,小窗杂植花卉,水仙、梅花、蔷薇、白荼蘼、黄海棠、石榴、莲花、茉莉、芭蕉、桂花、山茶等依次开放,四时光景常新。庭院成为他休憩精神的处所。沈复在《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中写道与妻子陈芸寄居在“宾香阁”,那里“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于篱下”,“几不知身居城市矣”,⑯可见,在都市生活中寻找乡村山林般的感受已经成为明清时期文人雅士普遍追求的一种生存方式。明清时期,园林的大量出现,正是人们在都市生活中,呼唤山林乡野之美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样,文人士大夫的绘画、诗文中出现大量的表现山川、乡村景象的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力求与城市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找回乡村诗意生活方式的努力。
文人生活在城市中,却力求远离都市的喧嚣和商业的庸俗,表现出文人的清高和雅致。文震亨认为在瓶中插花“止可一、二种,过多便如酒肆”⑰,盆栽的兰花“每处仅可置一盆,多则类虎邱花市”,表现出文人艺术化的生活追求和对商业气息的极端排斥心理。再如陈继儒是有名的“市隐者”。他三十岁就绝意仕途,过着隐居都市的生活。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处处表达着对乡村诗意生活的向往和留恋,他指出:“檐前绿蕉黄葵,老少叶,鸡冠花,布满阶砌。移榻对之,或枕石高眠,或捉尘清话。门外车马之尘滚滚,了不相关。”⑱让各种鲜花布满庭院台阶、与门外的滚滚红尘了无关系,这正是身处红尘中,却心在山林中的市隐者的生活的高度写照。这就是广泛存在于明清时期的“市隐”现象。
李渔的《闲情偶寄》正是这种隐居城市的文化形态的体现,在“藤本部”中,李渔指出:“觅应得之利,谋有道之生,即是人间大隐。”⑲关于市隐,李渔认为:“避市井者,非避市井,避其劳劳攘攘之情,锱铢必较之陋习也。”⑳李渔关于隐居城市的看法有着必然的历史背景,它正是明清时期,城市有了一定发展,人们事实上已经习惯生活在城市,但却努力地保持乡村诗意生存方式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市隐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在纷纷扰扰的城市生活中寻求超越的心态,是一种与城市功利化的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审美心态。
改革开放后,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化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开始引起了强烈的阵痛。同时,对城市发展的反思又一次成为文人思考的中心话题,如在贾平凹、张炜、孙惠芬等作家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城市从羡慕到反思的历程。在这些作家的笔下,人们还能感受到一丝泥土的馨香,这是因为这些作家还有着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活经历,他们大部分都是先生活在农村,后来才走向城市,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这个“游走阶段”很快就将过去。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对乡村完全陌生。“在整个世界都被城市文明深耕了一番以后,乡村的自然对于人来说,已经不再是家园,而只是度假村了。”㉑而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没有阳光、绿叶的办公室中,他们有限的闲暇时间更多的是在电视机前,在网络的虚幻世界中,或在健身房中度过的。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乡村急剧消失,人们对城市的反思的能力也越来越小。像明清时期的“市隐者”一样,隐居于城市,享受着城市的一切便利条件,但是却还努力营造富有乡村诗意氛围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现代城市生活的状况折射到艺术作品中,则是在人们很难再读到有关乡间小溪与河流的文字描写。这意味着即便是作为一种诗意想象,在虚幻的艺术世界中,乡村也已经变得很模糊了。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与其有着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和乡村景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乡村变成一个模糊的影子时,诗意正在消失。
综合以上论述,乡村社会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乡野的花草树木、小溪河流是中国文人灵感的源泉。伴随着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人类诗意生活的空间在逐渐消失。明清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开始生活在都市中,但是在那个时代,身居城市,却还能够追求一份乡村的闲暇情调和生活氛围。李渔的《闲情偶寄》集中表达了居住在狭小城市生活空间中的文化人营造诗意生活氛围的努力。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着一种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乡村急剧消失。人们在城市中开辟乡村诗意景致的空间已经很小。随着乡村的消失,生活节奏的加快,中国将不再是一个诗的国度。精神家园的消失,以及诗意情怀的消失,这都是城市化过程中急需人们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100081)】
①②③《李渔全集·笠翁一家言诗词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165、89页。
④⑤⑥⑦⑧⑨⑲⑳《李渔全集·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195、195、283、209、236、278、27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⑪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⑫⑰文震亨《长物志》,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76页。
⑬陈植《园冶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⑭刘士林《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界定及其人文研究路向》,《江海学刊》,2007第1期。
⑮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年版,第页。
⑯沈复《浮生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⑱陈继儒《小窗幽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6页。
㉑高建平《美学的围城:乡村与城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