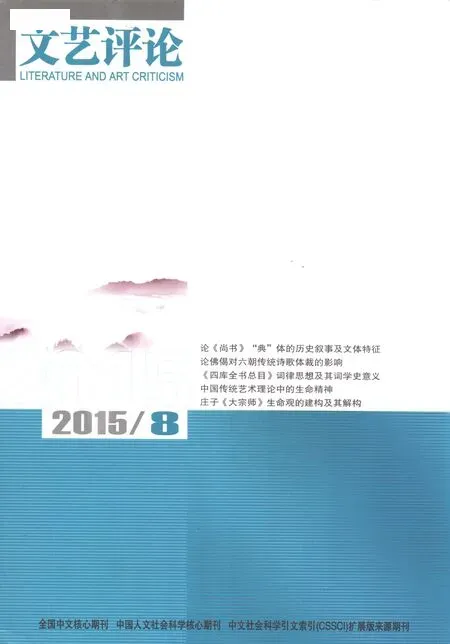“三礼”中仪式用乐的政治含义及礼、乐之关系
李敦庆
“三礼”中仪式用乐的政治含义及礼、乐之关系
李敦庆
乐,包括祝辞、音声,舞蹈等,在原始仪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仪式操作者所利用,作为实现群体共同利益的工具。礼与乐在最初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礼乐制度的建立将礼仪的地位凸显出来,而乐则逐渐开始作为礼仪的从属存在。作为儒家典籍的“三礼”中的祭祀礼仪形式在很大程式上是导源于原始宗教及巫术活动。原始宗教及巫术仪式与周代的祭祀礼仪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从发生上来看,二者都是以万物有灵及灵魂不死的观念作为心理基础;从目的上看,二者都以实现群体的共同利益为最终归宿。但是,在西周时期,鉴于夏商亡国的历史教训以及周初的政治形势,祭祀之礼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对天地神灵的淫祀,而将重点转向对人事的关注。传说时期的古乐不少具有巫术及原始宗教的特征,《大章》为传说中帝尧之乐,本为带有巫术色彩的乐舞,到周代被用于祭祀地示。《吕氏春秋·古乐》中载《大章》的创作过程: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①
此乐作为原始仪式中使用的乐舞,带有比较浓厚的原始社会农业文明的特点。但这些原始乐舞在礼乐文明建立之后被用于礼典之中,被奉为经典,具有神圣的力量。可见,原始乐舞与礼仪乐舞之间并不是截然断层、毫无联系的,原始乐舞之所以在周代礼仪中得到运用是基于其自身所蕴含的深厚的政治含义。
因此在“三礼”的祭祀仪式中,天、地、鬼、神的观念仍在发挥作用,但已经摆脱了原始宗教的色彩,而是披上了政治的外衣,成为证明政治权力合法性及维护等级秩序的有力工具。在原始仪式中所采用的歌舞往往在礼仪得到运用,承担着相应的政治功能。
一、“三礼”中乐的政治含义的表现方式
礼乐制度建立之后的乐歌,无论是用于祭祀仪式还是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仪,其表达情感与意愿的功能均已退居次要地位,体现相应的政治含义成为乐的首要功能,乐的政治含义的建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以先王之乐来彰显“三礼”中仪式用乐的政治含义。
“三礼”祭祀仪式所使用的乐舞最为人所称道者就是六代之乐,据《周礼》记载,这六代之乐分别是:《咸池》、《云门》、《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除《大武》为周代之乐有较为明确的资料可循外,其他诸乐舞的年代都不易确定。但这些乐舞被纳入到礼仪乐舞的范畴之内,《周礼·大司乐》:
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②
这是《周礼》对六代之乐所用祭祀对象的记载,其实施原则是按乐舞产生的先后顺序来使用于不同的祭祀仪式当中,产生时代越早被使用于的仪式规格则越高。《云门》、《咸池》均为黄帝之乐,郑玄注:“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吕氏春秋·古乐》:“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与郑玄所注稍异。黄帝之乐所使用的仪式为天、地祭祀,而《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分别为舜、夏、商、周之乐,按照祭祀规格的高地依次使用于四望、山川、先妣、先祖等由自然神到祖先神的祭祀仪式,可见在《周礼》中已经确立了划分尊卑等级的乐体系。
在《礼记·乐记》中有“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的记载,而《周礼》中却规定以周代之前的五代之乐作为祭祀中的盛乐,似乎与此记载相背,但郑玄之注可为我们提供解释的空间,不相沿乐,不相袭礼是“言其有损益也。”即对前代乐舞加以改造,为本朝所采用。
《周礼》将之前五代所使用的乐舞作为本朝的祭祀用乐,最主要的原因是先王的丰功伟业可以作为周效法的对象,《白虎通义》卷三《礼乐》:
黄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咸蒙德施也;……尧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箫韶》者,舜能继尧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顺二圣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汤曰《大护》者,言汤承衰,能护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③
黄帝、尧、舜为传说时代的贤君,而禹、汤、武王又是夏、商、周基业的奠定者,他们时代乐舞的产生、命名都是因为其功勋的卓著以及德行的高尚。西周时期鉴于夏、商王朝君主无德而亡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将“德”这一标准置于最高地位,这一点在西周时期的祭祀歌辞《周颂》中可以得到证明:
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这两首诗均为祀文王时所唱之乐歌,其中都有对文王德业的赞颂,这种在祭祀中歌颂有德君主或者将有德君主所创之乐歌用于祭祀仪式的做法在周代非常普遍。《周颂·思文》一篇,据后世学者解释就是祭祀周人的最高神昊天上帝时所使用的乐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毛传》:“《思文》:后稷配天也。”孔颖达《正义》:“《思文》诗者,后稷配天之乐歌也。周公既已制礼,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于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为此歌焉。”《大戴礼记·朝事》“率而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报德,不忘本也。”《礼记·名堂位》“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后稷能得以配天的根据是其作为周先祖的身份以及他功业的卓著:“立我烝民”“贻我来牟”,于是在祭祀上帝时一方面用后稷配祀,同时在祭祀仪式使用的乐歌中也对后稷之功德加以歌颂。
这种以先祖或以先王之乐作为天地祭祀仪式用乐的方式,其出发点已经远远超出了原始宗教或者巫术仪式中乐歌的功能,娱神的功能在这些祭祀仪式中固然存在,但最重要的功能却在于通过先祖或先王之乐在祭祀仪式中的运用,向上天表达周的建立是以“德”为基础的,并且要以历代先王作为效法的准则治理国家。因此,祭祀礼仪中乐舞及其歌辞与原始宗教中的乐舞及祝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同为向上天神灵传达信息,但二者在传达内容上有了很大不同:一为娱神或对神灵的祈求,一为向神灵表达待治理国家的态度。政治功利目的成为首要内容,乐歌的娱神功能大大减弱、退居次要地位。
2.以独特的奏乐方式体现“三礼”中仪式用乐的政治含义。
礼仪的重要作用之一是通过仪式的展演,来证明仪式参加者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与状态,并维护其地位。只有通过展演,仪式中所隐含的象征含义及所体现的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才能够向社会成员表达、证明,进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承认。这种通过仪式的展演来证明权力存在合法性的方式在各种社会形态之中广泛存在,而音乐在其中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乐舞作为礼仪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与礼仪一样也是一种凝结了特殊含义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含义的表达、呈现就是通过其在礼仪活动中的表演来实现的。乐舞在仪式中的使用已经成为表明统治者身份与地位的手段,礼仪乐舞的这种功能在原始巫术及宗教乐舞中也是具备的,但在这套符号系统之后所隐含的实际意义却有很大的不同。
在祭祀仪式中,西周以有德先王之乐作为本朝祭祀用乐,而在用于人事的礼仪中,乐舞的使用也是以体现上下等级、维护集团尊卑有序的统治秩序为目的。这主要体现在西周时期的用乐方式之中,即以有差别、有等级的奏乐方式体现上下尊卑的关系。燕飨、大射礼仪是周代礼仪生活中常用于君臣之间的礼仪形式,这些礼仪形式本身就以体现严格的等级秩序为目的:“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而大射礼之目的在于选诸侯、卿、大夫、士:“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即以大射礼中参加者的动作是否与仪式及乐节相一致作为甄选、考核人才的依据。
这些仪式中使用的音乐对仪式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它们必须依照礼仪等级的划分为奏乐依据,按仪式参加者的身份与地位来确定仪式中所使用乐器、乐舞的规格、内容及演奏方式。在乐器使用上,西周礼仪中所使用的乐器规格是严格按照身份地位来确定的,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乐器使用规格。《周礼·春官·小胥》中记载了自天子至于士所使用的乐器规格:“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所使用的舞蹈也以等级来划分,《左传》“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可见,乐器、乐舞的规格是体现等级差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成为等级与身份的象征。这种乐器使用方式是维护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的重要保证,一旦打破这种乐器的使用规则就会对等级秩序造成破坏。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不断下降,而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诸侯、卿大夫对天子礼乐的僭用。《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僭用周天子的八佾之舞,在维护西周封建礼制的孔子那里这是不可容忍的。
乐器乐舞之外,乐歌的使用也是以等级的差别来划分的。以大射之礼为例,《礼记·射义》中记载射箭时奏乐的规定:
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蘋》为节,士以《采蘩》为节。《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苹》者,乐循法也,《采蘩》者,乐不失职也。是故天子以备官为节,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④
孙希旦认为:“天子大射,歌《驺虞》以为射者之节;诸侯大射,歌《狸首》以为射者之节;大夫大射,歌《采蘋》以为射者之节;士大射,歌《采蘩》以为射者之节。而其节之多寡,则各以尊卑为差。”⑤在这里“节之多寡”当指《周礼·夏官·射人》所载之“九节五正”、“七节三正”、“五节二正”:
以射法治射仪。王以六耦射三侯,三获三容,乐以《驺虞》,九节五正;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获二容,乐以《狸首》,七节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获一容,乐以《采蘋》,五节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获一容,乐以《采蘩》,五节二正。⑥
所谓“节”是指乐曲演奏完一遍,而“正”是指在乐曲伴奏的过程中准备射箭的活动,即“在审听乐节,准备射箭时,端正观念与姿势的意思。”⑦地位尊者的准备时间较长,而卑者准备时间较短。从上引大射礼仪用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用于人事的乐歌中也体现出尊卑有等的观念:首先是以地位的不同来确定举行礼仪时所用的乐曲。其次,以地位的不同来确定奏乐时间的长短,地位尊者时间长而卑者短。这种尊卑有等的仪式用乐规则是整个西周时期等级制、分封制在具体礼仪中的反应。在整个礼仪活动中,音乐、歌舞、演唱已经不是以娱乐享受为目的,而是被赋予了现实的政治功能,成为统治者证明君权合法以及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
由此可见,从西周礼乐文化建立以后,乐舞在礼仪中使用是以体现其所蕴含的政治含义作为首要目的。“礼乐相须以为用”开始成为历代统治者所遵循的共同法则。礼仪用乐在西周乃至以后整个古代社会都作为礼仪的附庸出现,服务于政治目的,二者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同时仪式的娱乐功能及宗教色彩都大为减弱。
二、礼乐相须以为用——“三礼”中礼、乐之间的关系的探讨
在西周礼乐制度建立之后,礼乐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郑樵《通志·乐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恰当的概括:“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⑧在这里,郑樵所说的“礼”与“乐”的关系与本节所要论述的礼仪与其用乐之间关系在概念上并非完全一致,前者范围更广,可以将后者包括在内。用郑樵的归纳来描述“三礼”中礼仪及其用乐之间的关系的是颇为恰当的,下面就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1.仪式的完成需要乐舞的配合。
首先,乐舞本身的符号与象征含义为仪式能够达到既定效果提供保证。“三礼”中的大部分礼仪活动都有乐舞的伴奏,在祭祀礼仪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仪式中,乐舞部分都占了较大比例。《礼记·祭统》:“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祭祀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献、声、舞,概括来说就是仪式动作、音乐、舞蹈三个部分。其中仪式动作是在礼仪的实行者,即一场礼仪的发起者在礼仪中各种行为的综合,是构成仪式的主体。声音与舞蹈则是从属于仪式的部分。乐舞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仪式的顺利进行提供指示,另一方面是烘托仪式的氛围,将仪式的效果发挥到极致。下面将对此分别进行论述。
礼乐文化建立之后,礼仪的目的即在于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服务,同时也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礼仪活动中,所有的仪式组成部分都具有符号的性质,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语言形式的符号”、“物件形式的符号”、“行为符号”以及“声音形式的符号”⑨。这些符号以动作、歌舞、音乐以及各种礼器的形式呈现在仪式中,并相互协调,共同构成一场完整的仪式活动。在祭祀神灵的仪式(即后世所谓的吉礼)以及用以协调人事关系的仪式(即宾礼、军礼、嘉礼等仪式)中,统治者按照其制定的礼仪规则参与到仪式中去,成为仪式的主角。仪式的主持者和主要参与者在活动中的行为动作,是整个活动的主体部分,仪式的举行就是仪式的实施者为了证明其地位和维护其统治。乐舞作为声音、动作的符号形式也是仪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礼仪中的其他仪式动作一样也具有符号意义,尤其是在礼乐文化建立之后的各种仪式中,乐舞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周代乐舞《大武》是周天子用于祭祀天地宗庙的乐舞,据《礼记·祭统》:
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子孙纂之,至于今不废。⑩
可见,《大武》舞是周天子祭祀天地时所用的乐舞。而《大武》所舞的内容实际上是对周初历史事实的模仿。《礼记·乐记》孔子对宾牟贾言乐事:“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成天子。”此段中有“象成”二字,所谓“象成”就是对武王伐纣建国、分封诸侯这一系列历史事实的模仿,《大武》舞的各种舞容中都蕴含有相应的历史史实。其实这一舞蹈是将周灭商建国分封加以符号化,以舞蹈动作的形式表现出来。孔子曾对《大武》和《韶》进行过比较,“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之所以《武》未能尽善,是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对周初战事的模仿,是周初战争的符号化,战争杀伐在以人为本的孔子那里自然是会受到排斥的。
这种作为符号的舞蹈中所包含的意义极为深广,只有在礼仪中加以运用,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含义才能得以体现。西周时期,天神、地示、人鬼的三元神系统已经出现,祭祀天地的仪式已经成为证明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祭祀天地的仪式上使用这些乐舞,对于达到仪式效果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其次,礼仪中的乐舞不但以其本身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使得仪式的意义得以彰显,达到既定的仪式效果,同时音乐也起到协调仪式的作用。在许多仪式中,不同的环节都是依靠演奏不同的音乐来区分的。《周礼·乐师》:“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郑玄注:“教乐仪,教王以乐出入于大寝朝廷之仪。”贾公彦疏:“教乐以节仪,仪与乐必相应也。”此为王迎宾客时所遵循的法则,其行、趋、环拜等仪式环节都有不同的奏乐与之相配。在各种具体仪节中奏乐的作用,有学者将其归纳为行步之节、行礼之节、指示仪式进程等⑪。这一功能在魏晋之后的各种礼仪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郑樵指出了这一特点:“魏晋……但即事而歌,如牺牲之时则有《牺牲歌》,降神之时,则有《降神歌》。”郑玄实际上是为了批评魏晋时期的礼仪乐歌不能继承汉郊祀歌“因一时之盛事”的创作方法,但同时也指出了仪式与乐歌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根据不同的仪式环节来确定用乐内容及歌辞。这与《周礼·大司乐》“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的奏乐原则是相一致的。
除此之外,音乐在仪式中的作用还表现为渲染仪式的氛围,或庄重肃穆、或和谐融洽,不同的礼仪需要有不同的仪式氛围。《礼记·少仪》载不同仪式场合的仪式氛围:“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而音乐在仪式中可以发挥其感染力达到这种效果。《礼记·郊特牲》:“宾入大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礼记·乐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不同仪式场合的奏乐取得了不同的效果。
2.乐舞的演奏必须服务于仪式本身,不能有所偏离;同时,仪式对乐舞的选择有明确的要求,不能离开仪式来选择舞蹈、乐歌。
在礼乐制度建立之后,乐舞是作为仪式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不同的仪式类型要求使用不同的乐舞,如祭祀鬼神之乐舞与飨宴君臣之乐舞在内容、节奏、风格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在祭祀天神、地示、人鬼的仪式中,乐舞的使用以先王之乐为主,《周礼·大司乐》中的《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作为先王之乐,决定了它们要使用在国家祭祀礼仪中。据王国维等学者考证,《诗经·周颂》中的《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为与《大武》舞相配合的诗篇⑫,可见《大武》是诗、乐、舞三者的综合艺术,而自黄帝《咸池》而下的先王之乐,也应是诗、乐、舞相配合相协调的综合性舞蹈。第一,这些诗、乐、舞相综合的舞蹈在舞容上多集体表演,即《礼记·乐记》中所说的“旅进旅退”,在配乐上所使用乐器多质木无文:“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同时对舞蹈表演上用乐器相节制:“治乱以相,讯疾以雅”。所谓“相”、“雅”均为节乐之器,为了防止音乐演奏过快及舞蹈与音乐的脱节,用这两种乐器作为节制的工具,使得这一表演达到整齐划一的效果;第二,在歌辞上,与之相配的歌辞被称为“颂”,其特点之一就是在演唱时为了达到与歌舞相配合的效果而发声缓慢⑬。由此可见,在用于祭祀的仪式中,所采用的乐舞在内容上体现了先王的文治武功,在风格上以庄严、凝重为特色,节奏上较为缓慢,表现出鲜明的雅乐特色。
仪式对音乐的选择同样也体现在飨宴及其他用于人事的礼仪中,以乡饮酒礼为例,乡饮酒礼主要是乡大夫飨一乡之能者、贤者的仪式⑭,《仪礼》贾公彦疏引郑玄《目录》云:“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于五礼属嘉礼。”这一仪式的目的,在于对乡之贤能者的慰问,同时也是为贤者、能者献于君后能熟知礼仪做好准备。在此仪式中奏乐的目的是使贤能者熟知礼仪,其政治功利目的居于首位,而娱乐的成分则退居次要地位。在乡饮酒这一仪式中,乐歌的选择是别具匠心的:“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这三首歌诗都是《诗经·小雅》中的作品,据郑玄《注》:《鹿鸣》是“君与臣下及四方之宾燕,讲道修政之乐歌也。”《四牡》是“君劳使臣之来乐歌也。”《皇皇者华》是“君遣使臣之乐歌也。”如郑玄之注,这三首诗都是君主所用之乐歌,而为什么要在乡饮酒仪式上使用呢?归根结底是由此仪式的功能决定的,此仪式中主人所宴之宾最终是要献给君王的,他们在君王那里成为重要政治人物的可能性极大,作为君主的臣子,必须要学会相关的朝廷礼仪,乡饮酒礼中的奏乐,实际上是对贤者成为君王身边大臣以后所从事礼乐活动的一次演习。贾公彦在《仪礼》疏中说:
此时贡贤能拟为卿大夫,或为君燕食以《鹿鸣》诗也;或为君出聘以《皇皇者华》诗也;或使反为君劳来以《四牡》诗也。故宾贤能而预歌此三篇使习之也。⑮
这一解释指出了乡饮酒礼中所用之《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是对贤者、能者入仕之前的训练。这也正好说明了在礼仪中使用何种乐歌,取决于举行礼仪的目的,只有当乐歌的使用与仪式目的相一致时才会被采用到这种仪式中去。因此,在礼仪与音乐的关系上,礼仪处于主导地位,乐处于从属地位。郑樵虽然强调礼乐二者的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的重要关系,但他没有指出二者之间的主从关系。无论是应用于鬼神的祭祀音乐还是用于人事的宾、军、嘉礼中音乐,其对礼仪仪式的依赖性是不可避免的,仪式对音乐具有绝对的选择权。
三、结语
从根本上说,作为统治者实现上下有序、尊卑有等这一目标的工具,各种礼仪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的。作为礼仪中所使用的音乐,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与各种仪式行为动作一起为实现礼仪的最终目的服务,“三礼”中以具有鲜明政治含义的乐歌和刻意区分尊卑的用乐方式来为仪式服务的思想,就是实现乐的政治功能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礼乐关系上,“三礼”中的礼乐关系始终是以礼为核心,以乐为从属。后世的制礼作乐基本上是延续了“三礼”的这一礼乐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对中国礼制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473061)】
①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96页。
②④⑥⑩⑮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78、1686-1687、845、1067、985页。
③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1-103页。
⑤⑭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39、1424页。
⑦⑪许兆昌《先秦乐文化考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230、186-204页。
⑧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3页。
⑨薛艺兵《仪式音乐的符号特征》,《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2期。
⑫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58页。
⑬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113页。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2014年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魏晋南北朝礼仪用乐研究”(编号:2014-qn-098)、南阳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编号:zx2014020)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