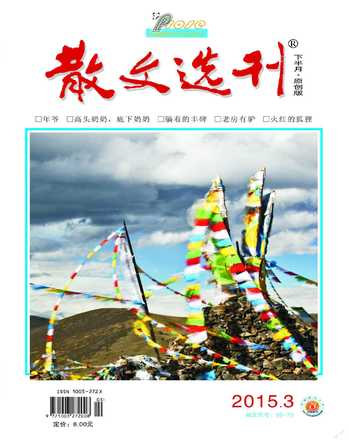老房有驴
王福利
已成街道的老宅上,那棵40年的老枣树还在,树身上那些啃疤一圈一圈的,重现着一头小驴拴在院里闲得啃树皮的画面。
那些年,小驴的弱小让我们家抬不起头来——在那个人扛马拉的非机械时代,每次赶着小驴下洼干活,总会成为路人打趣的对象:“大眼贼儿!”不管人们说什么,似乎也听不懂人们说什么,它每天都是精神百倍地高昂着头;现在再想起它的模样气质,虽然个头矮小,但绝对是驴中的“美男子”,只是车上人那时还是孩子,只看到了它的缺点。
庄稼人常年与牲口打交道,也如人与人之间摸透了彼此的脾气:偷奸耍滑的牲口,仿佛能比人看事看得更透彻——下地干活的路上,故意磨磨蹭蹭走得很慢,而且自己拣好道走,让车轱辘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干活的时候,叽叽歪歪,就是不听主人召唤,你把犁头插得深了,怎么抽打它也不动弹,你刚把犁头挨上地皮,它呼呼地一顿快行,反正就是剜着心眼地想着自己怎么省劲;只有在回家的路上,它才会显示出生机活力,恨不得一步到家快些歇着。如果用这些反面牲口对比的话,小驴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那些比它高壮很多的大牲口,尽管每次耠地耙地耩地都没有大骡子、大马干得快,尽管拉了没有太多庄稼、坐车的人怕它拉不动都下来走,但每一次,快步急行的小驴都是浑身被汗水打湿,站在它旁边就能感觉到汗水的热气,累得吃不下草料。看着它累成这个样子,母亲总会在槽里撒上厚厚一层玉米或高梁。
聪明的小驴也懂人的心思,只不过没有用在偷奸耍滑上。每年“耠青”的时候,邻居们又把它当成宝贝一样抢,东家借,西家牵,对于人们口中的“大眼贼儿”来说,不亚于一年年的生死坎。天不亮,母亲就提前给小驴加喂精料,没等小驴吃饱,借牲口的人来了牵着就走,一直到后半晌,甚至黑天,才将浑身像洗了澡一样迈不开步的小驴拽回来,不是累得没有一丝力气,要强的小驴何曾焉头耷脑、走路拖沓!那一次送驴人来的时候,母亲一眼就看到了它后腿上一尺多长的血道,走路也有些瘸了,可是牵驴人却只是一句轻描淡写,转身就走了;心软的母亲,那次甚至疼得掉了泪。
应该就是在体力透支的那几年里,本没多大气力的小驴,短短几年变成了老驴,虽然还是小驴的体型,但也如人一样在头顶、唇边有了斑斑点点的灰白。
小驴对于母亲,用父亲的话说,它就是母亲的“腿”;它的腿伤了,母亲能不掉泪吗?就是在我已上初中的时候,有次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去姥姥家,大冬天的正赶上顶风,十多里路歇了好几次,母亲看我累得大口喘气的样子,此后再没有让我用自行车带过一次,又像以前一样赶上了小驴车。那时已长大的我和姐姐,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坐在她身后的车厢里,也听不到她再跟我们念叨小驴是如何如何地认路通人性,不用人指挥,就一路小跑着跑到姥姥家,遇到对面来车,它还知道靠边让路。母亲赶车的时候,不同于父亲赶车时人们的调侃,而是变成了笑闹里的夸赞:“哟!可真不赖,自己赶着车出门啊!”如果没有小驴,不知母亲要少回多少次姥姥家。
也是在人们半真半假的夸赞里,每逢过年、过节、赶庙会,母亲赶着小驴车,拉着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拉着房前屋后的婶子大娘,踏着清脆的节奏,穿行在十里八村的土路上。虽然年纪小,却也像母亲一样心疼着满车人的分量给小驴带来的负担,却也更深地印存着那份沉浸在无比兴奋中的感受,至今那幅画面还是如此清晰——河堤两侧的树林里,被小驴的串串蹄声时而惊起一只啄木鸟,从这棵树飞跳到那棵树;时而一群麻雀从林中飞起,在天空闪过一片乌云;我和小伙伴坐在颤颤悠悠的车里,用弹弓瞄准着前面的一树喳喳嘈杂的灰白绒球,对笑谈着家长里短、乐得嘎嘎的婶子大娘们的闹腾劲儿抱以厌烦表情。好不容易赶次大集,待婶子大娘们凑齐在拴小驴的地方,已是下午一两点钟,小驴就那么老老实实地等在那里,一等就是多半天。
用母亲的话说,小驴特别“仁义”,不只是别人家的妇女能够放心大胆地赶着它下洼出门,就是一个小孩子,也能牵着它说走就走,不尥蹶,不咬人,不乱跑。每次母亲赶着它回姥姥家的时候,刚刚十一二岁的小表哥都抢先从母亲手里接过缰绳,非要骑着小驴满洼里转几圈;每一次,小驴都是低眉顺眼地听从着表哥稚嫩尖嗓的吆喝,缰绳拉到哪里,它就咯嘚咯嘚地走到哪里,直到在光溜溜的驴背上磨得屁股生疼、两条裤腿上沾满了驴毛,小表哥才在大人们的哄笑里恋恋不舍地下来。临走的时候,小表哥又抢过缰绳,帮着母亲套上车,看着小驴在母亲的一声命令下欢快地踏上熟记于心的回家的路。
我后来出去上学上班,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小驴留下的印象也越来越淡——姥姥姥爷去世后,母亲已很少赶着它出门,更舍不得卖它,父亲就买了一头驴,同时养着两头驴,它终于可以歇一歇了。再到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父亲还是将它卖掉了。
父亲说,买它的,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是为了赶集卖货拉脚儿用。早已不是孩子的我,虽然失落,却也心里好受了些——毕竟脱离了庄稼地里的重活,毕竟没有因为它的老去无用而被卖到屠宰场。但愿它在那个老人的平静余生里,安然度过一头老驴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