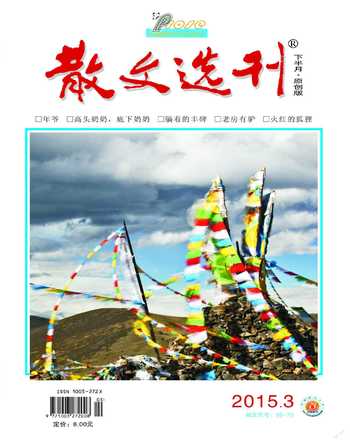碓砸的年味
王胜华
用碓臼舂饲料喂猪,猪一天比一天长胖,年味一天比一天加浓。
过年的前几天,家家都要将碓棚上的干枝腐叶清除干净,砍来叶鲜枝活的树枝翻新碓棚,洒上清水,铲草、除尘、净碓、晾干,在碓臼周围撒上青松毛,准备舂过年的粑粑了。
山村地多田少,有糯米的时候,人们就舂糯米粑粑;没有糯米,人们就舂饭米粑粑;没有米,人们就舂籼米粑粑。临近过年的那几天,整个山村从早到晚,碓臼橐橐,粑粑飘香,年的喧嚣、年的色彩、年的味道就布满整个山村。一到这个时候,山村里没有碓的、碓不好使的,都要来借爷爷的碓舂粑粑,我就可以和朋友小伙伴一起玩了:或一起帮着去踩碓;或裤兜里装着红红绿绿的鞭炮,跑到牛路上去,将鞭炮一个一个解下来插在牛屎堆里点燃,把牛屎炸得满天飞溅……用完了碓,邻居都客客气气,或以一块粑粑来酬谢我们,或以几句暖心窝子的话来酬劳我们,因而我们往往能够吃到不同口味的粑粑,也能够在年前就收获一堆比粑粑更受用的祝福。
邻居舂完了粑粑,自然就轮到我们家舂粑粑了。母亲就拿出那把用马樱花树筒挖出来的大水瓢,在清水里沤湿,从饭甑里撮出满满一大瓢饭,快步走来,将热气腾腾的饭倒在碓臼里,斜着身子,蹲在一旁来抱碓。母亲抱碓,同样是一把好手,她动作协调,眼明手捷,从不会让粑粑脱离碓杵,掉到地上,也从不会让碓头砸在脑门儿上,因此,我们家的粑粑舂得又快又好,从不会中途停歇。
舂粑粑和舂捣谷物还真不一样:粑粑有黏性,得两人踩碓,一人抱碓;开始的时候得轻轻地踩,悠悠地放,待饭粒完全黏在一起之后,脚上有多大劲,就得使多大力,让碓头高高地仰起来,重重地砸下去。幸好要过年那几天,家里人多,可以不停地更人换脚。如果舂糯米粑粑(糍粑),母亲就把粑粑牛屎堆一样放在炒面上;如果舂饭米粑粑,母亲就会扣一点猪油抹在手上,趁热将粑粑揉捏成白条小猪的模样,堆码在青松毛上面,青青白白,透出年的喜气,又惹眼,又逗馋。有时候,我们围站在母亲旁边不肯走远,母亲就撕下麻片,吐口口水搓成麻线,将粑粑头勒断了给我们解馋。虽然每次都能先饱口福,但每一次舂完粑粑,我们都会争着去啃干净粘在碓杵上的那点粑粑碎末。
都过去这么些年了。
有一年,我们提前奔回老家,准备过年,等打扫完房前屋后,正准备给碓棚撤旧换新的时候,母亲就说:“自从山寨通了电、跑了车,碓就不再适用了。不仅如此,年年都有外地人一车一车地拉粑粑来,只要撮几升包谷,就可以换回过年吃的粑粑,不用再舂了。”
就在这个时候,村口传来阴阳古怪的吆喝声:“换——粑粑过年喽!”“换——粑粑过年喽……”声音很大,让寨子里的什么角落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声音,虽然给年前的山寨添进一抹年的喧嚣,可我总感觉故乡的年味少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