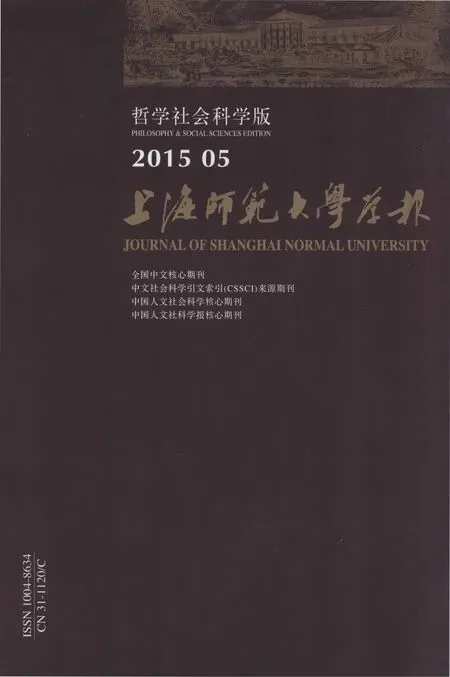《列子》自然本体论的音乐欣赏审美
卞鲁晓,张允熠
(1.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列子》文本中关于音乐的文字主要着眼于音乐作为一门具体艺术的审美经验及其内部规律,对于音乐的论述大多从艺术本身的特质出发,少有涉及音乐与政治、教育关系的问题。基于此,它的音乐实践活动更多地强调音乐本身所带来的审美愉悦,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谈及音乐实践活动中最后一个环节——音乐欣赏。《列子》以为在音乐欣赏中人们可获得音乐美感,这种美感不仅仅是感官的简单体验,更重要的是精神愉快和知性满足。这种感受既体现在“余音绕梁木丽,三日不绝”①的审美心理效应上,也体现在“子之听矣!志想象犹吾心也”②的明确音响感知、深度情感交流和想象联想之中,以及对“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③的音乐自然之道的理解。
一、“余音绕梁木丽,三日不绝”:审美心理效应的再现
音乐作品及作品的表演使欣赏者感受和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内容和思想意境,这是一个由表层欣赏到内在体验的过程,《列子》用“余音”来说明声音的表层结构消逝以后,欣赏者所感知到的音乐里层,用“三日不绝”的艺术夸张描述欣赏者被音乐精神等内在的情感深深打动的情形,由此而进入到忘记自我和身处无我之地的境界,在情感上无论悲伤还是喜悦总能与创作者产生共鸣,在痛苦或者欢乐中精神得到升华,从而产生审美效应。
《列子》记述了一则关于音乐的故事:“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木丽,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遗声。”这段文字涉及了音乐欣赏心理效应的几个层次,首先韩娥用原生态的演唱、无多余加工的声音,借声音的高低、长短、轻重、缓急等,从感官上深刻地打动听众,产生“既去而余音绕梁木丽”的效果,使人们在无关联的现实生活中仿佛还能找回音乐的踪迹,“三日不绝”时时回味声音的抑扬顿挫、丰满圆润,这是音乐所形成的听觉记忆,也是音乐感性知觉的最明确表述。这种感知本身也伴随着音乐欣赏的第二层心理,即情感体验。
音乐是长于激发感情的艺术,是常态情感与音乐情感交相传导的中介。“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韩娥因受辱而产生激烈的悲伤情绪,这一情绪是主体自身主观经验到的一般情感,是对客观所历与自身相联系引起的一种态度,是对现实的最贴近的判断、评估和反应,单纯而直接同时伴随着介于情感与理性之间的知性因素,即内在诉求的流露。然而这还不能称之为音乐情感,因为音乐本身所内含的情感并不只限于人的喜怒哀乐,它常常是某种精神和品格的结合。当韩娥长声哀哭以歌唱抒发情感,把痛苦、希求体现在旋律之中,把具体的不幸与心酸等一系列心灵体验置放于歌声中,这时她的心灵处于一种内容丰富而复杂的空间,并同时赋予所唱以具体的、可感知的音乐情景以及自我精神,使音响所形成的意象与情思、心愿密切联系,成为欣赏者可以感受和领悟的音乐。欣赏者的领悟并不是来源于单纯的声音的运动,而是源于内含了歌者特殊的、经过曲折转化的、以音乐为形式精巧安排的情感体验,正是这种音乐情感唤起了听众的想象和同情,相应地产生了激动的情感效应:“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如果说老者被触动了心弦,幼者则感于歌声所携之激情产生的知性之真,迅速转化为未成年人的情感体验,形成音乐欣赏中的主体间性,造成一种为之悲愁、垂泪相对、食不下咽的心理效果。由此可见欣赏者可以在充满激情的音乐中无限地把自身投射于音乐中去,这时的音乐欣赏心理正处于一种是“我”而“非我”的状态之下,形成一种歌者与听众的情感交相流淌的互动模式,即使音乐感性形式随生随灭之后,仍然渗透到听众的心灵并占领当下的意识,持久地感受着音乐传递的情感,使他们或“垂涕相对,三日不食”或“喜跃抃舞,弗能自禁”。
唐人卢重玄《列子解》对上述文字解曰:“夫六根所用皆能获通。通则妙应无方,非独心识而已。”“六根”即眼、耳、鼻、口、舌、身六种感觉器官,“皆通”表明感知在“意”的作用下形成审美通感,“心识”则指知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列子》对音乐欣赏心理的描述。美学家朱光潜认为:“近代美学所侧重的问题是:‘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至于,一般人所喜欢问的‘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算是美?’这一个问题还在其次。”[1](P3)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文本夹缝中,不仅有着对审美体验的具体描述,也在这些文字中暗含着对于审美心理的记录,这一记录既包括音乐创作主体的心理活动凝结在音乐作品中通过乐音流动展现出来的过程,也包括作为欣赏主体的心理活动,比如音响感知、情感体验、想象、联想和理解认知,等等,这些心理活动在欣赏不同的音乐时所起的作用不同,所占的比重也不同,倘若要达到对音乐及作者的深度理解即理性欣赏,那么对欣赏者自身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才有《列子》所谓“知音”的故事。
二、高山流水觅知音:乐山乐水知人的情怀
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用音乐寄情巍巍高山和潺潺流水,把自我的全部身心寄托于外界事物,以为心物可以相感,用乐声的音响形式模拟自然的风貌,并把自我的人格特征看成与山水相类,视山水为可以达成精神交往的另一主体,《论语·雍也》有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与仁兼而有之的人格理想经由音乐创造的山水意象传递出来,被真正的音乐欣赏者深切感受到,与演奏者内在情怀和精神品格形成共鸣,从而进入更高尚、澄澈、震憾的境界。《列子》所记伯牙一曲高山流水觅得知音的故事,体现了基于音乐自身的感情体验和哲理思考的音乐鉴赏乃至于对人自身的欣赏过程,集中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音乐美感的深度理解。
伯牙是战国时楚国人,曾在晋国为官,是一位抚琴大师,关于他的记载曾见于《荀子·劝学》“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伯牙有移情入乐、以琴表达心志的创作本领,据传作品有《高山流水》、《水仙操》、《怀陵操》等。钟子期也是一位楚国人,成长于音乐世家,曾是一位乐尹,后退隐山林之间。汉代高诱《吕氏春秋》注:“钟姓也,子通称,期名也。楚人钟仪之族。”可见,钟子期是一位有着很深的家学渊源和音乐修养的隐者。关于他们之间的知音故事曾出现在几十种古籍中,繁约不同、阐释各异,较早期的记载见于《列子·汤问》和《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就深层意味而言,《吕氏春秋》云:“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2](P140)其写“知音”意在强调知音难求,表述了普通人的心声,启迪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识人用人的道理。而《列子》则以此为结语:“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矣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其知音的故事重在音乐欣赏的深度分析,不执着于知音难求而是强调音乐审美在穷其趣,强调通过意境支配下的音响感知、想象和音乐所承载的情感、志趣以及哲理思考的结合,实现对音乐境界的充分理解并与创作主体的心灵沟通,其着重点在于音乐是人与人在境界层次沟通的中介,而非《吕氏春秋》的所谓王政之道。
就音乐的感知而言,轻松愉快的歌曲内容直浅,使人心神愉悦,听众无需从深层去感受乐曲的形象、意境,直觉即可欣赏这样的音乐,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只能算是音乐欣赏的最初阶段。而深邃的器乐曲如果达到真正的欣赏目的则需要通过音乐意象的触动,深入理解乐曲表现的内容,与音乐内涵的创作情感产生深深的共鸣,才能领悟到音乐所蕴藏的哲学构思以及所要表达的意向追求。“音乐不仅是一种用声音抒发感情的艺术,而且还能够通过感情的深刻抒发和音乐形象的逻辑发展来表达深刻的哲理思想。”[3](P79)音乐音响形式只是音乐结构的表层,透过这个表层以音响为载体的创作主体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能否被欣赏者准确把握或理解,还在于欣赏者自身的音乐感知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来存在着,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4](P79)这里的感知正是音乐审美的感知,是最早见于《礼记·乐记》的“知音”一词最本源的意义,“审音以知乐”、“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也是《列子·汤问》所谓“子之听矣,志想象犹吾心也”所表达的由音乐的深度感知进而发生联想,从创作者那里获取精神力量的审美过程。
就音乐的美感而言,不只是在乐音中获得感官愉快,更主要的在于精神的愉悦和情感的满足,这是音乐演奏与欣赏两者的互动过程,双方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实现精神的交流,其前提必如《列子》所言“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相同的人生经历、类似的生活体验、共同的志趣爱好使钟子期对乐曲的音响感知、感情体验、想象联想与伯牙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用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矣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④伯牙以高妙的演奏技法对高山河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音响再现,这些音乐意象的塑造融注了个人的情感、意志和理想,他期待人们通过音乐与其达成共识,否则亦不能在演奏获得美感,正所谓“若无子期耳,总负伯牙心”。⑤张湛《列子注》评价这段故事:“发音钟子期已得其心,则无处藏其声也。”认为钟子期作为一位理想的音乐听众,在置身于音乐之中的同时更置身于音乐之外,看见伯牙的创作意图,对他的生活与艺术表现出欣赏的态度,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两者成为知已,传为千古佳话。
《列子》用故事表述对于音乐欣赏的认识,卢重玄《列子解》对此做了总结:“夫声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声则随之。所以五根皆通,心为识心所传。善于听者,声咳犹知之;况复声成于文,安可不辩耶?”音乐本身并不是对事物确切的描绘和反映,而是对事物相关的情感世界的深度探掘和声音抽象,在仿若巍巍之山、潋滟之水的音响律动中,与欣赏者所见、所历形成理解的基点,在声音的所激起的遐想中传递富有意味的情绪和确定的思想意境。音乐作为媒介,一百个人听它可能就有一百种不同的主观联想,既然音乐创作本人带有情感内容去创作音乐的,那么欣赏者就必须带着探索音乐语言的能力才能把握正确的音乐运动形态。马克思说:“如果你想得以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4](P108,P109)否则不能从中体悟到创作的内在情感运动轨迹。伯牙志在高山之巍峨、流水之宽广的艺术境界和人生理想在音乐意象里展现,以音乐概念的形式尝试说明自己,善听的钟子期以听觉细心品味,以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共同的生活态度为基础,对伯牙创作的生动、凝纯的音乐主题形象做了大胆的联想,实现了相互间非语言的心智交流,也使音乐欣赏在理性认识的指引下达到了更深刻的阶段。
音乐的理性欣赏前提在于音乐情感体现着音乐主体的精神和性格,“志在登高山”强烈地表现出伯牙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不仅在于对现实客观事物高山的形象表现。钟子期在伯牙所演奏的乐曲中体验到并欣然接受的是伯牙对现实生活、人生际遇、意志理想的艺术表现,而且在自己的意识中再创造出来,他们两人的感情在音乐欣赏中获得交流、双方的内心世界得到沟通,审美评价因恰如其分而使彼此增加了审美的愉快。中国传统乐山乐水的情怀也在音乐的流动中朝向自然的方向发展,形成一种以自然之道为精神追求的音乐终极理想。
三、“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把握音乐的自然之道
《列子》文本多处论及音乐艺术,是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说,音乐是最纯粹的艺术,是能够通过声乐和器乐充分体现形而上之思的工具,它因无法借用具体事物的表象形式来表现理念,就在音乐本身的形式中内在地反映人的自由存在方式,同时传达给音乐欣赏者。《列子》是对人的自由生存方式进行深度思考的文本,它对音乐意象的描绘、音乐悲美精神的探索、音乐欣赏的深度理解无不彰显对于生存本身的哲学追问,那些流于表面化、片面性的音乐以及与此相应的最低层次的音乐感受,被《列子》看作生理上的快感,即使欣赏者痛哭流涕也不过是情绪上的共鸣,虚构意象的简单化的呈现,而最深远的志向和情操则在于形而上学的无限性,即音乐的自然之道。《列子》对这一音乐本体的表达是借孔子与弟子之间关于音乐的对话而以逐层推进的形式展开的,它运用了逐步破旧说从而立新说的方式,带入对音乐以自然之道为本体的新表述“无乐之乐”,把老子所谓“大音”和庄子“天籁”加以整合,开启对音乐的形而上学的认知。
琴在中国古代是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工具,音乐是文人们表情达意的中介,《列子》以儒家士人为故事的主人公究问音乐的本质,设定了三个不同的音乐层次,并对三个层次的内涵逐次进行了分析,最终推演出音乐的最高境界在于“无乐无知”。首先,音乐出于情性之本。故事中颜回援琴而歌、自得其乐,其言“乐天知命故不忧”,他的老师孔子对此评价说:“修一身,任穷达,知去来之非我,亡变乱于心虑,尔之所谓乐天知命之无忧也。”认为颜回沉浸在个人的无忧无虑的心境里,无视生存中的诸多可忧可惧,抒发自我的无关于治乱的小我情怀,在这个层面上琴歌是畅情的工具,是抑制心中变动混乱的自我修养法则,是最低层次的学养工夫。
其次,礼乐出于治国之大义。《列子·仲尼》借孔子之口对他自己关于儒家所谓礼乐政教的认识给予了否定:“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遣来世;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矣?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乐天知命者之所忧。”张湛在此文下注曰:“唯弃礼乐之失,不弃礼乐之用,礼乐故不可弃,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为忧者,将为下义张本,故先有此言耳。”当音乐被负荷治理天下、遗留后世的社会责任,用于修身乃为治国以平天下,心意执着于礼乐之所功用,音乐便失去了仁义情性之本,最终只能是无助于治乱,反而使仁义更加衰落、人情愈加浇薄,走向音乐之怡情的反面。音乐不再是自娱娱人的工具,不再是抒发人情哀乐的钟鼓之声,也不再是政教适性的统治手段,而是失其本而无所用之乐。
最后,音乐自然为本体的人生境界。《列子》音乐表现人生境界的态度终于呼之即出:“夫乐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谓乐知也。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故无所不乐,无所不知,无所不忧,无所不为。《诗》、《书》、礼乐,何弃之有?革之何为?”此言下张湛注:“庄子曰:‘乐穷通物非圣人。’故古人不以无乐为乐,亦不以无知为知。任其所乐,则理自无乐;任其所知,则理自无知。都无所乐,都无所知,则能乐天之乐,知天下之知,而我无心者也。居宗体备,故能无为而无不为也。若欲捐诗书、易治术者,岂救弊之道?即而不去,为而不恃,物自全矣。”在《列子》看来,音乐艺术既不是对现实的逃避,也不是对现实的描摹,它应该是士人对于自然宇宙总体的感悟理解,无论是个体的生命安放,还是群体的和谐存在,都已然包括其中,正像中国传统哲学所认为的,一切变易之数皆来自于不变之一,一切出于天命之性情自然之道的才是音乐之本,这个本是与道合而为一的终极,当这个终极之本统御音乐,作乐用乐顺应自然,则不治而治,《诗》、《书》、礼乐抛弃抑或者改革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忧与不忧的执念使音乐蒙上无法大全的阴影,那么音乐则无法超越时空之外,只能局限于物境空间的有限时空关系中,不能展现生命最本真的律动节奏,以及主体精神境界的高妙与神采,因此才有所谓“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至此《列子》音乐本体落实在自然无为的人生境界上,“真乐”成为声、情、道三者统而为一的本真之乐,使万物得以自然而然地显现,既没有语言、空间形式,也没有某种物质载体自身特殊性的束缚,因此在表现非个别物、普遍存在性方面更具有直接性,这与中国人以感应的方式进行的审美发生方式相互印证,也与中国特有的形而上学相互契合。这也正是《列子》关于音乐欣赏论述的真正终点,即对音乐自然本体的思考。
总之,在《列子》一系列与音乐相关的故事叙述中,有这样的一条由现实感受而至于艺术境界的思维路径。音乐欣赏的内容不局限于纯粹的自然事物的意象,更在于音乐意象背后音乐创作主体内在的生命追求,这种生命追求使音乐欣赏主体在音乐联想中回返自身、重新发现内在的自我,并在音乐的激发中以个体独特的情感去主动容纳和跟随音乐,达到主体间情感的融合和美感共鸣。这样的艺术共鸣在《列子》看来,是在感觉山水意象的瞬间,因音乐的引导而体悟世界万有生命形象的深层节奏的起伏。大自然无形的生命力在音乐音响传递中得到充分表现,内含着主体的人对于历史、人生、宇宙的情思,使有限的主体进入澄明的境界,这个境界蕴含着浑沌的生存意识,以及人生和宇宙的哲理,不是对宇宙生存的抽象概括,而是一种神秘的感悟,因音乐表现的不受拘束于任何具体物象和语义限制的特性,展现出无限性的本体特征。《列子》把音乐意象提升到境界的层面,万变归一的终极自然之道,使作为技艺的音乐艺术通过最初的感知到达虚实之间的领悟,这是深层的审美分析,也是对生存之娱的最根本看法,成为《列子》全部生存理论的具体出入口,从而完成了在本体层面对音乐的最后界定。
倘若我们能细致地清理这些见诸各类著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特别是在哲学史上偏于一隅的一些作品,如《列子》文本中的音乐美学思想,总结历史文著中的音乐实践经验,有助于科学地评价传统文化中的音乐学遗产,进一步丰富我国现有的音乐史学资料,提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更好地为丰富社会主义民族音乐服务。
注释:
①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7页。下引此书只注篇名。
②《列子·汤问》。
③《列子·仲尼》。
④《列子·汤问》。
⑤(清)秋瑾:《咏琴志感》。
[1]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广益书局,1936.
[2] 吕不韦.吕氏春秋[M].高诱,注.上海:上海书局,1986.
[3] 张前.音乐欣赏心理分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