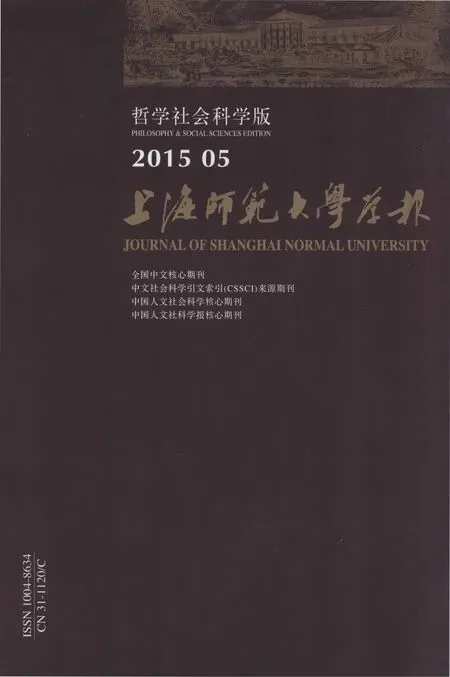帮会文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关系探析
——基于文化犯罪学的考量
汪 力,蔡 颖
(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716)
文化犯罪学(Cultural criminology)是近代学界对犯罪与文化的交叉领域进行探究的较新视角。[1]这一视角促使我们将犯罪及其控制放在文化的语境中,将其视为文化的“创造性的构筑物”。[2](P80)这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犯罪的本质,找到犯罪更本源的发生原因。我国学界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文化犯罪学研究,几乎都将其与帮会文化相联系。[3](P232)但是这些研究多是就帮会文化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促进作用进行剖析,而对帮会文化本身的内容、帮会文化何以在社会变迁如此巨大的今天仍能存在,以及帮会文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深层联系等问题的探讨略有不足。而这些问题是通过文化犯罪学来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前提所在,如果不能说明以上问题,帮会文化不可能成为文化犯罪学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切入点,更不可能通过帮会文化来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本文拟从帮会文化的价值层面入手,探析帮会文化的核心内容,梳理其历史变迁,发掘其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深层联系。
一、文化与帮会文化概念界定
“文化”最早的通行的定义是泰勒提出的。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概括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4](P1)这一早期的尝试一开始便试图使文化囊括所有与人相关的事物,[5]之后各个领域比如社会学、历史学甚至生物学等分别根据自身研究需要提出了不同侧重点的定义。[6]“文化”是极具包容性的抽象的概念,为其做出普遍适用的定义是极其困难的。这一概念缺乏学术研究应具有的定型性,所以需要效法前人根据研究需要为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划出一个明确的范围,以更深入具体地研究文化与犯罪的关系。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观念,尤其是它所带来的价值。[7](P8)文化的价值层面是文化的核心,不仅决定了文化本身的诸多因素,而且是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关键所在,对文化的价值层面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所指的文化则限定在文化的价值层面。①
帮会文化是帮会特有的文化,要认识帮会文化首先应该界定何为帮会。帮会一词出现较晚,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帮会(洪门、青帮和哥老会)都是清朝出现的。封建时期的帮会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在人员组成上,帮会由游民组成。帮会是由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游民等江湖流浪者组成的集团,[8](P81)在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上述的江湖流浪者都是脱离秩序之人,属于广义上的游民。其次,在组织结构上,帮会具有特殊的组织形式。“帮是以师徒宗法关系为纽带,是封建行会的变异形态;会是以兄弟结义关系为纽带,是血缘家族的变异形态,19世纪末期以来,帮与会相互渗透、混合生长,人们遂以帮会统称之。”[9](P1)其中,师徒关系是对父子关系的模拟,兄弟结义实际上是对兄弟关系的模拟,因此帮会实际上是通过模拟宗法血缘关系形成的组织结构。再次,在行为规则上,帮会有自身的行为规则,多为帮规、帮训等,而这些行为规则通常是凌驾于道德、法律等社会规则之上的。[9](P85)帮会的特点决定了帮会文化的特殊性,使得帮会文化成为与主流文化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亚文化。
1.“义”是帮会文化的核心
假如说中国传统宗法制的伦理核心是“孝”,国家君臣关系的伦理核心是“忠”,那么,帮会文化的伦理核心便是“义”。[10]义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之后更多地在民间流行。[11]据笔者计算,洪门入门誓词《三十六誓》(总共36条)之中与义有关的占35条(97.2%),帮规《二十一则》《十禁》全部与义有关,《十刑》中关于义的规定占9条(90%)。[12](P31~38)另外,“若有奸心辕门斩,忠心义气伴明君”。[13](P293)在洪门的诗句、口白等暗语中,也处处体现出洪门兄弟的义。可见,在帮会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义,帮会的行为规则、符号系统等都是围绕义展开的。
在古今汉语中“义”字有多个含义,笔者将《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及《两岸常用词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等工具书的相关词条进行总结,认为“义”的字义中与文化的价值层面有关的主要有二:其一与“宜”相近,指适当的、合理的,延伸为正义、公理之义;其二与“谊”相近,取情谊之义。帮会文化中的义(以下简称“义”)与上述两种意思都有联系,但其本身含义较为复杂,不得不分层述之。
“义”最表层是指伦理之义(正义),意思与“宜”相近。这个层面上的“义”与封建伦理中的义的意思基本相同,具有一定的自然法意味,代表着人应当具有的一般的道德准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正义并没有帮会与非帮会之别,这个层面的义是帮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通之处。
“义”的中间层的含义是游侠之义(侠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③这句话虽然是描写游侠的个性,却也将侠义的含义进行了全面的概括。侠义是舍己为人,重视诺言而且“不轨于正义”。这里所言的“正义”等同于前述的正义,也就是说侠义更在乎的是内心的信念和自己信奉的准则,而非主流伦理。侠义是一种游侠精神,游侠属于游民的一种生活状态。前面说过,游民属于脱序之人,与主流文化相脱离,所以游侠的行事方式已经不再以主流文化的正义为最高准则,甚至对主流文化有一定的对抗,这也是侠义区别于正义的关键。侠义包含了正义的诸多因素,但更加注重结果,轻视甚至无视主流道德、法律的约束。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张翼德鞭笞督邮等故事,便是通俗文学对侠义的注解。
“义”的核心层的含义是兄弟之义(义气)。侠义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义气则是对主流社会的公然对抗。义气是帮会文化中最重要的义,是指为了帮会中的兄弟、集体,可以牺牲自己,也愿意违反法律、道德。洪门三十六誓第一誓:“自入洪门之后,尔父母即我之父母,尔兄弟姊妹即我之兄弟姊妹,尔妻我之嫂,尔子我之侄,如有背誓,五雷诛灭。”[12](P31)这段话便是对义气的经典概括。帮会文化的主要功能就是将无数分散的游民联结起来,使之在互助中求生存。[14]义气作为联结游民的精神纽带,将兄弟、帮会凌驾于道德、法律甚至自身的利益之上。在帮会文化的氛围之下,弱势的游民不分彼此、相互扶助,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集体。在如此强排他性的价值观念的作用下,分散、弱小的游民才能组成集中、强大的帮会组织。如果没有义气作为纽带,帮会和帮会文化将不能存续。
正义、侠义与义气这三个层面的义以涟漪状的关系展开,最重要的是义气;而侠义和正义多是帮会成员自身的选择,经常被帮会文化作为标榜,却非帮会文化必须所有的。综观帮会文化三个层面的义,虽然各有侧重,但却总与一定的牺牲精神相关联。正义追求普遍的道德准则,必然意味着对私欲的克制;侠义强调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义气更是视兄弟、帮会等于、甚至高于自身。帮会作为游民组织,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集合,为何对牺牲精神如此崇尚?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帮会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
2.为利而生的帮会文化
帮会是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结合的集团,虽然建立在义的基础之上,但其最终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洪门天地会的“始祖”(万姓集团)实际上是打家劫舍的盗贼,[15]哥老会是由打劫旅客、船只的武装集团(啯噜)演变而来。[16]帮会的建立、发展甚至是壮大都与利益息息相关。利益又可以分为私利与集体利益两个层面。
集体利益是指帮会成员整体的利益,是帮会得以存续的关键。在帮会文化的价值中,集体利益是高于私利的。帮会成员为了帮会利益设赌贩私,为了帮会势力参与火拼,不惜违法犯罪、牺牲自身利益甚至是生命来维护和争夺帮会集体利益。私利是指帮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帮会成立或者个人加入帮会的最初原因。帮会的建立是为了实现帮会成员的利益,帮会成员之所以加入帮会也是为了从中获利。青帮秘籍中有诗云:“出门在外挨了打,露露家理沾沾光。若是断了盘费钱,凑上几吊你还乡。或者摊上小官司,众人拨钱你上堂……”④这两者虽然看似存在矛盾,但实际上帮会成员往往是通过实现集体利益来满足自身利益的。帮会文化,尤其是义气,使得帮会成员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完成私利与集体利益的统一。相对于其宣扬的牺牲精神,帮会文化更像是一纸契约。这一契约使帮会成员加入帮会后愿意为了帮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同时又能从帮会中获取其需要的私利。就算是为了帮会利益牺牲的成员,虽然其本身不能再获得任何利益,但是帮会将“感其忠义”而善待其家人。
义气形成了帮会组织的核心建构,而正义与侠义则推动了帮会的发展和壮大。例如近代美国的致公堂,作为洪门海外总部曾在“大佬”司徒美堂的带领下多次组织捐款支持国家革命与独立。上海青帮的杜月笙不仅没有受日本侵略者威逼利诱,还组织抗日后援、铲除汉奸。[8](P249~252)这些时候虽存在民族危机下正义的觉醒,但也有利益因素存在其中。正义、侠义的行为不仅为帮会存续的合法性、正义性背书,更为帮会带来好的名誉,吸引更多成员。因此,帮会文化的义并非是儒家思想中“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样对道德、正义的形而上的追求,义所包含的牺牲精神是悉心谋划的产物,是获取利益的工具。
二、帮会文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相关关系
虽然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个现代法学的词汇,帮会是近代俗语,两者并非同一层面的概念。但是如果将帮会文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视为独立的存在,则能看到两者诸多紧密的相关关系。
1.生存发展的同源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出现了长达25年(1953—1978)的社会治安黄金时期,其间黑社会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曾在大陆地区销声匿迹。[17](P90)彼时,由于文化结构的单一和排他,帮会文化亦如恶魔一般被封印于民间文化与传说中。改革开放后,经济、文化的开放与发展带来了必然的社会转型,在繁荣昌盛的另一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帮会文化不仅在流通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再度出现,还出现在街头帮派、犯罪组织中。帮会文化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如同一对双生儿同生同灭。帮会文化和黑社会(性质)组织之所以存在客观上的共生关系,是因为两者具有相同的存在基础。
如前所述,帮会文化是游民互助求生的工具。同样,黑社会(性质)组织也需要游民作为存在基础。社会转型中主要有两种情况造就大量的游民。首先,经济体制改革中,原有的计划经济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很多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相继破产。企业的破产潮带来职工的下岗潮、失业潮。原依附于计划经济的职工中大多数人能够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另谋生路,回归秩序。但是有一些并不具备赖以谋生的专业技能,使得其离开原来岗位后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遂脱离秩序成为游民。其次,城市的迅速发展和户籍制度的相对松动使得很多农民工进城“淘金”,由于农民工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不具备专业技能,所以在社会阶层中上升空间小,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其中一些农民工因此产生心理落差,脱离秩序沦为游民。[3](P237)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Q市已判决的1548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被告人进行统计,其中农民人数为373人(27.1%),失业人员为655人(42.3%)。⑤由此可知,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有近70%的人来自于游民阶层。也就是说,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样以游民阶层作为存在基础,在存在基础上与帮会文化高度一致。正是因此,帮会文化和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同生共灭,而且形影相随。
2.发展空间的共享
帮会文化之所以能够再生,主要是因为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道德规范控制的弱化加上法律规则的缺位共同导致了社会控制弱化。经济、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文化的活跃发展,而文化的活跃打破了传统道德的垄断地位,使得原有道德规则的约束力逐步下降。与此同时,社会变迁带来的人口流动使得熟人社会格局逐渐被打破,熟人社会的道德舆论工具不能再起到很好的规范调节作用。在道德规范控制弱化的时候,需要更加先进的法律规则进入以弥补其中的空白。当道德规范在社会诸多方面的作用逐步减弱,而法律规则还未真正起到作用时,就会出现规则的空白。在如此规则空白的时期和地域,个体的规则意识产生混乱,从而使得帮会文化有机可乘。同样,黑社会(性质)组织需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具有排他性的势力范围作为自身的发展基础,而其实现非法控制的行政区域或自然区域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区域的社会控制力比较弱。[18](P369)在笔者所在课题组重点研究的Q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多出现在娱乐市场、猪肉市场、客运市场、土石方市场等,而彼时相关市场或多或少存在监管缺位等情况。
3.目标行为的一致
帮会文化为利而生,是游民阶层互助求生的工具。同样,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犯罪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牟取利益。根据中国犯罪学学会对全国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统计发现,有高达86.3%的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获取了经济利益。[19](P16)在上述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存在的市场中,也多存在暴利。
不仅如此,在行为上,帮会文化具有组织性和反社会性。帮会文化具有一定的反社会性,将法律、道德等主流价值置于组织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之下。为了达到利益,帮会文化通常是通过将分散的游民组织成集体来达到。所以帮会文化所包含的行为规范是通过组织和违法犯罪来获取利益。根据《刑法》294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大特点亦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规范也包括组织化和违法犯罪两大特点。
帮会文化不仅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紧密相关,还不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影响。帮会文化分别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帮会文化促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和发展
我们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要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研究其为何以及如何在系统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复杂非线性相互作用下,自发组织起来实施犯罪。[20]社会系统中,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个自组织系统(非他组织),其形成、发展都是自发进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遵循如下过程:犯罪团伙→恶势力团伙→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组织→跨国黑社会组织。[17](P174)无论是其形成还是发展,都受到帮会文化这一内生力量的影响。
1.从分散到集中
帮会文化通过满足受众两大需求而产生吸引力。首先是情感需求。帮会文化的义是对血缘关系(通常是兄弟)的模拟,因此帮会文化使受众之间产生情感互动,当个人因为背井离乡或者其他原因脱离本身的社会关系时,帮会文化能够满足其情感需求。其次是利益需求。帮会文化的本质就是聚集力量互助求生,当个人获取利益的力量不足以获取目标价值时,帮会文化能够满足其利益需求。帮会文化通过本身的吸引力聚集一定的受众,帮会亚文化群体便产生了。帮会亚文化群体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该群体接受帮会文化但是并不一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表现为群体成员之间称兄道弟、互相帮助等。而且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互助具有排他性,即只在群体内部互相帮助,形成共同利益。
帮会文化是游民文化,无法从上层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文化、民间戏剧则是帮会文化的重要来源。[11]与游民紧密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多通过一些血腥、暴力的因素来渲染情节,刺激受众感官。这使得帮会文化与暴力、色情等亚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中有更多与暴力、色情等相关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流行于世,更加强化了帮会文化与暴力、色情等亚文化的关系。本身生活于底层的游民由于自我价值实现的缺失,生活于压抑之中,暴力、色情等亚文化为其带来感官刺激,扭曲地满足个人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帮会亚文化群体可能吸收暴力亚文化、色情亚文化等,从一个中性的亚文化群体走向越轨亚文化群体,从而具备违法、犯罪的倾向,典型的帮会越轨亚文化群体就是街头“混混”。当帮会越轨亚文化群体进行了犯罪行为,便从亚文化群体质变成犯罪团伙或者更高层次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2.从无序到有序
帮会文化中的义气并不是一律平等的义气,而是尊卑有序的义气。帮会文化不仅有吸引游民、不断壮大的天然倾向,而且还有不断完善组织体系使组织不断进化的倾向。这是由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生态环境和帮会文化两者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其发展严格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所以组织中更有资历、势力的成员会得到更多的资源。而帮会文化是协调帮会集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工具。为了使得自然淘汰规律更加具有合理性,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帮会文化会促使其产生内部组织结构分化,在内部分化出不同的层级。这不仅使得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利益分配更具有合理性,而且推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向更高、更复杂的方向发展。
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层级分化,犯罪的分工也会变得更加细致。高层级的成员进行组织、领导性质的犯罪活动,低层级的成员进行参与、实施性质的犯罪活动。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甚至分化出了专门使用暴力的“保安部”、进行贿赂的“公关部”等。这样的精细化分工使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更加“专业化”,形成更强的社会危害性。
3.从弱小到强大
帮会文化能够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帮会文化将利益,特别是集体利益作为最重要的价值目标。较为低级的组织只能进行成本较低的犯罪行为(比如抢劫、盗窃等),这些犯罪通常风险较大而且收益较小,无法完全满足组织的利益需求。为了进行更大收益的犯罪(比如贩毒、贩卖军火等),组织必须扩大自己的规模和势力。而当组织能够完成利益更大的犯罪且牟取了更大的利益,则又有了更多的资本来扩大自己的规模,为自身寻求保护伞以及培养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势力。如此不断循环,推动着组织的自我发展。另外,如上所述,帮会文化能够满足受众的生理、心理两方面的需求,这促使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够产生对外界个体,特别是游民阶层的吸引力;这也客观地推进了整个组织的发展。
另外,帮会文化与一些特殊的亚文化结合,扩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触及范围、更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方法。如市场竞争文化促使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进入市场,将犯罪黑手伸向市场领域,通过恶意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又如一些企业亚文化与帮会文化结合,使得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形式转变,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披上合法外衣。例如1999年破获的佛山“水房帮”就是以公司为组织形式;近来破获的刘汉、刘维的犯罪集团也是以“汉龙集团”为组织形式。这些亚文化本身是中性甚至是有益的亚文化,但是当帮会文化与其结合,就使得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加隐蔽、犯罪手段更加智能及犯罪触手无孔不入。
四、帮会文化产生多种力量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1.形成犯罪的内在驱动力
犯罪学家莫顿认为,将获取财富作为文化目标,而获取财富本身被过分强调以至于制度性手段的价值(道德、法律等)被忽视,致使人们认为无论是否通过制度性手段获取财富,都能被视为获得成功。这就导致了制度性手段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引发犯罪。[21](P168~171)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通过制度性手段来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希望很小,但是帮会文化的本质却将利益作为价值目标,宣扬“论称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方式。同时,帮会文化暗含对主流社会规范的排斥,导致制度性手段的价值被忽略、甚至贬低,使得组织成员犯罪的心理阻碍降低,客观上也促进了犯罪的内在驱动力。
帮会文化的义气将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过分强化,致使其具有鲜明的“我们的意识”,对群体有强烈的归属感。而组织成员的“我们的意识”是导致团伙之间发生冲突或者使伤害发生的重要原因。[22](P260)
2.强制犯罪的外部压力
在群体情境中,人们更容易抛弃自身的价值观,顺从群体行为,这被称为去个体化。去个体化的人更不自控、不自律,对情景的反应性也更为强烈。[23](P217~221)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将帮会文化变得直观、可视,通常为组织命名、发配统一制服、命组织成员在身体同一个地方进行纹身等。这些行为都会使得组织成员更加注重自己在集体中的身份,忽略自己的价值观,从而产生去个体化并服从组织的决定实施犯罪行为。
在帮会文化的控制下,组织成员还需要保持自己的行为与其他成员相同来完成自我认同。当组织成员与组织行为不一致时会出现焦虑、无助等情绪,当他们重新加入组织的活动中这样的情绪就会立即消失。[24]所以在组织进行犯罪行为的时候,成员将受到无形的力量迫使其参与其中。反之,如果有组织成员不参与组织的活动,其他成员也会通过舆论等内部机制对其进行惩罚,迫使其加入。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几乎都有“帮规”(明文的规定或者是众所周知的潜规则)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这些强有力的硬性规定也是组织成员遵守组织决定而进行犯罪的保障。
3.引发犯罪习得的感染力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并不是天生就有犯罪的欲望、懂得犯罪方法的,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犯罪。对犯罪行为的学习受到亲密程度、认可程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21](P198)帮会文化决定了组织成员将习得犯罪。
首先,通过对他人的模仿来习得犯罪。在有组织犯罪集团中,作为凝聚力核心的组织的领导者,同时也是组织的精神领袖。这决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成员中的认可度很高并且是模仿的对象,这就造成其犯罪动机和犯罪方法容易被成员学习。同时,成员之间通常以兄弟相称,日常活动都在一起进行,相互的亲密度较高,当其中有些成员进行犯罪时,其他与之较为亲密的成员也容易习得犯罪。
其次,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观察,并且总结其中的奖惩机制而学习犯罪。当其观察到身边的人通过犯罪得到他人的尊重以及巨大的物质利益时,则会对犯罪行为做出正面评价。相反,成员在组织内部观察到有人拒绝犯罪而被称为“懦弱”、“无能”,甚至因此受到处罚时,则会对拒绝犯罪的情况做出负面评价。在这样不断的强化下,当成员认为犯罪的正面效益大于犯罪成本,就容易进行犯罪。
再次,通过直接体验犯罪来强化犯罪动机、熟悉犯罪方法。犯罪本身通常都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的,加上因为犯罪得到的组织内地位的提升等隐性利益使得犯罪将会被视为一项高回报的行为,这使得未被追究的组织成员都会加强犯罪的动机。另外,在其进行重复犯罪的同时,对犯罪的方法越来越熟悉。
总之,帮会文化不仅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密切相关,而且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化犯罪学主张将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放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考量,从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两个方向共同作用才能起到良好的预防、控制犯罪的效果。现在正是我国社会从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放的年代,主流文化受到各种亚文化的冲击。社会中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一度在舆论中占据不小的分量,帮会文化更是在游民阶层中有着较高的地位。这些亚文化的挑战也正是主流文化在矛盾中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教育机构以及其他传播主流文化的平台,应该注重自身进步,而不是单纯地反对、甚至扼杀亚文化。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帮会文化具有复杂的结构和内容,并非只有价值层面与黑社会(性质)犯罪有关。其他层面,诸如符号、行为规范等,都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相当的联系。本文为了更深入细致地进行探讨,仅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价值层面作为切入点。
②《论语·里仁》。
③《史记·游侠列传》。
④《六庵全集》,第30页。
⑤数据来源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2009—2011年审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1] Jeff Ferrell .Cultural Criminology [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9,25:395-418.
[2] 麦克·马奎尔,等.牛津犯罪学指南[M].刘仁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
[3] 李锡海.文化与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4] 泰勒.原始文化[M].蔡江浓,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5] Leslie A. White .The Concept of Culture[J].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61:227-251.
[6] 冉家胤.西方文化概念面面观[J].国外社会科学,1995,(2):64-69.
[7]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新编(第二版)[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8] 秦宝琦.江湖三百年——从帮会到黑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9]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0] 郭莹.帮会意识初论[J].社会学研究,1993,(2):70-76.
[11] 刘平.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J].清史研究,2002,(1):71-78.
[12] 朱琳.洪门志[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0.
[13]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4] 刘平.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批判[J].江苏社会科学,2001,(2):138-143.
[15] 秦宝琦.天地会《会簿》中“西鲁故事”新解[J].学术月刊,2007,(7):142-147.
[16] 秦宝琦,孟超.哥老会起源考[J].学术月刊,2000,(4):68-73.
[17] 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第一卷)[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
[18] 谢勇,王燕飞.有组织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19] 王牧,张凌,赵国玲.中国有组织犯罪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
[20] 何秉松.黑社会犯罪的自组织原因论(上)——一种崭新的黑社会犯罪原因理论[J].政法论坛,2002,(4):80-92.
[21] 沃尔德,伯纳德,斯奈普斯.理论犯罪学[M].方鹏,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2] 罗大华,马皑.犯罪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3]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8版)[M].侯玉波,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24] 黄海.“灰色街角社会”的逻辑演绎和路径依赖探析——对湖南长沙某“街角青年群体”的实证考察[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2):5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