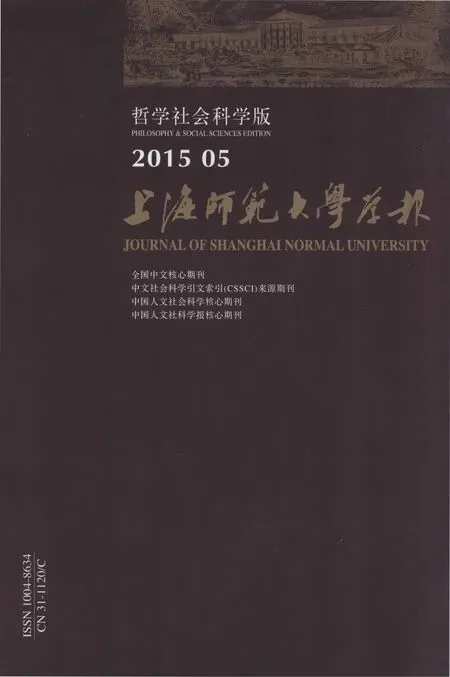艺术的终结或“最后一瞥之恋”
[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
(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卢布尔雅那大学,斯洛文尼亚)
一
从全球来看,今天无论我们生活于何处,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当然,一些特殊的地区除外,比如朝鲜、伊朗的部分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地区。当今的艺术观念主要与这一术语在英语中的含义有关。因此,当下所谓的“艺术”(甚至在哲学领域和欧洲大陆地区),不再是德语中康德主义意义上的“艺术”,也不再是法语语系中的“美术”,①而主要指英美语言中的艺术概念。这一点,不仅在今天所谓的西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同样适用于前苏联国家、第二世界的其他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的主要城市中心。
因此,今天对于“艺术是什么”这一问题,最直接的答案就是:艺术主要指涉英美语言意义上的“艺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这一认识逐渐形成,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传播。当下艺术和文化的商品化,与这种艺术概念的全球传播相伴而生,并成为传播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英语中所谓的“艺术”不仅统摄了在其他文化和语言框架中“艺术”的所指,而且囊括了当今英语中“艺术”的主要所指——视觉艺术。它涵盖了更广泛的艺术作品和创造领域,包括音乐、文学以及其他类似的“艺术”特征。随着1980年代“图像转向”②的盛行,视觉艺术已成为占主导优势地位的艺术形式和文化的核心内容。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现代主义艺术被视为人类创造力的最高表现(如卡尔·马克思所言),并且肩负神圣历史使命(如黑格尔所提倡)。彼得·毕格尔在《先锋派理论》(1974)中对从历史先锋派开始到现代主义艺术无法坚守这一使命进行了批判。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下,艺术不再拥有这样的目的。今天,在艺术和文化之间,不存在像阿多诺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那样将两者严格区分的必要。
当代艺术主要指视觉艺术。因此,从现在开始,我将把视觉艺术看得比文学、音乐或表演艺术等其他艺术形式更为重要。今天,在艺术这样一个管弦乐队中,其他艺术形式扮演着第二琴手的角色。我顺便要指出的是:文化的主要驱动力正从文学转向视觉艺术。这一点在文学占据优势位置的众多欧洲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按照赫尔德的解释,文学与语言和民族文化密切相关。民族原则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将会造成“过度使用文化作为政治替代品”③的负面作用。“这在第三世界和拉美国家同样重要,但在这儿,首先需要建立国家,受新成立国家的自身影响,民族和民族意识接踵而至。”④
目前出现的对于艺术本质的各种疑问,源自概念艺术(此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运用该词)的崛起。概念艺术起源于1913年马塞尔·杜尚的第一部现成品。自此以后,它扭转了正在发展的现代主义艺术方向。恰如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1971年的文章《反先锋》⑤所说,杜尚对“彻底的突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次突变与印象主义不同。因为印象主义虽然反对先前的艺术传统,但却以先前的艺术传统为基础,融合了传统,并没有促进艺术更深远地发展。
杜尚开启了20世纪艺术的新传统。尽管它与现代主义并行不悖,但是随着现代主义的终止和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因为后现代主义同样是非历史的,同样剔除了过剩的含义。
二
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欧洲文化扩张就从未停止过。众所周知,这种扩张伴随着经济和政治扩张而来。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象征主义被移植到这个遥远的大陆。在新生的殖民主义时代来临之前,这个大陆没有任何活动和手工艺品被赋予艺术这一名称。用菲律宾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帕特里克·弗洛雷斯的话说:“艺术领域使用‘艺术’这一术语来指涉物质文化,有意展示超越实用性的能力,并体现一种将自然转化为具有特殊价值和崇高事业的非功利社会价值观。但这一人为创造,本身存在很多问题。‘美学’这个词,实际上将这一问题变得更加让人费解,因为它展现了一种兼具理论与历史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往往将自己对于艺术的定义加以普遍化,认为它适合于所有的时代和人们。”⑥
近代殖民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西方的艺术教育引入殖民地国家。例如,1925年法国远东艺术学校的成立,促进了一些优秀的越南艺术家开始使用法国风格进行绘画。更广泛地讲,同一时期的一些非西方的知识分子吸收了欧洲艺术创作的最新趋势。比如,日本油画家万铁五郎(1918年)和柳濑正梦(1922年)以及巴西作家格拉萨·阿拉尼亚的作品共同见证了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存在和变异。
尽管现代性是未完成的,但在西方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然而在东方、殖民地、前殖民地、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它却遭遇了失败。在那儿,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或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类的概念和关系,通常没有什么意义。假使有,也已经改头换面成了一种全新的东西。
以中国为例,“对中国而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涉及全球化的历史时代或者全球历史哲学意识,而是一种在拥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个体主观性认识。对中国人而言,现代性等同于一种新的民族观,而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替换物。后现代性被认为是比现代性更新的东西,而非对现代性做出的本质性批判或者是与其的决裂。因此,中国的先锋艺术通常具有两副面孔,一面是现代性,一面是后现代性”。⑦
从艺术和艺术家的相关性以及艺术和艺术家的声誉来看,欠发达国家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事件做出较为消极的描述。在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这些不同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出现的原因是相似的。以拉美为例,“因为政治结构有时无法支撑民族认同感,拉美的观众为了发掘有关自身问题的真相,常常将注意力转向文学和视觉艺术。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通过别的途径无法寻找到真相。就这样,作家和艺术家往往被置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这些人被视为民族精英的代表,比那些被选举出来或者世袭的政治领袖享有更多的公信力。欧洲没有一个现代主义艺术家,哪怕是毕加索,可以享有像墨西哥的迭戈·里维拉那样高的声誉”。⑧
像迭戈·里维拉在墨西哥甚至整个拉美享有很高声誉的情况,在许多国家和文化中也存在着。显而易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艺术仍然拥有半个世纪之前现代主义艺术对于欧洲所具有的相关性、重要性和影响。艺术家和作家之所以如此重要和显赫,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拥有道德和诚信,另外还在于他们的艺术作品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菲律宾艺术家爱丽丝·古勒玛宣称:“艺术常常能够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与此同时,可以推动社会历史变化和发展的进程。”⑨毫无疑问,在菲律宾(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和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第一世界),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认为已经过时,不过是工业时代的一个索引而已。就如福柯所说,“在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像水里的鱼一样”。
如今,发展中国家的艺术,不管是视觉艺术、戏剧和其他表演艺术,还是音乐和建筑,依然对社会、政治、甚至国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承载的不是我们在当代发达国家所见到的那种超然的、非政治的、平淡的、甚至被迫的、可疑的政治信息,而是深受社会、政治、甚至民族的影响和介入的信息。在那些最发达的国家里,艺术很少能对政治和国家产生影响,因为供绝大多数人享有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安全体系明显地阻碍了艺术表达的需要。
令人震惊的是,在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欧洲,艺术不再是社会、国家和少数宗教群体表达自我的重要渠道;即便它依然在发挥作用,也是以饶舌、民族音乐、涂鸦、服装或者生活方式等亚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在过去,那些怀有文学艺术抱负、需要传达社会或政治信息的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尼亚、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的现代主义者,可以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以此来寻求主流社会和民族精英知识分子的支持。今天,这种情形刚好相反,少数文化的表达形式不仅被创造出来,而且大多数都停留和局限于他们自己边缘的文化群体之内,其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也仅仅局限于内部。当然,也有跨越民族局限的例外,出现在他们更为商业化的变体或延伸品中。
如果需要为艺术寻求一个当代性、全球化定位,不得不提及美国在当代艺术中扮演的角色。
美国曾经是欧洲文化一种特殊延伸。参观奥克兰加州艺术博物馆的欧洲游客会吃惊地发现,绝大多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展品实际上都是一些德国、意大利、法国画家的作品,因为很明显那时还没有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本土艺术家。这与巴黎作为当时世界文化中心有关。二战之前法国艺术一直居于中心和统治地位,直到二战之后世界艺术之都才由巴黎转向纽约。
众所周知,一直以来人们对学院派的艺术理论褒贬不一。虽然阿瑟·丹托与学院派有关,但他的观点实际上不是学院式而是黑格尔式的。他1984年的文章《艺术的终结》⑩无疑可以说明这一点。正如丹托后来所说,“这篇文章是对艺术世界惨淡状态的回应”。
就学院派的艺术理论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它没有提供对“什么是艺术”这一问题进行描述性回答之外的东西,但它至少揭示了一个事实: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答案。
虽然我做了以上的评价,但我还是要针对“什么样的艺术是艺术,它在哪儿”“在当今,什么样的艺术可以从理论或是哲学层面上被认为是艺术?依据是什么”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做出深入而有影响力的解答。
三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就“什么样的艺术才是艺术”这一问题,出现了一系列尝试性的回答。古典现代主义者的回答是阿多诺式的,在现代主义时代则是海德格尔式的。这两种回答,都将艺术视为通向真理的途径,避免工具理性和存在之失的一种方式。这两种回答都将艺术视为通向真理的优先途径。正如热奈特1997年所说,这两种现代主义观点似乎成为“艺术价值高估的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
正是这种与真理的相关性,构成了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艺术最核心的特征。现代主义抽象艺术致力于对真理的表达。这种表达是不可视的,因为它以非具象的形式出现并且摒弃了外在的物质所指。杰姆逊从哲学层面对现代主义指称关系的断裂做了相关考察,涉及的一方面是能指和所指,另一方面则是利奥塔的崇高观。绝非巧合的是,利奥塔对此观点的进一步深入与美国画家巴尼特·纽曼这位典型的现代主义艺术家相关。
另一种与艺术相关的理论是以认知为基础的。英国艺术史学家诺曼·布列逊在1983年创作的《视觉与艺术:凝视的逻辑》中,试图提出艺术的“唯物主义”读解方法;这与英国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提出的“本质复制”观念相反。恩斯特·贡布里希将“本质复制”看作艺术价值的历史标准。尽管布列逊成功地挑战了恩斯特·贡布里希的规范地位,但没有创造出一种以他所谓的“物质实践的绘画史”为形式存在的西方艺术史。
就传统艺术而言,艺术的经典定义和解释依然有效:我们珍视艺术作品,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认识熟悉事物的乐趣、贡布里希所谓的“认识的乐趣”以及普罗提诺所宣称的“艺术品能够提供喜悦和兴奋”。在许多方面,传统艺术遵循柏拉图最早提出而后被8世纪的大马士革的约翰全面阐发的艺术形象原则:“图像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具有和原型相似的特征,但又有一定的区别。它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和原型完全相似。”因此,一个图像和它的所指之间存在相似性,但通常又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不然的话,就不存在再现的问题:一个被描绘得活生生的人是艺术的原始范本,但他永远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再现,因此,他也不可能是肖像本身。这样一幅肖像(或者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物体的描绘)只能是一种再现、一种可以代表原型的艺术形象。它必须永远存在于一种表现的媒介中,这样既可以将所指和能指区分开来,又能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由大马士革的约翰提出的模式,囊括了整个绘画再现的领域,同时也界定了再现的范围。
然而移居海外的俄国哲学家鲍里斯·格罗伊斯对 “何为艺术”这一问题做出了另外一种回答。格罗伊斯认为,正是文化价值将艺术和非艺术区别开来。艺术作品只是彼此相关,而与外在现实无关。因此,它们构成了一个符号和等值体系;这一体系的内在关系划定了它们各自的位置,而且这种内在关系也会随着所谓的艺术系统的累积性变化而发生变化。在一个动态的艺术系统里,艺术作品行使符号这一功能。正如格罗伊斯所说,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什么是艺术或者什么是真理,而是通过如何认定具有理想地位的文化价值来创造一种艺术或理论作品。
四
如果我们从当代的角度看,上面引用过的热奈特关于海德格尔和阿多诺的“艺术价值高估”的论述,确实符合现代主义的情况。过去伟大的古典艺术十分重视艺术的职能,这一观念被广泛接受。在第一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艺术或至少是当代艺术,不再成为现存情感或者真理的表达方式和工具。艺术不再像20个世纪那样受到重视,甚至连一半的程度都达不到。艺术没有死亡,也没有终结,但是它的历史作用以及重要意义已经一去不返。尽管如此,认为这一说法适用于全球范围则有点言过其实。
在包括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第二世界,后现代主义在不久之前还是探讨艺术的关键术语。在鲍里斯·格罗伊斯看来:“至少从斯大林时代起,官方的苏联文化、苏联艺术以及苏联意识形态开始变得兼收并蓄、引经据典和‘后现代化’了。”路易斯·加姆尼在分析古巴的当代艺术时,也运用了这一术语。他谈道:“西方观察家在看完整个20世纪80代的古巴艺术后,惊讶地发现它并未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反而与资本主义主流艺术产品之间明显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一点被艺术家冠以后现代标签掩盖了。古巴艺术家经常使用的这种标签,似乎方便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它既从外部提供了一种更容易的归类方法,又从内部获得了一种有效的语境感。对于绝大多数处于边缘位置的艺术而言,这种对于艺术作品肤浅的看法似乎确认了这种分类,因为在许多时候,有意识借用艺术观念来解决自身问题的情况确实存在。”
加姆尼同时指出,边缘文化“会产生一种所谓的绝望的折中主义,也就是说,各种因素通过挪用被结合起来。顺从、碎片化模拟异域资源,与对其防御性合成利用和语境重构的情况同时存在。结果就出现了一种虽先于后现代主义但又与其表面上匹配的美学形态”。“就古巴的情况(跟拉美其他地方相似)而言,这种挪用并不像西方那样集中于抽象考察历史主义和历史循环方面的话题,相反,它与试图融合外来影响和现存现实的悠久传统密切相关。”
类似的情况在亚洲、非洲、中欧、东欧国家的众多小国和文化中同样存在,这可以为他们乐于借用后现代主义这一现象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对他们而言,后现代主义不过是一个长期对源于欧洲文化中心的文化和艺术发展以及影响加以挪用的显著例子。数个世纪以来,他们的命运一直如此:要么接受各种各样的艺术影响,并将他们融合进自己已经接受和吸收的语言、艺术和文化传统当中,以此创造出一种本土的形式;要么跟众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迷失”在一种强势文化及其都市文化中。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这种挪用变得合法化,甚至成为理想状态(虽然会有一些来自推广和分配方面的阻碍)。在这些边缘文化中,尽管第一世界文化和观念的影响日益增加,艺术在它们那里发挥的作用似乎正在减弱,但依然保持着先前的相关性。究其原因,这些变化与资本主义的蔓延以及市场意识形态的传播有关,而后者产生了与 “现存的市场意识形态”有关的居伊·德波的 “‘综合’景观”。
五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许多西方人认为,东方应该像20世纪早期的“俄国艺术实验”那样让西方艺术重新焕发出活力。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这种论调有所降温,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前苏联国家的艺术是不是依然跟以前一样重要,是不是依然存在曾经的相关性?它是不是和第一世界的艺术逐渐趋同?与此相关的问题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即使在这些国家,就如同在第二世界,艺术也许拥有比第一世界更重要的地位,但这也不足以宣称这儿的情况和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所有这些例子都可表明,艺术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发挥重要性,即使它依然发挥重要功能,那也在渐渐消退。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整体上(就跟我们说“艺术”是一种整体类型)宣称艺术已死或者艺术已经终结?还是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的情况并非如此?
书包是各位同学学习生活中的必需品,它能帮助大家收纳一些零散的物品,如水杯、钥匙、钱包、课本、铅笔盒等,还能提升大家的学习意识。新学期伊始,许多同学最期待的就是背着一个漂亮的新书包去学校。不过,书包对骨骼的发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各位同学正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所以选书包可不能只选漂亮的。那么,什么样的书包才是理想的书包呢?
另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艺术能否重获曾经的重要性?那种重要性的本质或核心是什么?热奈特针对阿多诺和海德格尔“艺术价值高估”的相关论述,见证了当今艺术不再具有重要作用和崇高价值这样的当代艺术观。结果是,现代主义艺术与当代艺术在社会和理论重要性上相比显得不成比例。
符号的变化使得对于物体和观念符号的消费处于同等位置。这一点已经渗透到第二世界。跟在那些更为发达的国家一样,自它进入第一世界,第一世界的艺术开始经历同样的进化(或退化)。我们不应当感觉惊讶的是,过去20年,从斯德哥尔摩到维也纳和威尼斯,欧洲展览馆中展出的来自俄罗斯、东欧以及中国、巴尔干的首批作品,被认为依然具有重要性,能够发挥艺术和政治的影响。但这一点在第一世界的本土艺术中已不复存在。即便存在,它已不再激进;或者,如果真的激进,那也不会被展出,不再被当作艺术。
今天越来越多元的文化在第一世界涌现,但它们通常是让·鲍德里亚早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的“LLC”,即低等的大众文化:“大家共享的不再是‘文化’: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一种集体的真实存在……而只是一个术语,用来指代一种最低等的常见的物质集合,而这是普通消费者为了在这个消费社会维护公民身份必须拥有的东西。”
要阐明第一世界的现状和人们的感受,我们只需引用阿瑟·丹托在20多年前的文章《艺术的终结》就足够了。他写道:“多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你做什么都无关紧要,这正是多元化的意义所在。当一个方向同另一个方向一样好时,方向概念也就不再适用了。当然,装饰、自我表达、娱乐化正等待着人类的需要。艺术总要发挥一定的功能,如果艺术家对此也满意的话。自由随着它的实现也走向终结。从属的艺术永远与我们同在……已很难预见幸福如何令我们幸福。不过请想一下美食烹调在普通美国人生活中引起的狂热影响。另一方面,它是生活在历史里的巨大特权。”
在最近这些年,艺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了谁而变化?说“艺术重要”意味着什么?无论是从英伽登所指的层面来看,还是从表达层面来看,它意味着艺术具有存在意义上的重要性,可以表达并且唤起人类的情感。它同样也意味着艺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艺术承担着社会和政治的使命,无论它们被称为正义、自由、反对、颠覆、平等、民族还是阶级。它还意味着,艺术是一个“事件”。
从发展中世界的现代主义时代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艺术,但这就像一个并非来自热带的西方游客参观热带一样,不过是享受了短暂的释放。
另一方面,艺术就像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生活一样,“总能找到一种出路”。事实上,艺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是不可预测的,是一种利奥塔式、鲍德里亚式粉碎我们感知和观念的变化的事物。让我们看两个例子:一个是法国艺术学院校长布格罗对于印象主义的评论,另一个是对杜尚的现成品的评论。当初没有人会想到印象主义和现成品艺术可以取得成功,并在艺术风格和地位方面获得高度认可。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资本主义时代,应该补充的是,这个时期的工业生产与艺术创造仍然被严格区分开来。
如今,我们不仅见证了先前现代主义大师们关于艺术的宏大叙述,而且也看到了多元化的小叙述。这是并未生活在历史时代的我们不曾想到的结果,但这也可能促使我们会去谈论一些没有经历过的事件。与此同时,这种由宏大叙述向小叙述的转变,可以解释我们在有关“艺术”的问题上感觉到的空白:我们面对的不是之前以艺术之名而存在的宏大叙述,而是今天都以特定方式宣称艺术的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
第三世界和非西方国家因为境遇有所不同,艺术仍然扮演着大多数西方世界的艺术无可比拟的角色,尽管它也没有被大众传媒所展现和扩散。如果说在过去,如同帕特里克·佛劳尔斯所说,在殖民地国家,艺术这个术语是“值得怀疑的诡计”。那么,在当前全球化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艺术不仅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通常发挥着批评和解放的功能。然而,在缺乏全球媒体关注的情况下,与那些存在于受奇观社会束缚并加以推广的艺术相比,这样的艺术有可能更加切实地履行艺术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并不存在阿多诺、海德格尔以及热奈特所说的“价值高估”现象。
进一步讲,尽管艺术是一种大众甚至是媒体事件,我们也不应忘记它作为公共、私人和主观事件的重要身份,这一点不管在第三世界、第二世界还是第一世界都应如此。因此,你可能要讲艺术的终结,但是这样的论述就全球范围而言有点夸大其词。确实,艺术的历史职责自从现代主义以来逐渐减弱、消逝,这种消失并不是人为臆造的。然而,与艺术相关的另一个事实则是当我们需要艺术或者类似事物出现时,它总会重复出现。正如帕特里克·佛劳尔斯在论及亚洲艺术时所说,艺术是殖民时代的发明。但他同时也提到,在同时期或之前“一些东南亚的宫廷文化已经吸收了‘艺术’的观念,并且将之伪装成自己的传统中固有的东西”。正是在这更宽泛或者“他者化”的、不被人注意甚至是遗忘的艺术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偶然艺术作品的其他侧面、功能和重要性超越了同时代的第一世界,而且以艺术更为个人化的接受方式取代了大部分媒体产生和呈现。换句话说,艺术不再主要是一种媒体事件或者现象,而是一种与个体、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事物——不管艺术是不是商品,情况都可能如此。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主义艺术似乎就承载着重要的意义。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经写过一首《致过路者》的诗。在诗中,他写道,自己坐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看到一位女士经过,就在她要从街角消失以前,他俩中的一人转过身来,两人眼神交汇在一起。那一刻,诗人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她。瓦尔特·本雅明在评论这首诗时,称之为“最后一瞥之恋”。也许今天,在现代主义走向衰落时,我们才逐渐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一件事情一旦成为过去,我们就会留恋这场缺憾,就如同波德莱尔和他的过路者一样。
(贾永平译)
注释:
①For a 20th century French notion of the arts, see Etienne Souriau, La correspondence des arts. Éléments d’esthétique comparée (Paris: Flammarion 1969), esp. pp. 126-27.
②See W. J. T. Mitchell, The Pictorial Tur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see also Aleš Erjavec, Das fällt ins Auge ... , in Gianni Vattimo & Wolfgang Welsch (eds.), Medien-Welten Wirklichkeiten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8), pp. 39-57.
③Tamás Hofer, Construction of the ‘Folk Cultural Heritage in Hungary’ and Rival Ver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más Hofer(ed.), Hungaria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ree Essays on National Myths and Symbols (Budapest: Museum of Ethnography 1994), p. 48. The passages quoted by Hofer are by Georg L. Mosse.
④Luis Camnitzer, New Art of Cub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p. xxii.
⑤Clement Greenberg, Counter-Avant-Garde, Art International, vol. XV, no. 5 (May 20, 1971), pp. 16-19.
⑥Patrick D. Flores, Razstavitev Evrope v jugovzhodni Aziji: konteksti nove sodobnosti (Undoing Europe in Southeast Asia: Contexts of a New Contemporary), Filozofski vestnik, vol. XXIV, no. 3 (Ljubljana 2003), p. 95. The quotation at the end of the passage is from Nicholas Dirks, Introduction: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 3.
⑦Gao Minglu, Post-Utopian Avant-Garde Art in China, in Aleš Erjavec (ed.),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Politicized Art under Late Socialism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249-50.
⑧Edward Lucie-Smith, Latin American Art of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3), p. 8.
⑨Alice G. Guillermo, Protest / Revolutionary Art in the Philippines 1970-1990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2001), p. 3.
⑩See Arthur C. Danto, The End of Art, in Berel Lang (ed.), The Death of Art (New York: Haven Publications 1984), pp. 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