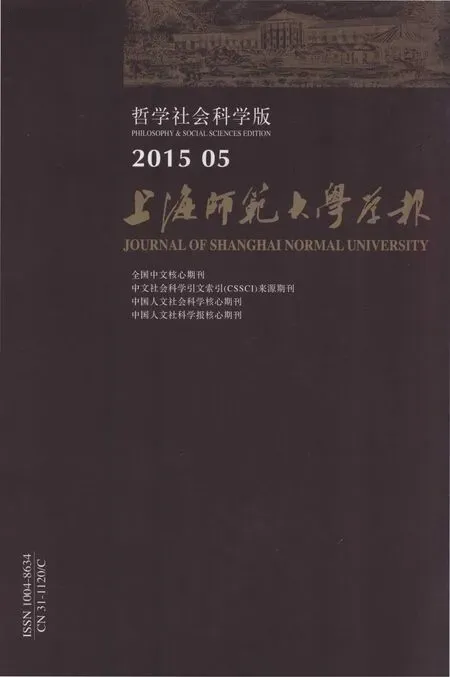“意象”与“比兴”碰撞融合的意义
——以《文心雕龙》为例
曹 旭,文志华
(1.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2.广西教育学院 中文系,广西 南宁,530023)
“比兴”和“意象”都是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术语。从发生学来看,“比兴”是源于古人对事物的意义进行的一种抽象解释,赵沛霖认为“兴”是“原始兴象”的规范化产物,而“原始兴象”“是观念内容与物象之间的一种联想”。①究其起源,一般认为“比兴”可以追溯到《周礼·春官》的“六诗”说,而“比兴”作为一个明确的文学概念则是以汉人的注疏为滥觞。
“意象”最早则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出现的,源出《周易·系辞上传》:“圣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其中的“象”只是为了“尽意”而设的一种符号、卦象,等到曹魏时,王弼进一步阐明“意”“象”“言”三者的关系,认为“存象忘意”、“忘象以求其意”,更明确地表达了意象之前的关系:以“意”为统帅,“象”只是一个显现“意”的媒价,并不一定需要指向具体的物象。②
那么,“意象”是怎样从一个哲学概念过渡到文学概念呢?
其实以古人的大文学的观念看来,哲学与文学是不分的。并且《易》象与文学还有着天然的联系。刘勰对于《易》象与文学的关系,就有过明确的论述: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文心雕龙·明道》)
亦即是说,《易》象与人文本来就是一回事。清初学者王夫之更是直接指出:“象者文也。”③他们所说的“文”比我们狭义的文学的含义自然要宽泛得多,他们所说的“象”当然也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概念。但是毕竟“象”与“文”便自始至终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所以当文学的概念开始形式后,“意”“象”这些概念也很自然地运用于古代文论当中,如范晔所倡文章“以意为主”,④挚虞的“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⑤这可以看作是“意象”成为文学话语的滥觞。但“意象”合用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则始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的“窥意象以运斤”。⑥
然而也是自刘勰起,“意象”便与另一个文学概念“比兴”纠结在一起(详见后文),自此古人多将“比兴”和“意象”笼统地看成一回事。唐代皎然《诗式》中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睢》即其义也。”⑦明显将“比兴”与“意象”互训。其后有宋代陈骙《文则》卷上言:“《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⑧明代张蔚然《西园诗尘》:“《易》象幽微,法邻比兴。”清代宋大樽《茗香诗论》:“(《易》)取象如诗之有比。”都是把意象和比兴联系在一起。一直到清代戴震更是明确地从理论上将“意象”和“比兴”等同起来,他说:“《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⑨
一、“比兴”和“意象”之关系
现代学者中较早论及“比兴”与“意象”关系的是闻一多,他在《说鱼》(1945)中提到:“‘象’与‘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亦兼《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⑩并总结说,“《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闻一多比起戴震更有所发挥,他从“兴象”这个词语中敏锐地觉察到了“比兴”和“意象”两个概念的融合。
钱钟书则对戴震的《诗》“比兴”即《易》“取象”的说法给予辩驳。他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乾》(1979)中指出两者实际上是“貌同而心异”,“《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故“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而“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
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
钱钟书说《易》象“不即”,即不执着于象,“忘象”的意思。他认为《诗》“比兴”不离于象,“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同时又指出“比兴”不可视同“意象”:
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等不离者于不即,于是持“诗无达诂”之论,作“求女思贤”之笺;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丧所怀来,而亦无所得返。
其实钱钟书并没有否定“比兴”与“意象”之间的联系,“舍象忘言,是无诗矣”一句已可见其用心。钱氏只是强调了《易》与《诗》的区别:《易》象是为了“存意忘象”,《诗》之“比兴”则是必需依托于具体物象。如果说闻一多的观点与戴震相近,那么,钱钟书的观点倒是与清代学者王夫之的观点相似。王夫之一直主张诗歌“以意为主”,但同时又指出:“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如以意,则直须赞《易》陈《书》,无待诗也。”从这些看似矛盾的陈述中,其实是在阐述一个道理,即强调诗歌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其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意象与诗歌的关系。
此后,对于“意象”和“比兴”是否存在关系,还引起过一场争论。胡雪冈《试论“意象”》(1982)中说:“章学诚明确地把《周易》中的象与诗之比兴联系起来考察,指明了‘意象’是心意在物象上通过比喻、象征、寄托而获得的一种具象表现。”而郭外岑提出相反的意见,他在《意象本质上不是比喻、象征、寄托》(1986)中指出:“意象的质的规定性,就审美心理的角度说,它是心和物的同一;就艺术认识论的角度说,它是意和象的契合;就作品表现的审美特征说,则是情和景的交融。所以在本质上,它不是比喻、象征或寄托,它和喻象文学是无缘的,它们各自属于两种绝然不同的审美范畴。”胡雪冈的说法其实并无不可,“意象”从表现方法上看,的确是通过比喻、象征、寄托的手段来达到的。而郭外岑说到“意象”质的规定性上也是比较中肯的,“意象”远比象征具有流动性,而不仅仅是一个静止的象征符号。但是,他由此断定意象在本质上与喻象文学无缘却是有失偏颇了。胡雪冈此后又撰写了《“意象”与“比兴”的关系及其多义性》(1989)一文,论“意象”的概念是宽泛和多义的,并重申在文学当中存在着“意象”与“比兴”的相互融合的现象。
总而言之,虽然还存在着争议,但多数学者还是赞成“比兴”和“意象”是两个关系密切的文学概念。而另一个方面,关于“比兴”和“意象”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成为另一个研究的热点,问题集中在这样一个话题:“比兴”和“意象”是文学本体论还是方法论?王元化(1978)把“比兴”看成是近于“艺术形象”的概念,他认为:“‘比兴’一词可以解释作一种艺术性的特征,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形象’一语。”“《神思篇》:‘刻镂声律,萌芽比兴’,就是认为‘比兴’里面开始萌生了刻镂声律、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法。”对此,张敏强(1991)补充说:“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比兴’概念已从文学方法论范畴上升到文学本体论,而具有了艺术形象的某种属性。当然刘勰到底没有将‘比兴’当作形象的代名词来使用,而是别创了较接近形象概念的新词。……刘勰却将意与象并列起来,铸成‘意象’新词。《神思篇》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这里的‘意象’显然指尚未形诸作品的作者头脑中的形象,与通常所说的艺术形象尚有一定距离。”“‘意象’即不能完全等同于艺术形象,但在本质上已与形象相通,可以说已具有艺术形式的属性了。”两人都敏锐地看到了“意象”和“比兴”两个概念的碰撞始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只是论述的侧重点不同,王元化是将“比兴”直接上升到文学本体的高度,将其看成是近于“艺术形象”,而张敏强则认为“比兴”在从文学方法论上升到文学本体论的时候,改用了“意象”这个词。
二、《文心雕龙》之“意象”与“比兴”
关于“意象”和“比兴”的关系,前人所论,不可谓不完备,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将其回溯到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一个具体的历史对象中来进行研究和讨论。在历代的文献中,对此论述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文心雕龙》,因此,我们将以《文心雕龙》为例讨论“意象”和“比兴”这一对概念的关系。我们认为在《文心雕龙》中已经体现出“意象”和“比兴”这一对概念从碰撞到融合的一种趁势,试述如下:
1.从艺术构思环节看“意象”和“比兴”的碰撞
前文已论及《文心雕龙》中《易》“象”与“文”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而“意象”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的介入,毫无疑问地是首先发生在艺术构思这个环节。这是因为“象”与艺术想像有关,“象”原本是一个动物名词,指的就是大象,《说文解字》释“象”:“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凡象之属皆从象。”因为气候的原因,北方的象灭绝了,象只能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点追想,于是后来象便引申为想象的意思,《韩非子·解老》对此有这样记载:“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以此而论,“意象”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创作的过程、想象的过程,而不仅是对一个静止的意义符号的运用。因此,从发生学来看,意象是诗歌艺术构思中的最为生动的艺术形成的过程。
《文心雕龙·神思》篇是说文学艺术的构思,《神思》篇与“意象”有关的描述有以下几处:“窥意象而运斤”、“意授于思,言授于意”、“神用象通”等,从刘勰的论述中可以得出,诗歌艺术的构思离不开“意象”,其对艺术创作的流程可描述为:“思”—“意”—“言”。“意象”是艺术构思的结果,是艺术创作的前提。唐代王昌龄提到诗歌的艺术构思时,也说道“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可见,“意象”的构建在诗歌创作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于具体的作品而言,“意象”具有先在的意义。
刘勰在具体谈到“意象”这个概念的时候也是与“比兴”的概念联系起来的。在其理论性的描述中,“意象”进入艺术构思后,就是与传统的文学话语“比兴”理论相联系着了。对此,仔细地分析一下《文心雕龙·神思》的“赞曰”部分,便一目了然了: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心貌求,心以理应。
所谓的“神用象通”即“神思”—“意象”的过程,“象通”亦即“窥意象”的意思。而“情变所孕”是指什么呢?《文心雕龙·比兴》:“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故“情变”云云,实为“兴”起的过程,诗兴在其中萌发了。当然这并不表明“兴”与“意象”在产生时间、或者产生的逻辑上存在先后关系。《文心雕龙·神思》篇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到底是“情”先动,还是“意”先动呢?我们认为这既是一个“感兴”的过程,也是一个“意象”产生的过程。因此,“兴”和“意象”的产生并没有时间上或逻辑上的先后。但由此产生另一个问题,“兴”不是可以表达这种“感兴”的过程了吗?又何必插入“意象”这个概念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兴”比较注重感兴动情这种方式,而不是注重去形成一种概念或意义,这就使得“意象”理论有了发挥的空间,所以才有“窥意象而运斤”,而不是窥“兴”,“兴”不可见,必须“发注而后见也”(《文心雕龙·比兴》),即,“兴”只是一种感兴的方式,只有通过注释,才可以把“兴义”昭示出来,“兴”天然地需要一种活泼的、生动的东西去替代它,那就是“意象”。
最后两句“物心貌求,心以理应”,对照“附理故比例以生”(《文心雕龙·比兴》)的描述来看,则是指的“比”了。那么整句话连起来看,形成这样一个艺术构思的序列:“神思”—“意象(兴)”—“比”,在“比兴”中间生生地插入了一个“意象”的概念。
2.从诗歌组织因素看“意象”和“比兴”的替换
陈植锷指出:“在一首诗歌中起组织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声律和意象。”其依据便来自刘勰的“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以运斤”。我们假定陈植锷的说法成立,那么刘勰还说过“刻镂声律,萌芽比兴”,试看《文心雕龙·神思》“赞曰”部分的最后四句:
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
在“声律”这个要素没变的情况下,刘勰将“意象”替换成了“比兴”,为了说明这种替换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在长期的文论话语中,因两者之间的联系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联想行为,我们考察了历代的文献,发现“声律”与“意象”或“声律”与“比兴”这两种并列形态都多次出现。
首先,看“声律”与“意象”并称的例子:
游默斋序张晋彦诗云:“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议论太多,失古诗吟咏情性之本意。”切中时人之病。(南宋 刘克庄《后村诗话》引游九言序)
诗有音节,抑扬开阖,文质浅深,可谓无法乎?意象风神,立于言前,而浮于言外,是宁尽法乎?(明 李维桢《来使君序》)
予谓学于鳞不如学老杜,学老杜尚不如学盛唐。何者?老杜结构自为一家言,盛唐散漫无宗,人各自以意象、声响得之。(明 王世懋《艺圃撷余》)
其次,再看“声律”与“比兴”并称的例子:
盖存於遗札者,凡三百有五十篇。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宪章、颜谢。(唐 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
且君富于文谊,恬于利欲,比兴、声律,播于士林。(唐 权德舆《送司门殷员外出守均州序均运亨通》)
从这些例子中可见,“意象”和“比兴”都是诗歌的重要表现方式,是诗歌组织中的重要因素,两者的功能大同小异。但我们并不是要因此证明两者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在刘勰那里,“意象”概念介入文学构思这个环节,与“比兴”碰撞并且可能开始出现融合趋势了。
3.从“比兴”的定义看其“意象化”的描述
从《文心雕龙·比兴》的相关论述中,我们认为刘勰是有重振“比兴”的愿望的,但是除了感叹“兴义销亡”之外,他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任何道路。尽管如此,从刘勰对“比兴”,特别是其中的“兴”的定义中还是发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比兴”与“意象”的概念发生融合的现象,我们暂时将之称为“意象化”,试看刘勰的论述:
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 《文心雕龙·比兴》
首先来看“比”。“比”是“附理”,“写物以附意”。“比”多用于赋颂,所谓“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文心雕龙·比兴》)。刘勰对赋的描述亦与“比体”相吻合,“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文心雕龙·诠赋》)我们这里注意到该篇中比《文心雕龙·比兴》中多出来的两句“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源出《周易·系辞上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可见,当象作为物象来解时,“比”就是一种写物、拟象的重要创作方法。因此,“比”的概念是与“意象”有内在的一致性的。
其次,看刘勰对“兴”的描述。在对“兴”的描述上,刘勰是将其“意象”化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一语原是《易传》用来描述“意象”的,出自《周易·系辞下传》:“易者,象也。”“夫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又东汉王充《论衡·乱龙篇》:“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正是因为“意象”和“兴”都有托物示义的意思,成为两者产生融合的基础。
总而言之,从刘勰对“比兴”与“意象”关系的论述中,的确体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刘勰本人也未曾预料到的,或许刘勰对此并不在意,也或者这根本不是其本意。但是两者后来毕竟是融合了,还在唐代形成了“兴象”的概念。只是在刘勰这里,这种融合还只是一个开始,显得有些生硬,正如张敏强所说“这里的‘意象’显然指尚未形诸作品的作者头脑中的形象,与通常所说的艺术形象尚有一定距离。”这种看法与德国学者W·伊泽尔所做的一个著名的论断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意象揭示了某种东西,我们既不能把这种东西和一个给定的经验客体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它和一个被表现客体的意义等同起来,因为它超越了知觉,却还没有完全形成概念”。但是,“意象”和“比兴”的融合毕竟为后来殷璠提出“兴象”说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最辉煌的唐诗也才有了与之相称的“兴象玲珑”的评价。
三、论“比兴”与“意象”融合的必然性
前面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比兴”和“意象”之间存在融合的趋势,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取消“比兴”或“意象”文学概念的独立性,而只是要说明两个概念的交叉和互动。另外,我们也暗示了“兴象”这个概念或许是这两者互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我们要论述的重点。我们只是在描述“比兴”与“意象”从碰撞到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确发生了,并且这个过程的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是我们这篇论文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1.“比兴”理论的困境——“兴义”的缺义
“比兴”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从“比兴”较早的定义来看,郑玄《周礼注疏》:“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并引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郑玄和郑众的定义便可以看作是两种不同角度的有代表性的定义,郑玄是从“比兴”注释学角度定义的,郑众则是从创作方法角度定义的。
我们认为较早的时候,“比兴”更多是作为一种注释的方法的。“比兴”原本就是汉人注释《诗经》的一门学问。作为注释之学的“比兴”,其中“兴”是解释诗的重心所在,所以刘勰认为“毛公述《传》,独标兴体”。盖“比显而兴隐”,兴是“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文心雕龙·比兴》)这些都体现了“比兴”作为注释之学的特征。证之以诗歌,例如《诗经》“比兴”所取的事物,先民便多将之与伦理观念相比附,时过境迁,的确是要“发注而后见”,这正是“比兴”作为注释理论的合理性。到了屈原时代,《离骚》中增加了许多个人创作、个人情感和想象的成份,其取象非常广泛,跟《诗经》相比,“屈原则把摄取比兴物象的范围从自然界扩大到社会生活,从现实扩大到历史,从人间扩大到神界”。但王逸《离骚序》依然是用“比兴”去诠释:“《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侫;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貌似亦无不妥,但是很明显,“比兴”理论已经开始僵化了,它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就成为了“美刺说”的图释。许多个性化的、活泼泼的想象和情感,便在“美刺说”伦理教化的大旗下被抹杀了。换而言之,“比兴”作为一种人们对《诗经》时代艺术形式的总结,过于依赖其历史的背景了,随着各种时代因素的改变,它的创作生命不免遭到一些破坏,从而变成了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只能供陈列和膜拜艺术的或者说美的标本。屈原而后,创作不免有一些新的特点,这是无法用过去的“比兴”理论去完全囊括的,那将是一个个人创作和想象的时代,表现丰富的想象和情感成为主流。这种理论与创作之间的悖逆,是“比兴”理论衰落的主要原因。
我们来看刘勰对此的论述,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描述了所谓的“兴义销亡”的现象,并总结其原因是两汉时“诗刺道丧”,“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其结果是,诗人们“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文心雕龙·比兴》)
“兴义销亡”其实是一种意义的丧失,是一种旧的艺术生命的结束,按刘勰说是“诗刺道丧”的结果。而“比体云构”的现象,我们认为这是“比兴”从艺术生命的终结并转化为艺术标本、成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所必然造成的结果。再看郑众的定义:“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如果不从诠释学的角度考虑,“兴”和“比”在创作方法上其实是很难分辨的。因此,在创作实践中, “兴”基本上不存在可操作性,“比兴”重心便向“比”转移了。我们来看刘勰对“比”的描述便可明了:
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文心雕龙·比兴》)
刘勰将“比”分成了“比义”和“比类”,需要指出的是,现在通常认为属于“兴喻”的,在古人看来其实都是“比”的内容。因此,以具体的创作方法论,“比兴”几乎就等于“比”了,“兴”基本上不属于这一范畴。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即,“兴”只是感兴,有感即谓之“兴”,并没有或者说并不需要实际的内容,这与郑玄“取善事以喻劝之”的“兴”判若二物了。故后人总结为兴不在义。兴不在义,自然“兴义销亡”了。因此,文学需要新的想象,而“兴”留下的“义”的空白正好成为“意象”理论生长的空间。
2.“意象”重新衔接对意义的指向
“比兴”作为一种历史的、观念的产物,离开它所产生的时代,“岁月飘忽,性灵不居”(《文心雕龙·总序》),渐渐地“兴义销亡”了(《文心雕龙·比兴》)。文学需要重构它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但却沦为制作,并为扬雄悔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汉赋没有能将它完成;而以“有韵”“无韵”为依据的文笔之分,也未能揭橥文学的意义,文学的毛病依然是“腾声飞实,制作而已”。(《文心雕龙·总序》)重振“比兴”已经成为当时文人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个时候,意象的撞入,便成为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我们看到刘勰对“兴”的定义中充满了意象化的描述,其实不止是刘勰,同时代的钟嵘也这样对兴的定义进行意象化的改造:“言有尽而意有余,兴也。”显然,“比兴”含义向意象化的过渡有着其历史的必然的一面。
我们认为,“意象”理论向文论的介入,正好填补了“兴义销亡”留下的空白,所谓的“窥意象而运斤”,体现了诗人个性化的想象,“意象”正是在个人想象的可解与不可解之间,重新衔接了“比兴”对意义的指向。
首先,“意象”是通过与“比兴”的互动融合来实现对“兴义”的补充。
前文用“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说明了“意象”和“兴”同时产生,然后又指出“意象”和“兴”都是有托物示义的意思,并且两者作为诗歌的组织因素,也发挥近似的功能。如果不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差异,我们几乎就要把它们当成一回事了。正是两者之间细微的差异,使得两者在融合之后,在对诗歌意义的诠释上达到一种互补的效果,清代朱鹤龄对此有精彩论述:“且子亦知诗有可解,有不可解乎?指事陈情,意含讽喻,此可解者也;托物假象,兴会适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强解之,日星动成比拟,草木亦涉瑕疵,譬之图罔象而刻空虚也。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后贸时,浅深乖分,欢忭之语,反作诽讥;忠剀之词,几邻怼怨;譬诸玉题珉而乌转舄也。”“指事陈情,意含讽喻,此可解者也”是指的“兴”,“兴义”可以“发注而后见”;“托物假象,兴会适然,此不可解者也”则指的是“意象”,这就为诗歌的意义开生面了,使诗歌在可解和不可解之间获得最大的自由和发挥想象的空间。
其次,我们并不否定伊泽尔关于“意象”的论断的合理性,但是我们的前提是诗歌有可解与不可解,因此,意象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替代意义,而且有时比“意义说”更符合诗歌本体特征:
我们认为:中国的传统诗学是意象的,“意象”作为文学表现对象,其本身就有审美的意义。因为诗歌并不一定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意义,这时,“意象”就代替了意义。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这样的呼声和论调基本构成了中国古代诗学的主流,不能一概将之否定,而是要考究其历史成因,挖掘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要像王夫之和钱钟书那样,既要肯定意义,又不至让意义成为枷锁,从而桎梏了活泼泼的艺术生命。抛开意义不论,有时候那种诗歌的迷茫和不可解反而才是最接近文学本质的。这正是“意象”理论真正的价值所在,正是“意象”理论这种灵光乍现、不求甚解的特点为后世的诗歌理论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注释:
①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页。
②王弼:《周易注·周易通例》“明象”条。“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用来说明一个道理(意)的象是不一定的。
③王夫之:《尚书引义·毕命》卷六。
④范晔:《狱中与诸甥姪书目自序》。见《宋书·范晔传》,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
⑤挚虞:《文章流别论》,引自《艺文类聚》卷五十六。
⑥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⑦皎然:《诗式》,《全唐五代诗格汇考》。
⑧陈骙:《文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
⑩闻一多:《说鱼》,《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