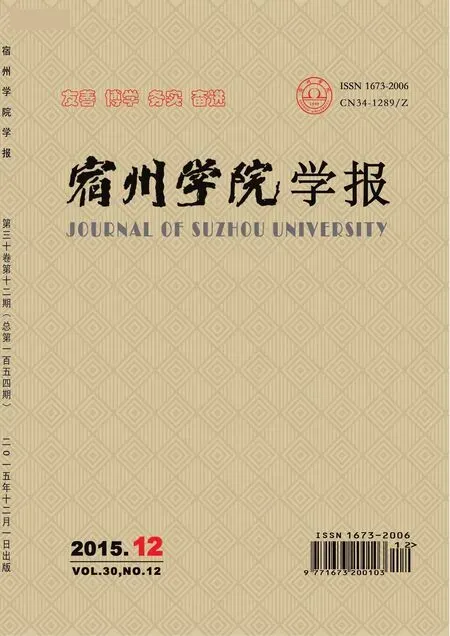社会转型视域下20世纪90年代安徽乡土小说叙事立场的转型
金大伟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宣传部,安徽合肥,230022
社会转型视域下20世纪90年代安徽乡土小说叙事立场的转型
金大伟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宣传部,安徽合肥,230022
从时代背景、叙事实践和叙事向度三个层面,对社会转型视域下20世纪90年代安徽乡土叙事立场转型进行研究,揭示了安徽乡土叙事立场转型的缘由、特点和历史贡献。转型既是外部因素刺激与促动的结果,更是安徽乡土叙事的自觉实践。在叙事实践方面,安徽乡土叙事通过反思确定转型立场,在边缘处彰显地域特色,于无名中坚守自我。在叙事向度层面,安徽乡土叙事立场的转型表现为四种向度,即体现为对乡土现实的理性关怀,对待两种文明的辩证态度,乡土人格的“去英雄化”,以及对生存家园的诗性回归与终极思索等。
社会转型;叙事立场;叙事实践;叙事向度;地域经验
作为地域文化、生存景观、精神价值表达载体之一的安徽,乡土小说是安徽文学的重要实验场和表现域。新时期以来,安徽乡土小说创作既与全国范围内的乡土小说创作保持了一致性,同时又彰显了安徽的地域特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下简称90年代),面对经济机制、政治环境、文化气候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安徽乡土小说一方面立足地域文化,继续抒写特定地域的经验,另一方面紧跟时代变革,努力进行叙事转型。在转换传统乡土小说二元对立叙事立场的基础上,安徽乡土小说逐步构建起多元化的叙事框架,呈现出一元与多元、共名与无名交错互生的特点。90年代安徽乡土小说的叙事立场一直延续至新世纪,为新世纪安徽乡土小说构建较为稳定的叙事模态奠定了基础,为此,探究90年代安徽乡土小说叙事的立场转型,梳理转型期叙事立场的表现向度便显得尤为必要。
1 叙事立场转型的时代背景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变可知,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遇到时代变革、社会转型时,都会发生量变或质变,或消沉湮没,或暗流涌动,或破茧新生。90年代的安徽乡土小说也不例外,其叙事立场的转型与时代背景的三个方面密切相关。
一是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乡土世界的浸染与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意识交织,工业文明迅速逼近农业文明,正如丁帆所说,“庞大的城市文明快速无声地向农耕文明下的田园牧歌乡村进逼:城市的价值观念侵蚀着乡村的价值体系,城市人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改变乡村人的生活,现代商品生产与机械理性改变传统小农生产及具有自由感性特征的农耕理性”[1]。这是当时社会转型的重要特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冲击并改变着乡土叙事的视域、观念与立场,如鲁彦周、许春樵等乡土叙事者在90年代初已察觉到上述变化,并在乡土叙事中传达了这种变化:“荷子走在四月稠密的阳光里,南方的风景在她宁静的视线里嗤嗤地生长。”[2]
二是转型期对“人文精神”等文艺理论的反思与探索。这是90年代安徽乡土叙事面对的文化与理论背景,它们直接介入叙事实践,影响乃至改变叙事立场。90年代以来,唯市场论、文学商品化、边缘化等现象频繁出现,社会心理、文学创作心理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文学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等问题日渐凸显。于是,安徽乡土小说的创作、理论和批评等层面便同时开始自觉地反思,出现了诸如信仰危机、价值扭曲和道德滑坡等类似“人文精神”大讨论性质的文艺理论探讨。在转型期文学理应坚持什么、高扬什么,叙事主体需拒斥什么、反对什么,乡土叙事应秉持何种叙事理念等,这些已成为安徽乡土叙事亟需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三是多元化思潮与理论推进乡土叙事观念与技法的新变。9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与理论同时出现,文学创作呈现多元化、碎片化、无名化等特质。就安徽乡土小说而言,乡土叙事整体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继续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相关叙事理念和创作技法,乡土叙事实践呈现一元与多元并存的局面。正如有论者总结,面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潮流,“安徽作家群体以一种清醒而热情的心态,广泛地接触各种流派、风格的作品,在保持自己艺术个性的基础上,借鉴、汲取新的艺术表现方式、手法,不断尝试、追求”[3]。鲁彦周、季宇、熊尚志、郭本龙等一批乡土作家在叙事中都进行了尝试与创新,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2 叙事立场转型的自觉实践
经济机制、政治环境、文化气候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必然影响文学创作的转型。受90年代诸多因素的影响,安徽乡土小说的叙事立场发生了相应的转型,这种转型既是外部因素刺激与促动的结果,更是安徽乡土叙事者的自觉实践。他们在转型语境的纷扰中,通过反思确定转型立场,在边缘处彰显地域特色,于无名中坚守自我。
2.1 在反思中确定转型立场
90年代的安徽乡土小说,是在反思中逐步确定叙事转型立场的。结合时代背景和地域实际,乡土叙事者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反思传统、反思当下和反思文学三个层面。反思传统,即反思90年代之前,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的安徽乡土小说叙事。80年代安徽乡土小说的叙事是和时代政治等宏大命题和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其中多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追求,鲁彦周、曹玉模、祝兴义等人的小说都以现实主义的姿态关注并忠实、审美地叙述客观现实,并取得了轰动效应。进入90年代,安徽乡土叙事的传统视阈是否应继续坚守,叙事追求是否继续坚持,叙事优势和特点是否适应时代转型的要求,是否会制约乡土叙事的发展等,都成为了乡土叙事反思的内容。反思当下,“当下”不只是时间概念,更多体现为乡土叙事的生存语境。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安徽乡土叙事在90年代的生存语境中应以何种态度与之“相处”,并涉及到反思文学自身。新时期开始,安徽乡土叙事秉承启蒙传统,与政治转折、时代进步密切联系,汲取现代主义精神,开始对人的主体性和文学本体性进行自觉关注。90年代后,在多元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的非意识形态化色彩日渐鲜明”,“文学逐渐丢弃了过去那种教化、指导读者的居高临下的优越地位和主动处境”[4]。文学的启蒙话语权逐渐弱化,但是文学的责任、使命是否需要坚持、应如何发挥,与之相关联的是文学的边缘化问题。社会价值中心的转移,对精神、意义、深度的消解和大众文化的流行,促使文学日益边缘化。此时的安徽乡土小说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是继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庄严性,还是追赶时代、迎合市场,成为乡土叙事者苦苦思考的问题。
2.2 在实践中确立叙事原则
“边缘化的写作,边缘人的写作身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作家以常态去感受体验现实,潜心艺术创作,以便写出独具特色的作品。但边缘化状态又是一个滑移不确定的状态,自觉坚守是一回事,迫于无奈而落坐是另一回事,心态不同,作品迥异。”[5]总体而言,90年代安徽乡土叙事者身处边缘,在多元话语中坚守自我,在边缘地带进行乡土叙事的实践。
一是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并致力于原生态写实。“半个世纪以来,尽管社会、文化的变化剧烈而深刻,但在安徽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一直是作家们主要的追求”,90年代以来的安徽乡土小说创作秉持了这种精神,“他们不约而同地朝向现实主义道路走去,继承和推进了皖军的现实主义传统”[3],将叙事视角对准了乡土世界的“原生态”。绝大多数作家将叙事视角由“俯视”转为“平视”,由全知视角转为限知视角,由主流意识形态视角转化为文化学、民俗学、心理学等视角,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许辉的《夏天的公事》、季宇的《当铺》、郭本龙的《儿本平常》等在这方面都作了成功的探索。
二是坚持高扬主体性而弱化启蒙性。随着个体意识的强化,安徽乡土叙事开始转向关注个体生存空间和主体性,熊尚志的《骚乱》就是其中的代表。与之对应的是,自“五四”开始并在新时期发挥重要政治功能的启蒙精神逐渐弱化,启蒙话语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遭受对抗与质询,但没有在文本中终结。如伍先飞的乡土小说《桃花》,启蒙性的话语在小说结尾处就出现一次。
三是消解宏大叙事但不放弃坚守人文精神。“宏大叙事”、“史诗”和“深度”被消解、削平,已成为共识,安徽的乡土叙事参与了这次叙事实验,坚持高扬主体性而弱化启蒙性。但在消解、削平之后构建什么以及如何构建的问题和风险是不容回避的。“消解了深度的平面化的原生态写作,已成为90年代文学的第一特征。平面化写作既是时尚,又是陷阱。安徽不少青年作家入于此道,取的是平面,忽视的则是深度开掘。没有对现实深度、精神高度的追求,作品只会平庸低走。”[5]欣慰的是,以鲁彦周为代表的老一代安徽作家坚守了人文精神,并发出了时代强音:“对于文学,我是主张现实主义,主张文学的社会性,主张文学负有时代的责任。”[6]以崔莫愁的《走入枫香地》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始终保持着对当下现实的关怀,传达出对历史和时代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文化的坚定信仰,对于坚守人文精神、保持文学独立性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3 在边缘处彰显地域特色
抒写地域经验,彰显文化特色,是特定地域作家的立足点。乡土小说叙事的重要内容和审美特征应标记上地方色彩和地域情调。然而,处在90年代多元与无名的时代,国内许多地域的乡土叙事却忽略了审美特征的表达。而安徽乡土叙事者面对多元和无名时的选择比较谨慎,他们在汲取外来经验的时候,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放大了对地域文化经验和审美特征的抒写,将之作为坚守自我、彰显特征、对抗无名的重要途径。如“在边缘域行走”的许辉,在90年代初就确定了抒写皖北地域文化经验和审美特征的叙事立场。潘军、苏北等皖籍作家也都自觉地将地域文化经验和审美特征作为乡土叙事的重要内容。总体来看,几乎所有的乡土小说中都出现对特定地域景观的描绘,且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等“三画”和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等“四彩”都有所展示。从所占篇幅比例来看,既有简短的地方色彩描绘,也不乏长篇大段的地域情调流露。从内容上看,既有对特定地域历史文化的描述,也有对乡土世界人情风物的追忆。
3 叙事立场转型的四个向度
无论是回到叙事文本还是回到研究文献,不难看出90年代的中国乡土小说打破了传统乡土小说二元对立的叙事格局,构建了多元化叙事格局,叙事立场、叙事视域以及叙事技法均发生了变化,这些已成为学界共识。90年代的安徽乡土小说叙事立场、叙事视域与大背景保持了一致性,同时因地缘、传统、环境等因素的差异性,这种转型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叙事立场的转型在文本中表现为四个向度。
3.1 对乡土现实的理性关怀
90年代的乡土世界在经济转型、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下的文化语境决定了本时期的乡土关怀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比的重要性和紧迫感”[7]。此时的安徽乡土叙事,在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多元化选择时,继续秉持着现实主义精神,致力于乡土世界的理性关怀,对乡土生存现状、社会矛盾作真实描绘,成为叙事立场的最重要向度。
首先,聚焦乡土世界里贫穷、落后、封闭的生存境遇。在90年代的安徽,作为乡土世界的核心问题——生存境遇发生的变化不如全国发达地域大,这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但在乡土叙事里对乡土世界生存现状的关怀却有增无减。大部分乡土叙事将视角对准传统封闭、贫穷落后的乡村,现代文明和社会转型并未影响到他们贫穷、落后、封闭的生存境遇。如安庆作家李光南的《水水》,小说选取皖水边的一个小镇里水水妈妈和水水母女二人的悲凉命运为叙事对象。水水妈妈被贩皮货的“负心汉”夺取了贞操,怀了水水后嫁给了水旺。后水旺醉酒后跌入河中死了,无奈之下水水妈妈做起了皮肉交易,水水也在无意间被糟蹋并开始了这种生活。伍先飞的《桃花》以江南大山镇妖塘打捞大逆不道、辱没族风被沉塘的桃花姑娘尸体为起点,终点是没有打捞到桃花的尸体。以倒叙、插叙等方式,对故事作了补充,对以七爷为代表的封建守旧势力的专横跋扈、因循守旧作了赤裸裸的揭示。戴玉的《新嫁娘》叙述了新媳妇玉英嫁人的过程,以及最终被捉弄致死的悲剧结局。在这类小说中,作者以“零度介入”的态度叙事,将乡土世界的传统封闭、贫穷落后彻底暴露出来,通过对负面境遇的揭示达到实现人文关怀的目的。
其次,关注乡土世界矛盾的复杂性。乡土世界并不只是恬静、诗意的栖居地,各类矛盾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乡土世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滋生了新问题、出现了新矛盾,乡土叙事关注当下、关怀乡土,须聚焦各类社会矛盾问题,并表达出相对理性的叙事立场。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讲述了皖南山区一个小村庄发生的故事,是法制与人情纠葛的故事。“执拗”的女主人公何碧秋在面对被侵权时,运用法律的武器来讨回尊严,要“讨个说法”。雨瑞的《十品官》讲述了新任村支书朱有国上任以来的种种经历:农民卖粮难,村民纠纷,接待上级检查,计划生育,农民负担重等,将乡土世界的复杂性进行了原生态描绘。需要指出的是,叙事立场不是阶级站位,大多数安徽乡土叙事保持了较为客观的叙事态度,而关注乡土矛盾与问题,关怀乡土社会主体,着力构建新型乡土社会关系,则是共同的叙事立场。
再次,对乡土人物的生存困境作深刻描绘。生存是乡土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处在转型期的安徽乡土世界主体经受着诸多生存困境的考验,面临着种种生存机遇的抉择,考验与抉择充斥着对生存欲的渴望,伴随着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生存焦虑。许春樵的“季节三部曲”《季节的景象》中叙写荷子女性意识的觉醒,对爱情的渴望以及自身发展要求,在乡土世界的转型过程中,她作了走向南方的艰难选择,尽管不知选择的结果如何。《季节的情感》中,塑造了一位高考落榜生形象——秋槐,面对家庭环境,迫于生存压力,遭遇现实爱情挫折,他毅然选择外出,通过烧窑挣钱,以此解决生存压力——为父辈争光,抹平兄弟的愤怒眼神,建立婚姻家庭。然而,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当秋槐终于带着血汗钱回家彰显自身价值时,却意外得到了素子已嫁人三个月的消息。《季节的背影》中乡村小学教师汪先生,作为一个乡土知识分子,肩负着教书育人的责任,面对不被理解的困惑,在贫病交加的状态中不放弃对孩子们的教育,最后落水而死。三部小说在反思与反省的疼痛中寻找生存出路,充满淡淡的忧伤色彩。
3.2 对待两种文明的辩证态度
有相当一部分安徽乡土小说,对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遭遇时的心理困境作了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既给乡土世界带来正能量,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乡土世界面对现代文明时,其态度既没有一味拒绝,也没有全盘跟风,而是选择了较为辩证的叙事态度。
一方面,对现代文明持质疑态度。现代与传统文明遭遇时,现代文明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但乡土叙事却对此持质疑态度。如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执拗”的女主人公何碧秋在面对被侵权时,运用法律武器来讨回尊严,要“讨个说法”。法制是现代文明的表征,当何碧秋试图摆脱传统习俗的约束,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时,却在“乡村情感”面前失灵了,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小说在法制与人情面前没有作出最终选择,而是留下了疑问。汪海潮的《古老的黄颜色——老人和大江的故事》,讲述了老人与孙子固守、保护长江中的家园——墩子的故事,老人在对现代文明——洋船的拒斥中坚守着传统家园,并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另一方面,对传统文明作理性审视。在很大意义上,乡土世界是生存家园的象征,具有诗性特征,但90年代的安徽乡土叙事却以较为审慎的态度作理性审视。如丁振川的《王婆婆》讲述了清河庄王婆婆的几则故事。王婆婆具有几个特点:一是有“福”,家住六间大瓦房,两个儿子都是所谓的“大学生”、国家干部;二是病态虚荣,经常编造假话让别人崇拜自己;三是对新一任生产队长张黑驴有怨气,因张黑驴不似前任队长那般崇拜她。在王婆婆的眼里,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大于一切,且必须凌驾于他人之上,传统的等级观念极强。面对乡土社会转型,以王婆婆为代表的乡土性格已落后,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传统乡土世界的不足在转型过程中日渐凸显出来。
3.3 乡土人物的“去英雄化”
与80年的乡土叙事相比,90年代的安徽乡土叙事中没有了英雄人物和悲壮情怀,只有为生计挣扎和追求欲望的芸芸众生,乡土人格进入“去英雄化”阶段。《阴阳关的阴阳梦》中的杨里仪、《骚乱》中的柏叶、《走入枫香地》的曾枫生,淮北平原的“杂耍班子”“蚂蚁湾”的少年……他们虽有对乡土的执著,对尊严和正义的渴望,但是“乡土小说的人物不再是时代精神的凝聚者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者,他们是卡里斯玛典型的终结,不再是一个一呼百应的神人”[8]。与80年代《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慧眼》中的于游水、《露水鸳鸯》中的袁登山等相比,90年代的乡土人格似乎逊色许多,但更加接近乡土现实,具有原生态的真实感。当个体自我意识不断强化,对个人生存空间和主体性的关怀成为主流,那么“去英雄化”就是安徽乡土小说叙事立场的必然选择。
这个时期乡土人格的叙事呈现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乡土性格的多元化和“去英雄化”特征。在人物类型方面,不同阶层人物均可成为中心人物,普通人物成为乡土叙事主角,如各类人物传记小说;在人物品性上,同一主体兼具多元品格,个性品性取缔类化性格,这些都成为乡土叙事的自觉追求。二是人格形象不完全借助矛盾的出现和解决来凸显。由于叙事的生活化、写实化,乡土叙事不再具有社会发展模式的论证效应,以及矛盾冲突的偶然性和人物关系的多维性。90年代安徽乡土叙事不再像启蒙叙事中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是由主流意识形态视角转化为文化学、民俗学、心理学等视角,人格形象不全借助于矛盾的出现和解决来凸显。如许辉的“淮北平原”系列小说,苏北的“蚂蚁湾”系列小说,以及皖西作家群的地域叙事等,在看似节奏舒缓的叙事中塑造原生态的人物形象。
3.4 生存家园的诗性回归与终极思索
乡土世界的一个重要参照是工业文明,在二元并立中乡土叙事方能彰显自身特色。作为经济社会并不发达的90年代安徽,乡土叙事一方面是对抗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彰显文学功用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凸显地域文化特色的主观要求。赫姆林·加兰曾经说过,“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9]。作为叙事立场转型的重要向度,90年代的安徽乡土叙事注重以地域经验为基础,抒写地域文化景观,探索叙事美学特征,追忆并构建理想自足的乡土世界。但又力图通过对生存家园的哲学思索,达到超越两种文明的终极思索。
一是对地域景观的诗意抒写。丁帆通过对乡土小说世界性发展轮廓的勾勒和中国乡土小说的概念阈定与演变流程的梳理,提出了乡土小说的现代审美特征,即以“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作为规范的“三画四彩”,将地域性、差异性放在乡土小说的核心位置。作为特定地域文学形态的安徽乡土小说具有天然的地域性和差异性,且一直如此,90年代也不例外。综观90年代的安徽乡土叙事,对地域景观的诗意抒写较之以往有相当大的增加。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追忆性的地域经验抒写,如苏北的“蚁民”系列小说,不动声色地对乡土世界作全景式的美学观察,如许辉的淮北平原乡土小说。他们对“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的抒写,不是要揭示深刻的社会学命题,而是试图追忆、还原并构建乡土世界的自足形态,不是以故事情节取胜,而是以平淡、纯朴为叙事追求。正如有论者评论许辉的乡土小说:“许辉从来都没有回避过乡村世界的清苦,但他也从来不会在文本中预先设定任何的价值导向,作为知识分子的许辉,在文本中是全然隐去的,他从不修饰,更不评判,只是原原本本地再现乡村生活,让其鸡犬相闻,让其琐碎平淡,而生命,自然会在这休养生息中寻找出路。”[10]这是对乡土叙事美学特征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具有积极的创新意义和地域文化价值。
二是对生存家园的终极思索。就叙事视域而言,叙事立场转型的前三个向度,主要聚焦现实乡土、城市乡土和历史乡土三个层面,或关注乡土当下现实,或反思乡土主体进城后的生存状态,或解构传统历史叙事方法和历史观念。与其他三个向度不同,持第四个向度的安徽乡土叙事,看似平淡无奇却隐藏深意,叙事文本或超越时空界限,注重传达作者的一种理想与情绪,着意营造一种意境和情调。或通过展现乡土民俗风物与历史文化,或聚焦乡土主体的生存状态,对生存家园作终极思索。如《碑》中,妻女与“我”阴阳相隔,“家”已不复存在,“我”被悲哀压抑得近乎绝望。洗碑的匠人王麻子虽不懂“我”的痛楚,他只是无意识地在“我”面前展示他的生活:他“像是不知,也像是不觉,木呆呆地坐在亘古的石头旁边,一锤一錾,洗了几十年,也还是不急不躁”,正是他的生活与态度,最终使“我”释然与解脱。在诸多地域经验抒写中,对生存家园的终极探索凝聚着乡土叙事的立场与动机,成为叙事立场转型后的重要向度之一。因为以地域经验为基础,超越既定的精神文化意义,达到对终极意义与价值的思考,这便是乡土叙事保持并彰显自身价值的重要路径。因此,尽管90年代的安徽乡土叙事并未能指出生存的终极意义所在,却还是始终秉持着对终极意义的思索,提供了终极探索的可能性,为建构乡土叙事立场提供了一种参考。
4 结 论
由于20世纪90年代时代转型的影响,安徽的乡土叙事在反思中确定叙事立场,在实践中找准叙事立足点,在边缘处抒写地域经验,并呈现为四个向度的叙事选择。应该说,90年代的安徽乡土小说实现了叙事立场的成功转型,逐步构建起了多元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对特定地域经验的抒写,为新世纪安徽乡土叙事形成稳态结构奠定了基础。实现转型有必要,然而成功转型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转型意识有高有低,叙事水平参差不齐,地域文化挖掘不深,与全国性的乡土叙事存有差距,以及或多或少依附西方叙事理论等。这些都应成为总结90年代以来安徽乡土叙事时必须直面的问题,并以此作进一步反思、探索,因为在相当长时期内,乡土叙事都将是彰显地域创作特色和皖军创作实力的最好途径。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1
[2]许春樵.城里的月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93
[3]严云受.略论九十年代的“皖军”[J].清明,2000(6):185-190
[4]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72
[5]王达敏.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安徽小说[N].安徽日报,2003-02-21(C3).
[6]鲁彦周.鲁彦周小说自选集 [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2
[7]许玉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叙事立场的转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13-116
[8]周礼红.2O世纪9O年代乡土小说四种范型综论[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49-51
[9]加兰.破碎的偶像[C]//美国作家论文学.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4:84
[10]汪洋.尘世间的田园抒情:许辉论[J].江淮论坛,2009(5):168-173
(责任编辑:李力)
2015-08-10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文化视野下的90年代后安徽乡土小说叙事研究”(2011SQRW171)。
金大伟(1982-),安徽合肥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106
:A
:1673-2006(2015)12-0062-05
10.3969/j.issn.1673-2006.2015.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