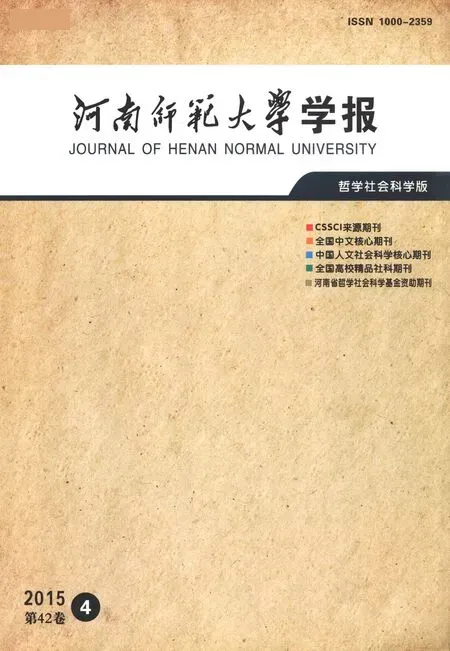道德教育神圣性的失落与回归
宋 晔,王佳佳
(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道德的产生蕴含在对超自然现象的崇拜之中,它是对“神”这个精神实体的信仰,因此道德活动无需论证便具有神圣特性。就其源初意义来看,道德由规范性与神圣性两方面共同构成,前者是外显特征,后者是精神内核,且原始道德主要依靠德育对象的虔敬心理来发挥其教化功能,也就是说,是神圣性在德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道德世俗化过程中,规范伦理大行其道,道德神圣性的一面逐渐失落,只留下了规范性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忽视其神圣特质对道德实践的精神作用,因为虔敬带来的神圣体验“会从内部强化进一步践行道德原则的动机”[1]。因此,不管对德育本身来说,还是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重塑道德教育神圣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信仰的道德意蕴
人生来便具有一种超越的本能冲动,信仰是满足这种超越性冲动的精神力量。它使人摆脱低层次的物质存在跃升为高层次的精神存在,使人从现实生活中获得救赎步入终极理想世界。因此信仰不仅代表主体对自身的超越,也代表了对现实的超脱,其超越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信仰使人类超越非理性到达理性。信仰对象的绝对化、神圣化使信仰本身具有非理性的特征,然而它之所以可以使人超越非理性到达理性则是因为信仰是理性认同的非理性表达,“是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力与无限完善的价值追求的界限所在”[2]。因为“信仰什么”是信仰主体经过理性思考所作出的理性抉择,是对未来人生的理想承诺。信仰作为人的精神航标,决定了人是否能够到达理性的彼岸,没有信仰,人生便迷失方向,沦陷于各种非理性的诱惑而无法自拔,更无法培养主体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说,信仰作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完美张力,对于道德生活的实现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其次,信仰使人类超越个体性到达群体性。存在主义认为,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中来的,他需要被拯救但又孤立无援,因此,作为个体人不能脱离社会和群体而活。但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是被“单子化”的个体,其所组成的是没有凝聚力的“碎片化”的社会,缺乏共同的精神基础与价值认同使社会失去了整合的可能性,而信仰的精神共有这一统摄性特质则能够为社会整合提供一个契机,它能超越独立的个体形成共有的精神世界,使人摆脱原子状态从而变成有机共生的群体,由单个的物质存在转化为群体的精神存在。西方信仰领域的历史流变也证实了“信仰生活本身作为一种维持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共享价值理想,仍保持着它自身的内在连续性和外在有效性”[2]。另外,现实合理的信仰也注定是要超越个体达至群体,它不会只是个人的追求,同样会成为社会群体性的诉求,这种群体性的共有精神以信仰的形式制约着其中每一个个体的道德生活。
再次,信仰使人类超越有限性到达无限性。当人于困境中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并产生超越的渴求时,信仰产生了。人是有限性的存在,会死亡,不完美,正因为如此,人才成为超越自身有限性的无限存在,追寻永生与真善美。也就是说,世界在给了人类“有限”这个答案的同时,也为人类敞开了一片无限的境域。从有限到无限需要人用道德的方式穿行其中,毕竟科学理性的发展壮大不足以满足人类的超越性需求,更无力引领人类步入“道德的目的王国”,而信仰则能够化解人类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与人类追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使两者获得统一。她作为一种终极关怀,解救人类于有限,代表一种“极值性”的皈依之所,从而铸造道德的人生。
总之,道德完善需要信仰,这是道德的本性反映,人作为一种灵性存在,信仰是人的本质需求。心理学家荣格说需要信仰是人类生命的延续性,这种需要从记忆难以企及的蛮荒时代就已经存在。而神圣感这种在人类悠久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沉淀出来的原始情感,与信仰天然契合,因为“信仰的基本内涵就是神圣性的建构,信仰的核心,在于对什么是真正的‘神圣’的认定”。她“不仅表达了神圣事物的性质,也表达了赋予神圣事物的品性和力量,表达了神圣事物之间或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之间的关系”[3]。总之,道德信仰是道德神圣性的表征,道德神圣性统摄着整个道德生活的最高意识形态,遗憾的是,道德神圣性的一面失落了,徒留下道德规范。
二、道德教育神圣性的缺失
21世纪以来,经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精神的贫瘠、道德的滑坡。当今社会,各种道德问题频发,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没有很好地实现它对个人、社会的承诺,反映了道德教育生命力的枯竭,神圣性的消解。信仰是神圣性的内核,神圣性源于信仰,学者檀传宝指出,“世界范围内的道德教育危机的实质在于深层次的精神危机(信仰危机)”[1]。没有信仰就无法谈道德,信仰的消弭给道德教育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我们不禁要问:道德教育神圣性何以没落?我们认为这与以下现代文化意识中的几种趋势很有干系。
(一)泛科学观的独大
科学成为驱散人类面对“未知”时恐惧敬畏心理的有效工具,是人类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但泛科学观却成为切断信仰来源的工具,因为未知正是信仰与神圣的来源之一,泛科学观使人们在知识层面拥有一种近乎狂妄的乐观与自信,它几乎霸占了现代人的整个精神信仰空间,这种偏狭的意识把道德、信仰、终极追求等价值系统排挤到了边缘地带,使道德教育再也没有神圣性可言;并且泛科学观在精神和道德层面培育出一种极端的怀疑主义和武断的取消主义,进而滋生了道德上的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扼杀了道德信仰,也扑灭了德育的神圣之火,因为,如果道德是自我的而非普世的,是多变的而非稳定的,那么,道德的神圣性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另外,这些思想意识的散布助长学校教育的“去道德化”与知识崇拜,遮蔽了教育的本体性功能与价值诉求,这正是当今社会学校德育困境的根源之一,它不仅削弱了学校德育意识,更加速了道德教育神圣性的消解,因此才让人感到“今天的中国,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4]。
(二)功利主义的横行
功利主义是现代社会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意识,并且已经成了现代文化的一种垄断价值。功利思想的泛滥侵蚀了群体凝聚力,阻碍人们建立共同的精神基础与价值认同,动摇了德育神圣性的根基。因为“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4]。功利成为否定信仰、结构道德神圣性的粉碎机,把我们变成一群“精致利己主义”者,笼罩在功利主义下的人际关系也逐渐扭曲变质,以情为核心的人际关系渐渐被以利为核心的市场关系所吞没,人类的有机社群变成了物化的社会,道德信仰没有生长的空间。这种环境下的道德教育只会成为利益的牺牲品,丧失其神圣性特质。如此德育培育出的学生从未被寄予这样一种期望,即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而把成就看做最高追求,但个人全面成长不应该也不能脱离德育活动的参与,因为“一个卓越人物的道德品质,可能比单纯的智力成就具有更大的意义”[5]。
(三)虚无主义的弥散
泛科学观和功利主义常伴生出人类精神的苦闷和心理的创伤,从而汇聚成现代社会的另一趋势——虚无主义。这直接昭示了人类精神信仰的空乏,不相信生命和宇宙有一个终极的意义,认为人的存活也无需追求终极价值。追寻终极意义这种观念曾为世界各高等文化传统所共有,而随着现代化的蓬勃发展,精神信仰正在逐渐消散。这种潜滋暗长的虚无感给现代德育带来的危机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信仰不仅与精神和心理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发展、学校的道德教育也都是很重要的,它直接或间接地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虚无主义的散播,不单在学校场域中营造一种空洞无力的道德空间、一种软弱的道德话语氛围,更重要的是在学生和教师的精神心理上抹上一层阴影,造成道德感的枯竭,道德教育只剩下规则的灌输,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内在价值和鲜活的生命力源泉,至于德育神圣性的重塑更是成为毫无意义的举动,虚无主义慢慢地却有力地掏空了德育的精神根基,使道德教育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
三、道德教育神圣性的回归
社会道德状况令人担忧,如何让德育回归原初尊严已迫在眉睫。如果说中国传统道德到现代道德是一个“脱圣还俗”的过程,那么回归道德教育神圣性必然要求助于传统德育,走“脱俗入圣”的“复古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可说是恢复德育神圣性的良方,它能够实现道德教育的精神内核的“返祖”,是建立道德信仰体系、回归道德教育神圣性的有效途径。
(一)德育神圣性何以必要
首先,个体健康成长需要道德教育神圣性的回归。全面健康的人决不能仅满足于遵守规则,停留于底线道德,更需要终极价值的引领去完善自身。德育的神圣性不仅是个体执行道德准则最可靠的内在力量,也是培育道德信仰的前提条件。正如梁启超所说:“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显然,个体健康成长既需要外在的行为规范的制约,也需要德育神圣性的观照,一旦道德的信仰者服从了道德神圣性所特有的权威,他们就会按照德育神圣性所下达的道德命令去生活。这也印证了康德的话:“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如果要维护道德的尊严,获得幸福,就必须有一个神并且信仰他。”[6]
其次,社会和谐发展呼唤道德教育神圣性的回归。现实生活中“德福不一”的现象表面上看是降低了人们对道德的信心,深入看来则是动摇了道德信仰的根基。德福分裂的现实状况内在要求回归道德及德育的神圣性,需要道德的神圣气质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进行道德审核,保证道德生活的正常进行,唤起个体的道德责任感,人应该有做了不义之事会受到惩罚的恐惧心理,对于道德要心存敬畏与信仰,更要求重立德育威严,认识到德育神圣性回归的重要性。这要求教师要注重道德信仰的培养,尊重信仰的幼芽,认识到单纯讲授理性知识并不是教育的全部,因为“儿童身心中必然有灵性的精神,但是,这个种子如果置之不顾,就会全部枯掉”[7]161。
最后,学校德育的良性发展也要求德育神圣性的回归。所谓德才兼备,德育为先,学校要培养这样的人,必须要认识到科学理性与道德信仰需建立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并非互相排斥的,重塑学校德育神圣性不仅有助于学生科学理性的发展,也能使学生的道德愈加饱满。越是科技发达的社会越是要求道德能够与其同步,因此学校德育必须对社会要求有积极的回应,为社会培养道德与能力均衡发展的人,教育不能抛开伦理道德而只关注科学知识,因为“科学也包含着信仰……两者不是相反的”[7]98。只有恢复了神圣性的学校道德教育才是健康的学校德育,才能进一步能促进个体成长、匡正社会秩序。
因此,借助传统德育资源回归德育神圣性是必要的,是个体发展、社会现实、学校德育的呼唤,道德的“圣化”,道德教育的“圣化”是其本体功能、社会功能及其价值合理实现的最高保证。
(二)传统资源何以能有所作为
首先,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谐与平衡代表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它注重人与外界的调和融通的关系。作为儒家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它特别注重事物发展整体的均衡,不让任何一个方面脱离整体作孤立的、极端的发展。这一观念必然会渗透到德育传统中去,对整个德育活动产生统摄性的思维观照,反映到德育活动中去,就要求现代学校教育打破德育与智育失衡的局面,挽回德育应有的尊严,提升学校德育应有的神圣地位。
其次,对泛科学观引发的道德相对主义,我国传统资源也有其应对之法。儒家传统文化体系坚信有终极价值,并且相信它所秉承的终极价值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可以说传统德育的神圣性正是源于这种强大的价值魄力及其稳定性。虽说按照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不同的文化孕育不同的道德价值,共同而永恒的价值不可能存在,但普世价值也不能因此被全盘推翻,因为虽然不同的文化孕育的行为规则各不相同,“但若从行为规则背后所依据的基本道德原则去看,则至少高等文化之间,甚多精神相遇之处”[8]133。比如,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观念不仅能够超越时间鸿沟,也能超越空间界限,把它放在现代社会或任一高等文化中都会得到认可,由此看来,儒家的超越伦理对于道德相对主义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反观浸润在道德相对主义的现代道德,时刻迎合着社会与文化的变革,这种弹性逐渐瓦解了德育权威,消磨了德育神圣性。从这个角度说,传统的超越伦理有利于巩固道德权威、维护德育的神圣性。
再次,面对德育神圣性的遗失,我们必须打破个人功利主义的藩篱。面对由“群体”到“个体”的价值取向的嬗变,传统文化可资借鉴的正是现代社会缺失的“社群意识”。“人不能,也不应该离开社会而生活”[8]131。传统社群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内心关切所维系的情感聚合体,并逐步扩大到社群,最终以包容全人类为目标,这奠定了传统德育精神共有的基础。我国传统德育“家庭化”的价值取向使各种利益聚焦在群体上,那时的人是群体性的,他承担着对家族、社会和国家的承诺,肩负着神圣的道德使命感和责任感。彼时,道德神圣不可侵犯。反观在个人功利主义笼罩下的现代德育,却一直在把人推向孤独疏离的境地,显然,传统资源能够把单子化的个人连接起来,“建构成一个共享的、建制型的价值体系,以表达它的信仰理念、规范信众们的行动逻辑”[15],为群体的精神认同和共有信仰筑基,为德育神圣性的回归提供条件。
最后,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很好地解决现代世俗社会精神性空虚的问题。有人把儒家称为儒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学价值系统具有宗教性,由于宗教性,儒家的基本价值都关涉精神信念,这表明精神信念并非只存在于“有神信仰”中,因此,儒家思想传统的特殊意义不言而喻,因为在愈发世俗化的今天,“有神信仰”的根基已然不稳,而儒家思想则显示精神信念至少可以以人文传统为载体,这不失为一种解决人类精神虚无的可能途径。另外,以性善论为基调的传统德育由于其宗教性影响,除了关注礼俗规范外,更加关注超越性精神理想及其实现方法,对于人性、道德有更高层次的追求。现代德育由于缺乏宗教性并以性恶论为基调,则很少考虑精神信仰、终极理想等问题,其关注点仅在于道德知识规范的传授,规则体系的建构,显然,现代德育缺乏深层次的价值皈依,德育神圣性没有凭依,庆幸的是,这似乎正在传统文化的料理范围之内。
针对现代社会上败坏德育神圣性的几种主流文化意识,传统文化资源都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一成不变地对传统思想进行复制粘贴,对现代文化进行盲目的解构与颠覆。但我们深信传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向,让思维跳出现代化观点的局限,真正发挥传统智慧对现代德育补偏救弊的功能,实现传统德育和现代德育的合理对接,使德育重新焕发出她本有的神圣性光辉。
[1]檀传宝.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兼论学校德育的相关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2]万俊人.信仰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及其文化解释[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3]李向平.两种信仰概念及其权力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4]卢新宁.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代序)[J].国家人文历史,2014(4).
[5]刁培萼.教育文化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220.
[6]文聘元.西方哲学的故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433-434.
[7]小原国芳.小原国芳论著选(上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8]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